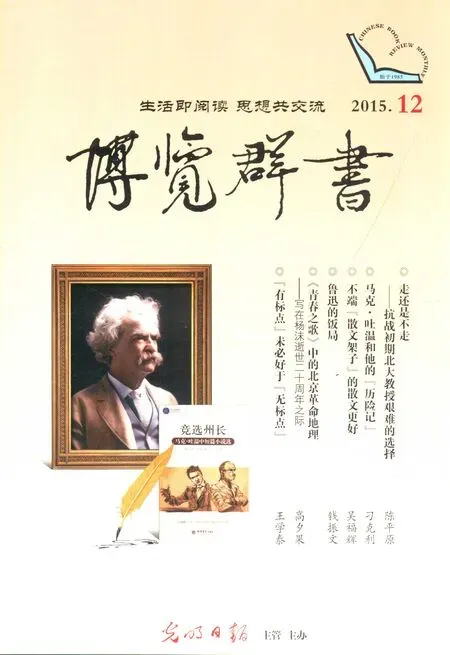從文學地理意義上看《拾稻穗》
梁東方
即使是現在上了年紀的北方人,大概也少有拾稻穗的記憶。人們說起來當時學農支農也無非是一大早就出發,排著隊去撿麥穗。無他,北方少水,更少種水稻的傳統。少是少,但是那時候還是比現在要多。現在的北方,無河不干,而那時候人口少,工業不發達,建筑更不多,還是有不少自然水系濕地能保持大致上的常流水、常有水的狀態的。這樣在有近水之便的地方,便有可能種植水稻。
北京及其周邊的廣大平原地區,在西部的太行山和北部的燕山高地合圍之下,古代曾經是水系縱橫之地,自然河流與人工渠道將平原連接成多有水漬的濕潤地帶,種植水稻的歷史有據可查者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及至明清民國更是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水稻種植傳統。著名的房山石窩米、涿州貢米、漁陽地區的稻產等都是有口皆碑的好大米。
我記得,上世紀70年代中期曾經跟著大人到北京西部的四季青公社,片斷的印象里就有大面積的稻田,稻田里特有的香氣彌漫開來,稻田邊的老柳樹排撻而去的景象至今歷歷在目。沒有想到,那時候以及更早的時候,在京南,順著南北中軸線延伸下去,在大白樓地方也曾經有過稻田。這就是當年的彩色連環畫《拾稻穗》的故事背景。
《拾稻穗》講的是當時大白樓公社的隊長王國福的故事。一個紅小兵在收割以后的稻田里撿了一把稻穗,想拿回家去喂雞,在王國福教導之下紅小兵把那稻穗還給了隔壁公社,獲得了人家的表揚。
王國福的教育方式當然是現身說法,新舊社會對比,說舊社會吃不上飯,還被壞人欺負,現在一切都好了,更要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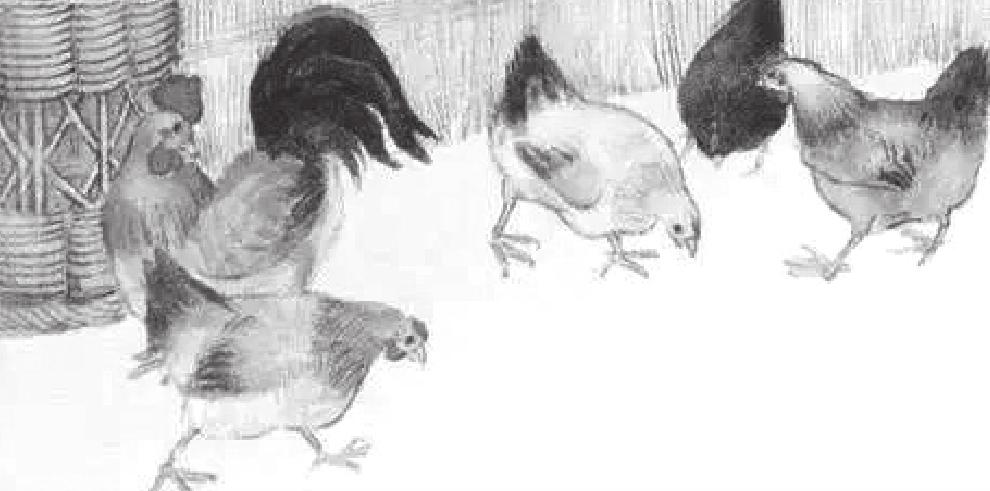
其實即使與12歲的時候從山東逃荒而來的王國福的過去相比,當時的大白樓乃至全國人民的生存狀態,雖然已經有了不小的改觀,但是普遍來說還是沒有解決溫飽。否則在物質極大豐富之后,是不會有人注意到一小把稻穗的問題的。
當然,在北方,在京畿,雖然有稻子的種植傳統,但是能吃到大米的也往往只是達官貴人甚至是朝廷中的皇室;清朝遍布京城周圍的官莊稻米種植就是為了直供皇家和旗人貴族而設。延續下來到了打倒了封建王朝之后的幾十年時間里,雖然這種在享用糧食上的明確的硬性等級劃分沒有了,但是客觀壁壘也還是存在。人多米少,即使有非農業戶口一年的大米供應也不過一斤半斤,且都是南方的三季稻,斷然不會是北方生長期很長的優質稻米。
這樣看來這位紅小兵撿了稻穗去喂雞的行為就非常奢侈了,其實現在看來,主要還是囿于孩子氣的物我同一,將同理心擴及她自己視如兄弟姐妹甚至是孩子的母雞。當然,客觀上這位紅小兵拿回家去喂雞的行為里,除了浪費糧食,還有一種當時來說很不正確的自私自利的問題,也就是那著名的私字一閃念問題。公家的糧食,即使是遺撒到了地里的稻穗也依舊是屬于公家的,不能歸為己有,盡管已經有不撿回來就有風吹日曬雨淋之后的發芽發霉的損壞之虞,但是撿回來也還是要歸公。
從宣傳的角度上說,王國福作為一個被全國主要媒體樹立起來的典型,挖掘其生前的事跡的時候,自然得注意到他在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的表現。盡管他更主要的表現是堅決走集體化道路,為全村其他村民都蓋上新房以后自己依舊住著低矮破爛的“長工屋”。這些內容在另外一本更為正式也更為全面地宣傳其事跡,甚至有很多真實的照片插頁的連環畫《無產階級優秀戰士王國福》里,都有詳細介紹。
王國福的故事是后來著名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的原型。浩然把王國福寫成了高大泉,把他寫得充滿了時代先鋒感,那個時代的先鋒感。實際上王國福作為一個逃難而來的山東漢子更多的還是基于自己艱苦生活的痛苦經驗而緊隨上級指示并且積極響應號召,他個人品性中樸素的愛惜糧食、愛惜萬物的閃光點是當年絕大多數老百姓共同的行為道德規范,而他先人后己的公心則是個人品質上的熠熠生輝之處。他從12歲逃荒到大白樓到47歲去世,用自己短暫的一生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從這個意義上說,《拾稻穗》倒是在一件小事之間將王國福的品質表現了出來。當然這本連環畫也不是沒有問題。比如,畫家應該是沒有進行實地考察,或者考察不夠詳盡,沒有意識到當地物產的順序:收水稻的時候哪里還會有向日葵?向日葵每年盛夏成熟,而北方的水稻成熟都在晚秋時節。兩種作物不會這樣一個成熟一個盛開地并置。這種在整冊連環畫里安排大量的盛開的向日葵背景的畫法,使作品喪失了一部分寫實的價值,變得是僅僅出于色彩與造型的美觀考慮了。
連環畫已經是古董,是過去時的東西,但是有些人類共同性的東西卻近于永恒,現在乃至未來依然有效,依然可以感動人。愛惜物產,敬畏天地,不暴殄天物,有公心有愛心,即便在諸多概念之下,這些本質性的東西是永遠有價值的。
今天的大白樓,已經沒有了過去鄉村的痕跡,變成了千城一面的鋼筋水泥建筑叢林。但是據說還是不斷有慕名而至的走訪者,他們訪得的總是這樣的結果:沒有紀念館,也沒有專門賣《金光大道》的地方,長工屋已拆,稻田已經沒有了,只剩下一座墓碑。歷史給大白樓留下了王國福,但是大白樓作為文學地理學的原型故事發生之地,當地卻未加刻意地保護和利用。于是連環畫就在不經意中成為過去風貌的特殊保存方式。前提是畫家曾經實地采風,在相當程度上還原了當時當地的風貌。在大白樓的這片向西曾經可以望見逶迤的太行山脈的京南平原上,地理風貌是一馬平川,而物產卻又有著本地的特征。與柳青的《創業史》完全忠實于神禾塬下可以遙望秦嶺的皇甫村的地形地貌以及物產的寫法不同,稻田在浩然據此原型寫成的長篇小說《艷陽天》里好像沒有怎么提及,連環畫《拾稻穗》因為以之為主題,所以成了畫面的主角。這就多少記錄了當時當地的一項物產,以及圍繞這項物產所進行的生產生活活動,成為一種堪稱珍貴的記錄。
大白樓和王國福的故事曾經發生過,曾經被包括長篇小說《金光大道》、單弦《王國福家住大白樓》以及這冊小小的連環畫《拾麥穗》在內的諸多公共話語系統的文本講述過,這就是人類歷史豐富性在特殊地域中的表現,是可資借鑒與紀念的文化積累,也是今天人們生活的根系所在。
(作者系花山文藝出版社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