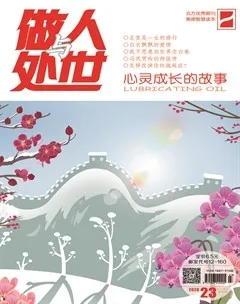“閏土”后代今安在?
長弓

讀過魯迅的散文《故鄉》,人們腦海中大多會留存這樣一幅畫面: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地刺去。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那個少年名叫“閏土”。
出身浙江省紹興市上虞縣杜浦村的章閏水,就是“閏土”的原型。他比魯迅長2歲。章閏水的父親一直給周家做短工,章閏水的母親更是魯迅的奶娘。14歲那年,章閏水被父親帶到周家,幫著看管祭器,因此認識了12歲的魯迅。兩個活潑潑的孩子一起捕鳥看瓜,結下深厚的友誼。
但和《故鄉》里,魯迅和閏土“從此沒有再見面”不同,一直到青年時代時,章閏水與魯迅依然有聯系。1900年,正在南京礦路學堂讀書的魯迅,在寒假里與章閏水一道在紹興城游玩,兩個人20歲出頭,“邊走邊談,漫步街頭,觀賞鬧市”,度過了一段難忘的青春時光。但災難卻在3年后降臨在章閏水身上。1903年,章閏水的父親去世,24歲的他從此撐起了整個家,守著6畝薄沙地生活。然后在歲月的摧殘下,變成了《故鄉》里,那“中年閏土”重逢“迅哥”時,“渾身瑟索著”“加上了很深的皺紋”“態度終于恭敬起來了”的樣子,讓多少讀者唏噓。
而在真實境況中,魯迅與“中年閏土”的這次重逢,發生在1919年12月他回家接母親北上時,當時章閏水帶著17歲的兒子啟生(《故鄉》里閏土兒子水生的原型)過來幫忙搬運行李。等到魯迅一家人啟程時,章閏水也領著女兒章阿花(《故鄉》里閏土5歲女兒的原型)前來送行,他帶著女兒站在魯迅故居前的張馬橋上,目送魯迅的船消失在視線里,許久才離開。這就是魯迅與章閏水的最后一面。也就是在這一次重逢時,魯迅記憶中那個“教魯迅捕鳥,講海邊故事的少年”,變成了眼前“衰老、陰沉、麻木、卑屈的人”。如此強烈的震撼,成了魯迅創作小說《故鄉》的動力。直到今天也有不少人在追問:“閏土為什么會變成這樣?”那得看看在與魯迅“重逢”前后,章閏水到底經歷了什么。
比起魯迅小說里“捕鳥撈魚看瓜”樣樣在行的閏土來,真實的章閏水也不差,以章閏水女兒章阿花的回憶,章閏水“鋤地捕魚,挑擔撐船樣樣做”,一年到頭不見休息,可即使這樣,卻還是“吃不飽,穿不暖,養活不了我們一家六個小孩”。1934年浙江大旱,章閏水被迫賣掉了6畝薄沙地,成了更苦的佃農。兩年后貧病交加的他背上“生癰”卻無錢醫治,病故于1936年9月。
這位勤勞憨厚的農民,去世前的情景,留下了許多讓人動容的時刻。“生癰”的他,每天要靠女兒章阿花為他擦膿血,可不管多痛,他都咬著牙不流一滴淚。臨終前的他,依然還在念著萬里之外的魯迅,叮囑家人說:“想辦法給周先生帶一點干青豆去,他是一個好人。”
同樣讓人心痛的,是《故鄉》里水生的原型、章閏水的長子啟生的人生。那個小說里“黃瘦些”“害羞”的少年,和他父親一樣,是個種地打獵捕魚撐船樣樣在行的好手,而且擅長“吹笛子”“敲鼓板”“拉胡琴”,每次村里的迎神賽會活動,他都是挑大梁的“大敲會”。可這樣聰明能干的小伙子,依然不能擺脫貧困,在1940年的霍亂瘟疫里染病身亡,年僅38歲。
而閏土的小女兒章阿花,即《故鄉》里那位“管船只”的“五歲的女兒”,則是嫁到了離杜浦村10里的中村毛家,苦熬過了多災多難的民國時代,過上了平靜幸福的生活。1975年,66歲的章阿花兒孫滿堂。她在接受紹興縣文化館采訪時,詳細描述了章閏水家的命運,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記述。也正是同一年,章閏水的三兒子章長明走入人們視線,他那年60歲,以章阿花的笑談說:“仍十分硬朗,越活越年輕呢。”
在章閏水后人里,最值得一說的,當屬章閏水的孫子章貴(章啟生的兒子),章貴通過努力學習,成為一名知名的現代文學研究者,還一度擔任了浙江紹興魯迅文學紀念館的副館長,如此成就,章閏水若有知,當可告慰。章貴說“每次來紹興,我都要見見魯迅的兒子”。二人的友情珍貴無比,章貴和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很合得來,他們都是文人,都了解魯迅。章貴認為自己十分幸運,生活在一個開放的時代,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過上想要的生活,自己的兒女也都在不同的領域做得非常優秀,相比章閏水的年代,章貴少了束縛和貧苦,在新的時代,他研究文學,并且成了魯迅研究專家,有了新的眼界和格局。
閏土和魯迅消失的友情,并不妨礙他們的后代繼續保持友情,如果章貴有著和成年閏土同樣的思想,也許他不會有新的成就,也沒有機會和周海嬰成為朋友。
(責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