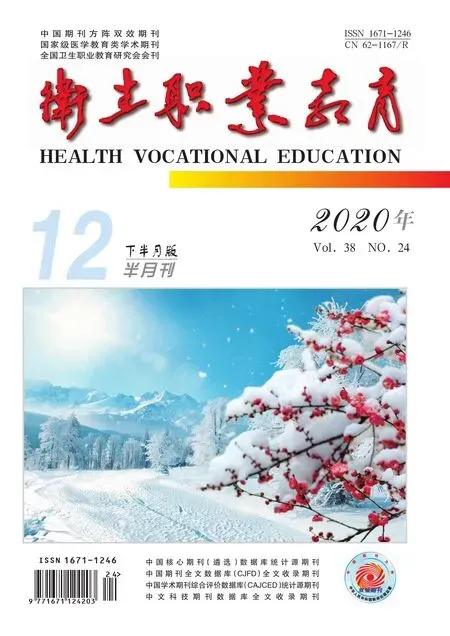微文化場域下大學生話語方式對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及對策
賈彩彩,王向珍
(首都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69)
隨著互聯網快速發展,以微信、微博、微視頻為代表的自媒體廣泛盛行,孕育了較為獨特且復雜多變的微文化場域。大量網絡語言不斷涌現,增加了語言的多樣性,豐富了語言生態系統,但也對原有的話語體系及方式造成不小的沖擊。尤其對于被稱為“互聯網原住民”的當代大學生,受網絡話語方式的影響極大。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感染青年,就要運用青年喜愛并接受的話語和活動方式。這提示要及時把握大學生話語特點,轉變思想政治教育思路和方式。因此,如何認識、分析和應用微文化場域下的大學生話語方式,成為有效開展網絡思政教育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
1 微文化場域下大學生話語方式的特點
語言的動態變化可以說是社會發展的一面鏡子,社會的快速發展往往是語言不斷變化的根基。與“彩民”“草根”這些已被廣泛接受的新詞不同,大學生網絡話語方式更多體現在短時間內被頻繁使用的“網絡流行語”中。這些詞往往來源于熱門事件、流行影視劇或綜藝、游戲、貼吧等,通過微博、微信、直播軟件、短視頻軟件等形式得以迅速廣泛在大學生群體中傳播,并成為其現實生活中話語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對大學生流行語料的整理分析,大學生話語方式具有如下特點。
1.1 形式多樣化
當代大學生話語交流形式打破了傳統規范的語言文字,呈現出文本與符號、短視頻、音頻的混搭,以求更迅速更直接實現個人表達。現代社會生活的某種特殊情境,不滿足于僅使用傳統語言作為交際工具,常常借助于各種各樣的符號以代替語言,以便更直接、更有效、更迅速地傳達信息[1]。相較文字,多樣化、圖像化的網絡語言更能傳遞包含情緒在內的豐富信息,獲得大學生青睞。
在高校大學生群體,以微信、微博、貼吧、直播平臺等為代表的微文化場域中,表情符號和“表情包”已經成為最具代表性的網絡話語方式。根據騰訊發布的《2018微信年度數據報告》,2018年僅在微信平臺,每個月有10.82億用戶保持活躍,每天有450億次信息被發送。“捂臉哭”成為“00后”最愛的表情符號,各種新穎的自制表情包更被廣泛使用。表情包以其鮮活傳神的形象、直接迅速的情緒表達、生動幽默的內涵成為網絡話語的重要符號。用表情包進行交流和表達,已經成為大學生網絡話語中常見的話語行為,甚至形成一言不合就“斗圖”這一獨特的溝通方式。新媒體技術的不斷發展極大地豐富了大學生話語交流形式,呈現出更加多樣化的特點。
1.2 內涵情境化
借助互聯網的廣泛應用,部分網絡用語得以迅速傳播和廣泛應用,成為大學生喜聞樂見的流行語。這些流行語往往出自某些熱點事件和具體情境,因此從詞義上已經突破原有內涵,更加富于畫面感,代表了某一種特殊情境。如“真香定律”原本出自某真人秀節目中的場景,主要是因為特定的某個人一開始表現出不屑的拒絕態度,但下一秒又老老實實妥協。這一流行語的形成和使用都是一種情境的遷移,往往很難用簡單的語言完全表述清楚。但由于大學生在生活中普遍體驗過類似心態變化,因此用“誰也逃不開真香定律”即可生動概括這一感受。“吃瓜群眾”也因其生動的形象描繪,從某社會事件真實的圍觀群眾演變為代指網絡中對某一事件、話題進行關注、評論、轉發的人,其所延伸出的“吃瓜”也成為大學生在互聯網中常見形態的生動概括。
1.3 群體區隔化
大學生網絡話語方式是大學生以交際為目的話語行為,與現實生活和網絡信息獲取連接緊密。由于網絡用語高度凝練和符號化,要求對話雙方處于相同的語境,掌握共同的背景知識,才能理解網絡流行語的內涵,因此形成了較為封閉的語境和會話場。大學生樂于在生活和網絡中尋求群體的認同,在話語方式上也容易趨同。很多大學生耳熟能詳的流行語,由于在短期內迅速在群體中傳播,形成了相同語境,溝通沒有障礙,但對群體之外的人而言卻并不容易理解。如網絡流行語最常見的構詞形式——英語單詞首字母縮略、英漢詞語夾雜混用而產生的新詞語,“C 位”“pick”“打 call”“CP”等就很難讓很少接觸網絡、英文的中老年人接受,而另一些如“菊外人”“走花路”則讓不關注網絡選秀節目的人一頭霧水。理解和采用同樣的流行語則往往能夠迅速拉近雙方的距離,形成一定的群體認同感,反之則造成了交流的區隔。
1.4 更迭常態化
大學生所熱衷使用的網絡話語,因其成因和傳播渠道,詞義更迭、新詞層出,往往呈現出動態變化特征。首先詞義本身往往脫離最初語境,其內涵在傳播過程中動態變化。如“Skr”原是嘻哈、說唱中的一個重要術語,表示突然漂移或旋轉時橡膠輪子的聲音,后來作為英語俚語,用來表達興奮和幽默。而作為網絡流行語廣泛應用,則取中文諧音中“是個”“死個”“死磕”等不同意義,詞義隨著使用者的語境隨時發生變化。其次網絡流行語往往在短期內被頻繁使用,又很快被新生詞語所取代。根據流行網站統計規則,微博實時熱搜榜每1分鐘更新一次,百度搜索風云榜“實時熱點”榜單每1~2小時更新1次,微信熱詞榜按照24小時內的搜索量排序。這樣的信息更新速度,使得“重要的事情說3遍”“主要看氣質”“城會玩”等詞迅速被淘汰。如果在與大學生的交流中所使用的網絡話語沒有及時更新,則會被認為是落伍。
2 大學生話語方式對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戰
語言是思想的載體,從對大學生網絡話語方式的特點分析,可了解當前大學生群體的思想特征,他們既逐新追潮又樂于解構傳統,既張揚個性又慣于標簽化,既需要情緒宣泄又長于自我隱匿。開展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從內涵上把握當前大學生思想脈絡,也要從形式上與大學生話語方式進行契合、對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這就需要對當前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方式進行分析和反思。
2.1 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方式相對單一
思想政治工作作為高校各項工作的生命線,其在網絡上的開展早已備受重視。但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絕不能僅僅將簡單的理論說教照搬到網絡平臺上,固守傳統教育理念,仍不改其“灌輸式”信息輸出方式。當大學生作為受教育者被動接受,雙方缺乏話語的互動性時,在豐富的網絡世界,思想政治教育也只能是沒有聽眾的“獨唱”。在當前層出不窮的思想政治教育類微信公眾平臺、網站中,不乏簡單理論性輸出、說教式內容,難以在大學生群體中形成關注熱點,更難以成為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提升的平臺。話語方式單一容易給大學生留下枯燥乏味的印象,缺乏進行深入理解和思考的興趣,難以達到教育效果。
2.2 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內容貼合度不高
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不言而喻,其核心內容是傳播主流意識形態,構建大學生正確價值觀,其話語內容天然具有一定的理論高度和抽象表達。在當前的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中,仍存在不能適應微文化場域和大學生話語特點的問題,理論性、教育性特征過于凸顯,從話語的情感表達上難以滿足大學生心理需求,從教育的切入點上不符合大學生現實需要,從話語的具體表述上不能貼合大學生生活和網絡話語語境,缺乏雙方平等對話的溝通基礎,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難以入腦入心。
2.3 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針對性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因其特殊性質與使命,必然以面向廣大群體的官方話語、學術話語為主,而缺少針對不同受教育群體需求與喜好的差異化方式。對于大學生而言,他們習慣于從互聯網上主動獲取自身所需信息,對于被動灌輸的內容不夠重視。一方面,自媒體的存在和大量小眾互聯網群落,使大學生能夠根據自身思想狀況、心理需求、話語方式偏好等個體差異進行選擇和交流,而網絡思想政治教育難以及時深入;另一方面,網絡信息快速變化,教育工作者很難對輿情熱點進行迅速跟進,適時引入教育內容。
2.4 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方式略顯呆板
互聯網時代背景下,信息豐富且更新傳播速度極快,各類平臺和自媒體層出不窮,大學生往往能夠敏銳獲取信息,關注熱點也時時變化。但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對于熱點信息及網絡文化的關注度普遍落后于大學生,且教育思維和方式相對模式化,話語方式和內容滯后于網絡發展和學生需求,創新性和應變性不足,較為呆板,容易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的局面,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3 對開展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議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間基于話語溝通而育德化人的過程[2]。而因長期存在的灌輸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使其話語方式偏向單向說教,與大學生熱衷的網絡話語方式相比,前者信息傳輸效率低、效果差,影響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甚至容易造成話語權丟失。因此,提升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需要從大學生話語方式的特點出發,針對性解決當前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方式存在的問題。
3.1 豐富話語形式,鮮活思想表達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是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承載一定社會主導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和道德規范并遵循語言規范和規律,向教育客體施加意識形態影響以改變人們思想和指導人們行為的言語符號系統[3]。思想政治教育的內涵決定了傳統話語方式中的單一向度和話語的規范性、意識形態的指向性。從“南航徐川”“寶哥說”等深受大學生喜歡的新媒體內容中可以看到,大學生不是不需要、不想了解思想政治內容,只是他們青睞更鮮活的話語方式,即使是傳遞一種思想主張,也追求生動的表達。思政工作中常用的“堅持”“高舉”,或者“一定”“保證”等充滿強制、命令色彩的表達往往直接引起信息接收方的反感和拒絕。動輒引經據典、抽象、哲理性的說辭也很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難。思想政治教育應嘗試以更加鮮活生動的方式,充分借助流行元素和符號系統,取代刻板抽象,增強話語方式的畫面感和故事性。信息的傳播有其特點,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循序漸進的過程,要首先吸引大學生的興趣,用鮮活的故事引導其進一步深入思考,進而了解其背后的深刻內涵。
3.2 貼近話語主體,引導個性發展
話語與語言相比更強調與現實生活相聯系,傳統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方式偏向于高度凝練的理論和觀念輸出,書面化現象嚴重,而忽略了意識形態傳播過程不僅僅是一個認知信息的傳遞過程,更是一個情感信息的感染過程[4]。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應更側重于與學生進行有溫度的互動,形成平等對話的教育關系。應嘗試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網紅”,合理使用網絡話語方式,與大學生進行順暢溝通,體現對話平等,學生的自主性會相應提升,排斥性會相對下降。網絡話語對大學生的最大吸引在于他們借助互聯網的言論自由與匿名性,得以擺脫現實的束縛,自由發表言論并獲得關注,擁有平等的身份表達和話語權[5]。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本身要在網絡上敢于亮劍發聲,形成正向的輿論場,對大學生形成隱性的思想引導;要善于跟蹤網絡熱點,及時從中分析、辨別大學生的政治、情感等心理訴求,并及時融入線下思想政治教育;要看到網絡話語方式所體現出的大學生對個性彰顯與群體認同的需求,及時提供平臺,鼓勵積極的個性發展,引導健康的群體認同方式;看到情緒化網絡語言的流行,要理解大學生對社會深層矛盾的焦慮和對公平正義的呼喚,及時引導其樹立法治觀念和增強理性思辨能力。
3.3 跟進熱點演化,突破話語區隔
網絡話語時時刻刻都在互聯網醞釀、誕生、傳播和消亡,這個過程往往伴隨著社會熱點而發生,并迅速進入大學生視野,被廣泛應用。思想政治教育要走出課堂、書本、辦公室,及時關注當前社會熱點,理解大學生網絡話語,并理解其樂于使用的心理動機和需求,適時對輿情熱點進行引導。思想政治教育也應嘗試創造自己的潮詞、流行語,形成積極正向的輿情態勢,吸引廣大大學生去關注、思考背后的深意。網絡上戲稱外交部發言人組成“新天團”,引起廣泛關注,也讓大學生領略了大國外交的風采,理解了“弱國無外交”;而發言人常常轉化網絡流行語形成的新語錄“青春不止眼前的瀟灑,也有家國和邊關”“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祖國這艘大船一定保你安全”等都受到網友熱捧和傳播;“厲害了我的國”“祖國一點不能少”,閱兵式“最帥天團”等成為網上的潮詞,傳遞了積極向上的價值理念。要主動把握網絡媒體議程設置規律,正向引導網絡流量和熱度。在“飯圈文化”“粉絲經濟”引起廣泛爭論的時候,“我們都有一個愛豆,他的名字叫中國!”“阿中阿中勇敢飛,中華兒女永相隨”等借助流行話語方式進行的愛國表達,讓大學生迅速以喜聞樂見的方式達成共識,對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益借鑒和有效途徑。
3.4 辨析話語內涵,矯正認知導向
思考、運用網絡話語方式,并不是一味認同和模仿。相反,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既要利用其好的、積極的方面,發揮其思想政治教育價值,更要及時分辨,去除語言糟粕,減少其負面影響。要善于利用網絡傳揚中國傳統語言文字中的精華,制造熱點,正向引導。從話語本身來說,在網絡流行語中不乏因精辟耐用而被納入主流話語表達詞匯,甚至被收入詞典,如“給力”“雷人”等。但也存在如“臉上笑嘻嘻,心里MMP”等粗鄙惡俗之語,應引導大學生提高理性思考能力,分辨惡搞、戲謔、粗鄙的網絡話語,避免跟風、模仿,形成粗俗低級的話語環境。
從話語背后的價值觀而言,要引導大學生分辨網絡話語背后的價值觀,提高獨立思考能力,形成正能量。例如“只怪袁隆平讓你們吃得太飽”被大家用來聲討一位在網上抹黑詆毀袁隆平院士的網友,后來一度成為揶揄別人的流行語。盡管用來表達不滿情緒,但其背后是人們普遍對我國雜交水稻事業成績的認可,對袁隆平的尊崇。但是網絡話語中不乏刻意顛覆經典博眼球、惡意戲謔博流量、偏激宣泄博關注的內容。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要及時引導大學生理性思考,積極正向發聲,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