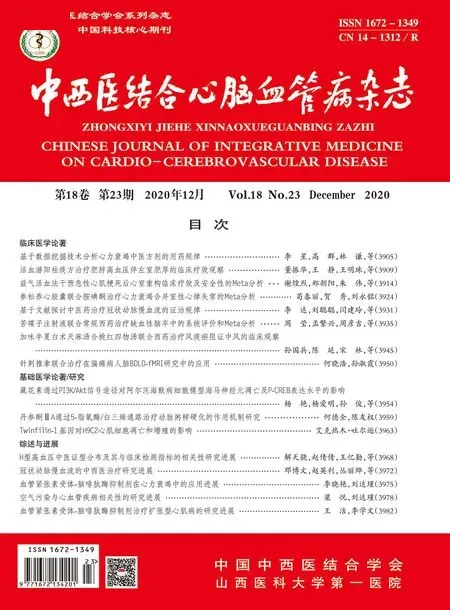出血性腦卒中病人睡眠障礙影響因素及睡眠結構改變與預后的相關性研究
夏文靜,陳媛媛,林 杰,閆明坤,武一平
腦卒中是目前臨床致殘率、致死率均較高的腦血管疾病,出血性腦卒中(cerebral hemorrhage,ICH)又稱腦出血,其發病率占腦卒中的10%~30%[1],對比缺血性腦卒中(cerebral arterial thrombosis,CAT),ICH預后更差,致殘程度更嚴重,病死率更高。腦卒中病人不僅認知功能下降、存在運動感覺功能障礙,還常伴有睡眠障礙[2]。相關研究報道顯示,存在睡眠障礙的腦卒中病人功能康復較慢、平均住院日延遲、腦卒中復發率增加[3]。目前鮮有關于ICH病人睡眠障礙的影響因素及睡眠結構改變與預后相關性的研究,本研究就此進行臨床研究,現總結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觀察對象 選取2016年9月—2018年12月我院神經內科收治的ICH病人126例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符合第四屆全國腦血管病學術會修訂的關于ICH診斷標準[4];②經頭CT檢查確診為首次ICH者;③年齡18~80歲;④發病2周內就診;⑤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評分≥7分;⑥無智力、語言理解明顯障礙,能獨立完成各種量表測評;⑦配合檢查并完成隨訪者。排除標準:①昏迷者;②既往有腦卒中史,除無癥狀性腔隙性梗死外;③嚴重的生理及心理疾病;④存在其他腦病病史;⑤存在已知的睡眠疾病;⑥既往長期服用如苯二氮卓類、抗精神病藥物、抗抑郁藥物等影響中樞神經藥物者。
根據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分為睡眠障礙組(56例)和非睡眠障礙組(70例)。本研究經本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檢測方法 采用Nicolet視頻多導睡眠儀(美國尼高力)對所有病人進行至少8 h的夜間睡眠全程記錄。多導睡眠監測(PSG)研究包括記錄腦電圖、眼動、口鼻氣流、心電圖,監測睡眠結構、睡眠呼吸功能等,次日采用儀器自動分析所有的記錄數據,由工作人員根據2007年美國睡眠醫學會睡眠及相關事件評分手冊進行成人睡眠分期。
1.3 觀察指標及評定標準 病人神經功能缺損程度采用NIHSS評分進行評估[5],輕度:0~15分;中重度:16~45分。分數越高提示病人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越嚴重。睡眠障礙采用PSQI進行評估[6],PSQI>7分為睡眠障礙,PSQI≤7分為非睡眠障礙。預后采用改良Rankin評分(mRS)進行評估[7],預后良好:mRS評分范圍為0~2分,預后不良:mRS評分范圍為3~6分。統計睡眠結構中S1、S2、S3睡眠階段及快速動眼期(REM)、覺醒期(WASO)參數值。比較兩組性別、年齡、NIHSS評分、既往史、腦卒中部位、并發癥等臨床資料,并對NIHSS評分、冠心病、肺部感染及尿路感染進行相關危險因素、睡眠結構與預后的關系進行分析。

2 結 果
2.1 兩組臨床資料比較 兩組性別、年齡、糖尿病、卒中部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睡眠障礙組NIHSS評分、高血壓、冠心病、肺部感染及尿路感染的比例均高于非睡眠障礙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1。

表1 兩組臨床資料比較
2.2 ICH病人睡眠障礙影響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多因素分析得出NIHSS評分>15分、冠心病、肺部感染及尿路感染為ICH睡眠障礙的危險因素(P<0.05)。詳見表2。

表2 ICH病人睡眠障礙影響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2.3 兩組病人睡眠結構比較 睡眠障礙組S1、WASO比例高于非睡眠障礙組,S2、S3、REM比例低于非障礙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3。

表3 兩組病人睡眠結構比較 (±s) 單位:%
2.4 兩組病人預后比較 所有病人于發病后6個月未進行mRS評分判定預后,睡眠障礙組預后良好16例,非睡眠障礙組預后良好45例,兩組預后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5.89,P=0.00)。
2.5 ICH病人睡眠結構改變與預后的相關性分析 ICH病人睡眠結構中S1及WASO與預后呈負相關,S2、S3、REM與預后呈正相關(P<0.05)。詳見表4。

表4 ICH病人睡眠結構改變與預后的相關性分析
3 討 論
ICH驟然發病且病情嚴重,容易導致機體神經功能、內分泌功能及免疫功能失調,具有突發性、嚴重性及難控性的特點,嚴重影響病人身體和心理健康,導致病人出現恐懼、焦慮等不良情緒,從而降低病人的睡眠質量[8-9]。長時間的覺醒,睡眠壓力不斷增加,導致覺醒狀態不穩定,損害腦高級功能區域。ICH后睡眠障礙的類型主要有失眠、睡眠呼吸暫停、日間嗜睡及不寧腿綜合征等。研究表明,睡眠可保證機體體力及精力恢復,且能夠使機體各項生理功能穩定而正常地運行[10]。因此,治療睡眠障礙有利于改善ICH病人預后,而有效治療方案的制定需明確ICH病人睡眠障礙的危險因素。
ICH后腦細胞釋放大量興奮性氨基酸,導致神經遞質代謝失調,如5-羥色胺和去甲腎上腺素等,睡眠-覺醒系統受到不良影響,導致睡眠障礙[11]。相關研究表明,ICH神經功能缺損越嚴重,發生睡眠障礙的概率越高[12]。本研究結果顯示,睡眠障礙組NIHSS評分高于非睡眠障礙組,NIHSS評分>15分是ICH病人睡眠障礙的危險因素,與相關研究報道一致[13],分析原因可能與ICH病人不宜下床活動,白天較長時間臥床,影響夜間的正常睡眠,致ICH病人出現睡眠節律及結構絮亂有關。相關研究表明,糖尿病病人的睡眠時間少于正常人。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等心血管疾病與睡眠障礙密切相關,糖尿病可損害多個器官,中樞神經系統的神經遞質受到影響,引發自主神經紊亂,進一步誘發睡眠障礙[14]。此外,糖尿病病人會出現夜尿增多、神經痛等并發癥從而加重睡眠障礙。合并冠心病的ICH病人夜間極易出現迷走神經興奮、冠狀動脈阻力增高、心肌缺血,冠狀動脈血流量不足對機體生理代謝需求無法滿足,導致病人常出現陣發性心前區疼痛、胸部壓迫性緊縮感,病人頻繁覺醒,進而引發睡眠障礙[15]。本研究結果顯示,睡眠障礙組高血壓、冠心病比例高于對照組,且冠心病是ICH病人睡眠障礙的危險因素。提示冠心病可增加ICH病人并發睡眠障礙的風險。繼發感染是ICH常見的并發癥,多數ICH病人為中老年人,長時間臥床,容易導致病人出現尿路感染及肺部感染。ICH病人合并感染需服用抗菌藥物,使中樞神經系統明顯興奮,引發睡眠障礙[16]。尿頻、尿急、尿痛是尿路感染病人常見的不適癥狀,均可影響夜間睡眠質量。本研究結果顯示,睡眠障礙組肺部感染及尿路感染的比例均高于非睡眠障礙組,肺部感染及尿路感染為ICH睡眠障礙的危險因素。提示肺部感染及尿路感染可明顯增加ICH病人睡眠障礙的發生率。
睡眠結構中的S3稱為深慢波睡眠,具有增強免疫,促進康復及預防疾病的作用[17]。深慢波睡眠減少可對身體及生活質量造成直接影響,其機制為在深睡眠期機體基礎代謝較低,合成代謝加強[18],對能量的儲存和新的神經突觸聯系的建立均有益,影響神經系統的康復,主防御系統的免疫功能得以增強,白細胞介素-1β和腫瘤壞死因子-α達到高峰,對各個組織器官的自我修復具有促進作用,宿主防御體系得以強化,機體產生抗體的能力得以增強,加快精力及體力的恢復。因此,ICH睡眠結構絮亂,深慢波睡眠期的比例減少,不利于ICH病人預后。本研究結果顯示,睡眠障礙組S1、WASO比例高于非睡眠障礙組,S2、S3、REM比例低于非睡眠障礙組。 ICH病人睡眠結構中S1及WASO與預后呈負相關,S2、S3、REM與預后呈正相關(P<0.05)。提示S2、S3、REM比例減少不利于ICH病人預后。
綜上所述,NIHSS評分>15分、冠心病、肺部感染及尿路感染為ICH睡眠障礙的危險因素,S2、REM比例減少不利于ICH病人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