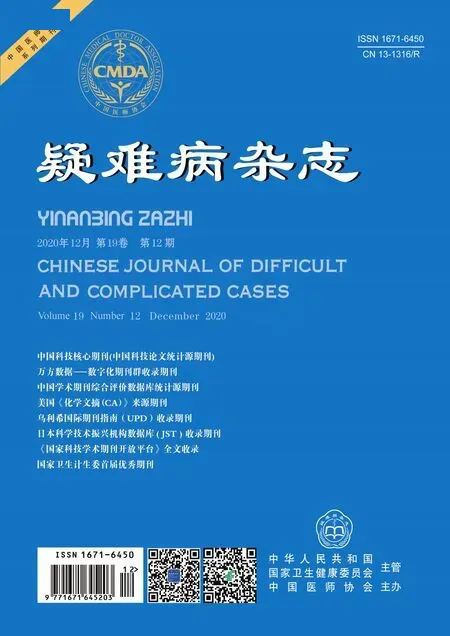重癥單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ECMO綜合治療3例并文獻復習
胡哲夫, 周晨亮, 嚴娟娟, 孫麗芳,程利,劉玉蘭,劉樹超,魏捷,王鑫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自暴發以來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該疾病對呼吸系統影響較大,患者表現為反復發作的乏力、喘息、胸悶、咳嗽及呼吸困難等癥狀[1],常伴有肺部影像學的異常改變。該病毒主要通過直接接觸、飛沫傳播及氣溶膠傳播,并有明顯的家族聚集性。在臨床工作中,典型病例的診斷治療并不困難,而COVID-19患者一旦發展為重癥并累及呼吸和循環系統,往往需要機械通氣及血管活性藥物維持生命體征。隨著研究的進展,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可通過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ACE-2)使感染宿主多個系統及臟器造成損傷[2]。對于免疫力較差或營養不良人群,由于抵抗力較差其預后欠理想。為提高臨床醫師對于體外肺膜氧合(ECMO)綜合治療COVID-19的認識,進行早發現早治療以降低患者病死率、改善遠期預后,現對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2020年1—4月ICU收治的3例行ECMO綜合治療的COVID-19典型病例進行討論分析,以期總結經驗,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例1.男,39歲,主因發熱14 d入院。患者于14 d前出現發熱,熱型不規則,最高達40 ℃,發熱前無畏寒、寒戰,無抽搐,無皮疹及出血點,2020年1月28日出現呼吸困難,在外院查胸部CT示雙肺少許滲出性改變,行冠狀病毒核酸檢測陽性,在家自服阿莫西林膠囊等藥物治療后患者仍有發熱,伴乏力、納差,門診擬“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收入院。既往體健。入院查體:T 36.0 ℃,呼吸困難,語音喘息不連貫,淺表淋巴結未及腫大,咽紅,扁桃體Ⅰ°大。雙肺呼吸音粗,未聞及干濕性啰音及哮鳴音,心界不大,心率89次/min,律齊,未聞及雜音及額外心音,腹軟,無壓痛,肝脾肋下未及腫大,雙下肢無水腫。實驗室檢查: WBC 5.69×109/L,N 92.30 %,L 5.40 %, E 0%;ALT 75.00 U/L, AST 52.00 U/L,γ-GGT 102.00 U/L,總蛋白(TP) 56.30 g/L,白蛋白(Alb) 33.90 g/L,總膽紅素(TBil) 19.90 μmol/L,直接膽紅素(DBil) 11.20 μmol/L,血肌酐(SCr) 53.00 μmol/L,預估腎小球濾過率(eGFR) 126.69 ml/min,氨基末端腦鈉肽前體(NT-proBNP) 134.50 pg/ml;hs-CRP>5.00 mg/L,CRP 191.8 mg/L,降鈣素原(PCT) 0.941 ng/ml,D-二聚體(D-D) 1.68 mg/L。血氣分析:pH 7.42,氧分壓(PO2) 83.00 mmHg,二氧化碳分壓(PCO2) 37.00 mmHg。床邊CR:(1)考慮雙肺炎性病變;(2)頸部—右側胸壁軟組織區積氣;心電圖正常。入院診斷: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入院后給予吸氧,利巴韋林、阿比多爾等抗病毒,甲強龍抗炎,免疫球蛋白以調節免疫,給予美羅培南+替考拉寧抗感染,孟魯司特減輕氣道高反應,但患者氧合狀態惡化,呼吸衰竭明顯,無創及有創呼吸支持效果仍不佳,入院第5天行氣管插管有創呼吸機輔助通氣,入院第6天在李蘭娟院士指導下行李氏人工肝治療方案阻斷炎性因子風暴。患者氧合指數持續下降,于入院后第10天經病情討論行ECMO治療(V-V模式,血流量 2.4 L/min,氣流量4 L/min,轉速2 600 r/min,監測ACT 160~200 s間波動, SaO285%~90%,SVO2>70%,尿量>1 ml·kg-1·h-1,體溫波動于35.0~36.0 ℃,肝素鈉持續泵入(1.8 ml/h),持續鎮靜鎮痛(咪達唑侖注射液8 ml/h+舒芬太尼5 ml/h),阿曲庫銨(5 ml/h)持續泵入,心血管活性藥物去甲腎上腺素持續泵入(3 ml/h)。入院第12天患者血氣指標惡化,并突發心率下降及室性心動過速,積極搶救后仍因呼吸循環衰竭死亡。ECMO治療前后CT影像學變化見圖1。

注:A.入科時;B.死亡前
例2.男,35歲,主因發熱、咳嗽10 d天入院。患者10 d前無明顯誘因出現發熱、咳嗽,1月28日外院胸部CT未見明顯異常,體溫最高38 ℃,1月31日復查胸部CT示多發磨玻璃狀影,2月1日于外院門診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給予激素治療2 d(具體藥名不詳)及口服奧司他韋治療,體溫稍下降,但仍咳嗽,2月4日復查胸部CT示雙下肺明顯加重,且患者咳嗽癥狀無緩解,故門診擬(1)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2)甲狀腺功能亢進收入院。既往史:甲狀腺功能亢進多年,現口服他巴唑,1片,1次/日,尿酸偏高。入院查體:T 37℃,SaO298%(吸純氧:5 L/min),淺表淋巴結未及腫大。雙肺呼吸音粗,未聞及干濕性啰音,心率97次/min,律齊,未聞及病理性雜音及額外心音,腹平軟,無壓痛,肝脾肋下未及,雙下肢無水腫。實驗室檢查:WBC 8.97×109/L, N 82.50 %, L 8.60 %, E 0%;ALT 90.00 U/L, AST 76.00 U/L, γ-GGT 115.00 U/L, TP 57.40 g/L, ALB 34.40 g/L, TBil 13.60 μmol/L,DBil 5.10 μmol/L, SCr 64.00 μmol/L, eGFR 120.58 ml/min,NT-proBNP 143.00 pg/ml, hs-CRP>5.00 mg/L, CRP 37.8 mg/L, PCT 0.051 ng/ml,D-D 0.48 mg/L。血氣分析: pH 7.40, PO2111.00 mmHg, PCO243.00 mmHg。床邊CR:考慮病毒性肺炎(重癥),右側氣胸;心電圖示:竇性心律,心電軸右偏。入院后痰培養及左腹股溝區切口培養出嗜麥芽窄食單胞菌,血培養檢出近平滑念珠菌,胸水培養檢出白色念珠菌。診斷:(1)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2)膿毒癥休克;(3)血流感染(真菌);(4)ARDS 呼吸衰竭;(5)MODS(心臟、肝臟、凝血系統、腎臟、免疫系統);(6)中度貧血;(7)低蛋白血癥;(8)甲狀腺功能亢進。入院后積極予以阿比多爾等抗病毒,甲強龍抗炎,免疫球蛋白調節免疫,伏立康唑抗真菌、哌拉西林鈉他唑巴坦鈉抗感染,加強腹股溝區及骶尾部換藥,營養支持等對癥治療。入院后第5天患者自覺呼吸費力,經高流量給氧(吸氧濃度60%)后氧合指數進行性下降,遂氣管插管呼吸機輔助呼吸。入院第7天氧合改善差,PO2低于100 mmHg,因頑固低氧血癥,單純呼吸機支持治療不能緩解,經病情討論予以ECMO治療。經過積極治療后患者一般情況逐漸好轉,于第31天撤離ECMO,行單純機械通氣。入院第60天患者復查相關指標未見明顯異常,胸部影像學提示,與前片比較,雙肺感染及胸壁軟組織積氣明顯吸收,右側少量氣胸,左側已吸收(見圖2)。患者行康復鍛煉后一般情況恢復良好,經并病情評估轉出ICU,后經隨訪療效顯著。

注:A.入科時;B.脫機時
例3.男,65歲,主因畏寒、發熱2個月伴胸悶、氣喘1個月入院。患者于2個月前開始出現發熱,體溫最高達39.6 ℃,無明顯咳嗽、咯痰,2月1日就診于外院,胸部CT提示肺部感染(具體不詳),給予奧司他韋及頭孢呋辛、更昔洛韋治療,1個月前患者自感出現胸悶、氣緊,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給予莫西沙星、阿比多爾、連花清瘟口服,因氣緊明顯緩解,遂住院給予吸氧,抗病毒(阿比多爾、克力芝),抗感染(莫西沙星),止咳平喘,后復查胸部CT提示雙肺重度感染較前加重,右肺上葉胸膜下可疑肺大泡,縱隔淋巴結增大,雙側胸膜肥厚粘連。患者病情逐漸加重,SaO2最低51%,予氣管插管有創呼吸機輔助通氣,俯臥位通氣及V-V模式ECMO治療。外院住院期間患者痰培養提示醋酸鈣不動桿菌、大腸埃希式菌,血培養提示MRSA,抗感染方案改為美羅培南及萬古霉素,后因病情加重轉入院。既往無特殊病史。入院查體:T 36.2 ℃,SaO299%(ECMO),淺表淋巴結未及腫大,雙肺呼吸音低,未聞及干濕性啰音,心率88次/min,律齊,未聞及病理性雜音及額外心音,腹平軟,無壓痛,肝脾肋下未及,雙下肢無水腫。實驗室檢查:WBC 5.90×109/L,N 92.80%,L 3.20%,E 0%;ALT 28.00 U/L, AST 63.00 U/L,γ-GGT 96.00 U/L, TP 56.60 mg/L, Alb 39.80 g/L, TBil 30.20 μmol/L, DBil 13.70 μmol/L,SCr 47.00 μmol/L,eGFR 110.89 ml/min,PCT 1.190 ng/ml,NT-proBNP 1 131.00 pg/ml, D-D 18.65 mg/L。血氣分析: pH 7.36, PO2108.00 mmHg, PCO242.00 mmHg。床邊CR:兩肺感染,頸部、胸部皮下氣腫,縱隔積氣可疑;心電圖正常。患者從外院轉至我院ICU一直依靠ECMO維持呼吸及循環,并積極予以美羅培南及萬古霉素抗感染,阿比多爾抗病毒,甲強龍抗炎,免疫球蛋白調節免疫,營養支持及穩定內環境等對癥治療。于入院第34天在陳靜瑜教授團隊指導下行武漢市首例新冠肺炎患者雙肺移植術。術后患者移植供肺功能尚可,能較好維持氧合參數,后經病情評估于入院第35天撤離ECMO,經密切觀察病情,患者目前移植肺能維持氧合指數于正常范圍,生命體征趨于平穩,于第43天轉出ICU,后動態隨訪。患者ECMO治療前后胸部CT影像學變化見圖3。

注: A.入科時;B.肺移植后ECMO脫機時
2 討 論
COVID-19是一種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肺炎,新型冠狀病毒主要的傳播途徑是經呼吸道飛沫、氣溶膠和直接接觸傳播,人感染后潛伏期為1~14 d,且潛伏期仍具有傳染性[3]。患者初始癥狀多為發熱、乏力、肌肉酸痛、干咳、呼吸困難等嚴重表現。自COVID-19暴發以來,其發病率呈現快速上升趨勢。新冠病毒主要侵犯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尤其是有基礎疾病或合并有糖尿病的老年人群,其通過結合機體各大細胞表面的ACE-2破壞各大組織器官,例如消化道、胰腺、心血管系統、神經系統及生殖系統等。在ICU,部分危重癥病例可出現ARDS、膿毒癥休克、MODS甚至死亡。在相關指南中缺乏針對病原體的有效抗病毒藥物,重癥單元主要加強以隔離及對癥支持治療為主。
我院應用ECMO技術救治了3例新冠肺炎患者。3例患者均診斷為COVID-19危重型,入院時胸部影像學均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磨玻璃浸潤影,其中2例患者因病情進展在入住ICU后常規有創通氣難以維持氧合指數,經病情評估采用ECMO治療,1例患者于外院已經啟用ECMO直至入科后成功移植供肺后成功脫機。1例影像學進展迅速并出現呼吸循環衰竭及多臟器功能障礙而死亡,另外2例患者經過ECMO綜合治療后情況趨于穩定,病變吸收且成功脫機并轉出ICU。
COVID-19可通過病毒毒力直接破壞肺泡組織,危重型患者往往表現為劇烈咳嗽、頑固性低氧血癥及呼吸窘迫導致的肺功能惡化[4],即使使用了積極的有創呼吸機維持通氣仍難以使氧合指數達到理想水平。除了傳統的抗感染、抗病毒、營養支持及人工肝技術外,ECMO的治療地位尤為重要。
ECMO技術在臨床應用已久,其本質是一種改良的人工心肺機,核心部分為膜肺和血泵,分別起到人工肺和人工心臟的作用,最早主要適用于心臟外科手術的體外循環輔助,可以對重癥心肺功能衰竭患者進行一定程度的心肺支持[5]。ECMO運轉時首先將血液從靜脈端引出,通過膜肺吸收氧同時排出CO2,血液經過氣體交換后在泵的推動下可回輸到靜脈(V-V模式)或動脈(V-A模式)。在不同的情況下,兩種模式可分別用于不同的患者。筆者認為,任何手段包括ECMO都存在利弊,由于管路的肝素化,相關并發癥如下肢缺血壞死、血液凝固、感染、大出血等同樣不可忽視。
本單元3例患者中所使用的模式均為右股V-右頸內V的ECMO體外膜肺氧合支持治療模式。例1患者較年輕,主要表現為高熱,入院行影像學檢查可見肺部少許滲出(圖1),經過積極常規藥物治療及有創機械通氣,患者氧合指數進行性下降后使用ECMO,入住12天后血氣指標惡化,并突發心率下降及室性心動過速,最終因呼吸循環衰竭死亡,且最后一次胸部X線片可見雙肺透亮度下降,存在肺部惡化。例2患者同樣為年輕男性,以發熱、咳嗽為主要癥狀,入科時肺部影像學提示嚴重滲出及實變影、右側氣胸,經過積極治療后出現氧合指數下降,啟用ECMO治療31 d后撤機,最后一次復查胸部影像學發現,雙肺感染明顯吸收,患者康復良好,能夠自主活動。例3為65歲老年患者,主要以畏寒、發熱伴胸悶、氣喘為主要癥狀,該患者在外院經過較長時間的治療后病情惡化仍較快,在短期內已啟用ECMO治療,轉入我科后行影像學檢查發現雙肺大面積實變,在陳靜瑜教授團隊指導下行武漢市首例新冠肺炎患者雙肺移植術,術后經病情評估,移植供肺能較好維持氧合指數,于第35天成功撤離ECMO,患者康復良好。
作為治療COVID-19的輔助治療手段之一,上述病例的治療經驗提示,除了積極的治療、護理、營養支持和心理安慰外,感染的控制及出血的預防至關重要[6]。首先穿刺部位是一個有創操作區域,其發生感染的風險較高,在護理工作中需密切監測及換藥,同時管路的清潔、氧合器的定期更換可有效減少病菌的定植;其次由于ECMO的運作需要血液循環的肝素化,患者的血液處于持續的低凝狀態,這對內臟出血包括胃腸道、腦、心臟、肢體末梢循環都存在一定的影響,通常將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設置為180~200 s的范圍,同時要密切監測管路中有無血栓形成。在日常工作中,部分患者存在口腔或氣管切口滲血等情況,有時需根據病情糾正凝血功能改善出血情況。
結合文獻復習,對于危重型COVID-19患者,如果存在ECMO的適應證,早期積極有效的治療依然顯得重要。臨床醫師要高度重視,特別是影像學進展迅速,呼吸循環功能難以維持的情況下要謹慎采取措施。任何輔助治療手段都各有利弊,要綜合評估病情進行選擇,以達到最好的治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