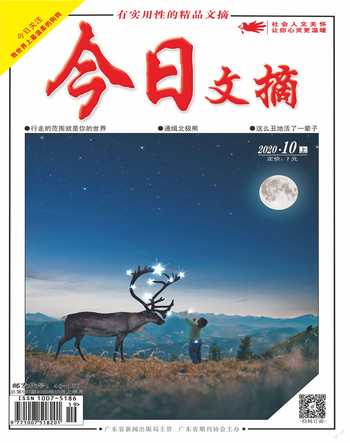平凡而偉大:一只導盲犬的使命
連勤(視障人士)和她的導盲犬Candie初次見面,是在2007年7月2日。
當時連勤在美國兼職做翻譯,那天完成工作后,客戶提議說,這里附近有一個導盲犬培訓學校,要不要一起去認識一下那些導盲犬。連勤就在這里見到了Candie。
那次見面,連勤對Candie的印象實在一般般,因為它太高冷了。連勤當時站在Candie旁邊許久,但Candie根本沒有理睬她,自顧自曬太陽,難怪人送綽號“冰公主”。
那個時候,連勤還不知道,“高冷”是一只優秀的導盲犬必備素質。
一年后,2008年殘奧會在即,國內需要一只服務犬作為服務犬科普形象大使,但當時的國內并沒有合適的狗能夠勝任。連勤當時身處美國,受中國殘聯之托,她向美國提交了導盲犬申請。
本以為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是不可能申請到狗的,沒想到機緣之下,她竟幸運地與Candie重逢。這一次,她與Candie成功配對,帶著Candie跨過大洋來到中國服役。
Candie成為了第一條在中國服役的、具有國際導盲犬資質的導盲犬。
狗狗“打好一份工”,
20小時不進食不大小便
回國后,連勤在某單位國際部上班。從家到工作單位大約20公里的路程,打車太費事又費錢,所以連勤會坐地鐵,10號線到國貿轉1號線,再從建國門轉2號線。這一段地鐵路程,總計約40分鐘。
一路上并不輕松。從家去地鐵站,小路上有很多東倒西歪的自行車,而且地處市中心區域,馬路上到處都是人。但有了Candie之后,連勤感到了“有陪伴”的安全。
令連勤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Candie從美國來中國的那次旅途:“那對導盲犬真的身心壓力太大了。”當時,連勤和Candie需要從洛杉磯到西雅圖再到首爾,最后到北京,整個航班時間長達20個小時。
一般導盲犬在工作狀態下是不能進食的,更不能隨地大小便。Candie在這20個小時飛行旅途內,就一直處于“工作”狀態,乖乖地蹲在她的腳跟前,不吼叫,更沒有進食、大小便,簡直是挑戰狗的生理極限。而且一路途經多個不同的地方,這對導盲犬的心理適應能力也是一大挑戰,但Candie全都做到了。
由于工作性質的原因,連勤經常需要在各地出差,有了Candie的陪伴,她輕松了許多。如今,連勤已經退休了。Candie在為連勤服務了11年后,也于2018年底光榮退役。
退休后,連勤沒有把自己關在家中。2018年,連勤突發奇想注冊了一個抖音號,專門記錄Candie的生活。如今Candie已達15歲“高齡”,過上了愜意的退休生活。
視障人士與導盲犬相互陪伴,他們并不僅僅是“主人”和“動物”的關系,而更像是一家人、好朋友。
厲陽(視障人士)也是導盲犬的使用者,他的狗狗叫威威,是一只金毛,來到他的身邊已經三年多了。
厲陽清楚記得,有一次出門,威威一直往馬路的左前方走,厲陽想著應該靠右邊走,但威威始終不肯改變。厲陽當時沒有相信威威,就拽了威威一下讓它靠右,結果自己一腳踩進了一個大水坑。
厲陽說,“威威就是我的眼睛,讓我能夠單獨地安全地出行,也讓我更愿意出門了。不過對我而言,它還是我的兄弟,我們互相保護。”
嚴格選拔:三代以內無攻擊性,難度堪比“高考”
一只合格的導盲犬,之所以能夠如此敬業盡責,是因為它們在正式上崗之前已經經過了層層篩選和嚴格的訓練,這一過程堪比服務犬中的“高考”。
一般而言,國內導盲犬多是金毛、拉布拉多以及它倆的第一代雜交。選拔預備役的過程,就要設置層層門檻:身體健康狀況評估、性格測評(偏差性小、溫和)以及三代以內無攻擊性。
成功選上后,在狗狗兩到三個月大時,就會和生父母分別,送到寄養家庭生活。在這段時期,它們要學習兩件大事。
第一,習慣與人類相處的模式。例如寄養家庭必須嚴格要求幼犬,不能食用人類的食物、不攻擊人、不能跳上家具(尤其是沙發)和人類的床,以及服從坐下、趴下、等待等基本指令。
第二,接受社會化的訓練。這一期間,寄養家庭會帶幼犬出入各公共場所,讓它們習慣各種環境、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為將來服務視障者的生活做準備。
寄養家庭非常深度地參與到了導盲犬的訓練中,這樣的生活一般將持續10個月到一年多。
姜丹是一位具有國際資質認證的導盲犬訓犬師,曾參與過上百只導盲犬的訓練。她發現:“很多寄養家庭養著養著就養出感情了,等到該還給我們的時候,他們就不舍得。”
因為舍不得歸還狗狗,有些人甚至會“特意”教狗狗一些壞習慣:“當然這也是少數,因為畢竟當初他選擇當寄養家庭,就知道總有一天會跟狗狗分開。”
姜丹覺得,正因為這樣,寄養家庭其實是很偉大的。“有時候我們去接狗,一些寄養家庭就會在后面追著車哭,對他們來說,是很難的。”
等狗狗長到12-18個月大時,它們會離開寄養家庭,接回基地開始專業訓練。在這個過程中,專業的訓犬師會對狗狗進行直行、上下臺階、避讓障礙等30多個項目的訓練。
“這些導盲技能的訓練也是循序漸進的。最開始我們會選擇在居民區這樣安靜、環境比較單一的場所進行訓練,之后會慢慢過渡到一些有車流、路況環境稍復雜一些的地方,最后會去菜市場、商場等交通狀況復雜、人流多的地方。”姜丹說。
最后,在導盲犬正式上崗之前,它們會與配對成功的視障人士一起進行長達一個月左右的“共同訓練”。這一過程是使用者與導盲犬之間互相熟悉、互相照顧、建立信任的過程。
從給狗狗洗澡、與狗狗相處到熟悉對方的聲音與行為,包括開始相信對方,這些都是共同訓練的內容。只有經歷了這些,導盲犬才能正式上崗,雙方才算“配對成功”了。
“導盲犬不是很聰明的嗎?你就讓它給你去找吧!”
盡管經歷了這么多的篩選與訓練,也不意味著導盲犬就是“萬能”的。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導盲犬是絕頂聰明的,不僅能隨便導航認路,還能讀懂主人的心思,快速幫助主人找東西。
“導盲犬是可以記住常走的一些路線,但它并不是真的導航。”厲陽說:“如果我們去了一些陌生的地方,導盲犬自然也是不認識的。我們也和大家一樣,使用各種導航APP查詢路線,然后根據導航給導盲犬下指令。這時,導盲犬的作用就是負責好我們的出行安全。”
導盲犬在外是應當處于嚴格的“工作狀態”的,打擾導盲犬工作的行為,會給視障人士群體的出行帶來安全隱患。但在導盲犬工作的時候,很多人還是會隨意觸摸、喂食甚至逗狗狗玩。
厲陽說,出門的時候,他會給狗狗穿上衣服,戴上導盲鞍,衣服上面寫著“工作中,請勿打擾”。但即使如此,在外行走時“還是會有人過來打擾導盲犬,逗它玩或者摸摸它。”
大連培訓基地的訓導師王鑫說:“我們希望大家在遇到視障人士和導盲犬的時候可以做到‘四不一問’:不呼喚、不拒絕、不喂食、不觸摸以及對需要幫助的視障人士多一些善意的詢問。”
遺憾的是,“拒絕”現象也頻頻發生。
導盲犬出入公共場所其實早有立法保障。我國2012年8月1日開始實施的《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第十六條規定,視力殘疾人攜帶導盲犬出入公共場所,應當遵守國家有關規定,公共場所的工作人員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供無障礙服務。
然而,不久前在山西,導盲犬坐公交被拒,還被罵哭的新聞再次引發熱議。據報導,司機拒載的原因是擔心導盲犬會傷害他人,甚至進一步導致狂犬病。
“這其實多慮了。導盲犬肯定是不會咬人的,它當導盲犬之前我們都會追溯它祖宗三輩兒,包括它的血系,不能有咬人或攻擊人的歷史。另外它們都是經過嚴格免疫的,每年都會有定期的疫苗和驅蟲。”姜丹說。
全國1700萬視障人士群體,僅200余只導盲犬
成立于2006年5月15日的中國導盲犬大連培訓基地,是我國大陸地區首家導盲犬培訓機構。截至目前,該基地總共培育出180余只導盲犬,占據了全國總量的絕大多數。而在全國范圍內,導盲犬數量大致為200只。
但這一數量相比中國1700多萬的視障人士群體,還是過于渺小。
大連培訓基地作為一個非盈利公益機構,訓練出的導盲犬全部免費交付視障人士使用。視障人士只要通過基地官網、電話等聯系方式,就可以進行預約。工作人員會評估視障人士的情況,進行后續配對工作。
作為一項公益事業,大連培訓基地的主要收入來源于大連市政府的財政補貼(12萬元/只導盲犬)以及不定期的企業捐助。然而一般而言,訓練一只導盲犬的總成本在15-20萬元左右。
目前,導盲犬的訓練成功率仍然較低,而且訓練時間較長。盡管在初期挑選篩選階段要求已經比較嚴格,但訓犬師姜丹說,在訓練過程中,可能還會陸續發現一些狗的某些方面比如性格不合適、噪音脫敏不成功,也就只能中途放棄了。
王鑫提到,一只導盲犬的總訓練時長是1-2年,不過由于國內的路況環境更加復雜,例如某些地區沒有人行道、沒有紅綠燈,只有小路,因此相比國外,訓練的時間會更長一些。
而訓犬師數量稀少也是導盲犬產量較低的原因之一。“因為這不是一個賺錢的行業,就是一個公益事業,所以收入不高,愿意來做訓犬師的人也比較少。”姜丹說。
目前,大連培訓基地一共僅有12名訓犬師,姜丹說,“訓犬師的工作是比較枯燥辛苦的,如果沒有很強大的責任感,或者說如果不是真的喜歡狗,一般很難堅持。”
姜丹回憶自己當時在國外學習的時候,因為同時訓6條狗,一條狗狗每天至少要保證1小時的訓練時間,當時鞋子都走壞了好幾雙。
除此以外,每天早上起來以后,還要打掃兩個小時的犬舍,其中包括清理狗狗便便的工作。“所以很少有人能堅持下來。”
和人類一樣,服務犬的一生有著清晰的節點:出生、訓練,工作,最后退役。
他們把絕大部分最好的時光獻給了導盲事業,做視障人士們的眼睛。對于狗狗而言,這意味著放棄了做父母的權利;放棄了與小伙伴自由玩耍的樂趣;放棄了共享美食的誘惑,進入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面對疾病、衰老,主人與導盲犬之間的相互支持、陪伴,似乎成了彼此最親密最堅實的依靠。從2008年到2018年12月3日退役,Candie為連勤導盲了整整11年。在Candie退休的那天,連勤發微博說:“Candie為我導盲11年,今天它光榮退役,往后的日子,我為你養老。”
(許一光薦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