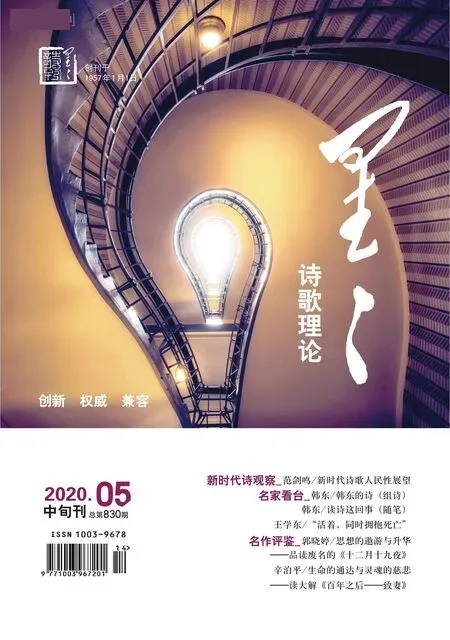我的詩歌札記
育 邦
一方面,詩歌來自于無處不在的生活經驗、不斷上涌的回憶、行走的足跡、想象甚至夢境;另一方面,還要求它不停地偏離生命航道,探尋那些晦暗的地帶,進行所謂超越的活動——試圖擺脫重力的白日夢。我一直以來的詩歌寫作就支持這些說起來正當但又虛幻的理由。好在,在多年前(打算以寫詩來表達我與這個世界關系之時),我就學會容忍自己這一純粹來自精神領域內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荒誕想法。里爾克在《布里格日記》中這樣寫道:“唉,要是過早地開始寫詩,那就寫不出什么名堂。應該耐心等待,終其一生盡可能長久地收集意蘊和甜美,最后或許還能寫成十行好詩。”也許我們認為這不過是詩人的謙遜與不實之辭,但事實并不是那么簡單。里爾克本人在他的內心深處就是對寫作好的詩歌有著審慎而執著的憂慮。他接著寫道:“因為詩并非像人們認為的那樣是感情,而是經驗。為了寫一行詩,必須觀察許多城市,觀察各種人和物,必須認識各種走獸,必須感受鳥雀如何飛翔,必須知曉小花在晨曦中開放的神采……”他要求詩人回想起童年的疾病、壓抑的日子、海邊的清晨、各種不同的愛情之夜等生活中與思想上遭遇的種種細致入微的情形。參照這種嚴格近乎苛刻的要求,里爾克總結他的創作,說:“迄今為止我寫的詩卻不是以這種方式寫出來的,所以都稱不上是詩。”
成就一名詩人需要一定的身體經驗和閱讀經驗,但僅有這樣的利器是遠遠不夠的。一名真正的詩人必須不斷地超越自身已有的經驗,因為有更多的隱秘的生活等待著我們去深入,有無限的神秘的書籍等待著我們去閱讀,有數不清超出我們經驗的道路等待我們去探索……真正的寫作必然是一種沉寂,真正的詩人必然是遭遇“寫作困難”的人。寫作就是不斷制造寫作困難,進而努力去解決這種困難。否則,就只能叫寫字。這是一種存在的艱難……
一定程度上講,詩歌是一件相當完美的認識工具:對自己的認識,對世界的認識,對人與事物關系的認識……但這實在是低看了詩歌。遠遠不夠。詩歌足以構建一個宇宙,有太陽,有月亮,還有星星點綴其間……它是與個人有關一切的總和。
作為技藝領域里的詩歌,微不足道,任何有志于詩歌寫作并有相應天賦的人都會在此范疇內實現自給自足。通過閱讀、模仿、練習,一名學徒會成功地掌握寫詩的技藝。有了技藝并不能保證你能寫作優秀的詩作來。也許,像狄蘭·托馬斯說的那樣:“優良的技術總是在詩的構件中留有空隙,以便詩外的什么能夠爬進來、溜進來、閃進來或闖進來。” 因而我們總是需要儲備好“優良的技術”,以期在某一刻實現詩。
詩歌首先是關于語言的藝術。詞語幫助我使瞬息萬變的想法、氣息、睡夢、感覺固定下來的泥沙,它們固執己見,哪怕正在建設的是一座不可能實現的巴別塔或一座明顯缺少存在基礎的豆腐渣工程。它們為滿足我一時愉悅或痛苦之感而奮不顧身。詩人的語言對于詩人而言是精確的,負載著自己個人信息和密碼的載體。較之其他文體,詩歌對語言的要求更高,它需要語言陌生化并流動起來。但同時我們不能僅僅把它看作言說的狀態。更多時候,它是無言的,沉默帶給詩歌巨大的存在空間,它在適當地點適當時刻停頓,留給我們。
詩歌的價值與意義何在呢?也許對于一個把生命與詩歌混為一談的人而言,這是一個并不存在的問題。因為他們在這個世界的關系是共生的,是互文的。在每一首詩,每一行詩中,都沉淀下我們的影子、我們的黑暗。詩是蒙上復雜色彩的自傳。
作為詩人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在詩中這樣寫道:“被詩歌埋沒了一生的人/黎明前又重新回到了想象中/他在一首詩的結尾處停了停/就想到了布達拉宮/他只朝前邁了一步/就與積雪一同融化……”詩人必然的命運就是融入這無邊的世界,那無垠寒冷的白雪。詩歌就是我們的出生地,是我們日復一日的睡眠,是我們的生老病死、怨憎相會、離愁別緒;本質上來說,對于詩人而言,是骨骼,是血。同時,我們也相信,詩人是這個世界的存在之謎,就像讓·科克托說的那樣:“詩人是一個謎。他不出謎語。他講述他所居住的世界,一個游人不知道怎么去、因而不能把油膩的紙扔得到處都是的純潔的世界。”詩人還是演員。他不靠相貌、聲音和動作來演戲,在生活中他喬裝改扮,一方面作為蹩腳的演員絮絮叨叨,經常穿幫;另一方面還精心化妝,裝得像某一個人。他的演出不僅不能取悅于人,倒是常常令人驚駭。他僅僅靠自己的心靈來實現自己與世界的疏離,使他在寫詩的那一刻擺脫人世的重力,獲得飛升的神奇機能。
佛陀在《經集·蛇經》中說:“他不在生存中尋找精髓,猶如不在無花果上尋找花朵,這樣的比丘拋棄此岸和彼岸,猶如蛇蛻去衰老的皮。”比丘是修行,詩人也是修行。比丘是求解脫之人,而詩人是在這反面。詩人也許永遠無法拋棄此岸和彼岸,也許無法退去自己衰老的皮,但這些正是詩人不斷走向詩人的必由之路。
談論寫詩,多么奢侈,多么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