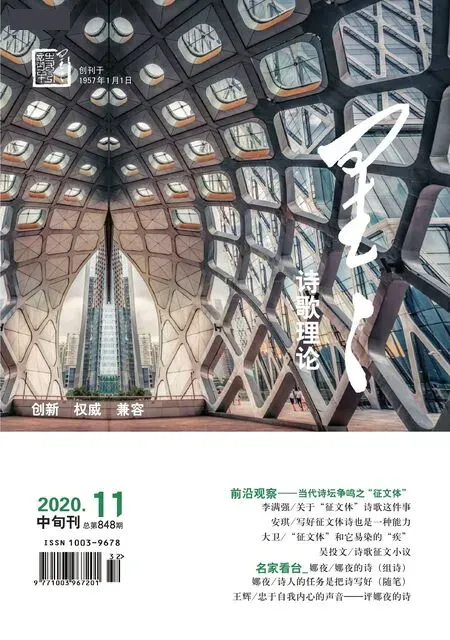以語言沖擊秩序:沃倫的鷹之詩
在20世紀的美國詩歌史上,羅伯特·潘·沃倫(Robert Penn Warren)是一位特別且綜合的存在。他是“新批評”理論的聯合創始人之一、美國第一任桂冠詩人。詩與小說均斬獲普利策獎,他也一度被評論家褒獎為“二十世紀后半葉最重要的美國詩人”。沃倫一生創作了十幾本詩集,哈羅德·布魯姆曾不吝贊美:“從1966年到1986年,沃倫寫出了幾乎是這二十年內美國創作的最好的詩歌。”同時,布魯姆將沃倫的晚期創作與哈代、葉芝和斯蒂文斯煥發的最后階段,相提并論。
詩歌牢牢占據著沃倫文學生涯的核心。沃倫曾長期生活在美國南方的肯塔基州,后來在耶魯執教時,居所也在郊區的小鎮。當時南方以農業為主,沃倫筆下有大量的南方田園、自然的風貌。就詩學理念而言,沃倫深受“新批評”的先導艾略特的影響,但越到成熟時期,他越有意回糾,轉向南方的自然精神。讀他的詩,田野、山林、樹木、河流是美式的;而家族史、當地傳說和獨立戰爭后的南方遺緒,被他大量地援引并化入詩中。這兩者決定了其詩沉思綿長的特點。隨著年歲增長,他的詩歌精神宛如一片抖動的田野,日漸開闊。尤其是一些極具心靈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形象,現在也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獨占鰲頭的,就是他詩中反復出現的鷹的形象。
對鷹鐘愛,能從詩人的傳記上看到源頭。1920年夏天,十五歲的沃倫經歷了人生一次嚴重的變故。當時他剛考上美國海軍學校,但左眼因意外被弟弟用石子擊中而失明,體檢未能過關,破滅了他當一名海軍軍官的夢想。在以后的人生中,他始終被失去另一只眼睛的焦慮所困擾,為自己的殘缺的視力而自卑。這讓他對擁有鋒利視野的鷹和各種飛鳥充滿欽羨。他曾在一首詩里有這樣的自白:“從童年以來,我就有驚人的欲望/要見識世界,尤其是/獲得關于北美洲鳥類的知識。”(《奧都本:一個幻象》)
讓我們先來看看沃倫的《夜之鷹》。在這首詩中,他從描摹鷹的振翅飛升開始,口吻相當冷靜。沃倫意欲在對鷹的動作的持續捕捉中,彰顯鷹所攜帶的精神羽翼。他把鷹置于一個相對“形而上”的環境中,比如用幾何學詞匯去界定環境。這樣,處于此環境中的鷹也就虛實兼具,從而就有了充沛的哲思感覺。你必須集中精力去面對它,就像在思考嚴肅命題——讀者一開始就被提醒,它并非一只普通的鷹。詩人寫道,鷹在黃昏時分如何乘著大氣向上飛升:
從光的平面到平面,雙翅潛穿
落日建造的幾何學與蘭花,
逃脫于山峰黑色棱角的陰影,騎乘著
最后一次混亂中的光之雪崩
在松林和喘氣的峽谷上,
鷹來了。
由“黑色棱角的陰影”,到“光之雪崩”,再到“他在最后一道光線上攀爬”。一首詩下來,鷹完成了對黑暗的逃逸和對光明的追尋。正如批評家肯尼斯·伯克所言,“一首詩就是一次象征行動。”把這些句子僅理解為語義的表達是不夠的;不如說它們本質上應被當作行動模式看待,而我們作為讀者可以讓其重演。所以,閱讀這首詩相當于跟隨著鷹開啟一趟飛行之旅。讀者也仿佛在歷經艱難的爬升后,像鷹一樣,斬獲內在的精神力量。換句話說,我們也搖身一變,成為那只振翅的鷹。如果回看英語原文,鷹飛升的艱辛則更為顯著。沃倫的詩用詞通俗,但語法緊湊。上引整節的英文實際上是一個句子:其中,主句就是末行簡單的“鷹來了”(The hawk comes),但之前五行都是由介詞短語、動名詞等組成的狀語成分。閱讀時,這些修飾成分會先在口腔中產生漫長的回響,從而延宕了主句鷹的出現。主句代表的主角登臨舞臺之前,表示動作的從句有五行之多。它們是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如起跑之前的熱身活動,為正賽蓄足勢能。
對詩的效果是如何產生的稍做分析,便見沃倫的語言功力。《夜之鷹》與那些直接象征的詩是截然不同的,就像指著玫瑰上來就告知你它代表“愛情”,實在過于膚淺。這方面沃倫富于耐心,攜同讀者去體驗逃逸和找尋的過程。而讀者與之隨行,才真正領會行動者的初衷。其中的道理簡單而深刻:與其對一個人喋喋不休傾訴自己有多辛苦,不如帶他一起工作一天來得有效。以過程之詩去構筑起鷹的形象和精神,反映了詩人對詩歌共情倫理的重視。這種詩學擁抱開放,與晦澀、纏繞的現代主義大異其趣。詩人目睹過工業革命后美國城市的繁華與喧雜,南方郊區的經驗為他提供了對比,使他看到人性的封閉。在此意義上,他是雪萊所說的那種“喚醒人心并且擴大人心的領域”的詩人。他讓我們看到,詩依然能對人心發揮作用,閃爍引領性的倫理光芒。
1930年,沃倫參與發表《我將堅持我的立場:南方和農業傳統》,表達了他反對工業化社會的立場,和捍衛南方重農主義傳統價值的決心。彼時北國美方正如菲茨杰拉德筆下描寫的那樣急劇發展,工業煙筒晝夜冒煙,資本興奮不已。沃倫等人的重農主張,是對北方社會工業化帶來的一系列沖擊的回應。他們抵制工業化對人的異化,強調家庭、傳統以及“人的完整性”,在文學中堅持探索生命和人性問題。資本主義對人性的傷害是沃倫的重要主題。他在一首名為《美國肖像:老式風格》的詩中曾為沉迷于“美國夢”的人畫像:“總是滔滔不絕談錢的奇怪之人——他們禮貌地微笑,但總是沉默寡言。”在《夜之鷹》的后半部分,沃倫通過某種殘缺和完整的對比,進一步確認他心中的人性理想。詩人寫道,在時間的“根莖”上,“盛滿了我們錯誤的金幣”;而鷹“對時間和錯誤一無所知”。“我們錯誤的金幣”(the gold of our error),蘊含巧妙的反諷,暗示了人被金錢霸占后的心靈圖景。而鷹對它們的“無知”反而是一種另類的品質:它不僅“不知道”錯誤和時間,而且超越了錯誤和時間。也就是說,錯誤和時間在鷹那里無足輕重。
說鷹“對時間和錯誤一無所知”(Who knows neither Time nor error),把(金幣的)錯誤和時間并置,相當于在兩者之間劃上了聯系。沃倫對時間的道德判斷背后,關乎工業社會里的時間性質。如果說鐘表的出現代表自然時間式微,工業社會時間誕生,那這種時間主要以數字來計量。它以穩定的抽象性抹去差異而維持權威,任何事物只能蜷居其中。我們每天難道不是盯著鐘表的指針,看其臉盤行事。于是,人的主動性被鐘表時間容器所監禁。而沃倫有意對這種時間發起挑戰。《夜之鷹》最后,鷹爬升至最高點時,雙翅磅礴地拍擊,宛如莊子《逍遙游》中的“大鵬”。如果說大鵬以巨幅的雙翅攪動天地,那夜鷹的翅膀則磨出了超現實的、驚人的鋒利。它不切割具象的東西,它切割的恰恰是抽象的時間:
他的翅膀
切割掉另一天,他的移動
是鋼刃打磨過的長鐮,我們聽見
時間之莖在無聲中墜落。
詩人把鷹的雙翅比作長鐮,讓時間好似長莖的植物。長鐮割倒莖稈,鷹翅割倒時間。或者說,鷹使時間失效。通過比喻,詩人以相對具體事物傳達對時間的思考。被鷹割掉的正是冰冷的現代時間,對它的克服代表鷹所象征的心靈力量對生存境遇的超越。值得一提的是,沃倫這種思辨時間的方式相當常見,比如“二重性纏繞在時間中,就像/水牛般粗的蛇纏繞在長葉的秋天”(《時間的二重性》),“時間,像被風吹破的煙”(《樹蔭里是安全的》)等。
批評家柳向陽曾借用中世紀神學家奧古斯丁對時間的闡述,指出沃倫詩中的時間是一種主觀的、心理的時間。但實際上,理解沃倫對平面、勻質化的現代性的沖擊,從時間和空間的雙重維度去看更為全面。而鷹幾乎擔當了發起沖擊的先鋒角色,提供持續的核心動力。它逃離空間的限制,還使時間變形;詩人借鷹的形象斬斷現世鎖鏈。在另一首驚心動魄的《致命的極限》中,主角同樣是在懷俄明上空飛旋的鷹。重重飛越中,鷹穿過黑暗的松林和尖哨,越過昏冥,抵達雪光之上,一個鴻蒙似的境界。那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于是在詩人對鷹的提問中,答案顯現:
陷入黑暗的側影,侵亂星座。此刻在何種高度之上
懸掛著黑點?超越何種范疇,金色雙眼才能看到
新的范疇觸及那最后一筆光的涂寫?
星座的紊亂只是超克空間的前兆。當鷹抵達某個臨界點后,新的范疇出現,新的空間來臨。也就是說,鷹的行動造就了空間本身的變形。行動帶來改變。它讓我們想起那個單純而艱難的愿望:不讓環境改變鷹,而是鷹可以改變環境。某種意義上,沃倫展現了一種華萊士·史蒂文斯式的“朝向最高虛構”的努力,以想象力的行動改變既有秩序。詩如果信奉想象力,它能沖破日常經驗和邏輯框定的空間,奔向未知范疇。沃倫的鷹之沖擊就是一種語言對秩序的創造,背后閃爍著人類心靈的光暈。詩人想告訴我們:憑借鷹一般的不懈飛升,人可以重獲完整。沃倫詩中的鷹都具備改變環境的“特異功能”。它們意志強大,不受晦暗世界的敗壞:
禿鷹。大氣中多么美!——雕刻出
緩慢、凝聚、下沉的漩渦圖案,閃爍的翼在
閃爍的翼上。
——《地里的死馬》
巨鳥,
伸展長勁,雙翅扇動氣流,宛如
移動的慢書,宛如轉動的曲柄
——《奧都本:一個幻象》
或雕刻大氣,或減緩氣流,有種厚積薄發之感。閱讀上引的這些片段,鷹無疑帶給我們心靈以力量。而“鷹”作為一個核心形象,其精神氣質也擴散并衍生到其他鳥類,如野鵝、貓頭鷹、松鴉等。沃倫是詩人,也是鳥類觀察家。他詩中不管是哪種鳥,都帶著決心、能量和崇高感覺。
布魯姆在評價沃倫時,將他與品達、葉芝等強力詩人放在了“崇高”一派的譜系上。布魯姆認為:“在他長期的重要階段,沃倫與詩之崇高的天使角力,帶走一個新名字的勝利。”布魯姆那里,“崇高”是與日常庸俗拉開距離的。它代表著一種超功利的追求——人有意識地從瑣碎的世俗生活中掙脫出來,為自己的心靈賦形。而崇高的文學,需要的是情感的投入而非經濟的保障。在這點上,同為好友的布魯姆和沃倫心有戚戚,他們都堅持,一首崇高的詩能使讀者得到提升。然而崇高絕非像唱歌贊美詩或布道那樣看起來輕易。正所謂,美好的東西總是伴隨著驚恐,崇高事物的復雜性就在于它不是單維的。崇高所蘊含著多重性的體驗,布魯姆說:“崇高事物的偉大同時引發歡欣和恐怖……崇高的體驗就是痛苦和歡愉悖論性的結合。”布魯姆之真誠,不亞于一位苦口婆心的導師。而我們確實既要憧憬那在精神花灑下的沐浴,也得準備好戰栗。沃倫的其他一些鷹之詩中,多重性的崇高感就在敏銳而激烈地沖刷。沃倫借鷹或其他鳥類,把這些時刻完全捕捉并重塑。其能量的爆發依舊,但精神內涵更加復雜。閱讀某些如有神啟的片段,仿佛在那罕有的瞬間,諸種電流向心靈沖擊而來。從中,我們感受到寬恕如海,或猛擊如箭。它們本質上反映著人與世界相遇時,心靈對尊嚴的渴望:
帶著折疊之足,在喧囂的真空里追蹤,
我的心受到尖銳的猛擊
觸及無言的話語——
臨近日落,在極限的高處。
——《秋天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