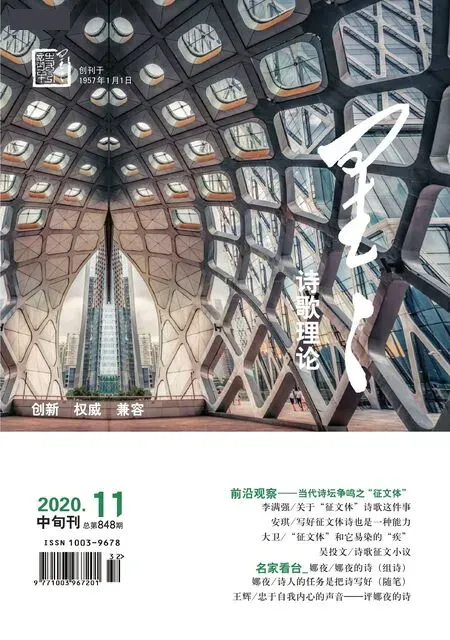詩是人類的母語
眾所周知,文化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任何人企望給它下一個嚴格和精確的定義都是一件難乎其難的事情。古往今來,不少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有過種種努力,嘗試著利用各自學科的優勢來界定文化的概念。據說,有關“文化”的各種不同的定義至少有二百多種。遺憾的是,人們迄今似乎仍然沒有獲得一個完全公認的、令人滿意的定義。一般而論,文化通常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傳承、地理環境、語言交流、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諸種。
就上述情況來看,文化實際與人和人性有關,也就是說,文化是人類這種動物獨有的。那么,文化是什么呢?這樣的問題通常是眾說紛紜的,如同追問“人是什么”?我們很難對“人”下一個準確無誤的定義,但我們絕不會因此而將猿猴當做人,論及文化,實際也是同理。
必須承認,在文化層面上,詩歌應該是一個高端性的存在。判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質地,詩歌絕對是一塊屢試不爽的試金石。可舉一例的是,俄羅斯之所以為全世界矚目,并不是它的軍事實力,不是它的核武器,不是它強大的海軍或空軍;而是它的文學,那指向詩歌的語言藝術,是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瑪托娃、曼杰施塔姆、布羅茨基等留下的精神財富,他們以自己創造性的文化行為替自己的民族贏得了崇高的榮譽。經驗告訴我們,武力讓人恐懼,而文化則受人尊敬。在詩歌中,有著人的自由、獨立、尊嚴和普世的善與美。一個沒有詩歌的民族很難說是一個具有高質文化的民族。
人類的精神發展史證明:詩,是人類真正的母語。這句話意指的是,詩與語言實際是同步誕生的,或者說,詩甚至要早于語言而孕育。當初民最早萌生了發言的沖動,實際是被內心詩意的洪流攪動到了一個逼近決堤的狀態。因此,所謂的“太初有道”,這“道”所倚重的乃是“太初有言”。當人的內心有情感的需要,有對美的向往,也就有了表達的愿望,要找到一個突破口。于是,語言產生了,它以恰切的方式為詩歌這種靈魂中的靈魂找到了一個可以棲居的家。世界則在“言”中重塑了另一個世界,這便是詩的魅力。這樣,我們在回眸中發現,上帝造人之后,人類又為自己創造了另一個奇跡——詩。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說,詩人在塵世的使命便是完成上帝未完成的事業,讓不完滿的人性向完滿的方向前進。詩,在語言的屋頂下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可以棲居的家。對此,我們從世界各民族任何一種語言中都存在著大量的詩歌文本這一事實便可以獲得印證。
當然,詩歌在任何時代都不是所謂的“主流”(顯性),但同時在任何時代也不會成為“支流”(隱性)。盡管有不少人認為它處在邊緣、沒落什么的。李白、杜甫在他們的時代都沒有獲得世俗意義的榮華富貴和大眾目光的高度關注,但他們的寫作在未來,亦即他們的身后贏得了大多數。
從中國文化的傳承來看,詩在很多時候都體現著一個為自由而來,逐漸向自由趨近的語言行為。詩,作為美的象征,已被中國詩歌史的發展所證實。中國的先民們最早以“斷竹,續竹,飛土,逐宍”的描述,“候人兮猗”的表白,奠定了詩的基礎。其后,它逐漸定格為四言、六言;接著,在漢代,又以自如、舒展為旨歸,發展為“五言”“七言”的“律”“絕”,于唐代大放異彩,殆至有宋一代,再蛻變為詞曲的“長短句”式的詠嘆;最終,中國詩歌脫掉了平仄、尾韻的束縛之后,以極為自由的形態來展現。人生而自由,自由是精神向往永遠的目標。“五四”以降,新詩(或現代詩)的寫作,已成了現代社會中的文學樣式中不可回頭的選擇。現代詩人為現代漢語鋪展了一條“裸體的瑪哈”式的純真道路,美在脫去一切衣衫后,贏得了名副其實的掌聲,并以實驗的方式為在漢語中生存的中國人洞開了一個新的精神空間。
人性的變化自然會導致詩歌形態的變化;不過,形態的變化反過來又會產生新的推動。在西方文學史上,王爾德的“讓生活模仿藝術”曾經廣受詬病,但實際說出了藝術和詩歌最根本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詩歌或藝術的存在,為未來的生活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模式。當代文化愈來愈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詩歌智慧也因著這變化呈現出多種變體。最明顯的例子是,文學與藝術之間的相互滲透,文體的模糊化,語言的龐雜。此外,詩歌的智慧已不再僅僅局限和蝸居于傳統的分行排列的文字中,而是滲透到了我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小說、散文、美術、電影、建筑,甚至最近出現的一些微博、微信等形式中展示了更多的表現可能性。由于詩歌智慧的存在,我們發現,甚至連廣告詞也不再僵硬,而顯現出人性柔軟的一面。海德格爾的名言“詩意地棲居”,便是由形而上的表述轉化成廣告的一個例子。另外,廣告商對海子的詩句“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襲用更是廣為人知。當然,坊間也出現了專為廣告撰寫的詩性表述。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平時注入一滴水,難時擁有太平洋。”“不要讓我們的眼淚成為大地上的最后一滴水。”前者是太平洋保險公司的一則廣告,后者是節水、環保的公益性廣告,它們都滲透了極強的詩歌智慧,其中有著廣闊的想象空間和大悲憫的情懷。再有某旅行社曾發布過這樣的宣傳廣告:“海到天邊云是岸,山登絕頂我為峰。”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找到了一個極佳的銜接點。
粗略地概括一下,詩歌智慧的當代轉型主要體現為四個方面:感受力的敏銳、洞察力的深入、想象力的豐富和創造力的擴大,上面那些例子無疑都不同程度地印證著這一點。套用一個當下時髦的詞,它們都是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正能量。詩歌智慧的當代轉型甚至還游走在領導藝術中。對于現代化的管理人員而言,它不僅是情操上的陶冶、審美上的愉悅,更是一種思維上的啟迪。比如:想象力與領導決策、整體思維與全局觀念、節奏與工作步驟、“詩眼”與工作重心,等等,都有很多話題可以展開。于此,我們可以發現,詩歌智慧已不再停留于文字的分行中,也不僅流動于節奏與韻腳之間,更是遍布于我們的生活各個角落,或顯在或潛在地影響著人類的生存。
對此,我想說,這是一個詩歌的“烏鴉時代”,但同時也是一個新詩的“詩經”時代。
如果說十九世紀上半葉以前是我們詩歌的“夜鶯時代”,那么,自從愛倫·坡的《烏鴉》在暗夜里發出的“永不再”(nevermore)的宣告,世界的詩歌已進入了烏鴉的時代。烏鴉向來被當作不祥、兇險的象征。相傳,烏鴉的血可以擦亮人們的眼睛,得知這一點,我們的詩人大概可以得到少許的慰藉,或許,由于他們的存在,人們可以看清被世俗生活所蒙蔽了的真實。另外,鳥類學家告訴我們,烏鴉具有不少優點,譬如:雜食性,忠誠,反哺。與之相對照,現代詩似乎同樣具備這些特性,首先,它有一個強健的“胃”,就內容而言,舉凡生活的方方面面,詩人們都敢于吸納進來,在形式上,敘事性、戲劇性、口語等因素作為亞體裁紛紛出現,詩歌越來越體現出某些綜合性的特征;其次,新時期以來,詩人們在自己的領域里孜孜不倦探索著漢語言的藝術,其作出的貢獻可以說超過了任何一種其它文體;至于說到反哺,青年詩人調整了相當部分老一代詩人的詩歌觀念,并且還為后者的寫作提供新的藝術經驗,也是屢見不鮮的事情。在這樣一個時代,詩人被賦予了新的使命,他必須持有批判的立場,對社會行使類似先知的責任,以現代意識來觀照世界,甚至具備一定的預知能力,而不是相反。試想,生活在二十一世紀,倘若仍然套用十九世紀的詩歌觀念來衡量當下的創作,無異于拿著牛鞭抽打著火車。
行文至此,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詩并未遠離我們,而是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間。另外,中國詩人在建設現代詩的過程中,實際承擔的是兩個任務,其一是完善和豐富現代漢語;其二是在未完全成熟的現代漢語中就現代詩的詩藝進行內部探索。這就是說,目前的中國新詩實際正處在一個“詩經”的時代。坦率地說,就詩歌藝術而言,《詩經》所收納的305首作品,盡管曾經孔老夫子的甄別和刪削,卻絕非每篇俱是佳作。剔除《關雎》《靜女》《蒹葭》《鶴鳴》《遵大路》等十余首,其余大多為歷史價值大于藝術價值的作品。即便如此,《詩經》仍然是中國古典詩歌一個偉大的開始,如果沒有這樣的開始,期望出現唐詩、宋詞那樣的繁榮是不可想象的。中國新詩由文言轉向白話文不過百年的歷史,已經積累了不少堪輿評說的成果,同時也毋庸諱言,它迄今還存在著諸多的不成熟。但是,我認為,這種種的“不成熟”恰恰為這個同樣偉大的開始從另一側面作出了確鑿的證明。如果在未來的某一天,中國新詩進抵繁榮的“唐詩”時代,它必須感謝今天從事新詩寫作的每一位“詩經”時代的作者。
詩歌的意義就蘊藏于人性,只要有人類存在,自然就有人性以及人性的自我完善。人性在,詩歌智慧就不滅,詩歌也永遠不可能死亡,哪怕它出現了當代的轉型,它的形式出現了巨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