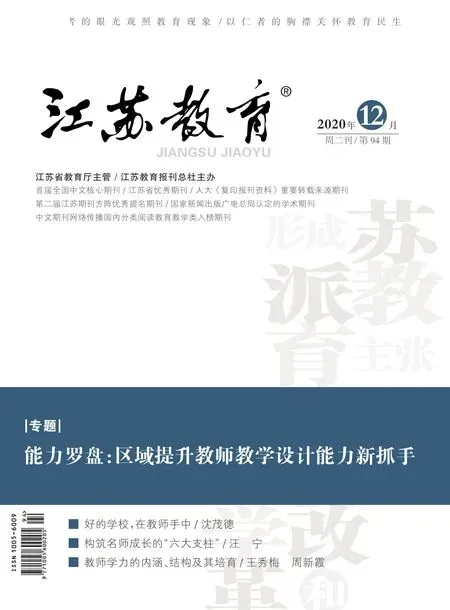涵養“設計智慧”:教師教學設計能力的“深度”跨越
呂林海
教學設計的理論知識體系是一個西方舶來品。從美國教育家杜威提出“聯系科學”開始,經由加涅、布里格斯、梅里爾等學者的深化與拓展,以及近來與計算機科學、學習科學等的彼此聯姻與嫁接,“教學設計理論”已經變得既相當成熟,也更加多元[1]。說其成熟,是指其有著比較公認的設計模塊、設計范式(特別是如ADDIE 模型,基本成了所有變式的基礎性模型);說其多元,既是指其取向的多元(如理性設計取向或創造性設計取向),更是指其方法的多元(如各種教學設計的變化性方法)。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教學設計理論走入中國教育實踐大地之后,有一種豐富性和復雜性被遮蔽的可能風險。在理性與藝術、技術與創造、共識與個性之對峙中,中國的學校教育可能更加接受“前者”,對“后者”的不經意忽視有可能消解“教學設計”背后豐富的“人性意蘊”和“教育意蘊”。具體地,教學設計的技術化、流程化特質被抬高,其固定的程式被突出地強調,教學設計活動更傾向于被定位為一種“剔除了”特定的人、特定的場景、特定的細節后的一種“工廠性流程”。應當看到,工業化時代的效率特征,無疑是“設計活動”的原初意向,但“教學設計”不同于“工業設計”的獨特性在于,其對象不是無生命的產品,而是有著獨特生命體驗的人。人的成長的評判邏輯不全是“效率計算”,也包含更多的“個性考量”。“個性考量”意味著對教學與學習中的獨特個體、獨特情境、獨特細節、獨特機遇的洞察、理解、審查、把握乃至創造。教學設計,從最深刻的意義上說,其實是一種設計者“設計智慧”的全面展現。本文將基于南京市雨花臺區的教師教學設計“能力羅盤”的研究項目之解析,從工具與實踐、理性與智慧、規則與創新的辯證角度,探究教師教學設計能力的深層意蘊、核心要素和未來培養,以望對中國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的提升貢獻些許啟示。
一、設計智慧:教師教學設計能力的關鍵成分
經由一種科技理性的孕育,現代教學設計理論越發體現為一種系統化的理論范式。通過運用傳播學理論、系統思維理論以及行為主義理論,現代教學設計更強調教學活動的各要素之間的協同性、體系性和可控制性,并特別地追求“教學的更有效、更高效、更具相關性”[2]。由此,這一“現代性”理念的集中性體現就是赫赫有名的ADDIE 模型,即分析、設計、開發、實施和評價的五要素模型。無論后續的教學設計研究如何對這五個要素進行“變式性的開發和轉換”,但追求一種程序性、順序性、工具性的“通用性”教學模板的特質明晰可見。
對教育的設計活動進行一種“共識性抽象”是人類的一種理性建構行為,其目的是找到一種普遍的、廣泛的、抽象的規律,進而構建出可傳播、可遷移、可發展的教學設計理論。但與此同時,我們越發地感受到,教學設計的理論研究者和實踐探索者,似乎對追求更普適、更抽象的“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型”以及“具體設計規程”特別癡迷,而對教學活動現場的個性化智慧、個別化應對則相對看輕,他們甚至還會認為,“現場的智慧”是個別的、臨時的,與“抽象的體系”相比,它們無法構成真正的“教學設計知識”。
筆者認為,上述的這樣一種對“普遍性”教學設計理論的追求以及對“特殊性”教學設計智慧的忽視,我們對其需要加以深刻的反思和警惕。實質上,對“普遍性”的理論性知識的偏愛深深扎根在人類早期對知識的劃分活動中[3]。眾所周知,亞里士多德將知識分為三類:1.episteme(理論知識或科學知識);2.phronesis(實踐智慧、實踐知識或明智、審慎);3.techne(技藝、技能或生產的知識、制作的知識)。在西方知識傳統中,真正起主導作用的知識是episteme,因為它關注的是不變的東西,它追究的是第一原因,它需要通過沉思來達到;與之相對,人的行動屬于可變事物的范疇,它關注的是人的行動,它需要通過類似“權衡”這樣的實踐智慧來生成,它產生的知識就是phronesis 和techne。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理論活動高于實踐活動,沉思的生活高于具體權衡的行動。
西方理性知識觀傳統其實對教學設計理論的影響是深刻的,它似乎僭越了設計活動的“實踐智慧”特質,而過分彰顯了一種設計理論的“理性認識”內涵。由此,開發出一種普適性的教學設計框架,生成一種普遍性的教學設計共識,進而去“科學化、技術化”地應用這一“框架”和“共識”,越發成了教學設計者的“標準行動方式”。在這一思路下,特殊的、個別的、情境的實踐,以及變動的、權衡的、行動的智慧,似乎是從屬性的、非重要的存在。
其實,我們應當特別重視“教學設計”的“活動/行動”之“實踐智慧”本質。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理性的知識追求的是正確的知識(true knowledge),但行動的知識追求的是正當的知識(right knowledge)。教學設計是一種“設計活動”,它追求的是“行動的本性”,即如何運用正確的設計知識,去做正當的設計。由此,正是在有關“設計的普遍性的東西”(即體現為“正確的知識”)和“設計的特殊性的東西”(即體現為“正當的訴求”)之聯結中,“實踐智慧”出場了。“實踐智慧”是一種教學設計中的權衡。權衡指向的是一種“可變的事物”,如變化的知識、變化的教學場景、變化的學生、變化的評價要求等。教師在教學設計中需要“權衡”,就是因為“權衡的對象”是可變的,它們不能被還原為一個精確的體系。由此,教學設計中的設計行動是無法被歸結為一套精確規則的,它具有某種不確定性,它需要教師在聯結普遍知識(理性的、正確的、系統化的教學設計知識)和特殊情境(具體的、可變的教學情境)的過程中去“計算”“衡量”和“判斷”,去運用更多的“自由裁量的成分”(discretionary component),去實現“正當的知識訴求”。
正是基于上述的考慮,筆者認為,亞里士多德曾經從法律的角度所給出的例證與說明,恰與“教學設計”構成了一個極佳的類比。亞里士多德認為,公道(equity)高于法律的正義(legal justice)。法律總是普遍的,但是,人的行動總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發生的,因此,總是有些情況是普遍的法律所無法覆蓋的,在這種情況下,法律需要公道的修正。由此可見,普遍性需要在特殊性的情境下做出修正和裁剪,使普遍性獲得一種公正的裁決。轉向教學設計,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教學設計的普適性框架是一種描述性話語或是一種正義的體系,但一個真正的教師所需要的則是在特定的教學情境中去“權衡”,去把“普遍的正義體系”和“具體的特定修正”聯系起來,讓“正義的設計框架”展示出一種“公道的實踐效果”,即讓“正確”與“正當”真正地聯系起來。很顯然,這種“聯系”所需要的,恰恰是一種“教學設計的實踐智慧”。
二、設計智慧的兩個特質:判斷力和模糊性規則應用
緊接著上文有關“設計智慧”必要性的論述,一個后續的追問自然產生,即,這種教學設計的“設計智慧”究竟表現出什么樣的特征?其內涵究竟如何?本文試圖從兩個角度來進行解析,一是“教學的判斷力”,二是“教學的模糊性規則應用”。當然,筆者選擇這兩個角度并非是統攝性的,而只是擇其要義、管中窺豹地展示“教學設計智慧”所具備的情境性、個別化、變化性之特質。
“設計智慧”首先蘊藏著一種有關教學的“判斷力”。教學設計的目的是理解并解決教學情境中的問題,這必然涉及思維活動中的“判斷”。所謂“判斷”,就是把教學活動中的特定現象放置在自身的認知框架中,并給出某種帶有普遍性的論斷。這里的“普遍性”,其實蘊含了一種科學性或主體間性,即它不能指向于一種個體隨意或主觀的論斷,而是力圖使自己的“教學判斷”得到“他者”的認可,從而體現出某種一般性、科學性。德國近代哲學家康德指出,“判斷”涉及主體一種獨特的能力——趣味(taste)。“趣味”有兩種:一種是感官的趣味,它是私人性的;另一種是反思的趣味,它是一般性的、公共性的。很顯然,教學設計中的“判斷”所體現的就是一種“反思的趣味”,它要求設計者所構建的設計不能是“自身的隨意的判斷”,而應該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普遍性。進一步地,對這種公共指向性的“反思的趣味”,并無一套明確規則來進行描述和規范,它需要的是主體的一種“判斷的智慧”。正如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一書中深刻地指出的,“不存在關于趣味的客觀規則”。這就是說,教師在教學設計中的“趣味性的判斷”是無法用一套類似于ADDIE 的教學設計規則來進行描述的或規定的,它需要教師直接面對對象,通過反思自己的認識能力,來做出“合目的性”的判斷。由此,教師自己的“認識能力”顯然就成了進行“趣味性的判斷”的關鍵基礎和要素。如何提升自己的“認識能力”,從而提升自己的“判斷的趣味”呢?康德認為,關鍵在于對“范例”的習得。“范例”是一種典范,是共同體所共同認可的經典樣例,也就是那種“在文化緊張中保持了最長久贊同的東西”。“范例”體現了人們之間(或者說“共同體”)所具有的一種共通感,這種“共通感”也是“范例有效性”(exemplary validity)的根本保證。正如康德所說:“因此,我在這里把我的趣味判斷說成是共通感的判斷的一個例子,因為賦予它范例性的有效性時,共通感就是一個理想的標準,在它的前提下人們可以正當地使一個與之協調一致的判斷及在其中表達出來的對某個對象的愉悅成為每一個人的規則。”[4]由此可見,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的提高,仰賴于去學習久為流傳的經典“教學設計范例”,并以此來涵養“共通感”,從而真正學會“寄生在”范例上的所謂“規則”。也正如康德深刻地表明的,“通過范例進行學習,意味著從范例的先行者本人所曾汲取過的同一個源泉中汲取,并且從他那里學會如何這么做”,只有在“大師的”范例中,才能展示出“應該創作什么以及如何創作”[5]。
“設計智慧”還體現出一種“模糊性規則應用”的特質。當我們在看待“教學設計”的體系時,我們不能將其看作一套“嚴格的規則”,而應將其看作是一套“模糊的規則”。所謂“嚴格的規則”(strict rules),就是類似于“乘法表”那樣的不給人留有解釋余地的規則;而模糊的規則(vague rules),就是類似于“技藝規則”那樣的給個人的判斷力留有很大空間的規則。即使是如“科學工作”,我們也可以看到,那些有關實驗、測量、計算、制作圖標等活動,雖然屬于嚴格的規則之范疇,且它們有助于又快、又精確地完成科學的操作活動,但這些規則其實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真正的科學,其實是那些具有原創意味的啟發性工作(heuristic work),如科學的發現以及對發現的證實或證偽。這些工作需要的是一套模糊性的規則,對這些規則的理解、感悟和應用,最終取決于科學家個人的判斷力。哲學家波蘭尼說:“科學探究的規則使其處于充分開放的狀態之中,讓它由科學家的判斷力來決定。這是它的主要作用。它包括發現一個好的問題,提出各種猜想來研究問題,以及確認一個解決問題的發現。”[6]其實,教學設計活動與科學發現活動一樣,需要主體把設計規則看作“模糊的規則”,看作對解決現實教學問題的一個啟發式框架。真正的高水平的教學設計者所擁有的精湛高超的技藝是不能完全被程式化、機械化、自動化的。實質上,無論是中國古典典籍《莊子·天道》中的“斫輪”之“不疾不徐”,還是西方古典典籍《尼各馬可倫理學》中的“道德”之“中道原則”,其實都表達了一個“共同性”的關鍵要義,即,實踐智慧本質上是一種對“模糊性規則”的“概要性運用”,而非“實質性規則”的“機械性應用”。總之,在主體與情境的對話關系中,教學設計的主體其實不斷地對“明晰的規則”進行解釋甚至改變,在這個過程中,設計者其實是把具體的教學情境看作是更具決定性的因素,把情境性的解釋和應用性的理解看作是優秀教學設計者的關鍵素養。
三、設計智慧的養成:走向真實的實踐參與
行文至此,一個新的追問自然會從讀者和筆者的內心涌出,即如何培養教師上述的“設計智慧”,如何真正實現教師教學設計能力的“深度”跨越?本文試圖從觀念、方法和制度三個方面略做解析。
首先,要從更加廣闊的視角認識“教學設計”。對于“教學設計”的理解,通常存在著“理性觀”和“創造觀”之兩種取向。“理性觀”強調的是設計的系統化、規則化、科學化,“創造觀”則強調設計的直覺性、藝術性、創新性。如果從“設計智慧”的涵養視角來看,“創造觀”其實是“教學設計”的更本質之存在。在西方的教學設計理論家們看來,教學設計活動不能僅僅被理解為一個“堅硬的工程化過程”,而應該更加體現為一種“柔軟的”理解過程、對話過程、修正過程、循環過程。教學設計者是在與情境的對話中不斷反思,在反思中去嘗試提出獨特的解決方案,在實驗中去測試理論模型。所以,我們應當深切地認識到,“設計既有理性的因素,也包含藝術的、創造性的因素,或者說理性與藝術、邏輯與創造的彼此結合,完整而準確地詮釋了設計的本質”[7]。我國著名教學設計理論家烏美娜教授也明晰地指出:“設計的本質在于決策、問題求解和創造。教學設計正是一種教學問題求解,它不是去發現客觀存在的、還不曾為人所知的教學規律,而是要運用已知的教學規律去創造性地解決新的教學問題。”[8]筆者認為,烏教授所提出的“創造性地解決新的教學問題”之觀點,其實已經清晰地點出了教學設計的“智慧性本質”,表明了一種更加深刻、更加準確的“教學設計觀”。
第二,要通過“真實的實踐參與”去涵養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前文的分析表明,“教學設計能力”幾乎可以劃歸為一種名為“設計智慧”的素質,它是一種判斷力,是一種“對規則的模糊性應用”或“對模糊規則的應用”。無論如何,教學設計能力是一種附著在設計者身上的“知如何”(know how)的知識,而不能被轉化成一個可明言的“知什么”(know what)的知識。用波蘭尼的話說,教學設計的能力是一種“親知”“具身性知識”,它是一種無法明言的體驗性知識、經驗化知識。正是因為教學設計能力不能被轉化為一套明確的教學設計規程或流程,而是一種默會的經驗、感知、體驗,所以,讓教師“參與到真實的教學設計活動”中,才是涵養“設計智慧”的正途。筆者建議,新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的習得過程,應體現為一種“邊緣化的合法參與過程”。“邊緣”意味著一種位于初始狀態的學習過程樣態,“合法”意味著一種共同體身份的賦予,“參與”意味著一種真實的活動方式。由此,新手教師從“新手”的邊緣身份出發,通過與優秀教師(如已經成為教研員的教師)的互動、跟隨、對話、討論,默會性地體悟、感受、內化優秀教師在教學設計中的判斷原則、要點找尋、方法使用、反思時機、改進策略等,用一種“親知性”的方式習得優秀教師的教學設計的“知如何”知識。不斷地累積就是不斷地學習,終會有一刻,量變產生質變,新手教師最終成為“像那個他所親知的優秀教師”一樣的優秀教學設計者。其實,上述的教師學習過程正體現了今天學習科學的學習本質觀,即“知與行是交互的——知識是情境化的,通過活動不斷向前發展。參與實踐促成了學習和理解,情境性在所有認知活動中都是根本性的”[9]。
第三,要通過一種整體性的制度設計來保證“設計智慧”的培養理念真正在教學實踐現場得以落實。其實,前文的分析幾乎表明了一種教師培養方式的顛覆式的構建。傳統的那種“講座+培訓”的教師發展方式所體現的是一種“知識獲得觀”“規則獲得觀”,這種方式顯然偏離于“設計智慧”的養成。與之相對應,“參與式實踐”則體現了一種“學習的參與隱喻”,它需要把教師“置于一種情境化的教學設計實踐”中,它需要教師的培訓現場就是“教師的教學設計現場與教學活動現場”,它需要教師的指導者“自身就能對教學設計實踐中出現的問題給出極具洞察力與實效性的設計方案”,它需要“教師指導者能向教師敞開自己的思想、洞見和智慧”,它需要“教師培訓現場成為一個極為開放、極為凌亂、有時又極具矛盾性的對話場、爭辯場、學習場”,上述所有的“需要”都必然性地意味著一種制度性的保證、落實和推進。筆者欣喜地發現,南京市雨花臺區的“能力羅盤”項目不僅體現了一種更加開放的教學設計觀、更具實踐參與性的教師發展觀,而且還通過“三教協進”(即教研員—教研組長—教師的共同進入)的行動推進制度和“三心融通”(教學研究中心—教師培訓中心—質量監測中心的整合融通)的管理支持制度,保障了這一體現“設計智慧”涵養的“教師教學設計能力發展項目”真正有效、有力的落實,并正不斷取得創新性的、有價值的實踐成果。筆者堅信,這一項目的系列成果的源源涌出,對于教學設計理論和實踐的深入發展將起到頗為有益的推動作用,并使更多的一線教師從中收獲“教學設計能力”的“深度”跨越式發展!
教學設計的設計學探究之深層推動因素
第一,隨著教學設計逐漸從系統設計范式向學習環境創設范式的轉變,設計活動本身的開放性、復雜性、情境性日益突顯出來,設計過程已經不像傳統的各種教學設計模型所共有的ADDIE 流程那樣簡單,有效的學習環境創設需要考察更多的設計變量、需要顧及更多的限制條件、需要反思更多的主體觀念,設計已不是一個流程的應用、規則的使用等簡單機械的行動,而承載了更多的復雜與變易之內涵。由此,對設計本身的探究就逐漸顯示出意義與價值,并漸至成了一個日益興起的研究主題。第二,隨著學習科學研究的崛起,基于設計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已成為學習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論,這是一種在設計活動過程中對介入性設計以及學習及教學理論同時進行精致與研究的方法,正因如此,“教學設計的設計活動本身的規律是什么?設計活動的機制是什么?”就自然成為學習科學研究者首先需要弄清的根本問題。
(摘編自呂林海《論教學設計的設計定位及其決策循環特征》,原載于《開放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