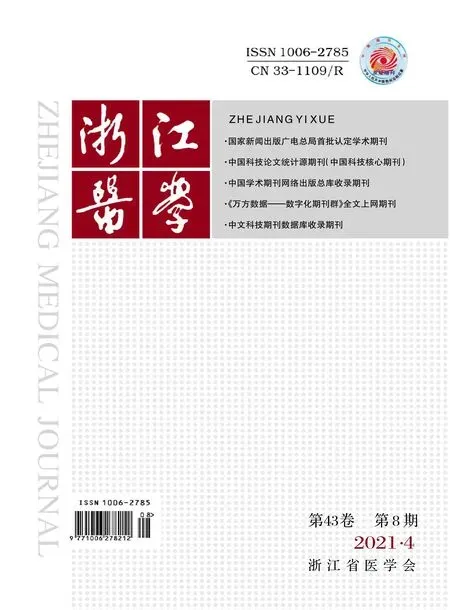放療聯合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相關肺炎研究進展
張邁 張衍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的出現極大地改善了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預后。目前,驅動基因陰性的晚期NSCLC患者二線接受單藥ICI治療的5年生存率可達16%,而在放化療時代,5年生存率只有不到10%[1-2]。雖然ICI單藥治療改善了預后,但有效率卻并不令人滿意[3]。放療作為重要的腫瘤局部治療手段之一,與ICI治療存在協同效應,這在ICI聯合放療的多個前瞻性Ⅱ/Ⅲ期臨床試驗中得到證實[4-6]。Ⅱ期臨床試驗PEMBRO-RT研究納入化療進展后的晚期NSCLC患者,結果顯示胸部立體定向放療(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聯合ICI治療對比ICI單藥治療進一步提高了治療有效率(36%比18%,P=0.07)[5]。但在改善療效的同時,胸部放療聯合ICI治療可能也會導致發生肺炎風險疊加,這增加了臨床醫生在實踐中應用這種聯合方案的擔憂。胸部放療聯合ICI治療是否會增加肺炎風險,目前存在爭議。本文總結了NSCLC胸部放療聯合ICI治療相關研究中發生肺炎的數據,就檢查點抑制劑相關肺炎(checkpoint inhibitor pneumonitis,CIP)、放射性肺損傷以及放療聯合ICI治療相關肺炎展開綜述。
1 CIP
ICI治療通過阻斷免疫抑制信號,增強抗腫瘤免疫反應以實現抗腫瘤的作用。但ICI治療同時可能引起免疫相關不良反應(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多數irAE是輕度且可逆的,少數irAE如CIP可能演變為重癥肺炎甚至危及生命。CIP通常表現為ICI治療后出現咳嗽、胸悶、呼吸困難等癥狀,伴有影像學肺部浸潤的表現。薈萃分析報道NSCLC患者單藥ICI治療CIP發生率約4%,≥3級CIP發生率約1%[7-8],而真實世界的數據表明CIP發生率可能高達19%[9]。不同ICI之間CIP發生率也略有差別,薈萃分析報道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death-1,PD-1)抑制劑 CIP 發生風險高于程序性死亡受體配體-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抑制劑(3.6% 比 1.3%,P=0.001)[8]。CIP 可出現在ICI治療后數小時至數月,其中位出現時間約2.1個月[10]。CIP是irAE的一種,其具體發病機制尚不明確。目前研究發現irAE有4種潛在發病機制:(1)靶向癌細胞的T細胞攻擊表達與癌細胞相同抗原的正常組織,引發irAE[11];(2)先前存在的自身抗體水平增加可能導致irAE[12];(3)細胞因子的水平升高與 irAE發生相關[13];(4)細胞毒T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CTLA-4)抑制劑與垂體細胞表達的CTLA-4結合可能誘發垂體炎[14]。研究發現有吸煙史、高齡(≥70歲)、合并間質性肺疾病等可能與CIP發生有關,而ICI聯合胸部放療、雙免疫聯合治療可能增加CIP發生的風險[15]。CIP的常見癥狀與普通肺炎相似,無特異性。CIP的影像學表現多樣,通常無特異性,主要分為5種亞型:(1)急性間質性肺炎;(2)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表現為彌漫性肺實變;(3)非特異性間質性肺炎,表現為外周肺的磨玻璃樣陰影和網狀陰影;(4)過敏性肺炎,表現為彌漫性磨玻璃陰影和小葉中心結節;(5)隱匿性肺炎,表現為雙側外周肺和下肺分布的多灶性實質實變[7,16]。CIP 的診斷標準包括:(1)有 ICI治療史;(2)新出現的呼吸系統癥狀或原有癥狀加重;(3)胸部CT表現為新發的肺實變或磨玻璃影等;(4)排除疾病進展、感染以及放射性肺炎等鑒別診斷。根據美國臨床腫瘤協會發布的CIP治療指南[17],1級CIP一般不需要干預和暫停ICI治療;2級CIP需要暫停ICI治療,口服潑尼松1~2 mg/(kg·d);3~4級CIP應永久停止ICI,靜脈給予甲潑尼龍1~2 mg/(kg·d)。如果2 d內病情沒有改善,應考慮加用額外的免疫制劑如英夫利昔單抗、環磷酰胺等。多數輕度CIP患者預后較好,但重度CIP患者預后不良。發生CIP恢復后能否再挑戰ICI治療是一個難題,有研究報道CIP患者再挑戰ICI治療CIP發生率約25%[7],目前再挑戰ICI治療還需謹慎對待。
2 放射性肺損傷
放射性肺損傷一般認為是由放療過程中產生的活性氧引起的DNA損傷和隨后的炎癥反應[18]。約10%~30%的接受胸部放療的肺癌或乳腺癌患者可能發生放射性肺炎(radiation pneumonitis,RP)[19],這部分患者可能會發展為晚期放射性肺纖維化(radiation-induced lung fibrosis,RILF)。RP和RILF分別被認為是放射性肺損傷的早期和晚期表現。RP癥狀無特異性,表現為咳嗽、咳痰等,重者可出現呼吸困難,典型RP影像特點為肺照射野內絮狀、斑片狀滲出。RILF一般由RP發展而來,表現為呼吸困難伴影像學肺纖維化的特征。放射性肺損傷發生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其發病機制可能包括:(1)放療通過DNA損傷及活性氧的產生引起Ⅰ型和Ⅱ型肺泡上皮細胞、血管內皮細胞等損傷,釋放細胞因子,如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TGF-β)、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IL等,進一步加重損傷。血管內皮細胞受到輻射后內皮細胞死亡,微血管通透性增加;Ⅱ型肺泡上皮細胞輻射后合成肺泡表面活性物質不足導致肺泡屏障作用減弱,繼而發生放射線肺炎炎性滲出改變[20-21]。(2)輻射后巨噬細胞、成纖維細胞、肺泡上皮細胞等釋放TNF、TGF-β、IL等細胞因子,細胞因子之間互相作用,激活信號通路,刺激成纖維細胞增殖轉化,促進晚期肺組織纖維化的發生[19-20]。研究發現肺平均劑量、肺V20、心臟照射劑量、肺基礎疾病、腫瘤體積和位置、化療藥物、TGF-β水平等是RP的危險因素[19,22]。RP主要的治療方式包括吸氧支持治療和糖皮質激素治療,但RILF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
3 放療聯合ICI治療相關肺炎
目前放療聯合ICI治療相關肺炎是否疊加尚無定論,但越來越多的文獻報道胸部放療和ICI聯合治療可能導致肺炎發生率增加。
3.1 發病機制和影響因素 胸部放療對腫瘤細胞DNA和其他細胞成分造成輻射誘導的損傷,隨后抗原呈遞細胞清除受損的腫瘤細胞,這也增加了抗原呈遞細胞對T細胞的活化。而ICI治療解除了CTLA-4和PD-1/PDL1等免疫抑制信號,進一步促進了T細胞的活化。釋放的活化T細胞則可能對正常組織造成損害。兩種治療的協同作用在放大抗腫瘤作用的同時也可能增加肺炎風險[23-24]。多項研究有助于揭示聯合治療后肺炎風險增加的潛在機制,例如Deng等[25]在放療聯合ICI的臨床前研究中觀察到TNF水平升高,而TNF在RP發生、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Naqash等[26]報道1例CIP患者的IL-6水平明顯升高。而IL-6水平升高是發生RP的危險因素[21]。另外,先前接受胸部放療的患者再接受化療、分子靶向和ICI治療時可能會誘導發生遲發型放射性肺炎,稱為放射性回憶性肺炎[27-29]。這說明接受過胸部放療的患者更有可能發生肺毒性反應,突出了放療在引發免疫應答中的作用。
一項研究發現接受過胸部放療發生CIP的患者中,肺炎主要發生在接受中等劑量和低劑量照射的肺部,而不是高劑量照射區域。該研究還分析既往胸部放療參數與CIP的關系,但未發現與CIP風險升高有關的放療參數[30]。放療參數與RP發生關系密切,提示聯合治療后發生的肺炎可能并不是一種特定的混合模式,而是RP、CIP或單純的RP疊加CIP。未來的研究需要直接比較單獨CIP、單獨RP以及RP+CIP患者的影像學特征以幫助臨床醫師鑒別。在PACIFIC研究中,同步放化療結束后14 d以內或晚于14 d開始PD-L1抑制劑度伐利尤單抗(durvalumab)維持治療,肺炎的發生率并未增加[31]。放療與ICI治療之間的時間間隔似乎不是一個危險因素。文獻報道發生過irAE的患者胸部放療后發生RP的風險明顯升高[32]。近期有研究發現一些血清學指標可能具有預測作用。Schoenfeld等[33]報道了1例晚期黑色素瘤接受放療聯合PD-1抑制劑納武利尤單抗(nivolumab)后發生肺炎的患者,發現血清CXC趨化因子受體2、IL-1受體拮抗劑和IL-2受體拮抗劑的水平增加與肺炎的發展相一致。Jing等[34]發現接受同步放化療聯合durvalumab治療的不可手術Ⅲ期NSCLC患者,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E選擇素、IL-6可溶性受體及干細胞因子等4種細胞因子與肺炎發生相關。
3.2 發病情況 薈萃分析報道晚期NSCLC患者接受ICI單藥治療CIP發生率約4%[7]。在ICI治療的基礎上引入放療可能會增加肺炎發生率。本文總結了放療聯合ICI治療NSCLC相關臨床試驗中肺炎的發病情況。
3.2.1 放療聯合CTLA-4抑制劑 放療聯合CTLA-4抑制劑治療在黑色素瘤、前列腺癌中已經顯示出良好的療效及耐受性,但應用在NSCLC患者的研究較少[35-36]。Chen等[37]比較了CTLA-4抑制劑伊匹木單抗(ipilimumab)聯合SBRT(17例)和PD-1抑制劑帕博利珠單抗(pembrolizumab)聯合SBRT(16例)在晚期 NSCLC患者中的療效與安全性。結果顯示SBRT聯合CTLA-4抑制劑組任意級別以及≥3級肺炎發生率分別為11.8%和5.9%,而SBRT聯合PD-1抑制劑組為31.3%和18.8%。兩組肺炎發生率差異較大,可能原因如下如下:(1)PD-1抑制劑導致CIP的風險本身高于CTLA-4抑制劑,既往研究結果也證明了這一結論[38];(2)該研究樣本量較少。關于結論的正確性仍需要在大樣本研究中進一步探索。
3.2.2 放療聯合PD-1/PD-L1抑制劑
3.2.2.1 治療早期NSCLC 立體定向消融放療(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SABR)主要在不可手術的早期NSCLC患者中發揮作用[39]。Chang等[40]展開的Ⅱ期試驗在早期不可手術的NSCLC患者中評估SABR聯合nivolumab治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對照組接受SABR治療。結果兩組≥2級肺炎發生率接近(4.4%比2.1%)。既往報道的SBRT治療早期NSCLC的研究中,≥2級肺炎發生率約6.7%[41]。因此,SABR聯合ICI治療并未明顯增加早期NSCLC患者發生肺炎的風險。
3.2.2.2 治療局部晚期NSCLC 一直以來,同步放化療(chemoradiotherapy,CRT)是不可切除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標準治療[42]。Ⅲ期PACIFIC研究結果證明CRT序貫durvalumab治療更具優勢,也確立了ICI鞏固治療在Ⅲ期NSCLC患者中的地位[4,43-44]。在PACIFIC研究中,CRT序貫durvalumab治療組任意級別和3/4級的肺炎發生率分別為33.9%和3.4%,CRT序貫安慰劑組分別為24.8%和2.6%,但該研究未報告肺炎數據的P值[44]。在另一項單臂Ⅱ期臨床試驗LUN14-179中,不可切除的NSCLC患者接受CRT序貫pembrolizumab治療,≥2級和≥3級肺炎發生率分別為17.2%和6.5%[45]。PACIFIC研究的亞組分析結果表明CRT后14 d以內開始durvalumab治療對比14 d以后開始治療可能獲益更大,同時早用durvalumab組并沒有觀察到肺毒性的增加,而且肺炎的發生時間對預后無明顯影響[31,43,46]。Ⅱ期DETERRED研究中,實驗組為CRT同步PD-L1抑制劑阿特珠單抗(atezolizumab)治療,對照組為CRT序貫atezolizumab治療。結果同步治療組肺炎發生率沒有明顯增加。同步治療組任意級別和≥3級肺炎發生率分別為23%和3%,序貫治療組分別為30%和0%[6]。Jabbour等[47]開展的Ⅰ期臨床研究將pembrolizumab治療與CRT同步,結果≥2級和≥3級肺炎發生率分別為26.1%和8.7%。此外,ETOP NICOLAS研究評估了nivolumab同步CRT治療的安全性,結果任意級別和≥3級肺炎發生率分別為42.5%和10%[48]。與歷史數據對比,CRT序貫pembrolizu-mab、CRT同步 pembrolizumab或 nivolumab≥3級肺炎發生率高于RTOG0617中CRT≥3級肺炎發生率(6.5%、8.7%、10% 比1%~5%),而CRT序貫durvalumab、CRT 同步 atezolizumab、CRT 序貫 atezolizumab≥3級肺炎發生率與RTOG0617相當(3.4%、3%、0%比 1%~5%)[49]。筆者發現CRT聯合PD-1抑制劑pembrolizumab、nivolumab發生肺炎的風險略高于CRT聯合PD-L1抑制劑durvalumab、atezolizumab治療,這可能與文獻報道的PD-1抑制劑發生CIP風險高于PDL1抑制劑有關[8]。Moore等[50]分析了真實世界39例接受CRT序貫durvalumab治療的NSCLC患者,發現56%的患者出現≥2級肺炎。提示真實世界CRT序貫durvalumab治療肺炎發生率可能更高,但該研究病例數較少。以上研究結果初步表明CRT聯合PD-1抑制劑治療增加了肺炎發生風險,但還需要更多前瞻性研究驗證這一發現。
3.2.2.3 治療晚期NSCLC Manapov等[51]報道了3例晚期NSCLC患者胸部放療后接受nivolumab治療發生3級肺炎的患者。在對KEYNOTE-001研究的回顧性分析中,先前接受過胸部放療的NSCLC患者與未接受過胸部放療的患者對比,pembrolizumab治療后任意級別肺炎發生率有增加的趨勢,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8%比1%,P=0.15)[52]。Barrón 等[53]回顧性分析 101 例接受 PD-1抑制劑治療的晚期NSCLC患者,結果既往任意部位放療明顯增加了肺炎風險。既往放療組與未放療組任意級別肺炎發生率(40%比9.8%),≥3級肺炎發生率(10%比0%)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1)。Botticella等[54]在318例NSCLC患者中探索既往胸部放療對肺炎發生的影響,結果接受過胸部放療的患者≥3級肺炎發生率明顯高于未接受胸部放療的患者(11.1%比0.4%,P<0.01)。與上述研究結果形成對比的是,Hwang等[56]研究發現患者有或沒有胸部放療史ICI治療后肺炎發生率相當(8.2%比5.5%,P=0.54)。Voong等[30]回顧性分析了188例接受ICI治療的NSCLC患者,發現既往胸部放療并未增加肺炎風險(19%比19.3%),接受根治放療的患者比接受姑息放療患者的肺炎發生率有升高的趨勢,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4%比7%,P=0.051)。一項回顧性研究納入了包括肺癌在內的多種實體瘤患者,接受CTLA-4、PD-1、PD-L1抑制劑治療,結果有胸部放療史的患者肺炎發生率為6%,無胸部放療史的為1%[56];另一項納入多種實體瘤患者的研究報道胸部放療聯合ICI治療≥2級肺炎發生率為6.3%[57]。上述研究都為回顧性,放療的劑量、放療與ICI治療間隔時間和不同的ICI藥物等因素都可能影響最后的結果。這些數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聯合治療會增加肺毒性。
3.2.2.4 立體定向放療聯合ICI治療 Ⅱ期臨床試驗PEMBRO-RT研究共納入76例晚期NSCLC患者,聯合治療組在SBRT后接受pembrolizumab治療,對照組接受pembrolizumab治療[5]。結果聯合治療組任意級別肺炎發生率為26%,對照組為8%,兩組間任意級別肺炎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在另一項針對晚期NSCLC患者研究中,患者在局部SBRT或手術后接受pembrolizumab治療,結果任意級別和≥3級肺炎發生率分別為11%和6%[58]。Tian等[59]展開的一項多中心回顧性研究分析了SBRT聯合或不聯合ICI治療在117例晚期NSCLC患者中的安全性,結果SBRT+ICI組和SBRT組任意級別肺炎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33.9%比 27.9%,P=0.47),但 SBRT+ICI組≥3級肺炎發生率明顯高于SBRT組(10.7%比0%,P<0.01)。Qin等[60]報道了12例晚期NSCLC患者在大分割放療后接受atezolizumab治療,最終2例(16.7%)患者發生3級肺炎。Miyamoto等[61]報道了6例晚期NSCLC患者接受肺SBRT后行nivolumab維持治療,其中1例(16.7%)患者發生3級肺炎。Li等[62]開展的Ⅰ期研究評估了胸部SBRT序貫低劑量放療聯合PD-1抑制劑信迪利單抗(sintilimab)治療的安全性,其中肺小病灶接受低劑量放療,肺大病灶接受SBRT。結果15例患者中任意級別肺炎發生率為20%,未發生≥3級肺炎。綜合上述研究結果,SBRT聯合ICI治療的肺毒性是可以接受的,但相較于單免疫或單放療可能增加肺炎風險。需要更多前瞻性研究來探索SBRT聯合ICI最佳治療模式。
3.3 鑒別與治療 CIP是一種潛在致死性的irAE,發生≥3級CIP需要永久停止ICI治療,而RP患者治療恢復后還可以考慮繼續接受ICI治療。因此鑒別診斷很重要,但通常要準確區分兩者較為困難,兩種肺炎除了會單獨發生之外,也可能同時存在。首先,RP多出現在放療后3個月內,CIP可出現在ICI治療后數小時至數月,中位出現時間為2.1個月。其次,RP一般局限在肺照射野內,出現在照射野外的雙肺間質性改變為CIP可能性更大。另外,發生CIP的患者常合并其他irAE。最后,需要重視ICI聯合胸部放療后出現肺炎的患者鑒別診斷除了CIP及RP外,還需與感染(細菌、真菌、病毒、結核等)、腫瘤進展等鑒別。治療上RP與CIP的治療原則類似,主要都是以吸氧支持治療和糖皮質激素為主,如果遇到確實無法明確的患者,可根據病情嚴重程度,酌情予吸氧支持治療和(或)糖皮質激素等治療。
4 小結與展望
放療聯合ICI未來發展值得期待。現有的研究主要以回顧性研究為主,ICI聯合胸部放療是否增加肺炎發生率仍存在爭議。大部分研究結果都展示出ICI聯合胸部放療并未明顯增加肺炎發生率,但小部分研究數據顯示聯合治療肺炎發生率增加,尤其是接受SBRT的晚期NSCLC患者。相信隨著放療技術的進步、聯合治療時機的不斷優化、放療方式及劑量的探索,聯合治療相關肺毒性可能進一步減少。目前仍存在一些問題有待闡明,如治療相關肺炎的發病機制和如何準確鑒別CIP與RP等。此外,胸部放療聯合ICI治療NSCLC患者的前瞻性數據較少。鑒于這類肺炎的潛在高致死性,在更多的前瞻性臨床研究結果公布之前,臨床應用放療聯合ICI治療尚需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