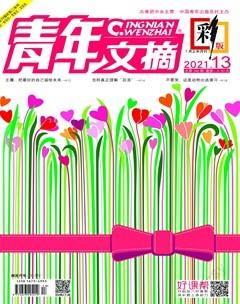鄧倫:保持對理想的執念
郭帖
“這渠修不成,我誓不下山。”這是1960年紅旗渠設計師之一的吳祖太在太行山上留下的執念。由鄧倫主演的系列短劇《理想照耀中國》之《天河》,講述了在勘測和修建紅旗渠過程中,27歲的吳祖太遭遇母親病重、妻子喪生的變故,卻始終堅守崗位。他將生命奉獻在“天河”的鑄造之上,以“理想當燃”的精神感染著當下。
鄧倫想抓住的, 正是吳祖太這個人物身上始終如一、不可動搖的執念。通過由表及里地抓住這種執念感,他讓自己逐漸靠近這個角色。


《天河》

綜藝《上新了,故宮》
進入險境
紅旗渠被稱作世界第八大奇跡,耗時10年完成。林縣,地處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處,降雨稀少,自古便是缺水之地。當時的林縣人,日行幾十里路挑水方可滿足日常飲水需要,新婚嫁娶,水就可當聘禮。新中國成立后,如何解決缺水問題成為林縣的工作重點。在林縣水利局技術員吳祖太的帶領下,“社社隊隊劈山鑿洞,家家戶戶打井修渠”,這段艱難修筑的水渠被命名為“紅旗渠”。
為了還原當年吳祖太艱苦險峻的工作環境,《天河》的取景點定在懸崖峭壁之上。在海拔近千米高的山崖上,只有寬度不足一米、羊群走出來的小道可供通行。人走在上面,得扶著一側的山體慢慢前進,另一側就是萬丈深淵。
在見到鄧倫前,導演焦永亮拍攝了一個d e m o小樣告知即將進行的危險戲份。誰知,鄧倫看完小樣,便往懸崖上走,與導演探討如何拍攝才會有更好的效果。導演一度覺得鄧倫不恐高,直到快殺青時,鄧倫才告訴他,自己吊威亞的時候根本不敢往下看。
這份“膽大”貫穿了整個拍攝過程。許多時候,焦永亮覺得鏡頭已經夠了,某些角度鏡頭太危險,“要不就別拍了。”鄧倫卻會堅持多拍幾個機位角度,以便為后期剪輯預留足夠的素材。
《天河》發布的首批劇照,就令人倒吸一口冷氣。鄧倫腰系麻繩,懸吊在90°角的半山腰上,腳下便是深淵。通過還原這樣的驚險場面,《天河》將觀眾代入紅旗渠建設時期的工作氛圍。當年,作為技術人員的吳祖太并沒有什么先進工具,為了完成工程設計,他常常需要腰系繩子,手持卡尺儀器,垂吊在懸崖之上。“他們(紅旗渠修建者)當時在現場的狀態一定要比拍戲更驚險。”紅旗渠精神支撐著鄧倫克服心理障礙。
《天河》的另一個主要拍攝地點是山洞。開拍時,鼓風機一打,灰塵便在空氣中飛揚。妝發師進去補妝,待不了5分鐘出來便一直咳嗽,但鄧倫在里面掄錘頭,一待就是一天。等收工出來時,灰蓋住臉,幾乎認不出樣子。
對于鄧倫來說,置身于懸崖之上、置身吳祖太當年所處的環境中,是一劑最好的藥,令他快速沉浸于角色,體會這個角色的心境。懸崖上的人,只能是心無旁騖的。在修建紅旗渠的過程中,吳祖太經歷了新婚、喪妻這樣戲劇性的波折。按照常規演繹方式,光表達這些情緒就足夠催淚感人,但鄧倫想抓住的,是這個人物身上更重要的特質——始終如一、不可動搖的執念。
抓住執念感
《天河》正式開拍前,在聊劇本、聊人物的過程中,導演很快感受到鄧倫是“有備而來”的。對于吳祖太這個角色,他不僅做了細致的功課,更有自己的見解。他意識到,唯有理解當時人的生活狀態,方能理解他們對水的渴望,以及在這種狀態下堅持苦干到底的拼勁。在拍戲時,鄧倫自覺地一整天都不沾水,讓自己盡可能接近人物的內在狀態。
而把握人物的特殊性格,則由其生平入手。吳祖太流傳下來的人生事跡,發生地總是在山川。由于測繪工作的需要,他長年累月地待在山上,家里有事也叫不回他。“什么樣的人,能夠做出這樣的事情呢?”鄧倫不斷思考,他感覺吳祖太是一個內心足夠強大,“所有事都往心里走,自己跟自己較勁,悶頭做事的人。”
新婚妻子的意外去世,是《天河》中的一場重頭戲。最初的劇本中,吳祖太在得知愛人意外過世后,難掩悲痛,大力宣泄情緒。但按照鄧倫的理解,吳祖太不應該有如此外化的表現。“他不是那種到處奔跑,沖著大山去喊、去嘶吼的人。”鄧倫對吳祖太的理解是內斂,“所有的痛苦應該是窩在自己身體里的。”導演認可了這一點,激烈的行動與臺詞被統統刪去。在新婚妻子意外喪生后,吳祖太把所有情緒釋放在砸開的石塊中,釋放在紅旗渠修建工作中。這段“無需臺詞”的表演,是《天河》中的華章。
鄧倫作為演員的職業素養,不僅體現在這些重頭戲中,更體現在一些不易注意到的細節中。在等待拍攝跑進山洞的戲份時,攝影指導看到鄧倫站在洞中,不斷用腳底去蹭鞋面,使鞋面粘上更多的灰塵,以接近吳祖太一路奔走的狀態。
而妝發師記得,每次自己進去補妝,鄧倫總是對他說:“再臟一點,再臟一點。”他檢視自己從頭到腳各個細節,希望更接近“刨山”的工作狀態。
以角色應有的狀態為準繩,鄧倫總是在不斷發現細微的差錯,并進行校準,最后達到準確的演繹,這也是歷史片拍攝應有的原則。
快與慢
鄧倫身上有一種極適合演員的敏感,能夠察覺、照顧周圍人的情緒。妝發師剛認識鄧倫的時候,大家一起去餐廳吃飯。碰上桌子沒擦干凈,鄧倫常常第一個站起來,拿起濕巾擦桌子,先擦對方面前,再擦到自己面前。
排戲的時候,鄧倫會提出各種點子。導演能感受到,鄧倫身上有種強烈的整體創作意識,“他不是只想著把自己的角色演好,他是希望所有人都好,這樣才能出現一個好的作品。”
曾經在某個時期,鄧倫身上的執念感是鋒芒銳利的。有兩年多的時間,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兩三個小時,甚至對50多個小時不睡覺習以為常,只顧著在各個劇組間連軸轉。在節目里,他放話:“我很愛我的工作,我愿意為了它不吃不喝不睡覺,我活該,一個愿打一個愿挨。”這種對于演藝工作的執念,讓他在一眾年輕演員中很快嶄露頭角,憑借《歡樂頌2》《楚喬傳》《香蜜沉沉燼如霜》等作品逐漸建立起知名度和觀眾認可度。
而如今,許多人都能感受到他逐漸放緩了腳步。不拍戲的時候,他會陪著姥姥看電視,一待就是一天。在“新人”時期過后,鄧倫對于演藝這份事業的追求,顯示出了另一種形式的執念——精而美。他陸續拒絕了許多東西,比如不合適的片約、不合適的角色。跟朋友聊天的時候,他經常說:“這個事情,要么不做,既然要做,就要做好。”
《天河》是鄧倫心中“要做就做好”的一部戲。在這類作品中,他能夠發揮自己所有的專業素養,去精雕細琢每個細節,也從中汲取演員所需的情感養分。
吳祖太與紅旗渠的故事中,還有許多那個年代的獨特人情味的部分。比如,他畫設計圖的時候,會去請教路過的老漢,從而了解到哪塊地方曾經遭遇過水患;他生病的時候住在當地農戶家中,主人省著雞蛋給他吃。反過來,吳祖太是一個外鄉人,卻為林縣奉獻了整個生命。
《天河》的故事,有太多這樣的情感支點。回憶起拍攝過程,鄧倫印象最深刻的是殺青前的最后一場戲,在懸崖峭壁上,吳祖太與林縣老鄉們奮戰在一起。他喜歡屬于那個年代的質樸感,即使是陌生人,也像親人一樣。而對于當下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學習紅旗渠的精神,保持對工作或生活的執念,“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出精彩”。
//摘自《博客天下》2021第9期,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