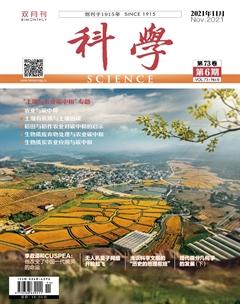應用3D大腦類器官研究人類神經發育和疾病
唐曉艷 張馨月 徐敏 劉妍
很多人對醫療事業的未來,都存在這樣一種憧憬:當身上的組織器官出現問題時,人們可以在體外培養新鮮健康的相同組織器官用于移植。其實在當下,類器官的出現就是這種技術的成果體現。
類器官模型是在模式動物模型不能完全代替人體模型,且人體實驗和流產胚胎存在倫理限制的情況下出現的。早在1965—1985年,科研工作者就已經使用“類器官”來研究發育生物學,但當時的“類器官”只是因為其形態類似器官被冠以此名。直至多能干細胞學科的興起,才使類器官“名副其實”,真正擁有類似器官的功能和結構。
人多能干細胞(包括胚胎干細胞和誘導性多能干細胞)在特定誘導條件下可分化為體內任意一種細胞或組織類型。隨著近年來干細胞領域的不斷發展,類器官技術應運而生。類器官是指利用人體干細胞或者由器官特異性祖細胞,在三維環境中培養出類似于器官的組織,具有自我更新和自我組織的能力。類器官的發展是從腸類器官培養系統開始的。2009年,研究者將小鼠腸道干細胞放置在凝膠基質中生長,用以模擬組織的細胞外基質微環境,結果發現這些干細胞最終形成了表面有孔、內部有類似腸道絨毛和隱窩的球狀結構[1]。隨著類器官培養技術的不斷發展,目前已培育出人的腸、視網膜、大腦、肝臟和腎類器官。

傳統模擬神經系統疾病的方法是從人多能干細胞中分化得到神經元。這是一種2D培養體系,該體系分化得到的細胞無法模擬人類大腦3D空間的內環境,也無法反映出3D層面細胞間的相互作用,所以3D培養體系應運而生。從人多能干細胞產生3D大腦類器官的最普遍方法是先形成擬胚體(形態學上與哺乳動物早期胚胎發育階段有著很高相似度的一種球狀結構),再將這些懸浮培養的擬胚體樣聚集體逐漸分化為幾個極化的神經前體細胞花環結構,隨即重新吹懸成神經球,最后用含有高水平神經元的細胞外基質蛋白的基質膠進行包埋。
迄今為止,利用人多能干細胞已經可以培育區域特異的類腦器官,如大腦皮質、前腦、中腦、下丘腦、小腦和海馬等。2011年,最早用3D技術培育出完整的神經組織:視杯類器官。2013年,研究者利用人胚胎干細胞,運用凝膠基質包埋的方法在3D培養環境中培育出大腦類器官,其具備人類大腦發育初期的一些主要區域,如視網膜、背側皮層、腹側前腦、中腦、脈絡叢和海馬等結構,并利用此模型闡明了小頭畸形的發病機理。還有研究者運用微型生物反應器生成3種類型的腦區域性類器官(前腦、中腦和下丘腦),揭示了寨卡病毒影響人類大腦發育的機制。此外,通過將人胚胎干細胞異位表達乙型肝炎病毒變體2,誘導在大腦皮層類器官中生成血管樣網絡結構,創建了具有脈管系統的血管化類器官。2017年,研究者首次在體外構建了皮層和基底前腦融合類器官,重現了胚胎發育時期中間神經元的遷移過程。近日,有課題組構建了大腦皮層和后腦/脊髓的類器官,并將它們與人類骨骼肌類器官融合,形成3D“皮質—脊髓—肌肉”運動組裝體。他們用該運動組裝體證實皮質下行神經元投射可調節脊髓功能網絡,同時脊髓源性運動神經元可進一步控制肌肉產生節律波動。研究人員對于3D大腦類器官模型的每一步探索都是在努力構建更貼合人體結構的體外模型,以此深入了解人體神經系統的結構。
探究人腦神經發育障礙疾病
神經發育障礙是由胚胎階段大腦發育異常所致的一類中樞神經系統功能受損的疾病,是一種廣泛、多樣化的神經行為學障礙。患者往往伴有認知、語言、社交互動及運動行為的缺陷。常見的神經發育障礙包括小頭畸形、自閉癥、提摩西氏綜合征、精神分裂癥、癲癇、威廉姆斯綜合征、唐氏綜合征、智力障礙、無腦回畸形、蕾特氏癥等。類器官技術的出現,規避了由于使用動物模型及流產胚胎而面臨的種屬差異和倫理問題,為研究神經發育疾病及藥物篩選提供了新的技術平臺。

以小頭畸形為例,該疾病是一種由于患者的祖細胞產生和細胞凋亡的失衡致使腦內神經元和神經膠質細胞數量減少,繼而導致大腦結構發育異常的疾病。小頭畸形分為原發性小頭畸形和繼發性小頭畸形,其中原發性小頭畸形是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的散發性神經發育疾病,發病原因是祖細胞有絲分裂過程中紡錘體失控和細胞周期動力學異常。
迄今為止,研究人員已經篩選出與原發性小頭畸形發生相關的18個基因突變。蘭開斯特(Lancaster)等首次使用大腦類器官對小頭畸形進行建模,他們將攜帶了編碼CDK5調節亞基相關蛋白2(CDK5RAP2)突變基因的小頭顱病患者的誘導性多能干細胞分化為大腦類器官[2]。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在分化而成的患者腦類器官中,中神經前體細胞顯示出增殖減少和提前分化等病理表型。同時,研究人員使用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將對照組類器官的CDK5RAP2基因進行敲減,結果顯示敲減組類器官同樣表現出相似的病理表型。此后,還有研究者構建了WDR62基因突變的人源性腦類器官模型,證實WDR62基因缺陷可使其下游效應因子中心體蛋白CEP70被募集到初級纖毛基體的過程中斷,纖毛分解延遲、纖毛長度增加、細胞周期進程受損,從而導致神經前體細胞增殖減少和提前分化,最終造成小頭畸形類器官體積減小,驗證了WDR62基因表達異常可導致小頭畸形患者神經發育障礙。這些研究結果表明,構建患者來源的類器官模型可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腦部疾病遺傳機制相關研究的發展。
小頭畸形的另一個主要致病因素是寨卡病毒。曾有多個研究小組使用寨卡病毒感染大腦類器官來觀察病毒致病的機制。在對包括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藥物、臨床試驗候選藥物和藥理活性化合物在內的約6000種化合物的藥物篩選過程中,研究者發現caspase-3活性抑制劑Emricasan和Niclosamide(B類驅蟲藥)可挽救寨卡病毒誘導的皮質神經前體細胞的凋亡,并有效抑制寨卡病毒的復制,因此確定了抗寨卡病毒藥物開發的先導化合物[3]。由此可見,基于人腦類器官的研究不僅加深了我們對小頭畸形發病機制的認識,也為驗證候選藥物提供了新的藥物篩選平臺。
探究人腦神經退行性疾病
神經退行性疾病又稱神經系統變性疾病,是一類以中樞神經系統和外周神經系統變性導致的結構和功能進行性退化為特征的疾病,主要包括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亨廷頓病和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癥。這些神經退行性疾病嚴重影響了美國600萬人的生活質量,且其病理機制尚不明確,針對此類疾病,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該綜合征病理特征復雜多樣,而動物模型不能完全概括人類神經系統的獨特性和復雜性,在開發用于神經退行性疾病治療藥物的過程中,科研人員面臨巨大挑戰。因此,基于多能干細胞技術的3D類器官模型則為研究上述疾病開辟了新的道路。
以阿爾茨海默病為例,該疾病又稱老年癡呆,臨床上往往表現為記憶、認知和執行功能的進行性和不可逆轉性衰退。截至目前,僅有兩種經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用于治療阿爾茨海默病的臨床藥物:乙酰膽堿酯酶抑制劑和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拮抗劑,但以上兩類藥物的治療效果非常有限,因此,開發新型藥物療法為當前生命醫學領域關注的一個焦點。
阿爾茨海默病主要的病理學特征為β-淀粉樣蛋白斑塊和tau蛋白纏結。這些病理過程的下游效應為神經元變性、突觸和神經元丟失,最終導致神經系統的萎縮。研究者在人神經干細胞來源的3D大腦類器官培養系統中發現,β-淀粉樣蛋白前體蛋白和早老素1突變可誘導顯著的β-淀粉樣蛋白細胞外沉積;此外,在神經突觸中也可見銀陽性的P-tau聚集物及絲狀tau蛋白。其他研究者在類器官中過表達家族性阿爾茨海默病基因,也觀測到了β-淀粉樣蛋白的聚集及遲發tau病理學特征。
另一項關于阿爾茨海默病患者來源類器官的研究證實了標志性阿爾茨海默病病理的自發出現,包括淀粉樣蛋白聚集體的生成和tau蛋白的異常磷酸化。此外,β-和γ-分泌酶抑制劑處理可有效減輕類器官中阿爾茨海默病的相關病理表型[4]。同時,研究者發現散發性阿爾茨海默病與APOE位點基因突變有關,其中APOE4突變被認為是散發性阿爾茨海默病最大的遺傳危險因素。研究團隊利用CRISPR/ Cas9基因編輯技術將APOE4基因引入健康人誘導性多能干細胞系,結果顯示,攜帶APOE4基因型的大腦類器官表現出β-淀粉樣蛋白積累和tau蛋白磷酸化增加,同時APOE4基因型來源的星形膠質細胞和小膠質細胞對β-淀粉樣蛋白42的吸收率降低,而將APOE4轉變成APOE3基因后,可明顯改善其阿爾茨海默病的病理特征。以上結果證實了APOE4基因在散發性阿爾茨海默病發病過程中的關鍵作用。
由此可見,利用中樞神經系統類器官建立的神經系統疾病模型是探究人類遲發性神經退行性疾病潛在病因的一個有力工具,同時也為篩選治療藥物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平臺。
3D腦類器官技術的發展至今還不足10年,仍處于起步階段。就其細胞和分子組成而言,目前腦類器官的體系可以模仿妊娠中期的人類胎兒大腦。然而,由于大腦類器官缺乏血管循環系統,因此其主要依靠自由擴散從培養基中進行氧氣交換和吸取營養。當在體外進行長期培養時,由于缺乏氧氣和營養,類器官中間的細胞會出現大量凋亡。因此,建立一種改進的腦類器官循環系統為大勢所趨。
最近,已成功地從誘導性多能干細胞中分化出血管類器官,包含自組裝成毛細管網絡的內皮細胞和周細胞。血管類器官可移植到小鼠中形成穩定的灌注血管樹,包括動脈、小動脈和小靜脈[5]。在未來針對人腦類器官技術的優化中,可將人腦類器官與血管類器官結合在一起,以期建立功能性的封閉循環系統,以支持體外的長期培養并用于研究神經血管的相互作用。
人腦細胞組成不僅僅包含源自神經外胚層的神經細胞,還包含各種類型的非神經細胞。當前大多數關于類器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將胚狀體誘導為神經外胚層,從而缺失了大量非神經細胞,例如小膠質細胞、內皮細胞、造血細胞和腦膜等。因此,當前的大腦類器官體系尚無法對由非神經元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或非神經細胞與神經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介導的大腦疾病進行建模。研究表明,在沒有添加雙重SMAD蛋白抑制劑的情況下,大腦類器官可自發生成中胚層祖細胞,它們能夠在神經外胚層細胞提供的中樞神經系統微環境作用下分化為成熟的小膠質細胞。此外,2D分化的小膠質細胞與大腦類器官的共培養體系也有助于研究小膠質細胞與神經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大腦類器官與更廣泛的支持性非神經細胞的共培養將成為未來的一項研究熱點。
人腦皮質溝回形成是其大腦皮層面積遠大于嚙齒類動物的一個重要原因,溝回的形成與認知能力高度相關。然而,使用當前體系在大腦類器官中通常未觀察到明顯的溝回結構。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通過激活PTEN-Akt信號轉導通路可使大腦類器官中產生類似溝回的褶皺[6]。這表明,進一步的技術改良有望使大腦類器官產生與實際人腦更為相似的結構。
總之,盡管目前大腦類器官培育體系尚存在技術缺陷,也不具有人體天然器官的立體結構及復雜的功能。但不可否認的是,3D大腦類器官模型已為人類研究大腦發育及疾病機制帶來了巨大進展,關于大腦類器官的構建及應用研究仍將是未來生命醫學領域的關注熱點,且應用類器官移植替代藥物療法治愈神經系統疾病依然是未來精準醫療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作為一種新興的生物培養技術,大腦類器官在研究人腦發育、疾病機制、組織替代療法以及藥物篩選等方面,均有著巨大的研究潛力和應用價值。
[本文相關研究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81922022, 91849117, 81471301)和國家重點研究與發展計劃(2016 YFC1306703)的資助。]
[1]Sato T, Vries R G, Snippert H J, et al. Single Lgr5 stem cells build crypt-villus structures in vitro without a mesenchymal niche. Nature, 2009, 459(7244): 262-265.
[2]Lancaster M A, Renner M, Martin C A, et al. Cerebral organoids model human brain development and microcephaly. Nature, 2013, 501(7467): 373-379.
[3]Xu M, Lee E M, Wen Z,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small-molecule inhibitors of Zika virus infection and induced neural cell death via a drug repurposing screen. Nature Medicine, 2016, 22(10): 1101-1107.
[4]Raja W K, Mungenast A E, Lin Y T, et al. Self-organizing 3D human neural tissue derived from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recapitulate alzheimer’s disease phenotypes. PLoS One, 2016, 11(9): e0161969.
[5]Wimmer R A, Leopoldi A, Aichinger M, et al. Human blood vessel organoids as a model of diabetic vasculopathy. Nature, 2019, 565(7740): 505-510.
[6]Li Y, Muffat J, Omer A, et al. Induction of expansion and folding in human cerebral organoids. Cell Stem Cell, 2017, 20(3): 385-396. e383.
關鍵詞:大腦類器官 多潛能干細胞 神經系統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