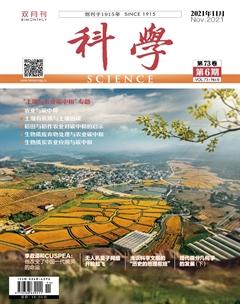淺談科學文明的“歷史的地理樞紐”
蔣謙

在地理學史上,有所謂“樞紐地區”或“心臟地帶”一說,認為某些地理狀況或地緣關系具有某種權重,發揮著“樞紐”的作用,從而制約著人類歷史活動的某些方面。以英國地理學家哈·麥金德(H. J. Mackinder)的“歷史的地理樞紐”說為代表。在科學史上也有類似說法,認為人類科學文明更易于起源于某一地區,在那里,由于科學或技術的發展會使其成為中心地帶。例如,有古代科學文明起源于新月地帶說,以及近代科學產生于西歐之說等。但是這些說法過于執拗于某一靜態的地區或國家,忽視了科學的生成,以及不同科學文明之間的互動,偏離了“樞紐”的真正含義。因為從詞源的角度來看,樞紐是指相互聯系的諸事物的中心環節或關鍵之處;它雖然強調的是中心環節,但也注意到事物之間的關系;沒有諸事物的“網絡”關系,也就無所謂中心“節點”。也就是說,“樞紐”一詞不僅有中心之意,也有開合、交通之實。過去,強調中心較多,強調開合、交通較少,從而忽視了具有地緣關系的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在歷史上,這種科學文明的樞紐很多,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層級(邊緣地帶、整個大陸、洲際之間以及全球范圍)上觀察到。
本文盡量撇開“歷史的地理樞紐”中的地緣政治和權力架構因素,側重于從信息流通的角度描述幾個在歷史上起重要作用的科學文明樞紐,并作簡要的分析討論。
歷史學家熱衷于談論科學上的“希臘奇跡”,可是,希臘的這一奇跡并不局限于古希臘這一地方,而是與它獨特的地緣關系有關。地中海及其周邊地區構成了形成人類早期科學文明的一個樞紐。
人類文明的第一縷曙光出現在古老的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地圖上看,一塊半月形富饒的土地把美索不達米亞相鄰的兩個海——里海和地中海連接了起來。雖然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相隔較遠,但它們兩者之間有著廣闊的空間和聯系:一個瀕臨地中海南部,一個通過敘利亞與地中海發生聯系。也就是說,它們通過地中海遙遙相望。起初,地中海的確是一種屏障,但隨著軍事征伐和經濟貿易發展,特別是隨著內河航運向海洋航運的過渡,人們逐漸開始“發現”海洋的價值。到公元前10世紀時,腓尼基人通過貿易成為海上強權,同時海洋航運技術有了新發展,地中海反而成為了周邊諸國和地區的聯系“紐帶”。“新月沃土”的中心地位逐漸被處于邊緣地帶的希臘所取代。我們可以把地中海看作是不同文明融合的大熔爐。

具體到希臘來說,它的地理位置顯得十分獨特和重要,它位于歐洲的東南部、地中海的東北部,范圍包括希臘半島、愛琴海和愛奧尼亞海上的群島和島嶼、土耳其西南沿岸(小亞細亞)、意大利東部和西西里島東部沿岸地區。可見,這是一個為希臘人所控制的非陸地型的廣泛區域。其中,位于愛琴海上的克里特島被認為是愛琴海文明的真正搖籃,而愛琴海是亞洲與歐洲之間的橋梁,也是歐洲與非洲之間的橋梁。有了這兩座“橋”的存在,愛琴海地區的建筑者可能從他們的埃及前輩那里學到了知識,甚至可能借用了埃及工匠的技藝。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古希臘科學搖籃的愛奧尼亞地區位于愛琴海東岸,也就是歷史上的小亞細亞地區。這個地區不僅與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很近,而且與“迦南之地”或巴勒斯坦更近。而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于亞洲先知與希臘賢哲進行交流,也有利于各民族思想文化的“中轉”與融和。在這個過程中,科學得以萌芽。正如科學家史家喬治·薩頓(G. Sarton)所說:“愛奧尼亞是東西方交流的主要中心,在愛奧尼亞,埃及和亞洲文化就像酵素一樣對希臘的天才起到了催化作用。”[1]
例如,作為古希臘歷史上的第一個科學家(自然哲學家)和幾何學家,泰勒斯(Thales)就出身于米利都的一個腓尼基人家庭。他從小就從其腓尼基祖先那里獲得了部分知識和天賦,也從愛奧尼亞人那里獲得了知識。隨著年歲增長,他開始游歷埃及,在那里,一些新的天文學和數學觀念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有一種說法認為,古老的巴比倫人已經發現了沙羅周期,這個周期使得他們可以預見日月食,而泰勒斯在埃及時已經聽說了這個周期,他甚至可能親眼看見了公元前603埃及的日食。這些知識對于希臘天文學來說,可稱為“東方遺產”。此外,泰勒斯還具有理性精神,他把埃及人如何測量土地和建筑物高度的經驗事實,用邏輯推理的方式加以概括和提煉,創立了演繹幾何學。
又如,古希臘醫學同樣得益于那里的獨特地理環境。科學史家們注意到,同樣是在小亞細亞的西南角,那里誕生了兩個重要的醫學學派:尼多斯學派和科斯學派。由于距離較近,信息通達,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鑒,并在這個過程中相互競爭。正是這樣一種環境和條件,催生出了希波克拉底醫學。據史料記載,希波克拉底出生在科斯島,后來在希臘進行了大量旅行。這些十分便利的旅行使他增加了見聞,開闊了視野,對他的醫學研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隨著海上貿易的擴展,希臘半島與愛奧尼亞殖民地和愛琴海諸島的商業往來加深,希臘與波斯諸強競爭的加劇,希臘地區,特別是雅典成為了新事物的匯集點。由于雅典文化強烈地受到了愛奧尼亞模式的影響,雅典的中心地位得到加強。按照科學地理學家的說法,在雅典的輝煌時期,它充當了四種自然哲學的地理中心,這種自然哲學包括愛奧尼亞派、畢達哥拉斯派、原子論派等。它們匯聚在一起,成就了雅典科學的鼎盛和繁榮。
總之,地中海沿岸由于島嶼(半島)與海洋的獨特關系,造就了一種星羅棋布的離散狀態,促成了多樣性文化的并存。許多時候,海洋的隔離起到了一種地理隔離與保護的作用。另一方面,地中海的通達性又成為了聯系沿岸各地的紐帶,使得各部分能夠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使信息能夠以最便捷的方式流動起來。其結果是,在地中海沿岸實現了智力的統一,產生了最具典型意義的希臘科學。
如果說地中海及其周邊地區是一種海洋型的樞紐,那么東亞板塊則構成一種陸地(內陸)型的樞紐。具體來說,與環地中海的點狀分布、平行輻射的網絡傳播結構不同,東亞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基于“中心—邊緣”構型的網絡擴散模式。
在某種程度上,東亞板塊可看作歐亞大陸的一個“孤島”。但這種情形并不妨礙該地區早期生態與文化的多樣性。這緣于東亞腹地的縱深性和地理的復雜性。在這個區域內,除了粗線條的“北方文化”與“南方文化”外,還有受游牧民族影響的“西北文化”和“東北文化”(因為在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中,尚有西北和東北部與外界相連的通道),以及受漁獵經營影響的“東南文化”。這些文化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融通。如距今4000年前的三星堆遺址既顯示了成都盆地文化與長江中下游文化的交流,也顯示古蜀國與周王朝以及西方異族文化的融合。在歷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始終是一種多元互補的共生關系。
在這個過程中,雖然出現了一些小的民族聯盟或較大的封建帝國,但彼此分封割據的狀況占據主導地位,以至于在周王朝后期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諸侯國,周王的實際統轄領土非常之狹小。與之相應,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諸子百家”的爭鳴局面。這一局面在公元前500年到前250年間達到了它的頂峰。其中參加爭鳴的有十多個學派,而影響最大的則是儒、墨、道、法四家。他們各自依賴于不同的地域文化,服務于不同的君王,形成了各種思想和流派爭奇斗艷的繁榮景象,堪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古希臘文明媲美。
不過隨著文明的演進,特別是生產力的發展,華夏中原地區以及長江流域中下游平原的獨特“地理控制”機制逐漸展現出來。雖說東亞板塊橫貫交錯著一些大的山脈(如秦嶺)和褶皺帶,造成某種程度的地理阻隔,但其間仍留下了相對寬廣、平坦的平原或盆地,且地勢愈是向東愈是如此。這些地形地貌對于任何一個有一定實力并覬覦弱小諸侯或民族聯盟的“霸主”來說,都是他憑借馬匹和戰車長驅而入的理想地帶。而東亞季風氣候以及其西高東低的地勢,也為霸主們沿著大多由西向東的河流實施控制提供了“舟楫之利”,這可謂“水陸并進”。在這種自然地理環境下,某一區域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共同體往往依靠某種地緣優勢(如易于耕作的糧食生產區)、眾多的人口、管理先進的國家機構、強大的軍事實力等條件,極容易形成統一的核心文明和國家,而周邊的小國或小文明體莫不圍繞在其周圍并臣服于它,從而形成一個“中心—邊緣”模式的“朝貢”體系。
我們看到,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為兼并諸侯、形成中央集權,秦始皇充分利用了自然地理尤其河流水渠方面的有利條件,修靈渠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到公元前214年,隨著靈渠的修成,秦始皇的軍隊解決了軍糧和軍用補給的運輸問題,隨即向嶺南增派援軍,一舉控制了嶺南,迅速統一了南部地區。由于中國內陸河湖相連、水道密布,疏浚河道、開鑿運河往往是統治者完成帝業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務。歷代統治者在不同時期修建或開鑿了包括京杭大運河在內的多條運河,使得長江和黃河等流域借此得以溝通起來,為大規模的物質交流、實現經濟上的互補、促進政治上的一體化進程創造了條件。從信息論的角度看,運河水渠網絡的形成還滿足了統一王朝的通訊和信息交流的需要。[2]
表現在科學文明方面,上述的社會控制機制以及對信息傳達的需求,有助于與信息和通訊相關的技術形成與發展。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造紙、印刷術和指南針均與信息和通訊有關。例如,統一的中央權力機構需要盡快傳遞國家的各項指令,而傳遞指令則需要一定的載體,即書寫文書的紙張。這就客觀上促成一種輕薄、易于保存和傳遞的紙的技術的發明。研究表明,造紙術的普及和傳播發生在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時期。

其次,統一的社會結構和組織運轉非常有利科學信息的匯集、科學知識的交流以及技術的普及與推廣。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南北差異很大,生態與文化呈多樣性,對自然的認知需要綜合不同的信息。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由于地勢高下之不同,在平原地區“三月花者”,到了山區則“四月花”。這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有學者指出,漢民族與少數民族在歷史上多有科學文化的交流。如古代的陰陽、八卦、五行等概念可能是在彝族的十月太陽歷的基礎上發展演化而成的。而某項技術一旦成熟便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推廣和普及。如耕田、冶煉和紡織技術就是如此。
再次,統一而強大的科技文明體必然對其周邊產生積極的影響,帶動、同化具有地緣關系的地區和國家。如中國很早就與朝鮮、日本進行科技文化交流。隨著著名的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國科技文化的“觸角”還伸向了中亞、南亞。而海路的開通則進一步擴大了中國對外的科技文化傳播。中國造紙術就是通過這樣的網絡傳播到世界各地的。明代鄭和下西洋影響十分巨大,從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間,航海家鄭和先后率隊七次下西洋,經37個國家,向南到了爪哇,向西到了波斯灣和紅海,最遠到了赤道以南的非洲東海岸,甚至到達了好望角。這是一種典型的由中心向四周擴散的傳播模式。
外部阻隔、內部四通八達的地理環境,隨著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其內部的文化上的多樣性逐步被消磨,科學思想和技術發明漸漸齊一化,文明的中心開始排斥外來技術。創新被視為異端,這一方面保護了文化的獨特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又使得科學文化趨于故步自封。
當我們把東亞與希臘地區統一起來看時,會發現它們恰好處于舊大陸(即歐亞大陸)的兩端,屬于大陸板塊的邊緣地帶。這一點很接近于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斯皮克曼(N. J. Spykman)在其“邊緣地帶論”中所描述的情景,也與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K. Jaspers)所提出的“軸心時代”說非常契合。后者認為,在公元前800前至公元前200年間存在一個軸心時代。從地域上看,軸心時代同時在東方的中國、印度和(西方)希臘展開;它們是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3]
那么,將東西方兩個重要邊緣地帶連接起來的、廣袤的中間地帶是什么情況呢?這一中間地帶因其氣候寒冷、干旱(半干旱),且遍布著不規則的巨大山脈,以及大片的草原、沙漠、沼澤、稀疏的林木等而被籠統稱為凍土地帶。然而就是這樣一片土地,在麥金德那里被稱作“樞紐地區”(后又被稱作“心臟地帶”)。在他看來,該地區西部被高大的烏拉爾山脈分成廣闊而又宜居的東歐平原和充滿沼澤地的西伯利亞平原,以及高寒、崎嶇不適宜居住的西伯利亞高原。[4]這個劃分,把中國的西北、伊朗、阿富汗等地也包括在內。
不過,麥金德把該地區看作類似于人體心臟的部位的認識,主要是基于隨著19世紀西伯利亞地區鐵路的開通以及俄羅斯的強大威脅的評估而作出的,即認為只有近代鐵路交通樞紐的形成時,心臟地帶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展現。類似的觀點也見于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說中。在他看來,由于舊大陸的巨大的中心平原與外部(沿海)區域從來都是被完全隔絕的,內陸地區交通困難重重,因而整個大陸塊的真正一體化從來就沒有真正實現過。[5]
然而實際情形并不完全如此。確實,在農業文明剛剛形成之初,東西方經過中間地帶的相互接觸非常之稀少。但這并不表明在漫長的歲月里,兩地之間沒有一條實際存在的通道。正如生物地理學家和人類學家的研究所證實的,在史前時代,舊大陸就存在著農作物和動物(如馬、牛)馴化的所謂東—西主軸線擴散路徑。例如,歐洲和印度農作物的大部分野生祖先都來自于西南亞;種植蔬果的嫁接技術是從中國西傳至羅馬的。進入文明時期,不遲于公元前1500年,在新月沃地西部發展起來的字母文字的原理,在大約1000年之內向西傳到了迦太基,向東傳到了印度次大陸。其部分原因在于歐亞大陸的東—西線軸向位于同一緯度的東西兩地,自然地理環境大體相近。除少數地方(如“世界屋脊”所形成的阻隔)以外,大部分地區仍然是可以聯通的。
自然地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文明的最初進程,但起主動作用的還是人類活動而不是地理環境。在遼闊的草原和平原上,曾出現了許多強大的游牧聯盟。它們逐水草而居,逐漸形成自己的文化。從公元三世紀到公元八世紀,這一帶發生的一波又一波游牧民族移民浪潮橫掃了中亞,拜占庭、薩珊伊朗、中國和游牧汗國并不是影響這一地區的全部力量。相對于歐亞大陸的南部地區,這些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憑借其剽悍的體魄、作戰勇猛的騎兵以及嫻熟的射藝等,往往成為入侵南部地區的外來者,但他們的作用既有破壞性的一面,也有良性刺激的一面。正如地理學家詹姆斯·菲爾格里夫(J. Fairgrieve)所評論的:“平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扮演著一種‘溶劑’的角色”。[6]他們給世界帶來廣闊的世界觀,使南部和邊緣地區看到了更多的新世界。及至公元13世紀,整個歐亞大平原被籠罩于蒙古大汗國鐵蹄的統治之下。可以這么說,東西方陸上通路的打開,主要源于歐亞大平原游牧民族擴張與征服(還包括隨之而來的商貿活動等)。
雖然北方游牧民族的擴張和征服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遷移和文明互動,但它客觀上促成了文化上的交流和文明的互動。正如同商貿活動的展開那樣,內陸的中間地段,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疊加區”“集散地”或“文化交易區”。即不同的文化或亞文化在這一地區發生交流、沖突、過濾,最終融合并生成新的文化。
非常重要的是,通過陸上通道,尤其是絲綢之路(它被稱為連接東、西方的“大動脈”),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科學文化能夠發生直接或間接(通過中亞、阿拉伯地區)的聯系,進而產生相互影響。在公元前500年,中國的絲織品便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了歐洲。在唐代,經由絲綢之路,由于在中國、中亞諸國和地中海,特別是拜占庭之間經貿流通和交換的擴大,中國與中亞和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更為廣泛。[7]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
數學家吳文俊先生曾依據科學史家李約瑟有關阿拉伯偉大數學家花拉子米出使可薩國一事的闡述以及他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中亞的古波斯地區(包括巴格達)乃“天下之中”的觀點,認為該地區是東西方科學文化思想的交匯之地,在歷史上曾起到了科技傳播的重要作用。[8]現在已經很清楚,可薩王國位于高加索以北,包括頓河、伏爾加河下游以及克里米亞向西伸展的地區。在公元842年至847年間,阿拉伯使節——數學家花拉子米被派駐可薩王國。這位數學家在這期間具體做了些什么,人們并不十分清楚,但從其所著的《代數學》一書與“契丹算法”(即中國算法)的高度相似之處,人們可以斷定,他的代數學不止受到印度數學的影響,更受到中國數學的影響。有意思的是,花拉子米的《代數學》一直是中世紀歐洲各大學的主要教科書,歐洲許多偉大數學家都從中吸取營養。
最后,從近代科學的起源來看,雖然它主要出現西歐地域,但它本身可看作是經由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居間作用而實現的不同文化(尤其是東西方文化)之間交流、沖突與融合的結果。只要看看阿拉伯帝國的疆域,從今天法國和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延伸到中亞的帕米爾山脈,就知道它構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全球文化交融區”。中世紀的科學文化傳播的基本路徑是由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出發,經過拜占庭,然而再到達歐洲的。
嚴格說來,中世紀阿拉伯帝國所控制的版圖還夠不上全球文化交融區的資格。它至多只能算得上舊大陸的文化交融區。真正具有“準全球”性質的文化交融區應該數由西歐科學文明的地緣性擴張而來的跨大西洋科學文明板塊:它不僅在陸地之間,而且在陸地與海洋之間建立起了通道,最終將地球上最大的兩個陸地板塊——歐亞非陸地板塊與美洲板塊真正聯結了起來。
相比較而言,東半球與西半球的文明進程有明顯不同。西半球的文明要比東半球落后幾千年。但西半球這個后開發的半球或古老的“沉默半球”并非一無是處。與東半球的新月沃地和中國一樣,美洲的安第斯山脈地區、亞馬孫河地區和中美洲也是較早的糧食作物區,那里種植有大量的玉米,而這是東半球早期所沒有的重要農作物。由于西半球的資源非常豐富,有的是東半球所沒有的,對于進入15世紀的、文明程度較高的東半球來說,比較落后的西半球是一個尚未被認識的大陸,是一個資源蘊藏豐富的夢幻般的異邦。
最先將這種夢幻般的理想付諸行動的是西歐的一些國家。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隨后是荷蘭以及英國等國。這些國家占盡了“地利”,它們直面大西洋。其中,伊比利亞半島的地理位置尤為特殊:通過西班牙最南端與非洲西北部之間的直布羅陀海峽,最大的內陸海——地中海與大西洋連接起來。歷史上,地中海沿岸國家的探險船隊曾頻繁地通過這里到達大西洋。生活在半島上的人們最有可能進行海洋探險與擴張活動。
僅僅把歐洲人的跨大西洋殖民擴張的全部原因歸結為地理因素是不夠的。從11世紀開始至13世紀末,西方人相繼在西班牙、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西亞和歐洲東部展開全面的進攻。其結果,逐漸控制了地中海西部這片水域。此時,南意大利因與拜占庭的特殊關系,成為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前哨。東方的“資源”(不僅僅是貿易)由這里源源不斷地進入歐洲。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技術,尤其是航海技術的輸入。像航海用的星盤、羅盤、斜掛大三角帆、船尾方向舵和方形船體等,有的是從阿拉伯人甚至中國人那里借鑒過來的,有的則是經過他們自己的實踐改進了的(包括使船只更適合大面積水域的航行和安裝金屬重炮以利于作戰等)。[9]到15世紀,歐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迅猛發展,從而為大航海創造了條件。1492年,意大利探險家、航海家哥倫布完成了對美洲的航行并發現“新大陸”。此發現開辟了后來延續幾個世紀的歐洲探險和殖民海外領地的大時代。而差不多與此同時,歐亞大陸中間的東西方大通道,隨著強大的沙俄帝國和大清國驅趕草原上的諸游牧民族而進入“關閉”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從東半球到西半球的擴張(文明的傳播),是集東半球的全部文明優勢和體量而實現的,它絕不僅僅是歐洲文明的跨洋西傳。但也不得不承認,西歐處在“橋頭堡”位置,“近水樓臺先得月”。在向美洲擴張的早期,所傳播的更多的是歐洲的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組織模式以及科技文化等。再加上北美洲與歐洲的地理位置處在大體相同的緯度,非常適合歐洲人的移民和生活,不久,美國就成為歐洲的一個“投影”(其文化主要源于歐洲),歐洲與北美的關系不斷加強。這時,大西洋不再是一種屏障,而更像一條高速通道,它將兩個不同的世界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
地理大發現和對美洲的征服與擴張,客觀上實現了跨洲的科技文化交流與互動。首先是歐洲人憑借其科技和工業(包括軍事)的強勢地位向相對落后的地區“輸送”他們的科技文化;其次,通過對新大陸自然資源的控制和占有,歐洲人豐富了自己的科技文化“寶庫”。例如,西屬和葡屬的美洲的科學家們發現當地大量的歐洲科學家所未知的動植物。這些發現不僅被用來糾正奧古斯丁和亞里士多德知識體系中的錯誤,而且被用來建立了一種更講求實證的自然史或博物學體系。由此形成的新的自然觀有助于遏止歐洲傳統科學中的唯理論的傾向。再次,服務于航海和殖民統治的科學技術從歐洲人對美洲和其他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擴張中獲得的“好處”,極大地資助了歐洲科學技術的發展。例如,美洲有著豐富的植物(農作物)種子。這些種子改變了歐洲和世界其他許多地方的食品結構,從而使得殖民統治者在美洲、印度和非洲等地創辦的殖民地種植園有可能發展為商業性產業,而這些產業反過來推動歐洲人的自然秩序知識的增長。[10]毋庸置疑,在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和殖民擴張所帶來的征戰、殺戮、販賣黑奴、掠奪財富,以及傳播疾病等的過程中,科學技術的傳播有時也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西歐人的地緣擴張除了向北美擴張外,還不斷地向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地擴張。但起始于15世紀西歐與北美的科技文明樞紐的雙向回路重心,后來逐漸由西歐偏向北美。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成為全球科技的中心,并與歐洲、澳洲以及東亞構成一個“一個中心,多元并存”的全球科技交互網絡系統。很顯然,這個全球網絡系統是由于海底電纜、無線電波、光纖和互聯網,以及現代化的交通運輸工具為載體逐漸演變而成的,它的實體性的地理位置或地緣關系變得不那么重要了,逐漸呈現虛擬化、抽象化的“空間”狀態。雖然不能說當代的科學技術是一種歐美化的科技文化,但是它的“根”仍然維系在西方的“土壤”之上,它仍然是一種具有歐美文化偏向的科技文化。未來是否還有一種來自于“東方”和“南方”的科技文化進一步增加自身的權重,進而重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的“歷史的地理樞紐”?這應當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1]喬治·薩頓. 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 魯旭東, 譯.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10.
[2]劉青峰. 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3]卡爾·雅斯貝斯. 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李夏菲, 譯.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9.
[4]哈·麥金德. 歷史的地理樞紐. 林爾蔚, 陳江,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0.
[5]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邊緣地帶論. 李爽喆, 譯. 北京: 石油工業出版社, 2014.
[6]詹姆斯·菲爾格里夫. 地理與世界霸權. 龔權, 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7]B. A.李特文斯基. 中亞文明史(第三卷). 馬小鶴, 譯. 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3.
[8]朱清時, 姜巖. 東方科學文化的復興. 北京: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4.
[9]約翰·霍布森. 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 趙建黨, 譯. 濟南: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9.
[10]威廉·E.伯恩斯. 知識與權力: 科學的世界之旅. 楊志, 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關鍵詞:科學文明 地理樞紐 信息 交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