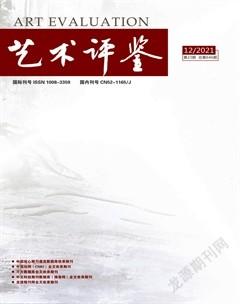“非遺”視域下江蘇傳統民間舞蹈文化探析
王雨虹
摘要:傳統舞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和審美、教育價值。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速發展不斷擠壓著傳統文化的生存空間,存續狀況岌岌可危。江蘇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匯聚了異彩紛呈的傳統舞蹈資源,具有豐富的研究價值。本文聚焦江蘇傳統民間舞蹈文化資源,通過梳理舞蹈文化內涵,辨明不同地域的藝術特征,繼而引入江蘇傳統民間舞蹈文化傳承的思考,寄希望對江蘇舞蹈的保護和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關鍵詞:非遺? 江蘇傳統舞蹈? 民間舞蹈
中圖分類號:J70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1)23-0047-04
我國從2004年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經過反復論證研究,于2011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傳統舞蹈作為“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十個門類中的一個類別,其保護實踐為增強文化多樣性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獨具特色的“中國經驗”。傳統舞蹈涵蓋民間舞蹈和宮廷舞蹈,由于社會歷史變革,作為獨立表演的宮廷舞蹈自宋朝以后逐漸式微,我國傳統舞蹈文化在傳播過程中流存下來的主要是傳統的民間舞蹈。民間舞蹈由廣大勞動人民集體創作并發展傳播,蘊含著該民族傳統文化的審美理想,不同的地域風貌、民俗信仰、勞作方式匯聚成獨具特色的身體語言。目前,專業院校民族民間舞蹈課程中漢族舞蹈主要圍繞“南燈北歌”開展活動,突出對東北秧歌、山東三大秧歌、安徽花鼓燈和云南花燈的表演教學。江蘇地區的民間舞蹈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教材體系去推廣和普及,探索研究便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和文化價值。
一、江蘇傳統民間舞蹈文化內涵
江蘇地處我國東部,物產富饒、水陸交通發達,孕育著燦爛悠久的歷史文化。通過文獻史籍中的記載和出土的大量漢畫像,我們得以窺見江蘇地區五彩斑斕的舞蹈藝術和其審美流變。它脫胎于吳越文化,歷經漢代古拙尚武與纖巧崇文的融合轉變,伴隨六朝時期人口遷徙的文化交匯,體現出抒情柔婉的特征,自宋以后的江蘇民間樂舞更是在前期的積累中蓬勃發展。舞蹈藝術作為一種身體和精神并重的文化形態,其形成和傳播依賴于所處的地域環境,水系文化塑造了江蘇柔美秀麗的表演風格,也為其提供了和稻作漁撈的勞作方式密切相關的舞蹈素材和體態動律。“海安花鼓”是流傳在南通市海安縣東部地區的傳統民間舞蹈,迄今已有400多年歷史。舊時當地的百姓多以打漁為生,為祈求親人出海平安歸來便有在門前廊下“掛天燈”的風俗,重大節日的表演中便持有紅燈籠歡欣鼓舞,逐漸演變成手持花鼓的民間歌舞形式。“擺頭屈膝微微顫,舞姿蕩扭三道彎”①是海安花鼓的典型動律,它來源于村姑漁民的勞作習慣。膝蓋的微顫伴隨著腳步交替輕點地,像站立在船頭撐漿搖櫓,搖肩擺胯的輕巧細膩增添了江南水鄉的韻味,也體現出稻作漁撈文化的深刻影響。
搖船采菱、織網捕魚的勞動形式不僅賦予民間藝術創作的想象空間,也通過藝術表達在人民心中筑起了“魚羹稻飯”的農業崇拜。舊時農業社會,為順應四時變遷便寄希望借助社祭活動祈求來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依存于民俗儀式中的傳統舞蹈隨之興盛。“大興旱船”是宿遷地區流傳甚廣的傳統民俗舞蹈。旱船原指陸地上的船,用秸稈、竹竿、麻繩編扎成船,外飾綢布紙花,又名“花船”。百姓對于跑旱船的喜愛源起于大旱時祭祀求雨的儀式,也抒發了湖泊干涸后對于過往泛舟捕魚生活的向往之情。同樣與宗教祭祀緊密相連的傳統舞蹈還有流傳在南京高淳的“跳五猖”和揚州“花香鼓”,如果說前者是在粗獷歡騰的表演中傳遞祛災納祥的意愿,后者則承載著江南女性的柔美雅致。舞者手持單面小鼓,鳳冠霞帔、裙綴銀鈴,時常扮鳥獸而舞,賦予了農耕社會對于鳥獸性靈的圖騰崇拜,又作“鳳舞”。但隨著時代發展和人們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深植農耕文化意識中的“娛神”逐漸轉向“自娛娛人”。江蘇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增加了調查研究的難度,但也為舞蹈表現的內容和形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據考察,江蘇傳統舞蹈按照功能劃分有即興自由的娛樂舞蹈,也有嚴謹程式的宗教舞蹈;表演形式上有模擬鳥獸舞,亦有雜耍技藝舞,形式多樣、風格多變的傳統舞蹈為江蘇繁榮興盛的文化進程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江蘇傳統民間舞蹈風格辨析
民間舞蹈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依據外部條件的變化體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以漢族“舞龍燈”為例,作為圖騰信仰的遺風和華夏精神的象征,全國各地分布著不同形式的龍舞。北有古樸剛勁的火龍舞,南有活潑敏捷的滾地金龍,眾則百人舞一龍,少則一人舞雙龍,板凳龍、荷花龍、香火龍、草把龍皆可入舞。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江蘇的地域環境和文化交融使得舞蹈藝術也呈現出南北不盡相同的風格特征。依據地域劃分,江蘇省內以長江為界,南北而分,但據經濟文化和淮河流域的自然條件,又可細分為蘇南、蘇中、蘇北。
吳儂軟語的蘇南有著“東方水都”清雅秀麗的文化特征,涵蓋長江以南的蘇州、無錫、常州、鎮江以及南京江南區域。得益于天地的鐘靈毓秀,連帶著這片土地的舞蹈藝術都浸染著雋永靈動的審美特質。蘇中②地區位于長江以北、淮河以南地界,包括揚州、泰州、南通、淮安、鹽城等地。受文化雜糅的影響,蘇中的舞蹈藝術呈現出南北兼而有之的風格特色,既有蘇南的婉約秀麗,又有蘇北的爽朗大氣。相較于蘇中端莊穩健的藝術風格,蘇北則承襲了北方地區質樸爽朗的舞蹈審美。這是歷史上由于人口遷徙導致的鄰近城市的文化交互現象,外省文化和當地藝術的碰撞融合使得徐州、連云港、宿遷等地的傳統舞蹈顯現出樸拙豪放的性格氣質。
民間舞蹈的風格性應建立在感受族群的審美心理和文化價值之上,并通過肢體語言構建舞蹈的地域性特征,二者缺一不可。江蘇傳統民間舞蹈的地域性差異帶來了藝術觀感的沖擊,在具體的舞蹈動作上亦有跡可循。按照舞蹈本體時、空、力的角度歸納:蘇南舞蹈受稻作漁撈文化影響較深,動作空間多集中在上肢部分,突出傳情達意的細膩表現,下肢部分強調膝關節的微顫和髖關節的擺動。運動空間路線突出“繞”的曲線軌跡,整體形成節奏舒徐、力度輕巧的格調;蘇中承接南北,受蘇北文化的影響,舞蹈下肢運動多頻繁,體現在碎而穩、穩而快的控制變化。上肢注重身體部位的合理調配,整體運動路線平穩,展現出兼容并蓄、剛柔并濟的藝術風格;蘇北地區受外來人口的文化沖擊,體現在民間雜耍技藝的興盛,舞蹈藝術上也充分融合了武術等元素。動作空間以下肢運動為主導,閃轉騰挪間增加了縱向空間的對比變化,髖部擺動的下沉感也突出了北方人民的熱情爽朗。相較于蘇南地區上肢精巧細膩的“盤繞”,蘇北地區則延長了動作的路線、擴大了運動幅度,通過急促的鼓點和下沉的力度彰顯出勞動人民生命的昂揚。
三、江蘇傳統民間舞蹈的傳承與發展
城市化進程加速了江蘇的經濟發展,城市和鄉村日漸模糊的界限雖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文化交融,但也撼動了傳統民間舞蹈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隨著“非遺”保護意識和學術研究的漸趨深入,一批學者專家加入到對江蘇“非遺”舞蹈文化的搶救保護工作中。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國家組織相關人員深入江蘇進行大規模的舞蹈普查并編輯成冊。2007年南京藝術學院成立“江蘇民間舞蹈實驗室”,2017年南京市文聯攜手南京藝術學院共建“江蘇民間舞蹈教學創造實驗室實踐基地”。江蘇傳統舞蹈通過院團、群文和校園三種路徑實現藝術價值的充分延展,呈現出一批具有不同時代烙印、但卻統一在江南水鄉意蘊中的典范作品。如建國初期黃素嘉、李玉蘭創作的《豐收歌》,該作品運用泰興花鼓的動作語匯再現了割麥打穗的生活場景,用熱火朝天的氣勢點燃了困難時期后百廢待興的創作熱情。后期群眾文藝工作者嶄露頭角,貼近群眾,從民間舞蹈中提煉素材,創作了《擔鮮藕》等具有水鄉情韻的群文作品。而校園舞蹈伴隨著“非遺”進校園的號召,在大中小學里呈現愈加繁榮的態勢,涌現出不少既體現時代審美又蘊含傳統文化精髓的教學成果。
自2000年我國“非遺”保護工作正式啟動至今,自上而下的輻射宣傳使得許多瀕臨消失的文化遺產得以重視,各地也掀起申報“非遺”的浪潮。保護工作的啟動取得了顯著的實踐經驗,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農村人口大量流失,伴隨著勞作方式的改變失去了傳統的農耕信仰,多元文化的沖擊使得依附于節慶民俗中的民間表演逐漸失去市場。許多曾經興盛的傳統舞蹈已斷演數十年,記錄在冊的民間舞種數量銳減。雖然政府部門加強對此類舞種的申遺保護,但傳承人大都年事已高,且后繼無人,如溧水“洛山大龍”已處于瀕危險境,發展狀況岌岌可危。基于此,政府在確保財政支持和積極投放的基礎上應通過多渠道的宣傳喚醒民眾對于傳統文化的保護和認識,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將其從靜態保護轉變為動態傳承。如合理搭建宣傳平臺,積極舉行不同層次的競賽慶典,調動廣大群眾對于江蘇舞蹈學習和創作的熱情,也將其推向更高的藝術平臺。同時,線上課程也是搭載文化平臺的一種途徑,疫情期間江蘇省文化館通過公眾號推送了海安花鼓、打蓮湘等一批頗具代表性的江蘇民間舞蹈慕課,為“非遺”的傳承和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指導方針使得許多瀕臨消失的民間舞蹈獲得一線生機,但也對保護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對民間舞蹈進行全方位的原貌傳承固然原汁原味,但卻忽視了民間舞在發展中即興變化的特征,從而失去其鮮活性。如“跳馬伕”是流傳在如東一帶的祭祀舞蹈,曾被質疑帶有封建迷信色彩而陷入困境。傳承人任乃貴老師在保留文化精髓的基礎上進行合理加工,使其成為符合當下審美的男子舞蹈,并進入校園推廣;另一方面,人們開始回歸本土,站在全局的高度領悟舞蹈背后的文化內涵,但也會出現剝離文化內核而急功近利的舞蹈現象。面對上述問題,首先應對“非遺”繼承和發展的關系進行辯證分析,尋根溯源是正確掌握舞蹈內涵進行傳播和創造的基礎,要“在‘變’與‘不變’尺度的把握中再造一種貼近時代精神,體現生命意蘊的民間舞蹈”③。其次要締結民間藝人和舞蹈工作者的緊密聯系。傳承人楊培杰老師在回顧海安花鼓被選拔鳥巢排練時的情境,曾表示“從選演員到排練結束,再沒有任何人來向我了解海安花鼓的源流,更沒有人來向我討教該舞的動作動律、風格特征……”④看似風風火火的表演卻掩蓋不了民間藝人的落寞,但并非一直如此。校園作為文化傳承的重要基地,在關注傳統文化價值引領的同時也強調尊重傳承人和文化主體的意愿。南京師范大學邀請“棲霞龍舞”省級非遺傳承人薛友進老師走進校園進行公益培訓,通過文化引導、創作分享和實踐體驗,最終道出了“舞龍就是舞人”的心聲,這指出傳承的不僅是儀式、技藝,更是于游龍擺尾間完成對華夏精神的重塑。
四、結語
蘊含江蘇文化精神的傳統舞蹈承載著這片土地的歷史記憶,亦是我國民族民間舞蹈中的重要一支。江蘇對于傳承和發展傳統民間舞蹈文化亦積累了豐富有益的經驗:政府和地方協同合作、民俗活動和舞臺展演互為補充;“記憶工程”正式啟動,數字化保護和數據庫建立雙管齊下;專業院校著力于江蘇民間舞蹈教材的整理和課程設計;大中小學重點挖掘所在地域的藝術文化價值,喚醒學生對于家鄉傳統藝術的熱愛。2021年6月10日國務院公布的第五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共計325項(含擴展項目名錄140項),江蘇泰興花鼓亦在其中。如火如荼的申遺熱情仍不減當年,但民眾意識覺醒,愈發注重申遺后的質量保護工作。傳統舞蹈文化的保護道阻且長,需要全社會、全方位、全局觀的指引和行動,方能探尋出一條用中華傳統文化滋養當代人民精神世界、樹立人民文化自信的路徑。
參考文獻:
[1]《中華舞蹈志》編輯委員會.中華舞蹈志—江蘇卷[M].上海:學林出版社,2014.
[2]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江南舞蹈藝術[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
[3]樸永光.論“非遺”語境下傳統民間舞蹈的保護[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7(06).
[4]何際峰,周亮.海安花鼓的歷史源流與當代傳承反思[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5(02).
[5]宋卉婷.江蘇民間舞蹈女子動作研究[D].南京:南京藝術學院,2013年.
基金項目:本文為江蘇省教育廳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名稱:江蘇“非遺”傳統民間舞蹈文化融入幼兒園藝術教育的路徑探析,項目編號:2020SJA0598。
①《中華舞蹈志》編輯委員會:《中華舞蹈志—江蘇卷》,上海:學林出版社,2014年,第170頁。
②蘇中:江蘇中部地區大致有兩種劃分范圍。除去本文采用的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劃分方法,還有一種較小的范圍僅包含揚州、泰州、南通等地,淮安和鹽城劃入蘇北地區。
③廖珩、李德金:《江蘇花香鼓舞的源流探尋》,《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第88頁。
④何際峰、周亮:《海安花鼓的歷史源流與當代傳承反思》,《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5,第2期,第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