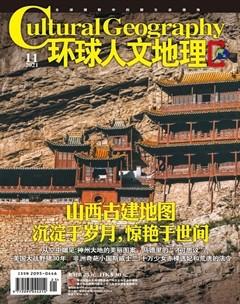北京城的禮儀空間秩序
唐曉峰
沒有看過地圖,也沒有登過景山的尋常百姓,在東華門-西華門、東直門-西直門、東四-西四、東單-西單、東便門-西便門、左安門-右安門等相對稱呼的城市地名中,也可以明確無誤地感受到對稱空間結構的存在。這種對稱格局形成的空間暗示,是最基本的治理語言,或稱為空間秩序的語法。
梁思成、侯仁之是論證北京城市中軸線的先行學者。中軸線概念的提出,是對北京城對稱空間格局的關鍵性認識。中軸線產生于對稱格局,而中軸線又是對稱格局的重心所在。北京城中軸線的主題段落是在皇城范圍內,即從大清門到地安門這一線,在這條南北直線上,坐落著一系列朝宮,它們是皇帝的住所和主政之所,但均以崇高的名稱命名,如太和殿、乾清宮、天安門等,這些名稱意味著一種高于皇權的至上價值。它與皇權重合,卻高于皇權,這便是中軸線的意識形態特點。
居中是至高、至尚的表示,這是很早便形成的空間價值觀。在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陜西岐山鳳雛西周院落遺址中,都有這類成熟的建筑形態。而在《周禮·考工記》所述關于國都的規劃模式中,更完整地表述了王宮居中、全城對稱的幾何結構。這種幾何結構乃是制度的表達,社會的尊卑等級在這一平面空間結構中可以得到完美充分的定位。《考工記》被納入《周禮》,宣告了其敘述的都城布局制度具有了禮制的高度。在走向禮儀化社會管理的歷史進程中,《考工記》都城模式越來越受到重視并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實施,最終在元大都城規劃中得到最充分的采納。明清北京城又繼承了大都城的基本模式,保持著都城禮儀化的性質。
由中軸線所主導的禮制空間結構,首先是覆蓋皇城紫禁城的,但也是覆蓋全城的。朝廷的文武百官與京城的眾多百姓,都受到這個禮儀系統的制約。從大清門到地安門這段中軸線的主題段落的不可逾越性,每個百姓都有切身體會。它在全城造成的分割,成為東城、西城的嚴格定義。崇文門、宣武門的東西設立、科舉士子與就刑犯人的東西分途,都是空間禮儀系統中人們習以為常的部分。而皇帝親祀的天、地、日、月四壇的四個方位的大典,更是轟動京城的舉動。
必須指出的是,建筑禮儀化在古代中國是滲透到社會深層的,它不只是在王朝宮室建筑的范圍內,在典型的百姓民居中,也有空間里的行止的禮儀性規定,這一點在北京城尤甚。北京城典型的民居是四合院,標準的四合院建筑布局,除了大門偏在東側(這是禮制規定),整個院落結構有著清晰的中軸對稱結構——正房、廂房、前院、后院分別對應著家族長幼的次序與行為禮節。垂花門是典型四合院的重要空間節點標志,一般宅門的垂花門就位于第一進院的中線上,與倒坐房對面而立。多進院的宅門,前邊還有過廳、廳房等,垂花門一出現就標志著內宅在此了。所謂的內外有別,就是以此為界。
然而,在景觀中,從宮廷到民居這些長短不一的中軸線卻都被圍墻環繞著,它們所直接統領的空間也是封閉的。這令人想到禮儀的本質是“內治”,即控制內部成員的秩序,它是為內部成員而設。因為圍墻造成了空間的分割,內、外之分是傳統人文空間普遍存在的特征,相應地,也是普遍存在的觀念。二里頭、鳳雛遺址表明,祖先很早就選擇了封閉空間的模式來建立秩序。封閉空間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自成天地,有自我存在、自尊的意味。除了被圍墻所環繞,另有一點值得注意,這條軸線上雖然鋪有一段一段的道路,但它并不是一條貫通的大道,所以在視覺上并不直觀。盡管如此,它在意識的“視覺”中卻是清晰地、完整地存在著,為此,它也更具有禮儀入心的意義。
對于空間的禮儀追求,往往要犧牲很多實用性的功能,這是傳統北京城空間上的最大問題之一。王朝解體,城市進入現代發展,于是一個兩難性的問題在今天出現。一方面要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另一方面要建設現代城市社會,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成為今天空間治理的挑戰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