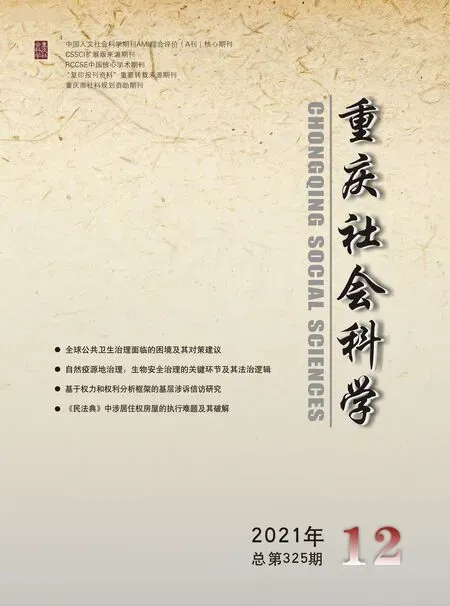基于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分析框架的基層涉訴信訪研究
孔凡義 程穎
摘 要:涉訴信訪在信訪案件中占據(jù)比重較大。從國(guó)家權(quán)力運(yùn)行來(lái)看,基層涉訴信訪的產(chǎn)生與國(guó)家權(quán)力邊界模糊和相互嵌入有一定的關(guān)系;從公民權(quán)利行使來(lái)看,訪權(quán)和訴權(quán)重疊以及群眾權(quán)利觀的衍化催生著基層涉訴信訪。以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關(guān)系為分析框架,我們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國(guó)家權(quán)力和公民權(quán)利的運(yùn)行對(duì)基層涉訴信訪的互相建構(gòu)和強(qiáng)化。因此,基層涉訴信訪法治化改革一方面需要明晰國(guó)家權(quán)力之間的治理邊界和協(xié)作,另一方面需要把訪權(quán)和訴權(quán)分離開來(lái),塑造民眾的公民權(quán)利觀。
關(guān)鍵詞:涉訴信訪;國(guó)家權(quán)力;公民權(quán)利
基金項(xiàng)目: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項(xiàng)目“新生代農(nóng)民工集體行動(dòng)的政治心理機(jī)制及其調(diào)適研究”(16BZZ007)。
[中圖分類號(hào)] D632.8 [文章編號(hào)] 1673-0186(2021)012-0058-011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 ? [DOI編碼] 10.19631/j.cnki.css.2021.012.005
長(zhǎng)期以來(lái),“信訪不信法”導(dǎo)致的涉訴信訪一直是困擾我國(guó)基層治理的一大痼疾。為解決這一問(wèn)題,最高人民法院、中央政法委和國(guó)家信訪局密集出臺(tái)多個(gè)文件來(lái)推進(jìn)訴訪分離改革。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人民法院第三個(gè)五年改革綱要(2009—2013)》正式提出“建立訴與訪分離制度”。此后,中央下發(fā)多個(gè)文件對(duì)建立涉訴信訪事項(xiàng)導(dǎo)入法律程序工作機(jī)制等做出明確規(guī)定。2013年12月,涉訴信訪和普通信訪分流處理,訴訪分離改革開始加速。2014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guó)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guān)于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wèn)題的意見》,強(qiáng)調(diào)政府行政的程序價(jià)值,基本厘清了行政體系與司法體系的界限。同年9月,中央政法委研究制定了《關(guān)于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事項(xiàng)導(dǎo)入法律程序工作機(jī)制的意見》《關(guān)于建立涉法涉訴信訪執(zhí)法錯(cuò)誤糾正和瑕疵補(bǔ)正機(jī)制的指導(dǎo)意見》《關(guān)于健全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jié)制度的實(shí)施意見》建立健全了導(dǎo)入、糾錯(cuò)和退出機(jī)制,防止界限不清、相互推諉、終而不結(jié)等現(xiàn)象。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國(guó)務(wù)院印發(fā)《法治政府建設(shè)實(shí)施綱要(2015—2020年)》,提出了“推進(jìn)通過(guò)法定途徑分類處理信訪投訴請(qǐng)求”。在此基礎(chǔ)上,2017年8月國(guó)家信訪局又制定出臺(tái)了《依法分類處理信訪訴求工作規(guī)則》,明確各級(jí)信訪工作機(jī)構(gòu)和其他行政機(jī)關(guān)對(duì)信訪訴求的分類處理。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huì)強(qiáng)調(diào):“完善信訪制度,健全社會(huì)矛盾糾紛多元預(yù)防調(diào)處化解綜合機(jī)制”,其中涉訴信訪改革是完善信訪制度的重要內(nèi)容。
一、文獻(xiàn)綜述:從涉訴信訪到訴訪分離
涉訴信訪作為一種信訪形態(tài),是信訪法治化改革的重點(diǎn)和難點(diǎn)。當(dāng)前,涉訴信訪改革的主要路徑是訴訪分離。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此問(wèn)題的討論是圍繞涉訴信訪的概念和訴訪分離改革展開的。
(一)涉訴信訪概念的討論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涉訴信訪”的概念。“涉訴信訪”指的是“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訴訟權(quán)利救濟(jì)的信訪事項(xiàng)”。目前由于對(duì)接訪機(jī)構(gòu)、信訪內(nèi)容、信訪目的等要素有不同理解,因而對(duì)“涉訴信訪”的界定尚未形成共識(shí)。有學(xué)者從涉訴信訪與信訪的關(guān)系角度出發(fā),認(rèn)為涉訴信訪是信訪的一種類型,歸屬于法院處理[1]。而從信訪目的來(lái)看,有學(xué)者認(rèn)為涉訴信訪即針對(duì)法院就具體案件的立案、審判或執(zhí)行等環(huán)節(jié)的行為或結(jié)果不滿時(shí),人民群眾通過(guò)各種信訪渠道提出的來(lái)信來(lái)訪[2]。與上述些許不同的是,肖文認(rèn)為涉訴信訪是當(dāng)事人對(duì)法院處理“訴類”事項(xiàng)的過(guò)程或結(jié)果不服,以寫信或走訪形式,最終以法院為處理主體的信訪[3]。有學(xué)者贊同上述說(shuō)法,認(rèn)為涉訴信訪是因訴訟活動(dòng)而引起的信訪,但認(rèn)為信訪與訴訟是兩種不同的程序,不能與司法程序并存,更不能先于司法程序而行使[4]。目前許多信訪案件在信訪中夾雜著涉訴的法律問(wèn)題,“訴”與“訪”難以截然分開。與一般信訪比較,涉訴信訪的獨(dú)特之處在于與訴訟活動(dòng)的關(guān)聯(lián)。
(二)訴訪分離的相關(guān)研究
訴訪分離首先要明確的是“訴”與“訪”分離的標(biāo)準(zhǔn),在現(xiàn)實(shí)中判斷信訪訴求應(yīng)通過(guò)哪種途徑和程序來(lái)解決,目前學(xué)者主要有兩種分類:一是以信訪人的訴訟內(nèi)容為標(biāo)準(zhǔn),對(duì)案內(nèi)、案外的訴訟請(qǐng)求分別劃分給訴訟程序和信訪程序的實(shí)質(zhì)案件;二是以程序是否終結(jié)為標(biāo)準(zhǔn)的形式要件劃分,訴訟程序尚未終結(jié),就得在訴訟程序中來(lái)解決,若已經(jīng)終結(jié),信訪人脫離了當(dāng)事人的身份,就在信訪程序中解決[5]。除此之外,對(duì)于分離的內(nèi)容,學(xué)術(shù)界與實(shí)務(wù)界也存在不同意見。有學(xué)者認(rèn)為,訴訪分離是指將信訪案件中的涉訴信訪案件與普通信訪事項(xiàng)分開處理的程序,即外部分離,而法院按不同程序處理信訪事項(xiàng)即為內(nèi)部分離[6]。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司法程序尚未完成的來(lái)信來(lái)訪事項(xiàng),屬于“訴”的范圍,而司法程序已經(jīng)完結(jié),當(dāng)事人仍來(lái)信來(lái)訪反映問(wèn)題的,屬于“訪”的范疇。“訴”與“訪”內(nèi)涵的不同決定了其性質(zhì)的差異。信訪在本質(zhì)上是行政管理行為,以此來(lái)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治理的目標(biāo)。而司法則是通過(guò)法律的判斷行為,遵循的是法律邏輯,主要是公正解決糾紛[7]。
以上學(xué)者對(duì)于涉訴信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訴訪內(nèi)涵之分、訴與訪分離的標(biāo)準(zhǔn)以及訴訪分離的類型化解讀。對(duì)于如何完善訴訪分離機(jī)制,實(shí)務(wù)界和學(xué)術(shù)界也進(jìn)行了探討。從訴訪分離的標(biāo)準(zhǔn)出發(fā),明確訴訪分離標(biāo)準(zhǔn)是大多數(shù)學(xué)者的一致意見。明確劃分方法,需要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和口徑,最終實(shí)現(xiàn)科學(xué)分類,分別管理[8]。此外需要對(duì)訴訪分離實(shí)現(xiàn)差異性回應(yīng),按照立案前、訴訟中和程序退出后等不同層次合理設(shè)置訴訪分離的不同層面[4,9]。
涉訴信訪的改革路徑是訴訪分離,它也是實(shí)現(xiàn)涉訴信訪法治化的重要內(nèi)容,同時(shí)也是我國(guó)信訪制度改革的必經(jīng)之路。目前許多信訪案件在信訪中夾雜著“涉訴”的法律問(wèn)題,與訴訟活動(dòng)密切關(guān)聯(lián),“訴”與“訪”難以截然分開。國(guó)內(nèi)學(xué)者雖然對(duì)信訪主體之間互動(dòng)的關(guān)系構(gòu)建了諸多框架,對(duì)信訪改革及其困境進(jìn)行了深入研究,但是聚焦于涉訴信訪問(wèn)題的研究仍然比較稀少,缺乏對(duì)涉訴信訪的理論分析框架。
二、權(quán)力與權(quán)利關(guān)系:信訪制度研究的一個(gè)分析框架
對(duì)信訪制度的研究,可以從兩個(gè)角度來(lái)解釋。一是權(quán)力的角度,從國(guó)家權(quán)力配置及其相互關(guān)系來(lái)闡釋信訪制度及其運(yùn)行過(guò)程;二是權(quán)利的角度,從個(gè)人權(quán)利及其動(dòng)員運(yùn)作來(lái)闡釋信訪制度及其運(yùn)行過(guò)程。
(一)信訪制度的權(quán)力視角
從歷史上看,權(quán)力一直被視為一種支配地位的權(quán)威。不同學(xué)派對(duì)權(quán)力的解釋也不盡相同,諸如權(quán)力就是不受壓迫的自由[10],權(quán)力作為一種權(quán)利存在于世界各地[11]。權(quán)力是和平的,它是基于使用和平力量創(chuàng)造的權(quán)力本身和關(guān)系的個(gè)人內(nèi)化[12],權(quán)力即知情參與[13]等,以上這些觀點(diǎn)都源于特定的思想流派。對(duì)于權(quán)力的認(rèn)識(shí)主要有權(quán)力意志論和關(guān)系論等爭(zhēng)論。
伯特蘭·羅素認(rèn)為權(quán)力的意志是基于人類的欲望,權(quán)力欲在人類無(wú)限欲望中居于首位。同時(shí)他認(rèn)識(shí)到權(quán)力具有不斷擴(kuò)張的特性,掌握權(quán)力的人在權(quán)力運(yùn)作過(guò)程中會(huì)加速這一進(jìn)程,有權(quán)力的人使用權(quán)力一直到遇到邊際才休止。他明確提出要節(jié)制個(gè)人、組織和政府對(duì)權(quán)力的追求,告誡人們要始終把權(quán)力當(dāng)作手段而不是目的。為此明確提出要節(jié)制政府對(duì)權(quán)力的追求,但他并不僅限于尋求政治學(xué)層面的一般路徑如用權(quán)力、法律和多元社會(huì)團(tuán)體規(guī)制權(quán)力,而是以更加宏大的視野從政治、經(jīng)濟(jì)和心理與教育等方面共同入手來(lái)改善權(quán)力[14]。
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論者以法國(guó)著名學(xué)者米歇爾·福柯為主要代表,通過(guò)對(duì)監(jiān)獄和性的歷史研究提出了權(quán)力的一般概念,認(rèn)為權(quán)力是一種關(guān)系,是一種相互交錯(cuò)的非中心化的網(wǎng)絡(luò)。在這種權(quán)力觀里,權(quán)力并不是一種壓制性的外在控制,而是一種生產(chǎn)性實(shí)踐。作為關(guān)系,編織起一張權(quán)力的網(wǎng)絡(luò),不斷創(chuàng)造出社會(huì)成員之間的新的聯(lián)系和作用線。
權(quán)力意志論和權(quán)力關(guān)系論為參與信訪的各主體的行為提供了一種理論解釋。由于權(quán)力具有不斷擴(kuò)張的特性,相較于司法權(quán)的消極,行政權(quán)比較集中且活躍。行政權(quán)的擴(kuò)張沖動(dòng)導(dǎo)致超出法律授權(quán)的越軌現(xiàn)象時(shí)有發(fā)生,法內(nèi)處理與法外解決并行,對(duì)一些司法權(quán)的行使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二)信訪制度的權(quán)利視角
權(quán)利是現(xiàn)代社會(huì)重要的個(gè)體價(jià)值訴求,是個(gè)人至高無(wú)上的被賦予的權(quán)力和自由。權(quán)力在一般意義上來(lái)源于權(quán)利的集中和轉(zhuǎn)化,在權(quán)利分散的常態(tài)下權(quán)力會(huì)高于權(quán)利,因而在更大空間上權(quán)力具有可操作性[15]。在對(duì)權(quán)利現(xiàn)象的深入研究中,人們的視野主要集中在權(quán)利的來(lái)源上。其中霍布斯和盧梭的“天賦說(shuō)”與黑格爾、米德等的“互動(dòng)構(gòu)建說(shuō)”是主要觀點(diǎn)。“天賦說(shuō)”認(rèn)為權(quán)利是個(gè)人與生俱來(lái)的道德品質(zhì),是現(xiàn)代自由主義崇尚的權(quán)利觀念,不依賴法律且不可被剝奪。人類的權(quán)利是建構(gòu)政府和法律合法性的依據(jù)。權(quán)利“天賦說(shuō)”帶有強(qiáng)烈的目標(biāo)建構(gòu)性,缺乏客觀的事實(shí)依據(jù)而常常被人詬病。而“互動(dòng)構(gòu)建說(shuō)”認(rèn)為權(quán)利在人與人的交往互動(dòng)中產(chǎn)生,它的存在主要是基于人際互動(dòng)和人際關(guān)系,是人際互動(dòng)所確定的人際邊界。另外有學(xué)者也認(rèn)為,權(quán)利是人們?cè)诨?dòng)過(guò)程中對(duì)于什么是構(gòu)成共同或共享的不間斷的對(duì)話達(dá)成,話語(yǔ)建構(gòu)物的基礎(chǔ)是時(shí)間文化等[16]。
在我國(guó),人們對(duì)權(quán)利的認(rèn)知主要有兩個(gè)來(lái)源。一是“祖賦人權(quán)”,認(rèn)為權(quán)利是來(lái)源于世代相傳的風(fēng)俗習(xí)慣,是社會(huì)文化的賡續(xù)和傳遞。幾千年的直訴傳統(tǒng)在人們心中烙下了信訪權(quán)的深深印記。二是“群眾權(quán)利”,黨政文件的文字表達(dá)、領(lǐng)導(dǎo)講話的政治表述都強(qiáng)化了人們對(duì)群眾權(quán)利的印象。無(wú)論是“祖賦人權(quán)”還是“群眾權(quán)利”,都只是確認(rèn)了信訪權(quán)的正當(dāng)性,但是沒有給信訪權(quán)劃定必要的邊界。這為信訪權(quán)利的擴(kuò)張和模糊邊界提供了空間和機(jī)遇。
(三)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的互相建構(gòu)與基層涉訴信訪
權(quán)力與權(quán)利是互相建構(gòu)的。查爾斯·霍頓·庫(kù)利認(rèn)為,權(quán)利是先于權(quán)力存在的,因而不能夠漠視權(quán)力的權(quán)利內(nèi)蘊(yùn),否則就是對(duì)權(quán)力的一種誤讀。權(quán)力從根本上來(lái)說(shuō)是來(lái)自權(quán)利,權(quán)利話語(yǔ)享有道德和價(jià)值的至高地位,權(quán)力的運(yùn)行服務(wù)于權(quán)利甚至要將自身轉(zhuǎn)化成權(quán)利[17]。權(quán)力同樣也可以建構(gòu)權(quán)利[18-19]。權(quán)力通過(guò)其強(qiáng)制力和暴力來(lái)規(guī)范和劃定權(quán)利的范圍和行使方式,通過(guò)長(zhǎng)期的權(quán)力運(yùn)作把它內(nèi)化為權(quán)利的心理認(rèn)同和心理秩序。
權(quán)力與權(quán)利的互相建構(gòu)催生了我國(guó)獨(dú)特的基層涉訴信訪問(wèn)題。一方面是國(guó)家權(quán)力邊界重疊和嵌入,另一方面是民眾信訪權(quán)利的群眾性和彈性,它其實(shí)是涉訴信訪的一體兩面。從國(guó)家權(quán)力這個(gè)層面來(lái)看,一些司法案件通過(guò)信訪方式得到解決,這為民眾提供了司法信訪化的示范。從民眾信訪權(quán)利的層面來(lái)看,民眾通過(guò)信訪途徑來(lái)解決本可以通過(guò)司法解決的問(wèn)題,也迫使政府通過(guò)信訪途徑來(lái)解決民眾訴求。
信訪人選擇信訪而非訴訟的一個(gè)重要原因是因?yàn)槿鄙俦WC和維護(hù)其權(quán)利的權(quán)力力量。因此,信訪作為與訴訟、仲裁、調(diào)解、行政復(fù)議等并存的權(quán)利救濟(jì)方式,應(yīng)當(dāng)接納的是上述法定途徑救濟(jì)管轄之外的剩余部分,發(fā)揮糾紛解決的替代功能。然而,來(lái)源不同、種類繁多的權(quán)利之間交叉重疊的要求以及彼此間的邊界的模糊,導(dǎo)致權(quán)利的濫用及與權(quán)利相關(guān)的沖突不可避免。在片面甚至錯(cuò)誤的權(quán)利觀指導(dǎo)下,信訪根據(jù)個(gè)案情境和自身利益選擇適用信訪或司法的規(guī)則和資源進(jìn)行棄法轉(zhuǎn)訪及以訪壓法,非法律因素侵入司法過(guò)程,基層突破政策、法律因素解決問(wèn)題。一般而言,對(duì)于一些信訪方式,一些政府部門容易用“拖與推”來(lái)應(yīng)付,這正是權(quán)力對(duì)權(quán)利的侵蝕。非正常上訪的產(chǎn)生一方面是訪民對(duì)信訪權(quán)利的濫用,另一方面也是訪民對(duì)部分政府部門的拖延之術(shù)采取的一種越軌行為方式。但是無(wú)論是哪種形式,它們都表現(xiàn)為權(quán)利對(duì)權(quán)力的干擾。公民向權(quán)力組織信訪和表達(dá)意見,但由于權(quán)力邊界重疊或者權(quán)力規(guī)則缺失等,如果有權(quán)管理部門推諉拖延順理成章,公民權(quán)利實(shí)現(xiàn)受阻就會(huì)轉(zhuǎn)而尋求其他救濟(jì)途徑而非法定途徑,造成了涉訴信訪。
三、國(guó)家權(quán)力:邊界重疊和嵌入
確定國(guó)家權(quán)力的邊界同時(shí)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權(quán)力之間的協(xié)調(diào),是任何國(guó)家的政治設(shè)計(jì)都需要解決的難題[20]。在我國(guó)體制下,司法權(quán)和行政權(quán)配置存在邊界重疊的特點(diǎn),這是體制的優(yōu)勢(shì)所在。一般意義上,司法權(quán)威通過(guò)維護(hù)權(quán)利及深化政權(quán)合法性,在法治的框架內(nèi)解決利益沖突和矛盾,形成一種法律秩序[21]。同時(shí)在憲法層面上,人民代表大會(huì)也通過(guò)制憲在法律上確定司法權(quán)與行政權(quán)的相互分工及配合關(guān)系,使二者在具體事務(wù)中各司其職,按照自身邏輯運(yùn)行。
(一)以塊為主的權(quán)力重疊
在權(quán)力的實(shí)際運(yùn)作層面上,行政權(quán)力因其主動(dòng)強(qiáng)勢(shì)性對(duì)消極性的司法權(quán)力進(jìn)行著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影響,形成了二者不對(duì)稱的關(guān)系。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立法法》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在我國(guó)體制中,政府除了承擔(dān)行政職責(zé)之外還同時(shí)承擔(dān)部分立法職責(zé)。因此在制度上,司法權(quán)對(duì)行政權(quán)的監(jiān)督存在一定的困難[22]。從現(xiàn)有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分析,“條塊結(jié)合,以塊為主”的司法領(lǐng)導(dǎo)模式,決定了法院同時(shí)承擔(dān)著國(guó)家審判機(jī)構(gòu)和黨政單位的雙重角色。在法院這一組織化體系中,司法機(jī)關(guān)對(duì)政治系統(tǒng)有依賴性,其中的人、財(cái)、物的管轄歸地方“塊塊”。在司法機(jī)關(guān)內(nèi)部運(yùn)作中,領(lǐng)導(dǎo)的行政權(quán)力限制著承辦法官,作出司法裁判后的案件需經(jīng)過(guò)層層審批,無(wú)法“一錘定音”,低層級(jí)的司法權(quán)力受到上層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與影響。
現(xiàn)實(shí)中,完成息訪罷訴的上級(jí)規(guī)定任務(wù)的同時(shí)又要嚴(yán)格遵守法律程序,精通法律技術(shù)遠(yuǎn)遠(yuǎn)不夠,還要熟悉行政運(yùn)行邏輯,這模糊了法官的法律思維,無(wú)法嚴(yán)格地予以界分[23]。同時(shí)作為一個(gè)黨政單位,維護(hù)社會(huì)穩(wěn)定是其重要職能之一,社會(huì)秩序價(jià)值需要得到更多關(guān)注與重視。法院具有雙重角色,既要司法公正又要社會(huì)秩序,這如何定位容易產(chǎn)生一定的張力。
在上述情境下,基層司法人員積極性和責(zé)任感受到打擊,司法裁判的質(zhì)量面臨調(diào)整,可能會(huì)出現(xiàn)“聽從指示辦案”等現(xiàn)象。作為書面性規(guī)范的法律在政治權(quán)力的介入影響下遇到挑戰(zhàn),司法權(quán)置于其他機(jī)構(gòu)的支配與控制之下,審者不判,判者不審。以塊為主的領(lǐng)導(dǎo)體制模糊了司法與行政的邊界[24-25]。
(二)國(guó)家權(quán)力的互相嵌入
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后,在很長(zhǎng)一段“政治掛帥”的時(shí)期內(nèi),法律運(yùn)作要服從意識(shí)形態(tài)要求,法律標(biāo)準(zhǔn)和政治標(biāo)準(zhǔn)要統(tǒng)一。改革開放后,法律地位上升,被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關(guān)于政治和法律模棱兩可的關(guān)系,目前學(xué)界已有眾多討論。有學(xué)者認(rèn)為政治和法律在何種情況下都是一體的,即不論是政治決定法律抑或是法律決定政治[26]。“政法”作為一個(gè)本土概念頗有中國(guó)特色,根據(jù)強(qiáng)世功的研究,在國(guó)家政權(quán)的建設(shè)過(guò)程中,黨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明了權(quán)力的組織網(wǎng)絡(luò),即可以利用組織、民主動(dòng)員、化解矛盾技術(shù)等一整套技術(shù)整合社會(huì)。國(guó)家內(nèi)部的各種權(quán)力之間相互配合,聯(lián)系緊密,而黨的政治領(lǐng)導(dǎo)權(quán)則是主導(dǎo)和協(xié)調(diào)各種國(guó)家權(quán)力的。因此,在執(zhí)政黨的地位特殊的背景下,政治與法律實(shí)質(zhì)上通過(guò)政黨組織的運(yùn)作相互聯(lián)系起來(lái),黨的領(lǐng)導(dǎo)是當(dāng)代中國(guó)政法體制的本質(zhì)特征。在當(dāng)代中國(guó),政法部門主要包括公檢法司等機(jī)構(gòu),承擔(dān)著信訪事務(wù)等維穩(wěn)工作。信訪是新中國(guó)政法傳統(tǒng)下的一個(gè)制度設(shè)計(jì),是一個(gè)“政法問(wèn)題”,信訪人、基層政權(quán)和國(guó)家三個(gè)主體均在政法傳統(tǒng)的權(quán)力網(wǎng)絡(luò)內(nèi)進(jìn)行著相關(guān)信訪活動(dòng)和行為。人們對(duì)國(guó)家權(quán)力的互相嵌入很容易形成一種錯(cuò)覺:可以通過(guò)信訪來(lái)影響司法。
針對(duì)有關(guān)司法訴訟的投訴,包括對(duì)生效判決及其執(zhí)行的申訴,刑事、民事、行政訴訟法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都有明確規(guī)定,“當(dāng)事人可以申請(qǐng)?jiān)賹彽确杀O(jiān)督程序進(jìn)行司法救濟(jì)”。但是,由于人民法院和檢察院法律監(jiān)督程序往往采用與信訪形式相近的方式,而且同時(shí)設(shè)有對(duì)司法人員行為投訴的信訪渠道,因此,案件的申訴往往與對(duì)司法人員工作作風(fēng)和廉政問(wèn)題的投訴相交叉,一度出現(xiàn)訴訟與信訪高度混同情況。部分當(dāng)事人、律師甚至公職人員利用信訪干預(yù)司法訴訟,造成涉訴信訪數(shù)量居高不下。
四、信訪權(quán)利:群眾權(quán)利觀和權(quán)利模糊性
從信訪權(quán)利角度來(lái)看,信訪群眾所信奉的群眾權(quán)利觀模糊了憲法和法律權(quán)利的邊界,用政治話語(yǔ)賦予信訪權(quán)利以政治正當(dāng)性,從而把權(quán)利的濫用正當(dāng)化。如果說(shuō)公民權(quán)利觀的依據(jù)是憲法和法律的話,那么群眾權(quán)利觀的依據(jù)則是政治話語(yǔ)。我國(guó)憲法和法律雖然對(duì)信訪權(quán)進(jìn)行了一定的界定,但仍然不清晰,而且相關(guān)法律對(duì)信訪權(quán)利濫用缺乏應(yīng)有的限制。這些都導(dǎo)致了信訪權(quán)利是一種模糊化的權(quán)利,是一種有彈性的權(quán)利,一種容易被濫用的權(quán)利。
(一)觀念中的權(quán)利:群眾權(quán)利觀與公民權(quán)利觀
在我國(guó),群眾路線是黨執(zhí)政的政治認(rèn)同機(jī)制。群眾路線體現(xiàn)了執(zhí)政黨對(duì)傳統(tǒng)政治資源的依賴,體現(xiàn)出執(zhí)政黨對(duì)群眾的高度重視。深入基層的群眾工作思路則體現(xiàn)了執(zhí)政黨地位的憂患意識(shí)[27]。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在長(zhǎng)期的革命戰(zhàn)爭(zhēng)中創(chuàng)造了“深入群眾、下鄉(xiāng)上山”的意識(shí)形態(tài)和工作傳統(tǒng),這些保證了黨獲得強(qiáng)有力的社會(huì)基礎(chǔ)。因而,群眾路線深刻影響著國(guó)家治理體系的運(yùn)作,而與之對(duì)應(yīng)的“群眾權(quán)利觀”則牢牢支配著我國(guó)信訪制度的運(yùn)作,作為群眾政治屬性的信訪,其政治意義超越法律意義[28]。
在群眾權(quán)利觀支配下,“群眾利益無(wú)小事”,于是科層體制內(nèi)部也發(fā)生了重大變革,黨委直屬的群眾工作部開始出現(xiàn)。群眾工作部旨在用群眾工作統(tǒng)攬信訪工作,黨委直屬表明其地位上升,反映出黨對(duì)于群眾的重視和關(guān)懷[29]。“三到位一處理”的原則正體現(xiàn)出執(zhí)政黨意識(shí)形態(tài)的群眾權(quán)利觀預(yù)設(shè),黨員干部踐行群眾路線需要幫助群眾解決實(shí)際困難。而在某些信訪人邏輯里,群眾通常被定義為“弱勢(shì)群體”,部分群眾罔顧事實(shí),刻意矮化自己的身份。“有事沒事找政府”的萬(wàn)能政府觀念深入人心,信訪行為的合法性和目的的合理性都存在疑問(wèn)。“群眾”的概念在表述上具有相對(duì)抽象性,在實(shí)踐中難以準(zhǔn)確把握其靈活性。
公民權(quán)利觀與群眾權(quán)利觀相對(duì),它意味著國(guó)家強(qiáng)調(diào)制度、程序和法治的地位及權(quán)威。群眾路線模式強(qiáng)調(diào)與民眾打成一片是干部的責(zé)任,而公眾參與模式則強(qiáng)調(diào)參與是民眾的權(quán)利[30]。公民是具有法律意義上的概念,權(quán)利由法律賦予,義務(wù)由法律規(guī)定。與群眾相比,公民具有更多的自主意識(shí)和獨(dú)立性,為民主政治的發(fā)展貢獻(xiàn)自己的力量,同時(shí)為國(guó)家的良性協(xié)調(diào)運(yùn)作提供支持[31]。從國(guó)家角度出發(fā),在“公民”邏輯支配下尊重和保障公民個(gè)體的權(quán)益。在信訪程序上,逐漸朝著科層化、理性化方向發(fā)展,而對(duì)于以往的通過(guò)無(wú)規(guī)范的群眾運(yùn)動(dòng)來(lái)監(jiān)督科層體制的做法則不再依賴。除此之外,在普通民眾的觀念中,公民身份及其所背后承載的政治理念具有重大意義。當(dāng)自身利益受損時(shí),理性民眾在公民意識(shí)指導(dǎo)下會(huì)選擇正當(dāng)途徑和渠道維權(quán),并非盲目的無(wú)秩序的信訪或訴諸法律,而是根據(jù)自身案件屬性選擇正確渠道,提出正當(dāng)、合理、符合法律政策規(guī)定的要求。
因此,自上而下權(quán)利觀的模糊性使信訪人兼具群眾和公民雙重身份,混淆了信訪人的權(quán)利觀,在不同的身份邏輯里遵循著不同的行事風(fēng)格和依據(jù)。帶有群眾色彩的信訪人缺乏程序和法律意識(shí),可能會(huì)突破政策和法律底線而不是根據(jù)糾紛性質(zhì)而合理地上訪或上訴,試圖將社會(huì)糾紛和矛盾以案件形式進(jìn)入司法程序或者將普通案件拖入司法程序解決,為某些托“群眾”之名行各種投機(jī)之實(shí)的人留下謀利空間。與此同時(shí),在“群眾利益無(wú)小事”的群眾權(quán)利觀支配下,出現(xiàn)了相關(guān)部門或領(lǐng)導(dǎo)將信訪案件、司法案件在不分大小、不加分類的情況下不走正常程序進(jìn)行批示督辦及處理。當(dāng)信訪人以公民身份嚴(yán)格要求自己時(shí),法治思想和理念支配著其進(jìn)行著理性信訪行為。黨和國(guó)家對(duì)待具有法律意義的公民時(shí),也越來(lái)越強(qiáng)調(diào)制度、法治的地位和權(quán)威,法治理念滲透到信訪工作中[32]。然而,在信訪實(shí)踐中,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基于政治原則的群眾權(quán)利觀與法治原則的公民權(quán)利觀,可能會(huì)陷入顧此失彼的兩難境地。在其中容易形成守法主義的法治與群眾路線立場(chǎng)不一致的問(wèn)題,更有甚者出現(xiàn)講求的工作方法間的互不兼容的問(wèn)題。群眾權(quán)利觀與公民權(quán)利觀的內(nèi)在張力的處理關(guān)系著訴訪分離改革的深度和廣度[33]。
(二)法律中的權(quán)利:信訪權(quán)的模糊性和彈性
憲法第四十一條明確規(guī)定公民有批評(píng)、建議、檢舉、申訴、控告和取得賠償?shù)葯?quán)利,這些權(quán)利是公民信訪活動(dòng)的法律依據(jù),也是信訪權(quán)的憲法淵源。2005年國(guó)務(wù)院修改后的《信訪條例》中也規(guī)定著有關(guān)信訪權(quán)利與信訪制度相關(guān)的規(guī)范依據(jù)。其中第二條對(duì)信訪的定義與信訪的權(quán)利內(nèi)容作出了明確闡述,根據(jù)規(guī)定信訪權(quán)利主要包括提出建議、意見或投訴請(qǐng)求。但對(duì)于信訪的權(quán)利屬性定位,實(shí)務(wù)界和學(xué)術(shù)界都存在爭(zhēng)議,即信訪是一種權(quán)利還是行使權(quán)利的一種方式和手段?
從權(quán)利性質(zhì)而言,信訪權(quán)是公民的一項(xiàng)基本權(quán)利,包含了憲法規(guī)定的等多項(xiàng)權(quán)利內(nèi)容,體現(xiàn)出政治參與、民主監(jiān)督和權(quán)利救濟(jì)的多重屬性。除此之外,有學(xué)者從功能角度來(lái)看,認(rèn)為是政治性權(quán)利的監(jiān)督權(quán)和非政治性權(quán)利的救濟(jì)權(quán)[34]。另外有學(xué)者將憲法第四十一條的內(nèi)容統(tǒng)稱作“信訪權(quán)”,認(rèn)為它是由建議、申訴、控告和檢舉的參政權(quán)延伸出的一種較為特殊的政治權(quán)利[35]。作為一項(xiàng)不可或缺的基本權(quán)利,信訪權(quán)被《信訪條例》確認(rèn)為一種法定權(quán)利的同時(shí)也被認(rèn)定為是一項(xiàng)現(xiàn)實(shí)權(quán)利,為行動(dòng)者提供了一種親近權(quán)力資源的可能。公民在實(shí)踐中可以反復(fù)行使這項(xiàng)權(quán)利,采用合法形式向黨政部門提出意見、建議。但有學(xué)者認(rèn)為,憲法和《信訪條例》的本意不在于直接賦予信訪人某種權(quán)利,而是通過(guò)制定相應(yīng)程序規(guī)則,使信訪人能夠啟動(dòng)并進(jìn)入程序,信訪權(quán)是作為一種程序性權(quán)利而存在的。進(jìn)入相應(yīng)程序后再根據(jù)實(shí)體權(quán)利分析確定其訴求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是否存在夸大事實(shí)和謀取利益的空間,最終決定是否被采納或得到救濟(jì)。如果實(shí)體權(quán)利得不到維護(hù),就會(huì)造成程序空轉(zhuǎn),信訪權(quán)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36]。
然而,與上述觀點(diǎn)相悖的是,有學(xué)者指出信訪僅僅是行使上述這些權(quán)利的手段和方式,它們與信訪之間存在邏輯上的交叉關(guān)系。批評(píng)、建議、申訴、控告、檢舉等權(quán)利的行使方式多樣,信訪只是其中重要的形式之一,諸如網(wǎng)絡(luò)新聞媒體或者國(guó)家機(jī)關(guān)都可以行使上述權(quán)利。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信訪作為傳統(tǒng)的實(shí)現(xiàn)權(quán)利的一種方式可能會(huì)被終止,不復(fù)存在,但權(quán)利會(huì)依然存在。消失的是行使權(quán)利的一種方式,而信訪自身并不構(gòu)成單獨(dú)的法律權(quán)利[37],而且信訪的內(nèi)容紛繁多樣,除了負(fù)面的批評(píng)、控告等信息外,表?yè)P(yáng)、激勵(lì)等正面內(nèi)容也廣泛存在,如信訪人寫信感謝政府機(jī)關(guān)及其工作人員為人民辦實(shí)事[38]。因此,作為一部行政法規(guī),盡管列明了相關(guān)權(quán)利內(nèi)容,但卻并不意味著就屬于“信訪權(quán)”。《信訪條例》旨在規(guī)范行政機(jī)關(guān)處理信訪事項(xiàng)的工作流程,真正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不在于確立并保障公民信訪權(quán)利,而是尋求維護(hù)信訪秩序與社會(huì)穩(wěn)定的解決之道[39]。
五、基層涉訴信訪法治化改革的實(shí)現(xiàn)路徑
正確處理權(quán)利與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調(diào)適權(quán)利與權(quán)力的邊界范圍是涉訴信訪改革的重要工作。涉訴信訪改革的重要內(nèi)容就是訴訪分離厘清權(quán)力邊界,對(duì)行政權(quán)和司法權(quán)作出合理調(diào)適,讓權(quán)力運(yùn)行回歸到正常軌道,進(jìn)行法治化正常運(yùn)轉(zhuǎn),主要表現(xiàn)在重塑公民權(quán)利觀,提高司法權(quán)威性和公信力,合理定位信訪救濟(jì)和司法救濟(jì)的關(guān)系。
(一)重塑公民權(quán)利觀
公民權(quán)利觀是基于憲法和法律的權(quán)利觀念,具有比較明顯的邊界性、法律性。群眾權(quán)利觀是基于政治話語(yǔ)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權(quán)利觀念,具有模糊性和抽象的彈性。建立在公民權(quán)利觀基礎(chǔ)上信訪行為在追求自身權(quán)利的同時(shí)也會(huì)兼顧責(zé)任、秩序和義務(wù),從而避免一些群眾借助于政治話語(yǔ)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模糊表達(dá)而無(wú)限擴(kuò)展,甚至吞噬法律規(guī)定的信訪人應(yīng)該承擔(dān)的責(zé)任、秩序和義務(wù)。
首先,重塑公民權(quán)利觀要明確信訪權(quán)的邊界,即要告知信訪人信訪權(quán)包括哪些內(nèi)容,哪些不屬于信訪權(quán)的范疇。其次,重塑公民權(quán)利觀要正確處理公民權(quán)利觀與群眾權(quán)利觀的關(guān)系,在相關(guān)的黨規(guī)國(guó)法中要明確群眾權(quán)利觀服膺于公民權(quán)利觀。最后,重塑公民權(quán)利觀要正確處理情理法的關(guān)系,在信訪治理過(guò)程中,法處于最高地位,理次之,情最輕。
(二)以訴訪分離提高司法的權(quán)威性
司法權(quán)威是“法律至上”理念在司法領(lǐng)域的體現(xiàn)和延伸。許多當(dāng)事人將獲得救濟(jì)的希望寄托在諸多偶然因素上,抱著機(jī)會(huì)主義的心態(tài),動(dòng)搖了司法程序的正當(dāng)性和生效判決的不可變更性。當(dāng)事人應(yīng)該積極行使自己的訴訟權(quán)利,而不應(yīng)該無(wú)故放棄,轉(zhuǎn)而抱著“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心理去惡意信訪,干擾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秩序。
訴訪分離在司法訴訟的各個(gè)程序階段都起著重要作用。在司法程序尚未開始時(shí),訴與訪的分離強(qiáng)化訴權(quán),讓訴訟的歸訴訟,信訪的歸信訪,通過(guò)甄別發(fā)揮司法裁判的作用。對(duì)于司法程序尚未完成的涉訴信訪和已窮盡司法程序的信訪矛盾分類處理,有利于維護(hù)人民法院的訴訟程序。通過(guò)起訴、上訴或申請(qǐng)?jiān)賹従S護(hù)合法權(quán)益的案件,納入訴訟制度框架之內(nèi),有利于減少外部因素對(duì)審判活動(dòng)的不合理干涉,打擊當(dāng)事人在訴訟過(guò)程中惡意濫用信訪的投機(jī)心理。同樣,在司法程序已經(jīng)結(jié)束時(shí),實(shí)行訴訪分離發(fā)揮著司法裁判的終局性作用,對(duì)已做出判決的案件實(shí)行終結(jié),提高司法的權(quán)威性。
除此之外,實(shí)行訴訪分離可以有效對(duì)司法程序和信訪程序終結(jié)。以往針對(duì)涉訴信訪案件,各級(jí)法院迫于信訪人纏訴纏訪的壓力,為了息訴罷訪,不得不一次次啟動(dòng)再審,甚至在多次再審后仍繼續(xù)信訪,“結(jié)案不息訪”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信訪的終結(jié)并非公民權(quán)利的終結(jié),訴訪分離中對(duì)當(dāng)事人因客觀因素如生活困難信訪做好幫扶救助工作,通過(guò)法律援助和綜合治理等手段積極救濟(jì)。對(duì)于無(wú)法律依據(jù)的無(wú)理信訪和存在情理的有理卻無(wú)法的信訪仔細(xì)甄別對(duì)待,對(duì)無(wú)理信訪人員采取果斷措施,而信訪人合理的法外要求給予教育疏導(dǎo)之外適當(dāng)?shù)貙?duì)有困難的人員申請(qǐng)司法救助,使信訪終結(jié)事項(xiàng)依法有序退出法律處理程序,從而在整體上提升涉訴信訪矛盾糾紛的化解效力[40]。
(三)合理定位信訪救濟(jì)與司法救濟(jì)的關(guān)系
伯爾曼曾說(shuō)“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shè)”[41]。維護(hù)當(dāng)事人合法權(quán)益是權(quán)利救濟(jì)存在的前提,不論是司法救濟(jì)或是信訪救濟(jì)。但二者存在區(qū)別與先后之分,信訪救濟(jì)只能是彌補(bǔ)司法救濟(jì)不足的糾錯(cuò)機(jī)制。權(quán)利救濟(jì)是正當(dāng)?shù)模瑫r(shí)也是有限度的。因而,治理涉訴信訪問(wèn)題,堅(jiān)持司法救濟(jì)的有限性原則是必須的。
從國(guó)家角度來(lái)看,信訪人所需解決矛盾的成因和性質(zhì)存在較大差別。有些因司法因素引起的糾紛需要經(jīng)過(guò)法院訴訟,由法院牽頭解決。但并非所有矛盾糾紛都需要經(jīng)過(guò)法院,由法院處理。這樣客觀上會(huì)超越司法的職權(quán)范疇,容易使“案多人少”的法院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尷尬境地。實(shí)行基層訴訪分離正是可以分類解決上述問(wèn)題的有效途徑,對(duì)由非司法因素引發(fā)的信訪問(wèn)題進(jìn)行救助幫扶,納入社會(huì)綜合保障體系,減輕法院壓力并重點(diǎn)強(qiáng)化司法審判工作。
從信訪人角度來(lái)說(shuō),諸多涉訴信訪案件成因復(fù)雜。當(dāng)事人的訴求眾多且缺乏相關(guān)法律知識(shí),運(yùn)用多種渠道去投訴或信訪,抑或是信訪當(dāng)事人主觀上存在某種惡意,沒有積極行使自己的訴訟權(quán)利,而選擇去信訪。在法律明確賦予了公民訴權(quán)的情況之下,通過(guò)基層訴訪分離,可以有助于公民充分認(rèn)識(shí)和辨別自己所享有的訴訟權(quán)利,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cuò)誤的,最后按照正常合法程序行使權(quán)利。引導(dǎo)當(dāng)事人在權(quán)利受到損害時(shí)及時(shí)尋求司法救濟(jì),避免延誤訴訟時(shí)間最后失去訴權(quán)后去尋求其他的救濟(jì)方式。同時(shí)在司法手段還未窮盡的時(shí)候,督促當(dāng)事人合法合理地行使訴求,最大限度地獲得司法救濟(jì)。
參考文獻(xiàn)
[1]? 楊小軍.信訪法治化改革與完善研究[J].中國(guó)法學(xué),2013(5):22-33.
[2]? 彭小龍.涉訴信訪治理的正當(dāng)性與法治化——1978—2015年實(shí)踐探索的分析[J].法學(xué)研究,2016(5):86-107.
[3]? 肖文.非正常涉訴信訪治理的路徑探討——以電影《我不是潘金蓮》為引[J].石河子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5):32-39.
[4]? 杜睿哲.涉訴信訪法治化:現(xiàn)實(shí)困境與路徑選擇[J].西北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4):112-120.
[5]? 唐震.“訴”“訪”分離機(jī)制的正當(dāng)性建構(gòu)? 基于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和法律規(guī)范的雙重視角[J].法律適用,2011(9):91-95.
[6]? 謝家銀,陳發(fā)桂.訴訪分離:涉訴信訪依法終結(jié)的理念基礎(chǔ)與行動(dòng)策略[J].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xué)報(bào),2014(6):96-101.
[7] 吳英姿.從訴訪難分看治理模式創(chuàng)新[J].法治現(xiàn)代化研究,2017(1):120-133.
[8]? 羅劍銘.訴訪分離制度初探[J].法制博覽,2016(21):66-67.
[9]? 盧偉.訴訪分離的實(shí)現(xiàn)困境與制度應(yīng)對(duì)[J].決策導(dǎo)刊,2014(3):38-41.
[10]?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M]..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70: 36.
[11]?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 Gordon, Ed.)[M]. New York: Pantheon, 1980: 45.
[12]? CHINN, P. (2008). Peace and power (7th ed.). Boston: Jones & Bartlett, 2008: 87.
[13]? CAROSELLI, C., & BARRETT, E. A. M.(1998). A review of the power as knowing participation in change literature[J]. Nursing Science Quarterly, 11, 9-16.
[14]? 龐飛.為權(quán)力之“惡”辯護(hù)——權(quán)力的話語(yǔ)遁入與效用[J].南京郵電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3):60-68.
[15]? 嚴(yán)存生.“新權(quán)利”的法哲學(xué)思考[J].江漢學(xué)術(shù),2019(3):5-12.
[16]? Jim Lfe.人類權(quán)利與社會(huì)工作[M].鄭廣懷,何小雷,譯.上海:華東理工大學(xué)出版社,2016:92.
[17]? 段凡.法的國(guó)家屬性與法治國(guó)家意識(shí)的構(gòu)建[J].江西社會(huì)科學(xué),2016(11):16-22.
[18]? 劉樹橋.法的內(nèi)容:權(quán)利、權(quán)力、義務(wù)之思辨[J].南昌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8(4):56-60.
[19]? 王莉君.法學(xué)基礎(chǔ)范疇的重構(gòu):對(duì)權(quán)利和權(quán)力的新思考[J].法學(xué)家,2005(2):118-124.
[20]?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卷[M].許明龍,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9:171.
[21]? 季金華.司法權(quán)威論[M].濟(jì)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45.
[22]? 朱玳萱.憲制視閾下我國(guó)司法權(quán)和行政權(quán)配置的障礙與途徑[J].特區(qū)實(shí)踐與理論,2017(4):71-76.
[23]? 梁平,陳燾.司法權(quán)力去行政化改革——基于H省某中院案件評(píng)查糾錯(cuò)與動(dòng)態(tài)式主審法官負(fù)責(zé)制的調(diào)研[J].河北法學(xué),2015(10):125-139.
[24]? 周永坤.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規(guī)范化——論司法改革的整體規(guī)范化理路[J].蘇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6):59-64+199-200.
[25]? 李桂林.司法權(quán)威及其實(shí)現(xiàn)條件[J].華東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3(6):4-14.
[26]? 伍德志.欲拒還迎:政治與法律關(guān)系的社會(huì)系統(tǒng)論分析[J].法律科學(xué)(西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2(2):3-14.
[27]? 劉平.單位制的演變與信訪制度改革——以信訪制度改革的S市經(jīng)驗(yàn)為例[J].人文雜志,2011(6):154-162.
[28]? 秦小建.信訪納入憲法監(jiān)督體制的證成與路徑[J].法商研究. 2016(3):80-91.
[29]? 田先紅.群眾工作部改革:緣起、效度及限度[J].求索,2017(3):20-28.
[30]? 王紹光.不應(yīng)淡忘的公共決策參與模式:群眾路線[J].民主與科學(xué),2010(1):47-49.
[31]? 李華,徐友龍.群眾路線: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執(zhí)政規(guī)律的邏輯起點(diǎn)[J].觀察與思考,2017(3):85-92.
[32]? 田先紅,羅興佐.“群眾”抑或“公民”:中國(guó)信訪權(quán)利主體論析[J].華中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3):34-43.
[33]? 李賀樓.信訪制度改革中的兩難問(wèn)題:實(shí)質(zhì)與解決方向[J].中國(guó)行政管理,2018(4):115-120.
[34]? 孫大雄.信訪制度功能的扭曲與理性回歸[J].法商研究,2011(4):52-55.
[35]? 林喆.信訪制度的功能、屬性及其發(fā)展趨勢(shì)[J].中共中央黨校學(xué)報(bào),2009(1):89-90.
[36]? 任喜榮.作為“新興”權(quán)利的信訪權(quán)[J].法商研究,2011(4):37-41.
[37]? 范進(jìn)學(xué).信訪行為之權(quán)利與功能分析[J].政法論叢,2017(2):17-27.
[38]? 林華.信訪性質(zhì)的溯源性追問(wèn)[J].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1(6):15-30+158.
[39]? 洪丹娜.信訪的重新定位——兼論公民監(jiān)督權(quán)與信訪的關(guān)系[J].貴州社會(huì)科學(xué),2015(7):101-106.
[40]? 唐龍生,劉菲.論訴訪分離工作機(jī)制之構(gòu)建[J].法治研究,2010(1):77-80.
[41]? 伯尓曼.法律與宗教[M].梁治平,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2:39.
A Study of Grassroot Petitions Related to Lawsuits basis of Power and Right Relation
Kong Fanyi1? ?ChengYing2
(1.Wu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Maxism,Wuhan, Hubei 430072; 2.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Abstract: Petitions related to lawsuits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in petition c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power, petitions related to lawsuits are the result of vague boundaries and mutual embedding of state pow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 right, they are the derivation of the overlapping of petition rights and litigation rights and the concept of mass righ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right, we can clearly observe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state power and civil right in letters and visits related to lawsuits.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the reform of petitions related to lawsuits needs to clarify the governance boundaries between state powers; on the other hand, it needs to separate the petition rights and litigation rights, and shape the petitioners' view of citizenship right.
Key Words: Petitions related to lawsuits; State Power; Civil Rights
(責(zé)任編輯:易曉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