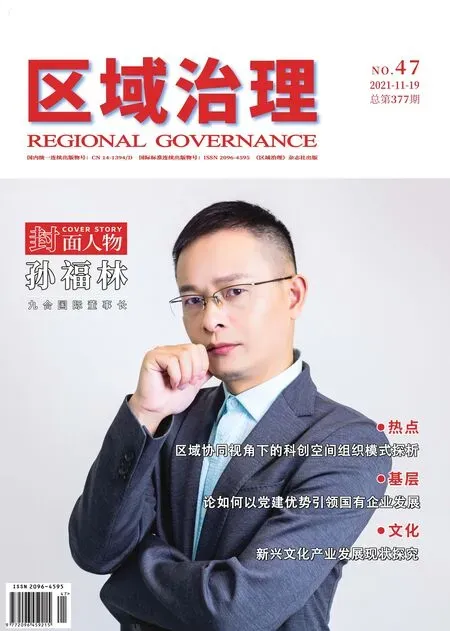論著作權法上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定性
沈陽師范大學法學院 李雨桐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現狀及問題提出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現狀及分析
具有獨立訓練、決策的機器不僅能夠對社會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且具備經濟優勢,整體而言也更符合長期發展的趨勢。“微軟小冰”這款第七代對話式人工智能由微軟互聯網工程院首次發布于2019年8月,僅用五年時間便占據全球絕大部分流量份額。目前為止,小冰可以同時擔任歌手、詩人、設計師、播音員等多個社會化角色,成為人工智能的典型代表,同時,其參與“創作”的歌曲、詩篇也產生了大量的市場價值和經濟利益。李世石是韓國高水平的職業圍棋九段選手,以總比分4比1不敵谷歌創造的人工智能系統AlphaGo。這一系統亮相之初,就超越了人類職業圍棋的最高水平,即使柯潔這名世界排名第一的圍棋選手,在之后的比賽中也不敵更具備專業表現的AlphaGo。
AlphaGo本身的系統具有嚴密的神經網絡,久之生成比人類更加獨到的圍棋思維,使得對弈手法已經達到了頂尖級水平。與其說其在利用人類智慧生成的已知棋譜來戰勝人類,倒不如說其通過分析、匯總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對弈理念,并處在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中。這種經過嚴密數字計算的圍棋智慧是否歸功于人工智能本身,需要我們進一步分析。
(二)問題提出
在目前學術界,主要存在兩種觀點,分為“作品觀”與“非作品觀”。“作品觀”認為,人工智能通過深度學習網絡構建出的生成物,與自然人創作出的作品沒有本質區別。①“非作品觀”認為,人工智能的運行機理僅是算法和程序,并不存在個性化思想表達的過程。②而在人工智能的生成物的認定上,對于核心判斷條件也存在些許差異。有學者認為,假設同一成果是由人類創作的,能夠被認定為具有獨創性,那么,若同一成果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在不考慮該成果所源自的主體身份這一前提下,其獨創性亦應被認可。”③這一觀點認為,在認定時只關注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外在特征,是一種以相似為判斷標準的客觀外在表現形式,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體身份是判定其生成物是否具有著作權的關鍵因素。還有觀點認為,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有一個隱含要件,那就是“作品”必須是自然人所創作的,非人的動物等其他主體的生成物不被著作權法所保護。④而人工智能作為主體的“非人性”特點,是否可以作為獨立的法律主體享受其生成物帶來的著作權有待進一步討論。歐盟于2017年頒布的《歐盟機器人認識法律規則》中規定,對智能機器人的認定必須滿足至少有一點生理上的支持。⑤這表明,是否具有獨立的意思表示等生物特征是將機器人認定為人的必要條件。而截至目前,人工智能并不擁有真正的智慧,也沒有自主的意識,它們的存在是基于對整個人類社會的已知,由人類自主將各項數據資料輸入系統中,以此深入模擬人類的某些思維活動與智能行為,同時根據人類的各項指令進行相應的“創作”活動,只是一個沒有思維、沒有意識的輔助工具,既然其本身不存在主體性,那么其生成物需要被視為作品得到特殊的法律保護嗎?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界定條件
(一)作品本身的獨創性
作品是一種不僅具有獨創性,還具有文學、藝術或科學性質的藝術成果,通過作者以一定有形的形式復制的獨創性而體現。從該定義中不難發現,必要因素是其獨創性,只有作品以有形的形式表現出來才有被認定的可能。包括文學、音樂、戲劇、舞蹈、錄音和建筑等作品,在我國著作權法中是符合著作權的客體。但是,僅僅是模仿的作品并不受著作權保護,更重要的是原創性和獨立性。⑥作品當中可以體現創作者的獨立思維能力,有作為創作物本身的獨立藝術特點,并不是通過隨機性質的任意組合拼裝在一起的機械化行為。雖然人工智能一直努力向人類的思維模式看齊,但由于現有認知水平的限制,人工智能一直未能真正實現像人類一樣思考,即使數據庫中的內容和人類大腦中存儲的知識一樣多,也無法真正模擬人類的創作活動,其作品本身需要體現人工智能的獨特所在表明其作品的特定屬性,而且還要完全具備獨特思維和顯著特征。
(二)創造過程的獨特性
在創作過程方面,如果人工智能系統除最初的程序設定是高度獨立于制作者或使用者的指令,可以通過自我信息整合、數據匯總凝練的結合產出生成物,而不單單是由人類設定寫作字數、創作風格、慣用詞匯等框架性問題,才可以認定人工智能的生成物已符合創建條件的一個方面。在人類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中,直覺或靈感恰恰是賦予作品價值的靈魂所在,在高水平的創作過程中,這種重要性體現得尤為明顯,同時這也是造成同類型作品之間有差別的主要原因。⑦但是,人工智能的運行是基于人們在現有的知識儲備與探索領域的基礎上的一種復刻、發散,這種神經循環網絡的思想是由人類所賦予的一種模仿行為,故只具有“近人性”。確定其生成物是否為獨創作品更需要考慮的是,其必須是由獨特的創造力的過程中產生的智力成果物,而不僅僅是制造者或使用者發明出來的現代化設備的機械運動。
(三)運行模式的智能性
僅僅通過幾組復雜函數或繁瑣算法運行的人工智能系統在運行過程中缺乏必要的“人類思維”,其仍然沒有掌握人類智慧的精髓,而通過智能化學習或獨立訓練的人工智能系統,在日積月累的不斷深入分析數據、積累經驗的過程中,才有可能生成一種高度的智慧與人類相媲美。人工智能獨立創作出符合條件的客體,那么就應該認定,從整個過程出發到最終創作結果是應當為法律所承認的。換而言之,如果人工系統被創建了一個嚴密且基礎的神經網絡系統,其基于此高度整合后,創造出更加體現其獨特“思維”的生成物,那么,人工智能系統應該被視為創作者,其作品也應當被賦予相應的著作權等知識產權。但是,這樣的假設可能會導致對所有權合法性的疑問,因為人工智能系統本身還沒有被視為是自然人等主體資格。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具有著作權
(一)不具有獨創性
首先,人工智能系統就其整體而言既不是獨立的法律主體,也不是擁有獨立人格的公民,其從屬于制作者或者使用者,是他們的私有財產,受人支配。而人工智能既不可能成為利益的負擔者,也不可能成為主體。因為其不會“犯錯誤”,即便“出錯”也是由于程序出現BUG,不是其自己的選擇和決斷,因為其沒有自由意志。⑧故我們需要區分惰性工具與真正創造性的人工智能系統之間的區別。其次,獨創性中的“獨”也需要體現在作品的產生過程,不能僅僅參酌智力成果的外在表現形式就斷定性質歸屬問題。人工智能系統在產生智力成果的運作過程中,是由人類編程創設并且由人類主動進行操作的,人工智能系統只擔任了一個輔助參與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服從指令后生成人類需要的特定物,也是無法體現其“獨”的存在。最后,制造者可以根據使用者的購買需求,將相應的程序輸入人工智能系統中,各項數據經過高度匯總形成一個體系化的神經網絡,基于此進行各項“創作”活動。人工智能可以根據莎士比亞的寫作風格創作出風格近似的詩篇,也可以根據概率算法精準計算地震的發生時間,還可以依照周杰倫的曲風譜寫出膾炙人口的歌曲等等。但是,歸結到底還是一種對人類創作的仿制,是基于對人類社會當前了解的知識整合,這種機械化的模仿行為并不具備感性的創造。
(二)違背開發利用的最初目的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書中提到,如果社會科學中的進步要求摧毀我們所熟悉的關于規則、義務、權利和法院的法律本體論或者熟悉的法治等價值,這種社會科學研究就會變成某一事物的社會學,而不是法律社會學。⑨人類利用現代化技術開發人工智能之初,旨在使用更為先進的技術輔助人類,以滿足社會發展需要。如果已經涉及到破壞現有的相對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那么就不完全屬于法學的研究范疇。故人工智能的發展應該側重于補充人類能力,而不是取代人類。受實證主義與功利主義的影響,一些法律特征被認為具有相似性,但不符合創作本質的作品,也可以作為著作權的客體。這種模糊的界定會使在認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權問題時,出現著作權無主等無法管控的混亂局面,這與人工智能系統開發的目的是不符合的。由于人工智能系統的思想是由人類所賦予的,故其產生的主要作用應該在于利用智能化程序思維實現對人腦的模擬,并為人類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條件。而且,如果任何法律主體都有可能成為作家,那么他們無需具備相應的文化素養、理論基礎、感性認知等內在品質,也無需花費畢生心血潛心研究,只要有足以購買人工智能系統的金錢就夠了。豐厚的資產可以讓購買者或使用者同時擁有多種智能化系統,再用資金促使系統更新換代,以提高創作效率,在更短時間內以量產的方式同時成為文學家、哲學家、作曲家,甚至是一個棋牌高手。久而久之,人工智能系統實時運轉、批量授權,變成了一場比拼速度的較量,評價標準也從最初美感與意境的審美體驗變成了秒產速度的數量對決,創作活動就成為了消遣游戲,其產生的智力成果也會導致產品泛濫等亂象。
(三)判定成本高,不具備可操作性
法律在知識財產工具論的立場上被認為是一種工具,計算知識產權保護的社會成本也獲得支持。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具備著作權,執法成本是重要的判定因素,更加有利于衡量可行性問題。承認人工智能產生的智力成果在法律上的主體地位不僅需要創作成本,還需要保護成本及尋租成本等加成。
人們從事創作的熱情不會僅僅由于缺乏物質激勵而產生絲毫的減損。人腦的能力不僅不如人工智能系統、精確、高效,效率也遠遠落后。在持久性的產出下,可能會使得某些領域的作品在不遠的將來達到極致。因此,人工智能的生成物基本不可能出現供給不足的情況,在理論上便不再具備稀缺性。利用現存科技手段消耗大量司法資源,從人員到技術的調查斟酌、逐一判定是否應賦予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問題是一種司法浪費,投入遠遠高于可以得到的文化收益與經濟效益。可以預見的是,由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所具備的特點,不僅使法律的解讀變得更加復雜,還將增加權利人維權以及法院的執法成本。同時,法律解讀會因為著作權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護變得更加復雜。而由于人們固守傳統著作權法的理念,保護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的執法成本、執法難度也會隨之加大。
四、結論
不能否認,或許人工智能會產生一種全新的創作方式,是足夠智能化的,而且有些創作背后也確實蘊含著一些機理是人工智能更容易實現的。這種創作方式的創新也許可以產生人類無法完成的杰作,給文化、藝術領域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但就當下而言,這些可能性尚不存在,人工智能的生成物是否具有獨創性仍需遵循原有的法律體系去衡量。將人工智能生成物認定為作品的現實意義可能僅僅在于使企業因此獲得更多的融資,或者產品獲得更好的售價。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產業發展,但其收益遠小于破壞著作權法原有體系所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在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若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僅為了迎合短暫的產業呼聲而修改,這對法律應當具備的權威性、穩定性將會造成巨大沖擊。
注釋
①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著作權認定[J].知識產權,2017(3):3-8.
②羅祥,張國安.著作權法視角下人工智能創作物保護[J].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7(6):144-150.
③曾田.人工智能創作的版權侵權問題研究[J].河北法學,2019(10):176-189.
④鄭國梁.人工智能生成物之著作權法保護的理論基礎[J].法制與社會,2019(3):126-128.
⑤參考知乎《歐盟人工智能相關法律規則之-歐盟機器人民事法律規則-中文譯文》https://zhuanlan.zhihu.com/p/31457515?edition=yidianzixun&utm_source=yidianzixun&yidian_docid=0I4UtZlI
⑥吳維錠,張瀟劍.人工智能致第三方損害的責任承擔: 法經濟學的視角[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9(3):11-26.
⑦郭少飛.“電子人”法理主體論[J].東方法學,2018(3):38-49.
⑧龍文懋.人工智能法律主體地位的法哲學思考[J].法律科學,2018(5):58-63.
⑨參見哈特《法律的概念》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