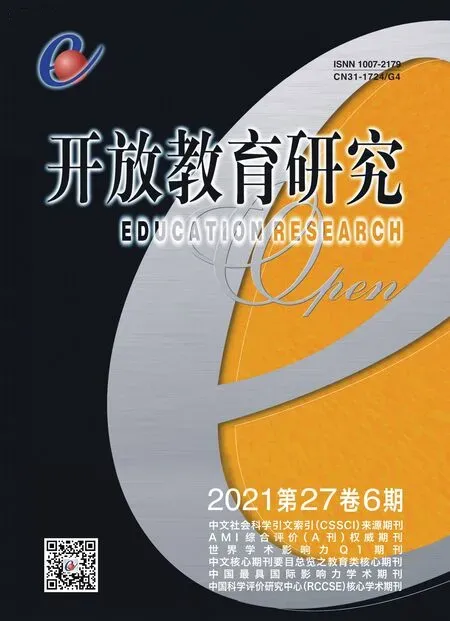邁向“生態正義”的新人文教育:論后疫情時代教育的范式轉型
彭正梅 王清濤 溫 輝 連愛倫 劉 釵
(1.華東師范大學 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2. 華東師范大學 教育信息技術學系,上海 200062)
202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20)提出2050教育宣言(以下簡稱《2050年教育宣言》),指出必須告別西方傳統的人文主義教育傳統,拋棄其《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中對人文主義給予的信任和希望。《2050年教育宣言》要求,面對人類造成的多重生存威脅,人類應對可持續發展以及全球生態危機教育做出革命性的調整,概言之,人類必須轉向基于“生態正義”(ecological justice)的教育新范式,必須尋求“超越西方視野”的知識形態、認識思維及生活方式。
中國傳統文化智慧早指出,“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等,2000)。也就是說,教育是一種化成天下,需要在“觀乎天文”和“觀乎人文”的基礎上不斷調整(其命維新)。因此,當世界變化了,人也要跟著變化;當事實變化了,我們的結論也需要調整。按照這種思路以及教科文組織《2050年教育宣言》的精神,我們亟需新人文教育,而不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教育。
國內已有學者翻譯、介紹《2050年教育宣言》(王夢潔,2021;吳文婷等,2021;阿弗里卡·泰勒等,2021),但缺乏進一步的研究。也有學者對人類教育的未來提出了類似的憂慮及積極設想。例如,范國睿(2020)指出,新冠病毒全球大暴發,宣告人類教育系統正處于這個時代最危機的時刻,我們迫切需要從教育生態學的立場,重新思考和審視教育的未來,以恢復和重建教育生態,保持教育系統活力。石中英(2001)也指出,人文教育在教育系統中具有獨特的價值。當前的教育改革應積極彰顯教育的人文性,改革和振興人文教育。周洪宇(2015)更是直接提倡以新人文精神引領教育未來,認為“新人文教育是一種建立在全球視野、全球意識和全球觀念上的新教育,是以人為核心的和諧共生的新教育,是在張揚個性的基礎上又具備人類整體性意識的新教育,是一種注重綠色生態可持續的新教育,是繼承西方人文主義歷史傳統和精神,同時又融入中華文化人文價值和精神的新教育”。
鑒于此,本研究在簡要討論西方人文主義后,主要從近年來逐漸復興的西方、日本、印度以及中國關于生態教育資源的智慧傳統中探討和確定以生態正義為核心的新人文教育的基本特征,強調人類需要通過“爭取承認”的文化斗爭和教育斗爭來超越西方人文主義知識的主導和霸權地位,扭轉人類整體所面臨的緊迫的生態危機,促進教育服務人類未來福祉,實現人類與世界共生。
一、引言:西方人文主義的基本信條——個人是世界的中心
教科文組織《2050年教育宣言》所說的人文主義,源于西方的文藝復興時期。皮科·米蘭多拉(Mirandola,2012)在其被視為“人文主義宣言”的《論人的尊嚴》(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一書中指出,人被置于世界的中心,但人沒有被賦予確定的形式和特性;與其他萬物擁有確定的特性但受制于設定的法則限制不同,人沒有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決定自己的特性;人是自身自由的形塑者,可以把自身塑造成自己愿意的任何形式。在米蘭多拉看來,人的本質在于人能夠反思,能夠體驗生命的困頓,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人在世界萬物的等級中沒有固定的位置,可以向上成為天使,向下墮落為畜類,這都取決于他如何使用自己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說,人的精神力量就是改變生命世界的中心。
米蘭多拉(2012)所謂的人是世界中心的“人”,是個體的人,不是人的共同體或集體。每個人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世界的中心。每一個體都是世界的中心。人之所以為人取決于他的行動和決心。笛卡爾繼承了這種精神氣質,強調“我思”是唯一確定的事情。康德把這種“我思”的能力界定為“獨立使用自己理性的”啟蒙,并認為作為一種理性精神的啟蒙會不斷地向全球擴展,最終實現每個人獨特的自然天賦,即理性。康德(1990)認為,這是大自然偉大的隱秘計劃。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一書中探討了精神(理性)如何逐漸獲得實現(即精神的自我認識)的世界歷史的進程。
隨著西方現代文明的不斷擴展,這種理性至上的個體自主和個體主義,幾乎被認同為現代性的基本標志,成為所有追求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努力追求的精神氣質。培養這種理性自主及個人主義幾乎成了所有重要的現代教育家如盧梭、洛克、赫爾巴特、杜威以及布魯納的基本信條,成為西方教育乃至現代教育的基本特征(彭正梅,2010b)。同樣,這種西方人文主義也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哲學”,體現于《學會生存》《學習:財富蘊藏其中》以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等報告中,構成其核心精神。
但是,對于人類面臨的不斷增加的全球議題,如可持續發展、和平、生態、人權等無法獲得國際社會更多的共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越來越認識到西方人文主義的內在缺陷與不足。正如《2050年教育宣言》參與者之一西洛娃(Iveta Silova)指出的,人類已經陷入到主體和客體、自然和文化、心靈和肉體、時間和空間、自我和他者等被分離開來的笛卡爾式教育中不能自拔。進而言之,正是由于現代學校教育的主導邏輯,即人的獨特主義和(新)自由的個人主義的現代學校教育的主導邏輯永恒化了等級性秩序,把人置于萬物之上,把人和世界分離開來,并為對他者/它者的控制和剝削加以合理化,強化了人類面對新冠疫情危機的分裂意識和分裂行為(Zhao,2020)。
實際上,對于西方人文主義以及奠定在其之上的現代性的批判,如各種后現代、后殖民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可謂汗牛充棟。人們對西方人文主義教育傳統的批判和反思也從未停止過。例如,美國當代環境教育哲學家包華士(C. A. Bowers)更是直接揭露了西方現代化教育的后果就是“對自然的剝削、對環境的破壞、對傳統價值的否定、對個人絕對權威的肯定以及文化遺產的遺失”(徐湘荷,2010)。他認為,教育不僅僅是政治性的,而且都具有生態和文化意義。無論是批判教育學還是進步主義教育,都帶有強烈的文化“潛臺詞”,均基于“人類是世界的中心;變化即進步,傳統即阻礙;批判性反思是獲得知識的唯一方法;被解放的個人是社會的最高目標”等一系列所謂的西方“現代性”假設,不僅忽視了生態危機的潛在文化根源,還同謀強化了這種思維模式。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地支持“解放”和“進步”,實際上是在損害世界上許多其他人民和我們子孫后代的正當利益(Edmundson,2004)。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西方對教育的人文主義以及笛卡爾式的理解并非是唯一的教育邏輯,還有其他生態友好的教育模式、思想和實踐存在著,或者說,已經存在幾千年了。特別是,那些來自一直被視為不具有現代精神的如日本、印度、非洲和中國等非西方的教育智慧傳統,甚至也包括被西方現代人文主義所拋棄的古代和中世紀的沉思傳統。這些非西方的、非現代的教育傳統不僅有助于理解后疫情時代生態正義的教育新范式的基本內涵,也有利于補充論證文明之間可以互學互鑒,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生態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
二、沉思重新進入教育
我們知道,在傳統文化中,沉思性修行的歷史源遠流長,如佛教的冥想、印度教的瑜伽、基督教的冥想禱告、柏拉圖對話中的自省、伊斯蘭教中形而上的反思以及猶太教中的深思(Hart,2004)。 但是,隨著西方人文主義以及自然科學逐漸占領主導地位,這種沉思性實踐被推向邊緣(Zajonc,2013),并被教育學家如杜威宣布為一種旁觀者的認知而被忽視或邊緣化。于是,對象化和簡化、物質主義、二元論、機械論和決定論的假設,成為現代主義認知方式的主要工具。對“他者/它者”的理解是通過分離繼而控制的認知方式。無論是原子、鄰國抑或是不同的意識形態,我們的工作是讓它們服從我們的意愿。盡管這種認知方式有巨大的價值,但也導致我們的世界支離破碎、失去平衡,甚至遭遇巨大災難。但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過去15年里,一場無聲的關于沉思性實踐的教育革命在美國高校興起,并逐步擴展至世界各地。沉思性實踐向教育從業者提供了一系列方法支持學生的注意力、情感平衡、移情連接、同情和利他行為的發展。從詩歌到生物學、從醫學到法律,幾乎高等教育的每個專業領域都在進行冥想練習。人們對長期冥想減壓練習的欣賞正在迅速增長。有研究表明,沉思性練習,即使是短時間的練習,也能提高注意力、認知和認知靈活性(Shapiro et al.,2011)。
阿姆斯學院(Amherst College)物理學家亞瑟·扎榮茨(Zajonc,2013)教授總結了正在廣泛使用的四種沉思性實踐方法,即正念、專注、開放意識以及持續沖突。第一,正念由即時即刻以及非判斷覺知(nonjudgmental awareness)構成,實踐者將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旨在培養集中注意和專注的能力。第二,專注與正念類似,但要求實踐者將注意力集中在某個簡單的物體上,專注比正念更具意圖性,更集中。在兩者的練習中,一旦發現思緒有分心,只需將思緒釋放并將注意力回到呼吸或被關心的物體上即可。第三,開放意識指“個體對感知范圍內的一切身心現象都保持開放的覺知,注意力不固定在某一特定的目標上,而是對當下發生的一切經驗都給予關照”。第四,持續沖突強調對立立場引發的沖突,但它的目的不在于解決沖突,而是維持甚至強化沖突,使兩種相反的立場能同時變得真實,并在真實的沖突中獲得“對立中的一致”(coincidence of opposites)(宋燕等,2019)。
按照傳統的沉思理論,自我和理性不是人的可能性的最高頂峰,人的認知可以超越基本邏輯和推理,而進行復雜的辯證思維,但是傳統教育并未充分發掘這一深層本質。就像愛默生指出的,“我們不相信教育的力量,我們不認為會從人自身喚出神性,也沒有嘗試去這樣做”(Hart,2007)。 但沉思性教育正試圖喚起那些深層部分。“諸如理解和智慧等能力不只出現在個體發展的更高階段,或只出現在個體的較高年齡階段;實際上,它們在兒童時代就已存在,或可能存在。因此,對這些深度的探究可為每一年齡和發展階段的個體提供轉化性的擴展和擴張”(Hart,2007)。
在沉思中,認識自己包含認識“‘小我’,即自我(ego)、人格,和‘大我’,其涵義更廣,可外延至宇宙萬物,是一切的‘一’”(Hart,2007)。 個人自我的概念是人類自我的意識,也是現代理性的基礎,是古典人文主義用以對抗神中心的核心。大我則是“能量和智慧”的源泉,對于虔誠的宗教信徒而言,大我也許是印度人的“世界靈魂”(atman),基督教徒的“基督意識”;對于神秘主義者和圣哲而言,大我也許是“心靈的存在”(psychic being),“超越之靈”(over soul)、“內在人”(inner man)等(Hart,2007)。這些名稱不同,但這種內在的智慧都是個人的向導,是“深邃的洞察力、指示方向或提出警告”(Hart,2007)。
沉思有助于培養我們理解和移情能力。學習過程中深度的理解,要求我們培養心靈的共情、欣賞、開放、容納、服務、傾聽和愛,打破培根和笛卡爾分離式認識世界的范疇和分類法,學會通過深度精神的意向和投入的服務來產生共情與移情。理解與移情不僅限于人與人之間,也流淌于人與萬物之間。即使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也可以利用移情來縮小與研究對象之間的差距。諾貝爾遺傳學獎得主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曾說:“你必須對有機體有一種感覺;你必須有開放的心態,讓它進入你的生活”(Hart,2014)。不僅在科學領域,可以說在所有領域,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可以為我們提供多種視角。這要求我們能夠重新考慮自己的假設以及對方的優勢。
當我們拉近自我與客體之間的距離,我們將越來越不愿意對他者施暴,不管這個他者是樹還是鄰居。事實上,移情被認為是我們最人性化的特性,也是道德的基礎。移情也是認識世界的方式。它開啟了合作、社區和交流的可能,并由此產生了更為親密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感,這對全球社會至關重要(Hart,2014)。
過去半個世紀的沉思性教育研究表明,沉思性實踐的應用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提高認知和學習成績。沉思性練習可以培養保持定向注意力和提高準確快速處理信息的能力。有證據表明,長期練習冥想可能對學業成績產生積極影響。二是沉思性練習可以幫助減輕學業壓力、焦慮以及抑郁狀態,正念冥想有助于調節情緒反應以及培養積極的心理狀態。三是培養“完整的人”(whole person),即一種平衡的教育范式,培養的是超越語言和概念的能力,著重培養心靈、性格、創造力、自我認知和專注力。研究表明,冥想訓練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有效的方式來培育創造力、發展人際關系的能力,增加移情反應,以及培養自我同情(Shapiro et al.,2011)。
三、把人文主義推向世界萬物
薩卡爾(Prabhat Ranjan Sarkar)是印度的一位精神領袖和哲學家。他基于印度傳統的冥想、瑜伽以及宗教思想,重新定義了人文主義,其著作《理智的解放:新人類主義》和創立的組織體現和推動了他的新人類主義(Neo humanism)。
什么是新人類主義?薩卡爾(Sarkar,1982)這樣說道:“新人類主義……以新的視角闡釋人文主義,拓寬人類進步的道路,使之更容易行走。新人類主義將為人類的生存理念提供新的靈感和解釋。它幫助人們理解,人類作為世界上最有思想和智慧的存在者,將不得不承擔起關照整個世界的重大責任,將不得不接受其被賦予的為了整個世界的重要使命”。
在薩卡爾(Sarkar,1982)看來,人文主義以人類為中心,而“新人類主義將人文主義提升為普遍主義,是對宇宙萬物的愛的信仰”。因此,普遍主義(universalism)是新人類主義的核心概念和特征,“普遍主義”也多次出現在其著作中。普遍主義被描述為對所有被造物的愛的實踐,它不是狹隘意義上的“主義”,而是指向宇宙萬物的人文主義,是一種具有道德和情感基礎的普遍的情感和愛(Nimbekar,2016)。薩卡爾認為,通過擴展人文主義的原則可以建立以普遍主義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普遍主義也被描述為一種無私、忘我的感覺,即不把宇宙的其他存在看作是與真實自我相分離的,是一種神圣的愛的宇宙觀。普遍主義強調對宇宙萬物的精神性的愛,是一種對理性的超越。
新人類主義倡導萬物平等的原則。在薩卡爾看來,以人為中心的人文主義帶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和偏見,新人類主義則致力于減少這種沖突的可能性。新人類主義重視存在價值而非功利價值,反對地緣情緒(geo-sentiment)和社會情緒(socio-sentiment),認為任何經濟政治剝削都伴隨精神剝削(spiritual exploitation)。精神剝削是政治經濟剝削和心理經濟剝削(psycho-economic exploitation)的基礎。也就是說,社會情緒和地緣情緒阻礙了理智思考,造成對別的群體或內部群體的傷害,無法對是否有利于人類共同的福祉作出正確判斷,破壞了和諧友愛的精神社會契約。殖民和剝削源于缺乏理性和良知。人類既有智慧又有本能,如果感性地使用理智,容易滋生教條;如果理性地運用理智,就可以達到奉獻(devotion)。在薩卡爾看來,奉獻是人的最高使命,是最高的人性體現。
平等原則意味著所有被造物都有生存和成長的權利。薩卡爾(Sarkar,2011)指出:“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得到最低的物質需求保障;每個人都有充分開發其精神潛能的機會;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去獲得絕對真理。”薩卡爾認為,原初精神意識(proto-spiritual mentality)是社會平等原則的基礎。這種原初精神意識是不斷地從內部或外部感知事物的過程,是最高意識的表現,能幫助人們架起溝通內外部世界的橋梁。當人們深刻認識到社會平等原則的意義時,自然會形成理解的原始精神意識,將奉獻作為實踐原則,進而消除有害的社會情緒。
為了構建新人類主義社會,薩卡爾(Sarkar,2011)提出了社會經濟漸進功用理論(Progressive Utilization Theory,PROUT),并在1968年成立了PBI(Proutist Bloc of India)組織,希望通過政治和社會行動推進新人類主義。他強調建立在可持續基礎上的合作,主張通過協調與合并形成自給自足的社會經濟單位,以防止社會經濟剝削,達到高度的社會經濟平等。基于該理論的社會經濟運動旨在關照所有存在的個體和集體的共同福祉,認為只有把心靈從時間、空間和人的一切束縛中解放出來,才能達到全面的人的解放。
薩卡爾沒有追溯古希臘的人文主義傳統及相關哲人的思想,而是詳細地表述了自己的想法并進行例證。在薩卡爾(Sarkar,1982)看來,西方現代人文主義不僅不能解決世界問題,還會制造問題。新人類主義當然也強調自由理智和理性,因為理性有助于產生奉獻。他進一步提出了精神性實踐,將愛擴展到所有存在物。對薩卡爾來說,生命的所有方面包括身體、精神和心靈都同等重要,但世界上仍有很多人無法滿足基本的物質需求。薩卡爾倡導建立世界政府,通過實踐社會經濟漸進功用理論改善和解決這些問題,讓全世界的人都有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空間來提升心靈。新人類主義構想了一個以尊重所有人與其他生物的共同價值觀為基礎的全球社會,解決生態環境破壞和貧富差距的問題,建立一個正義和可持續的全球社會(Avadhuta,2009)。
為了理智和心靈的解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薩卡爾通過教育來實現他所倡導的新人類主義。薩卡爾(Sarkar,2010)認為,教育的真正意義在于人的三重發展——身體、精神和心靈的同時發展。這種發展應當增強人的個性的整合。薩卡爾1978年創立了PROUT Universal組織,旨在通過社會和文化活動喚醒人們的心靈,應對人類面對的挑戰和困境。其中,古魯古附屬學校(Ananda Marga Gurukul affiliated school)遍布世界各地,專門致力于兒童身體、智力和精神的全面發展。學校的課程和教法因各地需求不同而異,不過課程內容有共同的價值追求。薩卡爾(Sarkar,2010)指出,PROUT教育體系不僅強調哲學和傳統,更強調道德教育和理想主義。道德實踐應是各級教學大綱中最重要的內容。普遍主義的意識也應當在兒童中被喚醒。
在薩卡爾看來,教育應當建立在普遍主義的基礎上,真正的教育將人引向對所有存在物的愛和同情。根據新人類主義的教育理念,薩卡爾主張融合東方哲學和西方科學,重新思考人類共同的經驗,促進合作的實現,這就要求教育具有文化敏感性。新人類主義教育強調課程和教學以普遍主義為核心,其中包含可持續生態發展等社會價值,并通過學術和實踐,用靈活創新的教學方法,結合瑜伽和冥想,建構新人類主義課程。
薩卡爾的新人類主義連接人的心靈和世界,他的普遍主義尤其得到國際的關注和討論,也為國際教育實踐帶來新的視角和創造性。20世紀偉大的靈性導師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1974)也說:“要幫助學生生存,就有必要讓他們對生命滿懷強烈的情感;不僅對他們自己的生命或者他人的生命,而且對生命本身,對村莊,對樹,都要有情感。”這種萬物一體的終極關懷充滿愛和理解,幫助人尋求更高的發展維度,并推動世界走向和平。
四、審美有助于加深人與萬物的關系
人的生命通過體驗和經歷才能展開和成長,而審美可以提供深度和強化性的經驗。優異的教師可以讓學生看到事物或觀點的靈魂,通過每個學科特有的認識論和美學來引起靈魂的共鳴。
人生的目標不止在于善與真,還在于美。馬克思說,人按照美的規律來建構自己的世界。在宗教美學中,美將拯救世界。普羅提諾(Plotinus)認為,我們的身體從神圣中分離開,但我們的靈魂帶著神圣的印記,在美中我們瞥見了神性,我們真正的家園,我們感到另一個世界的完美,靈魂努力與之重聚。用現代的方式來說,我們天生就是被震撼靈魂的美所吸引的,這種吸引力在內心深處以及靈魂的更高處讓我們互相連接。審美能使認知者和知識更接近,這是綜合思維的基本方向之一(Hart,2014)。審美能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深度關聯,這尤其體現在日本“物哀”的審美傳統之中。
物哀(もののあわれ)一詞最早出現于日本平安時代初期的隨筆作家紀貫之的《土佐日記》中:“船夫卻不懂得這物哀之情,自己猛勁喝干酒,執意快開船”①。此后,物哀便在眾多的物語、和歌及隨筆之中顯現,尤其是紫式部所作的《源氏物語》中。“物(もの)”指客觀世界存在的萬事萬物,而“哀(あわれ)”是日語中表示感動和感嘆的修辭,類似于中文感嘆詞“啊”“嗚呼”等。本居宣長(2010)認為,“世上萬事萬物的千姿百態,我們看在眼里,聽在耳里,身體力行地體驗,把這萬事萬物都放到心中來品味,內心里把這些事物的情致一一辨清,這就是懂得事物的情致,就是懂得物之哀。”物哀是人通過感知世界萬物來感受、體會自我的情感。換言之,物哀的重點就是人自身對世界萬物的感知帶來的情感感受,這種情感感受被認作是“物哀之美”。平安朝的物哀成為日本美的源流,是人自發產生的主體感受,與人的自然感受相關聯。
近現代以來的日本學者在西方思想理論的影響下,對物哀進行了更為多元化的美學闡釋。大西克禮在存在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拓展了知性要素的視野,即觀照人與世界的“存在”,為物哀賦予普世意義的“世界苦”的審美體驗。杉田昌彥、田中康二等人受休謨、康德等人的啟發,以“同情”“共感”等話語闡釋物哀的美學意義,這種解讀聚焦對他者境遇的認同、理解及共鳴,是關注相互交流的同情美學。總之,物哀之美由物而生、自心而發,無需理智和理性參與的心物同情的主客合一,是通過人對某種事物的感覺、感知、瞬間靈動或者感受到的一種“意會”。它超越了具象事物而將其擬人化、主觀化。正如中村元(1987)所說的,日本人是現實主義的,他們企圖在現象界當中去把握絕對者,他們承認被給予的現實,承認人的自然性情。
在日本,對自然的欣賞是物哀的表現。日本最重要的傳統審美教育手段之一是自然。日本人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者,因為宗教的作用被對自然的美麗崇拜所取代。自然是美感的衡量標準。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愿望是日本藝術的主要特征。日本的審美教育通過對包括自身在內的世界萬事萬物的欣賞、感悟來培育人性,即把人從被工具理性,以及社會所異化的人性轉變為擁有完美的人性。
近代日本的審美教育也受到了西歐特別是德國審美教育理論的影響,其中以席勒的審美教育為主要代表。席勒(2009)認為:“因為美是人的表現中感性與理性之間的一致性表達,基于美和藝術的情感教育實際上意味著人類的自身發展。也可以說,人的教育從根本上就是基于美和藝術的審美教育”(下中直也,1971)。在席勒(2009)看來,只有當人是完整意義上的人時,他才游戲;而只有當人在游戲時,他才是完整的人。席勒(2009)堅信,只有游戲性的審美活動,才能改變人的異化狀態,治愈人性(感性與形式沖動)的分裂,達致人性完滿的狀態。概言之,就是通過游戲沖動來達到形式沖動和質料沖動的協調統一,使人成為完全的人。席勒將美與藝術同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緊密結合,體現出啟蒙時代對人性的高度追求。
不過,日本獨特的物哀傳統對萬物的欣賞以及由此體現出的對萬物、大自然的敬畏與敬仰,不僅在日本國內,在國際上也受到廣泛的關注和重視。例如,日本學者金吾増田論述了日本藝術教育政策的簡史,以及從現代到現在日本藝術教育的正式體系是如何組織起來的。金田拓考察了日本藝術教育主要改革運動的歷史演變基礎(Okazaki & Nakamura,2003)。巖野正子描述了日本社區的跨文化美育案例,以及通過藝術文化互動如何影響社區(Okazaki & Nakamura,2003)。艾斯納(Eisner,2017)通過在日本的三周經歷的敘述性報道,展示了日本真實的社會背景下的藝術與教育,并通過比較,介紹了自己作為美國藝術教育家的理論與實踐。此后,湯姆·安德森(Anderson,2009)通過為期三周考察日本真實社會背景下的藝術和教育,描述了日本藝術和學校藝術教育。阿德爾(Adal,2016)論述了日本由最初模仿西方的繪畫教育到現在作為藝術教育一部分的本土化繪畫教育的轉變。
西方世界對日本社會獨特的自然美學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他們發現,日本古代美學的物哀、幽玄(Wabi-Sabi)、留白(Ma)等獨特的美學范疇引導著日本國民對自然的感知和欣賞,并對其當代藝術、文化和藝術教育產生持續影響。日本社會也力圖把工業技術與古代的自然美學傳統聯系起來。比如京都地區的城市設計就體現了技術與自然的融合和連續。城市已經發展到京都山區,但是其中無數錯落的寺廟和花園體現了城市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如果沒有自然元素,這些寺廟就會顯得格外冷寂和分離。相反,正是因為自然美學提升了人們對這些人造設施的情感,才有了這種自然與工業社會的融合,才能降低工業與自然的對立和疏離。盡管日本社會對自然的生存依賴在不斷降低,但技術永不能消除自然,人們仍需保持對自然的眷戀和欣賞。總之,源于物哀的審美之根很好地調節著自然和人類創造之間的平衡(Prusinksi,2012)。 從這種意義上說,強調生態正義的新人文教育就是一種審美教育,它強調和提醒著天地神人之間和諧共存和人在大地上的詩意棲居(Hung et al.,2020)。
五、以修身來抵達“萬物一體”
作為不同于西方人文主義的傳統教育范式,儒家的修身傳統近年在國際話語體系中不斷崛起。筆者通過跨數據庫搜索教育學、哲學、社會學等領域,共檢索9136篇篇名與摘要包含“修身”(self-cultivation)及China或Asia的英文期刊論文。得到該主題相關論文發表量總體上逐年上升,近年來保持高位。對修身傳統的關注不但體現在論文數量上,而且越來越多的域外學者開始從不同的方面對這一古老的寶藏進行多視角的全新闡釋。
邁克爾·A·彼得斯(Peters,2020)認為,以修身為基礎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文化精神傳統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東方的儒家、道家和佛教傳統以及西方的古希臘哲學。在他看來,“修身養性”的文化溯源體現了中國人的人文精神,而理解中西方人文主義差異可以成為全球理解的橋梁,這在當下世界秩序中顯得日益緊迫而重要。修身傳統作為西方了解和學習東方古老智慧的窗口,在西方話語體系中正不斷凸顯出自己的獨特價值與重要性。
我國臺灣學者洪如玉(Hung,2017)在《教育哲學與理論》雜志上主持了“東亞教育哲學中的自我修身”專題特刊,探討許多具有當代重要性的問題,包括環境教育、公平與正義、批判理性主義、權力與治理等,提供了東亞教育哲學和西方見解所闡釋的自我修身的新觀點。不同學者從儒家、理學、道家等中國古典哲學的“修身養性”入手,深刻闡釋中國古代智慧對當今教育的重要意義,并揭示東西方教育思想之間的密切聯系。
新加坡陳惠萍教授(2020)發表多篇文章,論述儒家、道家中自我修身的概念以及如何將其運用于當今的教育體系,強調朱熹思想的當代意義,指出應該將標準化考試置于更大的旨在自我完善和個體轉化的教育議程中。韓國學者(Han,2016)將理學看作是失去的藝術,儒家思想是一種對心靈的培養,可以幫助治愈文化中過度的自我中心化。
菲律賓學者(Sta.Maria,2017)從《道德經》和《莊子》入手,提請人們注意道家非二分法思維的重要性以及在教學中的可能運用。道家倡導無為、無名和無欲來避免任何形式的強制和壓制,謹慎使用領導力,平衡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因此,道家反對新自由主義條件下學校教育的區分、測量、競爭和個人主義,因為這會導致社會不正義,并使之永恒化(Tan,2021)。
可以看出,儒家和道家都把修身放在核心位置,不同的是,前者強調積極的修己以安人;后者強調消極的無為、無名和無欲,但兩者都強調個人的行為可以影響群體、社會和天下。儒家的《大學》更是把修身作為天下治理的根本,界定了個體修身的方向,即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這樣一來,儒家的“小我”與天下的“大我”聯系起來了。
王陽明指出,“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谷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但如果“拆人房舍、掘人家墓,猶恬然不知痛癢,此是失其本心”(陳來,2020)。 盡管每一個都具有這種與物同體的本性或本心,但不是每個人都能認識并落實這一點,因而大學之道首先需要明其明德,即修身。
王陽明把體悟、認識和落實這種萬物一體的過程,稱為致良知,也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②。顯然,根據之前的探討,這里的“事事物物”不僅指倫理活動和社會政治生活,而且指一切涉及生態正義的活動,即宇宙萬物。在儒家看來,無一物非我,莫非己也。因此,祛除麻木不仁,把宇宙病視為自己病,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具體而言,個體在家庭生態上養育孝心和孝行,在社會生態養育惻隱、同情之心,在政治生態上培育親民之心,在自然生態中培育生生之仁心,愛及萬物的情懷。這樣,通過修身,人抵達了萬物,并與萬物同體(彭正梅,2010a)。他人不再是地獄,自然也不再是壓榨和索取的對象,而是形成與我息息相關的共存、共生和共愛關系。在儒家修身傳統看來,自然并不會自動地實現“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們需要通過“贊天地之化育”與世界一起成長,裝扮和美化這個世界。
六、結論:邁向“生態正義”的新人文教育
我們還可以舉出更多受到重視,并倡導集體取向和生態正義的非西方文化教育傳統,譬如強調“你在故我在”的非洲烏邦圖哲學(UBUNTU)。這些非西方現代人文主義的智慧傳統,強調人類的同情、相愛和相通,強調集體和共同體的價值,也強調生態性的關聯、關照和關愛,從而也更有利于我們深刻地理解和落實教科文組織《2050年教育宣言》對自然、對人類的終極關懷。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基于“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邏輯,“文明” “人文”變了,化成天下就需要新人文教育。本次全球新冠疫情以及近年來不斷出現的世界自然異象再次提醒和警示我們,人類正處于生存危機之中。我們要珍惜和熱愛我們的地球,要協同一致建立包括生態命運共同體在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也要拋棄處于主導地位甚至霸權地位的制造分離和隔離的西方現代人文主義,轉向一種新的更具生態友好型的人類發展哲學。因此,有必要激活和發展不同文化傳統的教育智慧資源,從而促進形成新的以生態正義為核心的新人文教育和教育學。
當然,這并不是說,新人文教育要剔除個人主義和個體自由及其與之相連的現代西方人文主義,因為它們的存在是事實,而且,這種人文主義也構成了現代工業、現代技術發展和現代化的基礎。今天,高度發達的科技進步也得益于西方人文主義所鼓勵的科學思維方式和民主文化風氣。新人文主義不是要把人類引向前現代所謂的詩意社會和神秘社會,人類也無法回到前技術時代詩意的浪漫生活了。這一點對追求現代化并被迫卷入激烈的國際競爭的中國來說,尤為重要。相應地,以生態正義為基礎的新人文教育也不是要排斥西方人文主義,而是要扭轉其主導的霸權位置,規制其合法界限,使之從屬于生態正義的邏輯,與其他的生態文化資源形成良好互動。基于此,我們認為,后疫情時代教育范式的轉變應體現在以下方面,這也是新人文教育不同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言所預言的基本內涵。
(一)從西方知識到全球知識
生態正義的教育學不僅需要近代以來的西方科學知識,還需要以生態友好方式激發和容納其他民族文化的智慧傳統,從而形成包容性的生態友好的全球知識。因此,這里不是像過去多元文化主義那樣,僅僅承認和欣賞其他文化,而是要借助非西方文化的生態知識幫助解決全球生態危機。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的:“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文學”③。因而,沒有這樣一種共同的“世界文學”,就難以形成共同的全球性的知識和認識方法,也無法全面認識我們所面臨的生態危機,遑論去解決它。
(二)從生存導向到為每個人的更高發展
21世紀以來,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繁榮與創新,社會生產力水平持續增高,人類社會生活條件不斷改善,人們已不滿足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需求,而致力于追求更高層次的發展需要,實現更加幸福和完滿的生活。費爾巴哈有言:“動物只為生命所必需的光線所激動,人卻關注那遙遠的星辰所發射出來的無任何功利性質的光線”(洪曉楠,2013)。可以說,馬克思所想象的“人的全面發展”的時代正在形成。馬斯洛(1987b)也指出:“當我們在種系階梯中上升時,我們可能會逐漸發現新的(更高的)欲望,發現另一種本能,它在本質上是本能的”,“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假設,人有一種內在的或先天的趨向自我實現的成長傾向”。新人文教育就是使得每個人“更真正地成了他自己、更完善地實現他的潛能,更接近他的存在核心,成了更完善的人”(馬斯洛,1987a)。教育的功能、教育的目的根本上就是人的“自我實現”,是豐滿人性的形成,是人能夠達到的或個人能夠達到的最高度的發展(馬斯洛,1987c)。當然,這種高度勢必也應包括生態正義的維度。
(三)從基本技能到高階能力
生態正義的新人文教育需要把高階能力的培養置于教育的核心位置,從重視基礎性讀寫算的“3R”技能轉向重視面向所有人以“4C”技能(Critical thinking、Communication、Collaboration、Creativity)為核心的高階性、多維性和復雜性的能力(彭正梅等,2019)。這是因為一方面人類常規的工作以及常規的能力將會被日益發展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所替代;另一方面,生態危機的應對和解決以及人類在高科技時代的創造性生活都要求發展人的高階能力。發展人的高階能力在《2050年教育宣言》中沒有被特別強調,但毫無疑問,這顯然也應是未來教育的重點。
(四)從個體到全球共同體
新人文教育的核心是破除西方的個體中心主義,強調群體和人類共同體的價值和關懷。人類今天所面臨的諸種生存危機,非憑借一國、一民族、一群體之力能得以解決。它們需要世界各國攜手并肩,著眼全球共同利益,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合力培養具有國際意識的世界公民。誠如習近平總書記(2017)所倡導的,宇宙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共有一個家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各國攜手合作,共同行動。具體內容包括:“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因此,在全球共同體的建設中,生態文明教育應處于優先位置。
(五)從主體到萬物一體
自然不僅是人類主體活動的對象,同時也在人類活動中發生著變化。海德格爾把人稱為在世(Das In-der-Welt-Sein)的存在者。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不是以一種主體或客體的方式,而是以一種在世的形式、在在世的展開狀態中領會存在本身;要走出主客分離的天—人、人—自然、人—我和人—人的關系,實現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和共生,即確立一種“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萬物一體的關系。我們必須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樣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在自己的生命中體驗其他生命(施韋澤,200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7)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中有個形象的隱喻:“我們應將全人類視為一棵樹,而我們自己就是一片樹葉。離開這棵樹,離開他人,我們無法生存”。可見,近代以來的西方人文主義把自然視為開發和壓榨的對象,把他人作為自由的阻礙,把他人視為地獄。這種對待他者/它者的態度需要替之以“民胞物與”的仁者情懷。
誠然,新人文教育的內涵還在形成和發展之中,取決于各個文化智慧傳統中生態教育資源的良好互動。以上五點歸納也并不完全,需要其他學者參與討論、補充或更正,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50年教育宣言》明確呼吁這種轉變。教科文組織的行動邏輯:一是人類的命運與地球的可持續性是一回事;二是要實現可持續性發展的未來,人類不能與世界其他地區分離;三是教育需要發揮關鍵作用,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在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一個完整的范式轉變的要求:從社會正義轉向生態正義;學會與我們周圍的世界融為一體,共同成長。我們未來的生存取決于我們能否做出這樣的轉變(UNESCO,2020)。
顯然,我們所面臨的生態正義的問題不僅是教育問題,還有我們如何重新理解和重塑或重新想象我們與地球的關系,特別是改變西方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國家治理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但是,我們為什么不從教育開始呢?
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了國際教育未來委員會,啟動了“教育的未來:學會成長”(The Futures of Education: Learning to Become)項目,旨在重新思考教育未來并構想知識和學習如何重塑人類與地球的關系(連愛倫等,2021)。應該說,這樣一種基于生態正義的教育,不僅給予我們個體,還有人類作為整體的未來生存能力。
需指出的是,這種“生態正義”的教育新范式,不僅與我國正在倡議和實行的綠色發展、碳達峰、碳中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發展目標相契合,也與儒家及馬克思主義的包容性的正義理念深度呼應,更是與新時代我國持續推進“五位一體”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優先的戰略總布局相統一。
因此,后疫情時代,我國教育學者需表現出更大的知識綜合能力和終極人文關懷,把“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莊子語)的知識傳統綜合起來,勇于進行文化競爭和創造,建立我們具有原創性的話語體系和教育自信。因應后疫情時代以生態正義為根本的新人文教育范式的轉型,無論從國家戰略、文化傳統、世界趨勢以及人類關懷來看,對我們來說都是一次難得的機遇、挑戰和使命。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M].北京:人民出版社:35.
②《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1992).《王陽明全集》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45.
③日本古典文學大系:第20卷(1977)[M].東京:巖波書店: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