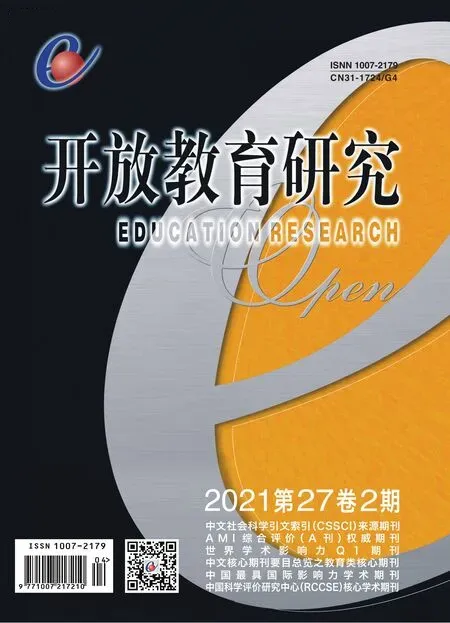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歷史、邏輯與未來
——兼論人工智能的教育意蘊
周子荷
(華中師范大學 國家數(shù)字化學習工程技術(shù)研究中心,湖北武漢 430079)
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是轉(zhuǎn)型發(fā)展的重要杠桿。長期以來,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技術(shù)變革教育的效果不彰。在人工智能時代,推進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是推進技術(shù)與教育雙向深度有效融合,切實發(fā)揮信息技術(shù)變革教育之革命性力量,切實促進人工智能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戰(zhàn)略選擇和必由之路。
一、推進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信息技術(shù)變革教育的現(xiàn)實困惑及破解之道
“信息技術(shù)對教育發(fā)展具有革命性影響”已成共識,但歷史經(jīng)驗和現(xiàn)實觀感卻令人困惑。自20世紀初視聽教學運動把以電影和廣播為代表的第一代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于教育以來,教育技術(shù)就始終不忘變革教育的初心與使命。一百年前,發(fā)明家愛迪生(Thomas Edison)曾樂觀地預計:“不久將在學校中廢棄書本……有可能利用電影來教授人類知識的每一個分支。在未來的十年里,我們的學校將會得到徹底改造”(Saettler,2004)。時至今日,電影放映機早已退出了技術(shù)變革教育的歷史舞臺,但教育并沒有徹底改觀。面對一次又一次技術(shù)浪潮的沖擊,班級授課制這一基本制度框架下以分班授課和分科教學為核心特征的現(xiàn)代學校教育體系并沒有發(fā)生根本變化,教育的生產(chǎn)方式仍然停留在工場手工業(yè)的水平(楊宗凱等,2019)。正因如此,才有形形色色的“喬布斯之問”(桑新民等,2013),而其背后潛藏的卻是技術(shù)變革教育效果不彰的事實。
更令人擔憂的是,自現(xiàn)代媒體技術(shù)應(yīng)用于教育以來,便始終存在著一個被稱為“非顯著性差異現(xiàn)象”的魔咒:不同媒體和技術(shù)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在效用上沒有顯著差異!自20世紀20年代起,就不斷有研究報告了這一結(jié)論。20世紀末,羅素(Russell,1999)對這些研究進行了匯總,竟有355項之多!進入21世紀,仍不乏有這樣的研究結(jié)果(McDaniel et al. , 2016)。同時不斷有學者指出:“還沒有一項研究能夠證明,學生成績的提高是應(yīng)用計算機的結(jié)果”(索耶,2010);“和傳統(tǒng)的技術(shù)手段相比,很多信息技術(shù)在提升教育與學習的績效方面并不具有壓倒性優(yōu)勢”(楊浩等,2015)。非顯著性差異現(xiàn)象表明:在改進學習的效用上,新技術(shù)并不必然比原有技術(shù)更優(yōu)越。如此一來,就很容易得到一個令人沮喪的推論:如果在改進學習的效用上,不同媒體和技術(shù)差異不顯著,那就意味著它不能給學習帶來實質(zhì)改變;如果在微觀上不會給學習帶來實質(zhì)改變,它又如何能夠在宏觀上推進教育革命呢?
已有學術(shù)史研究表明,“非顯著差異現(xiàn)象”與媒體比較研究如影隨形(Lievrouw,2001),是媒體比較研究必然會得到的兩種結(jié)果之一。媒體比較是20世紀上半葉視聽教學運動的主流研究范式,即通過實驗對比不同媒體改進學習的效用,試圖找尋超越其它媒體的“萬能媒體”或“超級媒體”(Wilkinson,1980)。鑒于教育研究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條件下實現(xiàn)對無關(guān)變量的完全排除和控制,因此必然會出現(xiàn)有研究報告有顯著性差異,也有研究報告無顯著性差異(Surry et al. , 2001)。更嚴重的是,媒體比較研究得到的只是 “優(yōu)”或“劣”的簡單結(jié)論,不能對此提供進一步的科學解釋,因此無法產(chǎn)生新知識。這對一個專門研究領(lǐng)域無疑是致命的。20世紀70年代后,媒體比較研究逐漸式微,能傾處理交互(aptitude-treatment interaction)日漸成為教學媒體與技術(shù)研究的主流框架(Salomon,1972;Thompson et al. , 1992)。但隨即產(chǎn)生了新的問題,即在闡釋作為教學處理干預措施的媒體技術(shù)與作為學習者能力傾向的認知過程交互作用的過程中,開始追問究竟是什么對學習產(chǎn)生了影響。這就是教育技術(shù)學術(shù)史上具有廣泛影響的“學習與媒體大辯論”。論辯的一方認為是某種媒體具有的特定的技術(shù)屬性對學習產(chǎn)生了影響(Kozma,1991),另外一方則認為是媒體在使用過程中嵌入的教學策略對學習產(chǎn)生了影響(Clark,1983)。雙方各執(zhí)一詞,莫衷一是。自20世紀80年代初,這場持續(xù)近二十年的學術(shù)大論辯最終也沒有得出明確結(jié)論,旋即被互聯(lián)網(wǎng)大潮的興起沖擊得七零八落。
今天回頭重新審視這場論戰(zhàn),或許可以獲得新的教益,超越雙方立場,從更高層面探尋技術(shù)變革教育的深層邏輯。教育技術(shù)研究是實踐導向的,這使對技術(shù)的關(guān)注長期停留在應(yīng)用層面,教育領(lǐng)域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都屬于應(yīng)用創(chuàng)新而非原始創(chuàng)新。迄今為止,教育領(lǐng)域的技術(shù)大都從外部引入。這些技術(shù)屬于通用技術(shù),最初既不是在教育領(lǐng)域中被發(fā)明,也不是為教育服務(wù),因此它的教育應(yīng)用往往還需要額外尋求教育理論的支撐。通用的技術(shù)和教育的理論來自兩個不同場域,遵循不同的邏輯。這往往使技術(shù)與理論之間難以匹配,無法耦合,從而導致實踐中長期存在無法克服的教育和技術(shù)“兩張皮”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信息技術(shù)的進步及其應(yīng)用的不斷深入,教育領(lǐng)域涌現(xiàn)了大量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成果,如MOOCs。但這些技術(shù)創(chuàng)新很少建立在學習科學的基石上(Sawyer,2014)。可以試想,如果某種技術(shù)本來就是在教育領(lǐng)域被發(fā)明出來的,就是為教育服務(wù)的,那么它的應(yīng)用過程是否還需要額外尋求教育理論作為支撐呢?答案顯然是不需要!這樣一來,教育和技術(shù)“兩張皮”的問題自然也就不復存在。從這一意義上講,不管是破除非顯著性差異現(xiàn)象的歷史魔咒,還是追問究竟是技術(shù)屬性還是教學策略對學習產(chǎn)生了影響,甚至解決信息技術(shù)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難以推進的難題,都可以歸結(jié)到如何推進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上來。實事求是地講,長期以來對這個問題的重視是不夠的。面對層出不窮地被引入教育的新技術(shù),很少有人意識到教育本身也需要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和從外部引入的通用技術(shù)相比,通過原始創(chuàng)新從教育內(nèi)部生長出來的技術(shù)又能給教育帶來什么呢?如何更好地推進教育領(lǐng)域的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呢?這或許可以從歷史中獲得些許啟發(fā)。
二、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兩重境界:從歷史中汲取經(jīng)驗與智慧
從歷史中汲取經(jīng)驗與智慧,在時代變遷中探尋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必要條件與內(nèi)在邏輯,是未來推進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基礎(chǔ)與前提。盡管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數(shù),但并非沒有先例。回首過去一百年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歷史征程,可以發(fā)現(xiàn)有兩個原始創(chuàng)新的案例值得關(guān)注。這兩個案例充分體現(xiàn)了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兩重境界。
(一)從基礎(chǔ)科學到技術(shù)創(chuàng)新:教學機器展現(xiàn)的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第一重境界
教學機器是過去一百年間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第一個范例,展現(xiàn)了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第一重境界,即科學向技術(shù)的線性延伸——學習基礎(chǔ)研究的突破推動了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的原始創(chuàng)新。1954年,斯金納(Skinner,1954)曾經(jīng)感慨,教室的機械化水平甚至還不如家庭的廚房,因此“必須來一場教育的‘工業(yè)革命’,把教育的科學與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教育技術(shù)結(jié)合在一起,使傳統(tǒng)教育低下的效率和笨拙的程序現(xiàn)代化。”(Benjamin,1988)他基于獨創(chuàng)的操作性條件反射學習理論,設(shè)計了一臺教學機器,發(fā)展了程序教學技術(shù),迅即引起廣泛關(guān)注,有力推動了教育領(lǐng)域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在世界范圍內(nèi)掀起了程序教學熱潮,極大提升了教育實踐的技術(shù)含量,有效提升了教育的現(xiàn)代化水平。
實際上,早在20世紀20年代,教育心理學家普萊西(Sidney L. Pressey)就發(fā)明了類似的教學機器,但最終應(yīng)者寥寥,很快便歸于沉寂,未能在教育領(lǐng)域得到認可和推廣。斯金納與普萊西的教學機器遭遇了迥然不同的歷史命運。斯金納本人把這一結(jié)果歸結(jié)于“文化慣性”,即普萊西的時代還沒有為教學機器的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做好準備(Skinner,1958)。但在“文化慣性”外,似乎還有更深層的原因: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除了受時代變遷進程中“文化慣性”這一外部因素影響外,還必須有基礎(chǔ)科學研究的源頭。斯金納的教學機器源自于基礎(chǔ)科學對學習研究的重大突破,而普萊西的教學機器則缺乏有關(guān)學習之原創(chuàng)型科學理論的支撐。換句話說,不管是斯金納的教學機器,還是普萊西的教學機器,都是教育領(lǐng)域的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但二者的根基不同。斯金納的“操作性條件反射”重大理論成果能夠為教學機器這一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提供系統(tǒng)、有力的理論支撐和指引,讓程序教學技術(shù)成為“基于科學的技術(shù)”(science-based technology)。在學習的基礎(chǔ)研究沒有取得重大突破的情況下,普萊西設(shè)計的教學機器只能停留在經(jīng)驗層面,其發(fā)展主要借助于常識而不是理論,屬于“工藝訣竅”,依靠反復試錯進行修正與完善,以此取得進步。
斯金納的教學機器作為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的原始創(chuàng)新,成為推動學習的基礎(chǔ)科學研究向程序教學實踐應(yīng)用轉(zhuǎn)化的關(guān)鍵杠桿(Holland,1960),充分展現(xiàn)了基礎(chǔ)科學推動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巨大力量。斯金納的成功和普萊西的失敗,從正反兩個方面揭示了學習的基礎(chǔ)科學研究與教育的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近代以來的科技發(fā)展史表明,沒有基礎(chǔ)科學作為基石,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注定走不遠。這一普遍原則在教育領(lǐng)域同樣適用。工業(yè)革命以來,我們見證了無數(shù)基礎(chǔ)科學研究促進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成功案例。
(二)科學技術(shù)的耦合發(fā)展:LOGO語言展現(xiàn)的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第二重境界
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LOGO語言作為世界上第一款兒童編程語言,是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第二個典范,展現(xiàn)了不同于由教學機器所展現(xiàn)的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第二重境界。LOGO語言的誕生立足兩大基石:皮亞杰在建構(gòu)主義和明斯基(Margaret Minsky)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開拓性貢獻,是學習科學家和人工智能專家通力合作的結(jié)晶(Solomon et al. , 2020)。作為人工智能在教育領(lǐng)域內(nèi)的第一個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它展現(xiàn)了科學與技術(shù)如何以耦合發(fā)展的方式推動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歷史軌跡。從學習研究看,LOGO語言的發(fā)明源于皮亞杰建構(gòu)主義理論對學習的新解釋,而LOGO二十年的應(yīng)用又有力地推進了學習理論的建設(shè)與發(fā)展,其代表性成果即建構(gòu)主義(constructionism)在20世紀80年代的崛起,極大地拓寬和深化了對學習的科學理解,并為學習科學的崛起做了思想啟蒙和理論準備(Sawyer,2006)。正如帕伯特(Papert,1986)所言:“從建構(gòu)主義心理學的理論視角看,我們把學習視為知識的重構(gòu)而不是傳遞。從大量教育經(jīng)驗中,我們意識到當學習被嵌入活動中時就會變得非常有效,因為正是在活動中學習者才能夠經(jīng)驗到對一件有意義作品的建構(gòu)……建構(gòu)主義不僅包含而且還超越了構(gòu)成學習深層結(jié)構(gòu)之基礎(chǔ)的認知主義原則,對學習科學來說至關(guān)重要:它在認知的深層結(jié)構(gòu)外增加了很多其它深層維度,包括情感的、審美的、社會文化的,在我們看來,這些維度起碼和那些認知方面的因素同等重要。”由此不難看到,皮亞杰有關(guān)建構(gòu)主義的學習基礎(chǔ)研究為LOGO語言的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提供了科學支撐,而LOGO語言二十年的應(yīng)用實踐反過來又深化了對學習的科學理解。學習的基礎(chǔ)科學研究與教育的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之間的雙向交互與耦合發(fā)展,在這里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xiàn)。
從人工智能看也是如此。“編程是對人類認知的復雜性進行建模,因此也是理解人類認知這一行為的一種手段。”(Pea et al. , 1985)正如所羅門(Solomon et al. , 2020)所言:“人工智能和LOGO語言之間思想的流動不是單向的。一開始被引入LOGO語言的一些重要思想對人工智能以及更為一般意義上的計算機科學也有所回饋。”歷史地看,LOGO語言的發(fā)明離不開以明斯基為代表的一批人工智能學者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沒有明斯基等人在人工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和Lisp等人工智能編程語言方面的開拓性工作,便不可能有LOGO這一世界上第一款兒童編程語言的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而LOGO語言反過來又有力地推動了人工智能、計算機科學等相關(guān)學科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其典型代表即是對Lisp這一人工智能編程語言的發(fā)展,比如Lisp LOGO作為未來孩子編程環(huán)境的原型(Miller,1979),不僅可以在計劃制定與錯誤糾正方面與學生溝通、互動,而且還可以用于測試由Lisp代碼編成的其它人工智能微世界,以及用來測試、拓展基于LOGO之上的新編程語言。從LOGO語言的誕生和發(fā)展還可以看到,以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為牽引,真正實現(xiàn)了教育和技術(shù)兩大領(lǐng)域的雙向互動。一方面,LOGO語言的誕生有賴于人工智能研究的進步,特別是相關(guān)技術(shù)成熟的有力支撐;另一方面,LOGO的持續(xù)發(fā)展也有力推動了人工智能及更為廣義的計算機科學的進步。這樣一來,教育就不再是技術(shù)單純的消費者,教育領(lǐng)域內(nèi)的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不光讓教育受惠,同時也帶動了相關(guān)技術(shù)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
三、巴斯德象限:人工智能時代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新邏輯解讀
進入21世紀,無論是科學技術(shù)發(fā)展,還是社會生活進步,乃至教育技術(shù)的創(chuàng)新應(yīng)用,都已進入了更高境界。時至今日,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這兩大范例留給后世的也不再是這些技術(shù)成果本身,而是其背后展現(xiàn)出來的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經(jīng)驗與智慧。教學機器的發(fā)明展現(xiàn)了基礎(chǔ)科學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之間的線性關(guān)系,LOGO語言的發(fā)明則展現(xiàn)了二者之間更復雜的交互作用,為理解人工智能時代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的邏輯,重新審視科學研究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之間的雙向交互給教育領(lǐng)域基礎(chǔ)科學突破與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帶來更多的可能。
(一)巴斯德象限:基礎(chǔ)科學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耦合發(fā)展及其教育意蘊
科學與技術(shù)的關(guān)系,大體上有三種解釋框架:第一種是“獨立模式”,認為科學和技術(shù)是兩個相互獨立、基本沒有互動的知識領(lǐng)域,這一框架可以用來有效解釋古代及中世紀早期的實踐;第二種是“依賴模式”,認為不是科學依賴技術(shù)就是技術(shù)依賴科學,這一框架在解釋從中世紀早期到19世紀的實踐時卓有成效;第三種是“互助模式”,強調(diào)科學和技術(shù)之間形成了共生關(guān)系,且二者的區(qū)分越來越模糊,它是解釋20世紀以來科學與技術(shù)實踐的主導框架(Channell,2009)。這三種解釋框架基于不同時期的科學技術(shù)實踐,反映了不同時期科學與技術(shù)之間關(guān)系的認知。由技術(shù)創(chuàng)新所催生的科學遠不如基于科學而產(chǎn)生的技術(shù)的歷史久遠(趙克,2015)。基礎(chǔ)科學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之間曾被認為是“層次相關(guān)”,即科學與技術(shù)之間展現(xiàn)出線性延展的特征(周子荷等,2020),科學理論單方面推動了技術(shù)進步(Barnes,1982)。這在一定時期內(nèi)是符合事實的,但隨著實踐和認識的不斷深入,人們越來越發(fā)現(xiàn)兩者呈現(xiàn)平行交互、動態(tài)相關(guān)、相互促進的關(guān)系(Klahr,2019)。斯托克斯(2011)基于歷史發(fā)展劃分了科學與技術(shù)研究的類型,認為在由好奇心驅(qū)動的純粹基礎(chǔ)研究和以應(yīng)用實踐為導向的純粹應(yīng)用研究之外,還存在著由應(yīng)用激發(fā)的基礎(chǔ)研究,并把其命名為“巴斯德象限”,用巴斯德作為范例以隱喻基礎(chǔ)科學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之間的耦合發(fā)展關(guān)系。在斯托克斯看來,純粹基礎(chǔ)研究與純粹應(yīng)用研究沿著各自的軌道獨立發(fā)展,但并非沒有交集。由應(yīng)用激發(fā)的基礎(chǔ)研究就是連接上述兩個軌道的樞紐,它穿透了長期矗立在科學與技術(shù)實踐之間的深溝高壘,開辟了基礎(chǔ)科學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耦合發(fā)展的新格局。如果說在斯金納時代,教育領(lǐng)域基礎(chǔ)科學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還處于早期階段,展現(xiàn)出來的還是基礎(chǔ)科學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之間的線性關(guān)系,那么到了佩珀特時代,教育領(lǐng)域基礎(chǔ)科學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步入了新境界,越來越呈現(xiàn)出協(xié)同共生、耦合發(fā)展的新趨勢。時至今日,這一格局不但基本形成,甚至還有所發(fā)展。正如科拉爾(Klahr,2019)指出的,斯托克斯的分析框架以更宏闊的視野分析了不同類型研究之間的交互作用,在價值判斷上也摒棄了以往厚“此”(基礎(chǔ)研究)薄“彼”(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立場,而目前對學習的探索覆蓋了斯托克斯2乘2這一分類框架的所有類型。
就教育領(lǐng)域而言,基礎(chǔ)科學意義上的研究主要是學習的科學探索,即學習科學技術(shù)創(chuàng)新層面上的探索主要表現(xiàn)為各種技術(shù)手段在教育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創(chuàng)新和集成創(chuàng)新,即教育技術(shù)。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學習科學與教育技術(shù)兩者各自獨立運作,平行發(fā)展。學習科學主要依賴于以心理學為主的學習研究不斷向前推進。教育技術(shù)主要表現(xiàn)為各種通用技術(shù)在教育領(lǐng)域的集成應(yīng)用。二者最后在教育實踐的場域中相遇。隨著時間的推移,教育領(lǐng)域基礎(chǔ)科學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兩條平行線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交互愈發(fā)頻繁,呈二元耦合、一體發(fā)展的趨勢。這意味著,教育的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越迅速,學習的基礎(chǔ)科學研究就越深入;反之,學習的基礎(chǔ)研究越深入,教育的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就越加速。這對于教育系統(tǒng)的變革具有重要意義。歷史地看,教育系統(tǒng)幾乎符合超穩(wěn)定結(jié)構(gòu)的所有特征,長期保持在超穩(wěn)定狀態(tài),缺乏自發(fā)變革的動力,面對外部因素遵循的是“沖擊—回應(yīng)”模式,面臨的也是強制性變遷,最終收獲的結(jié)局是“有變化而無變革”(Cuban,1997)。有學者曾經(jīng)指出:“到1520年,西方世界建立的約85個機構(gòu)至今仍以其公認的形式存在著。這些機構(gòu)有相似的功能,歷史也不曾中斷。它們包括天主教會,馬恩島、冰島和大不列顛議會,瑞士幾個州和70所大學(克拉克,1993)。”就變化相對較快的教育信息化領(lǐng)域來說,也長期存在著“新瓶裝老酒”的批評(Tay et al. , 2018)。教育系統(tǒng)的超穩(wěn)定性由此可以一斑。形成這種超穩(wěn)定結(jié)構(gòu)的原因很多,包括時代變遷和社會發(fā)展的制約等,但歸根結(jié)底還在于教育系統(tǒng)自身原始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教育領(lǐng)域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與基礎(chǔ)科學研究的二元耦合模式將有助于打破教育系統(tǒng)的超穩(wěn)定結(jié)構(gòu),擴大教育系統(tǒng)中以創(chuàng)新為基礎(chǔ)之轉(zhuǎn)型實踐的規(guī)模(Serdyukov,2017)。
(二)巴斯德象限的人工智能:既是學習的科學也是教育的技術(shù)
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反映了當代基礎(chǔ)科學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普遍規(guī)律,即基礎(chǔ)科學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一體化。當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shù)強勢崛起,為教育領(lǐng)域提供了基礎(chǔ)科學研究與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協(xié)調(diào)共生、耦合發(fā)展的新機遇。早在三十年前,人工智能專家尚克(Schank et al. , 1991)就提出了審視人工智能未來發(fā)展的三重視角:科學的、技術(shù)的和教育的。這三重視角有個共同主題,即對學習中心地位的強調(diào)。從科學的視角看,人工智能構(gòu)造的心智模型必須能夠解釋不同的學習現(xiàn)象;從技術(shù)的視角看,人工智能構(gòu)造的計算機系統(tǒng)要促進初始知識的習得并最終適應(yīng)各種新情境,擁有學習能力是一項最基本的技術(shù)要求。站在教育的立場上看人工智能,它既是學習的科學,也是教育的技術(shù),一如硬幣的兩面。人工智能的終極使命是用技術(shù)手段模擬人類智能。要用技術(shù)手段模擬人類智能,顯然離不開對人類智能特別是學習機制的理解與認知。對人類智能特別是人類學習的研究本就是人工智能科學的主要部分,甚至有部分人工智能專家在人工智能研究陷入最低潮時直接轉(zhuǎn)入對人類學習的科學探索(Kolodner,2004)。20世紀70年代,尚克試圖將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成果應(yīng)用于自然語言理解,卻屢屢受挫。他發(fā)現(xiàn):“要想讓機器變得更智能,就必須思考機器怎樣學習,而答案在于只有人才是能夠讓研究并得出答案的唯一實體”(Beach,1993)。其后,他轉(zhuǎn)入對人類學習的基礎(chǔ)研究,進而開辟了學習科學這一新領(lǐng)域。在第一代學習科學家群體中,很多研究者都來自人工智能領(lǐng)域,其背后的邏輯正在于此。同時,還可以看到學習科學家在探索人類學習機制的過程中,不斷從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發(fā)展獲得思想靈感和技術(shù)支持。事實上,早期研究學習的認知科學家正是從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研究中受到啟發(fā),才建立了人類認知的“計算機隱喻”和“機器隱喻”(Searle,1990)。
正如尚克(Schank et al. , 1991)所指出的,應(yīng)該放棄把人工智能理解為一種技術(shù)這樣膚淺的想法,只有從科學和技術(shù)兩個層面上才能夠揭示人工智能這一領(lǐng)域豐富的層次,并揭示它和教育之間的親緣關(guān)系。從科學層面看,人工智能的底層研究以對人類智能、人類學習機制的理解為基礎(chǔ)。經(jīng)典著作《計算機與思維》概括了推動人工智能早期發(fā)展的三大目標,其中兩個目標均涉及以理解人類學習為基礎(chǔ)的科學理論的發(fā)展:第一是形成“復雜信息處理”能力,構(gòu)建基于智能的計算機程序,發(fā)展智能系統(tǒng)的基本理論;第二是通過將任務(wù)拆解成人類處理類似任務(wù)的程序化過程進行智能挖掘,從而在理論層面探索如何對機器進行人類智能的模擬。人工智能是計算機科學的一部分(Newell et al. , 1967),同時也深深地植根于心理學和認知科學(Frankish et al. , 2014)。人工智能的大部分基礎(chǔ)研究是基于認知開展的(Glymour,1988),主要研究計算機執(zhí)行任務(wù)時智能化的解決方案,涉及到人類處理類似任務(wù)時的智能思維(Simon,1995),如最早的人工智能程序“邏輯理論家”的設(shè)計便受到了心理學研究關(guān)于記憶和問題解決能力的啟發(fā)(Newell et al. , 1956;Hutchins,1995)。近年來,人工智能圍繞認知架構(gòu),即基于認知主體信息處理系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和性質(zhì),發(fā)展計算機的認知功能(Carter,2007)。智能與適應(yīng)能力密切相關(guān),包括解決問題、學習與改進的能力,而人工則是研究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具體手段(Simon,1996)。認知科學是一門人工科學,關(guān)注心智適應(yīng)不同場景發(fā)生的變化(Simon,1980),這對于人工智能自適應(yīng)功能的發(fā)展有強大的支撐作用。人工智能高度關(guān)注人類的心智模式,這與學習科學家的追求是一致的。人工智能底層的基礎(chǔ)科學集計算機科學、認知科學、心理學、腦科學、語言學等為一體,這種交叉學科性質(zhì)蘊含了對學習的多視角、多層次理解,無疑可以有效提升技術(shù)設(shè)計過程中的科學性及其后續(xù)在教育場景中的應(yīng)用與轉(zhuǎn)換能力。長期以來,在認知理論能夠預測什么以及究竟什么才在真實場景中具有教育意義之間長期缺乏聯(lián)系,20世紀90年代初學習科學的崛起有效促進了二者的融合,使有關(guān)學習的科學研究與針對教育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之間實現(xiàn)了耦合發(fā)展(Hoadley,2018)。
人工智能內(nèi)在地包含了學習的科學與教育的技術(shù)。一方面,有關(guān)人類學習的科學理論為人工智能系統(tǒng)的搭建提供了精細、便捷的指南;另一方面,可操作的人工智能系統(tǒng)包含了大量結(jié)構(gòu)化的程序,而不同腳本的實現(xiàn)方式代表了不同的理論,在程序運行時表現(xiàn)出不同的特性,從中可以提煉學習的基本規(guī)律,促進相應(yīng)的學習理論的形成、檢驗及完善。對學習機制的科學探索為人工智能時代教育技術(shù)的設(shè)計提供了基礎(chǔ)支撐(Luckin,2019),極大地豐富了人工智能技術(shù)在教育場景中的垂直應(yīng)用,同時又不斷從人工智能的理論發(fā)展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中汲取靈感和力量,持續(xù)深化對學習的科學認識。就人類學習而言,認知和情緒是兩個基本的組成部分。以情緒這一議題為例。情緒狀態(tài)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學生學習態(tài)度和效率產(chǎn)生影響(Nkambou et al. , 2010),所以受到廣泛關(guān)注。人工智能利用技術(shù)手段針對涉及學生情緒的各種可察覺因素與可測量行為獲取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梁迎麗等,2018),可以有效實現(xiàn)對學生情緒的感知、識別、調(diào)節(jié)與預測,提升對學習過程中學習者情緒的理解與認識的科學化與精準化水平,同時認知科學、心理學等模型也為實現(xiàn)人工智能技術(shù)教育應(yīng)用的情緒識別、情感計算等工作提供了科學理論支撐(Petrovica et al. , 2017)。由于人工智能內(nèi)在地包含了學習的科學與教育的技術(shù),并在應(yīng)用中實現(xiàn)了二者的耦合一體發(fā)展,必將改變技術(shù)與教育融合的基本格局。既往對信息技術(shù)與教育融合的強調(diào)主要是單向度的,即信息技術(shù)在教育領(lǐng)域內(nèi)的應(yīng)用。人工智能時代需要超越這種單向度,更全面地認識信息技術(shù)與教育的深度融合,更注重推進人工智能與教育實踐的雙向交互而不是單向應(yīng)用。這不僅可以把教育領(lǐng)域的基礎(chǔ)科學研究與技術(shù)原始創(chuàng)新推進到新的高度,同時也必將有力地促進人工智能自身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在內(nèi)部實現(xiàn)學習的基礎(chǔ)科學與教育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耦合發(fā)展,在外部實現(xiàn)技術(shù)和教育的雙向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