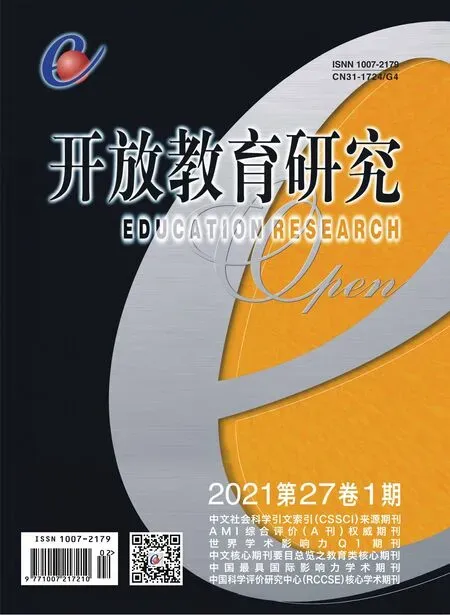理論與技術
□文 青
教育研究領域有一對冤家:理論研究與技術研究,兩者互不對眼。搞理論研究的人覺得技術研究膚淺,沒有深度,因此常常對技術研究鄙視、輕慢。搞技術研究的人覺得理論研究故作高深,不務實,說得天花亂墜,但大多數只是鏡中花、水中月。
這樣的暗斗,不知道始于何時,又會止于何時。在我看來,雙方都是弄錯了“ 斗爭”的焦點,誤以為研究講究的是文章好看、耐看,而不是如何更好地改進教學實踐。就理論研究而言,即便再抽象深奧,若不能改進教學實踐,又有什么價值呢?近年來教育學原理方面的新作可謂汗牛充棟,但對改進教學實踐的作用可能還不如蘇聯霍姆林斯基的《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等著作有用(那都是來自實踐的真知)。而對于技術研究來說,即使再淺顯、再沒有內涵,如果能對教學實踐產生積極作用,這難道不是教育研究所欲求的目的嗎? 所以,評判教育研究優劣的標尺應該是:能否改進教學實踐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進教學實踐。除此之外,其他的標尺大概率是虛枉、裝飾、無意義的。
日本同行的做法也許很值得學習。佐藤學教授在《靜悄悄的革命》 一書中說:“ 我每周到各地的學校訪問,在各個教室里觀摩,近20 年一直如此。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養護學校等,我看過數不清的教室。”正因如此,才使書本中討論的學生“ 手勢”“ 潤澤的教室”等,讀來親切而又令人感動,因為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發生在課堂中、教室里的故事。日本東京大學牧野篤教授指出,東京大學一直嘗試踐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終身學習研究室走出大學,在千葉縣柏市的居民區推進“ 多世代交流型社區建設”項目,組建當地老齡者的多世代交流型社區建設委員會,促進居民交流的社區咖啡廳開展活動,切實推進社區建設。
我不知道日本同行的研究是否都如此,但這兩個案例足以展現他們的教育研究方式。在我國教育技術領域,曾有何克抗、李克東等老一輩技術人,他們走進學校和課堂,親臨實踐一線。何克抗老先生背著書包坐在教室聽課的場景,依然清晰地印刻在很多人心中。今天,這樣深入一線探尋“ 真”問題的研究者,能有幾人?
有學者指出,教育是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所謂實踐性,以我的理解,是指不能一地味強調理論,而要把實踐、經驗放到比較重要的位置。滿足于在書齋中“ 指點江山”的“ 應然”研究,大多是“ 屠龍術”。有朋友甚至說,美國沒有所謂的《教育學原理》《 教育學》 等論著,但我們能說美國的教育研究不發達嗎?
所以,重抽象深奧、輕指導實踐的教育研究,是迷失了方向。這從小的方面來說,是研究風氣的不正;從大的方面來說,則是貽害國民,切不可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