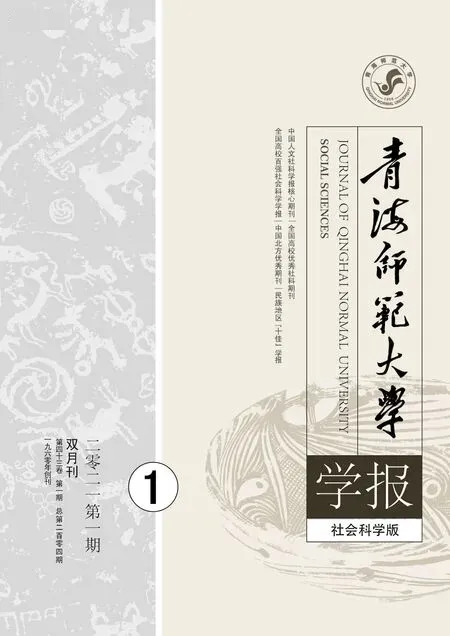規訓主體的沉默與歷史斷裂處他者的聲音
——《一場冰激凌戰爭》中的后現代歷史書寫
常智勇
(1.中國人民大學 外國語學院,北京 100872;2.唐山學院 外語系,河北 唐山 063000)
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1952-)是當代英國文壇一位著名的后現代作家,在20世紀80年代被評論界視為新憤怒的青年代表作家。他在1982年出版了長篇小說《一場冰激凌戰爭》,同年榮獲約翰·萊維林·萊斯紀念獎(John Llewellyn Rhys Prize)和布克提名獎(Booker Prize)。小說書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東非戰場的一個戰爭場景,一個殘酷的、但鮮為人知、滑稽的戰爭場景。福柯曾提出以“考古學”的方式重構歷史,這是對歷史書寫的一個重大轉變,他告訴我們,要對歷史中的“裂隙”“非連續性”“斷裂”關注,對歷史中時代之間的差異重視。目前一戰史的書寫主要以歐洲戰場的宏大歷史敘事為主,博伊德的這篇小說書寫了斷裂處的、小寫的他者歷史,承認并尊重差異的歷史,豐富了歷史的多元性,把歷史上 “曾經消失的他者語言”與被遺忘的角落的歷史重現在歷史的洪流當中。在《后現代主義詩學》中,琳達·哈琴引用赫伯特·林登堡的話說“文學作為一個知識體系拋棄了此前的圍欄、界限……歷史開始顯現斷裂趨勢,有時確實只不過像又一虛構之物而已。”[1]用文學的方式重溫那段鮮為人知的血與火的歷史,反思人類生存和發展、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從而更加珍惜生命、珍愛和平。由于非洲天氣炎熱潮濕,“我們都會像冰激凌一樣在太陽下融化”[2],從小說的題目“冰激凌戰爭”我們推斷戰爭將可能不會持續太久,但事實恰恰相反,英德在東非殖民地的矛盾沖突在一戰爆發之前已經開始,因為消息滯后的原因,英德兩國之間已經簽署停戰協定,而東非戰場的沖突還在繼續。小說題目本身就暗含著對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殘酷的爭奪戰爭的無情諷刺。作者通過讓小說參與歷史的闡釋,把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請上歷史舞臺,賦予他們言說的機會,訴說他們個人經歷與感受到的不同歷史,揭露官方宏大歷史斷裂處的他者歷史。因為在后現代語境下,歷史的書寫不再是連續的、線性的,而是要在宏大的歷史語境中尋找斷裂的、碎片化的反思空間。這部小說重寫了非洲戰場戰爭創傷,進一步闡釋了一戰不僅給歐洲國家和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而且也給在非洲地區參加一戰的無辜的士兵及其家庭也帶來了無盡的創傷,作者淡化并打通了文學與歷史的界限,把斷裂處的他者歷史以小說這種文學形式呈現給讀者,這部以后現代方式書寫的歷史小說充分體現了博伊德尊重差異的、多元的歷史觀。福柯認為“從政治的多變性到‘物質文明’特有的緩慢性,分析的層次變得多種多樣:每個層次都有自己獨特的斷裂,每個層次都蘊含著自己特有的分割;人們越是接近最深的層次,斷裂也就隨之越來越大。”[3]透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宏大歷史的斷裂處,結合《一場冰激凌戰爭》這部小說文本,把握邊緣話語的聲音,揭露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精神影響下的保守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壓抑,讓他者言說歷史,重新闡釋一戰歷史的殘酷性和無意義性。
一、維多利亞時代精神壓制下的主體的規訓與沉默
現代西方哲學從啟蒙現代性開始探討主體性、意識與存在的關系等哲學議題,強調主體性、統一性、宏大敘事 、元話語等,而“他者”被排斥到了邊緣地位。張劍教授在《他者》一篇文章中指出,他者的存在對自我的總體性和自發性構成了一種質疑,因此列維納斯認為,整個西方哲學傳統就是自我不斷消化他者、吸收他者,不斷將他者納入自我意識、對其進行感知和認識的過程。如果他人的言行對于我們來說不可理解,那么最容易解決的辦法,就是將其視為庸俗和低級加以歸納和拋棄。這樣一個過程,也是一個不斷使用壓迫性策略對他者進行收編、同化、馴化的過程,一個自我對于他者行使主觀暴力的過程。[4]
葛蘭西認為,資產階級將自身的哲學、道德等滲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經驗和實踐,并最終使他們“保存了統治集團的心態、意識形態和目標”,上層集團的統治與壓迫由此被轉化為對普通人的常識進行塑造的話語實踐和策略。[5]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時,雖然維多利亞時代過去了十多年,但是“維多利亞精神”已經凝縮成為一種文化存在形態,不僅是時代精神面貌的抽象概括,同時還潛藏了時代烙印,蘊含了從維多利亞時代過來的英國人的思想觀念、道德規范和意識形態。在小說中出現了以科布少校為代表的斯塔克波爾莊園一家人,這家人仍然受到“維多利亞時代精神”的影響,在思想領域仍保持著維多利亞主流社會的功利主義思想,在道德與性別方面則用維多利亞時代的“紳士”與“淑女”觀念進行規訓與塑形,以科布為代表的這家男性有幾位是軍人出身,懷有大英帝國是“殖民帝國”和“日不落帝國”思想。維多利亞時期的“紳士風度”是與貴族精神融合后的結果,其特點為理性主宰一切,盡量抑制感情色彩,具有堅韌不拔、勇往直前的氣概,為維護個人和國家榮譽在所不惜,但是它過于保守和傳統,這也是維多利亞后期英國工業逐步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除菲利克斯之外,這家人完全是被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收編、同化、馴化”的主體,尤其科布少校完全受英帝國是“日不落帝國”的思想觀念的影響。實際上英國參戰的主要原因是維護大英帝國的殖民利益和軍事霸權、挫敗強敵德國,并不是像官方宣稱的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這也決定了英國方面帝國主義戰爭的非正義性。在一戰前夕,英國阿斯奎斯政府推出新的征兵議案,科布少校恨不得把自己的兒子、女婿一家所有男人全部送上戰場,從不考慮子女的個人感受,也不考慮戰爭是為了什么,他完全被“維多利亞時代精神”馴化了。只有他的小兒子菲利克斯一直在質問“我們戰爭是為了什么?”只有他質疑、控訴戰爭,究竟為什么要戰爭,究竟是誰在默默地承受著一切,但是菲利克斯在這個家里完全是被邊緣化的他者,而當菲利克斯姐夫亨利·許亞姆斯聽到他去牛津讀書時,說他是“逃避兵役者”。“蓋布里埃爾是他父親一生的抱負和關注點,而他(菲利克斯)幾乎沒有被軍國主義所腐蝕。”[6]當一戰爆發時,科布少校的長子蓋布里埃爾正在法國和新婚妻子度蜜月,但是聽到戰爭的消息,很堅定地結束了蜜月回歸軍隊。“我們必須回家,我就知道會發生。沒有其他事情,一定是歐洲戰爭,卡麗絲。我們必須回去,立刻,今天。”[7]由此可以推斷這家人除了菲利克斯之外,全部是被維多利亞精神吸納的沉默主體,根本不質問戰爭為什么發生,有何意義。雖然菲利克斯質問戰爭的意義,但他又是被這些馴化的主體邊緣化的他者。
博伊德不只批評維多利亞時代的“紳士”腐朽和保守的思想觀念,更重要的是批評維系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每個時代的建筑是同時代人們文化、思想觀念的反應,作者從描寫斯塔克波爾莊園的建筑物入手,抨擊了受維多利亞時代精神影響的沉默的科布一家人的迂腐、守舊思想。菲利克斯在寫給朋友霍蘭德的信中諷刺了自家的建筑,“這幢令人討厭的房子就像掉在肯特郡的一個龐大的具有惡臭的尸體,因腐敗物閃著銀光,住著光滑的、灰白的、自鳴得意的蛆,他們大多數穿著軍裝。我的家,上帝把我從我家拯救出來吧。”[8]菲利克斯把自己家的房子比喻成了腐爛的尸體,而把自己的家人比喻成了生活在尸體里的令人惡心的蛆,這種比喻一方面體現了菲利克斯對自家的莊園的厭惡,同時也是他對一家人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很迂腐的諷刺。有一次菲利克斯從學校回到家時,“菲利克斯站在石子路上,抬頭望著莊園的房子。那是一座很奇怪的建筑物。房子的正面朝北,是一座古典的三層喬治時代的磚結構的樓房,樓房的前門有整齊的廊柱,樓房正面還有幾排整齊的可以上下拉動的窗戶。然而,之前房子的擁有者,菲利克斯的伯父杰拉爾德實際上已經在這座樓后面加添了一座完全新的、更大的建筑物,用很現代的大廈擋住了原來舊樓房的南面。在菲利克斯眼里,這幢不自然的緊密連接的建筑物是一個褻瀆神靈的行為。因此現在被修整的漂亮的南草坪面對著一個混亂的、不優雅的建筑風格”[9]。菲利克斯眼里的斯塔克波爾莊園,就是維多利亞時代建筑的縮影,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筑設計思想,既有面向傳統的一面,也有面向創新的一面,建筑設計思想表現出矛盾的兩重性,即一方面復古思潮下的設計思想強調對傳統設計風格的復興,是一種尊重傳統的保守主義態度,注重在歷史風格中尋找符合時代要求的建筑形制;另一方面變異思潮下的設計思想看重的是建筑類型的創新,是渴望變革的激進主義的面孔,鐘情于新材料、新技術和新結構的應用,渴望創造符合功能需要的建筑新形制。這兩種設計思想在價值取向上是矛盾的,前者強調傳統風格的純粹性,維護既定的秩序,后者強調建筑風格的創新性,傾向變革的效率。“建筑是每一文化背景下整體文化現象的一個環節,是這種文化的表現”。[10]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筑呈現的“復古與變異”并存的特色,很大程度上是由該時期英國文化決定的。斯塔克波爾莊園既有傳統的元素,又有現代的設計風格,反映了以科布少校為代表的這一家人的迂腐守舊思想,也體現了菲利克斯追求新思想的現代觀念。小說的時代背景正處于從維多利亞時代向現代化轉變的過渡時期,以科布為代表的一家人受維多利亞時代思想觀念影響很深,忠君思想、帝國思想始終影響著他們,在面對突如其來的戰爭時,對于君主與國家的命令,只能沉默地遵從,因此造成了這家人的悲劇不斷。對這一建筑物的描寫充滿著深刻的含義,斯塔克波爾莊園既有古老建筑風格,又有現代建筑風格,但是古老建筑在正面,其“奇怪的建筑”事實隱藏了更大的象征和深遠的思考。房子的裝修僅僅是一個借口,這說明在20世紀初,這家人自我主體意識不強,他們只是君主制社會從屬的、規訓的、沉默的主體,保守思想仍然很嚴重,與所處的時代很不相稱。這樣的描寫隱含著作者對科布一家保守的憎惡,以及反戰思想。
羅蘭·巴特認為“城市是一種話語。實際上它是一種語言”[11]。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們帶來了悲觀的情緒,昔日教育與經濟文化中心的牛津和倫敦在小說中被描寫成像經歷過某種疾病的城市,“牛津已經變得十分的沮喪。這不是牛津的錯誤,而是因為戰爭”[12]。這兩座病態的城市以沉默的語言訴說著戰爭所帶來的痛苦。很明顯,博伊德賦予像城市這樣無生命的東西以生命,通過城市的書寫,以沉默的方式向世界訴說著因為戰爭給人們帶來的精神上的失望與痛苦。在帝國主義國家殘酷戰爭的籠罩下無疑這兩座城也成了被“收編”的、沉默主體的再現。城市好比一個滿載意義的交流系統,作者通過小說的文學形式進行想象、建構,幫助城市言說自身、講述歷史,城市里的每個印記、符號都訴說著某段歷史,以沉默的方式訴說這里曾經發生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們心靈造成了無盡的創傷,而此時菲利克斯所就讀的牛津大學也給人一種悲涼、凄慘的感覺,“幾乎像所有牛津的建筑物一樣,石頭現在很黑,由于巖石剝落顯得很破敗。持續的下雨和烏云加重了這種印象:這些宿舍看起來好像正在經受某種特殊的令人不愉快的萎縮病。菲利克斯抬頭望頂層的窗戶,霍蘭德房間的燈還在亮著。穿軍服的士兵好像到處都是。”[13]如同菲利克斯自己所感慨的,自己曾經崇拜的、向往的文化之城、知識之城,現在就讀于此的牛津城,不能再實現自己的夢想了。博伊德把牛津作為患有疾病的城市探討,是他在作品中譴責英國當局為了帝國主義之間利益的爭奪而進行的無意義的戰爭,國家為此也忍受著嚴重的傷痛。 牛津大學“在往年的每個學期,熙熙攘攘的人們要么和朋友們去聽講座,要么去吃早餐,而此時由于戰爭的原因,大學里空了一半,甚至就這些人還有一部分從其他大學來的,因為那些大學給各種軍隊的士兵用作臨時軍營了。”[14]戰爭把昔日書香飄逸、莘莘學子書聲瑯瑯的學術殿堂變成了英國大兵的臨時兵營,校園里沒有了往日學子們青春洋溢的臉龐,干凈、純潔的大學校園也因為戰爭遭到了英國當局的無情踐踏。而此時這座城市只能以沉默的語言向人們傾訴,訴說著在當時統治者官方政治氛圍的壓抑下,城市也成了被官方“收編”的沉默主體。
二、非洲自然環境他者“抵抗”帝國主義殖民者的隱喻
《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提出了“由于我們許多的社會現實是以隱喻來理解的,也由于我們的物質世界概念是隱喻性的,因此隱喻在決定我們的現實內容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15]小說中隱喻修辭手法的使用可以增強作品的感染力,使作品顯得更加精彩和深刻,更能打動讀者并能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從而加深讀者對文本的理解和記憶。在文學史上,自然環境和自然界中的生物一直是作家表達觀點和抒發感情的重要載體,它們本身及其外在表現往往承載著作者的某些情感。結合小說《一場冰激凌戰爭》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社會背景,小說對非洲自然環境與生物表現出來的對戰爭憎恨的隱喻進行分析,來幫助讀者理解作者反戰小說的深刻內涵,引發人們反思戰爭、珍愛和平。
書寫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非洲戰場的著作相對比較少,與歐洲戰場的重要性相比它可以被忽略不計,博伊德選擇了一戰中的非洲戰場,他描寫的非洲惡劣的環境,不同于英國柔和的氣候環境,非洲用懷有“敵意的”、有時是無法容忍的氣候條件“歡迎”闖入的英帝國的士兵。難耐的炎熱、具有攻擊性的昆蟲首先成為被派遣到東非的英國士兵不得不忍受的、無法逃避的“對手”。小說中非洲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具有攻擊性的生物成了作者抨擊戰爭的隱喻對象。
在當時西方社會以人類為中心的哲學思想指導下,人是這個世界的主宰,而世界上的自然、生物都是受人類支配的他者。當征服世界的英帝國軍隊踏上非洲大陸時,作者在小說中利用了非洲的自然環境“他者”,發出了對英德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爭奪非洲殖民地的“抗議”。小說中沒有同歐洲戰場一樣英德雙方對壘的大規模戰爭場面的描寫,而是描寫個別人物的遭遇,以及來自歐洲的士兵不適應非洲惡劣的自然環境,遭到了這里的自然環境的“抵抗”,這樣的滑稽描寫凸顯了英國士兵的無能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戰爭的無意義。小說中很多的地方描寫了非洲的高溫炎熱、潮濕的氣候,使來自英國的軍隊難以忍受非洲的酷熱,造成軍隊的混亂,而潰不成軍。當英國軍隊剛剛到達德屬東非殖民地坦噶的時候,炎熱潮濕的天氣讓他們非常不適應,軍容不整,“英國士兵們只穿著襯衫,看上去熱得面紅耳赤,被曬傷了。”[16]在非洲大草原上蓋布里埃爾也是又熱又渴,“一直到現在他(蓋布里埃爾)一直淌著汗水。……他摘掉太陽帽,用手掌擦掉前額上的汗珠。他的頭發完全濕了,好像他剛剛浸在了一盆溫的鹽水里似的。”[17]從這些英國士兵散漫、慵懶、缺乏軍人的戰斗力的表現,很難看出是參加前線戰斗的,非洲酷熱的氣候使他們很不適應,從軍官到士兵都難以忍受這里的炎熱,非洲大陸以它獨有的環境無聲地“抵抗”這些剛剛踏上非洲大陸的西方闖入者,還沒有參加戰爭就已經潰不成軍,揭露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的殘酷性和無意義。
另外非洲各種自然生物很多,對來自異域的無知的闖入者造成恐慌,其中“蜜蜂的戰斗”很有諷刺性,最初愚蠢的英國士兵以為是遭到了密密麻麻的子彈的掃射,實際上是他們被一群蜜蜂蟄得鬼哭狼嚎。“他被擊中了!突然使他驚訝的是,空中有‘密密麻麻的子彈’。不知不覺的這個詞就進入了他(加里布埃爾)大腦……他突然感到脖子上一陣灼痛。他被擊中!哦,天哪,他想,不在脖子上。他被絆倒,起來繼續跑,用手去捂住傷口,子彈還在嗡嗡的朝他發射過來。但是過了一會兒,他想,這不是子彈,是蜜蜂!他停下來轉過身,看到他的戰友們遭到蜜蜂的攻擊,像癲癇患者在地上鬼哭狼嚎地翻滾。”[18]生活在非洲大地上的小小的蜜蜂只不過是這個世界中弱小的他者,但是在以人類為中心的英帝國主義軍隊面前,蜜蜂也以自己的抵抗方式,對闖入的帝國主義殖民者進行了無情的攻擊。作者用“蜜蜂的戰斗”嘲諷了英國士兵不能區分子彈的嗖嗖聲和蜜蜂的嗡嗡聲,滑稽地諷刺了英國軍隊的無能、無戰斗力,“蜜蜂的戰斗”是對英國帝國主義列強入侵非洲的“抗議”,揭露了英德帝國主義國家發動戰爭的無意義和非正義性。
小說中寫到在戰爭即將結束時,英國軍隊感染了西班牙流感,造成大量士兵死亡,甚至比在戰場上死亡的人數還多,給英國軍隊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很多人在戰場上死于疾病和惡劣的自然條件,“自從那時起,一百多名搬運工和三十多名士兵死于各種疾病,大多數得了瘧疾和痢疾,但是后來因為鋌而走險的尋找營養,大多數搬運工食用了有毒的樹根和水果而死。”[19]菲利克斯說:“四年戰爭之后,死于流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你知道,他們多一半已經死了。”[20]當時這種新型的流感疫情已在全球流行,造成了全世界的恐慌,軍隊也不例外,造成了大量英國軍人的死亡,因此戰爭也不得不提前結束。作者以當時人們不熟悉的新型流感造成大量軍人死亡結束了小說,從而也用這種神秘的隱喻形式暗示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殘酷和無意義。非洲大陸上的惡劣的自然環境、被激怒的生物、突如其來的流行疾病等這些無聲的他者,給英帝國軍隊士兵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這些來自遙遠歐洲的年輕士兵沒有戰死沙場,卻斃命于異域惡劣的環境。這些惡劣環境“抵抗”的隱喻批判了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統治者為了爭奪世界的霸權,發動戰爭,給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災難,這些無聲的他者不再沉默,對強大的西方闖入者用無情反抗的方式控訴著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的殘酷與無意義。
三、被邊緣的他者抗議主體的權威,痛斥戰爭的無意義
現代主義的倫理是主體主宰、控制著他者,而他者大多數情況下只能以沉默的方式存在,后現代倫理承認差異、尊重他者,為他者負責。反思文學,它意味著每一個文本都參與了知識和權力的游戲。福柯描述了一個強大的無處不在的權力體系,及其對他者實施的霸權性壓迫,《一場冰激凌戰爭》中的菲利克斯和坦普爾是被邊緣的他者,是一種抵制權力的建設力量,他們對帝國主義國家官方的政治話語、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發出了抗議,諷刺了戰爭的無意義。列為納斯認為“歷史中布滿了斷裂,在這些斷裂處,歷史承受著審判。當人真正接近他人時,他就被從歷史中連根拔起。”[21]
20世紀初英國政府與整個社會都處于普遍保守的狀態,菲利克斯是他的家庭里唯一一個能對官方及其意識形態提出質疑的人。他憎惡維多利亞式的舊家庭觀念,鄙視各種權力機構和虛偽的教堂,討厭、排斥無意義的參軍參戰。當時很多人都把這場戰爭說成是神圣事業,反戰者屬于極少數。菲利克斯不情愿接受當局機構的欺騙,所以成了被邊緣的他者。當得知蓋布里埃爾在戰場上受傷被俘時,他感到“家里的生活變得幾乎難以忍受,許多憤怒的面孔都指向了菲利克斯,好像他要對蓋布里埃爾的艱難的困境承擔責任似的。”[22]因此不得不提前返回了學校。
菲利克斯·科布的家庭是一個軍事世家。他的父親曾是一名陸軍少校,擔任過重要的職位,哥哥也應征參加了軍隊,姐夫也在軍隊任職,這樣的大家庭是典型的尚武精神的軍人家庭。按照英國舊家庭傳統思想,父親非常期望菲利克斯繼承家庭軍事傳統,然而卻令父親很失望。菲利克斯曾說“我向你保證我沒有當兵的打算,從來沒有,永遠不會有。”[23]于是他決心去牛津大學讀書,而他父親非常反對他的決定,認為他的兒子正在被叛家庭的傳統,從此父子關系緊張。其實緊張的父子關系不僅僅是因為菲利克斯的不參軍,而是他們之間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原因。父親科布少校是英國舊式的、維多利亞式思想代表的化身,他對軍事的熱情態度讓菲利克斯難以忍受,菲利克斯認為他父親“看上去有些像發狂的維多利亞式的神父”,對他父親說話的方式也說明他對英國貴族舊的體制的反抗,對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抵制。
英德兩國在非洲的戰爭是為了爭奪在非洲的殖民地,雙方都沒有正義性,因此菲利克斯認為完全是資產階級統治者強迫這些年輕士兵在戰爭中自相殘殺,因此他面對強勢的官方主體,作為他者的代表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菲利克斯震驚地認識到,在前線的三個月,他從來沒有看到敵人的士兵。他的仇恨完全是被他的同伴們宣揚的……他荒謬的 ‘追尋’終于在Kibongo的泥水里失敗,他高大的理想和熱烈的追求被對潮濕的天氣的牢騷和關于吃什么的無窮推測代替。”[24]菲利克斯一直在質問戰爭的無意義,這場無意義的戰爭只不過是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集團為了爭奪世界霸權而發動的,卻給無數的家庭帶來了無盡的悲痛和創傷。“他(菲利克斯)對在非洲的戰爭一無所知,也忘記了在歐洲的戰爭。……他很氣憤地責問自己這是哪一種戰爭。沒有看見敵人,你們的人慢慢地被餓死,就是為了守衛被雨水濕透了的叢林中間的一堆茅草屋。”[25]在不知道戰爭緣由的情況下,很多英國青年來到遠離國家的非洲大陸參加戰爭,不但經歷了槍林彈雨的洗禮,而且還遭遇了惡劣自然環境和疾病的侵襲,給遠離自己家庭的這些英國青年帶來了身體上和精神上創傷。
菲利克斯除了對舊式貴族思想、軍隊風氣進行了諷刺之外,他對教堂以及在教堂舉行的傳統儀式也進行了批判與諷刺,因為在他看來教堂也是一個過時的機構,他作為小說中的發聲者對舊式貴族思想、軍事風氣、代表宗教的教堂儀式三者都進行了批評,表現了菲利克斯對宗教反感與不信任。 當哥哥蓋布里埃爾和卡麗絲正要在教堂舉辦婚禮儀式時,“菲利克斯又感到了惡心。教堂里突然充滿了古代灰塵與石頭的味道,與鮮花的香味和玫瑰香水混雜在一起。”[26]在菲利克斯眼里,教堂里舉辦的婚禮屬于舊式的傳統,很反感繁文縟節的禮節。當參加完蓋布里埃爾的婚禮之后,“維納布爾斯醫生問‘菲利克斯,你沒事吧?你看上去有點兒筋疲力盡。’‘我很好。我步行回去就會好了,我想跟教堂里的氛圍有關吧。’”[27]從他們的對話中可以看出菲利克斯多么的抵觸宗教儀式,在西方宗教、教堂畢竟是很神圣的,從菲利克斯的話語當中可以推斷他對西方神圣與權威的抵抗。而且他認為教堂虔誠的儀式是虛偽的,是感觸不到的東西,是虛無的。 “當然不否認。只是不信仰那個儀式。然而,儀式……虛偽的虔誠。”[28]菲利克斯無情地批判了代表西方神圣與權威的宗教儀式,顛覆了西方國家的崇高的精神信仰。在某種意義上,菲利克斯作為一個接受現代啟蒙的人,公開不接受教堂的精神教義,強調只依靠自己理解的知識,蔑視任何與精神性和宗教狂熱相關的事情。
作為小說中另一個被邊緣化的他者——坦普爾的聲音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揭露了英國軍隊的無戰斗力、精神渙散,英國軍官的腐敗、官僚作風以及指揮者的無能。坦普爾是一個美國人,來到東非的坦桑尼亞經營自己的農場,不屬于兩個交戰國的任何一方,可以很超然地面對這場戰爭中的人與事。但是戰爭讓他失去了自己安逸的家園,破壞了他追求更高的生活夢想。開始時,坦普爾寄希望于英國殖民者,向殖民當局提出抗議“我是難民”“我是德國戰爭犯罪的受害者,理所當然地你們要保護照顧難民”[29],因為看到了英國在非洲的參戰軍隊的無能與腐敗,起初殖民當局向坦普爾承諾的會有保險公司的賠償,隨著保險公司業務員的死亡,他被賠償的希望破滅。后來坦普爾接收了惠奇·勃朗寧的建議“你打算回到你自己農場的唯一辦法就是參軍,為你的夢想戰斗到底”[30]。坦普爾被迫加入了英國的軍隊,為的是親自奪取自己的家園。但是在后來的戰斗中讓他不能理解的是英國的毫無戰斗力的軍隊,他對負責指揮的英國軍官的無能感到很震驚。當惠奇·勃朗寧的參謀告訴坦普爾戰爭將在幾周后結束的時候,坦普爾對英國軍隊的表現很失望,認為和平的實現仍很遙遠:“……無論什么時候看到破衣爛衫的軍隊的時候,在自己的內心里斗爭之后,他天生的實用主義思想建議他不要抱太大的希望。”[31]作為一個旁觀者,坦普爾譴責了英國軍隊的愚蠢和無能,同時也諷刺了英國軍官的官僚作風。
當坦普爾來到英屬殖民地肯尼亞首都內羅畢時,對于英國殖民者的殖民化管理,非常地反感和憤怒,他認為內羅畢是被踐踏的和混亂的空間,城市里到處彌散著英國元素:模仿英國都鐸式的政府大樓,賽馬俱樂部、高爾夫球俱樂部等各種滿足英國殖民者的享樂場所,英帝國軍隊與在非洲的德國殖民者參戰,只不過是為了爭奪非洲殖民地而已,從而滿足英國統治者的更大利益。坦普爾對在內羅畢的英國殖民者異常反感,所以他說“在發球座上的戴草帽、穿長白色裙子的女高爾夫球手正在被黑壓壓的成千上萬的嗡嗡的蒼蠅推向了荒野。”[32]這里的女高爾夫球手象征著腐敗的英國殖民者,坦普爾這句話好像意味著英國殖民主義的死亡,也是他向英國殖民者發出的抗議聲音。雖然在當時坦普爾的抗議只是“曠野中的呼喊”,但在小說中作為他者的坦普爾向英殖民當局發出了抗議的聲音。
博伊德選擇書寫一戰中被遺忘的角落——英德在東非戰場的故事,是為了諷刺戰爭的殘酷與無意義,其目的是反映1914年至1918年發生在歐洲的英德之間的戰爭殘酷、荒誕和無意義。在小說開始的摘錄就揭示了作者對戰爭的批判:“當歐洲各國互相攻擊的時候,我們悄悄地獲取了屬于共同敵人的殖民地,不覺莞爾。”[33]在小說中,作者描寫了士兵在非洲戰場上乏味、無聊,并且乏味達到了無法忍受的程度。蓋布里埃爾·科布這樣說最初在非洲大陸的軍隊動員:“他看見到處來回行走的小分遣隊,這樣其他的人能安心下來盡量舒服的過夜。這有許多交接時高喊的命令,有些地方有人有力地吹著口哨。這看起來不像一個入侵的軍隊,這里完全沒有危險意識。”[34]英國士兵對戰爭很麻痹,正因為如此小說中的每個人都是被迫卷入戰爭,這一點也譴責了戰爭的無目的性與無意義。當菲利克斯看到哥哥尸首兩地、被禿鷲殘忍地啄食后的尸體時,他不理解“是什么讓人們做這樣殘忍的事情”[35],“我不知道”。坦普爾堅定地說“這根本沒有任何意義。”[36]坦普爾的話概括了博伊德的反戰思想,諷刺了戰爭的無意義。除此之外,小說中還有兩個方面強調了戰爭的無意義,在非洲惡劣的環境中,小說中炎熱的天氣和蒼蠅的描寫諷刺了戰爭是不合時宜的。蒼蠅在戰場當中不斷出現,蒼蠅的單調的飛行與士兵們所承受的乏味和他們被迫承擔的無價值的使命是相似的。
四、結語:承認差異的他者聲音,書寫豐富、多元的歷史
后現代思維積極維護事物的多元性、豐富性,堅決反對使異己的事物屈服于主體意志的統一性。后現代主義歷史書寫承認并重視歷史中的不確定、非連續、無序、斷裂和突變等現象,強調開放性和多元性,承認、容忍存在差異的他者。歷史不再是線性發展的、連續的,而是通過歷史斷裂處的碎片尋找歷史的真實。這樣看來,歷史不再是矢量的時間延伸,而是一個無窮的中斷、交置、逆轉和重新命名的斷片。透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宏大歷史的斷裂處,結合《一場冰激凌戰爭》這部小說文本,把握邊緣話語的聲音,揭露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精神影響下的保守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壓抑,讓他者言說歷史,重新闡釋一戰歷史的殘酷性和無意義性。博伊德運用了文學對歷史的闡釋和在歷史中闡釋文學的策略,利用文學與歷史的互動關系,讓文學主動地反映歷史事實,通過對《一場冰激凌戰爭》小說文本化的歷史的闡釋,參與歷史意義的創造的過程,甚至參與對政治話語、權力運作和等級秩序的重新審視。也就是蒙特洛斯所說的文學與歷史相互依存、互相交錯的“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的特點。后現代歷史的書寫就是一部顛覆宏大歷史意識、宏大歷史敘事,否定目的論、理性啟蒙,瓦解主體、統一性、元話語的歷史書寫,是承認差異、尊重他者聲音,重寫更多元、更豐富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