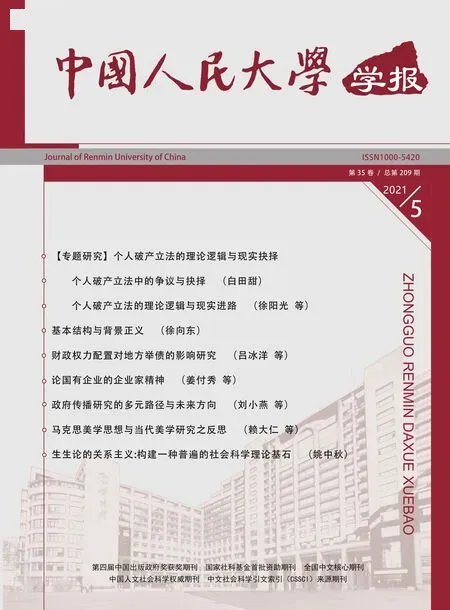正義的穩定性與市場社會主義①
——以《正義論》為中心的考察
林育川
眾所周知,羅爾斯《正義論》中的差別原則以其平等主義的傾向而備受關注。然而,《正義論》的理論影響似乎并沒有進入社會現實的層面,20世紀后半葉西方發達國家居民的貧富差距仍在急劇擴大。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已經充分地向我們揭示了這一點。當然,理論與現實的脫節有可能是由于理論本身并沒有明確的實踐指向,但羅爾斯并非不關心現實的思想家,他不僅關注能夠實現其正義原則的背景制度,還專門討論了正義社會的穩定性問題,即這種理論如何能夠被公眾接受并轉變成行動的可能性問題,這表明該問題——正義理論如何為人們所接收并付諸實踐或曰正義的穩定性問題——是一個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真問題。我們的分析從羅爾斯對正義穩定性的論證開始。
一、正義穩定性的理論前提——正義感的來源
在論證正義社會(良序社會)的穩定性時,羅爾斯關注的是該社會的成員是否持有一種依照正義原則的要求而行動的強烈的和通常有效的欲望,也就是說,他認為穩定性取決于正義觀念是否在社會成員中間產生正義感。(1)羅爾斯:《正義論》,359、11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他斷言:“當制度(按照這個觀念的規定)是正義的時候,參與這些社會安排的人們就獲得一種相應的正義感和欲望以盡他們自己的努力去維護這種制度。”(2)羅爾斯:《正義論》,359、11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當然,這一提法首先要求一種正義的社會制度能夠為人們所選擇,后者又要求原初狀態中的人們具有一種樹立正義感的能力。這里似乎存在著循環論證。它表明,正義的穩定性不僅涉及人們為何能夠堅持依照正義感而行動的問題,而且涉及一個更加基礎的問題,即正義感的來源問題。
在羅爾斯所預設的原初狀態中,人們具有一種正義感的能力,這種能力有助于他們選擇正義原則并承諾遵守之。在無知之幕的背后,人們之間的相互冷淡最終實現了和慈善一樣的結果,也就是說,人們不用真的訴諸慈善或者對相互利益的關心就可以產生我們想要的原則。(3)然而,為什么無知之幕以及人們相互冷淡的機制就足以產生類似于慈善的結果呢?羅爾斯并沒有提供有力的論證。在羅爾斯關于原初狀態的描述中,我們了解到,他假定人們相互冷淡的目的是為了排除那種為了他人或者公共利益而犧牲自身利益的情況,這實際上突出了各方的自愛或者自我保護(即人們對自身利益的保護),無知之幕的預設則是通過屏蔽不同個體的背景信息,排除了人們在選擇正義原則時陷入利己主義(即過分重視自身的利益)。這兩種機制相結合的直接后果似乎只是維持了各方適度的自愛,但并不能從中合理地推出對于他人的愛或者類似慈善的內涵或者結果,即從適度自愛并不能合理地推出對他人的愛以及建立在后者基礎上的正義感。
羅爾斯所闡釋的自然義務似乎也可以用來論證人們的正義感來源以及對正義制度的支持。他所列舉的自然義務包括以下幾種情況:“當別人在需要或危險時幫助他的義務(假定幫助者能夠這樣做而不必冒太大的危險或自我犧牲);不損害或傷害另一個人的義務;不施以不必要的痛苦的義務。”(4)按照羅爾斯的理解,自然義務不僅不要求當事人的自愿,而且可以適用于任何制度,因此它能夠被原初狀態中的各方所接受,是一種被視為“絕對有效”的原則。“這一義務要求我們支持和服從那些存在并應用于我們的正義制度。它也促使我們推動還未建立的正義安排的產生,至少在無須我們付出很大代價的情況下。這樣,如果社會的基本結構是正義的,或者相對于它的環境可以合理地看作是正義的,每個人就都有一種在這一現存的結構中履行自己應盡的自然義務。”(5)羅爾斯:《正義論》,88、88、38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在筆者看來,盡管人們不會拒斥這種自然義務,但這種自然義務的力量仍然太弱。就羅爾斯所描述的幫助他人的自然義務來看,其特征是我們無須付出多大的代價就能夠做到,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在野外開車時捎上迷路的人,或者將自己極少量的財物贈送給窮人。這種自然義務弱得難以被理解為通常意義上的義務(與權利相對應的意義上的義務),我們也難以相信它真的能夠推動正義制度的建立。在政治哲學史上,這種“自然義務”其實接近于個人對其同類的憐憫之心,這種情感通常被視為人性的一部分,比如:盧梭就將人對于他人的憐憫之情視為人的基本情感之一;休謨也認為我們的人性原則中蘊含著認同他人的利益或關切的心理傾向,如果我們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或關切不相互沖突的話;它也可以被視為孟子所言的“惻隱之心”。然而,從人性的角度來看,人們關心和幫助他人的那種情感(正義感)遠不如人的自愛的情感來得自然和強烈。
因此,羅爾斯對于原初狀態中人的正義感來源的闡釋并不能令人信服。從根本上說,羅爾斯似乎是把正義感的來源歸結為人擁有善的觀念能力和理性慎思的能力,也就是說,只要預設人們在原初狀態中具有這些能力就能產生正義感。而在人們選擇了正義原則之后,日常生活中的人就能夠在正義的兩個原則以及正義的職責和自然義務原則的要求下考慮別人的權利和要求,從而使正義規則獲得穩定的支持。但是,這一論證思路之成立是有條件的,即:只有當人們不再優先考慮自己的利益時,才能合理地推斷出利他的正義感是客觀存在的。由原初狀態“規制”的契約各方也許能夠達到產生正義感的條件,但遠非“必然地”使人們產生正義感。
在人們如何獲得正義感的問題上,羅爾斯還從道德心理學的角度提供了更為細致的論證,但其論證仍然困難重重。在《正義論》的“目的”部分,羅爾斯區分了個人道德發展的三個階段:權威的道德階段、社團的道德階段和道德原則階段。與這三個階段對應的有三個法則。第一個法則假定家庭制度通過關心孩子表現出對孩子的愛,一旦孩子認識到這種愛他就會愛他們的父母。(6)羅爾斯:《正義論》,388、36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二個法則假定一個人通過第一法則發展出了友愛的能力,如果在其社會安排被認為是公正的社會里,人們帶著顯明的意圖履行其義務和職責并實踐他們的職位的理想,那么這個人就會在社團(生活)中發展同他人的友愛的情感和信任。第三個法則假定個人通過前兩個法則進一步發展其友愛的能力,在制度被認為是公正的社會里,個人認識到他和他所關心的那些人都是這些社會安排的受益者,這個人就會獲得相應的正義感。羅爾斯描述的這一道德發展進程是很清晰的:從家庭中對成員之愛,到社團中對他人的友好情感和信任,再到社會中產生的正義感。
同樣的,羅爾斯的論證似乎也只是揭示了人們的道德發展的可能性,即:人們在家庭、社團和社會生活中可能會產生出相應的道德感,而不是必然能夠產生出相應的道德感。羅爾斯的道德心理學論證的困難在于:第一,在后兩個法則中,羅爾斯明顯預設了社會制度安排的正義性,即正義的制度背景,但是,正義的制度背景何以能先在于人們正義感而形成呢?(7)前文已經指出羅爾斯對原初狀態中各方的正義感來源的闡釋并不能讓人信服。在此處我們再次見證羅爾斯陷入了循環論證。他在《正義論》中談到,他一直假定“關于世界的一般事實,包括基本的心理學原則,是原初狀態的人們了解的,并且,他們是在這個基礎上作出決定的”。(參見羅爾斯:《正義論》,36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這說明原初狀態中各方的正義感來自基本的道德心理學原則(事實),但他在具體分析人們的道德心理學的形成時又假定了正義的基本社會制度是前提性的。這是明顯的循環論證。第二,即便在正義的制度背景中,人們也未必就能順理成章地發展出正義感,“搭便車”現象就能充分反映出人們缺乏正義感。因此,在慈繼偉看來,“正義感是他律而非自律的道德情感”(8)。當然,這種他律既可以是一種以等利害交換作為條件的約束,也可以表現為法律的約束。“法律的強制手段迫使人們遵守正義規范,不論他們是否情愿。久而久之,一個道德有序的社會就可能逐漸形成,在該社會中,人們普遍遵守正義規范,從而為別人遵守正義規范提供了相應的社會和心理條件。這樣一來,社會一般成員就不會因為正義規范得不到普遍遵守而自己也不愿繼續遵守正義規范。”(9)慈繼偉:《正義的兩面》,17、28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第三,由于羅爾斯對三個法則的道德情感的論證背后有著一個明晰的由親及疏的推理邏輯,因此三個法則的論證并不具有同等的說服力。如果根據說服力的高低來排序的話,家庭階段對愛的情感的論證明顯高于社團階段對友情和信任的論證,后者又明顯高于社會階段對正義感的論證,因為隨著個人關系的疏遠,道德情感的形成所必須克服的阻礙就越多。換句話來說,羅爾斯所推導出來的三個法則一個比一個弱,特別是第三個法則,即處于社會中的人們的正義感的形成很可能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
對羅爾斯所闡釋的正義感來源的進一步追問,使我們想起羅爾斯曾經簡單處理過的問題,即如何對待情感形成的兩種傳統。羅爾斯認為,第一種傳統是經驗主義傳統,其主要形式之一是社會學習理論。它認為道德訓練的目標是提供道德行動的動機。這大概是一種外在論。第二種傳統是理性主義的傳統,主張道德學習不是為了提供動機,而是人們內在的理性和情感能力按其自然傾向的自由發展。這大概是一種內在論。(10)羅爾斯:《正義論》,388、36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那么,正義感的形成究竟是訴諸外在的道德訓練(道德教育)還是訴諸內在道德性的自我萌發呢?羅爾斯拒絕在這個問題上選擇站隊,而是主張把這兩種傳統各自的合理性綜合起來。從他對于道德發展階段的相關描述來看,似乎更明顯地服膺于內在論的傳統,但對于道德教育的某種程度的忽略顯然不利于他對正義感來源的證成。因此,我們可以說,羅爾斯對于原初狀態中人們正義感來源論證的不足、對于人們道德發展進程中個體動機復雜性的低估、對道德教育的忽略(11)羅爾斯在《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中談到了正義的社會基本結構具有教育公民的公共功能,但他強調的是“這種功能使公民擁有一種自由和平等的自我觀念”(參見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91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并沒有論及通過教育來培育或者塑造公民的正義觀,所以,在教育的功能問題上,羅爾斯的觀點是保守的。,都危及他對于人們具有正義感的證成,進而危及他對于正義穩定性的論證。
二、正義穩定性論證的困難:從社會基本結構到社會風尚
上文已經揭示了羅爾斯對正義感來源的論證存在的不足。但是,即便我們接受羅爾斯關于正義感來源的預設,我們仍然面臨著在無知之幕揭開之后人們是否和如何保持其正義感的問題,即正義穩定性問題。羅爾斯認為,如果能將原初狀態中選擇的兩個正義原則運用于社會的基本結構——包括社會基本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就可以使社會成員保持足夠強大的正義感。“在他們生活于正義的基本結構中所形成的性格和旨趣是既定的情況下,公民的正義感是如此強大,足以抵制通常的不正義傾向。公民能夠自愿地永遠以正義方式相互對待。這樣,穩定性是由某種適當的動機來保證的。而這種動機則是在正義的制度下獲得的。”(12)
然而,正義的社會基本制度究竟是如何塑造個人依照正義原則行動的動機呢?羅爾斯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指出,在一個其制度被認為是正義的社會里,個人認識到他自己和他所關心的人都從正義的社會安排中獲益,他們就能獲得依照正義原則行動的動機。羅爾斯的這一判斷預設了一些未經論證的前提條件:個人必須意識到別人也會符合正義地行動(自己依正義原則行動才不會吃虧),同時個人也必須有足夠堅強的意志抵御不依正義原則行動可能帶來的更多的收益。羅爾斯顯然低估了獲得這些條件的難度,所以樂觀地認為正義的社會基本制度能夠塑造出依照正義行動的個人。他明確指出,正義原則只應用于社會基本結構本身,而不直接應用于社會內部的機構和團體。但它能夠通過間接的方式對社會內部的公司、工會、教會、大學和家庭產生約束,也能對上述社團或家庭的成員的行為產生某種限制。(13)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305、18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羅爾斯并沒有對這種間接的影響形式做出系統的分析,他將其稱為局部正義問題。在羅爾斯看來,局部正義不同于作為公平的正義,即適用于基本社會結構的兩個正義原則,個人不必嚴格遵循正義的兩個原則,而只遵循自愿和公平的原則去行動。
柯亨不認同羅爾斯的上述分析,提出了反對羅爾斯的“基本結構異議”。他認為僅僅要求社會基本結構遵循正義原則是不夠的,正義的社會基本結構并不能自動地(或者間接地)在社會成員中產生正義感,使其自覺地依正義原則行動。柯亨的批評重點指向了羅爾斯兩個正義原則中的差別原則。在柯亨看來,羅爾斯的差別原則存在著內在矛盾。它表現為:一方面,羅爾斯認為差別原則要求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只有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利益的情況才能夠得到辯護。因此,當差別原則得到滿足時,社會就能夠產生出博愛,這種博愛使才能突出者不愿意獲得更大的利益,除非它有利于處境最不利者的利益。羅爾斯以家庭為例來證明上述的觀點:“家庭在其理想觀念中(也常常在實踐中)是一個拒絕最大限度地增加利益總額之原則的地方。一個家庭成員通常只希望在能促進家庭其他人的利益時獲利。”(14)羅爾斯:《正義論》,80-8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但另一方面,羅爾斯的差別原則又承認激勵的合理性,即有才能的人只有在獲得比普通工資更高的報酬時,才會更努力地工作。在根本上差別原則的精神是兼愛和平等,但有才能者的這種態度,即只有在獲得更高報酬預期時才努力工作,則明顯有悖于這種精神。因此,如果才能突出的精英真的認同差別原則,就不能合理地主張高工資是他們努力工作的理由。既然反映了差別原則的社會基本結構既激發了平等或兼愛精神,又為個人追逐私利保留了空間,通過正義的社會基本制度來塑造社會成員的正義感或者兼愛精神就顯得不現實。
另外,從羅爾斯所認同的財產所有的民主制度或自由社會主義制度——他認為二者均可能契合于他的正義原則——來看,正義的穩定性也難以得到實現。羅爾斯最認同的是財產所有的民主制度。這種制度的優點在于其能夠盡量將生產資料廣泛地分配給不同的個人,因而它優于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福利資本主義制度。因為放任資本主義制度將其目標設定為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僅以一種相當低的社會最低保障來制約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而福利國家則允許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所有權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從而導致少數人控制國家經濟和政治生活。羅爾斯也對自由社會主義持開放態度,他表示自己反對的是以指令性經濟為特征的國家社會主義,因為后者有可能危及平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而自由社會主義制度優于國家社會主義之處在于其中的“企業在一種有效的自由競爭的市場體系內部開展它們的活動,職業的自由選擇也得到了保證”(15)羅爾斯:《正義論》,228-230、81、214-21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從其闡釋來看,羅爾斯所認同的能夠契合于其正義論的社會背景制度有兩個重要特征:第一,對私有財產的適當限制。“財產所有的民主之背景制度力圖分散財富和資本的所有權,這樣來防止社會的一小部分人控制整個經濟,并從而間接地控制政治生活”(16)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231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這一制度是在個人參與經濟活動之初就使生產性資產和人力資本(通過教育資源的保障)分布得更為廣泛。當然,自由的社會主義制度則采取了更為激進的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的形式。第二,保障個人在社會內部選擇的充分自由。一方面,羅爾斯肯定了個人在遵從基本制度基礎上有自主選擇其行動——即便是追逐私利——的自由。“在由基本結構所建立的背景正義的框架內部,在制度之規則容許的范圍內,個人和團體可以做他們所希望的任何事情。”(17)羅爾斯:《正義論》,228-230、81、214-21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另一方面,羅爾斯強調利用市場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及引入市場來保障平等自由體系。羅爾斯不僅認為從管理的角度看所有政權都不得不運用市場來分配實際生產的消費品,而且指出了市場體系和平等的自由以及機會的公正平等相協調。(18)羅爾斯:《正義論》,228-230、81、214-21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然而,上述的兩個特征之間的確存在著內在的緊張,即在限制私有財產和確保市場機制下個人的選擇自由之間的沖突。生產資料的廣泛和較為平等的初始分配與個人經濟活動的自由選擇(特別是追逐私利的選擇)的結合并不能有效阻止不平等的擴大,后者易于摧毀社會成員心中非常稀薄的那種涵蓋兼愛精神的正義感。
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柯亨認為培育正義風尚對于正義社會的構建是不可或缺的。他指出:“一個按照差別原則是正義的社會,不單單需要正義的強制性規則,而且需要一種貫穿在個人選擇中的正義的社會風尚。缺乏這樣一種社會風尚,那些對提高最差者的境況來說不必要的不平等就會出現。”(19)然而,如果社會的基本制度本身不能催生出強有力的傾向于平等的社會風尚,柯亨所要求的社會風尚又能來自何方呢?柯亨在《為什么不要社會主義》一書中試圖通過一個熟人之間的野營旅行的案例來描述這種社會風尚,然而,他同樣沒有解決如何將一個小的共同體的博愛或者平等風尚擴展到一個更大的社會之中的問題。柯亨最終還是繞回到人性主題,并感慨即使人們認識到自己身上存在著自私和慷慨兩種品質,卻不知道如何使慷慨的品質發揮作用。(20)呂增奎:《馬克思與諾齊克之間——G.A.柯亨文選》,245、272頁,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應該說,柯亨對于羅爾斯的批評是準確的,即后者的差別原則和背景制度中隱藏著阻礙人們產生正義感的因素,良序社會中的基本社會結構并不必然會促進人的正義感,因而需要一種能夠反映到個人的選擇(包括正確地選擇正義的制度和符合正義地行動)中的社會風尚。但是,柯亨至此也只是揭示了問題,他同樣沒能提出保障正義穩定性的有效路徑。
三、市場機制對正義穩定性的挑戰
在柯亨對羅爾斯的批評中,我們看到了他對于市場機制易于激發個人的貪婪和逐利本性的擔憂。柯亨的這一擔憂也反映了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共識。客觀地說,羅爾斯并非沒有認識到市場機制的弊端,也并非不了解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的批評。羅爾斯與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的批評者之間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認真地對待市場機制的盲目性和逐利性。那么,羅爾斯是怎樣理解市場機制與正義穩定性之間的關系的呢?
羅爾斯明確地把市場機制視為其理想的背景制度的內在要求。“我所概述的理想體系在相當程度上利用了市場機制。我相信,只有采用這種方法,分配的問題才能作為純粹程序正義的一個例證被解決。再者,我們也獲得效率的益處,保護了重要的選擇職業的自由。從一開始,我就假設理想體系的制度是一種民主的財產所有制,因為這種情況可能較為人所熟知。”(21)這一段話的內涵很豐富,羅爾斯至少揭示了市場機制的三個優點:第一,市場機制的引入使分配問題成為一個純粹程序正義的問題,即只要社會的基本結構是正義的,個人依據市場機制做出的所有選擇都應被認為是正義的,即便它可能是不夠平等的。第二,市場機制帶來了效益。第三,市場機制保護職業選擇的自由。羅爾斯所分析的市場機制的這些優點不難得到認同,他所認為的市場機制契合于正義原則也可以得到理解,特別是當我們考慮的重點是正義的第一個原則——最廣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則——的時候。
不過,市場機制也存在同樣突出的負面因素,比如很多社會主義者批評市場機制催生了個人逐利性。這些負面因素不會有損于人的正義感的形成嗎?實際上,關于市場之惡的討論在近代西方早已成為一個焦點問題。羅爾斯并沒有回避市場機制的這個缺陷,他承認社會主義者擔心市場機制有一種內在的退化性質,也理解社會主義者想建立一種經濟制度,使人們在其中的主要動機表現為對社會的關心或者對其他利他目的的追求。不過,他并沒有完全接受社會主義者的判斷。首先,他認為市場機制中的人并不必然是自私的。“自由市場的使用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沒有本質的聯系”,自由市場因而并不必然直接服務于私有財產的增值。其次,盡管市場機制并不是理想的安排,但它并不是最壞的情形,因為“在某種必要的背景制度下,那些所謂的工資奴隸制的最壞情形肯定會被排除”(22)。再次,社會主義者要求人們具有一種主要是利他的動機,實際上是要求一個超越正義的社會。這對于仍然處于正義環境中的社會來說是過高的要求,所以羅爾斯說他的正義論對社會的和利他的動機的力量做了一種明確的限制。最后,羅爾斯認為從比較的視角來看,社會主義的計劃并不比市場機制更正義,“那種必然要在一個社會調節的體系中(無論是集中地指導的,還是由工業聯合體達成的協議來指導的)發展起來的官僚控制的經濟活動,總的來說竟比由(假定始終是那種必要的結構的)價格手段實施的控制更為正義”(23)羅爾斯:《正義論》,216、221、22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并不成立。概言之,羅爾斯認為:市場機制并不會帶來馬克思和其他社會主義者所批評的那種嚴重的剝削和極端的不平等;理想的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超越正義的,但它并不具有現實性;從經驗層面看,市場機制在提高效率和保障自由兩個方面都優于計劃機制,而不是反過來。
可見,即便羅爾斯承認市場機制并不理想,它可能會與正義的第二個原則(即差別原則)沖突,但這種沖突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會出現極端和最壞的情況(即嚴重的剝削情形)。然而,羅爾斯這一觀點,即“所謂的工資奴隸制的最壞情形肯定會被排除”,是基于某種理想化的理論所得出的判斷還是基于社會經驗得出的判斷呢?在筆者看來,顯然是前者。由于在現實中存在大量的來自經驗層面的反例,因此,羅爾斯所描述的市場機制并不是現實的市場機制,更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種處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進程中的現實的典型形態,而是一種得到修正的理想模型。就像羅爾斯所說的,他設想的這種市場機制已經受到了正義的社會基本制度的規范。(24)羅爾斯關于市場機制能為正義原則所約束的觀點已經遭到了質疑,比如有學者認為羅爾斯忽略了市場主體(尤其是某些特定治理結構的企業)基于其逐利本性對各種市場缺陷的利用,“為了在市場謀生存,有些企業只是遵守法律的條文,而不遵守法律的精神”。Wayne Norman.“Rawls on Market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2015,25 (1):39-40。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羅爾斯的確認為如果社會的基本制度符合正義,那么生活于其中的公民也會按照正義的要求去利用市場機制。然而,這種解釋仍然存在難以克服的困難:第一,這一整套和諧的理論是建立在正義的社會基本結構已經確立的前提下,而這個前提顯然不是實際存在的。第二,即便在某個歷史節點人們創立了正義的社會基本結構,這種基本結構是否足以有效地抑制市場機制的逐利性仍然很不樂觀。
對于第一個困難,即現實的正義社會是如何生成的,或者說如何從現實的社會進入到一個正義的社會(良序社會),羅爾斯并沒有提供足夠的論證。(25)艾倫·布坎南指出,羅爾斯不僅沒能提供一種道德教育理論,也沒能提供一個關于社會—經濟的轉換如何產生出來的理論,或者是使必要的動機轉變為可能的理論。參見艾倫·布坎南:《馬克思與正義》,18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對于第二個困難,羅爾斯曾樂觀地認為他所主張的財產所有的民主制度既可以利用市場機制,也足以規范它。然而,他顯然低估了市場機制的逐利本性對正義穩定性構成的挑戰。有趣的是,反對市場的柯亨,在強調正義風尚的重要性時也低估了市場機制的這一缺陷。柯亨舉例說,在1945年到1951年間,英國的很多企業被國有化,但仍然保持市場經濟,國有化企業和市場經濟的結合并沒有給英國帶來過大的工資差別(與美國相比),因為英國流行一種重視公共事業的風尚,這種風尚可以抑制個人對私利的追逐(使英國的經理不像美國的經理那么貪婪)。(26)呂增奎:《馬克思與諾齊克之間——G.A.柯亨文選》,255-256頁,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就這一具體案例來說,柯亨的分析可能是對的,但這種“風尚”能否發揮作用也跟個人追逐私利的便利程度以及私利誘惑的大小有關。在筆者看來,就我們當下的經驗(在人才和資本全球流通的語境中)而言,如果不提高優秀的英國經理的薪酬,他們將會被吸引到收入更高的地區(比如美國),這種情況又會回過頭來引發英國本地勞動者工資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因此,如果在世界范圍內盛行的是那種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貪婪的市場精神,那么人們基于憐憫心或者利他心理所產生的、通過正義的社會基本結構所培育出來的那種稀薄的正義感(或者柯亨所宣揚的正義風尚)將會被毫不留情地消解掉,正義的穩定性也將不復存在。我們必須更為認真地對待市場機制帶來的沖擊。
四、市場社會主義作為可能的解決方案
既然崇尚競爭和逐利的市場機制對以兼愛或者利他精神為內在要求的正義穩定性構成嚴重的挑戰,那么,二者之間是否還存在兼容或者和解的可能路徑呢?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放在一個更宏大的思想史背景里,即將其置入個人利益和共同體利益這一對矛盾關系中來考量的話,也許會得到一些啟示。在政治哲學史上,這是一個很傳統的問題。霍布斯通過強調利維坦的絕對權威來維持政治共同體的穩定,但未能使人們發自內心地關注共同利益,一旦政治強力喪失,人們就不會尊重共同利益;洛克認為人們除了關心自己的利益外還關心親友(父母、孩子、配偶、親戚和朋友)的利益,但這也意味著允許個人漠視甚至侵犯他人(親友之外)的利益,從而無法避免“搭便車”現象,也無法維持政治共同體的穩定性。這一對關系在盧梭和黑格爾那里得到了更為細致的處理。在盧梭那里,這一對關系實際上被轉換成個人意志和普遍意志(即公意)的關系。他認為公意(對于共同利益的意思表達)必然源于共同的個人利益,至于如何從維護個人利益的現實的個人意志達至公意,他不得不引入立法者的概念,提出通過創制法律來實現對人性的改造,從而推動公意的達成。因此,在盧梭那里,教育是一個實現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兼容的必不可少的路徑。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也指出:市民社會兼具特殊性和普遍性兩個原則,作為市民社會中的私人同樣具有普遍性。使個人的特殊性通達普遍性的理由就是個人在其需要的滿足中離不開他人的協作,因此個人得接受對他人的利益的尊重,接受公共性。“作為這種國家的市民來說,個體是私人,他們把本身的利益作為自己的目的。由于這個目的是以普遍東西為中介,對他們而言普遍物是作為手段出現的,所以,如果他們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只能按普遍的方式來規定他們的知識、意志和活動,并使自己成為這種聯系鏈條中的一個環節。”(27)黑格爾:《黑格爾著作集》,第7卷,3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不過,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個人參與的需要的體系中,市民們仍然主要是受私人動機推動而不是道德或者超越自我的理性所推動的。(28)Carsten Fogh Nielsen, and Emily Hartz.“Why Be Just? The Problem of Motivation in Hegel and Rawls”.Ratio Juris,2018,31 (3):335.因此,在黑格爾那里,最終還是訴諸作為普遍性的國家精神來實現對個體的塑造。可以說,對近代政治哲學史的簡要回顧使我們得以更積極地評價道德(規則)教育在實現個人私利向普遍利益過渡中的作用。
反觀羅爾斯,我們發現,盡管他曾經指出良序社會中的人不會反對灌輸正義感的道德教育實踐,但他顯然更相信人的道德感(正義感)內在于人的理性。如前所述,羅爾斯區分了對道德學習的兩種理解:一種認為道德學習的目的是為人們提供(本來缺失的)道德動機,另一種則認為道德學習并非提供缺失的道德動機,而是人們內在理性和情感能力按照它們的自然傾向的一種自由發展。后一種理解“把道德情感看作對我們的社會本性的充分評價的自然結果”(29)羅爾斯:《正義論》,36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如果我們聯系羅爾斯強調正義原則只需運用于社會基本制度的主張,就能明白他的確樂觀地認為正義的社會基本制度能夠“自然地”塑造出人們的正義感。也就是說,對于羅爾斯而言,人們的正義感的形成主要源于制度的塑造,而不是對外在道德規則的學習和遵從。在這個問題上,柯亨強調個人正義風尚的塑造之重要性顯然是對的,這是對羅爾斯不太重視外在性的個人道德教育——尤其是有助于個人形成共同體意識的教育——的一種糾偏。
客觀地說,在道德教育方面的重視不足,使羅爾斯的方案忽視了利用外在的道德規則對市場機制所激發的逐利心理的抑制。除此之外,由于羅爾斯本人對市場機制的理解在本質上仍然是理想主義的,這使得他所設想的市場機制同樣缺乏反制個人逐利性的考量。羅爾斯對市場機制的過度樂觀,客觀上與其對于財產所有的民主制下的市場機制能更契合于正義的兩個原則的判斷有關。因此,羅爾斯的方案要求矯正財富等社會益品的不平等分配,甚至要求矯正生產資料分配的不平等,但并沒有要求抑制個人利用市場的過度逐利行為。在他的方案中,一個利用市場制造和擴大不平等的機制和一個運用社會政策矯正不平等的機制同時被當作二元對立的雙方固定下來。至于這兩種對立的機制如何在一個社會中具體呈現出來(即制度化),羅爾斯認為應該依據“傳統、制度、社會力量和特殊的歷史環境”來確定。這意味著這兩種機制都有最終勝出的可能:有可能是抑制不平等的機制占了上風,也有可能是建立在財產私有基礎上的逐利的市場機制更具優勢。羅爾斯本人對前一種可能性較為樂觀,而布坎南則更擔憂后一種可能性:“假若總的不平等(包括基于財富的繼承)作為更大的生產力的刺激是必要的,是傳統的一部分,那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相對于我們社會的傳統、制度和社會力量,就什么是可行的‘政治判斷’而論,將傾向于以正義的名義把當下的不平等合法化。”(30)艾倫·布坎南:《馬克思與正義》,16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羅爾斯坦言這是一個他無法解決的、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的詰難。(31)羅爾斯承認:“馬克思可能會說,即使接受財產所有的民主的理想,但這樣一種政體所產生的政治經濟力量也會使它完全背離它的理想制度描述。”參見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291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不過,羅爾斯依然選擇相信財產所有的民主制度在實踐中能更好地滿足他的兩個正義原則,他甚至提出“應該現實對現實”地來比較自由社會主義與財產所有的民主這兩種背景制度。由于這兩種制度并沒有現實地存在過,自然無從比較。但無論如何,財產所有的民主本應從理論的層面回應馬克思主義者的詰難。瓦希德·侯賽因(Waheed Hussain)就曾經給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回應。他認為,實際上存在著兩種類型的財產所有的民主,一種是與自由市場結合的,一種是民主社團的。真正與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契合的是民主社團的類型,而不是自由市場的類型。(32)Waheed Hussain.“Nurturing the Sense of Justice:The Rawlsian Argument for Democratic Corporatism”.In Martin O’Neill and Thad Williamson(ed.).Property-Owning Democracy:Rawls and Beyond.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2,p.184.侯賽因的闡釋實際上為羅爾斯的方案補充了社團主義的因素,以矯正自由市場所激發的逐利性。
以上的分析充分表明,單純的市場機制不會帶來道德和正義的風尚,我們必須對市場機制予以必要的約束。正如布坎南所言:“馬克思對市場所作的第二個同樣重要的指責是:任何依賴于競爭而不是直接合作的動機、依賴于不僅使利益沖突合法化而且還鼓勵這種沖突的動機的體系,包括市場體系,都不可能是社會合作的最有效率的或最人道的形式。”(33)艾倫·布坎南:《倫理學、效率與市場》,15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然而,如何才能利用社會主義的因素來抑制市場所激發的逐利性和沖突本性,馬克思本人根本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更談不上提供明確的答案。我們需要在當代的歷史條件下思考市場和社會主義結合的難題,這是羅爾斯和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共同面對的難題。
在筆者看來,在我們基于經濟效益的考慮而無法放棄市場機制的時代條件下,市場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次優的選擇有其合理性。但是,市場與社會主義的結合不應該停留在表層的結合或者只是話語的關聯層面,更不應片面地強調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是發展自由市場經濟,而應該重視社會主義因素對于市場機制的矯正。也許市場社會主義最為重要的價值之一就是用社會主義的因素去約束市場的逐利機制,這也正是波蘭尼早在20世紀40年代所表達的觀點,即社會主義應該在經濟層面反對“使私人獲取金錢動機成為生產活動中的普遍動機”(34)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198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其具體的路徑包括:
第一,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企業管理制度以抑制資本的逐利性。比如,可以通過政府稅收和產業政策實現對于企業的利潤水平的調控和對投資決策的引導,抑制資本的盲目逐利性,這一類政策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實踐中并不少見;也可以通過加強企業員工對于企業的民主管理,對企業利潤的分配以及未來的投資計劃做出有效的管控,防止資本在市場中無限制的增值。施韋卡特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就主張通過倡導工人的自我管理和投資的社會控制來抑制資本的自我增值。這種模式在西班牙的“蒙特拉貢”合作社和中國的鄉鎮企業的實踐中都有所體現。
第二,采取更激進的再分配政策抑制結果的過度不平等。一個社會如果能夠抑制過度的財富不平等,就能夠抑制人們對于財富的迷信。分析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不可能容忍過度的社會不平等,他們不僅主張對作為勞動成果的財富的分配平等,而且主張生產資料占有上的相對平等,反對個別資本所有者在生產資料上的壟斷地位。羅默就提出,一旦私人企業達到一定規模時,應該通過贖買將其公有化,“一個企業一旦達到一定的規模,或一旦企業的創辦者去世,它就得實行國有化(予以賠償的),它的那些股份要被重新分配給一般大眾”(35)伯特爾·奧爾曼:《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爭論》,14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這一設想的要害在于消除無限制增值財富(無限度擴大財富不平等)的可能性,從而有利于抑制個人的逐利欲望。從現實層面看,羅默的主張似乎過于激進,但是,如果在社會主義實踐中能夠制定和完善各種遺產稅、房產稅和反壟斷法律法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達到抑制資本自我增值和個人逐利心的效果。
第三,限制金錢(資本權力)對其他社會領域的滲透。在貨幣拜物教盛行的時代,隔斷金錢對其他領域的滲透就意味著祛除金錢無所不能的神秘光輝,這既有助于實現社會正義,也能夠消除人們對于貨幣和資本的崇拜。沃澤爾在談復合平等時所反對的支配性或者壟斷性的善,在商品經濟時代的對應物其實就是金錢。因此,如果社會主義國家在接納市場經濟的同時,能夠劃出某些限制私人資本隨意侵入的領域,比如醫療衛生、教育和其他一些與民生攸關的領域,私人資本的逐利行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會減弱,社會成員的正義感也更易于養成。
以上的這些具體制度設想都致力于抑制市場的盲目性和逐利性,它們也都是羅爾斯的基本社會結構沒有涉及的。在筆者看來,這些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設計至少可以在理論層面為市場機制和正義穩定性之間的和解提供一種可能的路徑。反過來說,缺乏這些更為激進的抑制市場逐利性的細節性制度,羅爾斯所描述的那種蘊含適度利他精神的市場機制將是難以想象的,正義的穩定性也必然是海市蜃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