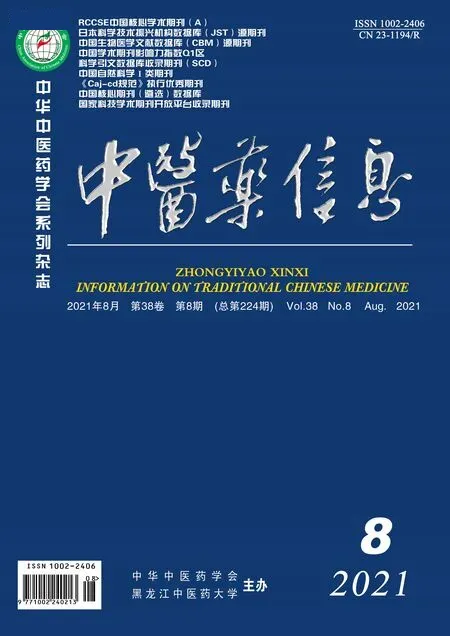王肯堂《醫學窮源集》運氣學診療體系初探
劉明洋,韓海偉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王肯堂為明代中后期著名醫家,臨床經驗豐富且著述等身,輯《證治準繩》、刊《醫統正脈全書》,為融通金元諸家思想以及傳承中醫學術產生了深遠影響。然而在王氏晚年所作《醫學窮源集》中,其醫療風格忽然改變,以運氣學貫穿理、法、方、藥的全新體系,沖破了以往診治疾病“平脈辨證”的固有局面,認為運氣學為“審證之捷法,療病之秘鑰”[1]2。且從書名“醫學窮源”來看,顯然王氏以為運氣學為中醫學之源,鄭重之意可見一斑。然而此書迄今為止研究者極少,故對其運氣學診療體系進行探析、推介,是十分必要的。
1 《醫學窮源集》理論發源脈絡
《黃帝內經·素問》的七篇大論奠定了中醫運氣學的基礎,唐代啟玄子《素問六氣玄珠密語》進一步對五運六氣的理論進行闡釋,強調了運氣理論產生的天文學背景,并詳細論述了六十年中運氣加臨的各種格局[2]。宋代陳無擇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載“天干方”十首、“地支方”六首,為運氣學的方劑應用提供了范式[3]。宋代官方刊布的《圣濟總錄》詳細地收集了六十甲子每一歲的天、泉間氣中運主客等運氣背景,以及所應的氣候、物候、民病、藥食所宜等,推動了運氣學說的普及。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這種“定數”式的推算,容易造成醫家在臨床的機械應用。如《傷寒鈐法》結合命理思想,根據患者出生以及生病時間,機械地建立一套推病定治法,幾乎拋棄了中醫學“因人、因時、因地”的辨證思想,因而產生了不少弊端。
金元四家則撇開繁復的運氣加臨推演不談,另辟蹊徑,從醫理、治法、藥性等方面對運氣學進行了發揮。如劉完素便是運用運氣學“亢害承制”的思想對《素問》“病機十九條”進行了發揮,極大地豐富了中醫學病機學的內容[4]。后世諸家在著述中雖然對運氣學多有闡述,但是至今運氣學在臨床上的應用還多停留在根據干支對發病時間的簡單推算、與運氣理論的初步結合,以及對已有運氣方(主要是“三因方”)的發揮運用。然而王氏的《醫學窮源集》不僅辨證地繼承和發展了運氣學的理論,更以運氣學之理融通貫穿了中醫學生理、病機、藥理、方劑等方面,并且因機應變地施用于臨床。
2 一以貫之的病理、生理、藥理體系
2.1 人體與天地氣化密不可分
運氣學難以在臨床上施用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運氣學體系和當今中醫學體系的脫節。一般來講,五運六氣所探究的對象為天地氣化以及對氣象、物象、人體的作用,當今中醫學體系雖然主張對疾病認識的“三因制宜”,但實際上,在臨床施用時,仍然以“因人”為主,所謂的“辨證論治”未超出此范疇。《素問》云:“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人生養于天地之中,如魚生于水而養于水,故人體的常與病、與天地之氣息息相關。王氏所構建的運氣學體系,始終把人放在天地氣化之中考慮。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氣化不平,人體自身的臟腑虛實、氣血盛衰、七情飲食,以及自然界六淫邪氣的侵襲均可使人體氣化不平而為病。然而人體氣機及自然氣候的變化、六淫邪氣的轉移,均暗自隨天地氣化而變遷,故五運六氣等運氣因素所構成的天地氣化背景,可以說是人與萬物共同的生、化環境,它們是密不可分的。
2.2 運氣學與病理聯絡
中國古代哲學的宇宙論,認為陰陽二氣的相摩相蕩和五行之氣的生成克制,是事物生、變的原因。王氏在《醫學窮源集》中言:“有是理而后有是氣,有是氣而后有是形”。無形的氣不可見,然而通過對陰陽、五行之理的把握,由其所生之物、所顯之象,便可從有形的“象”知悉其背后無形的陰陽、五行之氣,此為“司外揣內”的方法,即《素問·五運行大論》所言:“天地陰陽者……以象之謂也”。
陰陽在氣化的精微層面可分為三陰三陽——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厥陰、少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天、地、人三者本源相同亙古不變,且同受三陰三陽之氣的制約。“經”,有常而不變之意,也有經緯制約之意,故三陰三陽亦稱“六經”。關于六經應象,《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載:“厥陰所至為風生……少陰所至為熱生……太陰所至為濕生……少陽所至為火生……陽明所至為燥生……太陽所至為寒生”。寒、燥、火、濕、風、熱六氣即三陰三陽在自然界呈現出來的氣象。異常的六氣可變為六淫之邪,成為致病因素,三陰三陽之氣也就間接地成為病因學的因素。并且通過人體六經與經絡臟腑的聯絡,天地之氣的異常也可以直接加于人體的臟腑經絡而為病:“厥陰所至為支痛;少陰所至為驚惑、惡寒戰栗、譫妄;太陰所致為稸滿;少陽所至為驚躁、瞀昧、暴病;陽明所至為鼽,尻陰股膝髀?足病;太陽所至為腰痛”。此為三陰三陽系統對病因的統攝。
2.3 運氣學與生理的聯絡
王氏通過對人體臟腑的六經分屬、六經之間相比相配的深入分析以解釋人體的生理狀態。如人體太陽一經包括膀胱足太陽之脈、小腸手太陽之脈的經脈,以及膀胱、小腸的臟腑,還有“膀胱者……毫毛其應”的毛竅。臟腑、經脈、毛竅三者在太陽一經的統攝之下,完成太陽的氣化功能——“太陽寒水”的代謝。王氏在書中太陽的功能及水液布散的渠道總結為:“太陽之氣本于水府(膀胱的氣化功能),外行通體之皮毛(化為汗液),從胸膈而入于中土(精者灑陳于臟腑,濁者化為尿液出于前陰)。”太陽一經蒸化水液、循環周身的作用,王氏有形象的比喻:“太陽起于極陰(最下、最寒)之地,故海水極深之處,而日出焉”。
太陽一經須同時與他經相協才能完成自己的生理功能。太陽與少陰為表里之經,太陽為少陰之使、少陰為太陽之守,氣本相同,故王氏認為“太陽之氣,必藉腎經真水以養之”,太陽才能溫煦氣化。太陽外合皮毛,而肺主皮毛,太陽化汗外出的作用必有肺臟功能的參與才能實現,故“手太陰(肺),實與太陽之氣相合,此金水相涵之義也”。太陽主三陽之開、太陰主三陰之開,“太陽與太陰,則身中乾坤也……身中統攝手足六經之脈,全在于此”,地氣上騰、天氣下降之機在于二經。故王氏從相配的角度分析,認為只有太陰的氣化作用與太陽相配,太陽才能正常的氣化而不病。
2.4 運氣學與藥理的聯絡
中醫對本草的運用,多遵照本草學著作中藥物的主治功效,主治與病證相合,氣味與病情相投便可使用。《醫學窮源集》中王氏用藥卻與此大相徑庭,認為“讀本草有法,勿看其主治”[5]。因為所謂的藥物,是天地五行、六氣自然合化的產物,他們不是為了治病而生的。所以學習本草,應該“驗其味,察其氣,觀其色,考其何時苗,以何時花,以何時實,以何時萎”,因“象”而知“氣”。知悉藥物稟賦之氣的偏頗,便可以以偏救偏,糾正人體氣機的不平而使病證消除。主治功效只不過是先賢對藥物作用結果的部分總結,為末;對藥物由象測氣的分析以知藥理,為本;如果僅執功效治病,是為本末倒置,必然“舉一而廢百”,不能把握藥物功用的全體。
如“惟夏枯草近時專用為肝經藥”,但是其味辛性寒,辛為金所化之味,寒為太陽所化之氣,故“稟金水之氣”,加之夏至陰生而枯萎,故能以陰化陽,使陽氣流通無滯,所以王氏擴充其功用為:“而內消堅積,上清火熱,又能使水氣上行環轉”。再如陽明之氣為“介化”,故鋒芒堅硬之象的藥物皆稟陽明燥金之氣。所以藥物“兼鋒刃之形者,助金氣也”。如蒼耳子既可去濕,又能制約肝氣過亢的原因,就在于“其形之多刺”。“前方用蟹殼,而此方用象皮、猬皮,皆有戟刺之形,陽明之象也。”由此可見,王氏之所以能對藥物靈活運用于臨床,就在于他能把藥理、病理、生理放在天地氣化的統一整體中考慮和把握。這樣,紛繁的病因、病情、藥效就綱目井然,藥物的運用便可因機應變,而不僅僅局限于藥物的主治功效。
3 王氏運氣學臨床應用范式
通過對《醫學窮源集》112個醫案的梳理,可以發現王氏在臨床診治疾病有其大致的范式。首先根據疾病發生時間的運氣節點,推算該時間節點的運氣背景——大運、司天、在泉、主客氣、主客運等因素,并梳理諸運氣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以及隨著時間推移運氣因素的改變和改變之后的運氣因素的相互作用關系。其次,將運氣背景與患者病狀參合分析,以確定患者病情與運氣諸因素的生克、順逆情況,進而掌握患者的病機。最后,綜合病機與運氣因素,確立治法,選擇藥物。如《醫學窮源集》木運年第一個醫案:“鄭姓,廿七,感冒風邪,燥熱無汗。脈象浮數無力,兩尺沉細(注:兩尺不應歲氣也)。此壬子年立秋后五日方也”[1]70。
首先分析該患者看診時間的運氣背景為:大運-太角、客運-太宮、主運-少宮;司天-少陰、在泉-陽明、客氣-太陰、主氣-太陰(運氣背景推算法在運氣學著作中皆有論述,茲處從略)。其次,分析患者的病機與運氣背景情況:患者觸冒風邪之后,見燥熱而汗不出,當為風邪阻滯、毛竅閉阻、邪熱內郁之證,脈象之浮數與證相合,可知風在皮毛為邪實。但脈之無力顯出虛象,燥則津液受傷,單純從患者的角度分析,當為肺虛津傷,不能化汗外出,故使邪結于外不散,再加上兩尺脈沉細,還有陰血或者下焦肝腎不足的深層因素。治療的方法,應該益氣養陰清熱,兼以發散風邪(此為“辨人”)。但如果考慮到運氣因素,主客氣均為太陰濕土,主運少宮、客運太宮,都與濕土有關,所以其關鍵矛盾應該是人體的太陰系統(手太陰肺、足太陰脾,肺主皮毛、脾主布散水谷精微上合于肺),不能與自然界當令的太陰之氣相合而布散。脾不能化精于肺,導致太陰脾肺陰津不足而邪濕不化。再根據北政之歲(中運屬金、水之年為北政)陽明所在不應脈的特點,可以推知兩尺脈因運氣因素的抑制而呈現出與病情不和,并非營血或者肝腎不足(此為“辨天”)。最后,綜合“辨人”與“辨天”的分析,確定其治療方法應該清潤太陰,助脾化濕,升散風邪,故以麥冬、生地黃清肺滋脾,木香、茯苓化濕邪而助太陰運化,前胡、柴胡散風邪而升陽氣,秦艽、甘草交合天地之氣,使流通無滯。
王氏這種“辨人”“辨天”(實際上還有“辨地”——地理高卑、風俗淳散等)的綜合分析法,是中醫學“天人相應”以及“三因制宜”思想的完美體現。從多維角度分析病情,有利于更全面、深入地把握病機,提高療效。
《醫學窮源集》經王氏弟子殷宅心整理出版后一直未能流傳開,殷氏一脈卻“什襲藏之,珍逾拱璧,私為家學,不輕以予人”。然而該書為王氏一生對中醫理論及臨床研究的精華之作,也是升華之作,改變了運氣學重推演、重理論而與臨床難以貼合的局面,十分值得大家深入研究,故為拋磚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