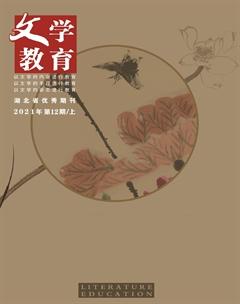淺析狄金森死亡主題詩歌中的矛盾性
孫偉
內容摘要:艾米莉·狄金森所創作的許多詩歌涉及到死亡主題,但是她在詩歌中所流露出對死亡的看法似乎是搖擺不定的。通過細讀狄金森的詩歌,我們可以發現貫穿在這些看似矛盾的詩行背后的是她對生命和生活的熱愛。
關鍵詞:艾米莉·狄金森 詩歌 死亡
死亡是文學作品中最永恒的主題之一。許多詩人都被這個主題所吸引,但很少有人像艾米莉·狄金森這樣有如此多的作品與死亡相關。Mordecai Marcus(1982:80)指出,狄金森一半以上的詩作涉及到了死亡,而且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詩作是以這一主題為中心的。由于死亡本身是基督教信仰的一個重要概念,也由于狄金森從當時的清教徒思想中借用了大量的意象,因此這些詩作中的大部分也觸及到了宗教主題。但是她對死亡的看法和對宗教信仰的態度看起來是搖擺不定的,人們似乎不能在她的詩作中找到明確的答案。其實,通過細讀狄金森所創作的關于死亡和宗教的詩歌,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些看似矛盾的詩行背后一以貫之的是她對生命和生活的熱愛。
一.狄金森詩歌中對死亡的思考
19世紀新英格蘭社區中年輕人的死亡率很高,因此,狄金森生活的小鎮上經常出現死亡的場景,這一因素促成了她對死亡的關注。作為許多死亡場面的觀察者,狄金森首先感受到的是失去親友的痛苦。“她活著的最后一晚”(第1100首)采用了第一人稱復數的視角,以強調目擊者失去親友的共同情感。過去式表明雖然那一夜已經過去,其細節卻被目擊者強烈地記住了。“普通的一夜”表明盡管逝者已經離去,世界仍在繼續,也映射出目擊者面對客觀世界的冷漠感受到的痛苦。作為目睹親友即將離去的緊張反應,他們“來回折返于她的臨終房間與起居室之間”。“其他人能存在,而她必須放棄”則更是敘述人對自己沒有能力將親人留在世上的自責。
艾米莉·狄金森也從一個臨終者的角度來描寫死亡。在“我聽到蒼蠅的嗡嗡聲——當我死的時候”(第465首)的開頭,敘述人就告訴讀者她已經死了,然后描述了她去世的時刻。房間的靜謐與臨終者聽到的蒼蠅的嗡嗡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彌漫在現場的緊張氣氛被比喻為暴風雨中的停頓。第二節的重點則是那些圍在四周的人,他們的眼神和呼吸反映了在面對死亡來臨時的緊張心情。接下來,焦點又轉回到敘述人身上,她一直在用她剩余的感官力量觀察自己的死亡。她將自己的財產分配給他人只是一個心理事件;她已經脫離了周圍的環境,既不能處理這些物質,也對它們不感興趣了。然后有一只蒼蠅飛了進來,敘述人用“藍色”來修飾蒼蠅的嗡嗡聲,暗示著她的感官功能正在衰退。蒼蠅在光線和她之間飛舞,似乎既是死亡時刻的信號,也象征了她即將離開的珍貴世界。最后兩行的“窗戶壞了——我什么也看不見了”則是一種心理學上的精準代入,并不是窗戶壞了,而是敘述人失去視覺功能了。
有論者指出,詩歌是狄金森“對抗、追問和思考死亡的最佳途徑,在對死亡的追問和思考中,她去找尋活著的意義。”(徐健翔, 2020:140)狄金森意識到死亡的必然性是生命苦澀的源頭,卻也賦予了生命以意義;正因為生命只有一次,才使得生命如此甜蜜與珍貴。在前面所提到的第1100首中,旁觀者因為親人的逝去,變得更加敏銳,從而注意到了“最小的東西,以前忽略的東西”(第5、6行)。狄金森通過這些詩歌清晰地表達出如果不理解死亡,就不能充分理解生命的意義。
二.狄金森詩歌中對永生的思考
死亡必然與基督教傳說中永生的可能性密切相關。艾米莉·狄金森不能完全拒絕這樣的誘惑。警句式的“屋里的忙亂”(第1078首)表達出了對永生的確信。它可以看作是第1100首的續篇。詩的開頭似乎是對一個親人去世后的家庭的客觀描述。雖然只是第二天早上,家里已經恢復了忙亂的常態。然而緊接著出現了大膽的反轉。第一節中所暗示的家務活動是收拾家里的物品,而在第二節中則變成了“打掃干凈心房,收拾起愛情”。與收拾物品不同,心和愛將“不再使用”,直到我們在永恒中與故去的親人相聚。
艾米莉·狄金森希望能夠相信永生,因為那樣她就能在天堂里見到心愛的人。但這位思想獨立的詩人永遠無法接受一種不需要任何證明的信仰。在“這個世界并非結局”(第501首)中,狄金森戲劇化地表現了這種對永生的信仰與深刻懷疑之間的精神沖突。這是一首典型的狄金森式的詩歌,“以斷言和肯定開始,但結尾即使不是徹底否定,也是有所保留或提出質疑。”(Baym,1989:2372)這首詩一開始就強調了死亡之外還有一個世界。雖然我們無法看見,但仍然可以直觀地理解,就如同理解看不見的音樂一樣。然后詩中引入了沖突。永生是有吸引力的,但又令人費解。即使是睿智的人也必須穿越死亡之謎,卻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困惑的學者不如那些像基督一樣、為自己的信仰慷慨赴死的人令人敬佩。敘述人想成為他們那樣的人,因此她需要尋找信仰的理由。她像一只鳥“摘下一枝證據,向風向標問路”。這意味著現有的證據就像小樹枝一樣微不足道,像旋轉的風向標所顯示的方向一樣不確定。她不能不對永生產生懷疑,而傳教士提供的麻醉劑(哈利路亞贊美詩)并不能平息這種“啃噬靈魂”的疑慮。
三.狄金森詩歌中對宗教信仰的思考
狄金森對永生的矛盾態度導致了她對宗教信仰的思考。以加爾文主義為核心的清教思想是19世紀阿默斯特社區的主流信仰,它建立在上帝的全能和人的墮落這兩大前提之上。然而,狄金森發現自己不可能完全向上帝屈服。
例如,“以前,垂死的人”(第1551首)對信仰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這首詩首先反映了十九世紀初人們認為死亡會把他們帶到上帝的右手邊的想法。第二節則斷言,如果沒有信仰,人們的行為就會變得淺薄和渺小。她最后宣稱,“一點磷火”總比根本沒有光亮(沒有精神指引和道德指引)要好。對狄金森而言,信仰的主要作用是幫助人類了解自己的起源、狀況和命運。所以狄金森宣稱,“‘信仰’是一個好的發明” (第185首)。這首詩告訴讀者,如果信仰是建立在具體的感知基礎上的,那么它是一種可接受的發明。但是,當我們看不到信仰的理由時,就需要“顯微鏡”來發掘真實的證據。
狄金森還在“圣經是一本古老的書”(第1545首)中批評了傳統的布道方式。狄金森通過嘲諷自以為是的說教來表達她的不滿,“罪是一面峭壁,其他人必須抵制,‘相信’的男孩非常孤獨,其他男孩都‘迷失’了”。最后她懇求像奧菲斯的琴聲一樣婉轉的教導,因為“它并不宣判”。總的來說,這首詩是對清教徒關于美德與罪惡的觀念的批評。只有有利于人們的福祉,宗教才能成為一種美好的發明。如果它的目的是將人們壓制在罪的重負之下,并用救贖的希望來束縛他們,那是狄金森所不能接受的。
狄金森對宗教的實用主義態度也使她對傳統的上帝觀念產生了懷疑。“我知道他存在”(第338首)把上帝呈現為一個惡毒的騙子,人的屈服從上帝那里得不到回報。與“這個世界并非結局”(第501首)一樣,這首詩也有一個從前兩節的肯定到后兩節的極度懷疑的重要轉折。前兩節堅信上帝的存在,他一直隱藏著,以使得死亡成為幸福的伏筆。與上帝相遇和永生的到來將會是一個驚喜。但在后兩節中,敘述人預見到,如果死亡的凝視既沒有帶來上帝也沒有帶來永生,那么這個游戲就會是一個惡毒的玩笑,而上帝則是一個無情的騙子,喜歡看人們愚蠢的期待。
“顯然沒有驚喜”(第1624首)則將上帝描繪成謀殺者的同謀。“幸福的花兒”可以代表任何自然界的生物,但對花兒的擬人化暗示著上帝對待其他生物和對待世人一樣無情。冰霜被比作“金發刺客”,將花兒“砍首”。代表大自然的太陽對這種暴行不為所動,運行如常,而上帝似乎贊同這樣一種進程。這意味著上帝對包括人在內的生物,要么無動于衷,要么殘酷無情。這首詩的微妙之處反映了一個敏感的詩人在如何看待上帝是否存在時遇到的痛苦和困惑。正如查爾斯·安德森所說,詩人“把絕望的體驗以及它所喚起的意象轉化為藝術。”(李麗波, 2017:254)
作為“介于清教徒和現代派之間的關鍵詩人”(Elliot,1988: 623),狄金森受到清教思想對人類苦難以及生命意義的思考的影響,并預示著現代派對死亡和缺乏確定性的認識。生命只有一次,這是人生苦澀的源泉,卻也正是生命的珍貴之處。如果死亡是連接此生與永恒的橋梁,人們愿意通過死亡與心愛的人重逢,但永生卻無法證明。宗教應以增進人類福祉為目的,但當人們看到的只是顯得苦難和殘酷時,上帝是否存在就是值得懷疑的。盡管她對宗教產生了懷疑,甚至失去了希望,但是她并未絕望,而是通過創作不斷探索此生的意義。艾米莉·狄金森懷著對生命和生活的執著的熱愛,記錄下了她對生命價值的思考,永遠啟迪著讀者理解人生的意義,為創造幸福的生活而積極奮斗。
參考文獻
[1]Baym N et al.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C]. 3rd ed. Vol. 1.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1989.
[2]Marcus M. Cliffs Notes on Emily Dickinson: Selected Poems[M]. Lincoln, Nebraska: Cliffs Notes Inc.1982.
[3]李麗波.狄金森詩歌中的神秘主義傾向[J].寧夏社會科學,2017(4):252-256.
[4]徐健翔.活著的意義——艾米莉·狄金森死亡詩的解讀[J].紅河學院學報,2020(3):139-141.
(作者單位:鹽城工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