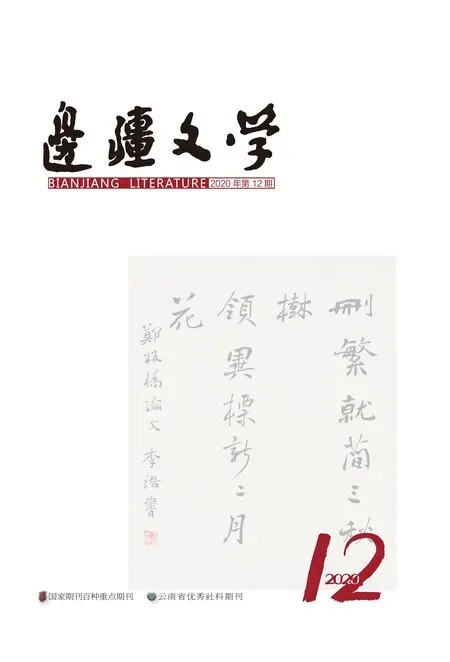明天見(jiàn)(中篇小說(shuō))
尹馬
1
文天嬌問(wèn)我:你發(fā)的那條短信是什么意思?
什么短信?我不清楚。我沒(méi)有給她發(fā)過(guò)短信,我甚至可以向所有人保證,近三個(gè)月來(lái),我從未給任何人發(fā)過(guò)短信。短信這玩意兒,不能隨便發(fā),整不好容易給人留下話(huà)柄,容易惹事,容易讓自己煩惱。我已經(jīng)夠煩惱的了,這個(gè)時(shí)候要是再給一個(gè)女人發(fā)短信,說(shuō)不定會(huì)“黃袍”加身。可是,文天嬌偏要說(shuō)我給她發(fā)過(guò)一條短信,偏要我解釋那條短信是什么意思。我拗不過(guò)她,便問(wèn),你收到的那條短信,寫(xiě)的是什么?
“祝你天天有個(gè)好心情。”文天嬌說(shuō)。
“那更不是我發(fā)的了。”我對(duì)她說(shuō),我不可能發(fā)這樣的短信,我又不是吃飽了撐的。
“什么意思?”她提高嗓門(mén),“你是說(shuō),你不希望我天天有個(gè)好心情?”
這樣的對(duì)話(huà)容易讓一個(gè)本就滿(mǎn)身煩惱的人迅速陷入巨大的沮喪之中。我肯定是無(wú)話(huà)了,差點(diǎn)把手機(jī)摔到地上,牙齒不由磨得咯咯咯響。那頭接著說(shuō),“你不愿我好,對(duì)你也不是什么好事,因?yàn)槲沂悄愕呢毨?hù)。”
“我當(dāng)然不是這個(gè)意思。”我說(shuō),“我肯定希望你好,希望你趕緊發(fā)家致富,迅速摘掉貧困戶(hù)的帽子。但是,我真的沒(méi)有給你發(fā)過(guò)什么短信。”
文天嬌說(shuō):“那不一樣嗎?既然這條短信不是你發(fā)的,就說(shuō)明你不想幫我,說(shuō)明你壓根就不想讓我脫貧。”
掛了電話(huà),我立即攔了一輛出租車(chē),去我扶貧的那個(gè)村子。四十分鐘后,我到了文天嬌的家門(mén)口。文天嬌坐在檐坎上的一條板凳上,一只手撐著下巴,另一只手拿著手機(jī),眼睛定定地看著顯示屏。我說(shuō),把你的短信給我看看,說(shuō)不定我能幫你把那個(gè)發(fā)短信的人揪出來(lái)。她看了我一眼,又迅速把目光收回去,嘴里說(shuō):“有什么用呢?”
“既然你不在意,就別管它,興許是誰(shuí)發(fā)錯(cuò)號(hào)碼了,原本他是想發(fā)給另一個(gè)人。”
文天嬌的兩只眼睛突然炯炯有神起來(lái),看了我半晌,說(shuō):“原來(lái)真是你發(fā)的,是你發(fā)錯(cuò)了號(hào)碼。”
“真不是我發(fā)的,你知道我的電話(huà)號(hào)碼不是這個(gè)。”
“你都承認(rèn)是你發(fā)錯(cuò)號(hào)碼了嘛。”文天嬌說(shuō),“對(duì)了,你可能是想發(fā)給王必藍(lán),或者小九妹,但一不小心,就發(fā)到我手機(jī)里來(lái)了。”
“我親自來(lái)你家,不是聽(tīng)你胡扯這些。短信的事,先放到一邊去,咱們商量一下正事。”我說(shuō)。
“你以為短信就是小事?”她的語(yǔ)氣很不友好。
“那你先說(shuō)說(shuō)你的想法。”我盡量壓低聲音,讓語(yǔ)氣顯得更加溫和。
“我得先弄清楚這條短信是什么意思。”文天嬌擺好陣勢(shì),“首先,我有沒(méi)有一個(gè)好心情,關(guān)誰(shuí)什么事?你說(shuō)我天天有一個(gè)好心情,我就能天天有一個(gè)好心情嗎?還有就是,我一個(gè)女人家,你給我發(fā)這樣的短信,還顧不顧我的面子了?還有就是,我的老公雖然丟了,也用不著你來(lái)操心我的心情,還有就是……”她好像暫時(shí)沒(méi)有想好下一句該怎么說(shuō),所以就停住了,從板凳上站起來(lái),使右腳往后將板凳踢翻在地,走到院壩里,拉開(kāi)雞籠的門(mén),惡狠狠地對(duì)里面僅剩的兩只母雞說(shuō):“叫叫叫,咯咯咯吵死人,有本事你給我生出一捆鈔票出來(lái)。”
文天嬌的丈夫是五年前丟的。說(shuō)是丟,是她自己的說(shuō)法。據(jù)村民小組長(zhǎng)穆興海說(shuō),文天嬌的丈夫之前是一個(gè)小老板,早年一直帶著文天嬌在浙江永康的工地上攬工程,掙了不少錢(qián)。掙了錢(qián)的文天嬌丈夫,回家把舊房拆了,修了三個(gè)進(jìn)出的兩層水泥房,個(gè)人出錢(qián)硬化了從村主路到他家的連戶(hù)路,還在山上的包產(chǎn)地里打了水井,把水管埋到自家的院壩。房子修好了,文天嬌的丈夫?qū)ξ奶鞁烧f(shuō),眼下正是孩子們讀書(shū)的關(guān)鍵時(shí)期,你在家里好好管管他們,也照顧老人,掙錢(qián)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文天嬌也就沒(méi)有隨丈夫出門(mén),而是留在家里。文天嬌的丈夫離開(kāi)的第二天,文天嬌就再也沒(méi)打通過(guò)他的電話(huà),開(kāi)始是通了沒(méi)人接,后來(lái)是直接關(guān)機(jī)了。文天嬌把公公婆婆送到小姑子家,一個(gè)人買(mǎi)了去浙江永康的車(chē)票,找遍了大大小小上百個(gè)工地,硬是沒(méi)見(jiàn)到丈夫的影子。問(wèn)之前那些在他們手底下做過(guò)工的老鄉(xiāng),他們都說(shuō)沒(méi)見(jiàn)過(guò),有幾個(gè)來(lái)自外地的工人聽(tīng)說(shuō)文天嬌找不到自己的男人,便說(shuō):“你兩口子是演雙簧嗎?我們還有一些工資沒(méi)到手哩!”
文天嬌沒(méi)有再繼續(xù)找下去,因?yàn)樗l(fā)現(xiàn),向她討要工資的外地人越來(lái)越多。她回到家里,在照顧孩子和老人的同時(shí),順便把后山上撂荒的三畝土地種了起來(lái),種的是土豆、玉米,當(dāng)然也在壟溝里套種了一些大豆和南瓜之類(lèi)的東西。日子越過(guò)越不稱(chēng)心,越過(guò)越焦慮,孩子讀書(shū)沒(méi)了零花錢(qián),老人生病買(mǎi)不上藥,三畝地?fù)纹饋?lái)的,不能叫做日子,而是熬日子。
村民小組長(zhǎng)穆興海說(shuō),文天嬌一家在四年前一下子成為監(jiān)測(cè)戶(hù),在三年前成為貧困戶(hù),實(shí)在是有些讓人難以接受。穆興海說(shuō),你看他們家這么漂亮的房子,這么寬敞的院子……你看文天嬌,穿得和城里的貴婦沒(méi)什么區(qū)別,早些年,人家不但擦脂抹粉,還戴了金項(xiàng)鏈、金耳環(huán)和金戒指。
“人家祝你天天有個(gè)好心情,其實(shí)也沒(méi)錯(cuò),這是一個(gè)美麗的祝福嘛,說(shuō)明還是有人惦記著你——們一家的。”我趕緊把差點(diǎn)說(shuō)錯(cuò)的話(huà)講得更加完整一些,生怕引起她的誤會(huì)。
文天嬌說(shuō),要不是我老公聯(lián)系不上,我才不稀罕什么祝福,我的日子又不是趕不上別人。她說(shuō)的這些,我都知道。三年前我成為文天嬌一家的包保干部,第一次到她家里走訪的時(shí)候,我問(wèn):你的丈夫丟了,你為什么不報(bào)案?
報(bào)什么案!她沒(méi)好聲氣地說(shuō),我不想讓公安局給我找回來(lái)一個(gè)死人。后來(lái),我又問(wèn)穆興海,你們?yōu)槭裁床粓?bào)案?穆興海說(shuō),這女人一聽(tīng)我們說(shuō)要報(bào)案,就稱(chēng)自己已經(jīng)聯(lián)系上丈夫了,她自己說(shuō)的話(huà)總是不一樣,在她嘴里,她的丈夫一會(huì)兒是在上海,一會(huì)兒是在新疆,誰(shuí)知道是真還是假呢?前些天,她說(shuō),吳建敏這個(gè)沒(méi)良心的東西,在外面找了小老婆,兩人私奔了。
那次走訪之后,我有一年多沒(méi)見(jiàn)過(guò)文天嬌,因?yàn)樗秩チ艘惶苏憬贿^(guò)不是去永康,而是寧波。文天嬌的三個(gè)孩子都在鎮(zhèn)上讀初中,只有周末回來(lái),在家里住一個(gè)晚上,平素費(fèi)用靠爺爺奶奶用養(yǎng)老金周濟(jì)。快過(guò)年時(shí),我與村里商量,給每個(gè)孩子一千元的臨時(shí)救助,同時(shí)我也把自己的工資拿出三千塊來(lái),給了他們。文天嬌從浙江打電話(huà)給我說(shuō):“蘇同志,感謝你關(guān)心我的孩子,欠你的錢(qián),過(guò)年回家還給你。”
“那倒不必!”我說(shuō),“你在外面好好做工,辛苦幾年,孩子上完大學(xué),你就輕松了。”
文天嬌在臘月末回來(lái),我問(wèn)她:“還行吧?”我的意思是,她這一年掙了多少。她說(shuō),光顧著去找孩子他爸了,沒(méi)工夫進(jìn)廠做工,回來(lái)的路費(fèi)都是問(wèn)妹妹借的。
大年二十九,我去我扶貧的村子看望我的包保戶(hù),給他們拜年,用了差不多一個(gè)月的工資。除了文天嬌,我的包保戶(hù)還有一個(gè)人供四個(gè)孩子上學(xué)的王必藍(lán)、早年在外面打工被機(jī)器剜掉左手五個(gè)手指頭的小九妹,以及特供人員胡勇耀和許平賢,還有幾戶(hù)去年摘掉帽子的脫貧戶(hù)。我扶貧的村子名叫歹摸梭,是一個(gè)用彝語(yǔ)命名的村莊,整個(gè)村民小組一共68戶(hù)人家,卡戶(hù)不足10戶(hù)。村民小組長(zhǎng)穆興海說(shuō),蘇同志盡管放心,再過(guò)兩年,這些人要是還不能脫貧,你拿我是問(wèn)。
我對(duì)文天嬌說(shuō),明天就過(guò)年了,你得利用全家團(tuán)圓的機(jī)會(huì),和孩子們說(shuō)說(shuō)話(huà),教育他們好好讀書(shū),將來(lái)都成為對(duì)社會(huì)有用的人才,不能給國(guó)家添負(fù)擔(dān)。文天嬌說(shuō),我也曾經(jīng)是有出息的人,這點(diǎn)道理我懂,蘇同志還是多關(guān)心王必藍(lán)和小九妹吧!
“這是什么話(huà)?”我不解。
文天嬌說(shuō),蘇同志,咱們明人不說(shuō)暗話(huà),上午你給王必藍(lán)和小九妹的錢(qián)都是兩千,為何只給我一千呢?
我一下子被她的話(huà)噎住,我沒(méi)料到曾經(jīng)有出息的她居然會(huì)這樣問(wèn)我。前些日子,我給他們家爭(zhēng)取了三千元的臨時(shí)救助,也給了他們家我自己的三千元工資,現(xiàn)在是拜年,我多給王必藍(lán)和小九妹一千元的過(guò)節(jié)費(fèi),她應(yīng)當(dāng)理解才是,況且,這錢(qián)還是我的工資。我說(shuō),文天嬌啊,我對(duì)你們家怎么樣,你心里就沒(méi)有個(gè)數(shù)嗎?她看了看我,從嘴角發(fā)出一聲“嘿嘿”,說(shuō),你的工資,想給多少就給多少,在你心里,人家就是比我可憐。
從她家出來(lái),我鉆進(jìn)一輛綠殼農(nóng)村客運(yùn)車(chē),行走在回城的路上。車(chē)?yán)铮切┻M(jìn)城置辦年貨的回鄉(xiāng)者一路討論著這些年在異鄉(xiāng)工地上的見(jiàn)聞,有人說(shuō)到文天嬌的丈夫吳建敏,說(shuō)這家伙這么多年來(lái)在外面攬工程,總是賠多賺少,在他手底下干活的,除了南廣老家的工友們,外地人就沒(méi)拿到過(guò)幾文工資。有人說(shuō),這家伙早就有預(yù)謀了,那次回來(lái)把家里收拾好,就換掉手機(jī)號(hào)碼去了別的地方,興許十年八年不會(huì)回來(lái)。
而我想到的是,我明天如何動(dòng)員我的妻子和我回老家,陪父母過(guò)年去。說(shuō)實(shí)話(huà),我有一肚子煩惱。
2
我逐漸意識(shí)到,當(dāng)我開(kāi)始不那么喜歡往人多的地方湊的時(shí)候,已經(jīng)沒(méi)有人愿意扎堆討論我的煩惱了。正如我的煩惱一樣,我越是不把它當(dāng)回事,它越是不具備煩惱的功能。更多的時(shí)候,我對(duì)待煩惱的方式是喝酒,一個(gè)人喝,使勁喝,最好是在很短的時(shí)間內(nèi)把自己灌醉,醉得只剩下上床睡覺(jué)的力氣。剛開(kāi)始,我還會(huì)一邊喝酒,一邊和自己說(shuō)話(huà)。說(shuō)些什么呢?比如,關(guān)于我的包保戶(hù)文天嬌的家庭收入問(wèn)題;比如,我任第一村民小組長(zhǎng)的那個(gè)村子68戶(hù)老百姓的安全飲水問(wèn)題;比如,脫貧戶(hù)張疙瘩一不小心又返貧的問(wèn)題……我和自己的對(duì)話(huà)導(dǎo)致我的老婆對(duì)我無(wú)比反感,最后就真的很氣憤,給我父母打電話(huà),說(shuō),你兒子怕是精神出了問(wèn)題,這日子沒(méi)法再過(guò)下去了,給二老說(shuō)清楚,我就搬出去住。
好吧,你既然要出去住,就多住些時(shí)日,待我把煩惱的事全部搞定,你再搬回來(lái)。在我老婆支小茵拎起箱子準(zhǔn)備出門(mén)的時(shí)候,我這樣對(duì)她說(shuō)。她似乎很不情愿和我說(shuō)話(huà),所以當(dāng)我這樣說(shuō)的時(shí)候,她假裝什么也沒(méi)聽(tīng)見(jiàn),徑直拉開(kāi)門(mén),走了。過(guò)了五分鐘,我聽(tīng)見(jiàn)鑰匙在鎖孔里扭動(dòng)的聲音,她又進(jìn)來(lái),氣喘吁吁地對(duì)我說(shuō),你擬一個(gè)離婚協(xié)議吧,越快越好。
“對(duì)了,擬協(xié)議是為了離婚方便,我什么也不要,反正咱們什么也沒(méi)有。”臨出門(mén)時(shí),支小茵又說(shuō)。
我們不是什么也沒(méi)有,我們只是沒(méi)有孩子。
我沒(méi)工夫搭理她,就點(diǎn)點(diǎn)頭表示同意。我現(xiàn)在最要緊的事,是趕緊把自己灌醉,然后美美地睡一覺(jué),把所有煩惱統(tǒng)統(tǒng)忘卻。然而,自打支小茵走了以后,我就不那么容易醉了——不是醉不下去,而是醉了也無(wú)比清醒,睡不著。睡不著怎么辦呢?那就再喝一點(diǎn),喝多了,全身沒(méi)有一點(diǎn)力氣,睡是睡著了,卻是睡在地板上,醒來(lái)時(shí)骨骼疼痛,手腳冰涼,后來(lái)還發(fā)了燒。醫(yī)生說(shuō),你再這樣下去,你的包保戶(hù)們恐怕真的很難脫貧了。想想也是,光喝酒也不是辦法,還不如勇敢面對(duì),試著去解決所有的事情。
怎么解決呢,還沒(méi)理出個(gè)頭緒,文天嬌的電話(huà)就打了過(guò)來(lái)。
“你的電話(huà)號(hào)碼是多少?”她問(wèn)。
“你真是神仙!”我實(shí)在想不出用一句什么話(huà)來(lái)反問(wèn)她,就說(shuō)了這幾個(gè)字。說(shuō)實(shí)話(huà),盡管我此時(shí)酒意未除,頭昏腦漲,我還是想笑,但我終究沒(méi)有笑出聲來(lái),因?yàn)槲抑浪钠⑿裕乙坏┥杂械÷蜁?huì)招來(lái)她無(wú)窮無(wú)盡的指責(zé),所以我接著說(shuō),我的電話(huà)就是你現(xiàn)在正在打的這個(gè)。
“問(wèn)你個(gè)電話(huà)號(hào)碼怎么了?”她明顯已經(jīng)生氣,“說(shuō)我是神仙,還不如直接罵我傻子。”
我一時(shí)說(shuō)不出話(huà)來(lái)。好久好久,才對(duì)她說(shuō),我只是提醒你,你家的明白卡上有我的電話(huà)號(hào)碼,只是你不小心忘記去找了。
“你明顯是在欺負(fù)人!”她的聲音提高了好多。“我承認(rèn)我是窮人,但我不是傻子。”
“我沒(méi)這個(gè)意思。”我說(shuō),“我現(xiàn)在正走在去開(kāi)會(huì)的路上,有什么事,明天再說(shuō)。明天我要來(lái)你們村里,當(dāng)然,也要去你家。”
“問(wèn)你一個(gè)電話(huà)號(hào)碼,也要等到明天嗎?”
“不是——”我說(shuō),“我真的要開(kāi)會(huì),要不,一會(huì)兒散會(huì)了,我告訴你我的電話(huà)。”
我強(qiáng)行掛了。坐在沙發(fā)上,全身直哆嗦。的確應(yīng)該勇敢面對(duì)了,我告訴自己。可是,我的煩惱居然越來(lái)越多,我能一下子全部面對(duì)嗎?酒醒的時(shí)候,我意識(shí)到自己犯了嚴(yán)重的錯(cuò)誤,我不應(yīng)該讓我的老婆支小茵搬出去住。我的家庭問(wèn)題給我?guī)?lái)的煩惱曾一度壓得我喘不過(guò)氣來(lái),在我接受包保任務(wù)之前,我連上廁所的時(shí)候都會(huì)聽(tīng)到別人蹲在不同隔間的便盆上討論我的家事,他們會(huì)說(shuō),“蘇陽(yáng)這次夠嗆了,聽(tīng)說(shuō)是他的身體出了問(wèn)題,生不了孩子,老婆又比他年輕,早晚得散。”
“我看是。”另一個(gè)隔間的人說(shuō),“他也夠可憐的。”
他們是我的同事,我們平時(shí)和諧相處,工作一起干,壓力共同分擔(dān),偶爾一起喝酒,會(huì)互相把手放在彼此的肩膀上,笑對(duì)世間破事,暢想美好未來(lái)。基于我們是朋友,我就想,既然他們喜歡說(shuō)點(diǎn)別人的事,就由著他們吧,如果能給他們帶來(lái)些許愜意的話(huà)。在我未接受包保任務(wù)之前,我連報(bào)個(gè)出差都會(huì)受到單位分管財(cái)務(wù)的領(lǐng)導(dǎo)奚落:“著急個(gè)啥,你兩口子這么高的工資,不愁吃不愁穿,又不撫養(yǎng)孩子。”我悻悻地離開(kāi),我想,我的老婆在單位上有沒(méi)有受到這樣的挖苦呢?后來(lái)我終于肯定了,她在她的單位所受到的打擊,肯定比我更甚。于是,我更加依賴(lài)喝酒來(lái)讓煩惱暫時(shí)隱身了。
這幾年,單位所有干部職工都領(lǐng)了包保任務(wù),多則十幾戶(hù),少則幾戶(hù)。似乎每個(gè)人都變了一副嘴臉,不再討論別人的是非了。對(duì),人一旦真正忙起來(lái),哪有功夫管別人的事,況且,我一看見(jiàn)人多的地方,就主動(dòng)躲開(kāi),他們只要看不見(jiàn)我,就想不起拿我說(shuō)事。當(dāng)然,這樣一來(lái),我只能一個(gè)人消化自己的煩惱,我的老婆漸漸不愛(ài)和我說(shuō)話(huà),我每次在家里喝酒的時(shí)候,她都會(huì)迅速走進(jìn)臥室,門(mén)“砰”的一聲。
3
本是星期天,可以適當(dāng)休息休息,但我還是約了單位的同事小蒯一起去歹摸梭。小蒯比我小十來(lái)歲,是一個(gè)在地方上有一點(diǎn)點(diǎn)名氣的詩(shī)人。小蒯曾經(jīng)對(duì)我說(shuō)過(guò),他懷疑自己的詩(shī)有可能是這個(gè)世界上最棒的,因?yàn)樗脑?shī)從來(lái)沒(méi)有“啊”字。我不懂詩(shī),但我尊重小蒯,我認(rèn)為,一閑下來(lái)手上就拿著一本書(shū)的小蒯絕對(duì)不會(huì)舍得花時(shí)間去議論別人的事,盡管很多時(shí)候他手里的書(shū)壓根就沒(méi)有打開(kāi),他只是盯著封面上的圖案安靜地發(fā)呆。小蒯的書(shū)很多,經(jīng)常被他遺忘在廁所的背水箱上,有時(shí)候過(guò)了好幾天了他都沒(méi)有去將它拿回來(lái),原因有可能是小蒯上廁所喜歡去不同的隔間,因?yàn)樗f(shuō)過(guò),詩(shī)人喜歡新鮮感。
小蒯把車(chē)停在村口,對(duì)我說(shuō),你去吧,我在車(chē)?yán)锼粫?huì)兒,你辦完事,咱就回去。我說(shuō),你不去看看你的貧困戶(hù)?小蒯嘿嘿嘿笑了一陣,說(shuō),有什么好看的,人家又沒(méi)打電話(huà)給我。
實(shí)際上,小蒯是和我開(kāi)玩笑。原本,他是要去一個(gè)叫烏路斯的地方的,那里是他扶貧的村民小組。小蒯和我一樣,也包了九戶(hù),不過(guò),他的包保對(duì)象大部分都不在家里,除了一戶(hù)特供人員外,其余的幾乎都舉家外出務(wù)工了。在路上的時(shí)候,小蒯就說(shuō),今天得去找“小矮人”聊聊,動(dòng)員他搬去敬老院。小蒯所說(shuō)的“小矮人”,是一個(gè)叫趙高的侏儒癥患者,60多歲,因?yàn)閺奈椿榕洌詿o(wú)兒無(wú)女。趙高有三畝土地,全部分給兩個(gè)侄子耕種,每年從他們手里獲取幾百斤包谷,順便在需要的時(shí)候讓他們幫忙做些磨玉米面、搬煤塊之類(lèi)的活兒。小蒯說(shuō),趙高這老小子不肯去敬老院,不是怕在里面過(guò)得不舒心,主要原因還是他老愛(ài)尿床,怕別人笑話(huà)。我問(wèn),成年人也尿床?他說(shuō),大約是名字的原因吧,和歷史上的某個(gè)宦官一樣,下頭堵不住。
“你不是要去找他聊聊去敬老院的事嗎?怎么這會(huì)兒又睡上了?”我問(wèn)小蒯。
“算了吧,聊也是瞎耽誤工夫,他不會(huì)愿意的。”小蒯說(shuō)完,閉上眼睛打起了盹。
經(jīng)過(guò)小九妹家的院子時(shí),我看見(jiàn)小九妹用一只手吃力地在地上搬起一塊磚頭,正準(zhǔn)備遞給站在一堵矮墻上的她的公公。公媳二人在壘豬圈,見(jiàn)我過(guò)去,小九妹說(shuō),蘇同志,你是來(lái)給文妹兒送電話(huà)號(hào)碼的嗎?
“你怎么知道?”我問(wèn)。
“她昨天來(lái)我家找我要你的電話(huà),我讓她看了明白卡,然后她說(shuō),她要打你的電話(huà)問(wèn)你的號(hào)碼。我看,這個(gè)人八成是腦子被門(mén)擠壞了。”小九妹說(shuō)完,笑得差點(diǎn)摔倒在地上的一堆砂石上。
我說(shuō):“不能這樣取笑別人,人家現(xiàn)在的確是遇到了實(shí)際困難,人在有很多煩惱的時(shí)候,腦子是容易短路的。”
“我沒(méi)有取笑她的意思,其實(shí)文妹兒這個(gè)人很不錯(cuò),只是她犯這樣的低級(jí)錯(cuò)誤讓人忍不住想笑。”小九妹接著說(shuō),“蘇同志,要不要進(jìn)屋喝點(diǎn)水,順便檢查一下我們這豬圈壘得合不合格。”
“先不說(shuō)合不合格的事,你們這樣磨洋工,一天還壘不了一尺高,什么時(shí)候才能養(yǎng)起豬崽呢?”我對(duì)她說(shuō),“還有,你得找石匠。”
“沒(méi)錢(qián)請(qǐng)石匠的。”小九妹說(shuō),“再說(shuō),這么一丁點(diǎn)活,哪個(gè)石匠愿意接?”
“壘著吧,盡量做好一些。”我說(shuō)。
文天嬌恰好從自家屋里出來(lái),正往小九妹家走,見(jiàn)我們?cè)谠鹤永镎f(shuō)話(huà),忽又折回身,被我喊住。
“蘇同志,我其實(shí)是想知道你有沒(méi)有用兩個(gè)電話(huà)號(hào)碼。”文天嬌走到我身邊,小聲地說(shuō)。
“我用的就是兩個(gè)號(hào)碼,不過(guò),經(jīng)常用的還是明白卡上的那一個(gè)。”我說(shuō)。
“怪不得!”文天嬌的聲音一下子洪亮了起來(lái),她在說(shuō)這話(huà)的時(shí)候,用眼睛看著小九妹,仿佛想從她那里得到一個(gè)有力的求證。
“你又不是移動(dòng)公司的,人家用多少號(hào)碼,話(huà)費(fèi)也不是你收。”小九妹又笑,手里的磚頭不由地從手里滑落,差點(diǎn)砸在自己的腳上。
“別嘻嘻哈哈的了,你讓我老者站在這墻上,腳桿酸得很。”小九妹的公公拍了拍胸前的圍腰,轉(zhuǎn)而對(duì)我說(shuō),“蘇同志,開(kāi)春后可不可以給我?guī)资啵蚁氚逊孔拥膲w處理一下,然后上點(diǎn)白灰。”
“沒(méi)問(wèn)題。”我說(shuō),“只是你這手腳,怕是活兒干不到一半,水泥就完全失效了。”
“那倒不會(huì),只要你肯給,我就能保證水泥不失效。你不相信的話(huà),你給我千兒八百包,看它會(huì)不會(huì)失效。”老者一邊說(shuō),一邊拍打著圍腰。
“我爹也真是的,人家憑什么給你那么多,你以為蘇同志扶貧只扶你一個(gè)人!”小九妹又拾起地上的磚頭,吃力地遞給公公。
文天嬌在一旁插不上話(huà),很不耐煩,便轉(zhuǎn)身欲走回家,又被我叫住。我問(wèn)她,“你想好沒(méi)有,去學(xué)縫紉的事?”
“不去。”文天嬌說(shuō),“那玩意兒掙不了幾個(gè)錢(qián),再說(shuō),學(xué)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你這不是說(shuō)瞎話(huà)嗎?上次我就講過(guò),你去學(xué)一個(gè)月,學(xué)會(huì)了,我讓你到城里易遷點(diǎn)的扶貧車(chē)間去務(wù)工,那里是一個(gè)服裝廠。”
“不去不去。”文天嬌說(shuō),“我早就打聽(tīng)過(guò)了,那個(gè)服裝廠的生意慘淡得很,一個(gè)月還掙不了五千塊錢(qián)。”
“四千也行啊。”小九妹在一旁插話(huà),“蘇同志,你看看我能不能去,我雖然只有一只手,但我靈活得很,說(shuō)不定那些雙手雙腳的人還趕不上我。”
我一時(shí)語(yǔ)塞,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小九妹的左手相當(dāng)于只是一根可以擺動(dòng)的木棍,抓不住什么東西,她要是去學(xué)縫紉,和一個(gè)左嗓子去學(xué)唱歌沒(méi)什么兩樣。我心里突然一陣酸楚,心想,其實(shí)我應(yīng)該幫助小九妹找一份適合她的工作,她太需要一份工作了,因?yàn)樗恼煞蛟谌昵熬谱砗蟀蚜硗庖粋€(gè)同樣酒醉的工友砍成了植物人,這輩子不知道出不出得來(lái)。我這樣想著的時(shí)候,文天嬌又說(shuō),“要是孩子他爸不丟,咱家也是養(yǎng)工人的。”
我正要反駁她,小九妹又說(shuō),“蘇同志,我真的能學(xué)縫紉的,其實(shí)那種活計(jì),用一只手就夠了,他們要是準(zhǔn)允我去廠里做工,工資我只要一半,兩千就行。”
“讓她去吧。”文天嬌在一旁說(shuō),“她吃得了這個(gè)苦。”
“那你呢?你到底想干點(diǎn)什么?”我還是想先搞定文天嬌,再考慮如何幫小九妹。
“我暫時(shí)還不確定,如果孩子他爸回來(lái),我們還是想出門(mén)做工程,我們家開(kāi)支大。”文天嬌說(shuō),“對(duì)了,蘇同志,你的另外一個(gè)號(hào)碼是多少?”
我把號(hào)碼告訴了她。我說(shuō),“你可以先撥一個(gè),聽(tīng)聽(tīng)我的手機(jī)響不響,然后,你再看看那個(gè)給你發(fā)短信的電話(huà)號(hào)碼與我的是不是同一個(gè)。”
其實(shí),我真的希望文天嬌相信那條短信就是我發(fā)的,這樣的話(huà),至少可以讓她不再因?yàn)檫@條短信而和自己糾纏不清。文天嬌為什么會(huì)在意這條短信的來(lái)源,我不知道,不過(guò)先前在來(lái)的路上,我和小蒯作了很多推測(cè),最有可能的是,文天嬌懷疑這條短信來(lái)自她的丈夫吳建敏。但是有一個(gè)問(wèn)題我們始終搞不懂,文天嬌為什么要從我身上找突破口?小蒯說(shuō),“這你都不明白嗎?眼下最有可能給她發(fā)短信的就是你。”
“為什么是我?”
“因?yàn)樗悄愕陌?hù)。”小蒯的臉上露出賊一樣的笑容,“她這樣做,用的是排除法。”
無(wú)所謂,反正我沒(méi)有給她發(fā)過(guò)短信。我對(duì)自己說(shuō)。我雖然可以對(duì)自己說(shuō)無(wú)所謂,但我還是有些擔(dān)心,我怕我戰(zhàn)勝不了自己。我問(wèn)小蒯,“你在蹲茅坑的時(shí)候會(huì)不會(huì)和別人談?wù)摃r(shí)事?”
“你為什么想起問(wèn)這個(gè)問(wèn)題?”小蒯說(shuō),“難道你認(rèn)為世間最美好的事情是找一個(gè)同盟把臉憋得通紅各做各的事情,然后故意裝作很忙的樣子,自欺欺人地關(guān)注人類(lèi)命運(yùn)?”
盡管他把一件其實(shí)是很容易發(fā)生的事情講得不那么容易發(fā)生,甚至講得很幽默,我還是沒(méi)有放松下來(lái)。我又問(wèn),“你有沒(méi)有覺(jué)得一個(gè)被別人在私底下議論的人很可憐?”
“有什么可憐的!”小蒯說(shuō),“這年頭,你就是干一件正確得只有唯一一個(gè)答案的事情,同樣也會(huì)被人當(dāng)做笑話(huà)來(lái)講。”
“比如呢?”
“比如,我寫(xiě)了那么多膾炙人口的詩(shī)篇,同樣也經(jīng)常遭到人們的嘲笑。”
“說(shuō)不過(guò)去啊!”我說(shuō)。
“人家偏要以沒(méi)文化自居,你能有什么辦法!”小蒯說(shuō),“有時(shí)候人家就是覺(jué)得詩(shī)人是一個(gè)莫名其妙的物種,就應(yīng)該被挖苦打擊,所以在吃飯的時(shí)候,有人會(huì)讓你針對(duì)某一道菜寫(xiě)一首詩(shī);有時(shí)候,在你不開(kāi)心的時(shí)候,他們會(huì)對(duì)你說(shuō),寫(xiě)首詩(shī)吧!”
“最讓人無(wú)法忍受的是,他們經(jīng)常會(huì)對(duì)我說(shuō):別寫(xiě)詩(shī)了,好好找個(gè)女人結(jié)婚吧。在他們看來(lái),寫(xiě)詩(shī)相當(dāng)于酗酒、吸毒,或者賭博。”我正要接話(huà),小蒯又接著說(shuō),“不過(guò)我還真的想把這一口戒掉,找個(gè)女朋友,然后結(jié)婚。”
如此說(shuō)來(lái),就算小蒯覺(jué)得完全可以因?yàn)橐粭l短信的事而把我和丟了丈夫的文天嬌扯在一起,這樣的事情也只能是別人去干,他和我是同一種容易遭受嘲笑的人,所以他干不出來(lái)。
文天嬌好像看出了我的窘迫,對(duì)我說(shuō),“我就是想弄清楚,到底是哪個(gè)不要臉的臭男人給我發(fā)這樣的短信,我有沒(méi)有一個(gè)好心情,與他有什么關(guān)系。”
“認(rèn)真考慮一下去學(xué)縫紉的事,不能再等了,你負(fù)擔(dān)那么重。”我說(shuō)。
4
我戒了酒之后,我的老婆支小茵還是沒(méi)有搬回來(lái)住。這段時(shí)間,我每天都要到我扶貧的村民小組來(lái),通常都是小蒯開(kāi)車(chē)把我送到歹摸梭,然后他一個(gè)人去烏路斯。這段時(shí)間,我在單位的工作相對(duì)輕松,或者說(shuō)基本上沒(méi)什么活兒。平常,我干的事就是在全縣范圍內(nèi)收集那些搞刺繡、捏泥人、做蠟染、刻石頭、吹蘆笙等民間藝人的基本情況,把他們的作品拿到市里或者省上,申請(qǐng)不同層級(jí)的非遺,幫他們弄個(gè)“傳承人”之類(lèi)的稱(chēng)號(hào)。接受包保任務(wù)以后,領(lǐng)導(dǎo)說(shuō)要全身心下沉到村里,先把貧困戶(hù)的事情辦好,讓他們徹底脫貧,才去張羅民間藝術(shù)的事。小蒯和我也差不多,他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全縣的應(yīng)急廣播。說(shuō)是管,其實(shí)也沒(méi)事可管,更多的時(shí)候,他只是在需要更換廣播內(nèi)容的時(shí)候把事先準(zhǔn)備好的數(shù)據(jù)輸?shù)较到y(tǒng)里去。村莊里的喇叭每天都會(huì)在規(guī)定的時(shí)段準(zhǔn)時(shí)響起來(lái),就算是某些地方的廣播壞了,也有專(zhuān)門(mén)人員去維修。小蒯和我是整個(gè)單位下沉?xí)r間最長(zhǎng)的包扶干部,他單身,沒(méi)有家庭瑣事?tīng)拷O;我雖然有家庭,但我的老婆已經(jīng)搬出去住了。
“怕不是這回事吧!”小蒯對(duì)我說(shuō),“你老婆那么通情達(dá)理,絕不會(huì)不理解你的壓力,她搬出去,或者是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呢??jī)煽谧臃志樱畲蟮脑蚓褪腔橐龀隽藛?wèn)題。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婚姻出現(xiàn)問(wèn)題是因?yàn)槲覀兪冀K沒(méi)有孩子。我和支小茵沒(méi)有孩子,不是那些在廁所隔間里憋得滿(mǎn)臉通紅氣喘吁吁的人所講的那樣,其實(shí)我們都不知道是誰(shuí)的問(wèn)題,至少我是沒(méi)去過(guò)醫(yī)院的。結(jié)婚三年以后,我們就意識(shí)到了問(wèn)題的存在,我曾對(duì)支小茵說(shuō),咱們還是去看看吧,如果是我的問(wèn)題,你就把我甩了,你還年輕。支小茵說(shuō),那要是我的問(wèn)題呢?我說(shuō),如果是你的問(wèn)題,就當(dāng)問(wèn)題不存在,咱們就這樣過(guò)完一生,也是美好的。我不知道支小茵有沒(méi)有私自去醫(yī)院里檢查過(guò)身體,以我對(duì)她的了解,她應(yīng)該不會(huì),因?yàn)樗辉敢饷鎸?duì)任何一種結(jié)果。再說(shuō),我們都相信,我倆是有愛(ài)的,對(duì)一對(duì)有愛(ài)的夫妻來(lái)說(shuō),婚姻是很重要的。
小蒯說(shuō):“你就沒(méi)有想過(guò),你們結(jié)婚之前她就知道自己的身體有問(wèn)題了?”
“你胡說(shuō)!”我有些不高興,用拳頭敲了他的肩膀。
“蘇哥,話(huà)雖難聽(tīng),但你也要聽(tīng)。”小蒯說(shuō),“我雖然還沒(méi)結(jié)婚,但我相信這世上沒(méi)有一個(gè)生理健康的女人會(huì)和一個(gè)沒(méi)有生育能力的男人過(guò)一輩子,女人這一生,最大的夢(mèng)想就是生孩子。”
我沒(méi)有說(shuō)話(huà)。小蒯把我刺得生痛。小蒯最大的毛病就是愛(ài)瞎揣摩,盡管我相信他不會(huì)與單位上的其他同事議論我的事,但他猜測(cè)的這些,有可能其他同事也猜測(cè)過(guò),說(shuō)不定早已在廁所的隔間里討論得沸沸揚(yáng)揚(yáng)了。
我給母親打電話(huà),問(wèn)支小茵這段時(shí)間有沒(méi)有和二老聯(lián)系。我媽說(shuō):“一直都聯(lián)系著的,我怕你難受,就沒(méi)告訴你。”
“為什么這樣?”我問(wèn)。
“擔(dān)心你接受不了,所以沒(méi)有火上澆油。”我媽說(shuō),“你還是去醫(yī)院好好看看吧,科學(xué)那么發(fā)達(dá),能治好的。”
原來(lái)是這樣。其實(shí)我沒(méi)有驚訝,因?yàn)樵趲啄昵拔揖蛯?duì)我媽說(shuō)過(guò),我們要不了孩子,其實(shí)是我的問(wèn)題。我撒謊的目的是為了把“我的問(wèn)題”坐實(shí),不讓我媽在我們中間橫插一杠,以此挽救我和支小茵的婚姻。這些年來(lái),我媽不但經(jīng)常讓我去醫(yī)院看身體,還每個(gè)月去給觀音老祖燒香,乞求我趕緊好起來(lái)。我媽做得最多的事,是從各種民間土醫(yī)生的手里給我弄來(lái)很多草藥,讓我煎了服用。有一次,我媽給我捎了幾截被磨得錚亮的木疙瘩,說(shuō)要先放在枕頭底下枕著睡過(guò)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才用來(lái)泡酒喝。我沒(méi)有這樣做,我把它們放在書(shū)房的博古架上,和一管洞簫擺放在一起,成為一種無(wú)用的擺設(shè)。
“那要真是我的問(wèn)題呢?換作是你,你該怎么辦?”我問(wèn)小蒯。
他好像遭到突然襲擊一般,半晌說(shuō)不出話(huà)來(lái),臉羞得通紅。“作為一個(gè)男人,這輩子如果沒(méi)有生育的能力,你是成全你的女人呢,還是殘酷地犧牲她來(lái)維系一個(gè)在別人眼里本身就不完整的婚姻?”我又問(wèn)。
很久很久,他才說(shuō),“其實(shí)我也沒(méi)有想過(guò),這樣的事如果被我攤上,應(yīng)該很可怕。”
小蒯把我送到歹摸梭,一個(gè)人開(kāi)車(chē)去他的村子里走訪去了。我下車(chē)的時(shí)候,他呆呆地看了我足足有兩分鐘。我說(shuō):“會(huì)不會(huì)有為我寫(xiě)一首詩(shī)的念頭?”他說(shuō):“太有了,你幾乎就是一首悲慘的詩(sh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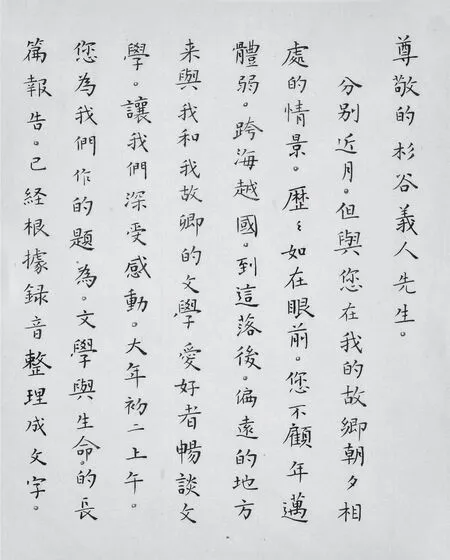
李浩 書(shū)法
小九妹家的豬圈終于壘完。豬圈雖然很小,但很規(guī)范,食槽、隔欄擺放得很清爽,圈頂上的瓦片也整整齊齊。小九妹的公公坐在豬圈外面吸旱煙,見(jiàn)我走進(jìn)院子,起身說(shuō):“蘇同志,圈倒是修好了,只是這豬價(jià)貴得很,怕暫時(shí)先養(yǎng)幾股風(fēng)耍耍。”
“你這老者,話(huà)不說(shuō)在明處,兜圈子干啥,你不就是想讓我給你弄兩頭豬崽嗎?”我說(shuō)。
“不愧是干部。”老者笑著說(shuō),“我這圈太小,最多只能養(yǎng)個(gè)三頭豬,你可別給多了,多了我收不住。”
小九妹從外面抱了一捆香椿回來(lái),聽(tīng)公公這么一說(shuō),便懟道:“我爹的脖子總是伸得好長(zhǎng)好長(zhǎng),都快夠得著天了,所以盡是談天話(huà)。”她把香椿一分為二,一半夾在咯吱窩下,一半用右手遞給我,說(shuō):“蘇同志帶回去,讓嫂子給你做個(gè)香椿炒蛋,營(yíng)養(yǎng)高的很。”
我說(shuō),“謝謝你,我們家平常都沒(méi)有生火做飯的,給了我就是浪費(fèi)。”
小九妹的公公把手上的煙鍋?zhàn)油i圈墻上敲了敲,說(shuō),“你這個(gè)干部真是精明,怕拿了東西手軟,豬崽的事,你不用上心,那是開(kāi)玩笑,香椿你拿回去,這東西,男人吃了,女人容易生兒子。”
老者的話(huà)又把握戳了一下,我感覺(jué)臉上火辣辣的。大約小九妹發(fā)現(xiàn)我的情緒有些許不對(duì)勁,便繃了個(gè)臉說(shuō),“我爹七老八十了,開(kāi)玩笑也不注意個(gè)場(chǎng)合,人家蘇同志是干部,是講文明的。”
此時(shí)文天嬌又從家里出來(lái),到了小九妹家的墻角,停下來(lái)聽(tīng)我們說(shuō)話(huà)。我問(wèn)她準(zhǔn)備去哪里,她說(shuō)她要去河對(duì)面找一個(gè)叫甘巾巾的女人。她說(shuō):“前些天聽(tīng)誰(shuí)說(shuō)過(guò),甘巾巾在江蘇見(jiàn)過(guò)我孩子的爹。”
“你記不記得是誰(shuí)對(duì)你提起這事的呢?這個(gè)人說(shuō)話(huà)可不可信?”我問(wèn)文天嬌。
“好像是劉寬兒吧!前些天王必藍(lán)家父親去世,河對(duì)面有很多人過(guò)來(lái)幫忙,有人在議論這個(gè)事情。到底是不是劉寬兒說(shuō)的,我記不得了。”文天嬌說(shuō)。
“劉寬兒是個(gè)日白匠,聽(tīng)他的話(huà),你就見(jiàn)鬼了。”小九妹的公公吐了一口唾沫,又把煙嘴放進(jìn)嘴里。
“別聽(tīng)他的,文妹兒,我爹話(huà)多得很。”小九妹一邊瞅了她公公一眼,一邊說(shuō)。
“去打聽(tīng)一下吧,好歹尋一個(gè)線索。”我對(duì)文天嬌說(shuō),“河對(duì)面也就幾步路,我和你一起去。”
到了劉寬兒家,院子里一個(gè)人也沒(méi)有。正要敲門(mén),卻看見(jiàn)門(mén)上掛了一把鎖。從隔壁的房子里走出一個(gè)四十歲左右的男子,穿著一件皮夾克,滿(mǎn)臉是汗。見(jiàn)了我們,問(wèn),“你們找誰(shuí)?”
我說(shuō),“我們來(lái)找劉寬兒打聽(tīng)一件事情,順便了解了解群眾外出務(wù)工的情況。”
男子盯著文天嬌看,目光從她紅色的上衣移到下面的緊身牛仔褲,到沾滿(mǎn)泥巴的白色運(yùn)動(dòng)鞋,看著看著,臉上的汗越來(lái)越多。他說(shuō),“劉寬兒兩口子昨天就走了,去安徽。村里用大巴車(chē)送去的,不開(kāi)車(chē)費(fèi),還提前在大城市的工廠里為他們聯(lián)系了工作。”
文天嬌見(jiàn)不到劉寬兒,就提議回去。我說(shuō),不急,說(shuō)不定這位大哥也聽(tīng)劉寬兒說(shuō)過(guò)什么。
“你們要打聽(tīng)什么事?”男子問(wèn)。
“你有沒(méi)有聽(tīng)劉寬兒說(shuō)過(guò),他在江蘇見(jiàn)過(guò)歹摸梭的吳建敏?”我問(wèn)。
文天嬌擺手打斷我的話(huà),說(shuō),“不是劉寬兒見(jiàn)到他,是甘巾巾見(jiàn)到的。”
我也懵了。我們來(lái)河對(duì)面,實(shí)際上應(yīng)該找甘巾巾,而不是劉寬兒。小九妹的公公說(shuō)劉寬兒是個(gè)日白匠,讓我忘記了文天嬌找人這件事的關(guān)鍵人物是甘巾巾。其實(shí)文天嬌也忘了,她一路上都在問(wèn):劉寬兒家住在哪里?
我懷疑,我的腦袋也被門(mén)擠了一下。我想笑,此時(shí)。
“甘巾巾也走了,和劉寬兒他們一起走的,今年不去江蘇。”男子說(shuō),“甘巾巾是我兄弟媳婦,我們都沒(méi)聽(tīng)她說(shuō)見(jiàn)過(guò)吳老板。”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打個(gè)電話(huà)問(wèn)問(wèn)?”我說(shuō),“你弟媳平常有沒(méi)有對(duì)你兄弟提起過(guò)這件事。”
“不用打。”男子說(shuō),“劉寬兒的話(huà),鬼都不信,他就是一個(gè)日白匠。”
回來(lái)的路上,我問(wèn)文天嬌到底要不要考慮去學(xué)一學(xué)縫紉,文天嬌說(shuō),“縫紉還用學(xué)?我早就會(huì)了,只是我沒(méi)有心思。你知道,我老公要是找不到,我就什么也干不了。”
“都好幾年了,不容易找到的,你還是接受現(xiàn)實(shí)吧。”我說(shuō)。
“你的意思是,就當(dāng)他已經(jīng)死了?”文天嬌停下腳步,轉(zhuǎn)過(guò)頭,“你們這些人,為啥就這么狠心,咋就不希望我們家有個(gè)好呢?”
我說(shuō),不是這個(gè)意思,我想告訴你的是,你一時(shí)半刻也找不到,不能白白浪費(fèi)時(shí)間,得冷靜下來(lái),先找份工作,把孩子們撫養(yǎng)成人,然后再慢慢找。
“說(shuō)得輕巧!”文天嬌轉(zhuǎn)過(guò)身去,邁開(kāi)腳步,步子突然加快,讓我有些跟不上。她邊走邊惡狠狠地說(shuō),就算是死了,我也要把骨灰盒拿回來(lái),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我又無(wú)話(huà)。文天嬌的態(tài)度如此堅(jiān)決,讓我不得不思考用另外的辦法來(lái)解決他們家的收入問(wèn)題。回城之前,我去了一趟村部,和單位的駐村工作隊(duì)長(zhǎng)張青討論文天嬌一家的問(wèn)題。張青說(shuō),我們也思考過(guò)好長(zhǎng)時(shí)間,硬是沒(méi)有辦法,只能給兩個(gè)低保名額,先解決眼前的困難。
“這真不是辦法。”我說(shuō),“文天嬌長(zhǎng)期這樣下去,會(huì)真正瘋掉的,到時(shí)候,這個(gè)家就毀了。”
“但她不配合我們的工作,能咋辦呢?”張青一臉無(wú)奈。
5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看見(jiàn)餐桌上放著兩件牛奶、幾盒糕點(diǎn),旁邊的一個(gè)舊紙箱里,裝著滿(mǎn)滿(mǎn)的一箱雞蛋。誰(shuí)送來(lái)的呢?當(dāng)然是她——我的老婆支小茵,只有她有這個(gè)家的鑰匙。這段時(shí)間,我一直打她的電話(huà),她從未接過(guò),偶爾給我發(fā)一條短信:很忙。或者是:沒(méi)事別打電話(huà)。
我的老婆在勞動(dòng)就業(yè)局工作,主要負(fù)責(zé)勞動(dòng)力轉(zhuǎn)移輸出,的確很忙。沒(méi)搬出去住之前,她經(jīng)常把單位上的事帶到家里來(lái)做,表格一大摞一大摞堆得整個(gè)書(shū)房、客廳到處都是。沒(méi)搬出去之前,我還沒(méi)有在家里喝上酒的時(shí)候,會(huì)經(jīng)常幫她填寫(xiě)各種表冊(cè),也差不多掌握了整個(gè)南廣縣外出務(wù)工人員的分布情況。對(duì)了,我是在一年前開(kāi)始在家里喝酒的。剛開(kāi)始的時(shí)候,支小茵沒(méi)管我,只是說(shuō),工作壓力大,少喝一點(diǎn)可以理解,可別把身子喝壞了。時(shí)間一長(zhǎng),家里的陽(yáng)臺(tái)上就堆滿(mǎn)了各種酒瓶,我的臉上也長(zhǎng)出了各種形狀的痘痘,她就有了意見(jiàn),幾次三番提醒我不能成為酒鬼。后來(lái),我就不怎么吃飯了,我的每一個(gè)下午都是從酒開(kāi)始的。后來(lái),她搬出去了。
支小茵回來(lái)過(guò),于我來(lái)說(shu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我可以這樣認(rèn)為:支小茵有了搬回來(lái)住的意思,最起碼,她已經(jīng)相信我這段時(shí)間再也沒(méi)有喝過(guò)酒。支小茵往家里買(mǎi)來(lái)牛奶、糕點(diǎn)和雞蛋,說(shuō)明她在為自己搬回來(lái)住作準(zhǔn)備,或者說(shuō),她想通過(guò)這樣的方式告訴我,我倆暫時(shí)還不會(huì)離婚。我一高興,就打她的電話(huà),可是她幾乎是在電話(huà)剛打通的時(shí)候就摁掉了。隨后,她給我發(fā)來(lái)一條短信:把自己照顧好。
這同樣值得高興。我?guī)缀鯊纳嘲l(fā)上跳起來(lái),甚至跑到臥室里去,對(duì)著梳妝臺(tái)大聲地喊了一句:支小茵,我愛(ài)你。我就是在喊完這句話(huà)的時(shí)候接到文天嬌的電話(huà)的,她說(shuō):“我病了。”
“去看醫(yī)生吧!”我的聲音很響亮,還保留著之前高昂的情緒。但文天嬌不知道是怎么聽(tīng)的,她理解成我很不耐煩,就說(shuō),“我只是想告訴你,我病了,我并不想從你那里得到什么幫助,你不用發(fā)脾氣。”
“我沒(méi)有發(fā)脾氣。”我說(shuō),“你是我的包保戶(hù),你把你生病的事情告訴我,說(shuō)明你沒(méi)有把我當(dāng)外人,我肯定無(wú)論如何也要幫你。”
“你別瞎說(shuō),你就是外人。”文天嬌說(shuō),“盡管我現(xiàn)在很窮,很多時(shí)候需要得到你的可憐,但我們非親非故。”
我說(shuō):“文天嬌,請(qǐng)你別多想,你現(xiàn)在告訴我,你生了什么病?”
“我又不是醫(yī)生,我哪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文天嬌說(shuō),“我現(xiàn)在感覺(jué)到心里發(fā)慌,頭暈得天旋地轉(zhuǎn),雙腿不聽(tīng)使喚,想吐。”
“我讓村里的同志開(kāi)車(chē)到你家來(lái),送你到醫(yī)院里去。”沒(méi)等文天嬌再往下說(shuō),我就把電話(huà)掛了。
我打電話(huà)給村里的掛片干部李顯定,讓他去接文天嬌去醫(yī)院。李顯定吃驚地問(wèn)我:“大哥,你確定我應(yīng)該這樣做?我們可是正在加班做表冊(cè)哩。”
“那也得騰出時(shí)間來(lái),文天嬌要是患了要緊的病,會(huì)很危險(xiǎn),我們這個(gè)時(shí)候必須幫她。”
二十分鐘后,李顯定給我打電話(huà),“這女人好好的,正端著一個(gè)大碗吃飯,啥事也沒(méi)有,大約她是想和你說(shuō)說(shuō)話(huà)吧。”李顯定在那頭打哈哈,讓我很不是滋味。
“把電話(huà)給她。”我說(shuō)。
文天嬌在電話(huà)里說(shuō):“蘇同志,我就是想知道你們這些干部心里有沒(méi)有裝著我們老百姓。”
“你覺(jué)得呢?”我沒(méi)好聲氣。
“還真像那么回事。”文天嬌嘴里在嚼著飯,“不過(guò),你們永遠(yuǎn)也解決不了我的問(wèn)題。”
“既然你沒(méi)什么病,就別浪費(fèi)時(shí)間了,你今天晚上準(zhǔn)備準(zhǔn)備,明天來(lái)縣里培訓(xùn)縫紉。”說(shuō)完,我掛了電話(huà)。
第二天,我去到村里的時(shí)候,小九妹告訴我,文天嬌一早就走了。我問(wèn)她知不知道這女人去了哪里,她說(shuō),“沒(méi)說(shuō)上話(huà),她背一個(gè)很大的包,有可能又去浙江了。”
“蘇同志,讓我去學(xué)吧,我能學(xué)會(huì)的。如果我一個(gè)月能在廠里拿兩千塊錢(qián),我就主動(dòng)退出卡戶(hù)。”小九妹說(shuō)話(huà)的時(shí)候,眼珠子清涼得像酒杯里的酒。
我沒(méi)有再猶豫,而是立即答應(yīng)了她。我說(shuō),“趕緊收拾,下午和我一起進(jìn)城。”
在村子里轉(zhuǎn)了一會(huì)兒,我又去了村部,再次和張青商量文天嬌的事情。張青說(shuō),如果文天嬌真的去了浙江,終點(diǎn)站應(yīng)該是永康,那里是他們之前的大本營(yíng)。如果她是去尋找她的丈夫的話(huà),肯定應(yīng)該從永康開(kāi)始。
“那又怎么樣?”我說(shuō),“再去晃蕩一陣,恐怕就會(huì)窮得叮當(dāng)響了。”
“如果是去永康的話(huà),應(yīng)該是明天上午到,我打電話(huà)給那邊的工作站,讓他們?cè)谲?chē)站把她截住,直接將這女人送到工廠里去。”張青說(shuō)。
“工廠又不是牢房,難道她不會(huì)跑出來(lái)?”我對(duì)張青的這個(gè)主意表示反對(duì)。
“先穩(wěn)住嘛。”張青說(shuō),“讓工作站的弟兄們慢慢做工作,就算她是一塊石頭,也有被感動(dòng)的那一天。”
眼下也沒(méi)有其他辦法,只能照張青說(shuō)的去做。吃了午飯,我給小九妹打電話(huà),問(wèn)她收拾好沒(méi)有,我們可以早些返回城里。小九妹說(shuō):“沒(méi)什么可收拾的,已經(jīng)和我爹商量好了,叫他自己平時(shí)爬坡上坎注意點(diǎn),再就是,星期六孩子們從學(xué)校里回來(lái),給他們弄一口熱飯。”
半小時(shí)后,我和小蒯去歹摸梭接小九妹,遠(yuǎn)遠(yuǎn)地看見(jiàn)她拎著一個(gè)編織袋站在路邊等候。她上車(chē)的時(shí)候,要小蒯把車(chē)尾箱的門(mén)打開(kāi),說(shuō):“這遭瘟的,滿(mǎn)身屎臭,不能把車(chē)子弄臟了。”
“你帶的是啥?”我問(wèn)。
“沒(méi)啥,一只雞,送給你的。”小九妹說(shuō)。
“我不能收你的東西。”我說(shuō)。
“咋不能收?你以為能值幾個(gè)錢(qián)!養(yǎng)在家里不長(zhǎng)肉,拿去街上賣(mài)又沒(méi)受主,給你帶回去,宰了,下燒酒。”小九妹用一只手拍了拍上衣的下擺,上了車(chē)。
“你家里這么困難,我不忍心收你的東西,如果非得給我,我就得給你錢(qián)。”我當(dāng)即把手伸進(jìn)口袋里,可什么也沒(méi)有摸到,原來(lái)我一分錢(qián)也沒(méi)帶。
“給我兩百塊。”我輕聲對(duì)小蒯說(shuō)。
“你說(shuō)什么?我沒(méi)聽(tīng)見(jiàn)。”小蒯似是故意的。
我從牙縫里一個(gè)字一個(gè)字地?cái)D:給——不——給——
“你都沒(méi)帶錢(qián),我為什么要帶?”小蒯嬉皮笑臉地說(shuō):“這年頭把現(xiàn)金揣在身上的都是土貨,要不,你微信或支付寶轉(zhuǎn)給她吧。”
我弄得很尷尬,感覺(jué)臉上熱乎乎的。我對(duì)小九妹說(shuō),“你看,我們都沒(méi)帶錢(qián),你還是把雞拿到市場(chǎng)上去賣(mài)了吧,多少也能給孩子買(mǎi)幾個(gè)作業(yè)本。”
小九妹嗚嗚嗚地哭了起來(lái),邊抹眼淚邊說(shuō):“你們這些當(dāng)干部的,就會(huì)從心里防著我們窮人,以為收了一點(diǎn)東西,就會(huì)被我們逼著辦什么事。你要是不收,我就不去城里了,反正縫紉我也不一定學(xué)得會(huì)。”我轉(zhuǎn)過(guò)頭來(lái)正欲與她說(shuō)話(huà)時(shí),看見(jiàn)她用手去摸了一下車(chē)的門(mén)把手。我立即大聲地說(shuō):“別,我收下還不行嗎?”
我們直接把小九妹送到花鹿坪易地搬遷點(diǎn)的扶貧車(chē)間——中潤(rùn)服飾。成衣經(jīng)理王天美對(duì)我說(shuō):“既然錯(cuò)過(guò)了集中培訓(xùn),就邊學(xué)邊干吧,其實(shí)這活兒也不難。”看到小九妹把一只手放在背后的時(shí)候,她說(shuō),“別背著手,干活的人,首先要把手亮出來(lái)。”
我示意王天美往旁邊說(shuō)話(huà),告訴她小九妹的實(shí)際情況。王天美說(shuō):“上午劉經(jīng)理就給我說(shuō)過(guò)了,你們不是已經(jīng)溝通好了嗎?”
“那你還這樣說(shuō)!”我不解。
“我就是想讓她不要自卑。”王天美說(shuō),“只要她肯下功夫,也能掙著錢(qián)的。”
離開(kāi)服裝廠,我對(duì)小蒯說(shuō):“這只雞如何處置?”
小蒯說(shuō),“拿回去養(yǎng)著吧,反正你一個(gè)人,家里有點(diǎn)響聲沒(méi)什么不好。”
“要養(yǎng)也是你拿去養(yǎng),你家里可是從沒(méi)有過(guò)響聲吧!”
正開(kāi)著玩笑,我的手機(jī)響了起來(lái),從褲兜里掏出來(lái)一看,居然是我的老婆支小茵打來(lái)的。
“在哪里呢?”她問(wèn)。
“回來(lái)的路上,幾分鐘就到家。”我說(shuō)。我居然感覺(jué)到自己的聲音無(wú)比顫抖,像一個(gè)在老師面前接受訓(xùn)話(huà)的孩子。
“我剛在門(mén)口放了一只雞,一會(huì)兒你把它拿去菜市場(chǎng)殺了,放冰箱里凍著。”支小茵的口氣還像沒(méi)搬出去住時(shí)一樣,她“安排”我做事的時(shí)候,幾乎沒(méi)有商量的意思。
“什么?”我不敢相信,她宣告回來(lái)的方式居然是把一只不知從什么地方弄來(lái)的雞放在門(mén)口。讓我更不敢相信的是,我也正走在把一只雞送回家的路上。
“你大驚小怪干啥?”支小茵說(shuō),“人家送的。”
“我的也是人家送的。”我說(shuō)。
她大約沒(méi)聽(tīng)懂我說(shuō)的話(huà),半晌才說(shuō):“你又喝了吧?”
“沒(méi)有,我說(shuō)的是真的,我剛從村里回來(lái),人家送了我一只雞,我正要把它拿到菜市場(chǎng)里去。”我盡量讓自己說(shuō)得清楚一點(diǎn)。
支小茵馬上換了一種語(yǔ)氣和我說(shuō)話(huà),“你可別亂收人家的東西,我勸你明天一早給人送回去,老百姓原本就困難,你也不想想。”
“不是這樣的,你讓我慢慢給你解釋。”還沒(méi)說(shuō)完,那頭把電話(huà)掛了。
我把兩只雞拿去宰了,裝了兩個(gè)塑料袋,沉甸甸的。回到家,我把冰箱清理干凈,用保鮮膜把雞肉封好,塞進(jìn)冰箱,足足裝了兩格。做完這件事,我又折回菜市場(chǎng),買(mǎi)了些新鮮蔬菜回來(lái),然后給支小茵發(fā)短信:“我做好晚飯等你。”
“沒(méi)空。”她回短信神速。
“你在哪里?”我又發(fā)過(guò)去。
沒(méi)有動(dòng)靜。晚上,我照例點(diǎn)了外賣(mài),胡亂填飽肚子,早早就躺倒床上去,正準(zhǔn)備打一個(gè)文天嬌的電話(huà)試試她在哪里,不想她先打了過(guò)來(lái)。
“你去了哪里?”我問(wèn)。
“你先告訴我,你為什么要祝我天天有一個(gè)好心情。”文天嬌一句話(huà)讓我差點(diǎn)從床上摔下來(lái)。
“你這人怎么這樣?我都說(shuō)清楚了,我沒(méi)有給你發(fā)過(guò)短信。”我說(shuō)。
“那你告訴我,這條短信是誰(shuí)發(fā)的?”
“我怎么知道是誰(shuí)發(fā)的?我要知道,我早就告訴你了。”
“我想了好久,這條短信應(yīng)該不是孩子他爹發(fā)的,他和我從來(lái)沒(méi)有這么客氣過(guò),我們總是一說(shuō)話(huà)就吵架。”
“你為什么老是糾結(jié)這條短信呢?你一定要相信,真的有可能是別人發(fā)錯(cuò)了手機(jī)號(hào)碼。”我講到這里,突然覺(jué)得有必要問(wèn)文天嬌一個(gè)事,于是我說(shuō),“你的手機(jī)卡是什么時(shí)候買(mǎi)的?”
“五年前吧,當(dāng)時(shí)我們從浙江回來(lái)修房子,不想用外省號(hào)碼,太貴,于是就重新辦了這張卡。剛開(kāi)始的時(shí)候,是孩子他爹在用,后來(lái)他要出門(mén),就留給我了。”文天嬌說(shuō)完,又問(wèn),“你問(wèn)這個(gè)干嗎?”
“我就是想知道,會(huì)不會(huì)是別人給你老公發(fā)的短信。”我說(shuō),“你從來(lái)沒(méi)有給這個(gè)發(fā)短信的號(hào)碼打過(guò)電話(huà)嗎?其實(shí),只要你打個(gè)電話(huà),裝作找人,順便就可以問(wèn)他是誰(shuí)了。”
“我沒(méi)這么賤。”文天嬌說(shuō),“我是一個(gè)規(guī)矩的女人,我怕人家認(rèn)為我是送上門(mén)去。”
“那,你給我打電話(huà)的時(shí)候,怎么沒(méi)有這樣的顧慮?你不是一直懷疑這條短信是我發(fā)的嗎?”我想文天嬌肯定是在騙我。
“如果是你發(fā)的,我就原諒你。”文天嬌說(shuō),“你是國(guó)家干部,又扶貧我們家,我得忍著。”
我在被文天嬌搞得哭笑不得的同時(shí),心里突然蹦出一條線索:如果能找到給文天嬌發(fā)短信的那個(gè)人,說(shuō)不定就能找到她的丈夫。
我給公安局的朋友打電話(huà),告訴他我的貧困戶(hù)吳建敏五年前失蹤了,我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重要的電話(huà)號(hào)碼,完全有可能通過(guò)這個(gè)電話(huà)號(hào)碼找到一些線索。我的朋友問(wèn)我,“為什么不報(bào)案?”
我說(shuō),“人失蹤的時(shí)候,他們家還不是我包保。后來(lái),他的家人不愿意報(bào)案,說(shuō)實(shí)話(huà),我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故意玩失蹤。”
那頭說(shuō),“你這個(gè)人啊,這么大的事情居然捂到現(xiàn)在,酒喝多了吧!”
我說(shuō),“實(shí)際情況是這樣的,他或許是為了躲債,故意跑到什么地方藏起來(lái)了。”
第二天上午,公安局的朋友通過(guò)移動(dòng)公司查到了那個(gè)發(fā)短信的電話(huà)號(hào)碼,出乎意料,號(hào)碼的主人居然是河對(duì)門(mén)的甘巾巾。我感覺(jué)事情的真相很快就要浮出水面,卻又不知道怎么去揭開(kāi)謎底。我問(wèn)公安局的朋友該怎么辦,他說(shuō),“還是先報(bào)案吧。”
“我做不了主。”我說(shuō)。
6
小九妹的公公在村口堵住我。我正要去王必藍(lán)家走訪,不想剛下車(chē)就遇到這個(gè)叫張世仁的老者。
“我說(shuō)你這個(gè)縣干部,盡出餿主意,你把小九妹弄到城里去,把一大坡莊稼留給我,我哪收得住?”
“好大一坡莊稼!”我說(shuō),“你們家攏共就兩畝地,就算是精耕細(xì)作也花不了多少時(shí)間,再說(shuō),村里人誰(shuí)不知道,你是種懶莊稼出了名的,平常薅草都怕鋤頭喊痛。”
“亂球說(shuō)!你扶貧沒(méi)扶出什么道理,小道消息倒是掌握了不少。”張世仁把他種懶莊稼的事稱(chēng)為“小道消息”,倒是頗具幾分幽默感。我說(shuō),“那我問(wèn)你,人們?yōu)槭裁匆心恪K死人’?”
“我都快七十歲了,你一點(diǎn)也不客氣地和我開(kāi)玩笑,怕不怕雷響?”他說(shuō)的“雷響”,指的是天上的雷公。我說(shuō),“您老別介意,我是你家的扶貧干部,咱們算是一家人。再說(shuō),你現(xiàn)在獨(dú)自一人在家,與人開(kāi)開(kāi)玩笑,日子就會(huì)熱鬧一些。”
“隨你說(shuō)了。”張世仁笑笑,“不過(guò)你好像忘記了一件事情。”
“沒(méi)忘記。”我說(shuō),“豬崽我已幫你買(mǎi)好了,兩頭,明天就會(huì)有人給你送來(lái)。”
“真的嗎?”他似乎不太相信。
“真的。”我說(shuō),“扶貧干部說(shuō)到做到,兩頭豬崽活蹦亂跳,擔(dān)心你養(yǎng)出了感情,長(zhǎng)大了舍不得殺。”
“兩頭倒是舍不得殺,如果是三頭的話(huà),就好處理了。”老者開(kāi)的這個(gè)玩笑,不完全是一個(gè)玩笑。
“那又是什么道理呢?”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說(shuō),“你一生精明,就是忘記好好教育教育孩子,導(dǎo)致老了老了還為生計(jì)奔波。”
“唉,現(xiàn)在有人替我去教育了。”老者收了笑容,接著說(shuō),“真是臟死人。”
到王必藍(lán)家,見(jiàn)檐坎上趴著一臺(tái)被拆成兩半的微耕機(jī),王必藍(lán)的丈夫徐大榜正用一把鉗子在上面擰著螺絲。我上前打招呼:“榜爺何時(shí)成為修理工了?”
“這老伙計(jì)早就散架,八成修不好了,我也是死馬當(dāng)活馬醫(yī)。”他讓他老婆王必藍(lán)給我倒杯水,然后直接坐在一截鐵耙上,說(shuō),“娃娃些讀書(shū)費(fèi)錢(qián),能節(jié)約就盡量節(jié)約,要不,我也去買(mǎi)一臺(tái)新的。”
我知道王必藍(lán)家種了很多地,全是從那些外出打工的村民手中租過(guò)來(lái)的。王必藍(lán)家的地姓張,房子姓張,山包包周?chē)缤砩饋?lái)的炊煙,同樣也姓張。當(dāng)初,他們一家成為我的包保戶(hù)的時(shí)候,我問(wèn)村里的掛片干部,為什么這家人的戶(hù)主是王必藍(lán)。掛片干部李顯定告訴我,王必藍(lán)之前的丈夫叫張世江,在一場(chǎng)車(chē)禍中死掉了,現(xiàn)在的丈夫徐大榜是從鄰村團(tuán)山過(guò)來(lái)的,之前沒(méi)有婚配,整整小王必藍(lán)十歲。
“也就是說(shuō),他和王必藍(lán)承擔(dān)起了撫養(yǎng)幾個(gè)大學(xué)生的壓力?”我對(duì)李顯定說(shuō),“這人真值得佩服。”
李顯定說(shuō),“要不人都稱(chēng)他為榜爺呢!”
成為這家人的包扶干部以來(lái),我為他們辦了很多事,這讓我感到無(wú)比欣慰。王必藍(lán)有四個(gè)孩子,大兒子已經(jīng)大學(xué)畢業(yè),在家復(fù)習(xí)功課,準(zhǔn)備考工作,中間兩個(gè)女兒在讀大學(xué),最小的一個(gè)兒子現(xiàn)在已念到高三。王必藍(lán)一家的經(jīng)濟(jì)收入,除了靠丈夫徐大榜在周?chē)蛞稽c(diǎn)零工之外,就是王必藍(lán)自己張羅那十來(lái)畝從鄰居家租過(guò)來(lái)的土地了。徐大榜干的活計(jì),是給人家的新房做墻體,也算是裝修活,但是,他能干好的,也只是墻體工程的第一道工序,就是用水泥砂漿往墻上打底,干了五六年,到現(xiàn)在連上膩?zhàn)臃鄱疾粫?huì)。天氣太熱的時(shí)候,徐大榜沒(méi)什么活兒干,因?yàn)樗嗌皾{敷到墻上去容易開(kāi)裂;天氣太冷的時(shí)候,徐大榜也沒(méi)什么活兒干,因?yàn)樗嗌皾{不容易干。徐大榜一年下來(lái),平均每個(gè)月掙不到兩千塊錢(qián)。王必藍(lán)種地,種的是玉米、土豆,春天下種,秋天收割,中途照顧莊稼的環(huán)節(jié)潦草而隨意,產(chǎn)量也就很隨意。王必藍(lán)請(qǐng)人用拖拉機(jī)把玉米和土豆運(yùn)到街上去賣(mài),拖拉機(jī)往家里走三四個(gè)來(lái)回,糧倉(cāng)就空了。糧食賣(mài)了錢(qián),給讀大學(xué)和高中的幾個(gè)孩子匯到銀行卡上,截留一點(diǎn),買(mǎi)些鹽巴、洗衣粉,就沒(méi)有了。王必藍(lán)種一年的莊稼,最多夠孩子們撐一兩個(gè)月,缺口的錢(qián),靠的是徐大榜的零工收入,靠的是找親戚朋友借。徐大榜的收入上不去,親戚朋友也都借遍了,就再也沒(méi)什么辦法,王必藍(lán)只能坐在檐坎上發(fā)愁。我去走訪的時(shí)候,王必藍(lán)對(duì)我說(shuō),“蘇同志,你要是能幫我再貸點(diǎn)款,你就真的是在扶貧了。”
“去信用社申請(qǐng)了嗎?”我問(wèn)。
“幾年前貸的,現(xiàn)在都還沒(méi)還。”王必藍(lán)說(shuō)。
我問(wèn):“助學(xué)貸款呢?”
“辦了,但不夠。”我發(fā)現(xiàn)王必藍(lán)六神無(wú)主的時(shí)候,喜歡用食指和拇指拈自己的額頭,此時(shí),她的額頭已經(jīng)被拈得紅撲撲的了。
我想了想,對(duì)王必藍(lán)說(shuō),“要不,我來(lái)想辦法吧。”
想什么辦法呢?只不過(guò)是暫時(shí)讓王必藍(lán)放下心來(lái)而已。以我的能力,肯定無(wú)法支撐起這個(gè)家的超負(fù)荷運(yùn)轉(zhuǎn),眼下最要緊的,是趕緊會(huì)同駐村工作隊(duì)的張青他們進(jìn)行研判。研判到深夜,解決了一些問(wèn)題,即為他們家爭(zhēng)取了兩個(gè)低保名額。這當(dāng)然不是長(zhǎng)久之計(jì),張青和我達(dá)成了一致:把王必藍(lán)家的土地變個(gè)用途。
“種草?”王必藍(lán)一副無(wú)比吃驚的樣子,“種莊稼都變不了幾個(gè)錢(qián),草還能賣(mài)到大城市的超市里去?”
“種草養(yǎng)牛。”我說(shuō),“牛肉貴,農(nóng)村散養(yǎng)的牛,宰了更貴。”
王必藍(lán)用手指拈了拈額頭,說(shuō),“我哪有錢(qián)買(mǎi)小牛!”
我說(shuō),“只要你肯干,小牛的錢(qián)我出,平時(shí)買(mǎi)飼料的錢(qián)我也出,你把牛養(yǎng)大了賣(mài)掉,然后再還我的錢(qián)。”
幾年下來(lái),王必藍(lán)家漸漸有起色了,每年能賣(mài)三頭壯牛,可以?huà)甑眉兪杖虢鼉扇f(wàn)塊。王必藍(lán)每年都要把我借給她的錢(qián)還我,我說(shuō),你先用著,反正我也沒(méi)啥用處。王必藍(lán)問(wèn)我,“你老婆——我兄弟媳婦不知道吧?”
“知道。”我說(shuō),“我能搞定。”
“你們也要撫孩子讀書(shū),會(huì)花很多錢(qián)的。”王必藍(lán)說(shuō)。
“我們沒(méi)有孩子。”我把話(huà)題岔開(kāi),“我想給榜爺重新介紹一個(gè)工作,不知他肯不肯。”
“什么工作?”王必藍(lán)問(wèn)。
“去城里給人洗車(chē),我朋友的洗車(chē)場(chǎng)。”我說(shuō)。
我朋友沒(méi)開(kāi)洗車(chē)場(chǎng),我甚至對(duì)這個(gè)世界上的洗車(chē)場(chǎng)幾乎沒(méi)有什么了解,我這樣對(duì)王必藍(lán)說(shuō),真的只是想把話(huà)題引開(kāi)。那些日子,我經(jīng)常在單位廁所的隔間里聽(tīng)到同事們?cè)谧h論我和我的老婆支小茵無(wú)法生孩子的事,我的內(nèi)心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當(dāng)然,洗車(chē)這活兒很累,要不,我再想想,明天再商量。”我想抬腿走人,然而王必藍(lán)叫住了我,說(shuō),“洗車(chē)可以,只要一年四季每天都有活兒干。”
我說(shuō):“我再考慮考慮。”
徐大榜后來(lái)當(dāng)然沒(méi)有去洗車(chē),而是繼續(xù)干他的老本行,只不過(guò)我把他弄到鎮(zhèn)上的施工隊(duì)里去了,鎮(zhèn)上這些年有很多易地搬遷和農(nóng)村危房改造項(xiàng)目,一年四季都有活干。徐大榜去了施工隊(duì),才知道天氣再熱或者再冷都能干墻體工程,只是干法不同而已。
徐大榜想把那臺(tái)壞掉的微耕機(jī)修好,是要給他的老婆王必藍(lán)“整理”一下草地。徐大榜說(shuō),土地都快長(zhǎng)老繭了,草種撒下去,有一半生不出來(lái)。
我問(wèn)蹲在徐大榜旁邊給他遞工具的王必藍(lán),“前些日子你父親過(guò)世,河對(duì)門(mén)是不是有一個(gè)叫劉寬兒的人過(guò)來(lái)幫忙?”
王必藍(lán)說(shuō),“劉寬兒是我表弟,舅舅家的小兒子,肯定是來(lái)了,你找他,是為了打聽(tīng)吳建敏的下落吧?”
“你怎么知道?”
“我表弟當(dāng)著很多人的面說(shuō)甘巾巾在江蘇見(jiàn)過(guò)吳建敏,你一問(wèn),我就知道是這個(gè)事?”
“你表弟會(huì)說(shuō)瞎話(huà)嗎?”
“他這輩子說(shuō)的瞎話(huà)不少,不過(guò),甘巾巾見(jiàn)過(guò)吳建敏的事,怕是無(wú)風(fēng)不起浪。”
我又覺(jué)得這件事不好再問(wèn)下去了,因?yàn)槲覐耐醣厮{(lán)的語(yǔ)氣里聽(tīng)出吳建敏和甘巾巾之間是存在著微妙的關(guān)系的,我怕一不小心讓這件事情生出別的枝節(jié)來(lái),到時(shí)候激化矛盾,不好收?qǐng)觥N艺f(shuō):“你表弟這個(gè)人,倒是幽默得很。”
剛從王必藍(lán)家出來(lái),我就接到支小茵的電話(huà),她說(shuō):“不能讓冰箱里的兩只雞臭了,你今天回去,把它們燉掉。”
“你要回來(lái)了嗎?”我迫不及待地問(wèn)。
“就算我回來(lái),也吃不完這么多雞肉。我是說(shuō),你把他們燉了,買(mǎi)一個(gè)帶蓋兒的塑料桶裝好,明早我?guī)ё摺!?/p>
“帶哪里去?”我問(wèn)。
“別問(wèn)這么多。”支小茵說(shuō),“燉了便是。對(duì)了,少擱點(diǎn)鹽。”
支小茵第二天一早就給我打電話(huà),要我把煮熟的雞肉送到樓下去。我拎著塑料桶下樓,看見(jiàn)支小茵從一輛轎車(chē)?yán)锷斐瞿X袋,對(duì)我說(shuō)了一句“辛苦了”,便讓開(kāi)車(chē)的師傅下車(chē),從我手里接過(guò)桶子,放在后尾箱里,然后用幾個(gè)裝滿(mǎn)表冊(cè)的紙箱把桶子固定,關(guān)上尾箱門(mén)。司機(jī)上車(chē)之前,過(guò)來(lái)握了我的手,說(shuō),“蘇哥辛苦了。”
車(chē)開(kāi)走后,支小茵給我發(fā)短信,“我們今天開(kāi)展大走訪,我要好好犒勞我的隊(duì)員們。”
“什么走訪?”我問(wèn)。
她回:“我去單位的扶貧村對(duì)塔了,我現(xiàn)在是駐村工作隊(duì)長(zhǎng)。”
一會(huì)兒她又發(fā)來(lái)一句:“我是全縣唯一的女工作隊(duì)長(zhǎng),你驕傲嗎?”
我沒(méi)說(shuō)話(huà)。
7
文天嬌在三天后回到家。她沒(méi)去浙江,甚至沒(méi)有離開(kāi)過(guò)本縣,她去了一趟隔壁的花郎鎮(zhèn),因?yàn)樗?tīng)說(shuō),甘巾巾其實(shí)沒(méi)有同劉寬兒他們一起去安徽,而是在她的娘家,那天在河對(duì)面見(jiàn)到的那個(gè)男子其實(shí)就是甘巾巾的男人,他和他的弟弟是雙胞胎,長(zhǎng)得很像。
“他為什么要對(duì)我們?nèi)鲋e?”我問(wèn)文天嬌。
“誰(shuí)曉得!”甘巾巾說(shuō),“前些年在浙江,他們兩口子在我們的工地上做工,工資從來(lái)都沒(méi)有拖欠過(guò),有時(shí)候還給他們預(yù)支過(guò)錢(qián)哩。”
“這么說(shuō),他們應(yīng)該感恩才對(duì)。”我說(shuō)。
“八成是甘巾巾這個(gè)狐貍精作的怪吧,她男人就是一個(gè)尖腦殼,常年戴著綠帽子過(guò)日子的。”文天嬌越說(shuō)越氣憤。
我還是不明白,甘巾巾的男人為什么要隱瞞甘巾巾的行蹤;文天嬌的丈夫吳建敏這些年來(lái)杳無(wú)音訊,與甘巾巾的娘家居住地花郎鎮(zhèn)有什么聯(lián)系;吳建敏失蹤四年后,甘巾巾為什么要給文天嬌發(fā)來(lái)一條“祝你天天有個(gè)好心情”的短信——我更弄不明白的是,甘巾巾的那條短信,到底是發(fā)給之前使用過(guò)這個(gè)電話(huà)號(hào)碼的吳建敏,還是現(xiàn)在握著這張電話(huà)卡的文天嬌。
可以肯定的是,文天嬌在花郎鎮(zhèn)并沒(méi)有找到甘巾巾。甘巾巾有沒(méi)有去安徽,其實(shí)文天嬌也不知道,文天嬌只是聽(tīng)說(shuō),聽(tīng)誰(shuí)說(shuō)呢?這一次,文天嬌說(shuō)的是她做了一個(gè)夢(mèng),在夢(mèng)里對(duì)她說(shuō)這些話(huà)的,還是劉寬兒。
“你相信一個(gè)夢(mèng),我就無(wú)語(yǔ)了。”我說(shuō)話(huà)很小聲,但還是被文天嬌聽(tīng)到了。她幾乎是氣急敗壞,指著我的鼻子大聲說(shuō):“我干什么要你管嗎?是你自己非要多管閑事,我家的事和你有什么關(guān)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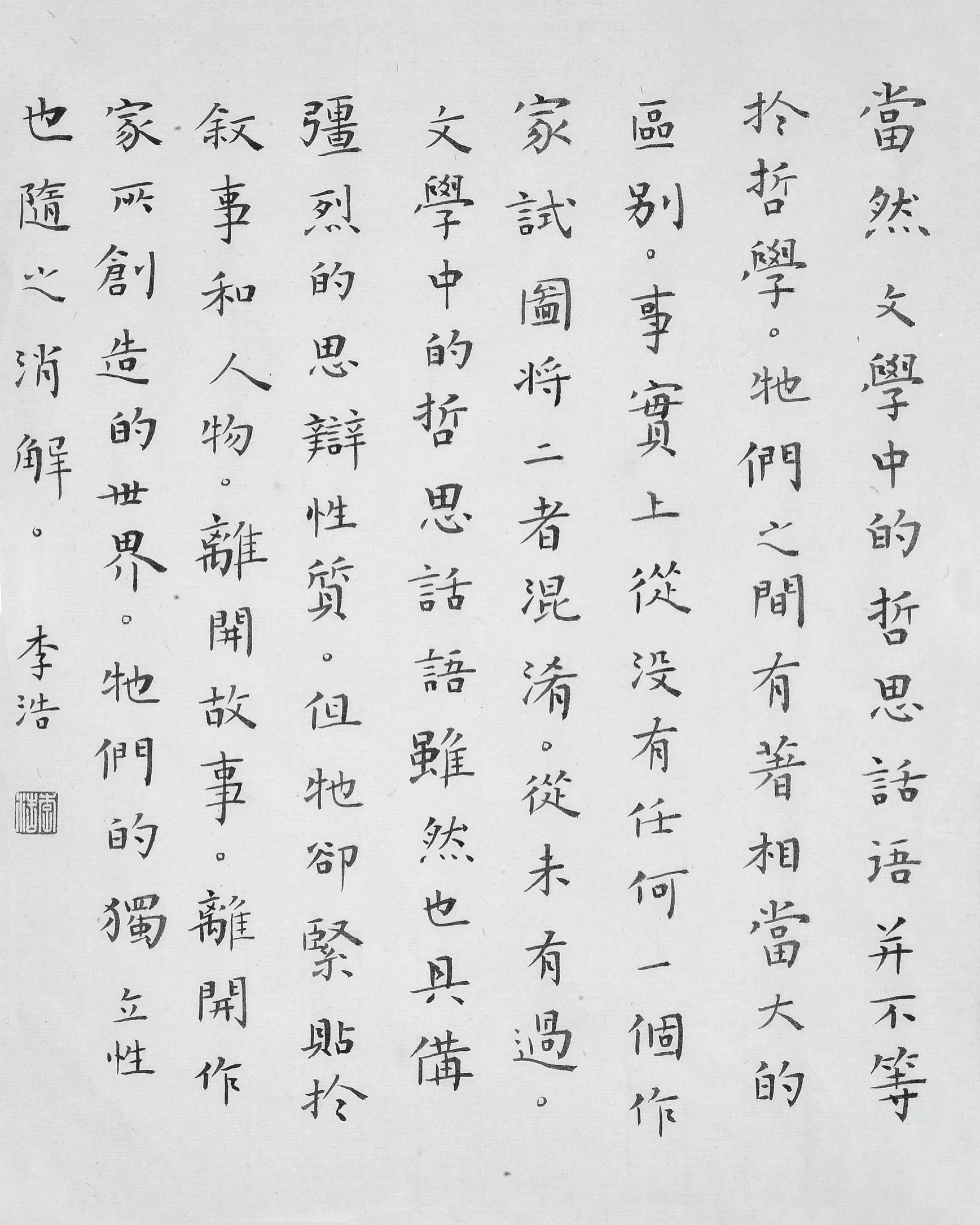
李浩 書(shū)法
“就憑我是你們家的包保干部。”我的聲音也大了起來(lái)。
“包保干部有什么了不起的?包保干部就能插手別人的家事嗎?”文天嬌說(shuō)完,蹲在院子里哭了起來(lái),哭得撕心裂肺,讓周?chē)拇迕駠^(guò)來(lái)了好多。
我在這個(gè)時(shí)候接到了支小茵打來(lái)的電話(huà)。
“很意外吧?我駐村了。”支小茵說(shuō)。
“我現(xiàn)在沒(méi)空,我得先處理一樁非常棘手的事情。”我說(shuō)。
“是那個(gè)丟了丈夫的女人嗎?”
“你怎么知道?”
“就你不關(guān)心我的事,我可一直掌握著你的一舉一動(dòng)。”
“老婆,我想哭。”我的鼻子發(fā)酸,眼淚已經(jīng)流出來(lái)了。
“別矯情,你一個(gè)男子漢,學(xué)學(xué)你的女人,堅(jiān)強(qiáng)一些。”支小茵在電話(huà)里笑。
“我不是為包保戶(hù)的事,而是因?yàn)槟恪!蔽艺f(shuō),“原來(lái)你說(shuō)的搬出去住,是下沉了。”
“當(dāng)然啦,我只是想在考驗(yàn)我自己的同時(shí)好好考驗(yàn)?zāi)悖绻F(xiàn)在還那么一蹶不振,每天靠喝酒來(lái)逃避現(xiàn)實(shí),我就不會(huì)給你打電話(huà)。”
“我……”我強(qiáng)忍著,盡量讓自己不哽咽,我不知道支小茵什么時(shí)候掛了電話(huà)。
文天嬌還在院子里哭,她把嗓子都哭啞了。周?chē)拇迕駥?duì)她說(shuō),“文妹兒,你還是報(bào)案吧!”
“文妹兒,不要擔(dān)心,吳建敏福大命大,不會(huì)出事的,小時(shí)候從馬背上摔下來(lái),掉進(jìn)山茅廁里,滿(mǎn)坑的糞便和臟水,硬是沒(méi)把他淹死。”
王必藍(lán)把文天嬌從地上扶起來(lái),對(duì)她說(shuō):“不怕,不怕,不怕……”周?chē)娜藗円舱f(shuō):“不怕,不怕,不怕……”
我對(duì)文天嬌說(shuō):“不怕,不管遇到什么問(wèn)題,有我在。”
“有你在,就什么問(wèn)題都不是問(wèn)題了。”晚上開(kāi)研判會(huì)的時(shí)候,張青半開(kāi)玩笑地對(duì)我說(shuō),“蘇哥歷來(lái)都有逢兇化吉的本領(lǐng),蘇哥解決疑難雜癥的能力首屈一指。”
“怎么解決?”我說(shuō),“文天嬌家的問(wèn)題,現(xiàn)在不是怎么幫她發(fā)展生產(chǎn)擺脫貧困的問(wèn)題,而是怎么幫助她解除心魔的問(wèn)題,說(shuō)白了,就是想辦法幫她把丈夫找回來(lái)。”
“這個(gè)恐怕要依賴(lài)公安部門(mén)了。”李顯定說(shuō),“萬(wàn)一查出來(lái)的結(jié)果文天嬌不能接受呢?”
“我看這個(gè)結(jié)果短時(shí)間內(nèi)出不來(lái)。”張青說(shuō),“不瞞大家,前些日子公安局在查那個(gè)發(fā)短信的號(hào)碼的時(shí)候,就同步啟動(dòng)這個(gè)案子了。”
對(duì)張青所說(shuō)的話(huà),我也沒(méi)有感到意外。其實(shí),當(dāng)時(shí)我也對(duì)公安局的朋友說(shuō):“文天嬌雖然沒(méi)報(bào)案,但我作為他們家的包保干部,我得嚴(yán)肅地向公安部門(mén)反映這個(gè)事情,有必要的話(huà),我可以寫(xiě)一份詳細(xì)的文字材料。”
工作隊(duì)長(zhǎng)張青怕我有顧慮,私下把材料寫(xiě)好交到公安局,并三天兩頭追問(wèn)進(jìn)展情況,得到的回答是:暫時(shí)沒(méi)有線索。
“文天嬌的事,是目前我們整個(gè)工作隊(duì)必須高度重視的事。文天嬌的丈夫吳建敏一天不現(xiàn)身,文天嬌的三個(gè)孩子在學(xué)校里就會(huì)一天心神不寧,文天嬌的這個(gè)家就會(huì)隨時(shí)散架。”張青說(shuō),“我建議,明天我們都去一趟花郎鎮(zhèn),當(dāng)然,去花郎鎮(zhèn)之前,得先去會(huì)會(huì)甘巾巾的老公陳大才。”
陳大才蹲在墻根腳不說(shuō)話(huà)。六月天,他還穿著那件皮夾克,臉上滿(mǎn)是汗水。我問(wèn)他,關(guān)于甘巾巾現(xiàn)在在哪里的這件事,你有沒(méi)有對(duì)我們說(shuō)謊?陳大才說(shuō),我沒(méi)說(shuō)謊,她的確是和劉寬兒他們一起走的,而且真的是去安徽。我又問(wèn),前段時(shí)間,甘巾巾還沒(méi)離開(kāi)家的時(shí)候,她真的沒(méi)有告訴過(guò)你她在江蘇見(jiàn)過(guò)吳建敏嗎?
陳大才猶豫了,半天沒(méi)有說(shuō)話(huà)。我又問(wèn),是不是她說(shuō)的時(shí)候你沒(méi)當(dāng)回事?陳大才的嘴唇動(dòng)了動(dòng),但還是沒(méi)開(kāi)口。張青在一旁說(shuō),我們只是想了解吳建敏現(xiàn)在在哪里,這件事很重要。你要是說(shuō)真話(huà),對(duì)于我們找到他有很大的幫助。你如果知道了也不說(shuō),下步只能是公安局的同志來(lái)問(wèn)你,你知道,對(duì)警察說(shuō)謊,是犯罪。
陳大才從墻根下站起來(lái),拍拍兩手,用一只手把皮衣里層撩起來(lái),揩了揩臉上的汗水,說(shuō),甘巾巾的確說(shuō)過(guò),她見(jiàn)過(guò)吳建敏。
“什么時(shí)候?”我問(wèn)。
“我沒(méi)有仔細(xì)問(wèn)她。”陳大才說(shuō),“我不想知道這些事情。”
“那你現(xiàn)在可不可以給甘巾巾打一個(gè)電話(huà),問(wèn)問(wèn)她什么時(shí)候見(jiàn)到的吳建敏,她見(jiàn)到他的時(shí)候,他在干什么?”
一聽(tīng)說(shuō)電話(huà),陳大才就開(kāi)始慌張起來(lái),臉上的汗水一顆顆往下掉。我問(wèn):“陳大才,你怎么這么緊張?”
陳大才再次用皮衣里子揩了揩汗水,改口說(shuō):“其實(shí),她沒(méi)說(shuō)過(guò)?”
“什么意思?”我問(wèn)。
“甘巾巾沒(méi)說(shuō)過(guò)她在江蘇見(jiàn)過(guò)吳老板,是我說(shuō)的。”陳大才說(shuō)。
“你為什么要這樣說(shuō)?”張青情緒有些激動(dòng),他說(shuō)話(huà)的語(yǔ)氣,讓人覺(jué)得他像一個(gè)警察。
“我亂說(shuō)的。”陳大才說(shuō),“我去年沒(méi)去打工,一直呆在家里,我弟弟陳大錢(qián)打電話(huà)告訴我,前幾年在浙江的時(shí)候,甘巾巾背著我和吳老板去開(kāi)賓館。我想,這女人去江蘇打工,八成是去找吳老板去了。”
“你又是怎么知道吳建敏在江蘇的?”張青問(wèn)陳大才。
“我弟弟說(shuō)的。”陳大才看了張青一眼,全身直哆嗦。“我弟弟說(shuō),吳老板那年回來(lái)修完房子,臨出門(mén)時(shí)問(wèn)過(guò)他,要不要去江蘇一起干工程。”
我和張青現(xiàn)在基本統(tǒng)一了思想,就是根本不用再去花郎鎮(zhèn)。但是,要怎樣才能找到吳建敏呢?我們始終拿不出一套完整的方案來(lái)。眼下最要緊的,是回去后立即告訴文天嬌,吳建敏并沒(méi)有丟,他很有可能就是在江蘇,至于在江蘇干什么,為何不與家里人聯(lián)系,我們暫時(shí)還沒(méi)想好怎么說(shuō)。
“那條短信到底是發(fā)給誰(shuí)的?”張青問(wèn)我有沒(méi)有線索。
“初步斷定,應(yīng)該是甘巾巾發(fā)給吳建敏的。”我說(shuō),“你沒(méi)聽(tīng)到陳大才說(shuō)嗎,甘巾巾和吳建敏關(guān)系不一般。”
“那也不一定。”張青說(shuō)。
隨后,我就從公安局的朋友那里得知,他們已經(jīng)在頭天晚上見(jiàn)過(guò)陳大才,且已經(jīng)從他那里掌握了我們今天掌握的信息。難怪這家伙見(jiàn)到我們的時(shí)候會(huì)如此緊張,我在心里說(shuō)。但我始終沒(méi)搞明白,警察已經(jīng)問(wèn)過(guò)陳大才一次了,為何他剛開(kāi)始的時(shí)候,還要對(duì)我們?nèi)鲋e?對(duì),他肯定還有什么沒(méi)有告訴我們。晚上,我一個(gè)人去了陳大才家。陳大才沒(méi)有開(kāi)燈,但屋里的電視機(jī)開(kāi)著。我敲門(mén)的時(shí)候,陳大才碰翻了他坐的那條板凳,慌慌張張地過(guò)來(lái)開(kāi)門(mén)。見(jiàn)是我一個(gè)人,便問(wèn):“又有什么事?”
我說(shuō):“再聊聊吧,我感覺(jué)白天你沒(méi)有把話(huà)說(shuō)完。”
陳大才看了我好一陣子,才說(shuō):“其實(shí),我對(duì)劉寬兒說(shuō)甘巾巾在江蘇見(jiàn)過(guò)吳老板,目的是讓他說(shuō)給別人聽(tīng)。”
“你是想試試甘巾巾有什么反應(yīng),對(duì)不對(duì)?結(jié)果呢?”我為了讓氣氛緩和一些,我接著說(shuō),“你也是一個(gè)聰明人,知道怎么收拾女人。”
“結(jié)果她什么反應(yīng)也沒(méi)有,從來(lái)沒(méi)和我談?wù)撨^(guò)這件事。”陳大才說(shuō)。
“那條短信是不是你發(fā)的?”我問(wèn)完,故意把頭轉(zhuǎn)到電視機(jī)的方向,裝作是不經(jīng)意的一問(wèn),或者說(shuō),我想告訴他,其實(shí)這條短信是不是他發(fā)的根本不重要。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居然馬上就回答我說(shuō):“是我發(fā)的,我趁甘巾巾不注意,就用她的手機(jī)給吳老板發(fā)了這么一條短信,我其實(shí)是想知道吳老板會(huì)回一條什么短信,但我沒(méi)想到,吳老板已經(jīng)沒(méi)有用這個(gè)號(hào)碼了。”
我真得差點(diǎn)開(kāi)心得笑出了聲來(lái),我為自己睿智的“問(wèn)話(huà)”感到些許得意。但我突然想到,如果每一個(gè)讓老婆外出打工的男人都像陳大才這樣竭盡心思去試探自己的女人,這世界還不亂成一團(tuán)糟!于是,我又有一絲難過(guò)。這世界,到底有多少婚姻是值得信賴(lài)和肯定的?我自己呢?我的婚姻現(xiàn)在是一個(gè)什么狀態(tài)?我自己也說(shuō)不清楚。我的老婆支小茵在我喝酒解壓的那段時(shí)間搬出去住,會(huì)不會(huì)真的如她所說(shuō)的“下沉”到村里去了?或許,她還有什么事情瞞著我。
“我昨晚上已經(jīng)對(duì)警察說(shuō)過(guò)了,警察說(shuō),發(fā)一條短信沒(méi)有什么大不了的,構(gòu)不成犯罪。”陳大才這么一說(shuō),又讓我無(wú)比受挫——原來(lái)我一直都是后知后覺(jué),我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反應(yīng)遲緩,當(dāng)然,從我對(duì)生活的態(tài)度上可以斷定,我謹(jǐn)小慎微,缺乏自信,我不是一個(gè)在遇到困難時(shí)可以當(dāng)機(jī)立斷的人。
“這事也需要重新去問(wèn),你真是笨到家了。”我回到村部的時(shí)候,張青對(duì)我說(shuō),“陳大才用甘巾巾的手機(jī)給文天嬌發(fā)了這么一條短信,對(duì)于能不能找到吳建敏根本沒(méi)什么用。”
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著,就給支小茵打電話(huà):“你在哪里駐村?”
支小茵說(shuō):“你終于想起問(wèn)我了,我告訴你吧,我在花郎鎮(zhèn)的對(duì)塔村。其實(shí)昨天早上在車(chē)上的時(shí)候我就告訴過(guò)你,只是你那時(shí)根本就是一副心神不寧的樣子。”
“你知道我攤上了一戶(hù)非常難搞的貧困戶(hù),我這段時(shí)間壓力真的好大。”我說(shuō)。
“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個(gè)女人把自己的丈夫丟了嗎?我都駐村快三個(gè)月了,你也全然不知道我的去向嘛,要不是我調(diào)轉(zhuǎn)馬頭,你也快把我丟了。”支小茵說(shuō)。
“但我想知道,這段時(shí)間我們之間到底有沒(méi)有發(fā)生別的事?”我說(shuō)。
“你說(shuō)的是什么事?”支小茵問(wèn),“你是想問(wèn)我倆之間有沒(méi)有第三個(gè)人?”
我說(shuō)不出話(huà)來(lái)。說(shuō)實(shí)話(huà),他這一反問(wèn),真把我問(wèn)住了,我甚至不敢肯定我要表達(dá)的是不是這個(gè)意思。然而支小茵并沒(méi)有生氣,反倒是用一種開(kāi)玩笑似的語(yǔ)氣對(duì)我說(shuō):“當(dāng)然有,我可以告訴你,她的名字叫文天嬌,三個(gè)月以前,你給她發(fā)過(guò)一條短信。”
“我沒(méi)有。”我說(shuō),“是一個(gè)叫陳大才的男人發(fā)的,他……”我還沒(méi)說(shuō)完,支小茵在那頭已經(jīng)笑得不行,笑夠了,才說(shuō),“我當(dāng)然知道不是你發(fā)的,你有不起這個(gè)膽子。”
我也笑。我和我的老婆很久很久沒(méi)有這么說(shuō)話(huà)了,今天晚上,我們?cè)谔接懼鴦e人的事情的同時(shí),也順便探討了我們自己。說(shuō)實(shí)話(huà),我真的很開(kāi)心,這一刻,文天嬌丟了男人的事情可以暫時(shí)放一放,我和支小茵必須在電話(huà)里好好溫存一番。
支小茵說(shuō):“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我前些日子去省城的醫(yī)院看了,是我的問(wèn)題。”
“你——”我沒(méi)有準(zhǔn)備,她說(shuō)出這句話(huà)的時(shí)候,我內(nèi)心無(wú)比復(fù)雜。
“其實(shí),我還想告訴你,我這不是第一次去醫(yī)院看身體了,咱們結(jié)婚三年后,我就一直在跑醫(yī)院。之所以我要告訴你我這一次去醫(yī)院的事情,是醫(yī)生終于為我找到了病根,而且還為我開(kāi)出了處方。”支小茵嘆了一口氣,接著說(shuō),“我都想好了,如果這次還治不好,我倆就離婚,我不能耽誤了你。”
仿佛這個(gè)家一下子發(fā)生了好多事情,我甚至有一種從來(lái)沒(méi)有真正參與過(guò)支小茵的生活的感覺(jué)。這些年,她一直走在尋醫(yī)求藥的路上,我竟然不知道。最不可思議的是,支小茵的小心思最終爆發(fā)成一種預(yù)謀,讓我不便接受。我甚至激動(dòng)得快要怒吼,但我還是克制住了自己,溫和地詰問(wèn)她:“這么多年來(lái),你為什么不告訴我?你難道沒(méi)有想過(guò)是我的問(wèn)題嗎?”
支小茵說(shuō),“我一直以來(lái)對(duì)你都心存感激,你沒(méi)有去看身體,說(shuō)明你對(duì)我很在意,你很看重我們的婚姻。”
“但是我后悔了。”我說(shuō),“我早就應(yīng)該去看的,我們現(xiàn)在結(jié)婚十年了,你看了七年的病,而我居然不知道,我現(xiàn)在才明白,我對(duì)你是那么不負(fù)責(zé)任。”
“但問(wèn)題確實(shí)是出在我身上,你當(dāng)初要是去看了,會(huì)一直飽受煎熬。”支小茵的語(yǔ)氣充滿(mǎn)了自責(zé),“你現(xiàn)在終于知道了吧,我就是一個(gè)無(wú)比自私、無(wú)比冷酷的女人,這些年來(lái),你替我背負(fù)沉重,而我還一直瞞著你。所以,在你天天借酒澆愁的那些日子,我作出了一個(gè)決定——離開(kāi)你,如果我能夠好起來(lái),我就回家;要是好不了,就離婚。當(dāng)然,現(xiàn)在我終于看到了美好的未來(lái),我希望你重新接納我。”
直到兩個(gè)月后,我才真正明白支小茵去駐村的理由:她要做全縣唯一一個(gè)女工作隊(duì)長(zhǎng),她要通過(guò)與每一戶(hù)貧困戶(hù)的接觸、交涉來(lái)獲得內(nèi)心的堅(jiān)定和坦蕩;她要讓我知道,我們除了需要一個(gè)孩子,更需要一種極具使命感的生活,以此打掃內(nèi)心的塵垢。兩個(gè)月以后,我不再對(duì)我的妻子支小茵所作的決定感到局促,相反,我為她的勇敢叫好,也為我們的婚姻再次邁出實(shí)質(zhì)性的一步感到欣慰和激動(dòng)。我們重新在整理得井井有條的客廳里擁抱,慢慢回到之前的節(jié)奏,在相互鼓勵(lì)的基礎(chǔ)上相互欣賞、加油。
“如果我懷上孩子,我就向組織報(bào)告,讓他們把我撤回來(lái)。”支小茵說(shuō)。
“不用著急。”我說(shuō),“不管你懷孕有多快,生孩子的事,都會(huì)是在這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以后。”
8
大雨說(shuō)下就下起來(lái)。文天嬌坐在自家的檐坎上,雙手捧著頭,一句話(huà)也不說(shuō)。我走到她跟前,說(shuō),“文天嬌,我想給你講講我的故事。”
“我不想聽(tīng)你的故事,我和你沒(méi)什么關(guān)系。”
“這是自然。”我說(shuō),“我只是想讓你知道,其實(shí),我比你更貧窮。”
她把頭抬起來(lái),雙手放到膝頭上去,想知道我說(shuō)的是什么意思。
我說(shuō),“一個(gè)人的貧窮,壓根就不在物質(zhì)上,而是在于精神。”
文天嬌好像沒(méi)聽(tīng)懂我說(shuō)什么,一副云里霧里的樣子。我意識(shí)到自己說(shuō)話(huà)的方式不對(duì),便改換了一種說(shuō)法。我說(shuō),“你們家現(xiàn)在的確很困難,但是你卻沒(méi)怎么當(dāng)回事,你一心一意地尋找著你的丈夫,說(shuō)明你是一個(gè)有情有義的女人,說(shuō)明你心里有一個(gè)希望,你看重的是一家人能夠和和美美地團(tuán)聚在一起,你認(rèn)為我說(shuō)得對(duì)不對(duì)?”
文天嬌盯著我看了一會(huì),點(diǎn)了點(diǎn)頭。看樣子,她這次聽(tīng)懂了我說(shuō)的話(huà)。我接著說(shuō):“而我就不同了,我和我的妻子結(jié)婚十年了,一直沒(méi)有孩子,前些天,她從家里搬出去住,一下子讓我覺(jué)得活在這個(gè)世界上沒(méi)什么意思。你,文天嬌,還有一個(gè)讓你牽掛著的丈夫,有三個(gè)聰明伶俐的孩子,你所做的事,讓你感覺(jué)到非常有意義。”
她又點(diǎn)了點(diǎn)頭。院子里,雨點(diǎn)打在地上,發(fā)出很響亮的聲音。我說(shuō),“文天嬌,你聽(tīng)懂我剛才說(shuō)話(huà)的意思了嗎,要不要我重新說(shuō)一遍?”
文天嬌從地上站起來(lái),對(duì)我說(shuō),“蘇同志,雨很大,下得嘩嘩嘩的,剛才你說(shuō)的話(huà),我什么也沒(méi)聽(tīng)到。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文天嬌也不是那種死無(wú)出息的女人,從現(xiàn)在起,我不找了。”
“你確定不找了?”我提高嗓門(mén)。雨聲很大,我怕她聽(tīng)不見(jiàn)。
“不找了。”文天嬌說(shuō),“他想怎么快活,就怎么快活去。我現(xiàn)在知道了,那年他回家修房子,是想把我一個(gè)人扔在家里。”
“不是這樣的。”我說(shuō),“或許他是迫不得已,出于保護(hù)你們而已。”
文天嬌讓我給縣里的扶貧車(chē)間打電話(huà),說(shuō)明天一早她就去上班。我對(duì)她說(shuō),你如果愿意去上班,就不必去那里了,你的三個(gè)孩子都在鎮(zhèn)上讀書(shū),你去鎮(zhèn)上吧,我早就為你在鎮(zhèn)上找了一份工作。
“什么工作?適合我嗎?”她問(wèn)。
“非常適合。”我說(shuō),“鎮(zhèn)上的中學(xué)缺一位宿管,你去當(dāng)孩子們的孃孃吧!”
“工資高嗎?”她問(wèn)。
我說(shuō),“有四千左右吧,你去那里,還可以順便照顧照顧孩子。”
雨停后,我走路回村部。水泥路上有很多被大雨從地埂上掀下來(lái)的泥層,粘得我滿(mǎn)鞋都是。張青給我發(fā)了好幾條消息,說(shuō)的都是文天嬌丈夫的事情。張青說(shuō),吳建敏這些年來(lái)一直伙同幾個(gè)外地人在做傳銷(xiāo),前些天被抓進(jìn)去了。張青還說(shuō),吳建敏這幾年壓根就沒(méi)在江蘇,而是在一個(gè)叫陌海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傳銷(xiāo)窩點(diǎn)。
我沒(méi)有回他,其實(shí)這些事情,今天一早我就聽(tīng)公安局的朋友說(shuō)了,我蘇陽(yáng)也不是一直都后知后覺(jué)。
在快要走到村部時(shí)候,我聽(tīng)到身后有車(chē)?yán)仍陧懀D(zhuǎn)過(guò)頭來(lái),看見(jiàn)小蒯把頭伸出窗玻璃,對(duì)我說(shuō),“蘇哥,上車(chē)。”
“不用了吧?”我說(shuō)。
“上來(lái),我給你講一個(gè)故事。”小蒯向我招手。
我爬上車(chē),小蒯說(shuō),“今天我去敬老院里看了趙高這老小子,可精神了,和一群老頭老太太打得火熱。”
“怎么個(gè)火熱法,他沒(méi)尿床了嗎?”我笑。
“他根本就不尿床,他之前就是耍無(wú)賴(lài)。”小蒯說(shuō),“他現(xiàn)在明白了,敬老院才是一個(gè)好地方,天天有人給他打飯,有人給他換衣服。他說(shuō),想不到我趙高居然也過(guò)上了神仙日子。”
我突然想哈哈大笑,但控制住了。我為這一句“想不到我趙高”發(fā)笑,我說(shuō),“他說(shuō)話(huà)的口氣還真的像歷史上的那個(gè)宦官。”
“最搞笑的是,他居然變得有禮貌了。”小蒯說(shuō),“我走的時(shí)候,他說(shuō)了一句‘明天見(jiàn)’。”
“明天你還要去看他嗎?”我問(wèn)。
“明天恐怕去不了。”小蒯說(shuō),“明天我要去相親,我媽安排的。”
反正小蒯要明天才去相親,我就讓他送我去一趟花郎鎮(zhèn)的對(duì)塔。小蒯說(shuō),“嫂子駐村的地方,一定很美吧?”
我說(shuō),“去了你就知道了。”
在路上,我分別接到小九妹和王必藍(lán)給我打來(lái)的電話(huà)。小九妹說(shuō),工廠對(duì)她很好,讓她當(dāng)了班組長(zhǎng),工資有四千多。王必藍(lán)說(shuō),他的大兒子參加公務(wù)員考試,面試第一名,不久他們家就不是貧困戶(hù)了。在路上,我接了好多個(gè)電話(huà),其中有一個(gè)是我媽打來(lái)的。
“陽(yáng)兒,你現(xiàn)在在哪里?”
“我去看小茵。”
“聽(tīng)媽的話(huà),那個(gè)藥你必須放在枕頭底下,枕著睡七七四十九天,泡酒喝,你要堅(jiān)持吃下去,我問(wèn)過(guò)觀音老祖了,真的能解決你的問(wèn)題。”
“我知道了。”我說(shuō),“我現(xiàn)在不用吃藥,我的問(wèn)題已經(jīng)解決了。”
汽車(chē)駛?cè)胍粋€(gè)很深的彎道,信號(hào)不好,我掛了電話(hu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