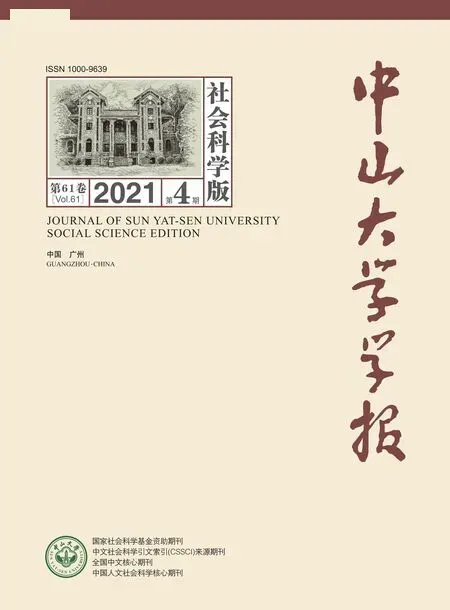論傳統小說文體在民初的通變*
孫 超
“筆記體”“傳奇體”“話本體”和“章回體”等古體小說在民初呈繁榮之勢,由于糅入時新興味而具獨特的現代品性,頗受讀者歡迎①所謂“古體小說”不是一個通行的概念,本文指“筆記體”“傳奇體”“話本體”和“章回體”四種古代文體的小說作品。。不過,在遭到堅決與傳統決裂的“五四”新文學家批判后,特別是1920年代初北洋政府推行“廢文言興白話”的教育政策,使得古體小說或黯然退場,或頂風堅守。從此,學界普遍將民初古體小說稱為“舊文學”,作為落后腐朽的代表,視之為“新文學”打倒的“文壇逆流”。本文擬通過對民初古體小說的系統考察來揭示傳統小說文體在現代轉型語境中的通變,認識民初文人從事古體小說創作“不在存古而在辟新”②冥飛、海鳴等:《古今小說評林》,上海:民權出版部,1919年,第144頁。。
一、沿傳統軌轍書寫的筆記體小說
清末梁啟超曾舉《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為代表,著意強調筆記體小說隨意雜錄的撰述特點③《新小說》報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1902年第14號。。民初的筆記體小說也多遵從此例。例如,何剛德在《〈平齋家言〉序》中說:“夜窗默坐,影事上心,偶得一鱗半爪,輒瑣瑣記之,留示家人。自丁巳迄去秋,裒然成帙。”④何剛德:《春明夢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7頁。王揖唐序《梵天廬叢錄》曰:“此書乃其平日搜討所得,隨時掇述者。”①王揖唐:《王序》,柴小梵:《梵天廬叢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頁。徐珂自序其《清稗類鈔》云:“輒筆之于冊,以備遺忘,積久盈篋。”②徐珂:《清稗類鈔(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85頁。從“瑣瑣記之”“隨時掇述”“輒筆”一類字眼可辨其撰述方式一如傳統的隨意雜錄,從“一鱗半爪”到“裒然成帙”“積久盈篋”等表述足見其由短章匯為巨編的輯錄方式。對于筆記體小說一事一記的特點,管達如在《說小說》中說:“此體之特質,在于據事直書,各事自為起訖。”③管達如:《說小說》,《小說月報》1912年第3卷第7期。對于包羅萬有之特征,蔡東藩稱其《客中消遣錄》“立說無方,不拘一格。舉所謂社會、時事、歷史、人情、偵探、寓言、哀感頑艷諸說體備見一斑”④蔡東藩:《客中消遣錄》,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34年,第2頁。;胡文璐稱譽《梵天廬叢錄》“上而朝廷之掌故,下而里巷之隱微,縱而經史之異同,橫而華夷之利病,無不能說,說之無不能詳”⑤胡文璐:《胡序》,柴小梵:《梵天廬叢錄》,第8頁。。對于全面繼承古代筆記小說的體式,民初文人常常表而彰之,如馮煦《〈夢蕉亭雜記〉序》說“其體與歐陽公《歸田錄》、蘇潁濱《龍川略志》、邵伯溫《聞見前錄》為近”⑥馮煦:《夢蕉亭雜記·序》,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頁。;易宗夔《〈新世說〉自序》直承“仿臨川王《世說新語》體例”⑦易宗夔:《新世說》,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第2,2,2頁。;吳綺緣稱《新華秘記》“體仿《秘辛》《說苑》”⑧吳綺緣:《吳序》,許指嚴:《新華秘記(前編)》,上海:清華書局,1918年,第6頁。,等等。研閱民初各家作品便知以上序說乃是據實而論。這些小說大多搖筆成文,每條(則)往往不設題目,一事一記,合集眾事而成編。因此,從單條(則)來看,其篇幅短小,整體觀之,又卷帙浩繁。相較而言,民初報載筆記體小說體式稍異,單篇作品為數甚夥,一般每篇都有標題。
在長期演變過程中,古代筆記體小說的實錄原則始終不變,這規定了它追求史著品格:不重修飾,崇尚簡約。這也使其與有意幻設、追求辭采的傳奇體區別開來。“在紀昀看來,所謂筆記體小說之‘敘事’即為‘不作點染的記錄見聞’。”⑨譚帆:《“敘事”語義源流考——兼論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傳統》,《文學遺產》2018年第3期。民初筆記體小說在理論與實踐上皆沿此實錄舊軌而行。管達如說:“此體之所長,在其文字甚自由,不必構思組織,搜集多數之材料,意有所得,縱筆疾書,即可成篇。”⑩徐珂:《清稗類鈔(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85頁。這就重申了筆記體小說應“據見聞實錄”,指出其優點是隨意雜錄。該體小說作者也普遍重視實錄。例如,孫家振《〈退醒廬筆記〉自序》謂“吾猶將萃吾之才之學之識仿史家傳記體裁將平生所聞見著筆記若干萬字”11潁川秋水:《退醒廬筆記》,1925年石印線裝本,第2頁。;蔣箸超褒揚《新華秘記》“事事得諸實在,不涉荒誕”12蔣箸超:《蔣序》,許指嚴:《新華秘記(前編)》,上海:清華書局,1918年,第1頁。;易宗夔聲明《新世說》“紀載之事,雖未能一一標明來歷,要皆具有本末”13易宗夔:《新世說》,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第2,2,2頁。,著述目的是成“野史一家之言”14易宗夔:《新世說》,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第2,2,2頁。。民初筆記體小說無論是以筆記集行世,還是單篇載于報端,大多遵循實錄原則,追求樸質雅潔的風格。也有一些作品由于受到《聊齋志異》和西方小說觀念影響,開始喜裝點,重修辭,呈現出與傳奇體合流的趨向。
民初筆記體小說既然仍沿隨意雜錄與講求實錄的書寫軌轍前行,勢必保持古代筆記小說內容廣博、功能多樣的文體特點。從創作實際看,既有野史筆記類小說、稗官故事類小說,又有雜家筆記類小說。由于受到民初小說界“興味”主潮的影響,以消遣為主的稗官故事類小說最為流行,其次是意在存真的野史筆記類小說。
民初稗官故事類小說題材廣泛,思想駁雜,富有供人消遣的興味。代表作有《鐵笛亭瑣記》《〈技擊余聞〉補》《退醒廬筆記》《黛痕劍影錄》《民國趣史》等。這些作品有的記雜事以志人,有的錄異聞以志怪,一部筆記中往往還兼收兩者。臧蔭松評林紓《鐵笛亭瑣記》云:“今先生所記多趣語,又多征引故實,可資談助者。”①臧蔭松:《〈鐵笛亭瑣記〉序》,林紓:《鐵笛亭瑣記》,北京:都門印書局,1916年,卷首。該書雜記朝野逸聞,篇幅短小,筆墨超妙。錢基博《〈技擊余聞〉補》記錄活躍在江南的俠客,每則文末均言明故事由來,謹守實錄原則。該作敘述簡潔有味,寫人白描傳神,令人讀之不厭。孫家振《退醒廬筆記》以記錄市民軼事為主,兼有少量志怪,尤喜記錄日常瑣屑,適宜市民閱讀消遣。胡寄塵《黛痕劍影錄》則兼記異聞、瑣事,說鬼怪、記名人、寫各類女子,語言簡雅,頗有六朝志人志怪之風。李定夷《民國趣史》記錄“官場瑣細”“試院現形”“裙釵韻語”“社會雜談”等,所寫奇聞逸事著眼于一個“趣”字。
民初稗官故事類小說普遍以奇聞趣事來滿足讀者的消遣需要,同時也注意增強文學審美性。周瘦鵑在《〈香艷叢話〉弁言》中稱著閱筆記是“茶熟香溫之候乃于無可消遣中尋一消遣法”②周瘦鵑:《香艷叢話》,上海:中華圖書館,1914年,第1頁。,所記多是香艷故事。該書采用隨筆摘錄、連綴成篇的傳統筆記成法,同時貫注周瘦鵑“小說為美文之一”③鵑:《自由談之自由談》,《申報》1921年2月13日。的現代文學觀念,呈現出“情文兼茂”的文體風格,是周氏所謂“有實事而含小說的意味者”④周瘦鵑:《說觚》,周瘦鵑、駱無涯:《小說叢談》,上海:大東書局,1926年,第73頁。,與其所作傳奇體愛情小說異曲同工。“有人喻之為:如‘十七妙年華之女郎,偶于綺羅屏障間,吐露一二情致語,令人銷魂無已。’”⑤鄭逸梅:《民國筆記概觀》,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101頁。值得注意的是,《香艷叢話》雖體式古色古香,意趣也很傳統,但其筆觸已伸向現代和域外,受到了西方文學觀念與印刷文化的改造。它在當時吸引了不少讀者,開辟了筆記體小說現代轉型的一條路徑。徐枕亞、朱鴛雛創作的稗官故事類小說也意圖創變,在突出強調消遣功能的同時揉進傳奇體因素,明顯增強了文學性。收在《枕亞浪墨續集》中的此類作品文筆流暢,敘事生動,講究塑造人物。尤其是搜奇述異的作品敘述恍惚迷離,辭藻趨于華美,已有明顯的傳奇化傾向。朱鴛雛《紅蠶繭集》收錄的作品短小精致,饒富趣味,且多文學的描寫和虛構,亦是傳奇化的佳作。
民初野史筆記類小說突出的特征是補史存真。其作者不少是近代重大歷史事件的聞見者,他們力圖將某段史事實錄以存真相。其中《德宗遺事》《辛亥宮駝記》《辛丙秘苑》《夢蕉亭雜記》《春明夢錄》《清代野記》《國聞備乘》等是當時的名著。我們略觀一斑。《德宗遺事》的作者王照是翰林學士、戊戌變法的積極支持者。他晚年以親身經歷為素材創作的這部筆記主要記述戊戌變法和庚子事變前后史事,筆墨集中于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的矛盾斗爭。由于“皆實錄所不敢言者”⑥語出王樹柟,載王小航述,王樹柟記:《德宗遺事》,北京師范大學藏本,第1頁。,該筆記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其敘說清末宮廷軼聞歷歷在目,人物對話口吻畢肖,多具小說風味。對讀陳灨一《睇向齋秘錄》中的《德宗軼事(三則)》,光緒這位憂國憂心、可憐可悲的傀儡皇帝就真實地呈現出來。袁世凱次子袁克文所撰《辛丙秘苑》記錄辛亥(1911)至丙辰(1915)間袁世凱及其周圍人物的掌故。雖有人批評該書因“既以存先公之苦心,且以矯外間之浮議”⑦寒云:《〈辛丙秘苑〉序》,袁克文:《辛丙秘苑》,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1頁。,故子為父諱之處甚多,但作者的特殊身份決定了所記多為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加之敘述饒有趣味,故受到當時讀者熱捧。《夢蕉亭雜記》由清末重臣陳夔龍撰述,主要記錄他親歷的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丑條約》簽訂、辛亥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史料價值頗高。同時由于作者精心結撰,文筆生動有趣。另外,《新世說》《新語林》《清稗類鈔》等幾部仿作也很有名,是“世說”“類鈔”類筆記的最后代表。
民初野史筆記類小說除了上述立本守正的作品外,也涌現出一些趨時創變的作品,其中許指嚴的作品最為典型。許指嚴素以創作“掌故小說”聞名,范煙橋稱“歷史小說允推指嚴”⑧范煙橋:《小說話》,《商旅友報》1925年第20期。。許指嚴有很強的文學加工意識,其所謂“采摭已征夫傳信,演述奚病其窮形”⑨許指嚴:《〈泣路記〉自敘》,上海:《小說叢報》社,1915年,第1頁。,希望在實錄基礎上演述得窮形盡相。因此,他的筆記體小說揉入了傳奇筆法,明顯增強了興味娛情功能。《南巡秘記》是其掌故筆記的定型之作,專記乾隆巡幸江浙秘極奇極之事,隨意裝點,趨近傳奇體。鄭逸梅曾回憶說:“所記《幻桃》及《一夜喇嘛塔》,光怪陸離,不可方物,給我印象很深,迄今數十年,猶縈腦幕。”①鄭逸梅:《民國筆記概觀》,第100頁。從此書開始他形成了“述歷史國情,本極助興趣之事”的看法,從而確定了將聞見與稗乘相發明的創作方法②許指嚴:《〈南巡秘記〉自序》,上海:國華書局,1915年,卷首。。《十葉野聞》是其筆記掌故的代表作,就清代十世雜史進行文學加工,以渲染清室趣事秘聞為能事,亦富傳奇性。當然,許指嚴筆記掌故也想為歷史“存真”,但又追求寫人繪景“窮形盡相”,敘事“必竟其委”,因此更接近現代意義上的小說創作。概觀之,許指嚴的野史筆記類小說融筆記和傳奇于一體,“因文生情,極能鋪張”③鳳兮:《海上小說家漫評》,《申報·自由談·小說特刊》,1921年1月23日。,增強了文學魅力,“有羚羊掛角之妙”④范煙橋:《小說話》,《商旅友報》1925年第20期。,吸引了大量讀者。
二、尊體與破體意識影響下的傳奇體小說
一部分民初小說家創作傳奇體小說具有明確的尊體意識。林紓在《〈畏廬漫錄〉自序》中聲明其“著意為小說”“特重唐之段柯古”⑤林紓:《畏廬漫錄·自序》,林薇選編:《畏廬小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31頁。,顯然意欲承續唐傳奇。葉小鳳在《小說雜論》中說:“唐人自有唐人之小說,文不可假于父兄,而小鳳獨可假諸唐人乎?小鳳曰:是有說也。暢發好惡,鉤稽性情,乃天地造化之功;如我陋劣,何敢以此自期。然俯視斯世,凡作文言小說者,或斜陽畫圖,秋風庭院,為辭勝于意,臃腫拳曲之文;或碧璃紅瓦,苗歌蠻婦,稗販自西之語;其最高者,則亦拾《聊齋》之唾余,奉《板橋》為圭臬……蒲留仙、余澹心等不過如小家碧玉,一花一鈿,偶然得態耳。在彼猶在摹撫官樣之中,何足為吾之師……此小鳳摹撫唐人之所由來。”⑥葉小鳳:《小說雜論》,《小鳳雜著》,上海:新民圖書館,1919年,第40—41頁。由此可知,葉小鳳認為唐傳奇是文言小說創作的最佳范本,他的一些作品就直接標明“效唐人體”。姚鹓雛贊同葉氏看法,曾在《〈焚芝記〉跋語》中說:“丁巳除夕,偶與友論說部,友謂近人撰述,每病凡下。能師法蒲留仙,已為僅見,下者,乃并王紫銓殘墨,而亦摹仿之。若唐人小說之格高韻古,真成廣陵散矣。余心然之。”⑦鹓雛:《焚芝記》,《小說大觀》1917年第11集。在上述名家的號召與示范下,民初傳奇體小說宗唐之風興起,而自清末流行的“聊齋體”勢頭稍稍減弱。不過,站在民初那個中西文化激烈交鋒的時間點上看,無論是以唐人小說為師,還是以《聊齋志異》為范,都是賡續固有傳奇體小說的尊體表現。
尊體意識影響下的民初傳奇體小說在題材上依然是婚戀、俠義和神怪三足鼎立;在筆法上多采用紀事本末體和傳記體的形式,講求辭章結構;在創作旨趣上作意好奇,注意暢發性情,追求一種詩意美。
民初婚戀傳奇脈承了唐傳奇以來的傳奇筆法和傳奇性,旨在傳播愛情奇聞和禮贊真愛精神,有的作品還意圖抨擊舊的婚姻觀念,引導時代新風。如葉小鳳的純情類傳奇《石女》《塔溪歌》《阿琴妹》等,歌頌男女間純潔美好的情感,是唐傳奇真愛精神的回響;奇情類傳奇《忘憂》《嫂嫂》《男尼姑》等,敘奇人、奇事、奇情,明顯繼承或戲仿唐傳奇的“艷遇”主題,但嚴守情淫之辯,旨趣仍在一“情”字。徐枕亞《簫史》寫落魄文人蕭嘯秋與客舍主人侄女小娥之間因簫聲相知、相戀,最終亦因簫而雙雙殉情的故事。從文體上看,該小說刻意規摹唐傳奇,傳示奇異之外,追求濃烈的詩意氛圍,敘事婉轉,抒情纏綿,形式上夾雜詩詞,使用麗詞藻句,兼有“文備眾體”之妙。民初俠義傳奇主要以唐傳奇為范本。特別是那些寫救厄濟困、復仇報恩故事的作品模仿痕跡更重,如姚鹓雛所作《觚棱夢影》《犢鼻俠》明顯模仿《昆侖奴》;李定夷《女兒劍》、張冥飛《雪衣女》則不脫《謝小娥傳》窠臼。這些作品所承續唐傳奇的詩意、理想特質仍為民初亂世中的讀者所喜愛。有些作品則在沿襲唐傳奇的基礎上,呈現出一些新氣息,如林紓所作《程拳師》《莊豫》等精于描寫高超武技,以尚武精神鼓動國民斗志;李定夷的《鸰原雙義記》傾心于展現俠義人格,以俠義精神砥礪民族士氣。還有一些作品將英雄與兒女合為一體,以俠風奇情娛目快心。葉小鳳所作《云回夫人》可為代表。它以《虬髯客傳》為范本,寫一位類似“紅拂妓”的女俠。民初神怪傳奇在體制上雖沿襲傳統,但因受西方科學文明的沖擊在創作旨趣上發生了較大變化,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借寫神怪來譏刺現實丑惡;一是借寫神人相戀歌詠愛情美好;一是借寫神怪使讀者獲得消遣。第一類作品首推許指嚴的《喇嘛革命》和《九日龍旗》。這兩篇小說以大膽的想象,恍惚迷離的情節曲折地反映民初世相。第二類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有吳綺緣《林下美人》、程瞻廬《嬰寧第二》等,這些小說亦可劃入婚戀題材。第三類作品單純講述鬼怪故事,如阿蒙《冢中人》、聊攝《甘后墓》等,這類小說主要滿足讀者的獵奇、消遣需要。
民初小說家在創作傳奇體小說時亦具自覺的破體意識。他們受域外小說影響,在寫人、敘事及環境、心理描寫等方面積極進行創作試驗,拓展了傳奇體小說的創作內涵,形成了新的敘事模式和創作旨趣。
民初傳奇體小說在創作內涵上有較大拓展,數量較多且較有影響的有都市情感傳奇、家庭傳奇和社會傳奇等。都市情感傳奇源出于傳統婚戀傳奇,是其富有現代性的變體。民初趨新求變的小說家如蘇曼殊、包天笑、周瘦鵑等活躍在繁華都市上海,面向西方文化一直持開放心態,對歐美小說積極譯介吸收,這就使他們有條件采用新的敘事技巧來呈現現代都市男女的情感世界。蘇曼殊所作《焚劍記》《絳紗記》《碎簪記》和《非夢記》揭露禮教和金錢勢力對都市青年愛情的破壞,積極回應民初婚制變革這一社會熱點。雖敘之以傳奇體,但又確如錢玄同所說其“描寫人生真處,足為新文學之始基”①錢玄同:《致陳獨秀信》,《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1號。。包天笑所作都市情感傳奇頗具當下性和真實感,如《電話》《牛棚絮語》等寫當時妓女的情海沉浮,試圖引發讀者對妓女歸宿問題的思考。《淚點》敘飄渺生與其表妹的一段情緣,其純潔真摯中的哀傷讓讀者不禁扼腕。這些作品表現出對過度提倡“戀愛自由”的警惕,同時又反對“盲婚啞嫁”,呈現出一種徘徊在新舊之間的過渡性特征。周瘦鵑創作的都市情感傳奇有三類:一是作者本人戀愛生活的藝術化呈現,代表作是《恨不相逢未嫁時》《午夜鵑聲》等;二是在言情中貫注著愛國觀念,如《此恨綿綿無絕期》《一諾》等;三是富有現代意味的至情、畸戀,代表作有《畫里真真》《西子湖底》等。這些小說所寫“奇情”“癡情”“至情”明顯繼承了唐傳奇以來禮贊真愛精神的傳統,同時也自覺汲取了西方自由戀愛的思想。家庭傳奇主要展現新舊家庭觀念的激烈碰撞及家庭生活的新氣象。代表作品有周瘦鵑的《冷與熱》,程瞻廬的《但求化作女兒身》《七夕之家庭特刊》等。
在破體意識影響下,一些傳奇體作品借鑒外國小說藝術技巧在敘事結構、敘事時間、敘事角度和非情節化敘事等方面進行了自覺變革,呈現出迥異于傳統的現代性特征。整體來看,這些作品多截取一個生活“斷片”,而非紀事本末體和傳記體。例如,包天笑的《電話》寫憶英生與舊情人蕊云的一次電話通話,除開頭與結尾外,通篇是對話;周瘦鵑的《午夜鵑聲》采用自述體反復渲染失戀的悲情;許指嚴的《女蘇秦》以旅途中談話起首寫一個獨立事件。這些作品普遍使用第一人稱敘事,增強真實效果,還有意打破傳統敘事時序來形成陌生化。如包天笑《牛棚絮語》先作回憶式倒敘,然后轉向主要情節的正敘,又以“牛棚絮語”的對話方式讓正敘暫停,變為追敘往事、談時下處境,最后才將敘事拉回現實,把故事講完。周瘦鵑《西子湖底》首先以老槳月下殉情開篇,接著以第三人稱敘述老槳的神秘身世和怪異行為,然后又敘述“予”與老槳的相識相交。小說主體部分回到傳統的敘事人聽故事模式,老槳自述其三十年來的詭異畸戀。末尾又返回“予”的視角,呼應開頭的老槳沉湖殉情。小說敘事視角的多次轉換,仿佛文藝片中的鏡頭切換,使敘事曲曲折折,也使老槳這一“畸異怪特之人”得到精細刻畫。單純從藝術技巧上看,這已是一篇很“現代”的小說了。有些作品還注重非情節敘事,加強了場景及心理描寫。周瘦鵑的作品就常以景色描寫開篇,包天笑的作品則常常穿插大段環境描寫,這大大改變了傳奇體以情節為中心的固有敘事模式,增添了更多詩意。包天笑、周瘦鵑、劉鐵冷的一些作品還直接描寫人物隱秘的內心世界,甚至完全以人物抒情和心理剖白為主體,這種“心理化”敘事更接近現代小說,而與古代小說漸行漸遠。
三、保留說話虛擬情境的話本體小說
在民初古體小說中,話本體的文體變異最大。在體式上,該體作品多數不再使用入話,而直接進入故事主體;基本不再使用韻文敘事,敘事完全散文化;一般篇幅不大。在功能上,該體作品賡續古代話本小說娛樂、教化的傳統,主要寫家庭、社會、情感、倫理、滑稽等內容,充滿了娛樂性、民間性和世俗性。
作為傳統話本小說的變體,民初話本體小說已呈現出不少現代性特征:更普遍地使用第一人稱,采用插敘、倒敘、補敘,進行橫截面式描寫,出現大段的心理、景物刻畫,談論時新對象,關注熱點話題,等等。例如包天笑的《友人之妻》演述“我”的友人之妻,談論對象是留學生和新派人物,關注的是小家庭建設這一熱門話題。他的《富家之車》一經刊出便被讀者視為創新之作,鳳兮指出:“描寫一個問題或一段事實者,如天笑之《富家之車》《鄰家之哭聲》……均確為自出心裁而有目的(指其小說之感痛力所及)者,均無所依傍或脫胎于陳法者也。”①鳳兮:《我國現在之創作小說》,《申報·自由談·小說特刊》1921年2月27日。這篇小說的問題意識和橫截面式描寫確有難得的創新,其半新半舊的小說體式也如鳳兮所說“尤能曲寫半開化社會狀態,讀之無不發生感想者”②鳳兮:《我國現在之創作小說》,《申報·自由談·小說特刊》1921年2月27日。。再如徐卓呆的《微笑》《死后》則以心理刻畫見長。它們不像傳統話本小說單純通過外部言行來展現人物心理,而是加入了對心理活動的直接描摹。《微笑》中男青年的心理活動是貫穿全篇的敘述主線,情節推進與其心理活動相輔而行。《死后》則將一個一度屈從于命運的知識女性如何追求人格獨立、如何成就文學夢的心理過程真實地描摹出來。又如周瘦鵑的《良心》開頭是一段景物細描:“話說上海城內有一個小小兒的禮拜堂。這禮拜堂在一條很寂寞的小街上,是一座四五十年的建筑物。檐牙黑黑的……”③瘦鵑:《良心》,《小說月報》1918年第9卷第5期。這種種創變是其作者主動學習域外小說的結果,其突出的現代性幾乎讓人忘記它們由古代話本小說演變而來。
不過,從上述作品中的“看官”“在下”“你道”“話說”“看官聽著”之類的“說話人”口吻中,我們仍能確認其話本體小說特有的說話虛擬情境——“作者始終站在故事與讀者之間,扮演著說故事的角色”④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264頁。。這種具有虛擬在場感和參與性的小說曾經讓數百年的中國讀者娛目醒心,成為他們重要的精神食糧。雖然在民初讀者那里話本體已遠沒有過去的魔力,但這種熟悉的“說-聽”虛擬情境仍能吸引一部分讀者。古代話本小說設置說話虛擬情境追求把人物、事件講活講真,民初話本體小說賡續這一傳統,運用白話俗語、通過塑造言行畢肖的人物來形成“似真”效果。比如包天笑《友人之妻》中錢玉美和孫玉輝的對話,讓民初讀者覺得人物很真實,就是身邊受過新式教育又情同姊妹的閨蜜間推心置腹的竊竊私語。“看官”仿佛看著她們,聽她們絮談,這正是話本體的長處。再如看胡寄塵《愛兒》中演述的瓶居、松雪夫婦在育兒過程中發生的種種齟齬、誤會與和解,仿佛觀賞一幕名為“成長煩惱”的家庭劇。更有趣的是,因了文中那聲“看官”,讀者仿佛也可走入劇中來。
對比古代話本小說,民初話本體小說雖還能借助說話虛擬情境“建立起真實客觀的幻影”⑤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84頁。,但已不能通過“說話人”之口講出“一種集體的社會意識”①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86,93。原因在于古代相對穩定的道德倫理觀念可以推出“說話人”作代言,而民初思想混亂、道德重構的現實使“說話人”失掉了集體代言的資格。因此,我們看到包天笑、周瘦鵑、姚鹓雛等的話本體作品不再通過“說話人”評議跳出情節來勸懲教化,而是借助情節自身的推動力量,自然流露個人對事件的態度。如姚鹓雛《紀念畫》的結尾是兩首詩,仿佛傳統話本體的下場詩,可不同的是那詩是順著小說情節自然生發的,是“我”為外祖母掃墓之后和在外洋輪船之上兩次萬感如潮而作的,言說的是個人化的情感。再如包天笑的《富家之車》,結尾是順著情節發展講述祖孫三代不同的出行方式,不露聲色地傳達作者的褒貶態度。又如周瘦鵑的《良心》雖仍以“話說”設置說話虛擬情境,但已是一種類西方短篇小說的結構,故事也在情節敘述中自然收束,并借梅神父的態度傳達作者對沈阿青因追求真愛而殺人的贊賞。
由于抒情、評判的個人化與新體白話短篇小說日漸趨同,設置說話虛擬情境變得越來越沒必要,“說話人”完全隱形成為小說發展之必然。正如王德威所說:“在作家強調抒發個人欲望及企圖的沖動下,說話傳統無可避免地被貶抑甚至消失。”②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86,93頁。
四、正宗與特創的章回體小說
中國古代章回體小說長期以來主要使用白話創作,民初文言章回體小說的大量出現打破了白話一統的局面,使章回體有了正宗與特創之別。從小說文體發展史來看,章回體具有與時流變的特點。作為正宗的白話章回體發展至民初,在保持基本體制風格不變的基礎上積極響應時代需求,產生了種種新變。而作為特創的民初文言章回體更是時風激蕩的產物。
民初白話章回體小說并非如新文學家所說全是“舊思想,舊形式”③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號。,而是繼續保持與時流變的特點,面向廣大市民讀者寫作,與世俗、時俗相通,呈現出很強的通俗性。因此,該體作品在語言、題材、適應報刊及類型化等方面都呈現出創變特征。
民初白話章回體所用白話與時變遷,大致形成三種情況:以《廣陵潮》為代表的向俗傾向;以《古戍寒笳記》為代表的尚雅傾向;以《人間地獄》為代表的趨新傾向,體現了民初小說家對白話語言的多元追求,意圖滿足各階層讀者的不同需要。這些白話均由傳統白話化出,以當時社會流行的白話為根本,同時吸收民間俗語和域外小說的某些語法及詞匯,形成了有別于新文學“歐式白話”的“中式白話”。當時,過于高古的文言和過于歐化的白話都只能局限于某些特定的讀者群,而“中式白話”倒是能夠雅俗共賞。這一點,從此后新文學家內部對語言問題的論爭和調整,從“五四”前后章回小說讀者數量之大、層次之廣都可得到確證。
民初小說的首發載體是報刊,白話章回體小說作為通俗文學適于在此大眾傳媒上發表,但同時也易于被其改造而發生文體變化。其最顯著的變化有兩點:一是有強烈的新聞意識,一是呈現出明顯的類型化。民初白話章回體小說受新聞意識影響,大多跳脫講史、神魔、傳奇等傳統題材,更傾向于寫當下,甚至將新聞融入小說,如《山東響馬傳》《人間地獄》《茶寮小史》《新舊家庭》《交易所現形記》等皆是富有新聞性的作品。受新聞大眾性、時效性影響,該體小說使用大眾最快接受的通俗語言,結構也普遍采用短篇連綴的《儒林外史》式。這樣可高效完成獨立故事講述,并可時時調整敘事視角、敘事內容和敘事節奏等,適應輿論或形成新的輿論。民初章回體小說的類型化與報刊進行小說的分類標注密不可分。因為作者要想投稿成功必然要看所投刊物的分類標注,讀者閱讀也必然受其引導,從而形成某種類型化的閱讀品味。
民初白話章回體大致形成了社會小說、社會言情小說、歷史小說、武俠小說四種類型,它們在近現代通俗小說類型史上具有奠基地位。社會小說佳作很多,諸如《如此京華》《留東外史》《傻兒游滬記》《怪家庭》《茶寮小史》《新舊家庭》《交易所現形記》等。這些小說敘事多元,側重于現代生活啟蒙。有的作品展現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亂世情態,表達一種激憤又無奈的愛國情緒和社會批判;有的作品描摹家庭生活,由家庭連接個人與社會,呈現獨特視角下的社會觀察。整體來看,其敘事場景遍布社會各個角落;敘事結構一般采用《儒林外史》式的“短篇連綴”或《孽海花》式的“串珠花”;敘事焦點與時流變,從北京到上海,從總統府到小家庭;敘事關節則是其中的“怪現狀”“活現形”。該類型小說的敘事模式對之后的張恨水、劉云若們有直接影響。社會言情小說以社會現狀為經,以男女婚戀為緯,側重于通過言情來反映社會。《廣陵潮》是此類型經典,它讓言情與社會緊緊捆綁,在民初言情小說潮中另辟出一條社會言情的道路。在《廣陵潮》的成功效應下,社會言情小說迅速定型,在民國時期僅以“潮”命名的同類型作品就出版不下幾十部。歷史小說賡續傳統“演義體”,在蔡東藩手中走向成熟。蔡東藩作品以朝代更迭為序,將中國兩千多年的正史加以演義,敘事曲折有味,形成了獨特的類型特征。另外,許慕羲、許嘯天等的同類型作品在民初也較流行,與蔡東藩作品一道成為現代通俗歷史小說的前驅。武俠小說沒有沿晚清俠義小說開啟的馴化英雄道路前行,而是回到《水滸傳》開辟的仗義行俠、聚義犯禁的英雄傳奇傳統。葉小鳳的《古戍寒笳記》是發生這一轉變的關鍵作品,其敘事立場明顯從官家轉到民間,完全擺脫了清末俠義+公案的敘事成規,突出強調打斗場面的“武”與義薄云天的“俠”。此后,顧明道、陸士諤、向愷然等的武俠小說逐漸形成了兩大基本敘事模式:一是以自圓其說的敘事邏輯敘述亦真亦幻“江湖”中的奇俠奇武奇情;一是以“尚武”“俠義”為敘事關節敘述某段特定“歷史”中的俠義英雄。這為現代武俠小說所傳承。
民初文言章回體小說發生的變化之劇,數量之多,影響之大,都堪稱特創。它保留了章回體的基本特征,篇幅蔓長、分章列回、回有回目、注意謀篇布局,兼采傳奇小說、駢散文及詩詞等的藝術技巧和審美旨趣,從而形成了嶄新面目。今人一般將民初文言章回體小說分稱為“古文小說”與“駢文小說”,或曰“史漢支派”與“駢文支派”①“古文小說”與“駢文小說”之稱見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1 卷,“史漢支派”與“駢文支派”之稱見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這在總體上抓住了該體小說受古文與駢文影響形成的體制分野。但真正如《燕山外史》那樣的駢文小說或純粹的古文小說在民初是找不到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是詩駢化或古文化的章回體。
民初創作詩駢化章回體小說影響最大的是《民權報》作家群,他們以這種特創別體掀起了一股強勁的“哀情小說潮”。如徐枕亞《玉梨魂》《雙鬟記》,李定夷《霣玉怨》《鴛湖潮》,吳雙熱《孽冤鏡》《蘭娘哀史》,等等。這些小說引駢入稗,大量穿插詩詞,在文體上形成典雅的陌生化,在題材上呈現通俗的焦點化,故能化古生新。從小說文體的演進過程看,該體小說明顯賡續傳統而來。中國古代從唐傳奇《游仙窟》引詩駢入小說到《紅樓夢》雅化白話章回呈現詩意美,再由《燕山外史》用駢文寫章回到《花月痕》在白話章回中大量鑲嵌詩詞,逐漸形成了一種以典雅修辭浪漫言情的書寫范式。該體小說正是沿此范式在中西古今的交匯點上再次嬗變。在嬗變過程中,該體小說還從整個古代言情傳統中汲取養分,夏志清曾說:“徐枕亞充分利用并發揮中國文學史上的‘言情傳統’(the sentimental erotic tradition),這個光輝的傳統囊括了李商隱、杜牧、李后主的詩詞之作,并《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長生殿》《紅樓夢》等戲曲說部名著。我以為《玉梨魂》正代表了這個傳統的最終發展,少了那部《玉梨魂》,我們會感到這個傳統有所欠缺。”②[美]夏志清:《為鴛鴦蝴蝶派請命——〈玉梨魂〉新論》,《“中國”時報(臺灣)》副刊,1981年3月17—19日。另外,因要滿足讀者興味娛情及確立小說審美獨立性的需要,該體小說還借鑒了一些時新的西洋思想和小說技巧。例如《玉梨魂》中梨娘送別夢霞時唱了《羅密歐與朱麗葉》里的詩句;《霣玉怨》中史霞卿大談西方激進的“不自由毋寧死”言論;《孽冤鏡》中王可青引歐西自由婚戀思想來控訴舊式婚制的罪惡。在敘事方式上,該體作品學習西方小說使用第一人稱限知敘事,由此形成濃郁抒情的自敘傳風格;運用倒敘法,形成強烈的懸念以吸引讀者;著意于場景描寫,形成了大段景物描摹的敘述模式;效仿《巴黎茶花女遺事》《魚雁抉微》在敘事中穿插日記和書信,等等。整體觀之,詩駢化體式使敘事節奏舒緩,抒情性增強,變情節中心為寫人中心,形成了哀婉凄迷的風格。此外,該體小說敘事與抒情的文本沖突,落后和先進的思想矛盾藝術地象征著如麻如猬的民初文人心態。這卻不期然而然地適應了民初那個新舊雜糅的過渡時代,因而風行一時——有人玩味其綺麗香艷的辭章,有人嘆賞其中西合璧的浪漫,有人沉迷其傷心傷逝的氛圍,有人在其中覓得堅守舊道德的偶像,有人卻恰恰由此產生反抗禮教的愿望。
林紓自清末用古文翻譯了大量外國小說,大大拓展了古文的疆域。1913年開始他陸續推出多部用古文創作的章回體小說,不期又引出一股章回古文化的潮流。除林紓《金陵秋》《劍腥錄》諸作外,姚鹓雛《燕蹴箏弦錄》、葉小鳳《蒙邊鳴筑記》、章士釗《雙坪記》等也是民初流行的古文化章回體作品。這些小說總體上是言情與歷史題材的融合,林紓所謂“桃花描扇,云亭自寫風懷;桂林隕霜,藏園兼貽史料”①林紓:《〈劍腥錄〉序》,《劍腥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第1頁。。在運用古文的基礎上,該體作品也借鑒了外國小說的一些敘事技巧,從而改變了古代章回體單一的全知敘事模式,注意敘事視角轉換;場景、心理描寫增多,敘事節奏放緩,增強了主觀抒情性,不再以情節敘事為中心,而是側重于塑造人物;注意敘事時間的變化,倒敘、插敘、預敘與順序相交織,使文本結構也出現一些新變。不過,由于林紓和其他作者都恪守古文筆法,苛求情中寓史,故而使作品束手束腳,沒有產生出詩駢化章回小說那樣的強大魅力。
五、古體小說的衰亡及其影響
經民初小說家一番守正出新的努力,古體小說呈現出一時繁榮的景象。可由于遭到“五四”新文學家的激烈批判,其創作開始走向衰落。
“五四”新文學家對用文言寫的古體小說批判最烈,認為“《玉梨魂》派的鴛鴦胡蝶體,《聊齋》派的某生者體,那可更古舊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現代的空氣以外,且可不必論也”②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號。。新文學家提倡“新文化”,主張“廢文言興白話”,自然徹底否定賡續傳統的文言章回體、筆記體和傳奇體。
以言情為主的民初文言章回體小說最先遭到新文學家否定。劉半農宣告:“不認今日流行之紅男綠女之小說為文學。”③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號。胡適提出的“不用典”“不講對仗”“不摹仿古人”等④胡適:《寄陳獨秀》,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頁。,也直刺文言章回小說的要害。徐枕亞、林紓等原以為趟出了化古生新的古今轉型之路,本自許著作堪能與古之作家相頡頏,堪與世界文豪競短長,沒料到竟成陳腐典型,革命對象。1920年代初北洋政府行政性地支持“廢文言興白話”,導致文言小說創閱后繼乏人。加之文言章回體主題題材單一、后期模式化嚴重,它在1920年代初“白話文運動”成功后迅速消亡。
“五四”后婚姻自主已成社會普遍思想,“五四小說”甚至追求徹底的個性和肉體解放,民初詩駢化章回體小說那種搖擺于自由婚戀與遵奉禮教間的言情書寫已失去現實基礎。隨著《玉梨魂》等作品風行,市場化使得原本富有創新性的文體日趨模式化。對于詩駢化言情作品整體的墮落,不僅新文學家大加鞭撻,就連曾與徐枕亞同為《民權報》編輯的何海鳴也痛批曰:“學之者才且不及枕亞,偏欲以其拙筆寫一對無雙之才子佳人,甚至以歪詩劣句污之,使天下人疑才子佳人乃專作此等歪詩者,寧非至可痛心之事耶。”①冥飛、海鳴等:《古今小說評林》,第106頁。讀者對于動輒“嗟乎,傷心人也”“我生不辰”一類的哀傷調子,對于“筆頭已深浸于花露水中,惟求其無句無字不芬芳”的詞章點染已不再欣賞②范煙橋:《小說話》,《益世報》1916年9月24日。。正如落華所說:“致以駢四儷六,濃詞艷語,一如圬工之筑墻,紅黑之磚,間隔以砌之,千篇一律。行見其淘汰而無人顧問,移風易俗則瞠乎后矣。”③落華:《小說小說》,《禮拜六》1921年第102期。古文化章回體小說也犯了同樣毛病,題材單一且模式化嚴重,林紓甚至成為新文學家打擊所謂“舊文學”的活靶子,而那些“效顰者都畫虎成了狗”④朱天石:《小說正宗》,《良晨》1922年第3期。,遭到淘汰成為必然。不過,我們也應看到,民初以文言寫章回的文體試驗及其試圖以中化西的寫作實踐對于章回體小說的雅化及對新文學的孕育曾做出過一定貢獻。它進一步提高了小說的地位,試探出了小說文體革新的限度。詩駢化與古文化合力推動了章回體小說的雅化,形成了范煙橋所說維新以來重詞采華美與詞章點染的時期⑤范煙橋:《小說話》,《半月》1923年第3卷第7號。。它們在題材選擇和主題表現上還啟示了新文學。如《玉梨魂》,早在五四時期,周作人就不得不承認它所記的婚戀悲劇“可算是一個問題”⑥周作人:《中國小說里的男女問題》,《每周評論》1919年第7號。,當代學者章培恒認為《玉梨魂》這一類的小說是新文學以個人為本位的人性解放要求的濫觴⑦詳見章培恒:《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兼及“近代文學”問題》,《不京不海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98—600頁。。除此之外,我們還發現這部小說首創的“戀愛+革命”模式影響深廣,不僅被其他章回體作品所用,還啟發了新文學中“革命+戀愛”小說的產生。
民初筆記體小說與傳統文化捆綁得最緊,“五四”前后一系列文化、文學、語言的激烈變革都以徹底反傳統為鵠的,傳統語境消失使該體小說迅速喪失現代轉型活力,但源遠流長的書寫慣性使其一直到20 世紀中葉才徹底消亡。需要注意的是,筆記體小說隨筆雜錄與講求實錄及樸質雅潔等文體特點,似乎都與講究結構技巧、虛構的、情感的、審美的西方小說大異其趣。那么,民初筆記體小說堅守的傳統書寫范式及其現代性探索是否對現當代小說產生了影響呢?據實來看,其文言筆記體的形式雖被淘汰,但其傳統書寫軌轍一直延伸到當代“新筆記小說”之中。孫犁、汪曾祺等創作的“新筆記小說”就有意識地繼承隨意雜錄、講求實錄的傳統,追求樸質雅潔的風格。
傳奇體小說因其幻設性、辭章化和詩意美契合了民初小說家對小說文學審美性的現代追求,故而很自然地發生著現代轉型。在藝術上,該體小說布局精嚴,情節曲折;人物形象塑造不重精描細刻,而重傳神得態;整體營構出詩般意境空間,召喚讀者流連其中;可以起到娛情作用,是作者“暢發好惡”的抒情載體,亦是閱者“鉤稽性情”的移情媒介。加之有的作品還融入場景、心理等西方小說技巧,更進一步強化了該體小說的詩意浪漫特征。可以說,傳奇體小說在民初已初步完成了現代轉型。不過,與其他文言小說一樣,傳奇體小說在“白話文運動”取得勝利后便一蹶不振了。雖然傳奇體小說在上世紀中葉以后難覓蹤影,但由民初傳奇體小說傳承下來的傳奇性——“作意好奇”的書寫本質及浪漫品格——并未隨之消失,而是以新的樣態和意蘊轉化到了現當代諸體小說之中,這已被相關研究所揭示⑧可參看吳福輝:《新市民傳奇:海派小說文體與大眾文化姿態》,《東方論壇》1994 年第4 期;逄增玉:《志怪、傳奇傳統與中國現代文學》,《齊魯學刊》2002 年第5 期;閆立飛:《中國現代歷史小說中的“傳奇體”》,《南京社會科學》2009 年第8期;李遇春:《“傳奇”與中國當代小說文體演變趨勢》,《文學評論》2016年第2期。。
話本體小說在民初之所以還能留下最后一抹余暉,一是因“撰平話短篇,尤能曲寫半開化社會狀態”⑨鳳兮:《我國現在之創作小說》,《申報·自由談·小說特刊》1921年2月27日。,一是復古、試驗、轉型的時代語境使然。“五四”后,在新文學家一片反傳統的呼聲中,話本體小說存在的空間變得更加逼仄,不僅“五四”短篇小說勢不可擋地要將其淘汰,白話章回體和新體白話短篇這兩種同源小說也在有限的閱讀市場上完全遮住了它。隨著民初話本體小說的某些創變成果被新體白話短篇吸收,1920年代中期后,短篇白話小說完成了由“說—聽”虛擬情境到“寫—讀”創閱模式的現代轉型。至此,話本小說的文體體制徹底終結。
白話章回體小說在“五四”前后已基本完成現代轉型,該體作品以切近大眾生活的“中式白話”在富有現代性的報刊上敘寫市民喜聞樂見的主題題材,在大量創作實踐基礎上形成了現代章回小說的四種基本類型,整體呈現出滿足廣大讀者多元興味、與時流變的通俗性。不過,因其為古體,亦遭新文學家批判。例如周作人說《廣陵潮》《留東外史》等在“形式結構上,多是冗長散漫,思想上又沒有一定的人生觀,只是‘隨意言之’……他總是舊思想,舊形式”①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號。。在這類成見支配下,新文學家不斷否定章回小說的價值,以致1947年張恨水發文感慨說:“自五四運動以后,章回小說有了兩種身份。一種是古人名著,由不登大雅之堂的角落里,升上文壇,占了一個相當的地位。一種是現代的章回小說,更由不登大雅之堂的角落里,再下去一步,成為不屑及的一種文字。”②張恨水:《章回小說在中國》,《文藝》1947年第1期。實際上,白話章回體非但未像其他古體那樣在1920 年代后漸趨消亡,還以另類“白話”“通俗”征服了文化市場和市民大眾,甚至影響到解放區文學的創作,出現了《洋鐵桶的故事》《呂梁英雄傳》那樣的作品。在當代,各類型的章回小說仍在持續創作,如金庸、梁羽生等的武俠小說,高陽、二月河等的歷史小說都曾掀起閱讀熱潮,進而成為被研討的文化熱點。現在方興未艾的網絡小說用章回體創作的各類型作品更是層出不窮。這都證明根植于傳統的白話章回體具有與時流變的文體活力,它在當代小說創作中仍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上,我們對古體小說在民初的繁榮、衰亡及影響作了比較系統的考察,從中可見傳統小說文體發生通變的真實過程。清末“小說界革命”以來求新求變的現代性訴求加速了傳統小說文體的演變,而民初小說家創作古體小說“不在存古而在辟新”也意欲開辟中國小說發展的新路。民初古體小說創作積極轉化古代文學遺產,化用域外文學資源,汲取民間文學營養,曾取得了不少實績。當“五四”時期古體作品被斥為“舊小說”而遭全盤否定時,其作者堅持認為“中國之舊小說固然有壞處,但須以中國之法補救之,不可以完全外國之法補救之”③胡寄塵:《小說管見》,原載1919 年2 月《民國日報》,見黃霖編著:《歷代小說話》第9 冊,江蘇:鳳凰出版社,2018年,第3439頁。。中國傳統小說文體原是在中華文化背景中孕育、成長的,對此,民初小說家有自覺認識,故希圖推動它們完成現代轉型。歷史證明,他們的觀點與實踐,為中國小說在古今巨變中避免與阻擋“全盤西化”起到過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