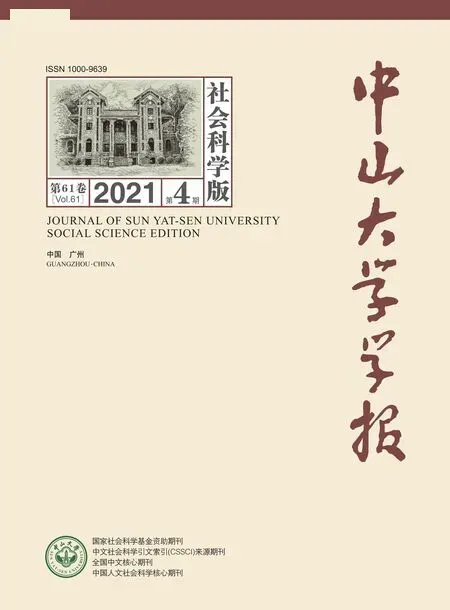編后記
本期含“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名家特稿”“中山大學學術名家訪談”“中國文體學研究”“文明與宗教研究”“大國治理的規模與效能”六個專題專欄,刊文凡19 篇。
從1921年至2021年,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百年征程,這一百年既經歷了中國的風雨與彩虹,也見證了世界的動蕩與發展。本期刊發一組三篇文章,以為百年之慶留下深刻的學術印記。中國共產黨一直重視對于建黨的紀念活動,紀念是為了不忘初心,紀念是為了總結歷史,紀念是為了開創未來。而在這些紀念活動中,情感維度是始終貫徹如一的。對歷史的敬畏,對英烈的敬仰,對人民的尊重,對政黨的自信,對世界的感懷,構成了基本的情感意蘊。簡言之,一部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也同時是一部中國共產黨情感史。這也印證了一個基本規律:情感不僅影響歷史,也構建著自身的歷史。政黨、歷史與情感的關系研究是一個有待深化和強化的學術領域。陳金龍的文章對此做了相當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中國共產黨瑞金時期和延安時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廣州時期”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合作,則為此后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礎。趙立彬的文章集中關注這一時期,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觀點。
在一般人的認知中,“文學”大概屬于可感知而難確定的一個概念,包涵著極大的彈性空間,所以喜愛“文學”的人可以到泛濫成災的地步。其實他們喜歡的到底是什么東西,還是需要進一步考量的,至少有大量的非文學的東西被摻雜到“文學”的范圍中了。這大概是文學研究者在直面現實生活中被標為“文學”的作品時深感不安甚至恐懼的原因之一了。大凡我們使用一種概念,敬畏是第一要務。如果概念本身在游離之中,則我們的認知和判斷也必然是飄忽的。而要把敬畏落實,就必須對概念在外延和內涵上進行精準的界定。至少名詞的演變不等于概念的演變,文獻的臚列不等于意義的剖析。一一勘察語境,把握同一系列概念之間的銜接點,才是界定概念的有效途徑。就“文學”這一概念而言,古今中外皆在使用。中國最早的“文學”詞源見諸《論語·先進》,與德行、言語、政事并列為“孔門四教”,“文學”一門的代表人物是子游與子夏。此后從范寧、皇侃到邢昺等人對《論語》的義疏中可知,“文學”一詞大率以博通先王典文為要義。魏晉以降,相關辨析愈趨精微而各有其致,既有返歸舊義,也有另立新說,當然也有彌綸群說者。張伯偉《重審中國的“文學”概念》一文,立足“中國”的文學概念,但在梳理中國的“文學”概念的歷史流變過程中,也時時參酌東西方對“文學”的種種界定,因此而帶有一種兼具全球化、集成性與精準度的認知視角。這應該是“文學”研究中不可忽略、難以替代與值得敬重的成果。
2017 年深秋,我因為工作關系,曾到訪巴黎,下榻的地方距離巴黎圣母院不過二三百米之遙。巴黎老城的建筑都已經有數百年之久,滄桑與古意酣暢而磅礴地彌漫在藍天之下,令人震撼,恍然穿梭在老舊的時光之中,而我希望邂逅的就是雨果。我一直覺得,對巴黎而言,雨果就是沉淀在歷史深處的一個精魂,氤氳著這個城市的氣象和精神。而在廣州的康樂園,就有個始終堅守著“我要回到雨果身邊”的八十多歲的老人,他就是法語教授程曾厚。一個人用四十多年的時間沉浸在自己的研究對象中,這是一種只有把學術當信仰的學者才有可能做到的。程先生早年求學北大,后來任教南京大學,側重在語言學的研究和教學。而他移席中山大學后,主要精力便集中在對雨果作品的翻譯、考訂以及與中國文化的關系研究上。他研究雨果不只是從文本到文本,而是注重走進雨果的創作現場,將實地踏訪、情感共鳴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所以他呈現出來的雨果是帶著體溫和鮮活的。他考訂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的“巴特勒”乃是杜撰的收信人,連書信的撰寫日期也是虛擬的。正在高城居埋頭撰寫《悲慘世界》的雨果對當時東方中國發生的圓明園劫難,并未及時關注,更遑論寫這樣一封書信了。他拍下了巴黎雨果故居“中國客廳”中諸多來自圓明園的陳列之物,他對《雨果和圓明園》一書的構想,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從腳下到眼前再到書中的。
本期“中國文體學研究”專欄涉及碑文、傳記、制義與小說四種文體,而跨文體研究成為值得注意之處。蕭統《文選》收錄的《頭陀寺碑文》,內容上跨僧俗兩界,中土建筑話語與佛教寺院、佛理結合,多種文化的介入,使寺碑文帶著別樣的風味。而傳記文體與肖像畫都以人物為中心,其間的關系乃是自然而當然的,尤其在內涵和功能上的重合更具意趣。胡大雷、趙宏祥二文于此各有專論。
“文明與宗教研究”專欄這次刊載了日本、匈牙利和美國學者的三篇文章,皆為專精之作,或探究敦煌出土元代回鶻文書中的行在緞子,或評騭摩尼教審判繪畫,或考訂蒙古史書中提到的亦列、合答、豁孛格禿兒三位金朝將領的情況。選題冷僻一些,但三文并有發明。我讀這三篇文章,竟然想起了1926 年9 月6 日王國維在陳寅恪到清華報到后致信羅振玉云:“頃陳散原之幼子名寅恪者已至學校,此人學東方言語學,言歐洲學問界情形甚詳,言倫敦有漢文摩尼教贊頌一卷,已印行,此卷甚有關系。又《元秘史》原本本藏圣彼得堡者,今在伯希和處,擬設法照之,但所費甚巨耳。”元史、摩尼教、言語學、西學,這些關鍵詞絡繹奔會在一信之中,暗合本組文章者甚多,諒陳寅恪若在世,或因標題誘惑而略起瀏覽之心。
本質上說,要認知一流的哲學家,需要同樣一流的哲學史家。因為面對思想的高峰,俯視的概率既然渺茫,仰視也同樣失去部分意義,而平視的學術才有可能是端莊敬肅的。康德是西方哲學的永恒話題,其淵深博大的哲學思想令后人往往沉潛其中而難識東西,或窺其一鱗半爪而以為思致已盡,讀不盡的康德大概是這樣形成的。但學術史的格局從來就是多維的,對學術史的推進也需要多方合力才能完成,這就是學術研究的責任和使命所在了。本期發表兩篇康德研究的文章:一篇論康德對強化版本體論證明的系統批判;一篇疏解康德的意志理論。對康德研究來說,此二文是各照隅隙,還是偶觀衢路,此當留待學術史的評判了。
中國是泱泱大國,在世界格局中,大國與小國的治理模式肯定有異。其實不遑說國與國之間,即一國之內不同區域之間的治理也存在差異。北宋慶歷八年(1048),歐陽修從滁州轉知揚州,在揚州呆了一年多,因為深陷于當地各種政治糾紛之中而生厭倦之心,所以就以有眼病為由,管理不了大揚州,要求去小一點的地方,結果還真的如愿所償去了潁州。看來地方大小對管理者的心態和能力也有著一定的制約作用。國之大小也類此。本期由韓志明主持的專題“大國治理的規模與效能”刊文兩篇,就規模焦慮與簡約治理、政府效能和政府規模之間的隱性張力展開論說,不僅契合歷史,也契合當下,其意義是顯在的。
時維七月,嶺南暑氣蒸騰。一期編訖,竟無詩興,異哉!這讓我聯想起清人江弢叔有詩云:
我要尋詩定是癡。詩來尋我卻難辭。
今朝又被詩尋著,滿眼溪山獨去時。
我有“尋詩”之心,無奈詩無“尋我”之念,看來都市書齋終究難敵滿眼溪山。下一期編后記當另覓林木水流勝處,待詩心涵養充盈,再把玩諸君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