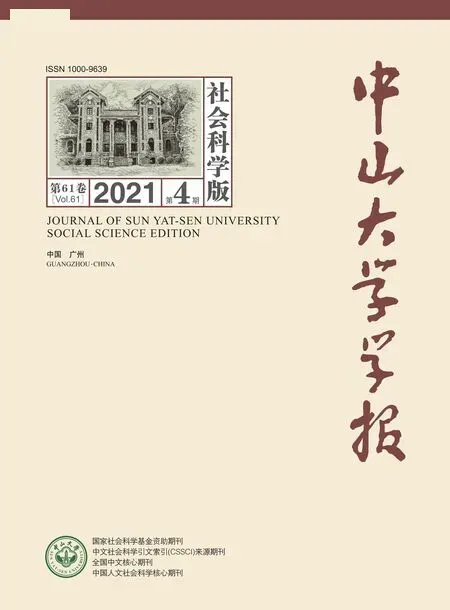理性與情感的統一:康德意志理論疏解*
董濱宇
一直以來,康德倫理學以其極具代表性的理性主義特征而受到情感主義者的攻擊。在情感主義這一廣泛的流派中,亞里士多德與休謨的相關學說往往被視為古代與近代兩個最重要的來源。亞里士多德將“德性”或者“美德”視為幸福生活的根本,而“德性”的本質則是理性與情感的內在和諧狀態。休謨則指出,“同情”是道德行為的根本動機,而理性只是負責提供適當的指導原則。在某種意義上,當代美德倫理學可以說是情感主義發展至今的一種頗有代表性的學說。很多當代美德倫理學學者都站在休謨主義的立場上反對康德,其中,康德將道德動機的根據視為“理性”而非“情感”,這在他們看來完全是錯誤的,這必將導致道德主體及其行動的一系列難以解決的問題。然而,這些質疑很大程度上是偏激的,情感主義者們未能看到的是,康德倫理學雖然以道德義務為中心,但就道德動機這一概念而言,它既是理智化的,也是感性化的。準確地說,它的理論根據是“理性”,但它的現實根據是以“敬重”為核心的實踐性情感。在康德復雜的理論術語中,它們其實都相當于其所說的“意志”乃至“理性”。對此,我們將結合文本做出深入的分析。
一、情感主義者的不滿
以休謨為代表的英國情感主義者早就認為,感性情感或者欲望才是道德的根源與動力,而理性只是提供具有指導作用的原則而已。“同情是我們對一切人為的德表示尊重的根源。”①[英]休謨著,關文運譯:《人性論》(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620頁。當代美德倫理學繼承了這一觀點,其中一些學者指出,康德將道德動機的根據置于“理性”之中,這實際上是錯誤的,它將帶來一系列難以解決的認識與行動上的難題。尤其是,由于理性與情感的分裂,康德式的道德主體將會遭遇嚴重的內心沖突的麻煩。
康德將行為者的道德動機僅僅視為對于道德法則的尊重,這在一些情感主義者看來很可能導致行為者動機與信念的不一致,斯托克爾(Michael Stocker)將此種情況稱為一種“精神分裂癥候”。倫理規則表達的是“應當”,而它未必與行為者的動機是相一致的。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你的理性認可一個道德法則,但是它并不構成你的真實的欲望。由此將產生兩種后果,要么你的信念并不能促成真正的行動,要么就是你表面上依照法則的要求這樣去做了,但其實內心情感是與之對抗的,從而出現了所謂的“精神分裂”。
斯托克爾的這一批評與威廉斯關于“內在理由與外在理由”的觀點相關。威廉斯指出,所謂“內在理由”,是指行動者出于內心的真實欲望而行動,在這里,動機與理由是相互一致的;所謂“外在理由”,是指行為者的動機與理由相分離,此時,作為外在理由的規范性原因無法作為行為者的真實動機①[英]伯納德·威廉斯著,徐向東譯:《道德運氣》,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第145頁。。無論是在斯托克爾還是威廉斯那里,作為休謨主義者,他們都認為只有情感、欲望等這些經驗性要素才能作為行動的內在理由,然而,像康德那樣將實踐理性及其法則作為動機,其實就會導致一個無效的結論。因為僅僅作為一個“外在理由”,它缺少轉化為行動的“內在理由”的根據。理性主義者以實踐理性及其法則作為行動的理由,在斯托克爾看來是不夠的,因為前者錯誤地以為道德上的良好意圖就會自然地轉化為行動上的動機。恰恰相反,現實世界中存在著大量這樣的現象:一個所謂的出于義務的要求而行動的人,其內心里卻充滿了抵觸。站在休謨主義的立場上,斯托克爾堅定地認為,理性與情感、動機與理由必須統一協調起來,由此才能激發真實的行動,而且只有如此,行動者才不會陷入二元的、“精神分裂”的生活。斯托克爾進一步指出,只有那些基于愛、友誼、同情、和諧親善等自然情感的行為才是值得肯定的,他們行動的動機就是理由。
斯托克爾以及威廉斯的觀點激發了很多討論。從道德動機問題出發,情感主義者否認理性及其規則有資格作為行動的原發性力量。他們站在休謨的立場上,認為理性對于激情只是起到調解作用,而真正激發行動的則是欲望或者情感。斯托克爾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只有以情感為依據,由“理性至上主義者”所導致的這種“精神分裂”才能得到治愈。首先,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一個好人就必須擁有正確的情感,它能夠指導人如何行動與如何生活。其次,像康德等理性主義者都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即認為情感、欲望僅僅是盲目的本能沖動,它們并不具有任何鑒別與判斷的能力,而只有理性才能夠承擔這一任務。相反,斯托克爾認為,情感本身擁有評價性功能,即能夠產生認知性行為。他以亞里士多德關于“憤怒”的論述為例指出:“在亞里士多德那里,被輕視就是被否定了適當的重要性與適當的尊重。因此,無須特意證明,憤怒之人必然會認為自己由于被否定了適當的尊重而受到了道德性傷害。因此——假設我的憤怒完全像亞里士多德所描述的那樣——如果你被輕視,那么我的憤怒就表明我仍然在意你是我的朋友。相似地,我在音樂會上感到厭倦,可能就表明我并不重視音樂或者這場演出。因此,情感能夠給我們提供關于評價的信息。它們與評價本身也有著系統的、認知性的聯系。”②Michael Stoker,How Emotions Reveal Value and Help Cure the Schizophrenia of Modern Ethical Theories,in Roger Crisp,Michael Slote,ed.,Virtue Eth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24-125.可見,我們通常所認為的無意識的情感,其實都是在某種理由的基礎上發生的,而這就意味著情感本身必然帶有一定程度的評價性功能。這一主張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們的認同,他們認為,情感并不是盲目的沖動,它能夠通過自身的敏銳感知而針對復雜的情境做出相應的判斷,甚至這種判斷比理性更加準確。
二、欲求、任性與意志
面對情感主義者們的強烈質疑,現在的問題是,康德真的是將道德動機的根據視為與情感完全相對的理性么?事實并非如此,在康德那里,理性與情感并未分離開,相反,就作為一種實際能力來說,它們共同居于“意志”之中,在康德的語境里,它也相當于一種廣泛意義上的“理性”,同時,它具體地表現為“對法則的敬重”這一情感狀態。
首先,應該說,康德確實主要是將純粹理性以及道德法則作為道德行為的動機以及根據。不過,文本似乎給我們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表述。一方面,“法則是獨一無二的動機”(Rel:37)。“道德法則作為動機的作用僅僅是否定的,而且作為這樣的動機,這動機是能夠被先天地認識的。”(KpV:72)另一方面,在《實踐理性批判》的“純粹實踐理性的動機”中,康德又表明:“對道德法則的敬重是惟一的、同時無可懷疑的道德動機”。(KpV:78)要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闡釋,就應該依據《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中那句著名的表述:“欲求的主觀根據是動機,意欲的客觀根據則是動因。”(GMS:427)①本文所依據的中譯本是李秋零主編的《康德著作全集》(簡稱《全集》)。康德的主要倫理學著作如《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簡寫為GMS)出自《全集》的第4卷(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實踐理性批判》(簡寫為KpV)、《純然理性限度內的宗教》(簡寫為Rel)、《道德形而上學》(簡寫為MS)出自《全集》第6 卷(張榮、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同時,本文還參考了劍橋版的英譯本(Immanuel Kant,Practical philosoph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J.Grego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中譯本與英譯本都是依據普魯士王家科學院版《康德全集》譯出。為方便起見,本文所用引文僅標出康德著作的簡寫形式及其編碼。這里,“動機”(Triebfeder,ince?tive)實際上就相當于“對法則的尊重”,因為它只能是一種主觀性的感性情感,是促使道德行動產生的直接原因,而“動因”(Bewegungsgrund,motive)則相當于作為意志的根據的道德法則,它是純粹實踐理性的產物。理性存在者是在認識到法則的正確性與權威性之后,出于對它的尊重而決定有所行動,即“對道德法則的敬重是一種通過一個理智根據造成的情感”(KPV:73)。然而,正如貝克所注意到的,在第二批判中,康德混用了這兩個概念,尤其是在“動因”的意義上使用了“動機”一詞。顯然,康德本人并未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②Lewis White Beck,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91.。貝克又指出,在雅培(T.K.Abbott)的譯本中,“動機”被譯為motive 或者Spring,這是一個不錯的翻譯,因為德文Feder本身指的是鐘表的主要發條③Lewis White Beck,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p.91.。這一看法在恩斯特龍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的闡釋,他認為,將“動機”譯為incentive 是不對的,難以準確地表達出康德所賦予它的精微涵義。因為在英文中,incentive是有外在對象或者目的存在的前提下所發生的一種效應,而康德所說的“動機”(Triebfeder)更主要地是作為選擇或者行動的內在源泉,它具有潛在的活性力量,因此,最好譯為“規定性力量”(determining force)或者“促發力量”(motivating force∕driving force)。恩斯特龍同時還建議,在第二批判中,Triebfeder在康德那里既包含著作為促發力量的“動機”,也包含著作為意志的規定根據的“動因”。前者是一種主觀狀態,具體表現為情感,后者是一種客觀原因,具體表現為法則。而且,更重要的是,康德借此是要解決“是”與“應該”的問題:“客觀原則是我們應該如何行動的依據,而就它是一個既定的主體的確這樣去行動所依據的原則來說,它又是一項主觀性原則或準則。同樣,我主張,被視為意志的客觀規定根據的道德法則就是意志應該被如何規定的表象;這一法則也被視為一個給定的主體意志的主觀規定根據,它是實際地規定主體意志的同一個表象。”④Stephen Engstrom,The Triebfeder of Pure Practical reason,in Andrews Reath and Jens Timmermann,eds.,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A Critical Guid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90-93.這篇論文比較準確地揭示了康德義務論的動機理論。
在這里,要準確地理解康德的“道德動機”概念,一個極為關鍵的環節就是要把握“欲求”(Begehren,desire)或者“意欲”(Wollen,volition)的真實涵義。在《道德形而上學》中,康德具體闡述了這種“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gen,faculty of desire):“就是通過自己的表象而成為這些表象的對象之原因的能力。”(MS:211)作為一種因果性活動,欲求能力能夠自己產生對象,可以說,它就是人的一種主觀的意愿能力。而且,欲求能力與情感有著必然的聯系:“人們可以把與欲求(對其表現如此刺激人的情感的那種對象的欲求)必然相結合的那種愉快稱為實踐的愉快。”(MS:212)康德又將它特意與“情欲”(Konku?piszenz,concupiscence)做了區分,后者是一種單純的感性能力,能夠作為“規定欲求的誘因”,不過,由于只是毫無理性的感官沖動,因此并不能夠像欲求能力那樣在心靈上規定行動(MS:213)。可見,相對于情欲,欲求能力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蘊含著潛在的理智性功能;其次,作為“一種根據喜好有所為或者有所不為的能力”,欲求能力又分為兩種形式:“如果它與自己產生客體的行為能力的意識相結合,那它就叫做任性(Willkür,choice)。但是,如果它不與這種意識相結合,那么,它的行為就叫做一種愿望(Wun?sch,wish)。”所謂“任性”,是指“雖然受到沖動的刺激,但不受它規定,因此本身(沒有已經獲得的理性技能)不是純粹的,但卻能夠被規定從純粹意志出發去行動”(MS:213)①關于Willkür,韓水法譯為“意愿”,([德]康德著,韓水法譯:《實踐理性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相當于英文的volition,鄧曉芒譯為“任意”,([德]康德著,鄧曉芒譯,楊祖陶校:《實踐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李秋零則譯為“任性”。筆者認為,“意愿”更符合德文的原意,因為它更加具有中性化色彩,而另外兩個詞都偏重于主觀性的自由活動,與理性相去較遠。需要注意的是,在康德那里,Willkür 并不意味著沒有理性,而只是在與Wille 相互區別的意義上,指并不依照純粹理性來行動,然而,它卻仍然離不開慎思理性或技藝理性,以便實現主體的目的。顯然,“意愿”能夠更加準確地表達這種一般性的欲求能力。為求表述上的一致,本文仍然主要使用“任性”一詞,然而其間的差別,卻不可不察。另外,Gregor 的劍橋版英譯本則譯為choice,相當于中文的“選擇”,也比較準確地表達了Willkür 的中性化涵義,而且顧及了理性在其中的作用。不過,相對于漢語的“意愿”,choice 喪失了其中所蘊含的主觀能動性因素,在這個意義上,choice其實不如volition(意愿)更加準確。。重要的是,康德又提出了一個與“任性”直接相關的概念,就是“意志”(Wille):“如果欲求能力的內在規定根據,因而喜好本身是在主體的理性中發現的,那么,這種欲求能力就叫意志。所以,意志就是欲求能力,并不(像任性那樣)是與行動相關來看的,而是毋寧說與使任性去行動的規定根據相關來看的,而且意志本身在自己面前真正說來沒有任何根據,相反,就理性能夠規定任性而言,意志就是實踐理性本身。”(MS:213)這里,康德把意志與任性區分開了,但是,接下來他似乎又把二者等同起來:“就理性能夠規定一般欲求能力而言,在意志之下可以包含任性,但也可以包含純然的愿望。”(MS:213)貝克認為,意志和任性都屬于一種統一性的意愿能力,而我們通過對于任性的“回溯”,能夠獲得對于意志的理解。有時候,康德將二者區分開,而有時候又將它們統稱為“意志”。然而,具體來說:第一,意志屬于立法能力,而任性屬于執行能力,意志是由純粹理性加以規范的任性。第二,由于不涉及行動,意志不包含動機要素,而任性則必然蘊含著動機。第三,意志是本體性的概念,任性則是這一概念在現象界的表現,所以會受制于經驗要素的影響,因此有時候是不自由的。第四,意志產生法則,而任性產生準則,不過,在隸屬于意志時,它也會成為服從法則的純粹實踐理性。第五,任性是自由的,它有兩種情況:消極的與積極的,消極的任性是指獨立于感性沖動的規定,而積極的任性是指作為純粹理性,它本身能夠產生實踐活動。在意志之中,兩種任性的自由能夠達到統一。第六,在貝克眼中,意志是“自律的”,而任性則是“自發的”②Lewis White Beck,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p.176-208.。伍爾特則認為,意志相當于西季威克所說的“善的或理性的自由”,即主體只有在遵守道德法則的情況下才會獲得的自由,而任性相當于西季威克所說的“中立的或道德的自由”,即主體在道德與非道德之間進行選擇的自由。由此,西季威克對于康德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即“中立的或道德的自由”)的批評是不成立的。而且,伍爾特認為通過“任性”這一概念,康德引入了意志主體在進行選擇時所必須具備的經驗性的情感要素,如尊重、愉悅等①Julian Wuerth,Kant on Mind,Action,&Eth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236-243.。
欲求能力和情感確實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康德在“導論”中指出,所謂的“情感”,是指一種與欲求或憎惡相結合從而產生實踐性的愉快或者不快的感受。同時,愉快的感受并不總是由欲求所產生的,而可能是通過鑒賞活動所產生的純然沉思的或者無為的愉快。不過,康德認為,就欲求而言,既存在著一種感性偏好的愉快,也存在著一種“近似于”鑒賞活動的“無為的愉快”,康德稱之為“理性興趣”,它是純粹的、無關乎功利的一種“繼欲求能力的先行規定而起”的理智的愉悅(MS:212)。這種愉快的感受既可以作為欲求的根據,也可以作為欲求的結果。結合康德以往的見解,前一種情況下將產生他律的行為,而在后一種情況中,如果是以道德法則為根據,以出于對法則的敬重而行動,那么所產生的就是自律者的純然愉悅的感受。
以上的論述能夠讓我們更加清楚地明白“道德動機”所具有的獨特意義。康德顯然意識到道德行動的促發力量與運行機制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關乎一項正確的法則如何轉變為實際行動。然而,在情感主義者看來,真正能夠促發行動的動機只能是作為感性情感的同情或者仁愛,康德主義者試圖以理性作為道德行為的基礎是并不成功的。而且,情感并不是盲目的,它具有一定的認知性功能,相比于理性,它是更加原初的能力,甚至能夠做出更加準確的道德判斷。然而,站在康德主義立場上的學者們認為,理性能夠作為道德動機,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實踐能力,而這種能力是通過“對法則的敬重”這一基本情感表現出來的。重要的是,正如康德所認為的,自然情感是盲目的、無知的感性沖動,而作為一種思維能力,只有理性才能夠產生具有指導意義的道德法則。我們則進一步認為,情感主義者的批評主要源于他們并沒有完全了解康德倫理學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或者說他們忽視了這些概念的復雜性含義,尤其是“意志”與“理性”的真正內涵以及二者的內在關系。
首先,在“意志”這一概念之外,康德其實將“欲求能力”視為更加一般化的心靈活動。在初始意義上,意志就是一種欲求能力,只是它與理性法則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正如我們此前所分析的,在康德那里,意志包含著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指作為規定性根據的“意志”(Wille),二是指作為實際選擇能力的任性(Willkür)。二者最明顯的差別是,相對于前者,后者具有“動機”的功能,即將法則轉化為行動的能力。不過,二者通常是作為一個概念——“意志”(Wille)而被康德加以運用的。從這一點來看,似乎可以這樣認為,康德其實是通過具有統一性內涵的“意志”(為方便起見,我們將其稱為意志Ⅱ,而將它所包含的只作為規定性根據的意志稱為意志Ⅰ)來指稱一種既能夠確定法則又能夠以此為動機而產生實際行動的能力。而且,康德有時也將這種統一性“意志”(意志Ⅱ)與“理性”等同起來,即理性也是一種欲求能力:“自身幸福的原則,無論在它那里使用了多少知性和理性,對于意志來說畢竟只包含有與低級的欲求能力相適合的規定根據,因而要么根本不存在高級的欲求能力,要么純粹理性必須就自身而言就是實踐的,也就是說,僅僅通過實踐規則的形式就能夠規定意志,無須以任何一種情感為前提條件,因而無須愜意或者不愜意的表象,愜意或者不愜意是欲求能力的質料,這種質料在任何時候都是原則的一種經驗性的條件。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理性惟有為自己本身來規定意志(不是為偏好效力),才是在病理學上可規定的欲求能力所從屬的一種真正的高級欲求能力,并且現實地、甚至在種類上與前一種欲求能力有別……理性在一個實踐法則中直接規定意志,并不借助參與其間的愉快和不快的情感,哪怕是對這一法則的愉快和不快的情感,而是惟有它作為純粹理性就能夠是實踐的這一點,才使它有可能是立法的。”(KpV:24-25)
顯然,在康德那里,已經對于欲求能力做出了低級與高級之分。只要是實踐規則將其根據設定為純粹的形式,那么這種欲求能力就是高級的,而如果設定為經驗性質料,那么這種欲求能力就是低級的。前者就是以道德法則為動機,而后者則是以情感或者欲望上的愉悅與滿足為動機,前者屬于將任性置于意志之中的活動,而后者則只屬于任性的活動(KpV:24)。作為高級的欲求能力,意志Ⅱ同時就相當于理性①康德在很多地方都表明理性(實踐理性)就是意志,或者更準確地說,就是我們所說的意志Ⅱ。“既然為了從法則引出行為就需要理性,所以意志無非就是實踐理性。”(GMS:412)“就理性能夠規定任性而言,意志就是實踐理性本身。”(MS:213)。
據此,可以說,康德的“意志”(如不做特別說明,以下都指的是意志Ⅱ)與“理性”首先都是一種“欲求能力”。很多時候,這兩個概念是等價的,即意味著依據法則而行動的意愿。正如康德所一再表明的,理性本身就具有一種實踐性:“純粹理性單憑自身就是實踐的,并給予(人)一條我稱之為道德法則的普遍法則。”(KpV:31)純粹理性既能夠產生行動,也能夠產生行動的原則。同時,它也是純粹意志:“因為純粹的、就自身而言實踐的理性在這里是直接立法的。意志作為獨立于經驗性條件的,作為純粹意志,被設想為被法則的純然形式所規定的,而這個規定根據則被視為一切準則的最高條件。”(KpV:31)可見,應該時刻注意到,在康德的文本中,意志與理性擁有著不同層次的涵義,要結合具體的語境才能對其進行準確的理解。由于理性相當于意志,因此,我們也應該對其做出進一步區分,即作為僅僅確立原則的理性(理性Ⅰ)與既能夠確立原則也同時具有行動能力的理性(理性Ⅱ)。也就是說,理性Ⅱ和意志Ⅱ也是等價的。在康德哲學的概念體系中,正像“意志”既包含著意志Ⅰ(純粹理性及其法則)也包含著任性一樣,“理性”也由于擁有實際的執行能力而能夠成為道德行為的動機。康德在《奠基》中的一段話十分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現在,人在自己里面確實發現一種能力,他憑借這種能力而把自己與其他一切事物區別開來,甚至就他被對象所刺激而言而與它自己區別開來,而這就是理性。理性作為純粹的自動性,甚至在如下這一點上還居于知性之上:盡管知性也是自動性,并且不像感官那樣僅僅包含惟有當人們被事物刺激(因而是承受的)時才產生的表象,但他從自己的活動出發所能夠產生的概念,卻無非是僅僅用于把感性表象置于規則之下并由此把它們在一個意識中統一起來的概念;沒有這種對感性的應用,知性就不會思維任何東西;而與此相反,理性在理念的名義下表現出一種如此純粹的自發性,以至于它由此遠遠地超越了感性能夠提供給它的一切。”(GMS:452)
可見,康德所說的“理性”其實是一種具有“純粹自發性”的實踐力量。而休謨式的情感主義者的誤解就在于,在他們的概念體系中,“理性”只是一種能夠產生理由或者原則的推理能力,至于經驗性的實際行動則必須用與這種“理性”完全判然有別的情感或者欲望去推動。這種觀點在威廉斯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表達,在他看來,只是作為“純粹的理性思維過程”,康德的“定言命令”屬于“外在理由”,而不是能夠促發行動的“內在理由”,因為只有情感或者欲望才能作為這種“內在理由”。
按照情感主義的見解,只有感性情感,或者康德所說的“偏好”才能夠真正地促發行動。但是,在康德那里,任何感性要素都不可能被作為道德行動的根據與動機,否則就喪失了行動的道德屬性。對于這種深刻的對立,本文認為,康德通過“意志”與“任性”確實提出了一種具有獨特含義的“理性”的概念,也就是以上所說的理性Ⅱ(或者意志Ⅱ),由于必然與情感相關,作為欲求能力的“理性”或者“意志”,既是一種理智性活動,也是一種情感運作,因此,它既屬于本體世界,也屬于現象世界。按照先驗哲學的觀點,它體現著人的“理智性品格”與“經驗性品格”的統一。
在《奠基》的第三章,康德區分了“兩個世界”:對于人而言,“就純然的知覺和感覺的感受性而言把自己歸入感官世界,但就在它里面可能是純粹活動的東西(根本不通過刺激感官、而是直接達到意識的東西)而言把自己歸入理智世界,但他對這一世界卻沒有進一步的認識”(GMS:451)。這種區分是基于康德在其理論哲學中所確立的“現象∕物自身”這一對概念所做的進一步闡述。康德認為,由于受到先天的感性形式的限制,我們只能夠認識現象世界,而對于作為其根據的物自身卻無法形成知識。某種意義上,物自身相當于“本體世界”。對于理性存在者來說,他的品格同時對應于兩個不同的世界:“首先,就它屬于感官世界而言,它服從自然法則(他律);其次,就它屬于理知世界而言,它服從不依賴于自然的、并非經驗性的、而是僅僅基于理性的法則。”(GMS:452)只是從兩種不同的視角(現象的與非現象的,即本體的)來說,“兩個世界”對于理性存在者才是存在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康德稱其為“經驗性品格”與“理智性品格”。重要的是,主體由于擁有統一性的理性而能夠將兩種品格同時置于自身當中。因此,理性存在者既能夠作為現象世界中的主體,通過理性(知性)對于自然世界的認識而掌握經驗性規律,又能夠作為本體世界中的主體,通過理性(意志)形成道德法則并且產生相應的行動。在前者那里,人是受因果性法則所支配的不自由的主體;而在后者那里,人是能夠以自己的意志作為原因從而“開啟”一項行動的自由的主體。
由此可見,作為一種統一性能力,理性以其認識性功能與實踐性功能將主體同時確立為本體世界與經驗世界的存在。從思維的角度來說,我們是自由的,但對這種先驗理念我們并不能獲得更多的認識,然而,它可以反映到現象世界中來,即通過道德行動證明這種本體性自由確實是存在的。“如果我們設想我們是自由的,我們就把自己作為成員置入知性世界,并認識到意志的自律連同其成果,亦即道德性;但如果我們設想自己負有義務,我們就把自己視為屬于感官世界,但同時也屬于知性世界。”(GMS:453)從這一基本觀點出發,可以認為,康德所說的“理性”,其在本體世界擁有著作為行動指導原則的理由,而在現象世界則仍然呈現為一種具體的感性情感。也就是說,這種統一性的“理性”(理性Ⅱ)在兩個世界中分別擁有兩種狀態,而后者是前者在經驗性條件下的“映射”,即作為根據的理性(理性Ⅰ)及其原則,它必然將以感性的方式表現為行為的動機,這就是康德所說的最為重要的道德情感—對道德法則的敬重。前一個世界相當于康德所說的“知性世界”或者“本體世界”,后一個世界屬于“感官世界”或者“現象世界”。同時,作為理性Ⅰ,康德將其稱為純粹的、認知性的理智能力,而作為理性Ⅱ,它不僅包含了理性Ⅰ,也同時具有實踐性的執行能力。作為一種欲求能力,理性Ⅱ或者意志Ⅱ,將本體與現象、理智與情感連接起來,規定了道德主體的統一性的品格。
三、理性與情感的關系:理論的與實踐的①通過本文以上的分析,在不做特別說明時,一般所說的“理性”就是指理性Ⅱ,它既具有理性Ⅰ的認知能力,又具有能夠促發行動的、作為“敬重”的情感能力,而在與“情感”相對的意義上,我們所說的“理性”則指的是僅僅作為認知、推理能力的理性Ⅰ。
貝克指出,康德在第二批判中并沒有清楚地區分出“動機”與“動因”,因此給我們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亂。但是,現在看來,這種區分至少對于康德來說并不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它們都是同一于“理性”之中,或者說,只是理性在不同維度的表達。因此,幾乎在同一處,康德既說道德法則是動機,又說對道德法則的敬重是惟一的道德動機(KpV:78-79)。其實,正像本文所一再論證的,如果說道德法則是客觀根據,那么敬重就是主觀根據。不過,一些學者仍然認為,有必要在根本層面上說清楚,究竟何者在康德那里才是真正的道德動機。麥卡蒂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是典型的理性主義解釋,像瑞斯就認為:“是敬重的理智性方面在促發道德行動時發揮著作用,然而它的情感性方面,即敬重的情感,則是這一理智性方面對于某種感性傾向的效果。”“當道德法則規定意志時,那么尊重的情感就產生了,然而并不是這一效果產生了動機。”②Richard McCarty,Kant’s Theory of A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70.其中,麥卡蒂所引用的瑞斯的觀點出自Andrews Reath,Kant’s Theory of Moral Sensibility:Respect for the Moral Law and the Influence of Inclination,Kant’s-Studien,1989,Vol.80,pp.284-302,p.287,p.290。第二種解釋也屬于理性主義,是由斯特拉通-萊克(Stratton-Lake)提出的,他和瑞斯一樣,認為只有對于法則的認識而非敬重的情感才能夠作為根本性動機。不過,二者的區別集中于這種情感與“關于道德法則的認識”的關系上。瑞斯認為尊重是由這種意識所引起的,二者是因果性關系;而斯特拉通-萊克認為二者是同一的,即尊重不是這種認識的附帶產物,而是它的另一種描述。
麥卡蒂進一步表明,第三種解釋是情感主義的,以格瓦拉(Guevara)為代表,他認為尊重的情感就是道德動機,它既是由對法則的認識產生的,又是與這種認識同一的。對于麥卡蒂來說,他更支持第三種解釋,因為在他看來,僅僅以具有約束性作用的道德法則為動機,而忽視了主觀性的情感,對于行動本身來說力量有些太弱了。不過,格瓦拉的解釋中蘊含著一個觀點,即尊重的情感被視為由道德法則規定的本體性的意志在感性世界的對應物,然而,這將導致理解上的困難:我們該如何解釋道德上的軟弱?這種現象是否也意味著某種本體世界中的道德軟弱?也許,人們會猜想,是因為本體世界在表象為現象時某些東西喪失了,或者在本體世界中,意志是絕對地、充分地被法則所規定的,只是現象世界對它的模仿太過于粗糙了①Richard McCarty,Kant’s Theory of Action,pp.171-173,p.175,pp.176-177.。
麥卡蒂認為,這些解釋都是很有道理的,但不能令人完全滿意。他的觀點是,并不應該將尊重的情感視為由道德法則所規定的本體性意志的感官表象。所謂本體、或者物自身,是就對象而言的。然而,尊重卻是我們自己的情感,它并不關乎被表象的對象。“在表象一個對象時,我們所感到的愉悅并不涉及作為一個對象的自身。也就是說,我們感到愉悅與否并不是將我們自己的意志作為一種觀念。情感可能是包括身體或者精神活動在內的感官顯象的主觀反應(reactions),也可能是物自身理念的主觀反應,但不是這些事物的顯象(appearances)。因此,康德并不認為尊重的情感就是本體性意志的顯象。他的主張是,這種是否愉悅的情感起源于一個行動是否符合道德法則的認知。”②Richard McCarty,Kant’s Theory of Action,pp.171-173,p.175,pp.176-177.
麥卡蒂指出,作為實踐情感的敬重,就是一種“啟動性”的力量,它是基于主體對道德法則的認識。首先,客觀性法則提供了動機的方向;其次,主觀性的敬重情感提供了力量。對于不同的人而言,客觀性方向是同一的,但主觀性力量卻有可能是不同的,有的人會感到快樂多一些,而有的人則會感到痛苦多一些。對于此前的三種解釋,他認為第一種和第三種更為正確,因為它們都主張尊重只是由法則所規定的意志的效果(effect)。然而,它們的不恰當之處在于,第一種解釋否認了敬重所具有的“動機”角色,而僅僅把它當作理性認知的附帶效果;相比而言,第三種解釋正確地承認了這一點,但它一方面將意志與情感的關系解釋為本體與現象的因果關系,另一方面,相比于同樣可以作為動機的偏好,這種情感所具有的多變性的動機力量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闡釋③Richard McCarty,Kant’s Theory of Action,pp.171-173,p.175,pp.176-177.。
可見,麥卡蒂的觀點與我們之前的分析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主要是,他反對將受到法則所規定的自由意志與作為道德情感的敬重解釋為本體與現象的因果性關系,而且,兩方面若是完全對應的,那么也就不存在作為現象的情感的多樣性變化。不過,如果仔細分析,這種觀點實際上與我們此前的理解并沒有太大的差異。因為麥卡蒂首先承認,本體性的自由意志是必然的存在,只是它如何具體轉化為實際的動機,其中的機制由于超出了人的認知界限而無法被真正地說清楚④在“現象∕物自身”的問題上,麥卡蒂不是“一個世界、兩種視角”的支持者,他批評了科斯嘉、阿利森等人的這一立場。后者主張只存在一個“中性的世界”,只是我們從肯定與否定的兩種視角來考慮,才產生了現象世界與本體世界的概念,也就是說,“物自身”沒有什么獨立存在的意義。麥卡蒂認為,這種解釋無法為真正意義上的道德行為提供有效的說明。只有承認本體世界的實存性,人才會是絕對自由的,而這要通過道德的行動加以實現。本體決定了現象,但是其中具體的運行機制是難以被領會的。經驗性品格不可能賦予人以自由,我們必須承認理智性品格的首要性(Richard Mc?Carty,Kant’s Theory of Action,pp.105-145)。。而麥卡蒂否認了自由意志與敬重之間存在著像本體與現象那樣的因果關系,因為在他看來,情感不是由作為某種物自身的對象的刺激而引起的顯象,而是生發于主體自身之中的感受。然而,本文認為,這種解釋很可能并不符合康德的本意,因為在康德看來,情感屬于我們的內感官,與外感官一樣,它是由某種作為物自身的對象刺激后所產生的顯象。“關于內感官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只是像我們在內部被我們自己刺激的那樣通過它來直觀我們自己,也就是說,就內感官而言把我們自己的主體僅僅當作顯象、而不是按照它自己所是的東西來認識。”(KrV:B156)本體性的自由意志能夠產生一種內感官,它呈現為經驗性的品格,在第二批判中,康德繼續說道:“主體的每一個行動的規定根據都處在屬于過去的時間而且不再受它控制的東西里面(必須歸于此列的也有他的已經做出的行為,以及在他自己的眼中作為現象對他來說可以由此得到規定的性格)。但是,另一方面也意識到自己是物自身的同一個主體,卻也把自己的存在本身就其不服從時間條件而言僅僅視為通過它憑借理性本身給自己立的法則可被規定的,而且在它的這種存在中,對它來說沒有任何東西先行于它的意志規定,相反,任何行動,而且一般來說它的存在的任何按照內部感官變更著的規定,甚至它作為感性存在者的實存的整個序列,在對它的理知存在的意識中都必須僅僅被看作后果,而絕不看作它作為本體的因果性的規定根據。”(KpV:97)當本體性的自由意志反映為作為敬重的道德情感時,由于主體自身特殊的感性要素的影響,將呈現為有所不同的情感現象,但是,“敬重”始終是最為根本性的情感,否則就不會是自由意志的體現。總之,本文認為,即便是麥卡蒂本人也承認,在理論上,對于法則的意識是敬重的情感產生的原因,但在實踐中,二者是同時發生的一種活動。在這一點上,理性主義解釋與情感主義解釋并不存在明顯的對立。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始終基于康德所說的這句話:道德法則是作為客觀根據的動因,而敬重是作為主觀根據的動機。二者的區別其實只具有描述的而非實際的意義。對此,可以借助康德關于“知識”的分析得到更進一步的理解。在第一批判中,康德指出,一切知識都是從經驗開始的,我們沒有任何先行于經驗的知識,但是,這些知識卻并不因此都產生于經驗,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為先天知識的純粹的知性范疇所導致的(KrV:B1)。在現實中,我們必然要同時憑借感性經驗與范疇才能形成真正的知識,但是,在邏輯意義上,范疇起著根本性作用,即范疇先于感性經驗,因為如果不以這些先天的概念為前提條件,那么“就沒有任何東西可能是經驗的客體”(KrV:B125)。通過對于意志的規定,理性不僅產生道德法則,而且理性及其法則就是道德行為先天的根據與動機,但在實際的意志活動過程中,它必然呈現為對于道德法則敬重的情感,康德也將其稱為“理性的興趣”或者“道德興趣”,它是促使行動發生的經驗性的表象與力量。純粹理性既是認識的、也是實踐的,它與敬重的情感是“二而一”的關系,在道德主體那里是同時發生的,但類比于范疇與經驗的關系,在邏輯意義上,純粹理性是在先的,而敬重是在后的。
其實,相對于其他三種主張,麥卡蒂只是在此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完善,從而使其最終的解釋更為“精致”而已。不管怎樣,麥卡蒂也一再表明,對于法則的意識與尊重的情感是同一的,它們統一于既具有理智性品格也具有經驗性品格的主體之中。而在我們看來,它們就屬于“理性”或者“意志”,即理性存在者所擁有的既能夠立法也能夠同時據此產生實際行動的能力。
結語
在康德那里,由于“理性”與“意志”在運作過程中實際上包含著情感要素,因此,并不存在情感主義者所批判的理由與動機之間的割裂,道德主體對于理性法則的認識必然要體現為內心的敬重,從而促使主體采取真正意義上的具有道德價值的行動。其中,康德通過“任性”這一概念,實現了“意志”從“理智性品格”向“經驗性品格”的轉換。并且,原來只具有認知性功能的“理性”擁有了實踐性能力。然而,情感主義者未看到這一點,在他們眼中,康德的“理性”僅僅是一種認知推理能力。但實際上,康德的“理性”既是理論的,又是實踐的,在道德主體那里,它體現為整體性的“意志”。另外,正如我們此前所介紹的,情感主義者們斷定只有情感(同情、仁愛)才能作為道德行為的根本性動機,因為它并不像康德所認為的那樣是無知的沖動,相反,它具有一定程度的認知性功能,從而能夠形成更加合適的道德判斷,而且只有這種純粹的情感或者欲望才能夠產生形成行動的促發性力量,這樣的論斷顯然是偏頗的。實際上,康德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即認知性功能只能來源于作為一種思維活動的理性(理性Ⅰ),作為低級的欲求能力,情感或者欲望只屬于感性沖動,康德稱之為“病理性的”,它們所產生的是心理上或者身體上的單純的知覺,其中不可能包含任何有意識的判斷。只有在理性的參與下,某種判斷才可能發生,而即便是那種極為“薄弱的”判斷,也必然是理性發生作用后的產物。與此同時,在實踐中,理性必須通過感性情感的方式被實現出來。也就是說,二者同一于一種心理活動中,由此才能促使相應的行為實際地發生,從而這種道德情感也具有認知與判斷的功能。作為一般性的欲求能力,康德將其稱為“理性”(理性Ⅱ)或者“意志”(意志Ⅱ)。如果僅僅就自由意志的表象來說,康德其實與休謨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即能夠作為行為動機的必定是一種情感或者欲望①蓋耶指出,休謨與康德的分歧并沒有那么大:“一方面,休謨確實認為我們的目的總是由激情(passions)所決定的,但他也認為,大多數時候我們最終是由平靜或者自由的激情所促動的。至少在否定的意義上,它擺脫了欲望的糾纏。因此,理性雖然可能是激情的奴隸,但我們也有一種根本性的成為理性的(reasonable)激情,并且享有它所帶來的平靜。另一方面,對于康德而言,道德的最終目的也是自由,盡管他對自由的理解比休謨更充分。而且,至少在經驗層面,康德的道德動機理論認為,沒有一種原初的對自由的激情,我們就不可能是道德的,盡管這種激情必須由擁有力量的理性(這種理性源于從我們的自由到所有人的自由)重新確立方向。因此,兩個人都將道德的內容和可能性置于對自由的激情中,盡管在休謨那里,這相當于傾向理性的激情(a passion for reasonableness),然而,在康德那里,我們原初的對自由的激情必須被理性所馴服,而一旦如此,康德就不會將其再視作一種激情。”(Paul Guyer,Passions for Reason:Hume,Kant,and the Motivation for Morality,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Vol.86,No.2,2012,pp.4-21,p.5)蓋耶進一步認為,由道德法則所規定的意志屬于本體性自我,但在我們有意識地進行決定與推理的時候,它必然顯現于經驗性自我中,即愉快或者痛苦的自然情感之中。但是,他也指出,這種“本體性的選擇”與“現象性的效果”之間的具體聯系,是難以被說清的(Paul Guyer,Passions for Reason:Hume,Kant,and the Motivation for Morality,p.15)。蓋耶試圖將康德與休謨的分歧消弭到最小程度,這種努力是值得同情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他也是對的。但是,本文的觀點更為細致:在理論意義上,康德堅持只有理性及其法則才是道德行為的客觀根據,也是根本性的動機,而情感作為它的表象,只是實際的動機。休謨及追隨他的情感主義者們,并不持有這一立場。。但是,與休謨不同的是,康德認為作為道德情感的敬重,其內在根據是理性及其法則,而非任何一種感性質料或者能力。理性與情感,都居于這種整體性的“意志”之中,而至于本體性的純粹理性具體如何發生作用并形成敬重的情感與行動的意愿,則已經超出了目前的知識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