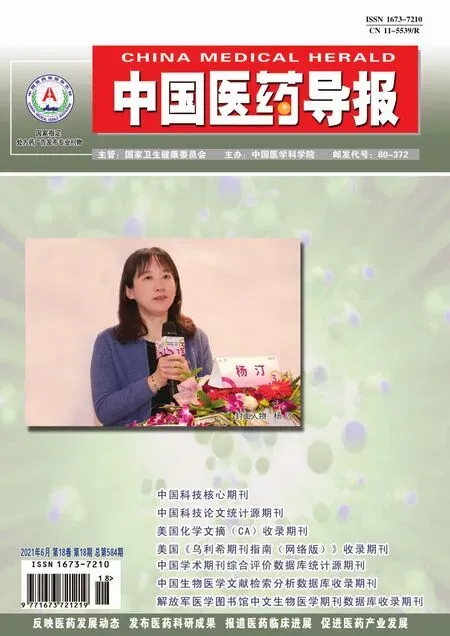古今中醫辨治亞臨床甲狀腺功能減退癥異同
鄒 嚴 張泰魏 李學會 周意園
1.貴州中醫藥大學研究生院,貴州貴陽 550025;2.貴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產科,貴州貴陽 550002
亞臨床甲狀腺功能減退癥(以下簡稱“亞臨床甲減”)是指由各種病因引起的甲狀腺激素合成、分泌不足或組織作用減弱導致的內分泌代謝性疾病,臨床以血清促甲狀腺激素升高,而游離甲狀腺激素在正常范圍內為基本特征[1-3]。此病通常發病隱匿、病程較長,缺乏特異癥狀和體征,可進一步發展為臨床甲減。JAMA表明[4]該病的患病率約為10%,以女性及老年患者居多。該病在中醫學中并無專屬病名記載,現代醫家多依其病位特點將其歸為“癭病”范疇。中醫學在治療亞臨床甲減方面歷史悠久、療效顯著,且古今醫家在看待亞臨床甲減的病因病機及審證論治等方面各具特色。因此,筆者通過追溯該病古今之異同,以期探討防治亞臨床甲減的思路和方法。
1 亞臨床甲減的病因病機
1.1 從古代醫家角度看待亞臨床甲減的病因病機
1.1.1 飲食、水土失宜 夫《說文解字》載:“癭,頸瘤也,從疒,嬰音。”癭聲同“嬰”,意繞頸之飾,是謂癭病形如環狀之飾佩于頸(喉間)也。《呂氏春秋·盡數篇》載:“輕水所,多禿與癭人。”《治病百法》云:“頸如險而癭,水土之使然也。”《諸病源侯論》云:“諸山水黑土中,出泉流者,不可久居,常食令人作癭病。”《雜病源流犀燭·頸項病源流》記載:“西北方依山聚潤之民,食溪谷之水,受冷毒之氣,其間婦女,往往生結囊如癭。”《名醫類案》云:“汝州人多病頸癭,其地饒風沙,沙入井中,飲其水則生癭。”亦如《淮南子·地形訓》中描述:“險阻之氣多癭。”綜上,古代醫家皆以該病病因為水土、飲食失宜,致脾失健運,水液無以敷布,痰濁、瘀血壅結頸前而發病。
1.1.2 情志失調 《醫學入門》[5]記載:“(癭病)原因七情勞欲,復被外邪。”《三國志·魏略》[6]云:“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外科發揮》:“此七情所傷,氣血所損之證。”《醫宗金鑒》中言:“多外因六邪,榮衛氣血凝郁;內因七情,憂憤怒氣,濕痰凝滯……而成。”宋代《濟生方·癭瘤論治》:“夫癭瘤者,多由喜怒不節,憂思過度,而成斯疾焉。大抵人之氣血,循環一身,常欲無留滯之患,調攝失宜,氣血凝滯,為癭為瘤。”《圣濟總錄·癭瘤門》[7]:“石癭、泥癭、勞癭、憂癭、氣癭,是為五癭。石與泥則因山水飲食而得之;憂、勞、氣則本于七情。”《三因極一病證方論·癭瘤證治》云“此(癭)乃因喜怒憂思有所郁而成也”“隨憂愁消長”。綜上,部分醫家認為情志內傷,喜怒無度,憂思善慮,易化癭病。
1.1.3 氣滯、痰濁、血瘀 《外科正宗》言:“夫人生癭瘤之癥,非陰陽正氣結腫,乃五臟瘀血、濁氣、痰滯而成。”《古今圖書集成》云:“癭皆痰與氣相結而成。”《明醫指掌·癭瘤證》記載:“癭……隨氣凝結于皮膚之間,日久結聚不散,積累而成。若人之元氣循環周流,脈絡清順流通,焉有癭瘤之患也。必因氣滯痰凝,隧道中有所留止故也。”且古代醫家多“百病多由痰作祟”“怪病多痰”之說。可見,古之醫家對氣滯、痰濁、血瘀互結致癭較為認同。
1.2 從現代醫家角度看待亞臨床甲減的病因病機
1.2.1 脾胃虛弱,腎失所養 李小娟教授明確其病機以氣虛、陽虛為本,責之于脾腎二臟[8]。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飲食、水土失宜,脾胃氣虛,失于健運,氣血乏源,腎失所養,則脾腎俱傷,易致亞臨床甲減的形成。倪林等[9]、趙樹龍等[10]認為亞臨床甲減病機為脾腎虧虛,精氣不充,溫煦失職,水飲濁氣搏結而致。
1.2.2 腎虛為原,兼夾實邪 曲竹秋教授認為,腎藏先天之精,寓元陰元陽,腎陽為諸陽之源,五臟之陽皆取助于腎陽,腎陽虛是亞臨床甲減病機之根本,久則五臟陽氣漸衰,終致脾腎兩虛、心腎陽虛[11]。潘立文等[12]、楊瑞霞等[13]認為亞臨床甲減病位責之于腎,以腎陽虛衰為本,氣滯、痰凝、瘀血為標。徐蓉娟等[14]認為其基本病機是腎陽虛衰,命火不足,火不生土,脾陽受損,或兼心陽不足;病位涉及腎、脾、心、肝四臟。此外,現代藥理研究證實[15],溫補腎陽方可改善甲狀腺及機體組織細胞的代謝功能,提高亞臨床甲減患者的甲狀腺激素水平。可見,現代醫家多認為亞臨床甲減以腎虛為本,兼夾痰瘀實邪、日久累及他臟而發病。
1.2.3 肝郁氣滯,痰瘀互結 高天舒教授認為情志不遂,肝氣乘脾,氣血瘀滯,日久脾陽不振,痰濁內聚是發病的重要原因[16]。王秋虹等[17]認為甲狀腺所在位置為足厥陰肝經所屬,情志不調,肝失疏泄,易致甲狀腺疾病。綜上可見,古今醫家皆認為該病的病因包括七情內傷、體質因素、水土及飲食失宜等,氣滯、痰凝、血瘀既是基本病機,又是重要的病理產物。古代醫家認為肝、脾、心與該病聯系密切。而現代醫家除上述外,還深入討論了因腎致病的理論,認為腎虛精虧是導致亞臨床甲減形成的關鍵,兼夾痰瘀濕毒等實邪,豐富了對該病的認識。
2 亞臨床甲減的辨證論治
2.1 古代醫家辨治亞臨床甲減
2.1.1 解郁散結,針藥并用 稽叔夜《養生論》云:“頸如險而癭,水土之使然也,可用人參化癭丹,服之則清也,又以海帶、海藻、昆布三味,皆海中之物,但得二味,投之于水翁中,常食亦可消矣。”取海帶、海藻、昆布化痰散結消癭之功,以防治亞臨床甲減的發生、發展。《醫宗金鑒》指出:“夫肝統筋,怒氣動肝,則火盛血燥,致生筋癭、筋瘤,宜清肝解郁,養血舒筋,清肝蘆薈丸主之。”《備急千金要方》載“諸癭,灸肩髃相對菀菀處……又灸風池百壯……”“癭者……憂郁傷肺,氣濁而不清,色白不赤,軟而不堅,陰陽失度,隨喜怒消長者宜服通氣散結丸”。晉代《針灸甲乙經》言:“癭,天窗及臑會主之。”《千金翼方》云:“癭惡氣,灸天府五十壯;癭上氣短氣,灸肺俞百壯;癭勞氣,灸沖陽,隨年壯;癭氣面腫,灸通天五十壯;癭,灸天瞿三百壯,橫三間寸灸之。”
2.1.2 益氣活血,化痰消癭 《外科大成》云:“活血散癭湯,癭瘤日久,無痛癢者,氣血弱也。”即癭病日久者,氣血耗傷,正氣虛衰,宜服活血散癭湯之意。“海藻玉壺湯……治癭瘤初起,或腫不腫,或赤不赤,但未破者服”,主張治癭當理氣活血、化痰消癭,創海藻玉壺湯,重用海藻、昆布、半夏、貝母化痰軟堅消癭,陳皮、當歸等理氣養血活血以使氣血通利、癭氣漸散。
2.2 現代醫家辨治亞臨床甲減
2.2.1 補腎健脾,益氣溫陽 現代醫家多認為陽虛是本病的病機關鍵,目前常見分型為脾腎陽虛型、陰陽兩虛型、痰氣郁滯型,在臨床中最常見的證型為脾腎陽虛證。馬越[18]和張丹丹[19]以溫陽益氣、脾腎雙補為法,自擬溫腎健脾方(熟地黃、山藥、山茱萸、枸杞子、當歸、杜仲等),治療后查患者甲狀腺功能明顯改善,促甲狀腺激素出現不同程度下降。張靜[20]、李娜等[21]運用溫陽愈癭湯治療脾腎陽虛型亞臨床甲減患者的結果顯示,溫陽愈癭湯治療組中醫癥狀較對照組明顯改善,且治療組促甲狀腺激素水平下降較對照組更顯著。鮑靈珠等[22]研究發現,在口服左甲狀腺素鈉片的基礎上,加用溫腎補虛方聯合治療本病,總有效率達93%,能有效調節血脂及炎癥因子水平,明顯優于單純使用左旋甲狀腺素。許莉等[23]采用健脾益腎溫陽法聯合左甲狀腺素治療妊娠亞臨床甲減患者,可顯著降低妊娠并發癥和不良母嬰結局的發生風險,改善母體甲狀腺功能,促進胚胎正常發育。
2.2.2 滋陰補陽,溫腎填精 亞臨床甲減脾腎陽虛型日久不愈,陽損及陰,終致陰陽俱虛。李發榮等[24]采用補腎益精、陰中求陽法,自創九味暖腎湯(熟地、淮山藥、山萸肉、補骨脂、肉桂、澤瀉等)治療56 例患者,治療效果與西藥組對比無明顯差異,但中藥療程短,隨訪2 年的復發率低。賈錫蓮[25]運用金匱腎氣丸加枸杞子、女貞子、龜板、鱉甲等,治以滋陰補腎、調補陰陽,諸藥合用水火共補,陰陽并調,邪去正安,療效顯著。
2.2.3 疏肝健脾,化痰祛瘀 梁蘋茂等[26]認為亞臨床甲減常因情志因素所致,痰氣交阻于頸,久病血行瘀阻,治以理氣解郁、散寒通滯,方用陽和湯加減療之。李莉等[27]認為該病以脾腎陽虛為本、痰瘀阻絡為標,治療選用桂附八味丸化裁加用通心絡膠囊,溫補脾腎陽氣,益氣活血通絡,治療亞臨床甲減33 例,總有效率為93.9%。鄧暖繁等[28]運用活血化痰、健脾益氣之法,方選健脾化痰活血湯,可明顯改善亞臨床甲減患者甲狀腺功能,調節血脂及炎癥細胞因子水平。可見,古代醫家認為亞臨床甲減分為兩個證型,屬于肝氣郁滯證,治以解郁散結,并以針藥并用;屬于氣虛血瘀、痰濕阻絡證,治以益氣活血、化痰消癭。現代醫家將亞臨床甲減按病種分為三個證型,屬于脾腎兩虛、陽氣虛損證,治以補腎健脾、益氣溫陽之法;屬于陰陽兩虛、腎虧精虛證,治以滋陰補陽、溫腎填精;屬于肝郁脾虛、痰瘀阻絡證,治以疏肝健脾、化痰祛瘀之法。由此可見,古今醫家都認識到了理氣活血、化痰祛瘀在治療亞臨床甲減上的重要性,古代醫家更加重視調暢肝脾氣機,而現代醫家治療亞臨床甲減側重于以補腎健脾為本。
3 小結
古今醫家關于亞臨床甲減病名、病證、病因、病機的認識有豐富的闡述。相同點在于,兩者都已經認識到該病的發生與情志內傷、體質因素、飲食及水土失宜密切相關。治療方面,古今醫家都認識到了理氣活血、化痰祛瘀的重要性。不同點在于,古代醫家多認為該病以氣郁痰凝血瘀為主,將病位責之于心肝脾,重視調補肝脾氣機,針藥并用特色鮮明。現代醫家多認為亞臨床甲減以陽虛為本,脾腎陽虛多見,兼夾氣郁痰瘀濕毒,日久累及他臟,突出強調因腎致病的概念,注重調節腎、脾、肝的功能,在遣方用藥時多以補腎健脾、調補陰陽、理氣化痰祛瘀為治療原則。筆者通過整理古今醫家看待亞臨床甲減病因病機及辨證論治方面的異同,以期為今后臨床中醫中藥的防治該病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