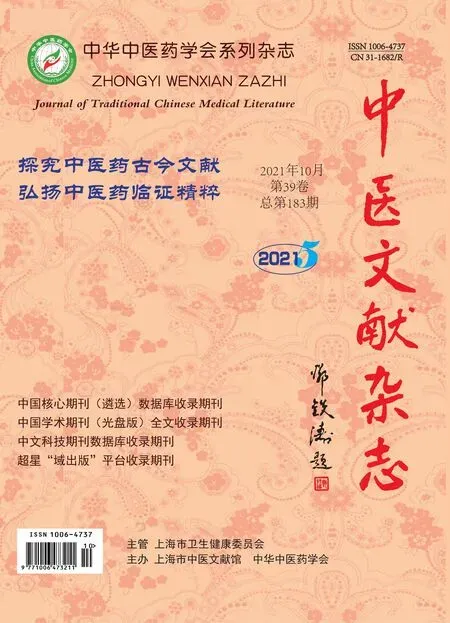近代上海中醫人的社會關系網絡與社會角色
——以陳存仁為例*
上海中醫藥大學(上海,201203) 何蘭萍
近代上海素有“十里洋場”“冒險家的樂園”之稱。百余年間,數以萬計的海內外人士懷揣著淘金夢來此打拼,同時也有一些生于斯、長于斯的上海人縱橫捭闔、長袖善舞,利用自身的地域優勢和特殊的社會關系網絡成為上海灘名噪一時的人物。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醫陳存仁就屬于后者。他生在上海,長在上海,運用靈活的頭腦以及超出同齡人的老道,構筑起廣涉文化界、政界、醫界、工商界的社會關系網路,得名“滑頭醫生”[1]。這里的“滑頭”并無貶義,而是形容他具有高超、圓滑的交際能力和交際智慧。本文擬以民國上海的傳奇名醫陳存仁為個案,探討近代中國社會關系網絡對于個人事業的影響、社會關系網絡與其社會角色的關系,從一個側面折射出近代上海城市和中醫界的生態,以期深化上海城市史和中醫“外史”研究。
家庭環境與原有社會關系網絡的積淀
陳存仁(1908—1990年),名保康,又名陳承沅,字存仁,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出生于上海老城廂一個世代經商的家庭。用陳存仁先生自己的話來說,“我家是上海縣城內的世家。我父親子晉公合了五房兄弟,在縣城大東門大街開設一家陳大亨衣莊、一家陳錦章衣莊,又開了陳榮茂、陳大升兩家綢緞局……我的叔父常常夸耀我們家的財富,他說:‘郭半城,朱一角,陳家兩頭摸。’意思是說,姓郭的地產占到半個城,姓朱的占一只角,姓陳的家宅與店鋪由城內開到城外,兩面可以摸到錢財”[2]。可見,幼年時代的陳存仁家境富裕,陳家在上海或者說在上海縣城內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社會關系網絡不可小覷。
1914年,上海南市商業日益衰落,陳存仁的父親孤注一擲地在東門開設綢緞鋪,后不幸倒閉。陳存仁8歲時,父親離世,家道中落,靠親友接濟度日。陳存仁遵照父親學醫的遺言,中學畢業后,靠四伯父的資助投考南洋醫科大學(東南醫學院前身)。一年后他身患傷寒,因西醫救治無效,轉服丁甘仁先生的中藥痊愈,于是改投考由丁甘仁先生創辦的、謝利恒先生任校長的上海中醫專門學校[3]351。
根據陳存仁的自述,他投考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是由四伯父轉托王一亭、朱福田推介的。“四伯父代我轉托王一亭、朱福田兩位世伯寫了一封介紹信,投考中醫專門學校。當時投考學校,這封介紹信就等于保證書一樣。經過考試后,我即被錄取。”[3]16這里提及的兩位入學推薦人均為當時上海的名流。其中,王一亭為1905年創辦的浦東同鄉會五位會董之一,朱福田為六位議員之一,而浦東同鄉會與寧波同鄉會是近代上海119個同鄉團體中最具影響力的兩大同鄉會。由此可見,雖然陳存仁已家道中落,但是陳家在上海灘仍有一定的人脈關系,這種人脈關系成為陳存仁進入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學習中醫的敲門磚。換而言之,陳家已有的社會關系網絡在陳存仁進入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求學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在此后的求學過程中,陳家已有的社會關系網絡或多或少地也起到積極作用,尤其表現在拜丁甘仁(1865—1926年)為師方面。
個人能力與新社會關系網絡的構筑
從陳存仁的成長軌跡來看,他的社會關系網絡主要有兩大來源:一是陳家已有的社會關系網絡和人脈,這一點助其進入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學習;二是在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求學期間及之后,陳存仁依靠個人能力構筑起涉及文化界、政界、醫學界、工商界等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
1.文化界與政界
陳存仁構筑新社會關系網絡起步于他在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求學期間(1922—1928年),從文化界開始,并由此向政界和醫學界延伸。
入學之初,為了攻克艱澀難懂的中醫典籍,他拜姚公鶴(生卒年不詳)、章太炎(1869—1936年)為國文教師。這是他編織文化界新社會關系網絡的起點。
姚公鶴先生為常州名儒,曾任《申報》主筆、商務印書館編輯。當時因要辦理法政講習所,姚公鶴先生想請一個謄寫鋼板和油印的人才,且免收補習國文的學費,陳存仁于是抓住了這個好機會。“我從姚公鶴老師之后,不但國文大有進步,而且對社會關系的接觸收獲更大。因為他的煙榻之旁,每晚都有不少名儒學者相聚傾談,如孟心史、蔣竹莊、莊俞、董康、胡樸安、陸爾奎、葉楚傖、戴季陶、陳冷血、陳布雷、唐駝等。他們所談的或是批評時事,或是臧否人物,都有很豐富的處世經驗,所有談話資料,也有極高深的學問。由此我智識頓開,見聞大增,對做人的道理懂得不少,覺得這許多學問都是書本上所沒有的。”[3]16- 17從這段話可知,拜姚公鶴為師,使陳存仁的社會關系網絡迅速擴大,讓他不僅可以接觸到文化界名人,還能結識南京國民政府官員,其中包括國民黨要員陳布雷、戴季陶等人。值得一提的是,拜章太炎為師也是從姚公鶴處發展來的。“我拜識章太炎先生是在民國十七年(1928年),那時我才二十歲,初在中醫專門學校畢業,常到武進姚公鶴老師家去補習國文。姚老師和章太炎先生友誼很深,三天五天總有書信往返,書信都叫我送去的,因此太炎先生對我很面善。”[3]59章太炎為近代國學大師、民主革命家,不僅社會地位高,而且中醫造詣很深。拜師章太炎,進一步夯實了陳存仁先生的國學和中醫功底,為其事業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人際交往空間和更大的社會活動舞臺。例如“海上聞人”杜月笙(1888—1951年)欲獲得章太炎的墨寶,只好找陳存仁幫忙[3]62- 63,而杜氏所欠人情對陳存仁在近代上海復雜的社會環境中生存以及事業發展有一定幫助。
陳存仁經濟學方面的造詣源自丁福保(1874—1952年),而這層社會關系網絡的構筑得益于姚、章二師。丁福保為近代著名藏書家、書目專家。他博古通今,著述甚豐,與國民黨政要交往密切,同時,致力于促進中國醫學事業發展。陳存仁回憶道:“恰好購到丁福保先生所辦的《中西醫學雜志》,篇末有一則招請抄寫和剪貼工作職員的小廣告,我就跑去應征。那時丁福保先生聲譽卓著,與衛生家伍廷芳齊名。我見他面色紅潤,一把銀白色的胡須,接待時笑容可掬,令人如坐春風。我說明來意之后,他看了我履歷上寫的國文教師是章太炎、姚公鶴,醫學教師是丁甘仁,即刻就錄取了我。”[3]18這段話印證了陳存仁與姚、章的師生關系對于結識丁福保具有重要作用。而拜丁福保為師則進一步拓展了陳存仁與政界的關系,其中,通過丁福保與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868—1943年)結識即是最佳例證。陳存仁先生提到,“經過(丁福保)介紹之后,林主席對我非常客氣,親自倒了杯茶給我”[3]19。從結識國民黨要員陳布雷、戴季陶,到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充分說明陳存仁的社會關系網絡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除了上述提到的文化界名人外,陳存仁在《閱世品人錄》中還講述了他與胡適(1891—1962年)、秦瘦鷗等文化名人的交往故事,由此可見他在文化界的人脈關系之廣。
2.醫學界
陳存仁在醫學界的人脈關系涵蓋中西醫兩大領域。從時間順序來看,中醫界的人脈關系積累要早一些,而這也對發展西醫界的人脈關系具有或多或少的助推作用。
陳存仁構筑中醫界的人脈關系最為關鍵的一步是拜丁甘仁為師。丁甘仁為近代上海中醫界泰斗級人物,進入丁門是無數中醫學子的夢想。陳存仁之所以入得丁門,與本人的天分和勤奮刻苦有關,但也離不開謝利恒的引薦。前文已述,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的創辦人為丁甘仁,但謝利恒為時任校長。“在中醫學校肄業的最后一年,就在校主丁甘仁老師處開藥方,謝利恒老師特別為我吹噓,說我的字清秀而迅速,所以別的同學做錄方的工作,總要等候三個月以上,只有我一進丁老師的診所,就為他寫藥方,寫了三個月,丁老師很是滿意”[3]24。
拜丁甘仁為師,對于陳存仁構筑醫學界的社會關系網絡具有重要作用。通過丁師,他結識了上海名中醫惲鐵樵(1878—1935年)、徐小圃(1887—1959年)等人,以及西醫界德高望重的人物,如顏福慶(1882—1972年)等。陳存仁將他跟隨丁甘仁學醫的這段時期定義為“否極泰來,進入鴻運”[3]25,可見丁師對他成長的幫助之大。1926年丁甘仁去世后,陳存仁改從丁師之子丁仲英(1886—1978年)。丁氏父子精湛的醫術、高尚的醫德及強大的人脈關系,對陳存仁的成長、成才和成名意義重大。1928年,陳存仁在業師丁仲英的鼓勵下開設門診,獨立行醫。《申報》廣告稱:“中醫陳存仁君,為名醫丁仲英君之高足,醫學精湛,經驗宏富,主辦《康健報》,提倡中國岐黃之術,極受社會歡迎。現自設診所于南京路望平街口柏林紙行二樓,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七時為門診時間,僅收診金一元。其診所中一切設備糜不注重衛生,與西醫無異,故求診者接踵而至。”[4]
3.工商界
丁甘仁在幫助陳存仁結識工商界人士方面具有穿針引線的作用,不過主要集中在藥材領域。如陳存仁通過丁甘仁結識了當時的北京首富、著名藥材商樂篤周(1894—1979年)和上海灘“商界奇才”黃楚九(1872—1931年)。樂篤周早年留學法國,“1923年開始投資經營藥店,最初與樂佑申等兄弟幾人開辦樂壽堂。1931年獨立出來,在北京大柵欄創辦宏仁堂總店”[5],后在上海、天津、青島等地開設分號。樂篤周對丁甘仁頗為敬仰,丁先生對樂篤周也頗為客氣,并教育陳存仁,“樂篤周家私百萬,是北京的首富,你以后該對他要多多聯絡,他們北方人是最講究禮貌的”[3]25。事實證明,通過陳存仁做東、丁甘仁參加以及諸多上海灘名中醫作陪的一次“鴻運樓宴請”,陳存仁結識了樂篤周[3]25- 26。在后來的行醫過程中,陳存仁先生還結識了號稱“商界奇才”的黃楚九。
1948年,陳存仁在香港結識了號稱“中國銀行界稀有的奇才”的陳光甫(1881—1976年)以及“一代船王”董浩云(1912—1982年)。
社會關系網絡與社會角色
陳存仁的社會關系網絡廣及文化界、政界、醫學界、工商界,稱得上是“黑白兩道皆有通路”。事實證明,如此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對他個人事業的發展以及諸多社會角色的扮演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
1.社會關系網絡與醫生
在陳存仁的事業發展和所扮演的諸多社會角色中,首先是醫生,確切的說,是一名中醫師,在他求學期間構筑的社會關系網絡對他的行醫生涯可謂意義非凡。
首先,他與丁氏父子的師承關系是陳存仁行醫的前提和基礎,更是他成為名中醫的關鍵。與西醫相比,中醫更講究師承關系。倘若陳存仁沒有與丁氏父子的師承關系,恐怕他很難成為民國時期上海灘的一代名中醫。這種師承關系對陳存仁行醫的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名師出高徒,丁氏父子深厚的中醫造詣、高尚的醫德為陳存仁醫術和醫德的培養提供了必要條件。二是,丁氏父子在醫界和社會上的名望有助于陳存仁在醫界立足。1928年,在業師丁仲英應允下,陳存仁先生開設診所,開始獨立行醫。
其次,他與章太炎的交情有助于診所維持營業。1928年,陳存仁獨立行醫時,章太炎特為其診所篆“誠敏勤樸”匾額[6]。對一個剛剛自立門戶的年輕醫生來說,這無疑有助于提升這家新開診所的知名度,吸引患者前來就診,增強患者信心。更重要的是,陳存仁通過章太炎結識了“海上名流”杜月笙,這也是他能在上海行醫數年的原因之一。
2.社會關系網絡與出版人
除醫生外,出版人也是陳存仁扮演過的社會角色,而辦刊出書進一步提升了陳存仁的社會知名度。
1927年3月,陳存仁獨立創辦《康健報》,這是近代中國首份介紹醫藥衛生常識的周報。此報刊得以出版,既得益于他前期構筑的社會關系網絡,又將其前期構筑的社會關系網絡向前推進了許多。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依據有三:其一,創辦報刊得到其業師丁仲英的支持,這屬于他之前編織的人脈關系。其二,為報刊撰文的大部分人屬于已有人脈關系之內。如“丁福保、丁仲英、謝利恒、惲鐵樵、俞鴻賓、秦伯未、陸士諤、章次公等中醫名家”[7]。這些名醫名家的撰文,提升了《康健報》的知名度和發行量。《康健報》“第一期發行就有1.4萬份,至1930年共發行150余期”[7]。此報暢銷,一方面得益于先前構筑的社會關系,另一方面又將已有的社會關系向前推進。陳存仁借此“認識了很多出版界中人。其中,有位鄭耀南是交際家,他聯合各方面友人發起一個‘吉社聚餐會’,每一會員都屬不同的職業,有律師、會計師、中西醫師等,中醫師就是我,每周聚餐一次……聚餐時例必邀一位特客,這位特客,多數為文教界或專業名流”[8]。通過吉社聚餐會,陳存仁還結識了近代文化名人胡適。
《康健報》停刊后,借助醫學專業知識和積攢的出版經驗,陳存仁堅持為各類期刊寫稿,甚至開設專欄,宣傳中醫健康知識。一方面,他為申報館編辦專刊《康健周刊》和副刊《國醫與食養》,為《新聞報》《商報》編辦《國醫與國藥》副刊等專刊專版。借助這些發行量大的報紙傳播中醫藥知識、凝聚醫界人心,推動中醫藥的發展。另一方面,他為《興華》《江蘇全省中醫聯合會月刊》《旅行雜志》《現代國醫》《幸福雜志》《長壽》《上海生活》《醫界春秋》《醫藥研究》《中醫世界》《中醫療養專刊》《家庭與婦女》《中醫藥情報》《華西醫藥雜志》《嘉定中醫周刊》《南匯醫學月刊》等撰寫了大量稿件,內容以防治肺病為主,兼及婦科、兒科等疾病,推進了中醫藥知識和文化的普及與宣傳。
除辦刊撰文外,陳存仁還編撰了《中國藥學大辭典》,推進中醫藥學科發展。而成功編纂這本藥學辭典,離不開他前期構筑的社會關系網絡。1929年,商務印書館力邀此前擔任《中國醫學大辭典》主編的謝利恒編一部《藥學大辭典》。謝利恒以精力不足為由婉拒,特推薦陳存仁作為主編,這才使得陳存仁有機會與商務印書館成功簽下出版合約。半年后,商務印書館一再發生罷工事件,因而宣布作廢一切對外簽署的出版合約。此事對陳存仁打擊甚大,最終是在丁福保的安慰并允諾出版保障后才得以繼續編纂。《中國藥學大辭典》的編撰創辦,標志著“民國中醫學術的藥物轉向”[9],在中藥學科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由此可見,無論是獨立行醫前作為專職出版人,還是后來兼職為期刊寫稿,以及編撰《中國藥學大辭典》,始終離不開他之前構筑的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
3.社會關系網絡與為中醫抗爭
前期構筑的社會關系網絡,為20世紀30年代后陳存仁參與為中醫抗爭等社會活動奠定了基礎。
1929年,余云岫等人拋出臭名昭著的“廢止舊醫案”,引發全國中醫界的極大憤慨。陳存仁一方面發文犀利駁斥,另一方面與謝利恒、丁仲英等發起組織全國抗爭活動。陳存仁先生的社會活動內容包括:(1)參與組織、策劃、召開全國中醫“3·17抗爭大會”,(2)被推舉為五名代表之一赴南京請愿,(3)組織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成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中醫藥界的組織“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這些社會活動的結果有三:一是使得南京國民政府不得不取消議案,保存中醫;二是將3月17日定為“國醫節”;三是陳存仁與謝利恒同被聘為衛生部顧問。在這場中醫維權運動中,陳存仁的社會關系網絡起到一定的作用。一方面,他與謝利恒、丁仲英的師承關系提高了中醫抗爭運動的效率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他與政界,特別是與南京國民政府政要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推動中醫抗爭運動朝利好方向發展。
抗戰勝利后,陳存仁在上海乃至全國的名望較之前更高。1947年,陳存仁當選為第一屆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當時有媒體評論道,“陳參議員存仁才能出眾,學歷、智力、財力、魄力高人一等”[10]。
4.社會關系網絡與慈善公益
陳存仁是近代上海多個慈善機構的董事,其中包括當時最大的慈善機構仁濟善堂。淞滬抗戰期間,大量民眾流離失所,各方正義之士紛紛通過救濟組織、慈善機構向其伸出援手。陳存仁作為當地最大的收治棄嬰的慈善機構“仁濟善堂”的董事,此時還擔任具有義務性質的堂長。面對日益增加的棄嬰,身為堂長的陳存仁不得不考慮如何擴大收容能力的問題。為了解決難民問題,陳存仁先生巧妙運用與上海租界當局的關系,說服租界當局允準仁濟善堂辦難民收容所。不言而喻,在這次與租界當局的斡旋當中,他構筑的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難民收容所的創辦,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租界的難民壓力,避免了更多同胞流離失所。
1840年以后,中國被西方國家強行拉入“世界全球化”的戰車,艱難地邁向近代化的征程。在近代社會轉型期,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由傳統的相對單一的模式逐步向社會網絡化模式轉變,這就要求我們多層次、寬領域地研究近代歷史人物。近代上海的城市格局為“三方四界”,這種獨特的城市治理和政治形態更是賦予了生活于其中的人更加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由此要求那些欲在此有所作為的人學會縱橫捭闔、長袖善舞的本領。近代生活在上海的中醫人當中,陳存仁即是為數不多的這類人物,他通過構筑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不斷將自己的事業向前推進,在做好中醫師的同時,扮演著諸多的社會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