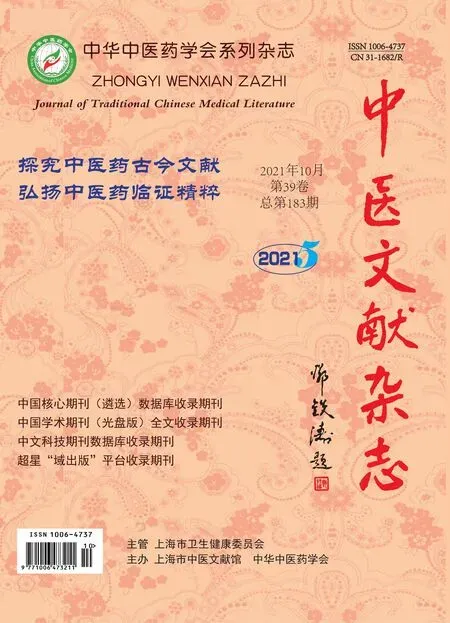1949年以來我國醫學文物研究概述*
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中醫藥博物館(廣州,510006) 薛暖珠
中醫藥學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在上下數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中醫藥學留下了極其豐富的物質文化遺存。在我國,物質文化遺存謂之“文物”。我國醫學文物見證了我國醫學文明的光輝歷史,是研究中華醫藥歷史文化的寶貴資料,也是傳承醫藥國粹的重要依托。整理研究我國的醫學文物,對保護和傳承中國醫藥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現就我國醫學文物研究情況概述如下。
概念與內涵界定
文物,是指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由人類創造并與人類活動有關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和紀念價值的,古代、近代乃至現代的物質文化遺存(如遺物、遺跡)的總稱[1]。對我國醫學文物的概念、內涵進行明確的界定,是進行醫學文物整理工作的首要任務。
在既往文獻中,相關名詞有“醫史文物”[2]、“醫學文物”[3]、“醫文物”[4]、“中醫文物”[5]、“中醫藥文物”[6]、“醫藥衛生文物”[7]、“醫藥文化資源”[8]、“醫藥文物及遺址”[9]等。就命名而言,筆者認為,“醫學文物”的提法更值得推崇。相對于“醫史文物”的提法,“醫學文物”兼顧了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兩方面的內涵;相對于“醫文物”“醫藥文物”“中醫藥文物”“醫藥衛生文物”等的提法,“醫學文物”從“醫學”大學科的角度出發,兼具學術上的專業性、語言上的簡潔性和內涵上的深廣度,它既涵蓋了狹義的醫文物、藥文物、衛生保健文物等,也涵蓋了中醫學文物、少數民族醫學文物以及現代醫學文物等;相對于“醫藥文化資源”“醫藥文物及遺址”的提法,“醫學文物”更為明確,又更具概括性,既點明了其作為歷史文化物質遺存的物質屬性,又涵蓋了狹義的文物和遺址的內涵。廣義的文物包含了不可移動文物和可移動文物。前者包括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現代重要史跡、近現代典型建筑等,后者包括古器物、古文獻、古書畫等。
在概念和內涵闡述方面,葉啟曉在《醫文物的保護和研究》一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醫文物是指歷史上與醫藥衛生活動相關的人類遺物”[4];廖果稱,“中醫文物指那些具有中醫藥功能、意義、價值的文物”[5];朱德明稱,“醫藥文物及遺址是指那些具有醫藥衛生學意義和功能的文物和遺址”[9]。和中浚、吳鴻洲主編的《中華醫學文物圖集》,對“醫學文物”的概念作了如下界定:“醫學文物,指具有一定醫學意義和功能的文物。它在我國眾多文物中,屬于按專業功能和用途分類,主要從科學價值角度進行認識和研究的文物類別。”[3]書中還提到醫學文物的命名和具體含義:“醫學文物過去常稱之醫史文物,主要基于它在反映古代醫學面貌和歷史成就上的作用。編寫者在多年研究過程中感受到,應從整個醫學范圍的角度去認識,將其內涵加以擴展,故本書命名為醫學文物。其狹義者,指出土醫藥文獻與行醫治病及古代名醫有關的文物。其廣義者,包括預防治療疾病、增進身體健康、養生保健、具有衛生學意義的各種器物,以及反映醫學內容的藝術作品。”[3]李經緯指出:“全國醫藥衛生文物是偉大的祖國醫學,包括藏族醫學、蒙族醫學與維族醫學等各少數民族醫藥學,是五千年發展的歷史遺存。”[7]劉學春提出:“醫藥衛生文物是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遺留下來的,與人類健康和生活密切相關的遺物、遺跡,包括醫學文物、藥學文物、養生文物和衛生文物4大類。它是人類在醫藥衛生發展過程中留存的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承載著醫藥文化的信息,是醫藥文明史研究的重要物證。它首先要滿足文物的基本特征,同時必須與醫藥衛生活動密切相關。其特征是:第一,具有歷史性、實用性、科學性3個方面的價值;第二,是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與人類健康生活有關的實物。”[10]劉學春還進一步指出,醫藥衛生文物的概念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醫藥衛生文物是專指具有明顯醫藥衛生學特征的文物。”“廣義的醫藥衛生文物是指具有文物特征,必須兼有醫藥衛生學功能、性質、形態,與人類的健康生活息息相關的,具有特殊意義和用途的文物,或在其發展過程中,具有影響力的醫家或醫療衛生機構生活或生產過程中涉及的物品。”[10]
綜合以上各家闡述,筆者認為,和中浚和劉學春的闡述較為具體,而后者對相關概念的界定更為明確,層次更為清晰。此外,兩者均提出狹義和廣義的概念,后者的表述條理更加清晰,也更易懂易記。
調研與整理
新中國成立以來,醫史研究的專家學者對我國醫學文物開展了初步的調研和整理工作。李經緯報道,全國尚存中醫藥衛生文物兩萬多件,主要分布于綜合醫史博物館,專題中醫藥博物館,名醫紀念館,歷代醫學家的遺跡、藥王廟、紀念地,綜合性博物館及文物研究所。此外,還有不少醫學文物散落民間及流失海外[7]。林琦報道,“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散在民間及各博物館、藥王廟和非文物單位臨時或在簡陋的條件下存放的古代醫藥文物約50萬件,近現代醫藥文物約50萬件。而全國多家具有相應基礎和規模的中醫藥博物館和陳列室,僅收藏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超過1.8萬件。”[6]顯然,就全國現存中醫藥文物總量而言,不同研究者所報道的數據相差甚遠。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一是既往關于醫學文物的概念和范圍的界定,在學科領域內尚未充分討論,并形成統一、權威的定論;二是在文博領域,醫學文物受重視的程度遠遠不夠,大量醫學文物未得到妥善的保護、發掘及整理;三是既往有關醫學文物的調研范圍尚不全面。劉學春也認為,醫藥衛生文物研究尚處于收集、調研和整理的初級階段,存在制約其發展的諸多問題,如醫藥衛生文物的概念不夠清晰、研究內容不夠明確,缺乏分類和鑒定標準,市場混亂,相關博物館的展陳文物內容受到質疑等。[10]
據了解,1949年以來全國范圍內較大規模醫學文物開展搜集、調研和整理的活動主要有3次,相關調研成果以文物圖譜、圖集、圖典的形式公開出版。其一是傅維康等主編的《中國醫學通史·文物圖譜卷》[2](2000年出版)。該書從全國各地、各單位的博物館、圖書館、醫藥衛生機構、個人收藏家,以及醫家故里、民間等廣泛搜集的3000余幅醫學文物圖片中,按照歷史性、科學性、代表性、思想性及拍攝質量,精選800余幅編成圖譜,堪稱“一部表達系統、全面的醫史文物圖譜,較之國外著名的醫史圖譜毫無遜色,從而填補了我國長期缺少彩色醫史文物圖譜的空白”[11]。據靳士英介紹,《中國醫學通史》是“七五”“八五”期間國家衛生部的重點科研課題,因種種原因至1987年始組織編撰,經10年奮斗成書。其二是和中浚等主編的《中華醫學文物圖集》[3](2001年出版),是以全國中醫院校醫史博物館中的藏品為主,兼集各地考古發掘的重要醫學文物選編而成。編者在多年工作積累和對全國醫學文物資料的全面搜集整理基礎上,初步確定了醫學文物的概念和范圍以及涉及的主要品種和器物,共收載圖片300多幅。其三是李經緯等主編的《中華醫藥衛生文物圖典(一)》[12](2017年出版)。全書共9卷21冊,匯集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及國家科技部立項的“國家重點醫藥文物收集、調研和保護”課題的調研成果,其收錄文物圖片5200余幅,來自故宮博物院等國內外100余家博物館及眾多私人收藏家,涵蓋陶瓷、金屬、紙質、玉石等多種文物形式。該書以圖片和中英對照的形式向國內外讀者闡釋中華醫藥衛生事業起源、發展、壯大和擴展的脈絡。以上均是中國醫史領域的知名專家牽頭組建課題組,以重大項目為支撐,依托權威的學術機構(如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等),開展的全國范圍內的、較大規模的調研工作。以上圖書作為課題的主要成果,匯集了全國范圍內較有代表性的醫學文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醫學文物研究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三部著作。
除了全國范圍內的醫學文物調研、整理之外,也有少數研究者對各地區的醫學文物進行了初步的整理研究。這些地區的醫學文物,既有我國醫學文物的共性,又具有較鮮明的地域性特色。林琦在《廣東省中醫藥文物整理研究的思考》一文中,介紹了廣東中醫藥文物的概況,闡述了中醫藥文物整理研究的意義,并重點探討了廣東省中醫藥文物整理研究的思路及方法:首先,全面調查廣東省中醫藥遺跡、文物的現況;其次,文物的考證研究;第三,文物信息的系統總結,建設廣東省中醫藥文物數據庫。[6]朱德明實地考察了1949年以前浙江醫藥文物及遺跡,并按照文物的功能和日常用途進行歸類整理。[9]
分類研究
對醫學文物的合理分類,是做好醫學文物系統性整理的關鍵步驟之一。廖果指出,中醫文物的分類,既是中醫文物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中醫文物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促進中醫文物理論體系構建與深化的楔入點與重要方面。[5]文獻研究發現,我國醫學文物分類整理的常用方法是按時代(朝代)順序、按醫學功用、按文物質地等分類。
傅維康等主編的《中國醫學通史·文物圖譜卷》[2],把收載的802幅文物圖片按照時間先后順序進行編排,分原始社會、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遼夏金元、明、清代前中期、近代、現代11個部分,而少數民族醫學文物專列為最后一部分。這種按照時代(朝代)順序為主進行劃分歸類的方法,是既往我國醫學文物常用的分類方法。國內各中醫藥博物館、醫史館在文物展陳方面,也多以歷史年代為主進行分類展示。如中國醫史博物館的《中國醫學通史基本陳列》,按中國醫學發展史的時間順序,將文物資料按朝代先后順次陳列,共分為原始社會、先秦、秦漢、晉唐、宋遼金元、明、清、近百年醫事歷程8個部分,各部分文物又適當按功用加以相對集中[13];廣州中醫藥大學博物館醫史館基本陳列以中國醫學史的歷史發展階段為時間線,按醫藥起源、經驗積累、體系形成、全面發展、宋金元醫學、明清醫學、近現代中醫藥的時代順序進行文物精品陳列[14]。其他如上海中醫藥大學博物館、陜西醫史博物館等,其文物也都按照時代順序分類展陳。這種按時代(朝代)分類的方法,從醫學史研究的角度出發,能夠集中展現不同歷史時期醫學文物的特點,勾勒出中國醫學的發展軌跡。
和中浚、吳鴻洲主編的《中華醫學文物圖集》[3],突破了傳統的歷史時代分類法,將文物按醫學專業的用途和功能進行分類編排。該書把醫學文物(廣義)分為5大類:醫學文物(狹義)、藥學文物、衛生文物、少數民族醫藥文物、養生保健文物5大類。其中,醫學文物(狹義)又分古代醫學文獻、醫家造像和畫像、名醫脈案處方和書畫作品、與名醫有關的物品、醫療器械、醫療器具、醫學官印、醫學模型、行醫用具、醫學內容書畫和塑像共10 小類;藥學文物分出土藥物及古代醫藥標本、制藥工具、煎藥服藥工具、盛藥貯藥器、明清宮廷藥用器具、煉丹器、中藥鋪物件共7小類;衛生文物分飲水排水、預防消毒殺蟲、個人衛生、環境衛生共4小類;少數民族醫藥文物分醫學文物和藥學文物 2小類;養生保健文物分養生文獻、運動健身和行氣導引、其他3小類。與傳統的歷史時代分類法相比,這種按照文物功用進行歸納分類的方法,更強調文物的醫學科學價值。
李經緯等主編的《中華醫藥衛生文物圖典(一)》[12]主要依據文物質地、種類分為陶瓷、金屬、紙質、竹木、玉石、織品及標本、壁畫石刻及遺址、少數民族文物、其他共9卷。同卷下主要根據歷史年代或小類分冊設章,每卷下的歷史時段不求統一。遵循上述規則將《圖典》劃分為21冊。這種依據文物質地、種類進行分類的方法,是目前文博界較為通行的文物藏品整理方法。
隨著醫學文物研究的逐步開展,近年來一些學者專門就醫學文物的分類進行了研討。劉學春探討了醫藥衛生文物的分類標準,指出醫藥衛生文物分類原則為:在遵從文物的分類標準(如時代分類法、存在形態分類法、質地分類法、功能分類法、屬性分類法、來源和價值分類法等)的前提下,按其特征進行分類,包括有醫藥衛生文物特征的文物和無醫藥衛生文物特征的文物兩大類。根據醫藥衛生文物的特殊性,對其同與異集合成醫學類、藥學類、養生保健類、衛生類、遺跡遺址類和少數民族醫藥衛生文物類,形成了醫藥衛生文物的6類分類法,且各類目下又有自己的小類。[10]廖果以中國醫史博物館文物展陳為背景,介紹了中國歷代醫藥衛生文物的特點,并對醫學文物的分類作了詳細的闡述:“從不同的角度,中國醫藥衛生文物有著多種的分類方法。如從時間的角度,可按時代(朝代)將文物歸類;按器物質地,可分為玉石、陶瓷、金屬、竹木、織品、紙質、標本、壁畫石刻、遺址等類;按器物功用,可分為文獻典籍、醫政文物、醫療文物、藥學文物、針灸文物、養生文物等類;從醫學類型的角度,可分為漢族醫學文物、少數民族醫學文物以及西方醫學文物等類。”[13]廖果還通過對中醫文物分類的探析,指出可以依照文博界通行的一般文物分類的方法,對現存主要中醫文物按所在位置、來源、存在形態、時代(朝代)、質地、功用、醫學類型、社會屬性等進行分類。但中醫文物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如按功用分類,不僅能充分反映出中醫文物的意義、價值,及有別于其他領域文物的自身特點,而且可操作性較強。因此中醫文物的功用分類法應該成為中醫文物分類學術研究的重點[5]。
專類研究與個案研究
在專家學者對我國醫學文物進行系統性調研、分類整理的同時,也有一些研究者就我國醫學文物中的某個類別、某處遺跡,或某件(套)具體的文物進行專門的探討。
針對某一類別的醫學文物進行研究的,有對宮廷醫學文物的專門報道,如關雪玲的《紫禁城中的杏林光華——清宮醫學文物漫筆》[15];有對醫藥相關的書畫碑拓進行專門整理報道者,如薛暖珠的《廣東中醫藥博物館館藏書畫碑帖整理研究》[16]、耿鑒庭的《醫藥金石過眼錄》[17~18]、林乾良的《從醫方真跡看中醫的傳承》[19];有對文物辭典中收載的衛生陶瓷進行專門評述者,如和中浚的《<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衛生陶瓷評述》[20];有整理研究古代針灸推拿代表器具、古代熬藥溫藥器者,如陳建杉等的《中國古代針灸推拿的代表器具》[21]、和中浚的《略論古代熬藥溫藥器》[22]。此外,也有針對數件同類型文物進行研究報道者,如傅維康的《針灸療法的古石刻》[23]、馬繼興的《北京藥鋪的針灸銅人》[24]、林沁臻的《廣州中醫藥大學醫史博物館館藏道家煉功圖研究》[25]。
針對某個醫藥史跡開展調查,或針對某個史跡的醫學文物開展研究者,如馬堪溫的《內丘縣神頭村扁鵲墓調查記》[26]、鄭洪的《廣東羅浮山沖虛觀》[27]、薛暖珠的《廣東羅浮山葛洪遺跡考察》[28]、曹鴻云的《北宋皇陵中藥石刻調查報告》[29]、田衛麗的《淺談何家村出土醫藥文物與唐代道教外丹術的發展》[30]等。
針對某一件(套)文物進行深入研究挖掘,如謝克慶等的《綿州涪翁詩碑注釋》[31]、鄭洪的《<名醫葉天士遺像>鑒辨暨題跋抄評》[32]、林沁臻的《<內經圖>拓片研究》[33]、張瑞賢等的《廣州中醫藥大學藏龍門方拓本研究》[34]、李珂等的《王羲之書法名帖<治頭眩方>與晉唐時期中醫藥》[35]、薛暖珠的《北宋王惟一<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殘石拓本考述》[36]和《宋大仁<中國藥史四杰圖>題跋解析》[37]等。
醫學考古與醫史文獻學
醫學考古文物研究與醫史文獻學關系密切。文物具有歷史、藝術、科學三方面的價值,具有證史、正史、補史三方面的史料作用[38]。醫學文物主要具有歷史和科學價值,是反映醫學發展歷史和不同時代醫學發展水平的實物例證。早在20世紀20~40年代,開創我國醫史學科的研究學者們就認識到文物對于醫史研究的重要意義。1919年出版的第一部中國醫學通史——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里面就應用了不少醫學文物考古的研究成果。王吉民、伍連德等醫史學家也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有目的、有計劃地廣泛征集和收藏研究我國醫史文獻及文物,歷時十數年,并于1937年4月成功籌辦“醫史文獻(文物)展覽會”(中國有史以來首次舉辦的,以醫學文物文獻為主題的大型展陳活動)。1938年7月,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創辦醫史陳列室,即中國第一座醫史博物館——上海醫史博物館,從此拉開了現代意義上有組織地對醫學文物進行專門收藏保護、研究與展示工作的序幕[4]。之后,隨著一大批與醫藥相關的考古文物的陸續發掘和研究報道,以及各地醫史博物館的相繼創立和發展,越來越多的醫學史研究者們開始發表文章,探討有關考古文物與醫史研究的相關問題。
關于考古文物于醫史研究的意義,早在20世紀50年代,醫史學家宋大仁先生就專門撰文《文物、史跡對研究醫史的重要性》進行探討。文中指出,我國過去從事醫史研究的工作者,大都只在書堆、文獻中偏零狗碎地為考據而考據,對于物質文化遺存注意不夠。他提出,研究祖國醫學史,不能單靠文獻所載,必須要文獻與實物史料結合起來研究。他通過舉例說明實物資料的重要性,實物資料可以證實、補充和修正文獻的記載,反映歷史當時活生生的形象,幫助人們理解醫學文化的發展歷程。[39]任何在《考古發現與醫史研究》一文中,列舉了西安半坡遺址、河北滿城劉勝墓等相關考古發現與醫史研究的關系,指出考古發現給醫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新的資料,并進一步闡述了考古發現在醫史研究中的地位與作用,提出要不斷地從考古發現中吸收實物資料來補充和印證文字資料的不足,以此來豐富中國醫學史,并把考古發現應用到醫史研究和醫史教學中去。[40]
考古發掘的醫學文物研究,多見于大量而零散的報道,也有一些研究者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整理考述。如傅芳的《考古發掘中出土的醫學文物》,全文分為三部分,較系統地介紹了建國以來考古發掘中出土的和醫藥有關的文物:第一部分介紹了考古發掘出土的與衛生有關的實物史料,如飲用水井、排水系統、環境衛生與勞動保護設施;第二部分介紹了出土的醫學簡牘、帛書和書籍,并分析其在醫史、文獻、醫學研究方面的意義;第三部分介紹了出土的醫療器具、藥物等[41]。戴應新的《解放后考古發現的醫藥資料考述》,以較大篇幅詳盡地考述了新中國成立后考古發現的醫藥文物資料,包括不同時代的醫藥文獻、藥物藥具、醫療工具和古人尸體標本等,為重新認識和研究祖國醫藥學的發展過程,發掘和繼承這份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料[42]。馬繼興在《中醫文獻雜志》上連續6期發表題為《全國各地出土的秦漢以前醫藥文化資源》的研究報道,詳盡地匯總考述了我國西北、華中、華南地區出土的秦漢以前的古醫藥文獻,以及全國各地出土的秦漢以前的古醫藥器物,并從三方面(失傳多種古醫藥著作的再發現、古代建立和發展的少數醫學學科、中醫藥學的重要學術成就)綜合概括了這些出土醫藥文獻的重要學術價值[8,43- 47]。李經緯等的《中國醫學史研究60年》,綜述了中華醫史學會成立以來中國醫學史研究的狀況,文中第三部分概述了1935~1995年間我國醫學考古與出土文物的研究情況,列舉了考古文物中發現的代表性醫藥器具、藥物、早期衛生設施,以及出土的醫藥文獻等的主要研究成果[48]。此外,和中浚的《醫學考古與醫文物研究》一文,通過對體質人類學、出土古尸研究、醫藥遺跡調查、醫學文物研究的回顧總結,用統計和分析的方法,介紹了我國醫學考古、醫學文物的研究現狀和成果,同時也指出了該領域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進一步的研究方向。如多種文物醫學內涵的揭示和宣傳介紹,它與其他用途文物的聯系和區別,它的主要特點和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演變等,均有待今后進一步開展系統深入的研究工作。[49]
綜觀我國醫學文物研究的過去和現狀,可以看到該領域研究的發展軌跡和發展特點。我國醫學文物研究的起步,與上世紀考古學、醫史文獻學的興起息息相關,而考古學的發展和醫史文獻學研究領域的拓展,也帶動了醫學文物研究的發展。從目前的相關研究成果看,我國醫學文物研究正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并開始了相關理論建構。如相關概念名詞的探討、系統性的調查、分類整理方法和標準的探討、針對某一類別或某件(套)文物的發掘研究,以及大量醫學考古發掘成果的整理和總結等,都勾勒出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構建的輪廓。目前,隨著國家對中醫藥文化的高度重視,全國各地醫藥博物館的蓬勃發展,醫學文物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該領域的研究內容必將不斷拓展和深化,理論更加成熟、明晰、系統化,終將形成一個新的綜合交叉學科,并不斷向前發展,以便更好地服務社會、傳承文明。
(致謝:導師劉小斌教授對本文的寫作作了重要指導,在此謹致謝忱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