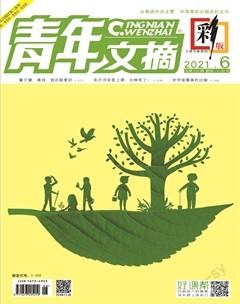我是小鎮做題家
南柯

從小我就生活在一種兩難的尷尬境地,但等到高中我才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這種尷尬,我一直難以描述,直至在網上看到“小鎮做題家”這個詞。“小鎮做題家”指的是那些出身小村鎮,有名校光環,卻缺乏視野和資源,導致“除了做題什么都不會”的寒門學子。這不正是我嗎?
我出生在湖南的一個小城鎮,七歲時家里搬到了安置小區。雖然我從小因為家里經濟窘迫,不能跟同學一樣去學舞蹈,也沒錢上任何補習班,卻意外地成績好,常常受到周圍鄰居的夸贊。初中時,作為年級第一的我很愛笑,和朋友們玩鬧起來總是大大咧咧沒心沒肺,跟老師們的關系也很不錯。而升入重點高中,進入重點班后,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眼前依舊是眾星捧月的場面,而這一次,我變成了一顆最不起眼的星星。
慢慢地,我發現,自己似乎變成了班里的丑小鴨。我沒看過梭羅和尼采,不懂她們閑聊時的娛樂八卦,也沒有任何特長加持,甚至連我最擅長的學習,也變得十分吃力。我坐在教室后排的角落里,艱難地適應著自己在班級里近乎透明人的角色。我變得謹小慎微,害怕因為見識少而鬧出笑話,害怕因為說錯話而顯得自己情商低,更害怕被別人看出自己小心翼翼藏起的自卑和脆弱。
直到今天,我都依然記得高一做早操時的情景。在寒冷的冬天,我穿著五彩條紋的厚棉襪和褪了色的帆布鞋,后面的男同學笑道:“你這搭配也太奇怪了吧,你不冷嗎?不會是買不起鞋子吧?”他的話惹得大家都笑了起來。我尷尬得恨不得鉆進地洞里去。不過是無心的一句玩笑話,我卻再也沒有穿過那雙鞋,甚至看到它就會想起當時的窘迫與無助。于是我穿著腳底破了洞的球鞋,過了一整個冬天。
這樣的場景在三年的高中生涯中不算少,與日俱增的敏感也漸漸地成了我交朋友的阻礙。我可以和同學們保持著友好的關系,卻總也跨不過那道無形的壁壘。我不知道如何巧妙回應他們開的玩笑,不知道如何自信又自然地加入他們的對話,不知道怎么放下戒備去建立起正常的友誼……
高三時,我的同桌是個性格溫和的城市孩子,她很優秀,卻常常因為成績上不去急得掉眼淚,我因此常常陪她去操場散心。一天,我們聊起自己的朋友,她突然很嚴肅地問我:“你沒有發現,你只喜歡和比不過你的人交朋友嗎?”我一時間啞口無言,因為她說對了。從小,我就是個很沒有安全感的孩子,在比我優秀的人面前,我太害怕被人看出自己的淺薄愚鈍,也太害怕因為自己的窮酸窘迫變成別人的笑柄。只有和那些家境或是成績不如我的人在一起,我才覺得自在,才敢肆無忌憚地做自己。
回想我的高中生涯,大抵就是在焦慮和窘迫不安中度過的。而當我逐漸成熟,再回看那段時光,透過日記本上歪歪扭扭的字跡,看到那時迷茫無助又焦慮的自己,才發現,很多的心情就像是一場漫長的獨角戲,別人的無心之語、無意之舉,被我敏感地察覺到,繼而藏在心里不停發酵,慢慢累積成情緒,畫地為牢,困住前行的腳步。
回頭去看,我也并非孤身一人。我的高中同學,大抵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那些家庭條件好、多才多藝、自信大方的“天之驕子”,另一類則是我們這些灰頭土臉的農村孩子,各有各的窘迫和敏感。
當我進入大學,才發現自己不過是井底之蛙,從來只關心著方圓幾里的生活,看不到這世界的廣闊與多彩。我更加深刻地在方方面面感受到差距,也更加清晰地發現自己的淺薄無知。但我開始明白,一定不止我一個人是這樣。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只要你發現你不是孤身一人,你不是最慘的那一個,心里就會好受很多。在網上,大家分享著自己的心酸故事,有人因為不懂公交車的規則在路口拼命朝公交司機揮手而被取笑,有人在現實強烈的沖擊下出現心理危機……大家在各自的生活里戰斗著,情緒在深夜波濤洶涌,卻又無從訴說。
而當我與這世界接觸越多,才真正明白“多樣性”的真正含義。正如梭羅所說,從一個圓心能向外畫出多少半徑,就有多少種生活。
梁衍軍//摘自《中學生百科·悅青春》2021年第1~2期,王果/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