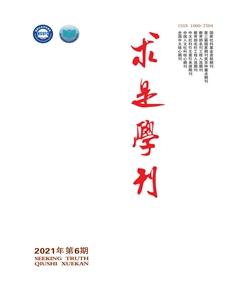忠義緣何在水滸?
摘 要:《〈忠義水滸傳〉序》是《水滸傳》主題解讀中一篇極為重要的文字,然而關于該序深層內涵的解讀尚難以讓人完全滿意。李贄眼中的豪杰往往有著強烈的入世情結、鮮明的俠之氣概與超凡的能力要求,而水滸英雄恰好完美地符合了李贄心目中的豪杰標準。在萬歷二十年(1592)的歷史背景下,李贄《〈忠義水滸傳〉序》中對于梁山英雄的崇拜,不僅指向文學世界中的人物,還和張居正、梅國楨、林道乾這三個歷史人物密切相關。李贄此文的寫作目的是想通過對江湖之盜的高揚,來反襯朝廷能力之不足,進而曲折地表達一種對于朝廷用人的抨擊與批判,并在其中表達李贄自我的人生寄寓。
關鍵詞:李贄;豪杰觀;《水滸傳》;忠義說
作者簡介:陳剛,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西安? 710119)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晚明常奇觀念的蛻變及其對文學之影響研究”(17CZW026)
DOI編碼: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6.015
李贄的《〈忠義水滸傳〉序》是《水滸傳》主題解讀中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獻,同時也是李贄《水滸傳》評點中目前唯一可以確定為出自其本人手筆的文字。在《〈忠義水滸傳〉序》之后,原本流于概念與表象的“忠義說”被李贄賦予了內在的靈魂與深層的內涵。然而,目前對于該序的解讀仍難以讓人完全滿意。1已有研究對于筆者有較大的啟發。然而前人對于李贄“豪杰觀”的具體內涵還未能予以充分挖掘,對于李贄的豪杰觀和當時歷史背景的內在關聯尚缺乏深入探討,對于此文思路生成的具體理路還未能加以清晰呈現。如果對李贄的評點過程加以回顧便不難發現,《水滸傳》的評點不僅持續了很長時間,也讓李贄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水滸傳》評點在李贄的生命中占據著極為特殊且重要的地位。誠如懷林在《李卓吾批評〈水滸傳〉述語》中所說:“和尚自入龍湖以來,口不停誦手不停批者三十年,而《水滸傳》、《西廂曲》尤其所不釋手者也。蓋和尚一肚皮不合時宜,而獨《水滸傳》足以發抒其憤懣,故評之為尤詳。”1那么,《水滸傳》到底是在哪個層面上引發了李贄如此巨大的興趣與共鳴?李贄到底有著怎樣不合時宜的憤懣?這種憤懣又為何只有借著《水滸傳》這樣的小說才能夠得以抒發?這就必須深入到李贄的思想觀念與序言寫作的歷史背景中才能加以解釋。
筆者認為,《〈忠義水滸傳〉序》的寫作和李贄的豪杰觀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水滸英雄正是李贄心中豪杰奇人的一個文學范本。而李贄的評點思路又決定了該序關注的重點并不在于文學技巧層面,而是和晚明諸多歷史人物、事件糾纏在一起,進而形成一種政治思考與社會批判。因此,不了解其背景,便無法復原該序的歷史語境,更無法深入理解序言的真正內涵。本文首先對李贄的豪杰觀加以梳理歸納,其次通過張居正、林道乾、梅國楨這三個歷史人物逐層捋清李贄此文寫作的思想理路,最后再結合此文寫作的歷史背景對李贄《〈忠義水滸傳〉序》的深層意義加以細致分析,以期對這一問題產生更新的認識。
一、李贄的豪杰觀
誠如黃卓越所言,李贄一生有著無法擺脫的“豪杰”情結2,他不但自己常以豪杰自居,而且對于世間豪杰之人有著高度的推崇與深情的呼喚。在《與焦弱侯》中,他開篇即言:“人猶水也,豪杰猶巨魚也。欲求巨魚,必須異水;欲求豪杰,必須異人。”3在李贄看來,無論是治國安邦還是成賢成圣,都需要境界闊大之豪杰,而非貌似謹厚之鄉愿。那么,李贄所謂的豪杰到底具備怎樣的特點呢?
1. 豪杰的入世特征
在李贄眼中,豪杰首先具有著鮮明的入世性,是一種轟轟烈烈的大丈夫人格,而不是一種猥瑣取容的犬儒人格。在《藏書》中,他這樣評論韓信之死:“今世人士,少知自好,猶能判身首以就功名,況烈丈夫之業乎!等死耳,牖下亦死,湯鑊亦死,自無用太較計為也。”4可見,李贄認為大丈夫應當積極入世,建功立業,轟轟烈烈地成就自己在現實世界中的功名。因此,在李贄眼中,豪杰并非隱居出世、“養成神龍虛譽”的高人隱士,而是委曲以求其用、委曲以濟其用的積極入世之人。在《復周南士》中,他最為推崇的一類人正是如此:“又若有大用之才,而能委曲以求其必用,時不必明良,道不論泰否,與世浮沉,因時升降,而用常在我,卒亦舍我不用而不可得,則管夷吾輩是也。此其最高矣乎!”5
也正因如此,李贄所推崇的豪杰往往是張居正、何心隱、梅國楨、顧養謙一類的人物,其著眼點正在于他們能夠在現實世界中有所作為。如他評價何、張二人:“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跡而原其心,不責其過而賞其功,則二老者皆吾師也。”6評價顧養謙、梅國楨也十分側重于二者積極有為的一面:“顧沖庵具大有為之才,負大有為之氣,而時時見大有為之相,所謂才足以有為,而志亦欲以有為者也。梅衡湘亦具大有為之才,而平時全不見有作為之意,所謂無為而自能有為者也。此二公之別也。然皆當今之杰也,未易多見者也。”1可見,積極入世、建功立業,才是李贄對于豪杰人生的基本定位。
李贄之所以極為強調豪杰的入世性特征,和他富國強兵的政治目標之間有著密切的因果聯系。正如周治華所說:“他只是主張在禮樂刑政和道德教化上無所作為,但在生財致富和計功謀利上恰恰要求有所作為。”2可以說,富國強兵既是李贄對于一個臣子在能力方面最大的期待,也是李贄對于一個人才最終的衡量標準。
在《藏書》中,李贄對于那些有能力、有辦法實現國家富強的人表示由衷欽佩。如其將西漢桑弘羊的均輸之法視作“國家大業”,認為這樣的政策乃“制四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3。又和傳統史論立異,認為王安石之罪并不在于有意生財,而在于“其才之不足以生財”,“不知所以生財”4。批駁司馬光反對理財的言論道:“光謂安石不曉理財可也,而謂不加賦而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以此謂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則可笑甚矣。”5這些言論都充分表明李贄對富國之事持一種十分積極的態度。
對于富國如此,對于強兵也不例外。如針對富弼向宋神宗所提建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李贄直接斥為“胡說!”6對于范仲淹“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這樣的言論,李贄直接反駁道:“兵豈名教外耶?”7可見,李贄認為強兵本身就應是儒者的分內之事。在李贄眼中,國家只有積極發展經濟、儲備兵力,才能達到富國強兵的政治目標。而這種政治目標也決定了李贄眼中的豪杰奇人必然是積極用世之人,因為隱居出世之士對于國家經濟軍事發展所起的作用無疑是極為有限的。
2. 豪杰的俠之氣概
李贄眼中的豪杰往往具備一種俠的精神與氣概,這表現在他們具有超常的氣魄與意志,在關鍵時刻敢于挺身而出、舍身成事,為天下人所倚賴,而非空有一腔道德情感,遇事卻束手無策的無能之輩。
袁中道曾這樣記載李贄對俠的定義:“俠從人從夾,為可以夾持人也。如千萬人在危急之中,得此一人即安,失此一人即危。人人可以憑借之,方謂之俠。今人不識俠,轉以擊劍報仇為俠,則可笑甚矣。”8可見,在李贄看來,俠的精髓并不在于擊劍報仇這樣的粗豪之舉,而在于讓千萬人在危急之中轉危為安的精神氣概。這也決定了李贄不是從個人性靈的抒發、個體生命的自適等角度來肯定豪杰價值的,而是從國泰民安、經世致用這種實際的社會效果層面來發掘豪杰意義的。這在諸多地方都有體現,如李贄在《復麻城人書》中談到自己對“高陽酒徒”的理解:
今之好飲者,動以高陽酒徒自擬,公知高陽之所以為高陽乎?若是真正高陽,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即撲滅,不至勞民動眾,不必損兵費糧,無地無兵,無處無糧,亦不必以兵寡糧少為憂,必待募兵于他方,借糧于外境也。此為真正高陽酒徒矣。9
又在《昆侖奴》中談及對于許中丞與昆侖奴的態度:
許中丞片時計取柳姬,使玉合重圓;昆侖奴當時力取紅綃,使重關不阻:是皆天地間緩急有用人也,是以謂之俠耳。忠臣俠忠,則扶顛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俠義,則臨難自奮,之死靡他。古今天下,茍不遇俠而妄委之,終不可用也。1
這兩段話透露出一種共同的思想理念:豪杰之所以成為豪杰,不在于為己,而在于為人;不在于自救,而在于救世。這種對俠的理解和認識也決定了李贄眼中的豪杰并非僅有一腔道德熱情,而應具備扶顛持危、舍身成事的勇氣與氣概,并以一種俠的精神在現實世界中產生積極且實際的效果。這一點李贄在《昆侖奴》中表達得尤為明確:“俠士之所以貴者,才智兼資,不難于死事,而在于成事也。使死而可以成事,則死真無難矣;使死而不足以成事,則亦豈肯以輕死哉!”2可見,和傳統士人在一種道德情感下的“死事”不同,李贄更加看重的是豪杰在關鍵時刻的“成事”。在《高翔程濟》中,對于明代建文朝的兩位名臣,李贄之所以更加欣賞以智術為忠的程濟,而非以殺身為忠的高翔3,其原因正和他對于豪杰輕道德、重事效的評價標準有著密切關聯。
3. 豪杰的能力要求
那么,李贄對于豪杰又有什么具體的能力要求?在李贄看來,豪杰應具備識、才、膽這三個條件。李贄曾在多處強調三者的重要性,他認為無論是學道還是修齊治平,皆須以識、才、膽作為基礎:“然則識也、才也、膽也,非但學道為然,舉凡出世處世,治國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總不能舍此矣。”4
而三者當中,李贄最為看重“識”的重要性,認為“才與膽皆因識見而后充”:
有二十分見識,便能成就得十分才,蓋有此見識,則雖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見識,便能使發得十分膽,蓋識見既大,雖只有四五分膽,亦成十分去矣。是才與膽皆因識見而后充者也。5
可見,在識、才、膽三者之中,“識”無疑占據著統領的地位。
對于才和膽,李贄往往將二者視作一種可以互生的關系。他說:“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膽者,有因膽而發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6而對于豪杰成事來說,才和膽又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空有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膽而無其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7
那么,到底何為才?何為膽?李贄雖曾說過“仁即才”8,然而以“仁”這樣的概念來解釋“才”多少有著模糊化與空泛化的弊端。上文曾引李贄《二十分識》中的“空有其膽而無其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一句,深味此句,不難發現:“才”在李贄的意識里更接近于智術。換句話說,識的作用在于知曉何者為正、何者為誤,認清整體的局勢與方向,而才的作用則在于讓人在實現自己的目標時不至于“冥行妄作”,具有實際而科學的道路與策略。在《復鄧鼎石》一文中,李贄談及救荒之策,就曾將才與術相連用:“世間何事不可處,何時不可救乎?……惟是世人無才無術,或有才術矣,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趨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斃。”9這里的“才”顯然被賦予了“處理緊急事件或應對危機局面的能力”這樣的含義,這也正和李贄對于俠“不難于死事,而在于成事”的理解相一致。
李贄所謂的膽,更多是指一種剛毅果敢的勇氣、威風八面的氣質。在《二十分識》中,李贄曾說:“空有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可見,“膽”賦予人一種勇往直前的勇氣。在《藏書》中,李贄曾多次稱贊項羽為好漢:在項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時,李贄評曰“好漢”;在項羽破秦之后,“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時,李贄又評曰“千古好漢”1。如果說前一處側重于項羽當機立斷、果敢干練的處事風格,那么后一處則側重于其人威風八面、膽氣充足的精神氣質。這兩者皆為李贄所謂“膽”的題中之義。
除以上三點之外,李贄還認為豪杰在道德人格上往往是不完美的,這種不完美正是豪杰區別于鄉愿、常人的一種外在標志。李贄曾明確表達:“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暇疵處必多。”2又說:“天下未有有才能而無過者。”3對于張騫,他持一種“略其節而愛其才”4的態度。可見,李贄在評價豪杰時,往往注重其闊大之境界與超人的才能,而對其道德上的瑕疵或行為上的過失,則有意采取一種淡化乃至忽略的態度。
如果以李贄的豪杰觀來審視《水滸傳》中的英雄人物,不難發現,水滸英雄可謂完美地符合了李贄對于豪杰的各種要求。首先,宋江等人具有較強的入世情懷,他們雖落草為寇,卻希望通過招安來擔負起對于社稷百姓的責任,正所謂“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5。其次,水滸英雄大多具有著一種俠的精神氣概,在危難之時,可為世人倚賴。這種俠的氣概一方面表現為在民間社會中的懲惡揚善、打抱不平,另一方面也表現為在國家層面上的征討方臘、報國安民,不當“自了漢”。再次,水滸英雄往往在識、才、膽這三個方面十分突出,李贄在《水滸傳》第五十九回就曾評價水滸英雄“只是才大、識大、膽大耳”6。最后,水滸英雄往往不是道德品行上完美無缺的人物,落草為寇本身就是他們身上的一種道德瑕疵,而他們也大都不是四平八穩的圣賢性格,而是性格突出、個性鮮明、言由心發、內外一致。可以說,水滸英雄是李贄豪杰觀念的一種形象化,《水滸傳》正是李贄豪杰觀的一個文學范本。李贄之所以將《水滸傳》作為自己孜孜不倦地加以評點的對象,除了對小說文字的欣賞,更多地其實是在抒發一種對于豪杰奇人的愛慕與敬佩,也是在通過小說評點的方式進一步表達自己的豪杰理想。
二、《〈忠義水滸傳〉序》寫作的歷史背景
當然,要理解《〈忠義水滸傳〉序》的深層內涵,不僅應該了解李贄的豪杰觀念,還要對該序寫作的歷史背景做出深入細致的考察。而要考察歷史背景,首先應大致確定該文的寫作時間。按照林海權《李贄年譜考略》對于李贄詩文的編年,此序寫于萬歷二十年夏在武昌朱邸批點《水滸傳》時7,張建業在《焚書注》中也大致認同此說8。二人編年的依據都來自于袁中道的一句話:“記萬歷壬辰夏中,李龍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訪之,正命僧常志抄寫此書,逐字批點。”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僅言萬歷壬辰夏(即萬歷二十年夏)李贄正在批點《水滸傳》,說明此時《水滸傳》的批點尚未完成,而對于古代和刻書密切相關的序言來說,序言更應該寫于著作完成之后、書籍刊印之前。故而筆者認為:此序的實際完成時間應該比萬歷二十年夏更晚。
那么,應如何考察該序的歷史背景?在《〈忠義水滸傳〉序》中,表達的最為核心的觀念便是:平庸之人與賢能之士顛倒異位,導致大賢大德之人不受重用,不得不落草為寇,從而使忠義盡歸于水滸。而這一觀念事實上在李贄萬歷二十年四月間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出現過,這篇文章便是《因記往事》。在此文中,李贄感嘆朝廷不能重用林道乾時說:“唯舉世顛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戚,直驅之使為盜也。”1這正可視作《〈忠義水滸傳〉序》中觀念徹底形成的前奏。而《因記往事》一文的寫作又和萬歷二十年的平西之事有著直接的聯系,李贄在《復麻城人書》中明言:“時聞靈、夏兵變,因發憤感嘆于高陽,遂有《二十分識》與《因記往事》之說。”2靈、夏兵變即寧夏哱拜叛亂之事,可見該文的寫作正處在“西事”的大背景下。哱拜叛亂的發生與張居正去世后明王朝政局的混亂有著密切關系,而此事的平定又有著李贄好友梅國楨的莫大功勞。故而不妨從張居正、林道乾、梅國楨這三個歷史人物切入,對該序寫作的歷史背景加以深入挖掘。
1. 張居正去世后的明代政局
萬歷初期,張居正以其出色的政治才能、有力的政治手段對明王朝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改變了文官作風,提高了行政效率,再創了明代國家社會的輝煌。然而,好景不長,萬歷十年(1582)張居正去世,繼張居正上位的張四維、申時行等人大多不具備至高的政治威望,也缺乏強有力的政治手段,朝廷對群臣的控制力日益減弱,朝中的政治氛圍也逐漸寬松。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長期以來被壓制的言路開始擺脫以往的束縛,言官大膽抨擊當道,造成言官與內閣輔臣之間的對立。而萬歷十四年(1586)的“國本之爭”又加劇了明代中期以來的朋黨之風,并逐漸演變成不同黨派之間的激烈斗爭。此時,萬歷皇帝的消極怠工、內閣輔臣的平庸調和,又讓明王朝出現了一種權力真空的狀態,國家的問題日漸增多,許多官位缺而不補,朝中群龍無首。3
誠如楊亮所言:“帝國權力運作機能的癱瘓和官僚機構的腐敗,讓整個帝國處于巨大的危險之中。而在萬歷二十年,這種危險醞釀出了極為嚴重的內憂外患。”4萬歷二十年二月,哱拜等人在寧夏起兵叛亂,朝野為之震動。同年五月,豐臣秀吉出征朝鮮,《明史紀事本末》中言其形勢:“是時,倭已入王京,毀墳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庫,蕩然一空,八道幾盡沒,旦暮且渡鴨綠。”5
李贄雖常以出世之人自居,但實際上對明王朝的朝政時局保持著極為密切的關注。他在萬歷二十年所寫的《因記往事》《復麻城人書》等諸多文章都表現出對于國家行政效率普遍低下、官僚集團平庸無能、人才儲備捉襟見肘的強烈不滿與擔憂。這種擔憂,決非李贄一人之思想傾向,誠如美國學者艾梅蘭所說:“這些正當的憂慮推動了一場運動,這場運動背離了理學的修身所導致的那種內省的寂靜主義(quietism)的理想,向著一種具有行動主義興趣的實學靠攏。”6而李贄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激進。在李贄看來,明代此時最需要的并非清而無用的道德楷模,而是類似于張居正這樣的鐵腕人物,因為只有這種具有實際才能的豪杰奇人,才能為疲軟怠惰的國家注入一劑強心針,為國家解決實際的矛盾與問題,進而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他在萬歷二十年所寫的文章中曾多次表達對于張居正的欣賞與懷念,如在《答陸思山》中,剛剛從友人那里得知“西事”,李贄就說:“些小變態,便倉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真令人益思張江陵也。”7在《與友山》中也感于“西事”說:“今惟無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負固。”8可見,他之所以大力肯定才能之士,熱情呼喚豪杰奇人,正是出于一種對張居正秉政時期國家事務井井有條、輔臣才士精于吏事的深切懷念。
2. 橫行海上的林道乾
在哱拜叛亂的初期,大約萬歷二十年四月的時候,李贄尚不知道有梅國楨請命之事。1出于對國家局勢的擔憂以及對朝廷不能重用才能之士的激憤,李贄寫下了《因記往事》一文。在文中,李贄積極地肯定識、才、膽兼備的江湖豪杰——林道乾,大力抨擊朝中那些“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的道德之士2,而林道乾恰恰成為溝通當時社會現實與《水滸傳》小說的一座重要橋梁。
林道乾,閩之晉江人,一說為廣東潮州府惠來人。明嘉靖、萬歷間以海盜身份活動于浙江、福建、廣東、臺灣一帶。李贄曾對其相關行徑加以描述:
夫道乾橫行海上,三十余年矣。自浙江、南直隸以及廣東、福建數省近海之處,皆號稱財賦之產,人物隩區者,連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殺戮官吏,朝廷為之旰食。除正刑、都總統諸文武大吏外,其發遣囚系,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也,而林道乾固橫行自若也。3
這種具體的盜賊行徑固然不是李贄欣賞的重點,但林道乾在這一過程中所表現出的非凡才能、識才膽兼備的豪杰本色,卻成為持“歷史功利主義觀”的李贄所激賞的對象。4在李贄看來,太平之時,林道乾依然能夠“稱王稱霸,眾愿歸之,不肯背離。其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群類,不言可知也”5。
然而很明顯,李贄并未止步于對林道乾才能的欣賞,而是以林道乾有大才卻不能為朝廷重用,最終卻只能在江湖施展才華為現實依據,展開了對于當時朝廷用人的激烈批判。他先是以假設的筆法點明,假如朝廷重用林道乾將會產生怎樣的效果:“設使以林道乾當郡守二千石之任,則雖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決不敢肆。”6而棄置林道乾這樣的大才不用,朝中所用又為何等人?在李贄看來,全都是些平庸無用的道學之流:“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為能明哲。”7故而兩相對比,李贄得出了擲地有聲的結論:
蓋因國家專用此等輩,故臨時無人可用。又棄置此等輩有才有膽有識之者而不錄,又從而彌縫禁錮之,以為必亂天下,則雖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爾。設國家能用之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當勝兵三十萬人已耶?又設用之為虎臣武將,則閫外之事可得專之,朝廷自然無四顧之憂矣。唯舉世顛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戚,直驅之使為盜也。8
這段話不僅對朝廷不能重用豪杰的現實進行了猛烈抨擊,還對豪杰之士為盜的原因與合理性加以了解釋:并非豪杰之士原本想要為盜,而是朝廷“棄置此等輩有才有膽有識之者而不錄”,“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戚”,因而豪杰不得不采取這樣一種無奈之舉。這一論斷不僅和《水滸傳》中英雄豪杰“逼上梁山”的故事模式之間形成了一種共鳴,也和《〈忠義水滸傳〉序》中“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于人……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于人……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1的思路如出一轍。
3. 平西之事中的梅國楨
李贄一方面熱情地呼喚具有實際才能的豪杰之士,另一方面在《〈忠義水滸傳〉序》中反復提及的現實卻是“小賢役人”“大賢役于人”。這種感觸的產生與李贄的好友梅國楨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李贄曾多次表達對于梅國楨才能的欽佩,可以說,梅國楨正是李贄心目中標準的豪杰之士,而這一認識離不開梅國楨在“西事”中的杰出表現。萬歷二十年春,寧夏副總兵哱拜及其子承恩殺死巡撫都御史黨馨、副使石繼芳,據城叛亂,成為轟動朝野的“西事”。2在李贄看來,此事甚為緊急,所謂“東事尚緩,西正急耳”3,而此時朝廷樞密大臣想要選鋒遣將,卻沒有合適之人能當其選,面對著危急局面束手無策。在此關鍵時刻,梅國楨上疏力薦之前雖有過失、能力卻極為突出的將領李成梁。4毫無疑問,梅國楨這種在危急關頭拋開道德清流的苛責浮議,大膽舉薦才能之士的行為,和李贄的用人思想不謀而和。而此時李成梁正在遼東,便命其子李如松先行,由御史梅國楨監軍。5李贄聞此消息,喜見眉睫,胸有成竹地認為:“西方無事矣!客生以侍御監軍往矣!”“軍中既有梅監軍在,公等皆可不必憂矣!”6在他看來,梅國楨這樣的豪杰之士,可以很好地應對這樣的危機。
果然不出李贄所料,平西之戰五月發兵,九月亂平,十一月即“獻俘于廣闕下,報捷于京師”7。然而之后的論功行賞卻極不公平,導致輿論大嘩。在這場戰役中,梅國楨運籌帷幄,勞苦功高,但卻“回朝半歲,曾不聞有恩蔭之及,猶然一侍御”8。而遠離戰場,戰事取勝后殺降以冒功的甘肅巡撫葉夢熊,卻由于與兵部尚書石星交往密切,升任正二品的右都御史。這怎能不激起李贄的義憤?雖然敘功封賞幾經周折,最終塵埃落定,梅國楨也在萬歷二十一年(1593)升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但這種豪杰之士舉步維艱、鉆營之徒青云直上的社會現實,又怎能不讓李贄產生“小賢役人”“大賢役于人”的感慨?
由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李贄之所以秉持著一種豪杰觀,并體現出鮮明的重能力、輕道德的取人傾向,和萬歷十年以后的歷史背景有著很大的關系。具體而言,李贄《〈忠義水滸傳〉序》的寫作受到三個歷史人物的重要影響,即張居正、林道乾、梅國楨。張居正去世后,由于朝中缺乏能夠平定禍亂、把控政局的豪杰之士,國家內憂外患。到萬歷二十年,寧夏發生了哱拜之亂。李贄出于對時局的擔憂,對張居正這樣的鐵腕式人物產生了強烈的懷念,并追憶了“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群類”的海盜林道乾,由此得出了“唯舉世顛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戚,直驅之使為盜也”9的憤激之論。在得知梅國楨以監軍身份前往寧夏平叛之后,李贄的這種情緒雖有所緩和,然而在平西過程中,梅國楨以無權之監軍歷盡艱險方能成其大功,戰事平定之后,朝廷一開始賞罰不明,使得梅國楨有功而不得其祿,這又重新激發了李贄對于朝廷用人的再度反思與憤慨。只有充分了解了這一歷史背景,李贄寫作《〈忠義水滸傳〉序》的一些深層動機與細微內涵才能顯現出來。
三、《〈忠義水滸傳〉序》之意義發微
可以肯定地說,李贄為《水滸傳》作序,其主要目的并不是站在盜賊的角度對盜賊本身進行謳歌,而是站在國家的角度,通過對于江湖之盜的高揚,來反襯朝廷能力的平庸與不足,進而曲折地表達一種對于朝廷用人的抨擊與批判。也正因為此,此文的言說對象并不指向于平民階層或者文士階層,“好事者資其談柄,用兵者借其謀畫”已被李贄明確地排除在關注范圍以外,瑣細的文學手法、寫作技巧又怎會是他關注的重點?李贄此序的言說重點實際上指向了朝中的達官要人,尤其是那些具有用人權力的“有國者”“賢宰相”“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者,其目的正在于借評論《水滸傳》為當政者說法,讓他們反思人才之道,不要以儒家苛刻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豪杰之士,而應唯才是舉,舉賢任能,改變“大賢役于人”的可悲局面。而這種“小賢役人”“大賢役于人”的說法又暗含了一層對朝中官員的激發之意,即他們不能身在其位卻尸位素餐,讓忠義旁落水滸,讓豪杰最終只能迎來“雖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爾”的可悲命運。
李贄的這種觀念在萬歷時期的文人中又有著很強的代表性,僅在公安派文人的文集中就可以找到大量例證。如袁宗道曾批判明朝的用人:“晚世過信德而過疑才,重無用而輕有用,崇虛而黜真,進名而退實,非古人察能授官之義也。”1在《雜說》中又說:“三人者……蓋抱奇才,負大用,而世乏具眼,不用于世,故頹然放于聲酒之間,以自排遣。……世有此等異人,而使之不用,豈非唱騶諸公之恥哉!”2袁宗道所表達的對于國家用人的批判與對于奇才不能見用的深深惋惜,與李贄《〈忠義水滸傳〉序》中的思想何其相似!袁宏道也曾說:“處今日之時,正古人所謂權以濟事者,似亦不當拘拘矣。”3又在《顧升伯太史別敘》中對當時豪杰之士不能為人所用,偽士滿朝、腐儒誤國的現狀深表不滿:“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杰不樂為用,而蔽賢為小。夫豪杰所以不樂為用者,非真世不我容,一時執政諸大臣,有、檜之奸,林甫、嵩之之媢嫉也。其人固皆方正儒者也。”4前者和李贄重其才而略其德的用人觀念可謂如出一轍,后者何嘗不是朝廷以道德衡人最終驅豪杰于水滸的另一種表達?袁中道也曾指出,明王朝用人最大的問題在于“避嫌之意多,憐才之意少”5:“人有大才而破格用之,人不以為是也。人本無才,而循格用之,人不以為非也。”6又在《報伯修兄》中說:“居今之時,而直以圣賢之三尺律人,則天下豈有完人?反令一種鄉愿,竊中行之似,以欺世而盜名;而豪杰之卓然者,人不賞其高才奇氣,而反摘其微病小瑕,以擠之庸俗人之下,此古今所浩嘆也。”7這正是“以小賢役大賢”的另一種表述。可見,萬歷時期相當一部分受左派王學影響的文人認為,國家在用人上有著過于以德取人、循格用人的弊病,用人者寧可錄平庸之士,也不愿包容豪杰的“微病小瑕”,這最終導致了豪杰不樂為用的局面。而李贄的《〈忠義水滸傳〉序》之所以能在當時引起共鳴,恰恰根源于這部分文人對國家用人的強烈不滿。
由此可見,李贄將“忠義”歸于水滸,其實并非一種“正說”,而是一種對于朝廷用人強烈不滿的“反說”,更是一種對于朝中用人者的“刺激之說”,其根本動機還是出自于一種傳統士人階層對國家命運的擔憂以及對國家富強的渴望。但時過境遷,序言中的這層意思顯然沒有被后人完全理解,才子金圣嘆便曾批評“忠義”之說道:“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以‘忠義’之目。……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為天下之兇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8又說:“世人讀《水滸》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義’目之,真不知馬之幾足者也。”1未能深入體會李贄將“忠義”歸于水滸的良苦用心與最終目的,也不去考察這一說法提出的思想軌跡、流行的歷史背景,僅以表面上的忠義歸屬就對忠義之說整體橫加批評,吾恐圣嘆此論才是真“不知馬之幾足者也”!
至此,再聯系袁中道《李溫陵傳》中對于李贄“本絕意仕進人也,而專談用世之略”的描述,便不難理解,這種看似“不可知”的矛盾行為,實際上恰恰是解開李贄思想的一把重要鑰匙。人們往往將李贄視作一種異端式的存在,強調其學佛出世或者悖逆傳統的一面,甚至連《〈忠義水滸傳〉序》這樣的文字也時常被人解讀為一種對于異端之盜的同情,然而又有幾人能看到,其實自居異端本身就是李贄的一種無奈之舉,而對于異端的同情背后實際上曲折地隱含著李贄革新傳統思想、完善主流社會的用世情懷呢?不少明末清初的學者在批判晚明學術“游談無根”“空疏頑固”時,往往以李贄為靶子,然而李贄的思想中又何嘗沒有腳踏實地的那一面,又何嘗沒有他們所提倡的經世致用之因素呢?
故而結合李贄的生平,便不難理解李贄為何會對《水滸傳》情有獨鐘,也不難理解懷林為何會說:“蓋和尚一肚皮不合時宜,而獨《水滸傳》足以發抒其憤懣。”李贄早年為官,“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2。這種性格無疑和當時繁文縟節的官場生活方枘圓鑿,故所遇輒與人觸。他之所以推崇有大才而又略帶性格缺陷或者道德瑕疵的豪杰之士,恰是因為他自己正是這種類型的奇人。之所以主動致仕,是因為他心里很清楚,當時循規蹈矩的朝廷是無法重用自己這樣的出格豪杰的。而后來的獄中自刎也再次反映了他的這一認識:以李贄在文人中的名聲與影響力,出獄回籍斷不至于無路可走,之所以選擇自殺,是因為他知道即便出去,在這個世界依然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而這樣遷延下去,他注定面臨“丈夫無故而死”的平庸。3
李贄人生選擇的深沉無奈其實在他評價林道乾時就已經表達得非常充分了:“夫古之有識者,世不我知,時不我容,故或隱身于陶釣,或混跡于屠沽,不則深山曠野,絕人逃世而已,安肯以身試不測之淵也?縱多能足以集事,然驚怕亦不少矣。吾謂當此時,正好學出世法,直與諸佛諸祖同游戲也。”4這看似是對林道乾的評論,其實又何嘗不是李贄自我人生道路抉擇時的一份心理獨白?而出世游戲的背后又何嘗不隱含著李贄對于時世的一種不平與憤激?故而,李贄一開始就將《水滸傳》定位為施、羅二公的發憤之作。事實上,施、羅二公是否借水滸之強人泄憤或未可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李贄的確是在借著評點《水滸傳》而泄憤,泄自己之憤,同時也泄當世豪杰之憤。明乎此也就不難明白,李贄為何會如此鐘情于《水滸傳》,因為《水滸傳》的閱讀與評點中正有著李贄自我的一份人生寄托。
余? ? 論
前人雖有通過豪杰觀這一角度來闡釋《〈忠義水滸傳〉序》意義的先例,但是對于李贄豪杰觀的具體內涵尚缺乏深入的探討。筆者通過文獻的梳理,總結提煉出豪杰具有強烈的入世情懷、救世成事的俠之氣概、識才膽的能力要求,有利于學者從更加深入的層面發掘李贄的豪杰觀與《〈忠義水滸傳〉序》之間的內在聯系。關于李贄此文寫作的歷史背景,雖然也有學者注意到了張居正、林道乾、梅國楨以及平西之事對于序言寫作的影響,但是這些人物事件的先后順序如何?內在的邏輯聯系又如何?這些因素又是怎樣一步步作用于寫作主體并最終形成這篇序言的?這些問題尚未得到有力的探討。本文通過對于這些人物、事件時間先后的梳理,更加細致也更加全面地還原了李贄此文寫作思路生成的內在理路,這對于人們深入理解《〈忠義水滸傳〉序》的寫作動機與深層意義都有一定價值。
通過對《〈忠義水滸傳〉序》的深入解讀,也可對目前的李贄研究構成一種啟發:大部分學者往往將李贄視作一種異端式的存在,重點關注李贄和傳統儒家文化、明朝官方政府之間對立或者不合作的一面,然而如果剝開李贄異端的外表,深入探討其某些言論的內在動機,不難發現,他和傳統主流文化之間仍有著諸多的溝通之處。就像《〈忠義水滸傳〉序》,表面上看似是一種對于異端之盜的同情,但其思想核心仍是一種對于朝廷局勢的憂慮、一種對于人才不能見用的不平,只不過用一種較為激進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已。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李贄的言論在當時并非一個孤立式的存在,在他“奇談怪論”的背后,實際上有著某種同時代文人共識性的意見作為他的言論后盾與思想根基。故而對于李贄,不僅應看到他“奇”的一面,更應該看到他“奇”之背后“常”的那一面;不僅應看到他突破規矩束縛的那一面,還應該看到他順應時代潮流的那一面;不僅應凸顯他在當時文人中的獨特性,更應該深究他離經叛道言行背后的歷史背景與文化根源。1唯有如此,才能領悟李贄那些所謂的“異端”言行在晚明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是真正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