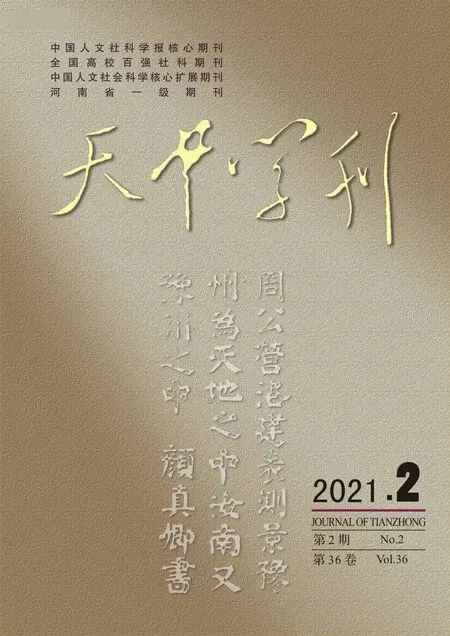作為一種方法的“詩胎考據”
——錢鐘書詩學考據學論略
項念東
(安徽師范大學 文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錢鐘書與陳寅恪的詩學研究恰好構成詩學研究的兩個基本范式。與陳寅恪堅守“詩史釋證”,矢志接續知人論世、比興說詩的學術傳統不同,錢鐘書側重屬詞比事的視角,將中國古代詩評詩話傳統與西方現代新學相融合,開創了以現代語言學、心理學、哲學和藝術學理論相貫通以說詩的另一路徑[1]。陳寅恪謹守說詩考史“第一義諦”,發明詩人之心以彰顯詩意所存,錢鐘書則立足“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2]1,在“連類舉似”之間掎摭詩藝。盡管二者學術性格、學術問題領域各有不同,但有一點很相似,即都在考據之學被批評的學術氛圍中以切實的研究為考據作了忠實的辯護。
錢鐘書的《談藝錄》《宋詩選注》《管錐編》均是富含考據氣息的著作,其中《宋詩選注》與《管錐編》完成于“對實證主義造反”的歷史年代。《宋詩選注》著于1955―1956年,1957年出版;《管錐編》主要寫作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版于1979年①。從這三部書的寫作體式看,《談藝錄》采用的是傳統詩話體,《宋詩選注》是注釋體,而世人傳誦的《管錐編》乃是一部龐大的“讀書筆記”。如果用當下流行的夾敘夾議式的“論著體式”來衡量錢鐘書著作的話,這三部書均近乎考據而遠于“論著”。
1978年9月,在歐洲漢學家第26次會議上,錢鐘書在以《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為題的發言中提出,“文學研究是一門嚴密的學問,在掌握資料時需要精細的考據,但是這種考據不是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不能讓它喧賓奪主、代替對作家和作品的闡明、分析和評價”,新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經過“對實證主義的造反”之后,“考據在文學研究里占有了它應得的位置,自覺的、有思想性的考據逐漸增加,而自我放任的無關宏旨的考據逐漸減少”[3]。那么,什么才是錢鐘書認為的恰如其分的考據呢?從發言中他舉例批評陳寅恪對“楊玉環入宮時是否處女”的考證來看,錢鐘書欣賞的不是陳寅恪式的“詩史釋證”,盡管后者通過考證楊妃入宮是否處子之身最終考見的是李唐王朝“胡漢”雜糅背后的文化精神。畢竟,錢鐘書始終強調與“詩眼文心”的“莫逆冥契”,故“作者之身世交游”之類的歷史考據只能被置于“余力旁及”的地位[2]346。錢鐘書對文史文獻可謂諳熟,著作中也多有精細的文獻考據案例,其對語詞的敏感及訓詁方法也多可稱道,但無論是詩學歷史考據,還是文獻與語詞考據,均非其著意所在。實際來看,錢鐘書的詩學考據可稱之為一種“詩胎考據”,即在錯綜排比之中考探詩學文本的“詩胎”所在,并批評其藝術得失,按《管錐編》的提法,也可稱之為“連類舉似而掎摭”[4]860。
一、從“薊丘之植植于汶篁”的解釋說起
“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語出樂毅《報燕惠王書》。這句話如何理解,寫作上有何藝術特點,陳寅恪與錢鐘書都曾談及,從中約略可見二者詩學考據方法的不同,以及錢鐘書“詩胎”考據的著眼點之所在。
1931年,陳寅恪曾發表《薊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簡易解釋》一文,篇幅不長,但考證工作背后的意味頗為深長。
《史記 · 樂毅傳》錄有《報燕惠王書》,在“薊丘之植,植于汶篁”一句下,裴骃《集解》引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于齊之汶水。”而司馬貞《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也。言燕之薊丘所植,皆植齊王汶上之竹也。徐注非也。”后此學者大多尊司馬貞之說。俞樾《古書疑義舉例》認為,這句話乃是句式倒裝,應當改為“汶篁之植,植于薊丘”。楊樹達《詞詮》則從文字訓詁的角度認為“于”“以”同義,此句實為“薊丘之植,植以汶篁”[5]297。陳寅恪認為,前此解釋中以俞、楊二家之說“最精確”,但同時指出:“夫解釋古書,其謹嚴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習見之義。故解釋之愈簡易者,亦愈近真諦。并須旁采史實人情,以為參證。不可僅于文句之間,反復研求,遂謂已盡其涵義也。”[5]297按照不改原有句式及用字的原則,他認為此句可理解為“薊丘之所植乃曾植于汶篁者”。看似差別不大,但陳寅恪將問題重點落到了“汶篁”二字的理解上來。
司馬貞將“篁”解釋為汶上之“竹”,而《集解》所引徐廣的解釋中卻提到“竹田曰篁”,后者恰是《說文解字》的解釋:“篁,竹田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引證《西京賦》《漢書》中的記載,指出“竹田曰篁,今人訓為竹,而失其本義矣”。此后,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等接續了這一解釋。陳寅恪指出,應參考段玉裁及曾國藩的意見,“‘薊丘之植,植于汶篁’既非倒句之妙語,亦不必釋‘于’與‘以’同義。惟‘篁’字應依《說文》訓為‘竹田’耳”[5]298。因為,“竹”與“竹田”雖僅一字之差,但文意表達卻有很大差別:
自來讀樂毅此書者,似皆泥于上文“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之語,謂此句僅與“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等句同例,而曲為之解。殊不知植物非財寶重器,可以“收入于燕”之語概括之。其實此句專為“故鼎返乎磨室”句之對文……蓋昌國君意謂前日之鼎,由齊而返乎燕,后日之植,由燕而移于齊。故鼎新植一往一返之間,而家國之興亡勝敗,其變幻有如是之甚者。并列前后異同之跡象,所以光昭先王之偉烈。而己身之與有勛勞,亦因以附見焉。此二句情深而詞美,最易感人。[5]299
詩文屬對最講究精切。燕曾大敗于齊,其國之重器珍寶曾被作為戰勝國的齊所劫掠,而今轉敗為勝,自然會將失去的一切“物”重新奪回。因此,“竹田”二字相對于“竹”而言,更是隱指家國之領土,唯此才足以與作為國家政權之象征的“舊鼎”對仗成文。且如此行文,才更足以彰顯樂毅此文意在表彰己身功績的用意。這是陳寅恪認為“篁”應釋為“竹田”的原因所在。更重要的是,“舊鼎”由燕至齊而今返歸燕國,而燕國竹田(亦可謂之燕篁)所植之物其實原本就來自于齊,而今又反以勝利者的姿態,重新移栽于戰敗國齊之舊域(汶篁),其一往一復之間,世事滄桑、家國興亡之感自可一覽無余。盡管這在樂毅,不過是勝利者一方的嘲笑,但燕齊之間勝敗轉換的歷史變遷則足以引發后人的無限唏噓。
再看錢鐘書對“薊丘之植,植于汶篁”一語的解釋。
《管錐編》第三冊中有一篇關于樂毅此語的專論。文章同樣引證司馬貞《索隱》的意見“古人詫為倒裝奇句”,然錢鐘書以《困學紀聞》卷一七引樓昉《太學策問》“夷門之植,植于燕云”為例指出,此一句式后世“不乏祖構”。而且,錢鐘書特別提到周振甫的意見:“不必矯揉牽強,說為倒裝。末‘于’與前兩‘于’異,即‘以’也。”[4]857周振甫所說,實際上與楊樹達的意見是相同的。錢鐘書并未就“以”“于”互訓的問題展開討論,而是將關注點落在了類似樂毅此語的句式倒裝現象的藝術價值上:
又有進者。此語逆承前數語;前數語皆先言齊(“大呂”、“故鼎”、“齊器”)而后言燕(“元英”、“歷室”、“寧臺”),此語煞尾,遂變而首言燕(“薊丘”)而次言齊(“汶篁”),錯綜流動,《毛詩》卷論《關雎 · 序》所謂“丫叉法”(chiasmus)也。聊復舉例,以博其趣。[4]858
在錢鐘書看來,“植于汶篁”對“薊丘之植”的“逆承”,形成了一種文辭表達的“錯綜流動”之美。而這種語言表達現象,在中國詩文中不乏其例。這里提到的“丫叉法”,錢鐘書在《管錐編》第一冊中談及《關雎》時已分析過,指詩文寫作中安排前后呼應時,“應承之次序與起呼之次序適反”的方法。如《毛詩序》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錢鐘書指出:“‘哀窈窕’句緊承‘不淫其色’句,‘思賢才’句遙承‘憂在進賢’句,此古人修詞一法。”[6]66正因為是“古人修詞一法”,錢鐘書同時舉了很多類似用例:《卷阿》“鳳凰鳴兮,于彼高岡;梧桐出兮,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以“菶菶”句接梧桐,以“雍雍”句應鳳凰;《史記 · 老子韓非列傳》“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以走、游、飛,倒換次序分別接獸、魚、鳥;謝靈運《登池上樓》“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云浮,棲川慚淵沉”,以“云浮”先接“飛鴻”,再以“淵沉”接“潛虬”;杜甫《大歷三年春自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以“明妃之曲”接“昭君”,以“高唐之夢”接“神女”。最后他提道:“其例不勝舉,別見《全上古文》卷論樂毅《獻書報燕王》。”[6]66
在錢鐘書看來,這種“丫叉法”最大的好處在于可以有效避免文字表達的呆板,而通過詞序交錯則可增強文辭回環跌宕的美感。緣此,錢鐘書在《管錐編》第三冊談到樂毅“薊丘之植,植于汶篁”一語時,與陳寅恪關注樂毅此語背后的家國興亡之感不同,他的興趣乃在此語以及類似用例的屬詞比事之技巧。所以,緊承其提到“丫叉法”之后,他梳理了大量詩文用例,“聊復舉例,以博其趣”。不過,錢鐘書不是為了展示知識的廣博,而是為了進一步指出,看似相類的“丫叉”用法中還存在具體表現上的細微差別。
錢鐘書舉例說明“丫叉”用法的差別,將之歸納為六種交錯類型②:
1.詞序交錯。《論語 · 鄉黨》“迅雷風烈必變”,《楚辭 · 九歌 · 東皇太一》“吉日兮辰良”。“‘風’、‘辰’近鄰‘雷’、‘日’,‘烈’、‘良’遙儷‘迅’、‘吉’,此本句中兩詞交錯者。”
2.句式交錯。《史記 · 平津侯主父列傳》載嚴安上書“馳車擊轂”,而《漢書 · 嚴朱吾丘等傳》下作“馳車轂擊”,“于義為長,非徒詞之錯也”。《漢書 · 王莽傳》下載“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不曰“灑鞭”而曰“鞭灑”,先以“鞭”緊承“赭鞭”,后以“灑”間接“桃湯”。
3.語句交錯。《列子 · 仲尼》篇:“務外游不務內觀,外游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備于物,游之不至也。”第二、三句于第一句順次申說,第四、五、六、七句于第二、三句逆序申說。王勃《采蓮賦》:“畏蓮色之如臉,愿衣香兮勝荷。”杜甫《有事于南郊賦》:“曾何以措其筋力與韜鈐,載其刀筆與喉舌。”王勃上句先物后人而下句先人后物,杜甫反是。李涉《岳陽別張祜》:“龍蛇縱在沒泥涂,長衢卻為駑駘設。”上句言才者失所,下句言得位者庸,錯互以成對照。
4.詩意表達中情思的交錯。韓偓《亂后卻至近甸有感》:“開中卻見屯邊卒,塞外翻聞有漢村。”“中”雖對“外”,而“塞”比鄰“邊”,“漢”回顧“中”,謂外御者入內,內屬者淪外,易地若交流然。李夢陽《艮岳篇》:“到眼黃蒿元玉砌,傷心錦纜有漁舟。”出語先道今衰、后道昔盛,對語先道昔盛、后道今衰,相形寄慨。韓愈《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幾山下作》:“旗穿曉日云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風物之山緊接云霞,軍旅之旗遙承劍戟。
5.謀篇布局中的交互成文。“并有擴而大之,不限于數句片段,而用以謀篇布局者。如諸葛亮《出師表》‘郭攸之、費祎,董允等’云云,承以‘臣本布衣’云云,繼承以‘受命以來……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承以‘至于斟酌損益……則攸之、祎、允之任也’,終承以‘不效則治臣之罪’,承以‘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長短奇偶錯落交遞,幾泯間架之跡,工于行布者也。”
6.隱藏的交錯。“至若《焦仲卿妻》……江淹《恨賦》……《文心雕龍 · 指瑕》……王維《送梓州李使君》……常建《送楚十少府》……胥到眼即辨。沈佺期(一作宋之問)《和洛州康士曹庭芝望月有懷》……同此結構而較詞隱脈潛。”
這六種用例,不僅可以見出古代詩文寫作中交錯成文之際所展現的語詞表達藝術,更可看出后來者的表達隨著文學創作的發展更趨復雜,甚至這種表達有意以一種近乎隱含的方式呈現出來。
由此可見,錢鐘書由“薊丘之植,植于汶篁”一語之解釋,關注到中國古代詩文創作中的句式倒裝現象,再由這些類似的語言現象,深挖“交錯成文”的創作傳統在中國詩文寫作中的不同表現類型及其藝術巧思之所在,這就是他所說的“連類舉似而掎摭焉,于賞析或有小補”[4]。應該說,錢鐘書以其充滿藝術發現的眼光,梳理清楚了各種“交錯成文”現象中作者在遣詞命意、謀篇布局乃至藝術構思上的巧妙之處,以及由此表現出的文辭之美。
就此而言,如果按照本文開頭提到的錢鐘書對考據的分類,陳寅恪的考據近于“有思想的考據”,錢鐘書的考據則更近于“詩眼文心”的考據,亦即在“連類舉似”中發現不同詩文“詩眼文心”之所在,由比較而見其遣詞命意之美。所以,錢鐘書考據工作的著力點,不在詩人意圖,也不在時代背景、文獻版本、語詞訓詁,而在詩人的某一藝術構思——包括字眼句法、遣詞命意等——在文學史中的因與革,既觀其“影響的焦慮”,又發現其藝術獨創的匠心。這實際上就是一種“詩胎”——宋人所說“奪胎換骨”之詩“胎”——的考據。
二、“詩胎”考據與詩藝“掎摭”
“詩胎”之“胎”,即“奪胎換骨”之“胎”,主要指前人已有的詩意構思。
“奪胎換骨”,出自惠洪《冷齋夜話》所引黃庭堅語:“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說文》曰:“胎,婦孕三月也。”段玉裁注:“《釋詁》曰:‘胎,始也。’此引伸之義。”《增韻》曰:“凡孕而未生,皆曰胎。”因此,所謂“詩胎”實際上就是一種詩意原型——某種現成的可以藝術再加工的詩思原材料,它可以是一種具有特殊美感表達的句法結構,一個美典,一個意象,一個母題,一種人生的情境,一種情感,等等。比如,黃庭堅《戲答王定國題門兩絕句》之二:“頗知歌舞無竅鑿,我心塊然如帝江。花里雄蜂雌蛺蝶,同時本自不作雙。”雄蜂、雌蝶“同時”卻不同類,帝江乃傳說中的神鳥,雖無七竅,面目混沌,但頗識歌舞。因此,黃庭堅此詩乃是以蜂、蝶之不同類,喻自己雖如帝江頗知歌舞,但早已過了歌舞少年的心境,“我心塊然”即心已木然,一如帝江之“無竅鑿”。對于后二句,任淵注引李商隱《柳枝》詞曰:“花房與蜜脾,蜂雄蛺蝶雌。同時不同類,那復更相思。”李詩即以蜂與蝶喻人生暌隔、相思之苦。錢鐘書在此基礎上,又考及李商隱《閨情》“紅露花房白蜜脾,黃蜂紫蝶兩參差”,指出這本是“漢人舊說”,并舉多例加以說明,如《左傳》僖公四年“風馬牛不相及”服虔注“牝牡相誘謂之風”,《列女傳 · 齊孤逐女傳》“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易林 · 大有之姤》“殊類異路,心不相慕”,等等。錢鐘書認為,李商隱詩取舊說為詩材,“一點換而精彩十倍”,然馮浩注李商隱詩,任淵注黃庭堅詩皆未能“推究本源”[2]9-10。《談藝錄》的這番考證,由黃庭堅到李商隱,一直追到《左傳》中的“風馬牛不相及”,實際正是在考探黃、李詩中“同時異類的暌隔”這樣一種人生情境的意義原型——一種“詩胎”。
值得注意的是,錢鐘書在上述考證中,不只是對“詩胎”作原始要終式的詳細追查,也是在考察此詩作何種再創造更能展現詩藝塑造之美。李商隱對“漢人舊說”的“點換”,才是錢鐘書“詩胎”考據的真正關注點。這與他對宋詩的認識有關。
前引黃庭堅的詩學思想中,相對易其辭而不易其意的“換骨”而言,“奪胎”法更看重在前人詩意基礎上的新變,“窺入其意”是發現舊有“詩胎”,“形容之”則是在此基礎上必需的藝術改造,亦即黃庭堅《答洪駒父書》中所說的“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因此,“奪胎換骨”的目的在于“以故為新”“點鐵成金”,而這正是宋詩的一個重要藝術特征。
在中國詩學史上,宋詩的地位一直不高。盡管有晚清“同光體”的極力提倡,但輕視宋詩的傾向在20世紀前半葉的學者中仍較常見。所以,在《談藝錄》中,錢鐘書即明確提出“詩分唐宋”,而且“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2]2,明確將唐詩、宋詩并提。這可以說是20世紀前半葉為宋詩做出的最有力的辯護。至寫作《宋詩選注》的年代,“筋骨思理”的問題不便多談,所以錢鐘書又從寫作技巧的角度再次談及宋詩的藝術獨特性:
整個說來,宋詩的成就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我們可以夸獎這個成就,但是無須夸張、夸大它……前代詩歌的造詣不但是傳給后人的產業,而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向后人挑釁,挑他們來比賽,試試他們能不能后來居上、打破記錄,或者異曲同工、別開生面……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這個好榜樣,宋代詩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有了這個好榜樣,他們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摹仿和依賴的惰性。瞧不起宋詩的明人說它學唐詩而不像唐詩,這句話并不錯,只是他們不懂這一點不像之處恰恰就是宋詩的創造性和價值所在……宋人能夠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長了,疏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險開荒,沒有去發現新天地。用宋代文學批評的術語來說,憑借了唐詩,宋代作者在詩歌的“小結裹”方面有了很多發明和成功的嘗試,譬如某一個意思寫得比唐人透徹,某一個字眼或句法從唐人那里來而比他們工穩……[7]
在批評宋詩具有“摹仿和依賴的惰性”的同時,錢鐘書也指出,正因為面對唐詩所提出的挑戰,宋人“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可以把一個意思“寫得比唐人透徹”,可以借用唐人的某個“字眼或句法”,但又可以寫得比唐人“工穩”。這實際上也就是宋詩注重“奪胎換骨”“以故為新”的創作取向。正是在對舊有“詩胎”的“點換”中,宋詩相對唐詩更注重“詩法”,藝術技巧也更趨精熟。
因此,錢鐘書的“詩胎”考據,就是要通過追查“詩胎”來考證詩人的“點換”技巧,發現其在詩歌“小結裹”方面的藝術經驗。譬如,補注黃庭堅詩是錢鐘書極為關注的一個題目,從大學時代研讀山谷詩任淵、青神二注,到歐洲游歷歸來“獲讀”冒疚齋《后山詩注補箋》后補訂山谷詩,所作訂補60條收入《談藝錄》后又多次再作補注、新補③,可見其心力。其中,考據“詩胎”正是一項重要的工作,茲舉一例。黃庭堅《演雅》詩:“絡緯何嘗省機織,布谷未應勤種播。”任淵注“但釋蟲鳥名”,至于引杜詩“布谷脆春種”無關詩意發明。錢鐘書首先補注了山谷詞意所本之“詩胎”最早者即《詩 · 大東》:“皖彼牽牛,不以服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至于《抱樸子》外篇《博喻》“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一節,《金樓子 · 立言》篇九下“全襲之,而更加鋪比”。錢鐘書由此指出,“山谷承人機杼,自成組織者,所謂脫胎換骨是也。”[2]6所謂“承人機杼”,乃是對現成“詩胎”的運用,而“自成組織”則是對舊有“詩胎”的藝術再創造。而要發現其“再創造”的秘密,則須考其“詩胎”,亦即考其詩意原型之所在。
但必須指出,錢鐘書的“詩胎”考據不同于文學批評中的“原型批評”。“原型批評”的重要奠基人諾思諾普 · 弗萊認為“原型”是“在文學中極為經常地復現的一種象征,通常是一種意象,足以被看成是人們的整體文學經驗的一個因素”④。從“極為經常地復現”、成為一種意義基型的“象征”而言,“詩胎”就是一種“原型”,無論是一種句法結構、一個典故、一個意象或一個文學母題,常常會以某種類型化的結構形態、程式化的言說方式,反復出現于不同的文本之中。但是,“原型批評”的落腳點是從“雜多”中見“統一”,即通過研究文學作品中反復出現的各種意象、敘事結構或人物類型,去發掘其背后某種普遍的心理經驗。而錢鐘書的“詩胎”考據,則是從“雜多”中歸納出一種基型,再由此基型反觀“雜多”自身的藝術特征或審美價值,亦即從辭章學的角度,在“連類舉似”大量“詩胎”中,“掎摭”其“奪胎換骨”的“點換”藝術,揭示其遣詞造句與詩意表現的藝術變化。鐘嶸《詩品序》曰:“辨彰清濁,掎摭利病。”“掎摭”就是批評、鑒賞。因此,“連類舉似而掎摭”,乃是通過對類似例證的分疏將語言現象舉例與藝術美感鑒賞融合在一起,是舉證分析,同時也是詩歌鑒賞。
這種“詩胎”考據的方法,在《宋詩選注》與《管錐編》中都有大量運用,《宋詩選注》尤為明顯,幾乎貫穿全書,如第一篇柳開《塞上》,錢鐘書注后二句“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云看”曰:
三四兩句的句調可參看唐人李益(一作嚴維)《從軍北征》“磧里征人三百萬,一時回首月中看”。[7]1-2
最后一篇蕭立之《偶成》,錢鐘書注后二句“城中豈識農耕好,卻恨慳晴放紙鳶”曰:
城里人不知田家盼望下雨,只恨天公不做美,不好放風箏。參看唐人李約《觀祈雨》:“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曹勛《松隱集》卷十《和次子耜“久雨”韻》第二首:“第憂沉稼穡,寧問浸芙蓉”;陸游《劍南詩稿》卷十五《秋雨排悶十韻》:“未憂荒楚菊,直恐敗吳粳”……也都寫出了對天雨天晴的兩種立場。劉克莊《朝天子》:“宿雨頻飄灑,歡喜西疇耕者……老學種花兼學稼,心兩掛:這幾樹海棠休也”;林希逸……又要寫同時抱有兩種態度的矛盾心理,但是語氣里流露出傾向性。[7]292-293
至如宋詩中的名句,考據“詩胎”更是明顯,對陸游名句“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錢鐘書先后舉證王維《藍田山石門精舍》“遙愛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忽與前山通”,柳宗元《袁家渴記》“舟行若窮,忽又無際”,盧綸《送吉中孚歸楚州》“暗入無路山,心知有花處”,耿《仙山行》“花落尋無徑,雞鳴覺有村”,周暉《清波雜志》卷中載強彥文詩“遠山初見疑無路,曲徑徐行漸有村”,以及王安石《江上》“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指出這些作品都寫到了“疑無路”之際的某種轉機,但“要到陸游這一聯才把它寫得‘題無剩義’”[7]176-177,即不僅可見一種轉折之際的跌宕起伏,更有一種人生寓意、詩意的回環。對葉紹翁《游園不值》“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一聯,錢鐘書認為:“這是古今傳誦的詩,其實脫胎于陸游《劍南詩稿》卷十八《馬上作》:‘平橋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靄浮。楊柳不遮春色斷,一枝紅杏出墻頭。’不過第三句寫的比陸游的新警。”緊接著又舉張良臣《偶題》“一段好春藏不盡,粉墻斜露杏花梢”,認為“第三句有閑字填襯,也不及葉紹翁的來得具體”。此外,他又列舉唐人溫庭筠、吳融、李建勛等類似的句子,指出這些句子要么和其他景色摻雜排列,要么沒有放在一篇中讓人印象最深刻的位置,都不及葉紹翁寫得醒豁[7]266。
至于《管錐編》,“詩胎”考據的例子同樣俯拾滿眼。
例如,古來送別詩之祖《燕燕》中的“瞻望勿及,佇立以泣”一句,錢鐘書考證了大量祖構此句的例子,通過比較顯現各家寫作藝術之優劣。許剴《彥周詩話》引述了張先《虞美人》“眼力不如人,逮上溪橋去”以及蘇軾《與子由》“登高回首坡瓏隔,惟見烏帽出復沒”。錢鐘書指出:張先詞原作“眼力不知人遠,上江橋”,許剴雖誤引,然“如”字含蓄自然,實勝“知”字,幾似人病增妍、珠愁轉瑩;相比邵謁《望行人》“登樓恐不高,及高君已遠”,張先《南鄉子》“春水一篙殘照闊,遙遙,有個多情立畫橋”、《一叢花令》“嘶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等,“許氏所標舉者語最高簡”[6]78。不僅如此,他又舉證朱超道《別席中兵》、王維《齊州送祖三》《觀別者》、王操《送人南歸》、梅堯臣《依韻和子聰見寄》、王安石《相送行》以及何景明《河水曲》等諸多遠紹《燕燕》、“與張詞、蘇詩謀篇尤類”的例證,指出梅、王詩“說破著跡”,而宋左緯《送許白丞至白沙,為舟人所誤,詩以寄之》“水邊人獨自,沙上月黃昏”,“庶幾后來居上”[6]79。
再如,對《詩 · 陟岵》中“遠役者思親,因想親亦方思己之口吻”的考證,錢鐘書舉了大量“機杼相同,波瀾莫二”[6]113的例子,如:
徐干《室思》“想君時見思”;高適《除夕》“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韓愈《與孟東野書》“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于吾也”;劉得仁《月夜寄同志》“支頤不語相思坐,料得君心似我心”;王建《行見月》“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白居易《初與元九別,后忽夢見之,及寤而書忽至》“以我今朝意,想君此夜心”,又《江樓月》“誰料江邊懷我夜,正當池畔思君時”,又《望驛臺》“兩處春光同日盡,居人思客客思家”,又《至夜思親》“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游人”,又《客上守歲在柳家莊》“故園今夜里,應念未歸人”;孫光憲《生查子》“想到玉人情,也合思量我”;韋莊《浣溪紗》“夜夜相思更漏殘,傷心明月憑闌干,想君思我錦衾寒”;歐陽修《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遙知湖上一樽酒,能憶天涯萬里人”;張炎《水龍吟 · 寄袁竹初》“待相逢說與相思,想亦在相思里”;龔自珍《己亥雜詩》“一燈古店齋心坐,不是云屏夢里人”。[6]113
接著又以古樂府《西洲曲》為例,指出《陟岵》的這種寫法,不僅用于遠行思親,更擴及男女相思之例。在錢鐘書看來,這些詩作均屬“據實構虛,以想象與懷憶融會而造詩境,無異乎《陟岵》焉”。而且,后世寫作中更由“我思人亦如人思我”,變化為“我見人亦如人之見我”這樣的寫作手法:“分身以自省,推己以忖他;寫心行則我思人乃想人必思我,如《陟帖》是,寫景狀則我視人乃見人適視我,例亦不乏。”[6]114故緊接其后,錢鐘書又以王維《山中寄諸弟》《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以及包融《送國子張主簿》等詩為例指出,金圣嘆評《西廂記》揭示出的“倩女離魂法”正是上述寫法的繼承。此外他又指出,辭章中“寫心行之往而返、遠而復者,或在此地想異地之思此地,若《陟岵》諸篇;或在今日想他日之憶今日,如溫庭筠《題懷貞池舊游》……一施于空間,一施于時間,機杼不二也”[6]116。
值得注意的是,在隨后的討論中,錢鐘書又列舉杜牧《南陵道中》、楊萬里《誠齋集》卷九《登多稼亭》之二、范成大《望海亭》、辛棄疾《瑞鶴仙 · 南澗雙溪樓》、翁孟寅《摸魚兒》、方回《桐江續集》卷八《立夏明日行園無客》之四、鐘惺《隱秀軒集》黃集卷一《五月七日吳伯霖要集秦淮水榭》、厲鶚《樊榭山房續集》卷四《歸舟江行望燕子磯》、《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四卓奇圖絕句、羅聘《香葉草堂詩存 · 三詔洞前取徑往云然庵》、張問陶《船山詩草》卷一四《夢中》、錢衎石《閩游集》卷一《望金山》、江湜《服敔堂詩錄》卷三《歸里數月后作閩游》之十、王國維《苕華詞 · 浣溪紗》等多個詩例,認為這些作品“詞意奇逸”,篇幅雖不及阮元《揅經室四集》卷一一《望遠鏡中看月歌》、陳澧《東塾先生遺詩 · 擬月中人望地球歌》、丘逢甲《嶺云海日樓詩鈔》卷七《七洲洋看月歌》等詩,但其藝術水平卻是“以少許勝多許”,且黃公度《人境廬詩草》卷四《海行雜感》第七首“亦遜其警拔”[6]115。從這里,鮮明可見錢鐘書“詩胎”考據中的“掎摭”眼光。
凡此,可見錢鐘書由“詩胎”考據而見詞旨再造之美的詩學考據方法,“連類舉似而掎摭”之中既有一種詩學創造的智慧,更有一份藝術發現的巧心。
三、“易”象“詩”象之別與“詩胎”考據及“詩史”批判
上文提到,錢鐘書的“詩胎”考據不同于“原型批評”,很重要的一點即在于“原型批評”關注的是某種定型化的“意象”背后所體現的普遍的心理經驗,而“詩胎”考據追問的是這種看似定型的“意象”在此后詩人筆下的藝術新變。這與錢鐘書對文學意象特殊性的認識有關。他在談及“易”象與“詩”象之別時提道:
《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語本《淮南子 · 說山訓》)。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變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戀著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見月忽指、獲魚兔而棄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謂也。詞章之擬象比喻則異乎是。詩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無詩矣,變象易言,是別為一詩甚且非詩矣。故《易》之擬象不即,指示意義之符(sign)也;《詩》之比喻不離,體示意義之跡(icon)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離者勿容更張。[6]12
“易”之象實為講明某種道理的事象,道理是普遍的、相對穩定的,而作為講說此道理的載體則可以更換。譬如,同樣表達對光陰流逝的感嘆,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論語 · 子罕》有“逝川”之象:“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莊子 · 知北游》有“白駒過隙”之象:“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曹操《短歌行》曰“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李煜《浪淘沙》則以“落花”為喻:“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所以,“易”象乃是一種指示意義的符號。而且,在錢鐘書看來,道理離不開言說,我們對言說內容的理解建立在語言或語詞理解的基礎上,而語詞既有其理解的普遍性,也存在當下的特殊性,因此一意數喻有助于以言說的多元消弭理解的固化或錯誤。“古之哲人有鑒于詞之足以害意也,或乃以言破言,即用文字消除文字之執,每下一語,輒反其語以破之。”[6]13
然而“詩”象則不同。如果說“易”象是一個可置換的概念,“詩”象則是一個獨立自足的藝術世界。也就是說,詩是一種借助語言塑造意象的藝術,即便蘊含的思想意涵相類,不同的語言表達所塑造的“詩”象本身卻是獨特的“這一個”。韋莊說“但見時光流似箭,豈知天道曲如弓”,雖然也感嘆時光流逝之迅疾,但更強調其“曲”行的一面,從而照應人生的坎坷,這與曹操的朝露之嘆、李煜的落花之感是不同的。所以,在錢鐘書看來,每一個“詩”象都是“依象而成言”的“這一個”,其中固然有意義的體現,但其關注點不在對意義的指示,而在其語言構造本身的美感。因此,每一個“詩”象都是一個獨特的藝術結構,“變象易言,是別為一詩甚且非詩矣”。
在錢鐘書看來,詩乃是一種藝術,而藝術形式、藝術表達本身有著不可忽略的規則:“詩者,藝也。藝有規則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為詩,而未必成詩也。藝之成敗,系乎才也……雖然,有學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學者也。大匠之巧,焉能不出于規矩哉。”[2]40詩人融匯才、學入詩,且做到“深藏若虛”,離不開對“詩藝”技巧的琢磨和提煉⑤。所以,他講宋詩相比唐詩而言,雖乏大判斷,但正因為宋人多注意“詩藝”層面的“小結裹”,故而宋詩能有其獨到價值[7]11。《談藝錄》中還特別提到詩的藝術結構問題:
詩者,藝之取資于文字者也。文字有聲,詩得之為調為律;文字有義,詩得之以侔色揣稱者,為象為藻,以寫心宣志者,為意為情。及夫調有弦外之遺音,語有言表之余味,則神韻盎然出焉。[2]42
這里,錢鐘書將詩之創作析分為“語言、形象、情感、意蘊”四個層面,這四層的關系既可視為一首好詩創作過程的層深結構,亦可看作才質不同的詩人的分野——詩人因藝術修養不同在創作中融涵這四者的水平亦不同。所以,正是從詩自身的藝術特性著眼,錢鐘書的“詩胎”考據特別注重“連類舉似而掎摭”,在比較中見其詩藝得失與藝術高下。
值得注意的是,強調“易”象與“詩”象不同,即是強調詩與哲學有別。甚或可以說,錢鐘書此說乃是反對以一種追求“普遍性”的哲學思維來看待文學。這背后,有其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思維大于形象”這一思潮的反撥,他在《管錐編》中提道:
是故《易》之象,義理寄宿之蘧廬也,樂餌以止過客之旅亭也;《詩》之喻,文情歸宿之菟裘也,哭斯歌斯、聚骨肉之家室也。倘視《易》之象如《詩》之喻,未嘗不可摭我春華,拾其芳草……哲人得意而欲忘之言、得言而欲忘之象,適供詞人之尋章摘句、含英咀華,正若此矣。茍反其道,以《詩》之喻視同《易》之象……以深文周納為深識底蘊,索隱附會,穿鑿羅織,匡鼎之說詩,幾乎同管輅之射覆,絳帳之授經,甚且成烏臺之勘案。自漢以還,有以此專門名家者。[6]14-15
正因為每一個獨特的“詩”象往往都有其感性面相,都與詩人的現實生活有聯系,所以一旦過于深文周納“詩”象中的現實思想指向,則難免造成“烏臺之勘案”。而且,在具體的文學創作中,即便面對同一時代背景,也會有作者感悟之不同、藝術心靈表現之多樣。這一點,錢鐘書在《中國文學小史序論》中就特別提及:
當因文以知世,不宜因世以求文……每見文學史作者,固執社會造因之說,以普通之社會狀況解釋特殊之文學風格,以某種文學之產生胥由于某時某地;其臆必目論,固置不言,而同時同地,往往有風格絕然不同之文學,使造因止于時地而已,則將何以解此歧出耶?……鄙見以為不如以文學之風格、思想之型式,與夫政治制度、社會狀態,皆視為某種時代精神之表現,平行四出,異轍同源,彼此之間,初無先因后果之連誼,而相為映射闡發,正可由以窺見此種時代精神之特征;較之社會造因之說,似稍謹慎(略見拙作《旁觀者》),又有進者,時勢身世不過能解釋何以而有某種作品,至某種作品之何以為佳為劣,則非時勢身世之所能解答,作品之發生,與作品之價值,絕然兩事;感遇發為文章,才力定其造詣,文章之造作,系乎感遇也,文章之造詣,不系乎感遇也,此所以同一題目之作而美惡時復相徑庭也。[8]
錢鐘書自始至終對“詩史釋證”多有批評,典型地體現在《宋詩選注 · 序》中對“詩史”說的批評⑥。錢鐘書固然反對文學研究偏向史實考證以致忽略自身的藝術問題,但其《宋詩選注》卻有不少“以史證詩”的例子。因此,理解錢鐘書所說的“‘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不應忽略這句話的特殊歷史背景⑦,以及錢鐘書對當時文學研究所面臨問題的考量。
注釋:
① 詳情見張文江《營造巴比塔的智者:錢鐘書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3頁、112―113頁。
② 見錢鐘書《管錐編》第3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858―860頁。
③ 詳見錢鐘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23頁、314―344、346頁。
④ 見諾思諾普 · 弗萊《批評的剖析》(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頁。
⑤ 如《談藝錄》批評黃公度詩和往昔“學人之詩”以及贊賞靜安35歲之后的詩,均可見一斑。見錢鐘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3、26頁。
⑥ 參見拙文《詩史釋證與審美想象的歷史還原——戴鴻森〈宋詩選注〉補訂讀后》,載胡曉明主編《中國文論的思想與智慧(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四十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470頁。
⑦ 楊絳曾回憶道:“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并未引起注意。鐘書1956年完成的《宋詩選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來了個‘雙反’,隨后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鐘書的《宋詩選注》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見楊絳《我們仨》(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