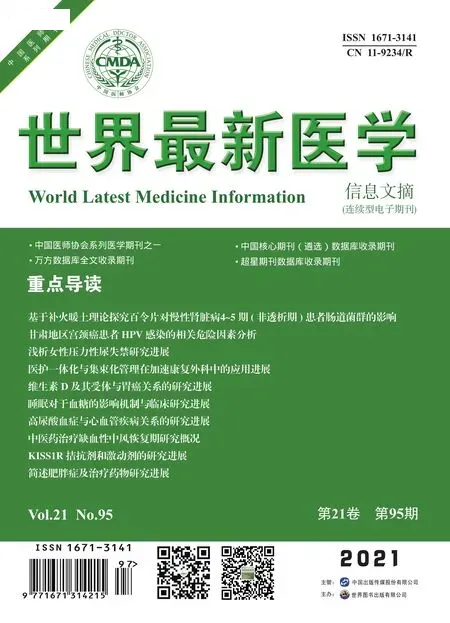主觀認知功能下降的生物標記物研究進展
董雅勤
(安徽醫科大學附屬宿州醫院,安徽 合肥 235000)
0 引言
主觀認知功能下降(SCD) 的概念最早是在1982 年由Reisberg 等[1]提出,但其相關術語不統一,包括主訴記憶障礙(SMC)、主觀記憶衰退(SMD)、主觀認知障礙(SCI)、輕度認知障礙前期(Pre-MCI)等,由于缺乏通用標準,早期對SCD 的研究受到了限制。直到2014 年Jessen[2]明確了SCD 的診斷框架:與以前正常狀態相比,自我感知認知能力持續下降,但在標準神經心理測試中表現正常。它與認知測試的表現無關,且認知是指任何認知領域,不單單僅指記憶,且需排除精神、神經系統疾病、藥物及物質濫用等疾病、意外以及急性事件引起的認知功能短暫下降等原因。雖然SCD 與許多疾病相關,但SCD 的患者進展為MCI 的風險是健康對照組的4.5 倍,而最終發展為AD 的風險增加了6.5 倍[3],所以對SCD 的研究可為減緩或逆轉AD 的病情提供可能。
1 生物標志物
1.1 腦脊液生物標記物
腦脊液(CSF)可檢測的生物標記物為Aβ42,t-tau 蛋白和p-tau 蛋白濃度等,有研究表明[4]Aβ 淀粉樣蛋白蓄積的生物標志物首先變得異常,神經損傷和神經退行性變的生物標志物隨后會異常,并在MCI 和AD 的臨床階段與認知表現保持密切關系;Rolstad[5]發現Aβ42 的水平與語義和工作記憶有關,而t-tau 影響所有認知領域,但最重要的是情景記憶和視覺空間功能,對SCD 患者隨訪兩年發現有很大比例的患者出現速度,執行功能的下降,而這與腦脊液t-tau 值的變化有關,然而在這一人群中的認知能力測試結果與Aβ 蛋白無明顯相關;van Harten 等[6]研究得出Aβ42 是SCD 進展為MCI 或AD的最強預測因子,而一系列病理事件的級聯始于Aβ42 蛋白的沉積,而tau 蛋白的神經元變性和磷酸化過多是下游事件,更接近于AD 的臨床表現,Jessen 等[7]研究提出SCD 組CSF的Aβ42 低于健康對照組,而tau 蛋白的濃度在兩組之間沒有顯著差異。這和van Harten 的研究結論相似,即Aβ42 沉積的發生要明顯早于tau 蛋白的神經變性;Soldan 等[15]將222名認知正常的成年人按照CSF 的Aβ42 和tau 濃度分為四組,分別為高Aβ 和低tau 組,低Aβ 和低tau 組,低Aβ 和高tau組以及高Aβ 和高tau 組,隨訪后發現tau 高水平合并Aβ42低水平的人群認知下降幅度最大;而Dumurgier 等[16]也通過研究提出CSF tau 高濃度和Aβ42 的低濃度組合比單獨任何一種生物標志物與認知結果的相關性更強;也有研究提出利用腦脊液異常蛋白比率來預測SCD 認知功能的改變,Steffen等[17]在一項為期3 年的隨訪調查中發現在異常的CSF Aβ42/tau 組中進展為MCI 或AD 的占60.7%,而正常比率的人群中僅有20.4%發展為癡呆,提示CSF 的Aβ42/tau 的比值可以預測SCD 的臨床進展,一些研究得出結論[8],CSF 生物標志物在SCD 患者與健康的老年人之間沒有顯著差異。但綜上所述,具有異常腦脊液生物標志物的SCD 患者在疾病發展過程中更容易出現認知障礙。
1.2 神經影像生物標志物
1.2.1 結構核磁共振
結構核磁共振成像(sMRI)主要是通過測量大腦皮層的體積和厚度來衡量大腦形態的變化的一種影像技術。AD 的sMRI 成像主要表現為全腦的萎縮,特別是海馬、海馬旁回和顳葉新皮質區,而AD 的認知障礙程度與腦萎縮率有相關性[9],研究表明[10]通過sMRI 的測量可以有效區分AD,MCI和正常人群,而部分SCD 患者作為AD 超早期人群是否也已經存在腦形態的變化近年來正逐漸被人們所研究。Saykin[11]研究發現MCI 組和SCD 組都提示類似雙側顳葉內側,額葉的灰質(GM)萎縮,且MCI 組的萎縮程度大于SCD 組,Dore[12]報道過類似的研究結果,他提出額葉和顳葉的萎縮程度和認知下降有關,隨著疾病的進展,顳葉萎縮變得更廣泛。Meiberth等[13]對41 名SCD 及69 名健康者進行結構MRI 成像發現,在與AD 相關的腦區域,即雙側內嗅區和海馬旁回中,SCD 組的皮層厚度明顯比對照組減少,Ryu[14]發現SCD 患者的內嗅皮質體積比對照組低,但海馬體積在兩者之間沒有明顯差異,這可能提示內嗅區的變化早于海馬,此外Whitehouse[15]曾在1982 年提出AD 與基底前腦膽堿能神經元細胞的丟失有關,而Scheef 等[16]在最近的研究表明SCD 患者出現膽堿能基底前腦核(chBFN)的體積萎縮,說明基底前腦膽堿能神經元細胞在SCD 階段已經發生改變;還有研究表明[17],SCD 組和健康組相比在大腦其他區域如梭狀回、后扣帶回、下頂葉皮質、杏仁核等有明顯萎縮。越來越多神經影像學證據顯示患有SCD 的受試者顯示出與AD 相關的病理學證據,這為我們客觀識別 AD 的臨床前期提供可能。
1.2.2 彌散張量成像
彌散張量成像(DTI)是一種無創定量MRI 技術,可應用于檢測白質(WM)細微結構的變化,DTI 的參數描述了擴散張量的不同方面,分數各向異性(FA)和平均擴散率(MD)通過檢測水在組織中的擴散來描述WM 的結構完整性,軸向擴散率(A×D)和徑向擴散率(DR)可以提供軸突變性和脫髓鞘的信息,有研究指出與正常對照組相比,SCD 患者白質結構變化比灰質明顯[18],提示WM 的病變可能早于灰質。Selnes等[19]提出在SCD 和MCI 人群中DTI 比CSF 標記物能更好預測AD 顳葉內側萎縮,與對照組相比,SCD 患者的徑向擴散率(DR)和平均擴散率(MD)的變化具有統計學意義。Luo等[20]研究發現與MCI 組相比,SCD 患者的WM 損傷的解剖結構與其相似,但SCD 患者的損傷較輕,具有WM 微結構破壞的個體在一般認知和記憶功能測試中表現較差,提示WM的微結構損傷可能是整體認知和記憶功能的重要預測指標,Ohlhauser 及同事[21]指出SCD 個體的WM 的結構完整性明顯低于健康對照組,且SCD 患者的執行功能與白質的完整性相關。眾多研究表明DTI 指標可能是早期AD 潛在敏感的生物標記。然而Kiuchi 等人[22]發現在DTI 中NC 組和SCD 組之間沒有明顯差異,這些研究結果的不同可能與樣本量過小及SCD 人群的非特異性有關,接下來仍需增加樣本量及進一步的縱向研究來確定DTI 指標和認知功能隨疾病發展的變化,為早期AD 的神經病理機制提供更全面的了解。
1.2.3 功能磁共振成像
AD 患者的腦形態變化通常是神經變性級聯反應中的晚期事件,因此功能成像檢測到的變化可能先于灰質萎縮和白質變性,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是利用神經細胞活動時引起的局部腦血流中的血氧動力學改變現象來進行成像,觀察局部腦活動,其包括任務態磁共振成像和靜息態磁共振成像(rsfMRI),有研究表明在臨床前AD 的早期,靜息態磁共振可能比基于任務的磁共振成像更為敏感[23],Raichle 等人[24]首先提出默認活動網絡(DMN)的概念,DMN 由幾個區域組成,包括后扣帶回皮層、后外側頂葉皮層、內側顳葉和海馬,在全腦信息整合及與其他腦區的連接中發揮重要作用。大腦網絡的功能連接完整性與保持老年認知能力密切相關;Wang 等人[25]指出CSF 異常水平的Aβ 42 蛋白和的Tau 蛋白與DMN 功能連接的減少有關,最近的研究表明[26]局部β-淀粉樣蛋白沉積與額葉和頂葉的功能連接有關,Tau 蛋白與額葉,頂葉,枕葉,顳葉和小腦區域的功能連接有關。也有學者選擇低頻波動幅度(ALFF)作為rs-fMRI 的成像指標,因為它可以捕獲血氧水平依賴性(BOLD)信號中自發性波動的區域強度并反映葡萄糖的區域代謝水平,Sun 等[27]通過rs-fMRI 和sMRI 測量在SCD 人群中的ALFF 和灰質體積發現和對照組相比,SCD 患者在雙側下頂葉,右下枕中回和右顳回以及右小腦后葉的ALFF 更高,而灰質體積無明顯差異,這一結果支持了SCD 患者在腦組織結構性萎縮之前可能已發生功能性改變的說法,而與sMRI 成像相比,rs-fMRI 成像可能是檢測臨床前AD 患者腦部改變更靈敏的成像技術。Rodda 等[28]通過基于任務的fMRI 成像發現和對照組比較,SCD 組的內側顳葉(MTL)活動增強,其強度與記憶任務性能相關,而MTL 是AD 發生組織病理學改變的最初部位,MTL 在AD 人群中顯示活動減弱,可能提示在SCD 階段存在代償作用,隨著疾病進展,代償作用逐漸減弱,最終導致MTL 的活動減弱,Rodda[29]的另一項研究表明SCD 組在左內側顳葉,雙側丘腦,后扣帶回和尾狀核的活動增強,與AD 患者相關腦區的激活減少的模式類似,進一步證實在SCD 人群中存在代償功能。
1.2.4 氟代脫氧葡萄糖(FDG)PET 成像
FDG-PET 顯像可以反映不同腦區域的葡萄糖代謝情況,AD 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特定大腦區域的葡萄糖代謝速率嚴重降低,且降低的程度與癥狀嚴重程度相關[30]。Mosconi 等[31]研究得出SCD 患者在海馬旁回(PHG),頂顳葉和額葉下皮質,梭狀回和丘腦區的葡萄糖代謝率明顯降低,以內嗅皮層為主的PHG 區的代謝低下是SCD 狀態最顯著的預測指標,同樣也有研究表明[32]顳葉內側(MTL)的代謝下降和SCD 的嚴重程度具有相關性,提示MTL 的代謝下降可能是臨床前AD 認知變化的標志,Scheff 等[33]發現和對照組相比,SCD 組在右楔前葉顯示低代謝,在右顳葉內側顯示高代謝,隨訪發現SCD組的縱向記憶力下降與右楔前葉的葡萄糖代謝降低相關。這表明在SCD 階段已經發生腦區域的代謝異常,縱向記憶表現下降與低代謝的相關性進一步支持了SCD 作為AD 的最早表現的說法。眾多研究表明,在SCD 患者中出現葡萄糖代謝降低可能會增加罹患AD 的風險,這對于我們早期發現并提前進行干預提供可能。
1.3 血液生物標志物
由于腦脊液提取的有創性及影像學的昂貴性,近年有人將目光放到血液生物標志物上來,Pratishtha 等[34]通過比較PET 成像(18F-Florbetaben 作為示蹤劑) 和血漿Aβ 評估腦Aβ 沉積的結果發現在SCD 人群中,與PET 成像提示Aβ-組對比,Aβ+組的血漿Aβ42/Aβ40 比率明顯較低,提示血漿Aβ比值是腦Aβ 沉積的潛在生物標志物,可作為臨床前AD 的潛在生物標志物,Verberk 等[35]在一項隨訪研究中通過對241名患有SCD 的受試者進行腦脊液和血液的比對分析發現腦脊液Aβ42 降低與認知相關的所有領域的急劇下降有關,而血漿Aβ42/Aβ40 降低與記憶力,注意力和執行功能下降的速度加快有關,證明血漿淀粉樣蛋白和認知功能減退的關聯與腦脊液淀粉樣蛋白的關聯相似,提示在認知正常的個體中,血液中的淀粉樣蛋白濃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在進行的AD的病理變化,腦脊液tTau 和pTau181 與認知領域的多項測試相關,但未發現血漿tau 與認知能力下降速率的關系,tau 蛋白除了在腦組織中表達外,在唾液腺和腎臟組織中也有少量表達,而血漿中tau 蛋白的半衰期也明顯短于腦脊液中半衰期[36],這可能是導致血漿與腦脊液相關蛋白的低相關性的原因,未來需要進一步開發高度靈敏的檢測技術來支持血液生物標記物的研究。
2 SCD 的研究前景與展望
綜上所述,生物標記物的檢測對SCD 的進展有一定的預測作用,而有效的識別高危人群可為AD 的早期干預提供更寬裕的時間窗,但對于臨床而言,影像的輻射性及高成本和腦脊液采樣的侵入性在人群中不易被接受及推廣,而近幾年新興的血液檢測因為操作簡單,費用低,并使患者和醫護人員更容易監測而更有可能轉化為常規臨床應用,但血液中的腦源性分子濃度要比腦脊液中低得多,所以開發更加敏感的血液檢測技術及新一代生物標志物成為未來的發展方向,目前對SCD 的研究還處于初期階段,仍需要通過在更大的樣本量和長時間的縱向研究中進行更多的驗證工作,以往的研究多是針對SCD 人群單一領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腦脊液,神經影像學,遺傳學,組織病理學及血液檢測等多學科檢測手段的聯合研究也將是未來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