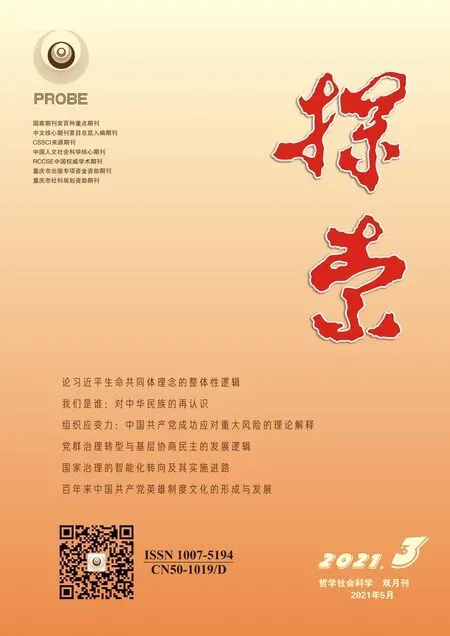中華民族的共性與特性
——時空關聯的視角
郭臺輝
(云南大學 民族政治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以具體的、歷史的、發展變化的方式在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同時展開。人們在生產生活中長期互動互助,社會關系逐漸凝結成以共同體為單位的穩定結構。穩定的共同體最初表現在血緣與地緣關系的社會生活層面,逐漸沉淀成更為深層的文化基因與道德規范,并上升到跨地域、更有力量的政治觀念、制度與行動。人類需要并棲息于多層多樣的共同體,而政治共同體是所有其他共同體形式得以穩定與延續的根本保障。共同體在具體時空中展開,而作為共同體成員的人們受時間與空間雙重意識及其之間關系的限制。其中,時間意識讓人們真實感知共同體及其外界客觀事物存在的各種變化,包括不變、漸變、突變、周期變與線性變,而空間意識讓人們感知共同體與外界存在物以及之間互動關系的物理占位與方位。時間與空間的雙重意識規定了“我是誰”和“我們是誰”這些關于共同體歸屬身份的元問題,也限定了人們對共同體形式的認知與想象。沒有時間意識,人們不知道自身所歸屬的共同體從何而來、向何處去;沒有空間意識,共同體及其成員迷失具體方位和變化方向。換言之,共同體意識、生存危機意識與歸屬意識決定于時間與空間雙重意識。
本文以中華民族為分析單位與研究對象,是基于上述關于共同體及其時空關聯的認知框架。一方面,中華民族是多重社會關系空間擴展和長期積淀的結果,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文化、道德規范和政治等諸多關系相互疊加,形成最為重要的政治共同體。另一方面,由于社會關系出現的時間不同、空間的占位也不同,以至于不同時期與不同地方的人們有不同的時間意識與空間意識,形成不同程度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因此,中華民族作為一種政治共同體觀念表現出來的具象非常復雜,而作為觀念表達的概念,其內涵與外延也無法得以本質性地清晰限定。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民族有必要置于特定的時空關系進行考察。歷史時間與世界空間交織互嵌為一個“時空體”結構,在此進程中,中華民族的形成契機與歷史遺產及其復雜性程度對空間維度的存在狀態與運行方式產生重要影響。本文把中華民族之樹置于世界歷史進程的民族之林進行形成過程的宏觀比較,以此定位中華民族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共性與特性。具體分為三個部分展開:一是時空定位,把握中華民族形成的時間意識和空間意識及其關聯;二是把中華民族視為國族,并對照西方現代早期形成的民族國家,尋找國族形成的共同特征;三是進一步探索中華民族的獨有特征,把這種獨特性轉化為文化基因、經濟優勢與政治自信。這種獨特性不僅是中華民族從傳統文化民族轉變為現代政治民族的特殊路徑,并且是中華民族崛起、復興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成功密碼。
1 中華民族的時空定位
合理全面地理解中華民族,首先需要進行時空關聯的客觀定位。話語分析是理解觀念的有效途徑,中華民族作為一種完整而獨立的觀念單元,其表述的命題很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崛起”這些政治命題耳熟能詳,但命題表達的語義及其適用的語境卻存在很大差異,需要立足于時空關聯進一步澄清。
其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對中華民族進行性質定位,可以分為三方面來理解。其一,中華民族是一種共同體單位。中國人可以因地域、習俗、語言、文化禮儀等諸多共同體來識別和界定,但中華民族作為一種超血緣、跨地域、超階層地位的政治共同體,其內在是高度同質化的共同體成員身份。在如今以民族國家為單位構成的世界體系,作為政治共同體的中華民族是最大范圍的、世界公認的實體性存在。其二,中華民族是一種政治和文化意識層次的觀念單元。從觀念本體論和意識實在論來說,中華民族是表達心理認同和情感歸屬的觀念性存在,制度形態與行動實踐都是觀念的具體落實。觀念單元作為整體存在,可以通過象征符號體系來表達,但無法化約成更小的組成元素,其性質和特征也無法用更次一級的觀念單元來描述。中華民族作為一種統攝性的觀念原則,把內部所有同質性的文化和文明元素匯集在一起構成一個獨立的、完整的觀念單元,唯此才能與現代國家觀念相匹配,并結合而成一個公認的政治共同體即民族國家,躋身于世界民族國家體系。其三,中華民族成為中國人最重要的共同體意識。20世紀的現代世界因民族國家之間軍事沖突與經濟競爭,招致大規模的戰爭及戰爭威脅,使現代世界充滿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宗教問題、種族問題與移民問題對民族國家體系的沖擊使人類面臨身份認同的結構性危機。中華民族成為中國人最強大、最可靠的政治共同體,中國人唯有團結并凝聚于此,從中落定身份認同感與安全感才能延續安定美好生活。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表達一種時間向度的預設,把過去的集體記憶、當下的生活體驗、未來的想象與期待緊密關聯在一起。“復興”是一種內生性演化邏輯和縱向比較意識,意味著中華文明史上曾有過偉大而輝煌的鼎盛時期,只是后來進入腐化與衰敗的歷史時期,而今萌生一種再生的渴望,強烈要求擺脫落后民族被動挨打的局面,重返集體記憶中的那種偉大時刻,并視之為一項作為統領性原則的政治工程。在這種預設中,興盛—衰敗—重建—復興的時間邏輯采信循環史觀,表達一種自我定義和自我強化的歷史周期意識,歷史過程中的具體人物與事件合乎邏輯地進入物質化和符號化的象征體系,再現由盛而衰的退化史與由衰而盛的進化史兩種歷史軌跡。中國新生的國家政權經過70余年建設,在經濟、政治、軍事等各領域取得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讓當下中國人體驗到積極奮進的團結與信心,感受到正處于復興的“偉大時代“,或者“偉大時刻”即將來臨,進而把中華民族復興的宏偉藍圖納入自然時間刻度上可見的未來想象。
相比較而言,“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一種空間結構的向度,以宏觀比較的視野表明中華民族、世界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共生關系,至少蘊含三層含義。其一,人類是以民族共同體形式聚居,而世界空間是以民族共同體為構成單位和地域范圍,諸民族不分大小、貧富與強弱,都躋身于當代世界這個由民族國家體系構成的共生空間,各民族的存在形態和運行特征基本相似,而中華民族不僅不能獨立于這個共生空間之外,還必須為共同繁榮與發展而積極參與全球事務。其二,由諸民族構成的現代世界形成一片森林,而民族之樹木必然有共同的成長環境,比如土壤、陽光雨露與氣候環境,遑論臨近的樹木之間盤根錯節、齒唇相依。森林需要包容性強,允許生物多樣性,樹木存在生命周期和成長過程的差異性以及基本形態的個體性,由此而形成的森林才有生命力、物種多樣性、復雜性與豐富性,不能用某一棵或幾棵樹木的標準來丈量其他樹木,更難以控制森林或壓制其他的生長空間。其三,每個民族都積極爭取自己的生長空間與資源,在特定情境下不得不與其他民族處于競爭與緊張關系,給共同相處的世界空間造成沖突與危機,甚至是弱肉強食的殊死斗爭。中華民族人口眾多、領土遼闊、資源豐富,是一個悠久歷史的文明連續體,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不可忽視的大樹,但也可能因此受敵,而“屹立”可以表達期待、尊嚴與力量等多重含義。
“中華民族崛起”表達時間與空間雙重意識及其關聯性。一方面,“崛起”時間無論長短,都不是一蹴而就,發展變化有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正如“站起來”(獨立)、“富起來”(富裕)、“強起來”(強大)所表達的時間次序。在此過程中,崛起是展示文明體的整體力量,但在各領域和層次并非一致。后發民族國家在現代世界崛起的一般路徑是在擺脫殖民統治之后,先從經濟領域開始,然后體現在軍事-政治領域,進一步投射到歷史-文化-心理領域,至此完成民族共同體的“崛起”過程。當然,在時間意識上,“崛起”并沒有“復興”那種歷史周期的長時段意識,更多采取一種由弱而強的線性史觀。另一方面,“崛起”體現為多層空間。最小空間體現在民族共同體內部特定地區和特定領域的顯著成就,尤其是地方經濟的崛起,進而帶動更大領域的經濟發展,推動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整體經濟繁榮。經濟實力推動政治組織與動員能力的提升以及軍事力量的強大,使民族國家共同體成為區域經濟、政治和軍事領域的主導力量,進而在全球經濟體系與世界民族-國家體系中成為不可或缺的結構性力量。因此,“中華民族崛起”展示時間進展和空間擴展的兩種動態交織過程,表達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時空關系轉型。
顯然,關于中華民族的幾種命題表述都具有宏觀大視野的比較意識與方法。“復興”是在時間軸上進行長周期興衰更替的歷時性比較,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一種世界空間范圍的宏觀比較,“崛起”強調時間延續與空間擴展的兩個動態變化過程,是在“時空體”中不斷涌現,并嵌入世界經濟體系和民族國家體系的雙重結構體過程中,因此具有時間與空間的雙重比較意義。研究中華民族既需要重視長時段的時間意識,才能把握中華民族起伏變化的基本脈絡與規律,還要重視大視野的空間意識,才能把中華民族置于諸民族單位構成的現代世界,尋找不同民族在進入世界體系過程中的共性與差異。一方面,任何政治民族的來源與形成過程借助其獨特的傳統資源,由于進入世界經濟體系與民族國家體系的方式、契機和時間節點不一致,在國際格局中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也不相同,從而呈現獨特性和差異性。另一方面,現代政治民族作為世界一個合法的政治單位,構成國際社會認可的現代國家,在基本運轉和屬性方面存在共同特征。這意味著需要對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進行時空關聯的比較,由此確定與其他民族相比較的共性與個性。共性是使特定民族國家彼此溝通成為可能,而個性是特定民族國家自我識別及其成員自我認同的來源。在某種國際情境下,個性可以導致一個政治民族走向衰落,而在另一種國際情境中走向繁榮。換言之,通過宏觀比較,可以尋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情境條件與機制。
2 中華民族作為國族的共性
國族作為國際社會通行的一種政治單位形式,是舶來的觀念與意識。中華民族觀念的興起在現實上是受西方列強侵略的刺激,近代中國需要內部整合與團結;在思想上是受西方民族主義的影響,政權構建需要民族構建的觀念支撐。但從觀念生成到普及主要經歷兩次轉換。其中,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日本與西方各帝國的持續侵略,梁啟超率先在蒙、漢、藏等社會民族之上提出“大民族”“中國民族”“中華民族”等概念,第一次在國族意義上奠定了中華民族觀念,并成為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的基本共識[1]。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華民國是現代國族與現代國家結合的首次嘗試,在制度上結束了單一社會民族支配王朝國家的傳統統治模式,中華民族觀念第一次成為中國人表達民族自覺與團結的政治象征符號。據此,馬克斯·韋伯在1914年指出,中國已經“獲得‘國族’特質”[2]174。當然,這個時期的中華民族是一種催熟的國族觀念,僅在知識與政治精英群體的小范圍傳播,而作為政體制度形式的民國卻完全不成熟,曇花一現,因帝制復辟而流產告終。然而,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成為現代意義的政治共同體單位,從此向國人和世界展示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形式,為后來的觀念傳播與制度落實奠定基礎。
中華民族觀念的廣泛傳播和大范圍普及是在日本侵華之后。侵華戰爭把所有中國人帶入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國共兩黨、各社會民族以及知識精英、政治精英、社會大眾高度認同中華民族觀念。顧頡剛關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命題以及孫科與芮逸夫的“中華國族”表述在學術界引起諸多爭論,圍繞“中華民族復興”話語展開前所未有的廣泛討論與宣傳,無疑擴大了中華民族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增強了全體中國人的國族意識[3]。“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新政權的國號,意味著中華民族與新型的現代政體即社會主義國家再次結合,以民族-國家的制度形態重新進入戰后形成的新世界格局。新中國的成立在國際社會逐漸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可,并建立平等和正式的外交關系,1971年聯合國承認新政權的合法身份,并獲得常任理事國席位。從此,中華民族作為國族形式、社會主義政權作為國家形式,在國際上獲得民族國家單位的合法身份。中華民族作為國族觀念的形成與體制性落實,既處于一個獨特的外部國際環境,又有一個復雜的、獨特的、具體的歷史過程。但從現代世界諸民族國家的國族性質和形成特點來說,中華民族具備現代民族國家之國族構建的普遍特征。
在基本原則上,國族是立足于現代國家構建而構建的政治民族,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意義上使用的“民族”,是相對于人們在長期交往中逐漸集族而居的社會民族或地方文化共同體而言。社會民族因地理環境與地方習俗等不同,產生小范圍、小規模、形態各異的地方文化共同體,但“國族”則是現代國家進程中為了“人口國民化”與“國民整體化”而構建的政治共同體[4]。所以,統一構建的政治民族與自然形成的社會民族之間存在性質上的本質差異,而且是“一”與“多”的包含與被包含關系。在現代世界體系中,任何領土國家的形成都因壟斷物質性力量的軍事與經濟,需要統一精神的現代國族相配合,用以壟斷非物質性力量的信仰與文化,以至于結合而成的民族國家成為現代世界最大規模、最為穩固的政治共同體單位。從此,民族國家具有統一的外在形式和象征符號標志,包括國號、國歌、國徽、國語、國土、國界、國民等。相應地,在國際社會里得以合法承認的現代國家都以國族為單位而構建,并以此作為國際法的基本單位和政治行為體,進行國際之間的政治交往、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以至于“國家政權”(state)與“政治民族”(nation)在概念上混為一體,實踐操作也彼此難分。
在形成動因上,國族觀念的興起源于傳統身份認同的總體性與結構性危機。人類歷史幾乎在任何時期都存在因社會關系而凝結形成的地方共同體,但國族觀念完全是現代現象。隨著傳統社會秩序的衰敗,一部分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再也無法在傳統身份等級秩序中找到位置,出現難以彌合的身份認同危機,他們往往在傳統秩序之外想象一種新的政治共同體,進而把身份平等的新秩序付諸實踐。但威脅舊體制和社會大眾生死存亡的外部力量形成一個必不可少的機會結構,使精英群體對傳統秩序的怨恨劇增,加速瓦解傳統的等級身份秩序,同時增強新興的政治民族觀念對社會的吸引力與向心力。在新興的政治民族吸納更多精英群體過程中,社會大眾也體驗到新型共同體的真實性與可靠性,精英與大眾出現空前的團結一致。新興的政治民族意識與認同不同于傳統的地方共同體意識,是以大范圍的特定地域為基礎,把所有棲息其中的人口不分財產、地位和階層都視為同質的平等個體,并以平等的政治身份觀念和制度統合起來。因此,構建政治民族成為動員社會大眾和構建政治新秩序的一項政治工程。隨著現代印刷技術的推廣和識字率的提高,社會大眾對接受新思想的知識精英比維持舊秩序的傳統王權和貴族更有親近感,而外來力量增強社會整體的威脅感、傳統身份認同的危機感以及對新興民族共同體的歸屬感,塑造出以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為主導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從而在觀念上完成傳統臣民的等級身份體制向現代國民的平等身份結構轉型。
在目標追求上,國族是立足于現實世界的世俗共同體。國族支配著地域范圍內大眾的精神信仰,為民族認同而壟斷公共文化、公共教育以及道德規范的解釋權。在西歐興起的國族觀念不是源于宗教觀念,也不是取代基督教的先驗地位和超越理念,而是僅關注此岸世界的世俗存在。因此,國族追求的目標是在一個世俗世界如何重建秩序,其目標與現代國家的政權構建與秩序鞏固相一致。但與現代國家注重當下秩序構建并強制落實不同,國族構建有三個任務:強調共同體成員的尊嚴捍衛與平等身份保護;把所有個體內在的道德規范和倫理責任以及外在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統合起來,致力于推動多重共同體的統一性;消除共同體內部群體或個體的多重社會身份之間的緊張,使之完全服從于政治共同體的成員身份。國族構建可以根據當下身份認同的要求追溯古老的文明來源,調動各種傳統資源,為共同體成員繪制共享美好生活的未來藍圖,在時間與空間兩個向度把社會個體的命運和尊嚴與政治共同體的發展和興盛有機聯系在一起。
從此,政治共同體成員以平等身份的觀念與制度為同質性存在,而國族成為捍衛個體尊嚴和命運的最有效保障,從而決定了現代人的共同存在樣式與狀態。反過來,社會群體所共識并確定的有序狀態轉化成規范與制度,成為國族構建的高級文化和共同信仰,而共同的道德準則為世俗世界的秩序構建提供倫理保障,知識生產為之提供邏輯論證。這樣,國族認同在多重身份認同的沖突和競爭中勝出,不斷塑造自我認同并獲得主導權,可以抵制超地域的先驗性認同,征服跨領土邊界的族群認同,壓制地方文化與社會認同。
在塑造途徑上,國族認同主要利用傳統與外來兩種資源。在現代世界,每個民族國家的國族形成很復雜,塑造方式尤其迥異。西歐早發的民族國家以法國為典型,經過一個絕對主義王權的過渡,以依附性的臣民身份實現社會大眾的同質化,消解民眾的地域性認同和對封建領主的認同。到18世紀后期,民眾對國王的依附、認同與效忠闕如,并轉向人民、民族、祖國的集體認同與忠誠,國族才得以形成。這成為幾乎所有后發國家效仿的典范,并以兩種途徑塑造現代國族。其一是利用傳統資源。致力于在世俗世界重建秩序的國族觀念興起于早發國家,其最豐富的傳統資源是基督教信仰與組織實踐,因此,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知識精英利用大量的基督教話語修辭、組織形式與傳播方式[5]。但這并不意味著國族產生或延續基督教傳統,而是傳統資源被用來塑造現代完全世俗化的國族觀念,創造共同的語言、習俗、信仰與傳統,塑造統一的政治認同,配合現代國家的想象與制度構建。其二是利用外來資源。后起的民族國家紛紛仿效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國族塑造,全新創造一種身份平等、同質化的國族觀念,用于取代對傳統身份結構的等級觀念。圍繞國族的革命性塑造,知識精英大量引入新觀念與新話語,創造新概念與新表述,填補自身傳統不具備的現代資源。然而,在非基督教傳統和非印歐拉丁語系的非西方世界,不具備塑造國族觀念的原初情境條件。
即便如此,新興的國族觀念塑造依然需要挖掘自身文化傳統,是本土與外來雙重力量的結合。這可以從三方面來理解。其一,利用本土主流的傳統因素重新闡釋人口同質化的國族觀念,使新興的共同體意識和身份認同嵌入傳統觀念的主脈,使社會群體或個體視之為傳統的正常延續。其二,激發與國族觀念不明顯沖突的傳統資源,改變傳統語詞表述的語義與語境結構,改造傳統象征符號的組合方式,重新挖掘并闡釋國族觀念之前的思維模式、歷史人物與文化心理結構,由此“發明傳統”,重新敘述歷史,“制造”國族塑造的內生性演化特征[6]。其三,明確拋棄并徹底批判與新興國族觀念明顯沖突的傳統文化及體制元素。剝離國族塑造在西方的地方性經驗和原初情境條件之后,直接上升為普遍的理想形態,進而作為規范化與標準化的整體觀念而仿效,按照國族塑造的基本元素,對相抵觸的歷史遺產進行重新排序。在此過程中,激進的知識精英群體始終是國族塑造的擔綱者與傳播者,對舊式的社會政治結構進行革命性改造,塑造新政治身份與樹立國民新形象。
總之,中華民族作為一種國族意義上的政治民族并無例外和特殊,而是具備國族構建的普遍特征,具體體現在構建原則、形成動因、目標追求與塑造方式等方面。中華民族呈現為國族形式,先后與兩種不同性質和主導力量的現代政體結合,即國民黨領導的民國與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共和國,后者最終走上成功,得到國際社會認可,并推動中華民族復興和崛起。
3 中華民族的基本特性
棲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民族,都要形成并發展其特性,民族特性決定國家的存亡。正如梁啟超所言:“國之成立,恃有國性,國性消失,則為自亡。”[7]148于中國而言,正是中華民族的獨特性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崛起的豐富資源,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識別中華民族的特征與“我們是誰”的身份標記。那么,中華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國家的國族比較,其獨特性何在?
在西歐形成的現代早期國家,其政治民族構建的時間并不一致,與國家政權構建的邏輯不同,但在18、19世紀匯合在一起,成就第一批民族國家。其共同特征是基督教神學體系衰敗帶來精神世界的秩序危機,需要在世俗化的世界重建信仰秩序,在國家權力和現代科學作用下把傳統宗教信仰的組織方式與動員策略作為現代世界的政治資源,催生了政治民族,結合為現代民族國家形態[8]。比較而言,后發民族國家之國族構建很不一樣,盡管是模仿早發國家的表現形式。國家政權構建與政治民族構建不是先后進行,二者在觀念上模糊不清并融合在一起而同步構建。其中,作為政體形式的現代國家可以自由選擇,并以政治民族為單位,對外接受既定的國際法準則,在國際競爭中求生存圖富強。但作為一種特定文明載體的國族必須標明和堅持某種價值理念以動員社會資源、塑造國民身份認同、凝聚與整合力量,由此形成民族特性。
在后發民族國家的群體中,中華民族的興起是特殊中的特殊,源于知識精英最初背離中國傳統的文化與政治體制,嘗試用西方文明替代和改造中國傳統,但為了激發中華民族的統一體觀念和民族精神,又不得不回到自身文明傳統,并充分利用傳統資源。矛盾的是,知識精英在理智上依賴傳統,視之為政治動員資源,而在情感上又背離傳統,使中華民族觀念內蘊西方傳入與中國傳統兩種競爭性的力量,兩種文明的精華統一服務于中華民族的政治構建。在民國的共和流產之后,知識精英才充分認識到中華民族的觀念構建必須充分利用傳統資源,并與西方文明拉開距離,以此守住國性,其“具象”是“語言、文字、思想、宗教、習俗,以次衍為禮文法律”[7]148。從此,傳統文明在中華民族的觀念構建與制度落實中重新煥發活力,并以此推動政治共同體成員的團結一致。因此,中華民族的基本特性之一是在同一個生存空間中延續中國傳統文明,通過中華民族的觀念構建重新找回對中華文明的自信心,把中國的傳統與現代緊密關聯起來。
那么,中國傳統如何有利于構建中華民族的現代觀念呢?這方面的歷史研究已經非常豐富,但最重要的傳統資源是“大一統”理念,可以從觀念體系、制度體系與日常行動實踐網絡來理解。在觀念體系上主要是圍繞“大一統”的元理念而展開。“大一統”理念是中華文明傳統的精髓與核心。秦王朝通過戰爭獲得統一,確立政治“尊王”與文化“崇禮”而追求天下一家的觀念,統一語言文字、貨幣、交通與度量衡等物質生產領域,而到西漢時期確立儒家的正統地位和象征符號系統,統一形成天—子—民的三級觀念體系和官階體系,把天下觀與人倫觀結合在一起。此后歷代王朝經歷重建、興盛、持續與崩潰的歷史周期循環,但都離不開作為統領性原則的“大一統”理念,并通過一套不斷完善的制度體系加以落實。“家”是最小的觀念單位,上升到邊界開放的“天下”觀念,使家—國—天下的倫理邏輯與天下—國—家的制度邏輯相互配合,成為制度體系的中樞機制,由此擴展到朝貢體系、行政區劃制度、官僚制度、科舉制度、戶籍制度等。制度之間彼此關聯,既鞏固王權又直接滲透到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實踐,使之時刻感知天下中心的存在以及天—地—人的一體。“大一統”理念把觀念、制度與行動緊密關聯,成為傳統中國人的信仰與精神追求,在近代之后成為中華民族構建的重要資源,也是現代中國人自我認同、追求領土完整與團結統一的內在精神支柱。
顯然,傳統中國的“大一統”理念與制度體系為中華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統一構建奠定了統一基礎。其中,壟斷軍事-經濟體系鞏固了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不用經過西方現代早期封建領主之間的自由競爭階段,而壟斷文化-信仰體系塑造高度認同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使之成為現代中國人追求家國一體的精神力量,而不用經過西方從超越性的宗教信仰衰敗到世俗性的民族精神構建之間的人為轉換。在這個意義上,“民族”(nation)作為一種人群劃分的政治觀念形態,雖然在形式上來自西方工業文明和現代國家,但在內容上完全符合中國文化自身的世俗傳統。以黑格爾的觀點理解,“作為國家的民族,其實體性的合理性和直接的現實性就是精神,因而是地上的絕對權力”[9]393,中華民族是“早熟”的民族國家觀念形態。具體來說,中華民族在現代理念上采取“民族形式的實在化”,而在傳統文化中“自在地存在著”,客觀上具有“倫理性的實體”,并落實到普遍化而具體化的國家制度與法律形式中。因此,幾千年以來的“大一統”理念與制度形態決定了中華民族的實體性、客觀合法性和自為合理性,其獨立不僅在形式上符合國際通行的政治單位,而且獲得國內與國際社會承認的最高主權[9]403。反過來,中國傳統文明的觀念與制度通過民族國家的現代單位形式重新獲得新生與希望,即杜贊奇所謂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10]。所有中國人都因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成員身份而獲得平等的尊嚴與地位,并從中找到精神歸屬,從而必須捍衛中華民族的存在、尊嚴與富強及其承載的文化價值與文明意義。
正是因為“大一統”理念及其制度落實非常成熟,是一種完全關注世俗生活的價值觀,沒有西方那種排他性、先驗性和神秘性的神權力量干預。在近代中國遭遇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中華民族觀念興起和傳播過程才可能迅速在傳統文化的精神信仰中找到牢固的支撐點。這正好符合政治民族構建的兩個要件:一是共同擁有豐富傳承的歷史記憶;二是同心協力發揚歷史傳承的決心和意志[11]。最集中的歷史記憶是“黃帝”與“炎帝”,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通過各種敘事方式和宣傳途徑,把傳統世俗的神話人物以及后繼的英雄人物塑造成中華民族認同的政治象征符號,而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中國人”,無論哪個歷史文化群體,都擱置爭議和沖突,全部是“炎黃子孫”,由此激發起政治與文化共同體的身份認同感,并根據“中華民族”觀念起源與發展過程重新書寫連綿不斷的中國歷史(1)關于黃帝與近代中國國族構建的關系,參見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皇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J].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997(28):1-77;孫隆基.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J].歷史研究,2000(3):68-79;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C]∥“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羅志田.包容儒學、諸子與黃帝的國學:清季士人尋求民族認同象征的努力[J].臺大歷史學報,2002(29):87-105;石川禎浩.20世紀初年中國留日學生“黃帝”之再造——排滿、肖像、西方起源論[J].清史研究,2005(4):51-62.。
在興起與構建進程中,中華民族觀念主要是受外部反帝反殖民的刺激,諸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接踵而至,暴風驟雨式、短暫而迅速地涌現一種政治共同體意識。政黨與國家動員并整合國內不同的社會群體,為救亡圖存而聯合,形成一致對外的團結意識。當然,隨著外部“敵人”及其威脅程度和性質差異,根據對外防御的要求不同,國族意識的動員方式與話語策略不同,所能選擇性調動的傳統資源也不同。但總體而言,現代中國在想象與塑造中華民族的過程中呈現出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獨特性,表現為世俗性、開放性、非排他性、自我捍衛與一致對外的防御性。
相反,西方許多民族國家的國族構建過程普遍夾雜著種族問題、宗教問題與移民問題,從而使現代民族的政治構建帶有排他性、侵略性與對抗性特征,而政治身份也始終面臨來自這三方面的挑戰。其中,美國主要表現為種族問題,其國族構建最初是針對非裔美國人的奴隸制,是在白人的“我們”反對黑人的“他們”中形成的。但其他大多數的西方國家是因神教的排他性及其超越性的衰弱而引起。比如,西班牙是在反對國內猶太人和穆斯林中塑造出弱的國族認同,法國是反對國內新教過程中形成強的認同形態,而英國也是在反對國內天主教的過程中發展國族構建。可見,西方國家的國族構建主要不是對外防御,而是主要源于國內種族與宗教群體的相互排斥。正如安東尼·馬克斯總結的:“統治者認識到,如果國內宗教沖突受到削弱,他們無法發動有效的對外戰爭,軍隊也難以忠誠,因此君主通過國內的宗教排斥來建立民族的統一忠誠,正好迎合底層大眾的行動意志。”[12]當然,不同文明體系有不同的歷史傳統,在特定歷史機遇的作用下形成特定國家的國族特性,這不僅錨定了世界民族之林中不同國族的性格特征,而且也對國族身份意識的動員機制和身份認同危機的發生機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4 結論與思考
中華民族的崛起與復興同時是一個時代命題、歷史命題和未來命題,已經成為當今中國與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重大議題,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將對中國的發展與世界格局的變化產生重要影響。把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完整的研究對象和分析單位,在歷史時間與世界空間的關系框架中進行宏觀的比較歷史研究,既是在世界民族之林和新國際形勢下理解中華民族具有的共性,又是總體把握中華民族形成與構建歷程的獨特性,為中華民族崛起與復興提供準確方位。
在方法上引入時空關聯的分析框架,可以把握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可挖掘的傳統資源的途徑及其現代承接的關系方式,避免完全沉迷于中國中心論的內生性演化機制。可以理解中華民族融入世界體系的方式與過程,并置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觀視野中進行比較分析。通過宏觀比較,可以發現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共同屬性,從而在世界空間定位其具體方位與世界責任,在歷史時間定位其獨特的歷史演變與政治構建進程。共性決定了中華民族在現代世界的政治共同體單位所具有的一般屬性,從而在人類共同生活的世界來理解中國,并進一步處理好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的相互關系;獨特性成為中華民族得以崛起與復興的發生機制,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我識別標志,也是中國人塑造“我們是誰”的身份認同基礎。
在認知上考慮內部機制、外部機制及其內部與外部關聯的關系機制。中華民族復興不僅需要國內安定團結的社會政治環境,還同時依賴于國際社會的外部環境即世界的機會結構,進而把“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種時空意識關聯起來思考。中華民族復興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既是過去幾代中國人的期待,也是如今所有中國人得以整合、團結與奮進的黏合劑,更是為中國社會、經濟與政治未來發展的指南針。但這項系統工程并不僅僅需要中國人自身的團結與努力,更需要國際社會持久的和平與發展,給予中華民族復興的機運,中國與周邊國家形成長期的睦鄰友好關系,中國與世界主要大國之間建立互信、良性競爭與合作共贏關系,中國的發展在世界整體文明進步以及參與處理國際公共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不斷獲得其他國家的認同、信任與支持。
在主導力量上需要發揮執政黨強大的組織與動員能力。中華民族觀念的構建、塑造與制度性落實始終離不開執政黨的核心領導,在過去100多年的歷史證明,共產黨在中華民族的觀念動員與制度化落實方面有著明顯優勢。國民黨的影響力僅限于部分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群體,難以擴展到社會大眾,而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有著豐富經驗,形成優良傳統。因為中國共產黨立足于社會底層的人民群眾,明確反帝反剝削的革命傳統,而所領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得到國際社會的充分認可,在于時刻把國際與國內兩方面力量緊密結合起來,充分考慮外部國際格局變化和內部團結穩定局面。中國共產黨根據國際國內具體的情境條件,在不同時期提出不同的動員策略與組織方式,始終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共產黨自身發展的命運關聯起來,并視之為政黨自身的宏偉目標和長期任務。因此,中華民族復興需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