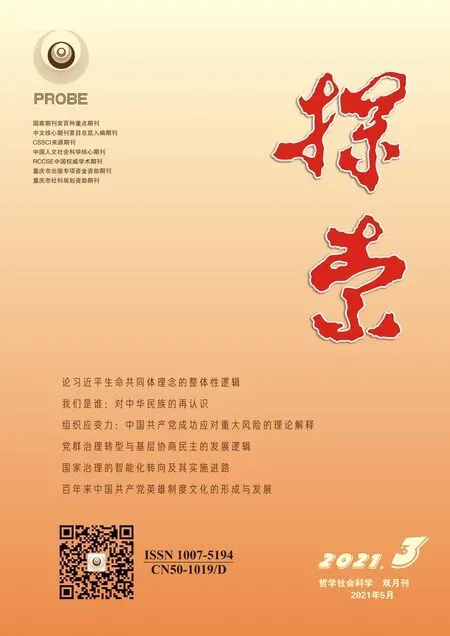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二維向度與演進邏輯
劉永剛
(云南大學 民族政治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自2014年5月28日習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在各民族中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至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國家戰略從國家整體與民族關系兩個層面有序展開。關于該議題的研究也成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構建中國特色理論體系與知識話語的新增長域。深入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既需要立足中國各族人民自覺凝聚為統一的中華民族進而建設現代主權中國的基本史實,也需要緊扣政治整合與國家認同的現代國家建構本質內涵。因此,立足中華民族多族聚合的內部結構與國民一體的共同體屬性,系統分析其結構屬性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和內涵的內在關聯,揭示近代以來百余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整體演進脈絡與階段性特征。這不僅是構建中國特色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是有效把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演進規律、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必要理論準備。
1 結構與屬性: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的基礎
中華民族建設與中華現代國家建設辯證統一于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總進程之中。這是因為現代主權國家的孕育、生根與發展是“世界之中國”到來的首要特征,并通過中國各族人民自覺凝聚為以“中華民族”為族稱的現代民族建立民主共和國家予以體現。相應的,作為中國社會意識一部分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質上就是全體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歸屬與贊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受到中華民族結構屬性的規定,又因不同時期社會意識狀況而呈現時代性與延續性。
1.1 從結構看中華民族是各民族自覺凝聚的再生型民族
要認識中華民族,總會陷入“民族”定義的沼澤。但“民族”的現代運用直接與主權國家相關,“若不將領土主權國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討論,所謂的‘民族國家’將會變得毫無意義”[1]9。而在世界民族國家體系背景下,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復興歷程從來都是與國家政治相融合的,所以中華民族“是以現代國家(state)為認同邊界的人們共同體”的國族[2]。
在西方列強侵略的亡國滅種時代背景下,將國內多個文化族體整合為統一的國族以建立主權國家是近代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中國悠久的“大一統”思想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史、“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各民族共創中華文化、各民族共育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3],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發展的肥沃土壤。而中華文明之外的西方列強“他者”的出現,在確立國人“認異”對象的同時,極大激發出中國內部整合的需要和目標。中華各族共享的歷史榮光與共同的屈辱經歷激起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在推動全民一體抗擊外敵力爭民族解放的背后,則是中華民族從歷史上的“自在發展”向現代的“自覺凝聚”的加速進程[4]。所以,從中華民族多族聚合的內部結構與鮮明主權取向來看,是典型的再生型民族。
同時,中國傳統“天下”秩序因西方列強入侵而終結,與之同步開啟的從“華夷”向“民族”的國家新秩序塑造的過程,卻總是受到傳統“夷夏”觀與“正統”歷史觀的制約,進而面臨著“漢族在中國的主導地位與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則之間難以化解的緊張關系”[5]。這在早期梁啟超提出“大”“小”民族觀與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綱領中已清晰地呈現出來。而“中國民族自求解放”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6]118,之所以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共同主張,在于由各族人民凝聚而成的中華民族能夠實現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自決,符合中國基本國情與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但歷史上“中國”意象的漢地印記、民族平等的現代敘事邏輯以及“反對大漢族主義”的政治原則,無疑均強化了中華民族多族聚合的結構烙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國家主導的“民族識別”、政治制度設計與系統民族政策,進一步確立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多元一體”維度。
1.2 從屬性看中華民族是以整體國民為根基的主權性民族
學界關于民族“建構”與“原生”的分歧,從未妨礙將民族想象為“有限的(limited)”且“享有主權的共同體”[7]6。這個被想象的民族共同體摧毀傳統王朝國家政治合法性的方式,是以主權為尺度與象征來衡量人的自由。而當社會人成為(或淪為)民族國家的“國民”,運用主權對自身的自由進行衡量時,“民族主義”也迸發出改造世界的力量。顯然,現代性是理解民族與民族國家的鑰匙,而清王朝所代表的傳統帝制國家應對西方列強時的系統性失敗再次證明了這個現代民族的威力。
雖然中國歷史分分合合、王朝更迭,但真正面臨“亡天下”的遭遇則是鴉片戰爭后。對內通過政治整合重建國家認同、對外抵御列強保全中華疆土,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旋律。將“帝國主義”確立為整體的敵人是中華民族從“自在發展”到“自覺凝聚”、從概念創制到實體構建的外部因素。而“民主”“主權”“共和”等現代政治價值則賦予中華民族自覺凝聚的現代性取向。中華民族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將人身依附的臣民改造為個體自由的國民,將一盤散沙的人口塑造成整體的國民是中華現代國家的政治底色。雖然,對內的民主革命因“救亡圖存”的急迫而服務于對外的民族革命,但如同清末“以‘新政’挽救王朝氣數的動機,卻換來了推翻王朝以實現改革的結果”[8]308一樣,整個中國近代以政治整合力圖強化中央集權的努力,總被拉回民主政治以鞏固國家認同的主權國家建設道路上。
從歷史中國的王朝國家形態向以民族為依托的中華現代國家的轉型過程表明,這個以“中華民族”為族稱、以主權為原則、以國民為屬性、與國家相融合的再生型民族,是現代中國的主權民族[9],因而“兼具多族聚合體和國民共同體兩種屬性”[10]。以至于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均被納入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以民主共和的新中國為目標。
1.3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二維向度及生成演進的非均衡性
“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人民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進行了前仆后繼的英勇奮斗。”[11]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序言”是我們認識并把握中華現代國家內涵的鑰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基本國情,規定了“外爭國權、內爭民權”的中國革命目標。國家獨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情下保全中華的最低目標;民族解放是中國加入世界民族國家體系的途徑;而民主自由集中體現中華現代國家的政治底色。
由之反觀自1840年以來180余年的中國政治進程大體經歷了從分散到一體、從王權到民權的轉型過程。而與現代中國互為表里、相互建構的中華民族,則經歷了屈辱史、凝聚史與復興史。雖然,中華各族凝聚為統一的中華民族有著“大一統”的治國傳統與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文化基因,但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外爭國權”抵御西方列強殖民統治與“內爭民權”推翻封建主義的民主共和建國歷程,顯然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興起、興盛的現實動力與鮮活素材。相應地,因多族聚合結構與國民共同體屬性,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演進也呈“多元一體”與“國民一體”的二維向度。
然而,中國現代化進程不斷被西方列強所打斷。因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矛盾的緊迫性與問題解決的優先性,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二重變奏,卻不時演繹為民族主義壓倒民主主義、民主革命服務于民族革命的現實場景。中華現代國家塑造整體國民的系統工程在一定程度上被延緩,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也呈現出對國民共同體屬性的關注往往服從并服務于多族聚合的政治一體需要。這種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多元一體”與“國民一體”二維向度上的非均衡現象,是中國近代以來特有國情與特定境遇決定的,反之也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的階段性特點與長期性要求。
2 “多元一體”:統一的多民族中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基于綿延性與統一性的中華民族進程,費孝通從過程、融合、實體、自覺、結構等方面入手,揭示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這也是習近平所講的,中華民族“一體包含多元,多元組成一體,一體離不開多元,多元也離不開一體,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12]150。這個中華民族共同體多族聚合的歷史進程與內部結構,系統體現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演進的歷史進程、族際關系與國家治理的維度之中。
2.1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自在到自覺的歷史進程維度
歷經綿長的“自在發展”到近代“自覺凝聚”,中華民族形成“多元一體”的特有格局,根源于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中國的統一性不在于政治而在文明”[13]164,以至于一些學者認為傳統中國“是國家、社會和文化三者異常超絕的統一體”[14]9。漫長的中國歷史,分裂與統一的背后是以中華大地為地域單元,各族民眾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4]。作為中國歷史記憶主要承載工具的《二十四史》系統記載了“‘自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譜系,以及其中蘊含著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15]。
中華民族自在發展的本土進程被打破,源于“非我族類”的“洋人”出現帶來的“亡天下”危機。而自覺凝聚的中華民族的特殊性是基于內部認同下的對外“認異”。向國內大力引介“民族”概念、提出“中華民族”概念、主張“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的大民族主義[16]75-76的思想巨擘梁啟超,基于古代、中世紀與現代的三分法對中國歷史進行系統研究。他提出血緣、語言、信仰是民族形成的因素,但根本性的要素是民族意識。所以,中華民族的成員是“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于其腦際者”[17]1-2。而梁啟超對于中華各族相互交流融合最終形成中華民族過程的考察,揭示的是在中華民族一體過程中各多元族體消失、交融的史實和條件。
自梁啟超開啟并在民國迅速興起的民族史研究,探究各民族“種族起源,名稱沿革,支派區別,勢力漲落,文化變遷,并及各族相互間接觸混合等問題”[18]2,成為之后中國民族史的規范體例。而1939年的“中華民族是一個”論戰中顧頡剛關于民族是“在一個政府之下營共同生活的人”的認識[19],從“超越種族”的國家角度定義“中華民族”與從文化角度認識中華各民族,在有力論證了中華民族“一體”的同時,也極大規范了國內的各民族“多元”敘事。從中國歷史進程中梳理民族過程,以民族為主體重述中國歷史,形成了系統的“統一的多民族”中國的話語體系,如此呈現的中華各民族自覺凝聚史與統一的中華民族建國史,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多元一體”維度形成發展的歷史邏輯。
2.2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多元一體”族際關系維度
中國100余年的現代化進程中“民族”概念的運用,始終相互交織于主權國家訴求、中國歷史進程和多元人口結構。外來的“民族”概念同中國傳統的“天下”觀與“華夷”觀相遇后,中華民族與中華各民族的同步構建成為不容忽視的客觀現象。梁啟超對“漢族對于國內他族”與“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的“小”“大”民族區別[16]75-76,以及“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20]4的認識,就已將中華現代國家建構中的族際關系揭示出來。
這種“多元一體”的族際關系維度也系統體現在國家憲法性文件中。《清帝遜位詔書》以“仍合滿漢蒙回藏之固有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昭示世人。《臨時大總統宣言書》確認“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21]2。這兩個國家轉型的重要文獻在法理上明確了多民族統一的共和國體和中華民族的多族聚合結構。孫中山曾大力批判“五族共和”并主張“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6]185,但1946年修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時中華民族“國族入憲”提案遭到少數民族代表強烈反對而失敗的事實表明,族際關系的維度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演進的深刻影響。
隨著對國情的認識與政治實踐,中國共產黨逐步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和民族理論。從整體國民與中國境內各民族聯合起來的視角,主張中國人所有“具有共同抗日意識的就是中華民族”[22]767,并進而認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是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總稱,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是共同祖國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命運共同體[22]808。這種從“國籍”角度確認中華民族的政治一體屬性并揭示多族聚合結構,實則建立了政治整合與國家認同的全新理論框架。
回顧中華民族近百年研究史,自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概念,到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中華民族作為一種政治意識與符號體系作用于國家進程的同時,承認并保障國內各民族的“多元”被系統納入國家框架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族際關系維度也清晰可見。
2.3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邊緣到中心的國家治理維度
中國自秦統一六合,以“大一統”為政治倫理、以“家國天下”為政治規范、以“有教無類”的文化觀包容多樣、以“華夷之辨”的分類法區分人群,形成了中國王朝國家時代的疆域治理格局。“守在四夷”“守中治邊”等疆域治理觀直接決定了邊疆地區在國家政治中的邊緣性與國家疆域的碎片化。隨著中國歷史軌跡被西方列強所打破,因皇權體制瓦解致使邊疆與內地的傳統政治紐帶斷裂,國家出現嚴重的政治整合與認同危機。國人運用“民族”概念救亡圖存加速的中華諸族“民族化”,因主權原則凸顯的邊疆、民族在中華現代國家建構中的地位而一躍進入國家的政治中心。
中國革命的歷史早已證明,孫中山的“國族論”以及蔣介石的“國族宗族論”均未能有效解決政治整合與國家認同的時代命題。1938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主張中國共產黨“允許蒙、回、藏、苗、瑤、夷、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的權利,在共同對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22]595。1939年,毛澤東指出抗戰后應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這個國家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23]623。1940年進一步明確中國共產黨人奮斗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23]663。中國共產黨基本確立在承認并尊重各少數民族平等權利基礎上,以實現民族統一與國家統一的中華現代國家建設思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主導的“民族識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施行、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供給,使得國家治理體系在整體國民基礎上體現出鮮明的族際取向。專門從事民族工作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與晚清的理藩院、民國時期的蒙藏委員會也有著一定程度類似的治理邏輯。這些國家治理上的制度設計與政策體系,通過保障少數民族權益的方式維護了國家統一,實現了對邊疆民族地區直接行政。因制度對于社會意識生成演變的根本性作用,國家治理上的族際取向進一步強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多元一體”維度。
3 “國民一體”:中華現代國家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統一多民族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緊扣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時代脈搏,通過中華民族解放運動成功啟動人口的現代國民塑造,從而實現了國家、民族、人民的政治整合與一體化。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但又歷經百余年西方列強入侵的后發國家而言,構建中華民族的整體國民屬性是彰顯其現代民族的基本內涵,更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構件。而梁啟超號召“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的大民族主義蘊含的塑造治國事、定國法、謀國利、捍國患的現代“國民”[24]56,早已揭示出中國轉型的國民根基與民主底色。
3.1 民主革命是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內核與中華民族復興的基點
近代中國社會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相交織、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二重變奏,將對外推翻異族殖民與對內爭取自由平等的國家改造辯證統一于中華民族解放運動之中。自20世紀初葉“民族復興”思潮興起并掀起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徹底否定傳統社會臣民體系和王治國家形態的同時,確立了整體國民體系與民主共和國家新形態。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樹立共同體意識自覺凝聚為以“中華民族”為族稱的現代民族的時代背景。
中國從歷史傳統的文明體系向現代主權國家的轉變,根植于中國“大一統”歷史,并在西方文明沖擊下完成從“天下”向“民族國家”的現代革新。雖然,這個過程并未脫離中國歷史自身邏輯,但因對于人和國家關系的全新設計,“人民掌握國家權力,安排國家制度”而賦予了民主政治的內核[25]4。主權、民主的現代國家觀念與理性、自主的國民意識,是中華各族人民自覺凝聚的“民族建國”實踐的政治邏輯。以政治革命優先實現國家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根源,在于國家轉型的民主政治取向與塑造現代國民的社會革命內涵。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訴求是中國革命之所以被命名為“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源,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基點。
雖然,“保全中華”是中國革命的原初起因,但民主政治的內核才是中國完成現代轉型的根本原因。所以,在國家轉型的不同階段,對國家主權的全民歸屬與國民地位的保障均得到系統的國家憲法確認。自《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族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族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開始,“統一民主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屬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人民”[26]299-315成為各時期憲法的核心內容,體現并保障了中國革命的民主成果。由此可知,外爭國權、內爭民權的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在彰顯中華民族整體國民屬性的同時,也將國民意識與國家意識深深地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中。
3.2 人民民主專政賦予全體國民以人民性共建中華現代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彰顯了一種有別于傳統中國的全新政治整合機制與國家治理方式。立足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多族聚合結構、彰顯其整體國民屬性,通過塑造整體國民與人民性改造,完成從多族聚合向國民一體的現代國家升華,是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現代國家對民主革命成果的繼承與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
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11]。外取民族主義以抵抗侵略、參與國家間競爭,內取民主主義賦予全體人民以國民身份成功創制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家,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既是中華民族的國家,也是中國人民的國家。以中華民族為依托的新形態民族國家較之中華文明為國家形式的帝制國家而言,最大的區別在于“人民”中心地位的確立,國家制度設計與運行體現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代表民意的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權高于行政權和司法權”[27]。同時,無論是對全體國民賦予統一的公民身份,還是在“民族平等”原則下全國人大代表及其常委會中“各少數民族都應當有適當名額的代表”的憲法規定,表明全體中國國民及各民族的權利與義務均是在中華民族的主權國家中得以確認并維護的。實現了中華民族的“人民主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權”的辨證統一。中華現代國家保障并實現民族認同國家的制度機制,就是人民民主機制。全國人民認同并凝聚為中華民族,在于中華現代國家將民主與正義體現為全體人民的進步與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直接根植于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實踐之中。
3.3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公民權利本位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民族征服國家建立的現代民族國家,意味著國家共同體與民族共同體“兩種不同的結構和原則的融合”[28]490。在民族國家的政治屋頂下以“民族”的形式對外贏得國家主權、對內向全體成員提供公共價值與公共文化。中華現代國家治理的進步性在國內與國際兩個維度展開:對內以人民為中心塑造整體國民、保障公民權利;對外以中華民族復興與國家崛起為形式,贏得國家生存與發展空間。而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振興之路,均是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下通過國家治理解決社會矛盾實現的。
在中華現代國家的憲法進程中,《共同綱領》具有承前啟后的時代價值,其繼承國民觀念將“國民”概念最后一次使用于國家憲法,并通過“人民”概念賦予全體中國人以人民性。在此后的國家憲制性文件中,均用法律意義上的“公民”概念替代政治意義上的“國民”概念,通過明確公民權利義務的方式奠定了國家治理的法治基石。雖然在憲法中對于社會人有“人民”“中國人民”“中國各族人民”“全國各民族”“各少數民族”“各民族”等多種稱謂,但“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條款,表明“公民”是全體國民的基礎性身份,公民權利和義務是國家治理的起點與依據。而“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公民權利確立治理根基、以憲法之治凝聚治理共識”[29]。以公民權利本位為基礎推動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顯然成為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的基礎性路徑。
再看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現了統一與自治、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的兩個結合,其“既保證了國家團結統一,又實現了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同時,“發展是解決民族地區各種問題的總鑰匙”[12]151-155。由此可知,維護國家統一、保障少數民族公民權益、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是該制度基本的國家治理功能。同時,“平等團結互助和諧”民族關系的鞏固與發展,既需要堅持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需要以全體國民為對象塑造整體國民身份為基礎。所以,因中華民族主權國家框架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使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振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內涵完整體現為“國民一體”的國家治理實際成效。無疑,國家治理的實際效能已成為全體國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雄厚基礎和鮮活素材。
4 百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演進邏輯
自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經歷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另一面是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民族復興之路。到21世紀隨著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華民族復興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2017年,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2018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寫入新修訂的憲法,更是將中華民族建設推進到“共同體”語境的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也從重點強調平等團結民族關系的“多元一體”維度向既重視“多元一體”又強調國家公民的“國民一體”的二維向度演進。
4.1 從“多元一體”優先向“多元一體”與“國民一體”二維協同演進
因應國內外局勢的變化呈現的國家治理階段性特征,直接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時代議題和建設狀況,同時,也因社會意識生成的社會制度背景間接影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展開與演進。而中華民族特有的多族聚合結構與整體國民屬性,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也因特定時期與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取向經歷了從非均衡向逐步協同的演進過程。
首先,國家治理的因外而內階段。因中國革命的世界革命浪潮背景與“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矛盾的優先性,決定了民族革命主導著中國現代轉型進程。雖然中國革命進程整體沿著政治民主的方向進步,但在救亡圖存、國家危機的特定背景下,民主革命的話語多服從于民族革命的需要。在清王朝“多族一統”的基礎上構建主權中國保全中華的“民族建國”方案,因外而內的族際整合特征十分鮮明。雖然在之后的國家轉型與社會改造中,國民共同體的意識漸被培育并不斷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社會基礎,但因應日益嚴峻的國家危機在社會意識中優先強調中華各族的“多元一體”與各民族平等團結一致對外,進一步彰顯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多族聚合要素。
其次,國家治理的內部優先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徹底扭轉了近代以來中國“亡國滅種”的國家危機。國家迅速展開的社會主義改造與全面建設,所面對的是疆域廣闊但內部差異巨大的“一窮二白”的基本國情。通過民族識別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維護國家統一與實現中央直接行政,有效保障了各族公民平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推動民族地區發展,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所以,在確立全體國民的人民性與公民權的國家框架內,以民族平等團結為基礎的民族理論、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等,使國家治理體現了鮮明的族際特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多族聚合結構得到系統性強化,而國民共同體的內涵雖已系統體現在國家制度體系之中,但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中隱而未彰。
再次,國家治理的內外兼顧階段。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在以少數民族為“民族”的特定社會語境下,1988年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將中華民族再次拉回到國家治理視域之中。以2002年“江澤民文化紐帶重要論述”研討會為標志,中國大一統文明史與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國家治理價值,取得政界學界的廣泛共識。國家大力提倡中華文化,強調中華民族的地位、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先鋒隊在黨的十六大修訂的黨章中再次明確。凸顯中華民族的整體統一性以應對來自國內國外雙重挑戰的時代背景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多元一體”維度繼續彰顯的同時,“國民一體”維度也因國家建設成就與法治水平的整體提升得到有力強化。
復次,國家治理的以內應外、內外兼顧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啟憲法宣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治國理政新時代,有力推動了系統全面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社會性反思與自覺性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塑造整體國民的基礎性社會政治機制得以揭示與挖掘,而整體國民身份的國家治理功能也有效地凸顯了出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從“多元一體”優先逐漸進入“多元一體”與“國民一體”二維協同發展的新階段。
4.2 從各民族平等團結到全體國民熔鑄整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憲法一方面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則系統確立了全體國民的人民主權地位和公民權利義務。這種憲法表述是在“多民族”的基本國情上凸顯了“統一”的政治主線與“一體”的國民根基。同時,以平等原則為基礎構建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使得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諧”在很長時間主導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和演進。
隨著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國家內外局勢變化,中國的民族國家屬性隨著國家崛起被進一步凸顯,以整體的國族參與國際事務與國家競爭的特征愈加鮮明。中共中央2010年提出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014年提出“民族互嵌”,黨的十九大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12]152-157,都是著眼于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時代奮斗目標。而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的總目標,則將民族平等團結的民族事務治理提升到鼓勵中華諸族文化創新交融共筑中華文化、經濟上相互依存共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情感上相互親近共享精神家園,從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時代國家戰略。
從社會意識的形成看,語言文字是基礎性載體。在全國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從公民權利保障角度看,這是教育權、工作就業權、文化權利的基礎性保障;從國家整體建設來看,是培養全民的國民意識和國家意識、促進民族地區現代化、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建精神家園、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的基礎性工程。同時,從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公民來看,“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而從民族自治機關來看則有著“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的職能[30]。所以,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在加速各民族深度融合塑造國民共同體的同時,進一步強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國民一體”向度。以上國家戰略體現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全新政治價值與知識體系,直接促進共同體意識中“多元一體”與“國民一體”的統一發展。
4.3 從差異治理尋求社會平等到“以人民為中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經由中華民族的自覺凝聚與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確立了以整體國民為根基的中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通過所有制結構的改造與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制度解放了社會生產力,保障了社會發展的成果,實現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通過解放社會生產力實現經濟的繁榮,“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31],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民族振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內涵的現實基礎。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制憲進程中,從《共同綱領》(1949)到《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1952)、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五四憲法”)的文本表述中,“平等、團結、互助”民族關系定位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憲法表述,體現了通過承認各民族多元保障其權利的方式以實現國家政治一體與全民平等發展的國家治理邏輯。經過70余年成功建設,“少數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區的面貌、民族關系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3]。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各族交流交往交融程度的加深與普遍的族際跨區域流動,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在于確認并回歸到以公民權利為本位的國家治理體系上,推動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以中華民族主權國家形式呈現于世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體系,有機統一并體現了人類文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與中國社會自身邏輯。而國家治理及其現代化就是要回應中國社會內外變化,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堅持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12]147,正確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多元”與“一體”的關系,強化其“國民一體”屬性,以充實完善中華民族承載的共同身份認同、共有精神家園、共通國家夢想的社會政治機制。其政治實踐的基礎是全體國民牢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國家治理的目標就是實現全體中國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5 結語
21世紀初,亨廷頓提出“我們是誰”的世紀之問,揭示了國家認同危機對國家特性/國民身份的挑戰與國家治理議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中華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的造“民族”易、造“國民”難的特殊時代境遇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時代要求,決定了中華民族建設是一個持續漸進的國家系統工程。這需要深入剖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多族聚合結構與國民共同體屬性,以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多元一體”,是歷史中國“大一統”治理史與中華各族交流交往交融史的現代呈現,體現的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共同體特征與多元并包的社會結構;“國民一體”是現代中國以主權原則對外抵御列強殖民、對內消除封建等級的民主進程,體現的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整體國民根基。隨著中華現代國家建構與建設,中國的社會結構與世界國際格局均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準確認識把握百余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多元一體”與“國民一體”的二維向度以及生成演進邏輯。鞏固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與保障國民權益相結合,已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時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