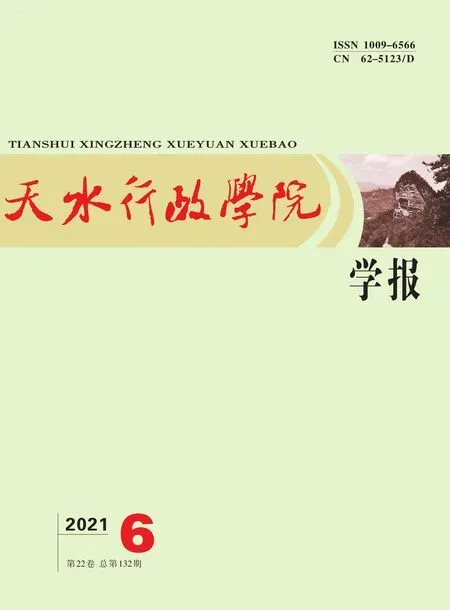《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形成的歷史背景與時代意義
賀奮清
(中共呂梁市委黨校,山西 呂梁 033000)
2021年2月20日,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于我們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要準確把握其中的主題、本質,正確評價和認識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兩個《決議》分別是:1945年4月20日,在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其中,1945年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最初起源于1941年“九月會議”,總結了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抗日戰爭爆發期間正面和反面的斗爭經驗,尤其是對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遵義會議這段歷史時期黨的領導路線的問題進行了批判性的審思,它的形成貫穿了延安整風運動的整個過程,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偉大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對歷史經驗科學總結的光輝典范。
一、《關于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形成的歷史背景
(一)1921年建黨到1945年這20多年中,黨內連續出現“一右三左”的錯誤
這些錯誤給中國共產黨、給革命事業帶來了重大損失,造成了思想認識上極大的混亂,尤其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使得革命事業陷入絕處。1935年召開的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會議解決了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但是由于形勢緊張,沒有全面解決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問題,沒有從根本上揭示出王明“左”傾錯誤思想的根源。這些錯誤思想又繼續表現在抗戰初期,王明帶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抗戰高于一切”“一切經過、服從統一戰線”的指示,認為紅軍強調獨立自主不利于團結國民黨,不利于抗日這一右傾錯誤。
探究當時黨內出現的“左”、右傾錯誤的原因可以從內因外因兩個角度:
從內因角度分析: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粗淺,對中國的國情缺乏正確全面的認知,對中國革命規律的把握程度不高。從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時間比較短暫,當時介紹馬克思主義相關的著作不多,談論中國情況的更是少之又少,加上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就著手“立即從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無暇長期從事理論研究與斗爭經驗的總結。”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要深入學習理解馬克思主義,并在學懂弄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來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就顯得尤為困難,也難免會在革命實踐中出現錯誤。
從外因角度分析:唯共產國際至上。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初期的發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邁步幾乎是在蘇聯的扶助下實現的,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不管是南方的陳獨秀還是北方的李大釗的經濟收入大部分來源于教書、編輯的薪水還有稿費。在操辦完刊物后所剩無幾,對于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的支持顯得有心無力。中國共產黨的經濟窘迫可以從陳獨秀被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重金聘請律師才將其救出可以窺探一二。維經斯基到了中國后一開始就向陳獨秀提供經費支援,這樣中共才能開展各項活動。所以,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一直宣稱要獨立自主,但是如果不能依靠自己穩定地解決經濟問題,想要獨立也是一句空話。也就是說,經濟問題解決不了,那么要想有獨立的判斷是很困難的,而且由于中國共產黨年幼,在經費上依靠共產國際,就不可避免地在革命道路、革命理論、革命方式等方面很容易受到來自蘇俄的影響,不管對錯,一切由共產國際說了算,不得不服從莫斯科的指令,長此以往會形成“一切均借俄助”的依賴心理,按照蘇聯的方式來理解馬克思主義,有的人甚至把共產國際指示當作金科玉律,由此,中國共產黨失去研究、批判到最后形成符合自身的社會主義觀的可能,導致國內教條主義盛行。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的20多年出現的“左”的或者右的錯誤,表面上是由于當時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粗淺、唯共產國際至上,究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思想認識方面的問題。思想認識、思想路線不同,世界觀也不同,認識和看待事物的態度也不同。如果不從根本上深挖這些錯誤的根源,在之后的歷史進程中就可能會犯過去相似的錯誤。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在革命中出現的“左”的或者右的錯誤都是由于沒有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沒有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僵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在這種情況下,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成為當務之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認識到這一點,清楚理論上的清醒是政治上堅定的有力保障和重要前提。所以從1941年開始,我們黨開展了延安整風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黨史學習研究活動,使廣大黨員干部認清錯誤路線的實質,解決了全黨對馬克思主義認識不清、思想混亂的問題,這些實踐都為總結歷史經驗的《決議》的寫作與形成創造了條件。
(二)當時相對穩定的環境也為這次的整風運動提供了外部保障
延安在1937年到1946年沒有經歷大規模的戰爭,一直處在比較穩定的環境中,為中國共產黨集中力量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解決歷史問題,科學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提供了客觀條件。
《決議》是延安整風運動的結晶,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修改,它的形成經歷了長時間復雜的過程,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決議》通過檢討歷史問題,總結經驗,做出歷史決議,凝聚了全黨的思想,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時代再次回顧《決議》,從中吸取經驗,對今天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堅持問題導向,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重溫《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時代意義
(一)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思想路線的重要內容,是我們黨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上,毛澤東對實事求是作了解釋,指出要在對實際情況進行調查和研究的基礎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去解決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問題,這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決議》通過對中國革命北伐的勝利、土地革命的兩次勝利,大革命失敗、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兩次失敗的對比,從政治、經濟、組織、思想四個層面在揭示錯誤路線的基礎上,展示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與框架,解決了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突出了毛澤東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在實事求是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實事求是,我們就能興黨興國,違背就會誤黨誤國”。這是被實踐證明的真理。習近平指出,當前我們中國最大的實際是什么?是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必須要面對的事實,是認清形勢與制定政策的客觀的出發點。但是,實事求是基于的“實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就需要人們解放思想,認識做出相應的變化。當然,實事求是與解放思想不是割裂的,而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立與破的統一。客觀形勢在不斷的變化發展中,打開思想才能適應客觀形勢的變化,才能做到實事求是。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現在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段性特征。新發展階段的重要論斷是基于一定的客觀實際。一是2020年我國GDP總量上已經超過100萬億元,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強國。二是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國家。之所以能取得現在的成就,是我國實事求是,一步步走過來的。縱觀我國崛起之路,改革開放之初,剛打開國門,既缺資金,也缺人才,更不了解國際市場。所以,要想發展就必須大力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而當時可以與國外合作或交換的,主要是國內廉價的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我國當時就是實事求是,從低端制造業起步,從為全世界生產衣服、玩具、小家電等勞動密集型產品起步,一步步取得今天的成就。現在看來是低端產能,但是當時是最適合我國做的,先從最簡單的做起,由易到難。因此,一個人口眾多、底子薄弱的大國要想成長起來,必須臥薪嘗膽、韜光養晦。這符合實事求是,也符合量變的積累才能達到質變飛躍的客觀規律。三是我國已經完成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正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階段。以上變化都是判斷我國進入了新發展階段的客觀依據。習近平總書記在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基礎上提出了用新發展理念引領發展,在這個基礎上致力于構建新發展格局。
(二)堅持問題導向
《決議》在回顧歷史時,重點放在了失敗教訓方面,更加突出了《決議》發表的迫切性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際意義。恩格斯曾經說過“要獲得正確的理論認識,最好的道路就是從自身的錯誤中和痛苦經驗中學習。”[1]審視歷史的錯誤并對其根源進行剖析,提出了針對歷史上我們黨存在“左”的或者右的錯誤的解決方案,就是要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其實也體現了我們黨善于直面問題的勇氣,勇于解決問題的傳統。
問題是矛盾的表現形式,矛盾通過問題表現出來。對于客觀存在的問題,我們只能直面,不能在困難面前退縮。在“十四五”時期,在全面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征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多樣,這就更加需要我們堅持問題導向,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而中國共產黨解決問題的過程其實也是自我革命、批評與自我批評、自我斗爭的過程。其中,自我革命是自己給自己看病,自己給自己療傷,很多人認為不能理解,但是從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的歷史來看,中國共產黨做到了。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中國共產黨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不管是堅持問題導向,還是自我革命,自我斗爭,從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到習近平,都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執政的過程中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和革命性。2021年是建黨100周年,“千秋偉業,百年正是風華正茂”,中國共產黨不只是奮斗一百年的問題,最高理想是要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成就千秋偉業,永遠走在時代的前列,永遠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這就需要實事求是分析問題,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解決問題,勇于自我革命、自我批評,自我提高,這也是新時代重溫《決議》的意義所在。
(三)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決議》分析了主觀主義錯誤思想的表現以及根源,而主觀主義以教條主義為主要表現形式,在此基礎上指出教條主義根本上是從書本和狹隘經驗的視角理解馬克思主義。對于教條主義,毛澤東直言“教條主義實在比屎還沒有用”[2],教條主義按照“本本”出發,把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致使中國革命受到很大挫折,走了很多彎路。教條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大阻礙。正如毛澤東所言“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應該像是一道強制的命令一樣,簡單地從一個環境傳給另外一個環境,而是應該在另外一個環境中獲得再生。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就如同箭和靶的關系一樣,僅僅把箭拿在手里,不愿意放出去,不愿意去射中國革命這個靶,中國革命永遠不會勝利。”[3]這段話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要有的放矢,要結合實際本土化。正如恩格斯在1872年的《共產黨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的實際運用要隨時隨地以黨史的歷史條件為轉移。”[4]中國革命的成功需要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而不能一味地、簡單地照搬共產國際的指示,因為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不可能充分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如果照搬肯定會導致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出現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歷史進程,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階段,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新的時代內涵,使得馬克思主義這顆參天大樹展現出永恒的生機和活力。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必須要繼續發展、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要科學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對于馬克思主義到底是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的講話中提到,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提供的不是直接可以搬過去的教條,而是一種方法,是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絕對不能純粹地抓住馬克思、恩格斯的某個具體的論斷不放,攻擊一點,或者當作解釋一切問題的準則。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本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運用蘊含于其中的觀點和方法去分析和解決問題,這才是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鄧小平同志也指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5]。
總之,《決議》做到了邏輯與歷史的相統一,做到了正本清源,揭示了錯誤思想路線的根源,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在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偉大貢獻,實現了思想的統一,全黨達成了認同和實踐毛澤東思想的共識,正如后來鄧力群回憶說,“很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懸著的石頭落地了”,《決議》為之后七大的召開,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做了充分的準備,它的成功對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重大的借鑒意義,對于新時代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同樣有重大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