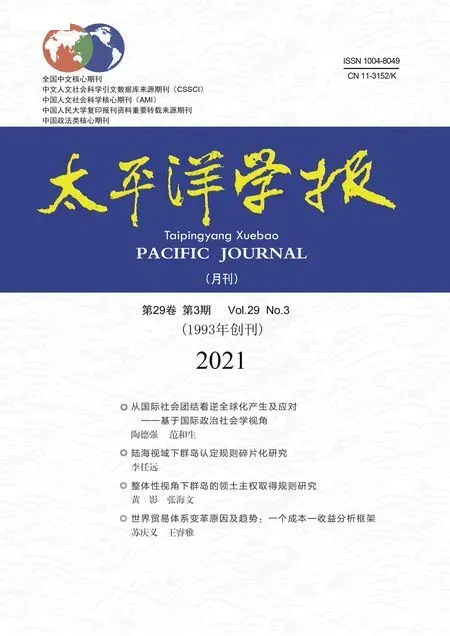21 世紀西方科學外交的內涵、概念、功能與困境
鄭澤民 鄧穎穎
(1. 海南師范大學,海南 海口 571158;2. 海南熱帶海洋學院,海南 三亞 572022)
進入21 世紀以來,“科學外交”(science diplomacy)日益成為國內外學界的研究議題,在語境上存在西方學界“科學外交”與國內學界“科技外交”在稱謂上的區別,但在具體含義上二者相同,本文基于主題需要,使用“科學外交”一詞。 在“科學外交”概念起源問題上,西方學界認為,雖然不清楚“科學外交”的概念是何時提出與首次使用的,但“科學外交”一詞的出現及學界對其予以研究是21 世紀以來的現象。①Vaughan Turekian,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Diplomacy,” Global Policy, Vol.9, Supplement 3, 2018, p.5.關于中國何時提出“科學外交”概念,一方面,時任科技部副部長馬頌德在2006 年、曾任中國國際科技合作協會會長吳貽康在2007 年曾先后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科技外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進展,②參見馬頌德:“對新時期科技外交的思考”,《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06 年第2 期,第5-11 頁;吳貽康:“關于科技外交的幾點思考”,《中國科技產業》,2010 年第 4 期,第 66-68 頁。但僅此仍難以得出中國在改革開放之時就已明確提出“科學外交”概念的結論。 另一方面,國內學界研究雖然有少量成果論及西方國家或韓國、印度科學外交動態,①參見趙剛著:《科技外交的理論與實踐》,時事出版社,2007 年版;王挺:“美、歐、日科技外交動向及啟示”,《科技導報》,2010 年第 6 期,第 19-25 頁;張翼燕、劉潤生:“日本科技外交的發展歷程與特點”,《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16 年第4 期,第 63-68 頁。但相關研究成果的落腳點主要集中在科學外交的中國視角上,②參見李世軍、吳嫻:“科技與總體外交的互動及我國的對策”,《科技進步與對策》,2006 年第 12 期,第 8-9 頁;王葆青:“中國科技軟實力與科學外交”,《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09 年第11期,第26-32 頁;王明國:“科技外交與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17 年第 7 期,第 40-47 頁。鮮有對西方科學外交的整體把握,尤其是其概念、內涵方面的理論探討。 基于此,本文擬在梳理西方科學外交發展、研究的基礎上,歸納科學外交內涵,嘗試界定科學外交概念,探討西方科學外交關注的領域與目標、面臨的挑戰與局限,最后,思考如何充分發揮科學外交積極作用及中國應對西方科學外交所帶來的挑戰。
一、西方科學外交的提出與發展
科學外交是西方國家政府、學界和其他社會行為體復雜相互作用的表現形式,是政策研究和外交事務等部門跨領域發展的結果,③Birte F?hnrich, “Science Diplomacy: Investigating the Perspective of Scholars on Politics-science Collabo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Public UnderstSci, Vol.26, No.6, 2017, p.688.與西方學界的推動和研究密切相關。
1.1 西方科學外交的發展
進入21 世紀后,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開始有意識地推行“科學外交”。 美國政府與科學界合作,陸續在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就高等教育、健康、環境、水、能源和農業等領域開展科學合作。④See “U.S.-Iraq Higher Education Partnerships Program,”International Research & Exchanges Board, June 10, 2020, https: / /www. irex. org/project/us-iraq-higher-education-partnerships-program; “Under Secretary Paula Dobriansky Leads Senior U.S. Delegation to Libya:An Effort to Bui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U.S.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0, 2006, https:/ /2001- 2009.state.gov/r/pa/prs/ps/2006/68783.htm; Edward W. Lempinen, “ Syria - U. S.Science Diplomacy Yields Agreement to Seek Collaboration in Water,Energy, Agriculture and Other Field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March 23, 2009, https: / /www.aaas.org/news/syria- us - science - diplomacy - yields - agreement - seek -collaboration-water-energy-agriculture-and.2008 年,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設立科學外交中心,旨在發揮科學家在官方政治關系有限的地方發揮重要國際聯系的關鍵作用,⑤Vaughan Turekian,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Diplomacy,”Global Policy, Vol.9, Supplement 3, 2018, p.6.成為美國科學外交的主要推動力量。 該中心的成立及之后召開的“關于科學外交的專題討論會”被認為對美國開展科學外交具有“統一認識”的意義。⑥孫孟新:“美國科學外交中心成立的啟示”,《科技導報》,2009 年第 22 期,第 125 頁。此后,美國科學促進會多次召開科學外交年度會議,發布年度報告,主辦各種類型的科學外交活動,與各國、各地區開展公共衛生等領域的合作。⑦張麗、蘇麗榮:“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科學外交的回顧與啟示(2008—2017 年)”,《今日科苑》,2019 年第 4 期,第 78-84 頁。2009 年6 月,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在埃及開羅大學演講,提出與伊斯蘭國家和地區開展科學合作,⑧“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Cairo University,”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June 4, 2009, https: / /obamawhitehouse.archives. gov/the - press - office/remarks - president - cairo -university-6-04-09.這是美國政府開展科學外交的重大宣示。 在美國推動科學外交的同時,英法德等西方發達國家也相繼制訂規劃和政策發展科學外交。 而歐盟在其成員國的推動下也于2016 年發布《歐洲愿景:開放創新,開放科學,開放世界》(Open Innovation, Open Science, Open to the World: A Vision for Europe)文件,⑨European Commission, “Open Innovation, Open Science,Open to the World: A Vision for Europe,” The European Union, May 30, 2016, https:/ /ec.europa.eu/digital- single - market/en/news/open-innovation-open-science-open-world-vision-europe.將科學外交上升到地區政策層面。
政府與學界合作開展科學外交推動了西方學界科學外交研究的熱潮。 西方學界認為,雖然其時未有“科學外交”之名,但美國和世界都有悠久的科學外交歷史。 一方面,美國有任命科學家外交官開展科學外交的傳統,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創立了美國科學外交。 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圍內,科學與外交也密切相關。 西方學界的研究將科學外交源頭追溯到中東地區古埃及與赫梯兩個王國之間的交流,延伸到古希臘羅馬、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殖民擴張時期,以及科學家幫助發明的戰爭技術導致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西方學界還認為冷戰期間科學外交盛行,特別是美蘇、中美等大國之間簽署的系列雙邊科學合作協議。
隨著實踐的增加,西方學界不斷拓展科學外交的范疇。 有學者認為,全球性問題和挑戰推動科學因素進入全球政策議程,使科學外交從作為服務國家軟實力和利己主義的工具轉變為全球治理工具,進而提出全球外交中的科學(Science in Global Diplomacy)、全球科學外交(Diplomacy for Global Science)、全球外交的全球科學(Global Science for Global Diplomacy) 概念。①Luk Van Langenhove, “Global Science Diplomacy for Multilateralism 2.0,” AAAS, December 29, 2016, http: / /www.sciencediplomacy. org/article/2016/global - science - diplomacy - for -multilateralism-20.也有學者使用“國際科學外交”(International Science Diplomacy)概念,認為解決全球性問題需要國際科學外交協調不同的經濟和社會體系,以及不同的經濟成本和效益、信仰和基本價值觀。②William R. Moomaw, “Science Diplomacy: Hard-Won Lessons,” AAAS, October 10,2017,http:/ /www.sciencediplomacy.org/hard-won-lessons.可見,無論“全球科學外交”還是“國際科學外交”,都可以被認為是科學外交的升級版,著眼于解決全球性問題和挑戰,將科學外交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1.2 西方科學外交的維度劃分
鑒于科學外交的新興屬性及其內容的廣泛性,西方學界對科學外交存在三種不同的維度劃分。 其一,“三維”劃分。 2010 年美國科學促進會和英國皇家學會共同發表一份名為《科學外交的新前沿:駕馭不斷變化的力量平衡》(New Frontiers in Science Diplomacy: Navigating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的研究報告,將科學外交分為三個方面,分別是外交中的科學(Science in Diplomacy),即為外交政策目標提供科學建議;科學外交(Diplomacy for Science),即促進國際科學合作;外交科學(Science for Diplomacy),即以科學互動和合作為工具改善國家間關系。③“New Frontiers in Science Diplomacy: Navigating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The Royal Society, January12, 2010, https:/ /royalsociety.org/topics-policy/publications/2010/new-frontiers-science-diplomacy/.該報告對科學外交的這一界定與分類在一定程度上可視作科學外交的一個連續過程,即一國為實現某一外交政策目標,通過“科學”參與外交行動或進程,推動國際科學合作,最后達到預定目標。
其二,“二維”劃分。 這是指按照上述分類方式將科學外交分為兩個方面,科學外交與外交科學,前者指以國際為導向的科學治理;④Birte F?hnrich, “Science Diplomacy: Investigating the Perspective of Scholars on Politics-Science Collabo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Public Underst Sci, Vol.26, No.6, 2017, p.690.后者指科學參與外交事務以支持外交政策,促進國際范圍內的經濟、安全、發展或環境目標。⑤Eugene B. Skolnikoff,“The Political Role of Scientific Cooperation,” Technology in Society,Vol.23,Issue 3,2001,pp.461-471.與上述“三維”相比,“二維”分類更強調科學外交的“國際”范疇,“外交中的科學”可能被看作為開展“科學外交”與“外交科學”提供建議的國內過程。 此外,“二維”分類不僅局限于緩和國家間關系,而且更著眼于達到國內、國際范圍綜合性的利益目標。
其三,從國家、跨境、全球三個層面的需求進行分類。 這種分類將科學外交劃分為直接促進國家需求的行動、解決跨境利益的行動,以及為滿足全球需求與解決挑戰而采取的行動三類。⑥Vaughan C. Turekian, Peter D. Gluckman, Teruo Kishi, and Robin W. Grimes, “Science Diplomacy: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from the Inside,” AAAS, January 16,2018, http:/ /www.sciencediplomacy.org/article/2018/pragmatic-perspective.與前兩種更多地體現科學外交概念性、過程性的分類性質不同,此一劃分更清晰地反映了科學外交的動機與指向,實踐性可能更強。因為即便是在西方學界所界定的科學外交的升級版中,各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科學外交的決策過程,仍然根據本國利益評估擬議的行動。
二、科學外交的內涵與概念
西方科學外交的發展是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實踐的結果,隨著西方學界研究的推進,科學外交的內涵、概念也在不斷深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科學外交是一種外交敘事和思考工具。 冷戰結束后,西方發達國家面臨新的國際環境,特別是美國霸權面臨著困境,急需改善形象。 西方學界認為,科學在政治中具有中性化特征,重視科學網絡和證據在外交活動中的作用,①Luk Van Langenhove, “Science Diplomacy: New Global Challenges, New Trend,” RSIS, April 12, 2016, https:/ /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6/04/CO16082.pdf.用于反思和塑造科學與政策之間的關系,能夠使不同領域的決策者之間實現共同的科學理解,從而為西方國家外交政策提供辯護,有利于形象改善。 在此基礎上,西方學界不斷拓展“科學外交”的內涵、外延,將“科學”因素賦予相關重要歷史事件或進程之中。 隨著全球性、區域性挑戰的增加,西方學界又賦予全球、區域治理等方面的外交政策更多科學意義。
其二,科學外交是一種外交政策工具。 一方面,西方學界認為,在理論上,科學外交是用某種方式限定某些政策,②Ibid.強調國際科學合作支持外交的作用,表現為大國將其文化和影響力投射到其邊界之外的愿望,在知識的獲得、利用、傳播過程中通過科學方法代表自身及其利益。③Vaughan C. Turekian, Sarah Macindoe, and Daryl Copeland, et al, “The Emergence of Science Diplomacy,” Worldscientific, http:/ /www. worldscientific. com/doi/suppl/10. 1142/8658 /suppl_file/8658_chap01.pdf, 訪問時間:2020 年 5 月 12 日。另一方面,在實踐中,美國政府創造了“科學外交”這一術語并且是系統地將“科學”應用于外交政策的國家之一,④Birte F?hnrich, “Science Diplomacy: Investigating the Perspective of Scholars on Politics-Science Collabo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Public UnderstSci, Vol.26, No.6, 2017, p.688.眾多“科學”項目、機構、“基金會”被美國用作科學外交的執行工具,如21 世紀之前就已存在的富布萊特項目(Fulbright Program)、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的國際科學基金會(ISF)等。 21 世紀初以來,美國政府又設置了科學顧問、科學特使等政府職位及科學技術基金,建立科學事業中心,通過這些舉措推動科學外交。 2012 年美國科學促進會《科學與外交》創刊,標志著美國主流社會認識到科學外交在發展科技和國家間關系方面的重要作用。⑤王明國:“科技外交與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17 年第 7 期,第 41 頁。可見,西方國家的科學外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反映了其政策工具特性。
其三,科學外交是一種外交實踐。 西方學界將西方國家政府在21 世紀之前的相關外交行動或進程的“科學”敘事,即科學外交作為一種外交實踐的表現,但西方學界對是否存在“科學外交實踐”分歧較為嚴重。 一種觀點提出,科學外交在工業化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外交實踐中已廣泛存在。⑥同④, 第 688-689 頁.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科學外交本身仍然是一種定義不清的東西,游離于國際關系主流外交實踐之外,新興的證據很少,⑦“Lecture on ‘New Frontiers in Science Diplomacy’ by Professor Daryl Copeland,” IIASA, April 11,2018, https:/ /iiasa.ac.at/web/home/about/events/180411-Copeland.html.大多數多邊組織缺乏專業科學知識,科學技術很少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突出或明顯的作用,科學可以幫助解決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或至少部分沒有得到解決。⑧Daryl Copeland, “ Wh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t Become Priorities for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AAS,July 29, 2015, http:/ /www.sciencediplomacy.org/perspective/2015 /bridging-chasm.西方學界這種對是否存在科學外交實踐的分歧,其實是對是否存在科學外交政策及其有效性的爭論,質疑的一方懷疑科學外交政策的效用,甚至否定存在科學外交政策本身,某種程度上說明他們認為科學外交還不是一種國家正式推行的外交政策,僅是一種實踐或探索的認知。
其四,科學外交是一種國際科學合作。 西方政府的主流實踐與學界的研究都表明科學外交是一種有政治目的的國際科學合作,是國際科學合作的表現形式之一。 然而,也有西方學者將著眼于科學本身的進步,或將涉及商業利益的一般性國際科學合作納入科學外交范疇。實際上,由于西方科學外交概念及實踐的演變,有學者將科學外交定義為科學合作和參與,推動與外國政府和社會建立積極的關系,①Vaughan Turekian and Kristin M. Lord, “The Science of Diplomacy,” Science, 2000,Vol. 288, Issue 5469, p. 1151.表現為從支持外交發展到支持科學研究與合作。 因此,在西方學界的研究話語下,其他形式的國際科學合作日益進入科學外交研究的視野。
雖然西方學界對科學外交的論述不斷深化,但對于何為科學外交,并沒有相對一致的看法,除了前文提及的對科學外交的一些概括性描述之外,還有兩種被廣泛引用的定義,一種定義指將科技合作、協作與交流作為工具,構建具有建設性的國際關系,②Albert O. Edwards, “Conscience Sans Science: Staging Science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CSPC, June 20, 2017,http:/ /www.thepresidency.org/storage/Fellows2011 /Edwards_Austen-_Final_Paper.pdf, 轉引自:王明國:“科技外交與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17 年第 7 期,第 40 頁。另一種則認為科學外交是利用國家間的科學合作,解決21 世紀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并建立建設性的國際伙伴關系。③Nina V. Fedoroff, “Science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Cell, Vol.136, No.1, 2009, p.9.這些描述和定義的總體特征是強調科學外交的不同側面,包括科學外交的目的、功能和形式等。 究其原因可能有三個方面:(1)科學外交相對來說是新生事物,無論政府還是學界,尚處在實踐和探索階段,有關科學外交的學術研究相當稀少。 (2)已有的研究成果存在泛化“科學外交”的傾向。 一方面,將凡是涉及科學因素或科學因素在其中發揮作用和影響的雙邊、多邊外交行動都歸入科學外交的范疇;另一方面,將一般性國際科學合作納入科學外交范疇,擴大了科學外交的邊界,增加了形成概念共識的難度。(3)科學外交的因果機制難以追溯與衡量。 由于科學外交并不局限于科學領域,更多的科學外交是體現在國家間政治、經濟及應對全球性挑戰等方面的外交行動或進程中,但前后相繼的事物或現象之間不必然存在因果聯系,多因一果的普遍性使被視作“科學外交”的行動或進程與其結果之間的直接因果聯系更加難以確定。
鑒于科學外交的新興性與復雜性,在形成科學外交概念時應注意三個方面:一是作為外交與國際關系領域的概念,科學外交首先應強調政治性,避免失去“外交”含義;二是應強調科學在外交中的主體性或關鍵性影響,避免涉及科學因素的外交行動或進程都納入科學外交范疇,防止科學外交泛化;三是需注意科學合作與交流對外交、國際關系和國家利益的結果性影響。 原本屬于一般性的科學合作交流,由于突發性事件或一方設置障礙而停滯甚至終止,必然損害另一國家的整體利益,放大了一般性科學合作交流在外交與國際關系中的影響,從而使這一進程具有政治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前兩點的查漏補缺。 基于此,可將科學外交概括為通過國家間的科學合作獲取科學知識、構建國家間關系、應對共同挑戰的一個外交領域和一種外交政策工具。 總體來說,科學外交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以科學為載體,具體表現為政府推動的各國科學主體之間的交流合作;二是以政治、經濟、氣候環境和公共衛生等外交領域為載體,科學在這些領域進程中或在其中某個環節發揮重要影響。
三、西方科學外交的關注領域與實現目標
西方發達國家提出科學外交首先是“外交”,但也注重“科學”,提升自身科學競爭力。隨著學界研究和政府實踐的增加,科學外交關注的領域不斷拓展,功能不斷深化,特別是在應對諸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性挑戰的議題時,科學外交話語更是占據了突出地位。
3.1 關注科學:促進科學進步
西方科學外交的主要動機并不是創造新知識(盡管并不排除這樣的結果),但國家間的科學競爭驅動各國在科學設備、知識產權和發現方面力爭成為第一。①“Scientific Drivers for Diplomacy,” AAAS, April 29, 2015,https:/ /www.aaas.org/programs/center-science-diplomacy/2015-scientific-drivers-diplomacy-resources.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加快科學發展,提升本國科學水平。其一,追蹤國際先進研究成果、發展方向。 無疑,這應是科學外交的基礎含義。 1723 年,英國皇家學會設置外交秘書一職,職責之一是確保學會成員及時了解科學領域的最新動態和研究成果。②“New Frontiers in Science Diplomacy: Navigating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The Royal Society, January 2010, https:/ /royalsociety. org/topics - policy/publications/2010/new - frontiers -science-diplomacy/,訪問時間:2020 年 6 月 12 日。其二,吸引、聯絡科學人才。 例如,英國諾貝爾獎得主弗雷澤·斯托達特爵士(Sir Fraser.Stoddart)將英國在科學方面的成就歸功于從世界各地招募人才;美國則明確表示要將高質量的研究留在本國。③Stefano Lami, “Challenges and New Requirements for International Mega-Science Collaborations,” AAAS, June 27, 2017, http:/ /www.sciencediplomacy.org/article/2017/mega-science-collaborations.其三,獲得并利用資金、科研設備和信息資源。 較為典型的例子是智利借助國際合力建設阿塔卡馬大型毫米/亞毫米陣列(ALMA)無線電天文綜合中心,大大推動了智利天文學的發展。④Gabriel Rodríguez García-Huidobro, “ Chile: Global Astronomical Platform and Opportunity for Diplomacy,” AAAS, June 29,2017, http:/ /www. sciencediplomacy. org/perspective/2017 /chile -global-astronomical-platform.新西蘭政府對澳大利亞同步加速器的投資反映了科學研究對設備能力的需求。⑤Vaughan C. Turekian, Peter D. Gluckman, TeruoKishi, and Robin W. Grimes, “Science Diplomacy: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from the Inside,” AAAS, January 16,2018, http:/ /www.sciencediplomacy.org/article/2018/pragmatic-perspective.
第二,參與大型國際科學合作項目,共享資源,共擔成本與風險,促進科學發展。 科學研究已經進入跨國界、大項目和高成本的時代,對更復雜、更昂貴的設備和專業知識的需求不斷增加,成本和風險不斷增加,一國難以獨力承擔。因此,大型科學研究項目要求全球科學界協調推進,盡可能多地開展互補性的項目合作,確保對基礎科學提供長期支持。
3.2 關注外交:緩和、改善國際關系
改善國家間關系是西方國家為科學外交設定的主要目標之一,這也是推動科學外交最初的動機,其主要表現包括:第一,國家之間恢復和建立信任。 “二戰”及隨后國際格局的演變,國家間信任深受侵蝕,推動科學合作成為改善國家間關系的重要途徑。 例如,1954 年西歐成立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推動了“二戰”后歐洲國家之間的對話;1961 年美日建立科學合作委員會,修復兩國知識界的關系等。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后,科學交流合作一直是雙方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 1979 年中美簽署《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建立中美科技合作聯委會機制,在奧巴馬執政時期,中美設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探討促進兩國青年研究人員互動途徑,推動了中美關系的發展。
第二,促進東西方關系緩和。 冷戰前期,美蘇科學外交的主要形式是美國國家科學院與蘇聯科學院之間的項目交流訪問,冷戰后期則達成了大規模、正式的政府間科學協議和項目。20 世紀80 年代,美國國家科學院和蘇聯科學院的專家小組定期舉行的“二軌”外交會議,促成美蘇雷克雅未克峰會并達成《中程核力量條約》。⑥William Colglazier, “War and Peace in the Nuclear Age,”AAAS, January 19,2018,http:/ /www.sciencediplomacy.org/editorial/2018/war-and-peace-in-nuclear-age.進入21 世紀后,為超越政治分歧,緩和中東地區局勢,促進合作,西方發達國家的相關科學學會發起“科學前沿:中東的研究和教育”論壇,召集中東15 國科學代表參與討論科學與教育問題。⑦Morton Z. Hoffman and Zafra M. Lerman, “The Malta Conferences: Fostering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s towar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ACS, September 2, 2015, https: / /pubs.acs.org/doi/pdf/10.1021/bk-2015-1195.ch008.而2015 年伊朗核協議的簽署被西方學界認為是利用科學外交手段減少美伊沖突的里程碑。⑧William Colglazier, “War and Peace in the Nuclear Age,”AAAS, January 19, 2018, http: / /www. sciencediplomacy. org/editorial/2018/war-and-peace-in-nuclear-age.此外,美國與伊朗開展地震科學和食源性疾病等領域的科學合作、美英與朝鮮的“白頭山地質科學研究”項目、美國與古巴在加勒比海海洋科學和傳染病威脅等議題上的接觸等過程,也都被西方學界視為利用科學外交維系西方發達國家與其“敵對”國家之間關系的紐帶,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雙方之間的關系。
第三,緩和領土與海洋權益爭端并加強跨界合作。 例如,加拿大與丹麥聯合收集、解讀關于格陵蘭島和埃爾斯米爾島北部海床數據的合作研究項目帶來了地緣政治和科學利益。①Elizabeth Riddell- Dixon, “Canada’ s Arctic Continental Shelf Extension: Debunking Myths,”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39, No.4, 2008, pp.343-359.北極周邊國家研究人員合作出版的第一部北極地質綜合地圖集,對有爭議的權利主張產生了積極影響。②“New Frontiers in Science Diplomacy: Navigating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The Royal Society, January 2010, https:/ /royalsociety. org/topics - policy/publications/2010/new - frontiers -science-diplomacy/,訪問時間:2020 年 6 月 12 日。此外,西方學界認為南海也存在科學外交實踐,成功的例子包括南海潛在沖突管理研討會等。③James Borton, “Science Diplomacy and Dispute Manage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Jonathan Spangler, Dean Karalekas, and Moises Lopes de Souza,eds.,Enterprises,Localities, People,and Poli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ritical Studies of the Asia-Pacific,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17, p.205.在跨界合作方面,主要涉及跨界生態系統和共享資源的管理,以及技術、安全標準,包括食品安全評估、藥品監管和工業標準等技術服務。
3.3 關注全球性挑戰:尋求共同利益,實現可持續發展
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增加。 一方面,氣候、環境、海洋和公共衛生等公共領域與公共空間治理構成了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其跨界性與全球性使確定國家利益的方式和領域不再局限于領土內,而要求各國通過科學方法合作應對;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快速進步對主權、安全、經濟與社會發展等領域帶來了不同于傳統因素所產生的全球性挑戰,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全球氣候變化及與之相關的環境、衛生等公共領域的治理。 科學技術對解釋這些領域挑戰的起因與尋找解決辦法具有決定性影響。 通過科學交流把重點放在超越政治壓力的關鍵挑戰和項目上,有可能為這些共同挑戰提出全球性解決方案。 西方學界將《蒙特利爾議定書》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視為國際社會進行科學外交、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典型事例,將2015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視為科學外交應對公共領域治理的成果。
第二,諸如公海、北極中心和南極等公共空間的治理。 西方學界認為,公海治理的矛盾源于各國都試圖爭奪國家管轄范圍之外的海洋和負責任地管理海洋、可持續開發海洋資源、更有效地利用海洋空間之間的沖突。④Jan-Stefan Fritz, “Observations,Diplomacy,and the Future of Ocean Governance,” AAAS,December 14,2016,http:/ /www.sciencediplomacy.org/article/2016/observations-diplomacy-and-futureocean-governance.南北極治理也是科學外交關注的重要內容,南北極科學外交已有成果和項目運行,如《南極條約制度》(ATS)的形成過程與運轉、“泛北極選擇”(Pan-Arctic Option)項目、國際極地年(IPY)活動等。但是,氣候變化帶來的后果與周邊國家對南北極領土或海洋權利提出的要求,仍可能激化周邊國家之間以及周邊國家與該地區以外國家之間的矛盾,如何進行管理仍然是問題。⑤“New Frontiers in Science Diplomacy: Navigating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The Royal Society, January 2010, https:/ /royalsociety. org/topics - policy/publications/2010/new - frontiers -science-diplomacy/,訪問時間:2020 年 6 月 12 日。
第三,科技革命帶來的全球性治理挑戰。科技革命與產業調整相互促進的深入,催生了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形態的發展,為全球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1)互聯網在政治上拓展了國家主權邊界、個人權利內涵,為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權力再分配和秩序的重建提供了新的驅動;⑥郎平:“國際互聯網治理:挑戰與應對”,《國際經濟評論》,2016 年第 2 期,第 131 頁。人工智能弱化了民族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影響,⑦吳雁飛:“人工智能時代的國際關系研究:挑戰與機遇”,《國際論壇》,2018 年第 6 期,第 39 頁。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霸權使技術水平較低的國家在產業發展、信息控制等領域的主權和安全面臨威脅。①趙駿、李婉貞:“人工智能對國際法的挑戰及其應對”,《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2 期,第12 頁。(2)互聯網在經濟與社會形態上加快了各國傳統產業和社會組織的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人工智能重構了人類的社會組織形態,重塑了全球社會經濟活動方式;②封帥:“人工智能時代的國際關系:走向變革且不平等的世界”,《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8 年第 1 期,第 129 頁。物聯網及其應用涉及數據的使用、收集和存儲,對商業分析和其他人類活動領域產生影響。③魏怡然:“物聯網數據保護的法律問題與歐盟相關立法的新發展”,《社會治理法治前沿年刊》,2018 年第1 期,第44 頁。在此背景下,如何既維護各國主權與安全,促進經濟轉型發展,推動社會組織形態平穩演化,又引導各國相互協作,深化全球科技治理,是科學外交面臨的緊迫問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科學方面的優勢,面對科技革命帶來的全球性治理挑戰,西方發達國家雖然也強調通過多邊和國際科學合作應對,但側重于技術方面的治理與監管。 西方科學外交強調,絕對的和排他的國家主權開始衰落,或認為國家主權是一個動態的概念,突出“人權甚于主權”,這就為科學外交的興起提供了動力,④See Vaughan C. Turekian, Sarah Macindoe, and Daryl Copeland, et al, “The Emergence of Science Diplomacy,” Worldscientific, http:/ /www. worldscientific. com/doi/suppl/10. 1142/8658 /suppl_file/8658_chap01.pdf, 訪問時間:2020 年 5 月 12 日;William Colglazier,“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Catastrophic Failures of the Science-Policy Interface,” AAAS,April 9,2020,http:/ /www. sciencediplomacy. org/editorial/2020/response - covid - 19 -pandemic-catastrophic-failures-science-policy-interface.西方學者還認為,科學外交的任務是要預測科技快速發展的影響,就科技可能對社會產生的破壞性和變革性影響提供建議,最大限度地緩和技術進步帶來的挑戰,使機會最大化和負面影響最小化。⑤William Colglazier, “Science Diplomacy and Future Worlds,”AAAS, September 13,2018, http:/ /www.sciencediploma cy.org/editorial/2018/science-diplomacy-and-future-worlds.西方發達國家對科技革命帶來的全球治理挑戰的認識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僅將其視為技術性問題來應對而忽視科學水平較低的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安全關切也反映了西方發達國家利用科學霸權侵犯后者主權、安全甚至干涉內政的一面。 例如,美國制定的所謂“清潔網絡”計劃的本質是借網絡安全之名,行“網絡監控”之實。⑥魯傳穎:“‘清潔網絡’計劃危害網絡安全”,《人民日報》,2020 年 11 月 12 日,第 3 版。
四、西方科學外交面臨的挑戰與局限
科學外交有其合理性,有利于維護和平環境,促進國家間關系發展,推動科學合作,應對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問題等。 然而,現實中科學外交面臨著諸多挑戰與局限,主要表現如下。
4.1 客觀現實與傳統政治制約
科學外交作為國際政治中的新興事物,其作用的發揮面臨諸多因素的制約。 其一,科學外交本身的復雜性。 這種復雜性包括全球性問題、區域性挑戰原因的多樣性;解決這些挑戰所需的戰略和規劃的優先次序;各國優先戰略目標與利益的差異;科學和外交兩個不同領域、不同專業之間的互動與協調;大型科學研究項目的全球化與其治理機制的滯后性等,都制約了科學外交作用的發揮。
其二,各國科學水平差異的挑戰。 科學外交涉及的科學合作過程要求參與國具備一定程度的科學知識。 然而,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落后,只是西方發達國家科學外交行為的被動接受者,不是平等的合作伙伴。 發展中國家的科學家往往發現自己處于助理或技術人員的角色。⑦Yekaterina Y. Kontar, Tom Beer, and Paul A. Berkman, et al, “Disaster-related Science Diplomacy: Advancing Global Resilien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s,” AAAS,July 27,2018,http:/ /www. sciencediplomacy. org/article/2018/disaster - related -science-diplomacy-advancing-global-resilience-through-international.在國際專利體系、氣候變化等涉及科學要素的治理領域的談判中,發展中國家的官員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⑧“New Frontiers in Science Diplomacy: Navigating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The Royal Society, January 2010, https:/ /royalsociety. org/topics - policy/publications/2010/new - frontiers -science-diplomacy/,訪問時間:2020 年 6 月 12 日。與此同時,科學水平差異還導致關于“互利互惠”問題的爭論,這一般發生在科學水平相近、具有競爭性質的國家之間,如冷戰時期的美蘇。 隨著美國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互利互惠”開始進入美國對華“科學外交”的視野。 美國政府認為,“與中國的科學合作交流改變了且還在繼續改變中國的科學技術,而中國對美國的利益和原則卻不認同”。①“美中雙邊關系:歷史的教訓”,美國駐華大使館,2019 年12 月 27 日,https:/ /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u-s-chinabilateral-relations-the-lessons-of-history-zh/。科學合作本身即互利互惠的體現,美國要求的“互利互惠”實質是利用自身科學優勢謀取單方面利益,并非真正的互利互惠。
其三,傳統政治的制約。 一方面,作為一種外交政策工具,科學外交的最終目標是推進國家利益。 因此,科學合作項目要獲得進展,首先需要各國國內科學顧問和外交官員同意,確保為應對全球性挑戰而制訂的科學解決方案符合他們各自所屬國家的利益。 即便是以科學進步為目的、無政治性或政治性不太強的大型國際科學合作項目,參與合作的各國科學家個人或科學團體仍然代表各自國家戰略,側重于國內科學利益。②Amy K. Flatten, “Global Research Infrastructures: A Decade of Science Diplomacy,” AAAS, September 27, 2018, http:/ /www.sciencediplomacy.org/perspective/2018/global-research-infrastructuresdecade-science-diplomacy.另一方面,國家間傳統政治關系制約科學外交的效果和影響。 國家間的制裁、禁運、簽證規定、數據流向、領土爭端乃至突發性事件等因素往往使科學合作流于形式或終止,使科學外交對國家間關系的調整、緩和效果有限,與傳統政治因素主導國家間關系的影響相比,不成比例,甚至忽略不計。 例如,隨著科學合作的結束,國家間先前存在的矛盾重新浮現,科學合作難以起到進一步緩和關系的作用。 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科學外交頻繁,美伊(朗)、美朝之間都有科學外交項目,但現實表明這些國家間的雙邊關系甚至“敵意”并未真正改善;存在領土主權、海洋劃界爭端的國家間也是如此,科學外交沒有改變各國的立場。
4.2 科學外交是西方發達國家追逐國家利益的工具
作為一個外交領域和一種外交政策工具,科學外交無疑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西方發達國家也不例外,具體表現如下。
其一,科學外交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影響國際政治議程的工具。 西方學界認為,科學是公共政策議程的決定因素。③“Scientific Drivers for Diplomacy,” AAAS,April 29,2015,https:/ /www.aaas.org/programs/center- science - diplomacy/2015 -scientific-drivers-diplomacy-resources.美國開展科學外交的初衷是,改變因入侵伊拉克而導致全球民眾尤其是伊斯蘭世界民眾對美國的負面看法,提升美國的海外形象,④Kristin M. Lord and Vaughan C. Turekian, “Time for a New Era of Science Diplomacy,” Science, Vol.315, Issue 5813, 2007,p.769.而通過科學因素參與外交,利用科學優勢影響、設置政治議程,有助于達到這個目的。 例如,2014 年,美國政府啟動有40 多個國家參加的致力于傳染病的預防、發現和應對的《全球衛生安全議程》(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⑤Matthew Lim and David Blazes, “Collateral Duty Diplomacy,”AAAS, September 21, 2015, http:/ /www.sciencediplomacy.org/article/2015/collateral-duty-diplomacy.2016 年,美國啟動外交部長科學技術顧問網絡(FMSTAN),包括塞內加爾、阿曼、波蘭等發展中國家紛紛尋求加入。⑥Vaughan Turekian,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Diplomacy,”Global Policy, Vol. 9, Supplement 3, 2018, p.7.
其二,科學外交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影響他國內政外交的工具。 知識和權力聯系在一起,為權力運行提供便利。⑦Lars ?hrstr?m,Peter Weiderud,Morsy Abu Youssef,and O-mar M. Yaghi, “Global Engagement in Science: The University’ s Fourth Mission?” AAAS, August 3, 2018, http:/ /www.sciencediplomacy. org/perspective/2018/global - engagement - in - science -universitys-fourth-mission.美國從一開始就視科學為影響他國內政外交的工具,通過各類“基金會”推出教育、科研資助項目,“培養”人才等方式影響所在國政策,甚至策動“顏色革命”。 21世紀以來,美國科學外交日益介入他國內政外交。 美國與中東、北非等發展中國家開展的衛生、教育等領域的科學合作,意圖通過科學協議、資助科學項目,影響這些國家民意輿論和內外政策走向,改變這些國家及其民眾對美國的敵視態度。 為應對俄羅斯在北極科學合作地理準入問題上日益強硬的立場,2009 年美國頒布新的北極地區政策,推動進入俄羅斯北極地區。①Baker Betsy, “Law, Science, and the Continental Shelf: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Promise of Arctic Cooperation,”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25, No.2,2010, p.271.近兩年來,美國以“科學”為名,意圖影響相關國家與中國的關系,損害中國形象,如不顧實際情況以所謂“科學報告”為依據就湄公河旱情攻擊中國。②參見“王毅談湄公河旱情”,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19 年 8 月 2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xgxw_682524/t1685608.shtml;“美國與東盟合作抗擊COVID-19,建設長期的適應能力,支持經濟復蘇”,美國駐華大使館網站,2020 年 4 月 24 日,https: / /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u-s-asean-partnering-to-defeat-covid-19-buildlong-term-resilience-and-support-economic-recovery-zh/。
其三,科學外交被西方發達國家用作地緣政治斗爭的工具。 西方科學外交并不脫離傳統地緣政治斗爭窠臼。 西方學界關于北極地區科學外交的敘事認為,北極科學外交起因于氣候變化與兩大地緣政治因素,包括冷戰后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政治斗爭與中國崛起帶來的全球化和權力轉移。③Michael Evan Goodsite, Rasmus Gjedss? Bertelsen, and Sandra Cassotta Pertoldi-Bianchi,et al, “The Role of Science Diplomacy: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of Arctic Research Stations under Conditions of Climate Change, Post-cold War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Power Transi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and Sciences, Vol.6, No.4,2016, p.646.在美俄北極科學合作過程中,由于烏克蘭危機,西方國家禁止向俄羅斯科學家提供旅行等相關資助。④See Eli Kintisch, “Cold War in a Warming Place: Can Eastern and Western Scientists Effectively Partner in the Arctic?” AAAS,December 12,2015, http: / /www.sciencediplomacy.org/article/2015 /cold-war-in-warming-place.此外,數十年來美軍一直在東南亞、中亞等地區實施公共衛生項目,原因之一在于這些項目有利于支持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及在相關地區軍事力量的前沿部署。⑤Matthew Lim and David Blazes, “Collateral Duty Diplomacy,”AAAS, September 21, 2015, http:/ /www.sciencediplomacy.org/article/2015/collateral-duty-diplomacy.近年來,美國倚仗其占據科學高地,視科學外交為其打壓、遏制中國的工具,在新冠肺炎疫情問題上攻擊中國,推動對華科技“脫鉤”,限制對華科技產品出口,企圖限制中國科學、產業發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國視中國為地緣“競爭對手”,擔心中國不斷增長的科學能力危及自身霸權。
以國家利益為指引是各國推動科學外交的應有之義,也有利于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 然而,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科學外交”幾乎完全以一己私利為導向,諸如通過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相關措施限制發展中國家創新,要求發展中國家同意不強制實施艾滋病藥物專利許可⑥Vaughan C. Turekian, Sarah Macindoe, and Daryl Copeland,et al, “ The Emergence of Science Diplomacy,” Worldscientific,http:/ /www.worldscientific.com/doi/suppl/10.1142 /8658 /suppl_file/8658_chap01.pdf, 訪問時間:2020 年 5 月 12 日。等。 這種對科學外交有利則為之、不利則廢之的工具性立場,使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的“科學外交”在結果上走向了科學外交目標的反面,損害了科學合作與發展,惡化了國家間關系,不利于應對共同挑戰,使科學外交對發展中國家乃至全球共同利益的意義變得無足輕重,甚至有害。
五、對科學外交的思考
雖然西方學界將科學外交的源頭追溯到古代,但科學外交應是全球化和科學發展共同作用的結果。 全球化是世界不斷相互加強聯系的一個過程,科學進步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 新技術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加之全球貿易、資金流動推動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一個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整體。⑦王和興:“全球化對世界政治、經濟的十大影響”,《國際問題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10 頁。全球化反過來又推動了科學的發展及其全球化,即科學全球化。 科學全球化是世界科學界在研究和科學發展領域加強聯系和相互依存的過程,表現為科學過程、能力和活動的同質性,是一種利用科學和技術進步促進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跨界能力,⑧Joseph Makhema, “Closing Keynote: Globalization and the Diplomacy of Science,”Journal of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Vol. XLI,No. 2, 2010, p.84.科學的全球化、國際化意味著知識、信息和技能成為發展的主要動力。⑨曉端:“布萊頓教授談全球化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1993 年第 9 期,第 65 頁。
科學全球化的表現及其作用為科學外交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冷戰結束和全球化進程的加深深刻地改變了全球政治環境,世界變得更小,聯系更緊密,國家主權受到侵蝕和國家內部沖突增多。 全球化造就的這種新環境帶來了眾多的問題,包括人與自然關系危機和人類內部關系危機,①李慎之:“迎接全球化時代——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五百年”,《瞭望周刊》,1992 年第 44 期,第 38 頁。解決這些危機和共同挑戰需要跨國界的科學技術的相互作用,要求打破科學和外交之間的界限,使科學在國際體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因此,一方面,全球化作為一種大趨勢,為科學外交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各國外交行為的方式方法、戰略戰術需要適應日益復雜的科學世界。 在此背景下,思考科學外交的未來發展極具現實意義。
科學外交作為一個外交領域和一種外交政策工具,既可以看作是科學因素在外交中發揮作用,為外交科學化、國際關系構建與治理提供新的驅動,也可以認為是外交借助科學影響打開新局面,緩和國家間關系、應對全球性挑戰。正如在各國科學外交實踐和學界研究中所看到的,科學外交在科學合作與科技水平提升、緩和國家間關系、應對共同挑戰方面有重要意義,值得進一步推進。 在推動科學外交的過程中,為避免西方科學外交的局限性,需堅持三個原則:一是堅持各國主權平等,共享科學合作成果。這不但有助于發展中國家更快提升科學水平,也為科學外交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 二是尋找各國利益的平衡點,聚焦共同利益。 在一個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社會里,外交追求利益、維護主權是應有之義,科學外交要通過“科學”尋求共同利益或尋求避免危及共同利益,尋求易于各國接受的利益平衡點。 三是堅持科學原則。 科學外交通過科學語言以一種容易理解的方式促進國家間交流,提升互信,如此才能充分發揮科學外交的積極影響,擺脫地緣競爭窠臼,推動科學外交得到廣泛認同,更好地應對共同挑戰,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學發展水平有了巨大提升,但與科學強國、大國相比仍有差距。 近年來,面對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以逆全球化、強化大國地緣競爭意識為特征的“科學外交”,中國在部分關鍵性科學領域的對外交流合作面臨阻礙。 對此,中國除國內加大研發投入、優化研發機制、培育科學人才,全力提升科學水平這一根本應對之道外,還需制訂、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適應新形勢的科學外交戰略、方向和重點。 第一,戰略上突出科學外交在總體外交中的地位。 科學外交是總體外交的一個方面,但與同屬總體外交的經濟外交、②經濟外交指為追求本國經濟利益而執行的對外交往行為,以及借助經濟手段為實現并維護自身戰略目標而執行的對外交往行為;經濟外交是財富與權力之間的相互轉化。 參見周永生著:《經濟外交》,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 年版,第22 頁;張曉通:“中國經濟外交理論構建:一項初步的嘗試”,《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3 年第 6 期,第 49 頁。軍事外交③軍事外交指以國家利益為核心、以國家戰略為遵循、以軍隊為主體、以軍事為主要領域,國家在對外交往中利用多手段維護安全利益、促進世界和平的行為、藝術及過程。 金燦榮、王博:“有關中國特色軍事外交理論的思考”,《太平洋學報》,2015 年第5期,第 18 頁。等領域的外交不同,科學外交兼具“硬實力”與“軟實力”雙重屬性,且不僅僅局限于科學領域,現實中更多地體現在其他領域或某個外交行動和進程中。 鑒于其重要性,制訂符合自身科學水平和國際社會現實需要與利益的科學外交戰略,凸顯科學外交在總體外交中的地位,有助于發揮科學外交優勢,更好地服務于國家利益。第二,加快科學外交“走出去”。 長期以來,受限于科學發展水平,中國“科學外交”主要聚焦于“引進來”,側重于從發達國家獲得先進科學技術。 隨著中國科學水平的提升,在以科學援外為主要內容的“走出去”方面也需逐步成為中國科學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過“走出去”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國際組織及各國科學主體的科學合作,推進科技創新,積極參與全球科技治理,構建自身的科學外交網絡,有助于實現科學外交目標。 第三,在科學外交方向上,注重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說明各國在公共空間、公共領域面臨的挑戰日益嚴重,發展中國家限于科學水平尤為如此,亟需國際社會提供科學外援,助力公共產品建設。 總體上,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宜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周邊和“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為主要平臺開展科學外交,主動應對西方發達國家“科學外交”帶來的地緣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