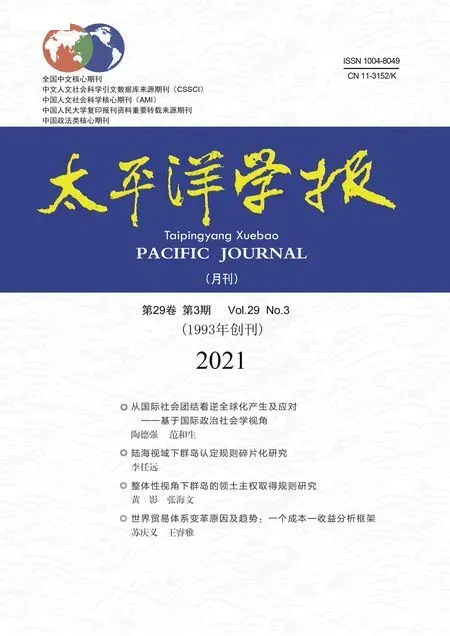從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看逆全球化產(chǎn)生及應(yīng)對(duì)
——基于國(guó)際政治社會(huì)學(xué)視角
陶德強(qiáng) 范和生
(1.安徽大學(xué),安徽 合肥 230601)
團(tuán)結(jié)問題歷來不容小覷。 盡管科勒斯(Avery Kolers)曾斷言,“過去二十年雖有出色著作問世,但在最近的政治哲學(xué)中,團(tuán)結(jié)一直是被嚴(yán)重忽視的問題”。①?gòu)垏?guó)清:“論人類團(tuán)結(jié)與命運(yùn)共同體”,《浙江學(xué)刊》,2020 年第1 期,第30 頁(yè)。然而隨著全球變暖、公共衛(wèi)生安全等問題的日漸突出,在全球化語境之下,團(tuán)結(jié)問題正在日益引發(fā)關(guān)注。 尤其是自英國(guó)“脫歐”和特朗普當(dāng)選以來,逆全球化②逆全球化即全球化逆流表現(xiàn),對(duì)此現(xiàn)象學(xué)界存在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三種表述。 其中,反全球化指反對(duì)全球化的觀點(diǎn)與行動(dòng),去全球化是制定規(guī)則與制度來限制全球化,而逆全球化強(qiáng)調(diào)出現(xiàn)否定全球化的負(fù)面行為并引起相應(yīng)指標(biāo)停滯或下滑的后果。 本文論述的逆全球化采用上文界定。 陳偉光、郭晴:“逆全球化機(jī)理分析與新型全球化及其治理重塑”,《南開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 年第 5 期,第 60-61 頁(yè)。浪潮正以風(fēng)起云涌之勢(shì)掃蕩全球,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正面臨新的考驗(yàn)。 因此有學(xué)者指出,團(tuán)結(jié)問題已成為21 世紀(jì)的最大問題。①李義天編:《共同體與政治團(tuán)結(jié)》,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85 頁(yè)。
逆全球化并非新生事物,“但是這次不同以往之處在于,曾一度是全球化主要推動(dòng)者的美英等西方國(guó)家,現(xiàn)在卻成了它的強(qiáng)烈反對(duì)者”,②周琪、付隨鑫:“美國(guó)的反全球化及其對(duì)國(guó)際秩存的影響”,《太平洋學(xué)報(bào)》,2017 年第 4 期,第 2 頁(yè)。這不得不令人深思。 對(duì)此,國(guó)際社會(huì)一方面思考團(tuán)結(ji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針對(duì)其何以出現(xiàn)展開反思。 聯(lián)合國(guó)將“團(tuán)結(jié)”寫入《千年宣言》,將其作為21 世紀(jì)處理國(guó)際關(guān)系的基本價(jià)值之一,國(guó)際社會(huì)“必須根據(jù)公平和社會(huì)正義的基本原則,以公平承擔(dān)有關(guān)代價(jià)和負(fù)擔(dān)的方式處理各種全球挑戰(zhàn)”。③2000 年9 月8 日,《聯(lián)合國(guó)千年宣言》經(jīng)聯(lián)合國(guó)大會(huì)第五十五屆會(huì)議第55/2 號(hào)決議通過,宣言內(nèi)容參見聯(lián)合國(guó)網(wǎng)站,https:/ /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55-2.shtml。前聯(lián)合國(guó)秘書長(zhǎng)潘基文(Ban Ki-moon)也指出,國(guó)際社會(huì)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必須堅(jiān)定倡導(dǎo)團(tuán)結(jié)和共同責(zé)任”。④“On International Day, Ban Urges Human Solidarity to Build New Sustainability Agenda,” UN News, December 20, 2014, https:/ /news.un.org/en/story/2014/12/486852-international-day-ban-urges-h(huán)uman-solidarity-build-new-sustainability-agenda.而關(guān)于逆全球化何以產(chǎn)生存在諸多分析,概括起來主要存在兩種取向:其一,從發(fā)達(dá)國(guó)家失利展開分析。 奧爾特曼(Roger C. Altman)、⑤Roger C. Altman, “Globalization in Retreat: Further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88,No.4, 2009, pp.2-7.博蓋吉克(Peter A.G. van Bergeijk)⑥Peter A.G. van Bergeijk, “One Is Not Enough! An Economic History Perspective on World Trade Collapses and De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March 29,2017, https:/ /www.iss.nl/en/news/one - not- enough - economic -h(huán)istory-perspective-world-trade-collapses-and-deglobalization-peter-ag.提出,逆全球化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經(jīng)濟(jì)危機(jī)之后的一種選擇;而克里希(Hanspeter Kriesi)也認(rèn)為,逆全球化是全球化贏家與輸家對(duì)立加劇的結(jié)果。⑦Hanspeter Kriesi, et 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Political Space: Six European Countries Compare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 45,No.3,2006,pp. 921-956.國(guó)內(nèi)學(xué)者鄭春榮將這一對(duì)立界定為結(jié)構(gòu)性分歧,認(rèn)為主要原因在于發(fā)達(dá)國(guó)家受損日益嚴(yán)重。⑧鄭春榮:“歐盟逆全球化思潮涌動(dòng)的原因與表現(xiàn)”,《國(guó)際展望》,2017 年第 1 期,第 34-51 頁(yè)。張剛生則著重圍繞發(fā)達(dá)國(guó)家成本收益、內(nèi)部貧富差距等,對(duì)此展開專門論述。⑨張剛生:“論美歐發(fā)達(dá)地區(qū)的逆全球化現(xiàn)象”,《國(guó)際觀察》,2020 年第 2 期,第 124 頁(yè)。其二,從全球化自身進(jìn)行分析。 卡魯納拉特納(Neil Dias Karunaratne)認(rèn)為,全球化具有“擴(kuò)散效應(yīng)”,經(jīng)濟(jì)繁榮會(huì)伴隨福利削弱等問題。⑩Neil Dias Karunaratne, “The Globalization-Deglobalization Policy Conundrum,” Modern Economy, Vol.55, No.3,2012, pp. 373-383.馬丁(Hans-Peter Martin)和舒曼(Harald Schumann)則明確表明,逆全球化根源于“全球化陷阱”。?[德]漢斯-彼得·馬丁、[德]哈拉爾特·舒曼著,張世鵬譯:《全球化陷阱》,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版,第297 頁(yè)。陳偉光、郭晴等國(guó)內(nèi)學(xué)者認(rèn)為,除了全球化發(fā)展引發(fā)的問題,發(fā)達(dá)國(guó)家內(nèi)部治理、民眾負(fù)面情緒等也是導(dǎo)致逆全球化的重要因素。?陳偉光、郭晴:“逆全球化機(jī)理分析與新型全球化及其治理重塑”,《南開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 年第 5 期,第58 頁(yè)。
總的來看,現(xiàn)有研究主要側(cè)重經(jīng)濟(jì)學(xué)分析路徑,社會(huì)學(xué)視野下的分析則鮮有論及。 對(duì)于逆全球化,目前的解釋主要借助經(jīng)濟(jì)理性,對(duì)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全球化中的行為變化展開分析。 盡管不可否認(rèn)利益因素的重要性,但是難免存在一些不足。 其一,在看到利益因素的同時(shí),卻淡化了文化、規(guī)則等因素在逆全球化中的作用。 其二,割裂了外部環(huán)境與內(nèi)部治理、利益追求與價(jià)值文化之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 由此在研究當(dāng)中,往往可以靜態(tài)地看到逆全球化的原因,卻難以更為深入地從前因后果方面對(duì)其展開一種動(dòng)態(tài)性的解讀。
受此影響,逆全球化與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往往被割裂看待。 一是逆全球化分析鮮有團(tuán)結(jié)話題,主要集中于歷史與演進(jìn)、表現(xiàn)與原因、風(fēng)險(xiǎn)與應(yīng)對(duì)等。?廖曉明、劉曉鋒:“當(dāng)今世界逆全球化傾向的表現(xiàn)及其原因分析”,《長(zhǎng)白學(xué)刊》,2018 年第 2 期,第 28-37 頁(yè)。二是團(tuán)結(jié)研究主要限于民族國(guó)家層面。 對(duì)于以“為民族國(guó)家的現(xiàn)代化服務(wù)”作為基本任務(wù)的社會(huì)學(xué)界而言,?文軍:“全球化與全球社會(huì)學(xué)的興起——讀科恩與肯尼迪的《全球社會(huì)學(xué)》”,《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shí)》,2001 年第 4 期,第87 頁(yè)。逆全球化則一直缺乏關(guān)注。 在此情形之下,本文關(guān)注的問題是: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是什么,具有怎樣的機(jī)理? 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中,逆全球化又是如何出現(xiàn)的? 就此問題展開探討,無疑是當(dāng)下國(guó)際政治社會(huì)學(xué)極具魅力的重要議題。
一、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與逆全球化浪潮
團(tuán)結(jié)即相互配合。 根據(jù)《現(xiàn)代漢語詞典》解釋,團(tuán)結(jié)既形容“齊心協(xié)力、結(jié)合緊密”,又表示“為了集中力量實(shí)現(xiàn)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務(wù)而聯(lián)合或結(jié)合”。①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語言研究所編:《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5版),商務(wù)印書館,2005 年版,第 1383 頁(yè)。一般而言,團(tuán)結(jié)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孔德(August Comte)、涂爾干(émile Durkheim)等經(jīng)典社會(huì)學(xué)家側(cè)重于團(tuán)結(jié)的廣義表達(dá),將其視為秩序與整合,而狹義的團(tuán)結(jié)則表示微觀層面的個(gè)體聯(lián)合。②Steinar Stjern?,Solidarity in Europe: The History of an Ide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5-41.可見,團(tuán)結(jié)的核心是聯(lián)合與配合,具有主觀意愿性和客觀共同性的雙重屬性。
隨著非國(guó)家行為體的國(guó)際社會(huì)活動(dòng)日漸活躍,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的主體存在一定爭(zhēng)議。 有學(xué)者認(rèn)為,伴隨國(guó)內(nèi)和國(guó)際事務(wù)處理能力的下降,“國(guó)家的時(shí)代可能將終結(jié)”。③[英]羅賓·科恩、[英]保羅·肯尼迪著,文軍等譯:《全球社會(huì)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1 年版,第117 頁(yè)。美國(guó)未來學(xué)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就曾直言,在全球化浪潮之下,“國(guó)家已經(jīng)壽終正寢”。④劉中民、田文林等著:《國(guó)際政治社會(huì)學(xué)》,軍事科學(xué)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2 頁(yè)。事實(shí)上,盡管國(guó)際組織、公民個(gè)人正逐步在國(guó)際社會(huì)嶄露頭角,但是國(guó)家在規(guī)范制定、機(jī)制創(chuàng)設(shè)和事務(wù)處理中的主導(dǎo)作用依然無可替代。 因此,本文認(rèn)同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的判定,國(guó)際社會(huì)是以國(guó)家為單位的。⑤孫興杰:“社會(huì)·國(guó)際社會(huì)·世界社會(huì)——三種國(guó)際關(guān)系史闡釋的視角?”,《史學(xué)集刊》,2009 年第 6 期,第 118 頁(yè)。基于此,本文將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界定成以國(guó)家為主體的團(tuán)結(jié),體現(xiàn)了“人類共同體為了促進(jìn)國(guó)際合作,愈合國(guó)際沖突與戰(zhàn)爭(zhēng)的創(chuàng)傷,消除民族國(guó)家之間的裂痕,戰(zhàn)勝人類貧窮和苦難做出的各種努力”。⑥張國(guó)清:“論人類團(tuán)結(jié)與命運(yùn)共同體”,《浙江學(xué)刊》,2020年第 1 期,第 35 頁(yè)。
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從來不乏破壞因素,逆全球化就是一個(gè)典型。 逆全球化即全球化的逆流表現(xiàn),與資本、生產(chǎn)和市場(chǎng)在世界范圍一體化的全球化進(jìn)程背道而馳。⑦Walden Bello, 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2, p.132.以單邊主義、貿(mào)易保護(hù)主義為集中表現(xiàn)的逆全球化,主要存在三個(gè)特點(diǎn):其一,全球性。 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是主流,其他國(guó)家也同樣存在。 其二,虛偽性。 “發(fā)達(dá)資本主義國(guó)家口頭上表示反對(duì)貿(mào)易保護(hù)主義,但實(shí)際上卻反其道而行之,只不過采取的貿(mào)易保護(hù)手段顯得更加隱蔽。”⑧廖曉明、劉曉鋒:“當(dāng)今世界逆全球化傾向的表現(xiàn)及其原因分析”,《長(zhǎng)白學(xué)刊》,2018 年第 2 期,第 29 頁(yè)。其三,復(fù)雜多樣性,手段與形式愈加多樣。 近年來,隨著希臘主權(quán)債務(wù)危機(jī)、英國(guó)“脫歐”、中美貿(mào)易摩擦等事件的爆發(fā),以“反自由貿(mào)易、反一體化”為特征的逆全球化正呈愈演愈烈態(tài)勢(shì)。 毫無疑問,逆全球化必然有悖于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 然而問題在于,在相互依存不斷深化、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日益加深之下,逆全球化卻能猶如幽靈一樣陰魂不散,這不得不令人深思。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逆全球化中扮演發(fā)起者的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作為全球化的主導(dǎo)者和最大受益者,⑨朱西周:“論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進(jìn)程中的國(guó)家”,《太平洋學(xué)報(bào)》,2005 年第 9 期,第 88 頁(yè)。卻同樣在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中發(fā)揮關(guān)鍵作用。 回答這些問題,必然要從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中找尋答案。
二、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的現(xiàn)有解釋及不足
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guó)際社會(huì)是工業(yè)革命后的產(chǎn)物,尤以世界經(jīng)濟(jì)和國(guó)際政治基本要素形成為標(biāo)志。⑩同④,第7 頁(yè)。究其原因,國(guó)際社會(huì)產(chǎn)生于民族國(guó)家交往之中,在此之前受叢林法則支配并無國(guó)際社會(huì)存在。?徐進(jìn):“國(guó)際社會(huì)的發(fā)育與國(guó)際社會(huì)核心價(jià)值觀的確立”,《國(guó)際安全研究》,2008 年第 5 期,第 4 頁(yè)。根據(jù)這一判定,有關(guān)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的研究,可以劃分為三個(gè)層面:
其一,從道德內(nèi)化層面分析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這種觀點(diǎn)注重道德、道義因素的分析,認(rèn)為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是道德內(nèi)化的結(jié)果。 19 世紀(jì)70 年代,面對(duì)普法戰(zhàn)爭(zhēng)和法國(guó)大革命帶來的社會(huì)混亂,涂爾干試圖從道德層面尋求解決之策。 在他看來,隨著分工發(fā)展,“機(jī)械團(tuán)結(jié)”將讓位于“有機(jī)團(tuán)結(jié)”,道德因素對(duì)于團(tuán)結(jié)的作用將日益顯著,人類將邁向一種超越民族國(guó)家的超級(jí)人類社會(huì),即“世界主義”道德團(tuán)結(jié)。 基于歐洲一體化,涂爾干設(shè)想“在這個(gè)國(guó)家之上,還有另一個(gè)國(guó)家正在形成,它將囊括我們的民族國(guó)家,它就是歐洲之國(guó)或人類之國(guó)”。①李義天編:《共同體與政治團(tuán)結(jié)》,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97 頁(yè)。同樣,霍耐特(Axel Honneth)認(rèn)為,團(tuán)結(jié)之所以產(chǎn)生,主要源于對(duì)諸如各類不尊重行為的道德義憤感。②同①,第201 頁(yè)。對(duì)于持這種觀點(diǎn)的學(xué)者而言,國(guó)際社會(huì)之所以團(tuán)結(jié),道德內(nèi)化作用極為重要。 對(duì)此有學(xué)者指出,雖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某種意義上,它忽視了道德源于現(xiàn)實(shí)生活這一事實(shí),難免存在“空洞”“抽象”的缺陷。③劉擁華:“道德、政治化與抽象的世界主義”,《社會(huì)》,2013 年第 1 期,第 80 頁(yè)。
其二,從制度規(guī)約層面論述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與前一種觀點(diǎn)不同,這種觀點(diǎn)注重從世界政治的制度與規(guī)范視角探討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 赫德利·布爾認(rèn)為,制度規(guī)則是國(guó)際社會(huì)的基礎(chǔ),基于制度規(guī)則,不同國(guó)家能夠形成團(tuán)結(jié)與合作。“當(dāng)一組國(guó)家意識(shí)到它們具有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價(jià)值觀念……認(rèn)為在彼此關(guān)系中受到一套共同規(guī)則的約束,并且一起運(yùn)作共同制度時(shí),國(guó)家社會(huì)(或國(guó)際社會(huì))就出現(xiàn)了。”④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41.同樣,羅伯特·杰克遜(Robert Jackson)也強(qiáng)調(diào)制度與規(guī)范的重要性,認(rèn)為“主權(quán)國(guó)家所組成的社會(huì),是一種觀念和制度,它不僅表達(dá)了關(guān)于分歧、承認(rèn)、尊重、關(guān)心、對(duì)話、往來及交換的道德,而且展示了那些規(guī)定獨(dú)立政治共同體如何共存共處和互利互惠的規(guī)范”。⑤陳志敏著:《開放的國(guó)際社會(huì):國(guó)際關(guān)系研究中的英國(guó)學(xué)派》,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03-304 頁(yè)。對(duì)于持這種觀點(diǎn)的學(xué)者而言,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要立足于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尤其注重制度與規(guī)范的作用,這也是與前一種觀點(diǎn)的最大不同。 問題在于,制度與規(guī)范只是為團(tuán)結(jié)創(chuàng)造了約束條件,但是本身未必能夠產(chǎn)生團(tuán)結(jié)。
其三,從風(fēng)險(xiǎn)刺激層面探討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在持這種觀點(diǎn)的學(xué)者看來,風(fēng)險(xiǎn)刺激在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貝克(Ulrich Beck)認(rèn)為,“全球化乃是人類遭遇的新命運(yùn),是世界正在經(jīng)歷的又一次歷史轉(zhuǎn)型……世界所有國(guó)家和民族已經(jīng)被納入一個(gè)休戚與共、相互依存的‘風(fēng)險(xiǎn)共同體’”。⑥[德]烏爾里希·貝克著,路國(guó)林譯:《自由與資本主義——與著名社會(huì)學(xué)家烏爾里希·貝克對(duì)話》,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04 頁(yè)。為了應(yīng)對(duì)全球化危機(jī),民族國(guó)家需要團(tuán)結(jié)行動(dòng),“世界主義”是唯一的出路。 而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也指出,全球化帶來的金融危機(jī)、生態(tài)危機(jī)等世界性風(fēng)險(xiǎn)很難在某一國(guó)家內(nèi)部解決,所有民族和國(guó)家將逐步集合為一個(gè)非自愿的風(fēng)險(xiǎn)共同體。⑦章國(guó)鋒:“‘全球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困境與出路——貝克的‘世界主義’構(gòu)想”,《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shí)》,2008 年第2 期,第50 頁(yè)。與上述兩種觀點(diǎn)不同,這種觀點(diǎn)主要基于人類生存的外在風(fēng)險(xiǎn),試圖對(duì)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展開探討。然而,這種以風(fēng)險(xiǎn)來預(yù)設(shè)團(tuán)結(jié)的分析也存在一定不足,最為明顯的是忽視了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行動(dòng)選擇的多樣性。
由上可見,學(xué)界對(duì)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的研究,主要圍繞道德、制度與風(fēng)險(xiǎn)三個(gè)層面展開。 針對(duì)團(tuán)結(jié)何以形成,現(xiàn)有研究分別從價(jià)值內(nèi)化、客觀制度、外在風(fēng)險(xiǎn)方面做出了大量分析,但是很少有研究將三者結(jié)合起來探討。 筆者認(rèn)為,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是一項(xiàng)復(fù)雜工程,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不同國(guó)家之間之所以產(chǎn)生團(tuán)結(jié),并不只能從道德、制度、風(fēng)險(xiǎn)三者當(dāng)中的某個(gè)單一層面進(jìn)行解釋。 霍林格(David A. Hollinger)就曾指出,團(tuán)結(jié)是一個(gè)綜合體,“即便在溫和的意義上,它也蘊(yùn)含著一種特殊的意義,即人們擁有彼此的力量、情感和資源”。⑧李義天編:《共同體與政治》,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 180-181 頁(yè)。事實(shí)上,作為一種主體間性產(chǎn)物,團(tuán)結(jié)本身必定遵循一定的邏輯。 作為對(duì)國(guó)際社會(huì)現(xiàn)象尋求一般性解釋的社會(huì)科學(xué),①曹瑋著:《國(guó)際關(guān)系理論教程》,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20 年版,第 5 頁(yè)。國(guó)際政治社會(huì)學(xué)在分析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中,勢(shì)必不能將道德、制度和風(fēng)險(xiǎn)分割對(duì)待;相反,要基于社會(huì)建構(gòu)的本質(zhì),在深入剖析團(tuán)結(jié)邏輯的前提下對(duì)此展開論述。
三、團(tuán)結(jié)的發(fā)生邏輯與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機(jī)理
與新現(xiàn)實(shí)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不同,以建構(gòu)主義為代表的國(guó)際政治社會(huì)學(xué)注重社會(huì)學(xué)理論與概念的運(yùn)用,在分析國(guó)家行動(dòng)時(shí)強(qiáng)調(diào)共有觀念與集體知識(shí)的作用。②[美]瑪莎·芬尼莫爾著,袁正清譯:《國(guó)際社會(huì)中的國(guó)家利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21 頁(yè)。根據(jù)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總結(jié),建構(gòu)主義的核心觀點(diǎn)在于:“社會(huì)及其制度安排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中,社會(huì)學(xué)的任務(wù)就是分析和研究這個(gè)永恒的變化過程。”③[英]安東尼·吉登斯、[英]菲利普·薩頓著,王修曉譯:《社會(huì)學(xué)基本概念》(第二版),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9 年版,第61 頁(yè)。可見,社會(huì)學(xué)意義上的團(tuán)結(jié)屬于一個(gè)能動(dòng)性的統(tǒng)一過程,包括兩個(gè)要素,即“因何團(tuán)結(jié)”和“如何團(tuán)結(jié)”。 其中,前者強(qiáng)調(diào)團(tuán)結(jié)動(dòng)因,后者側(cè)重團(tuán)結(jié)的實(shí)現(xiàn)。 基于此,解釋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首先需要從一般意義的社會(huì)層面,厘清團(tuán)結(jié)的發(fā)生邏輯之后,方可展開。
3.1 從個(gè)體需要到集體共識(shí):團(tuán)結(jié)的發(fā)生邏輯
團(tuán)結(jié)源于主觀情感,這是容易形成、也是并無爭(zhēng)議的一種解釋。 在本質(zhì)上,團(tuán)結(jié)是彼此支持的團(tuán)體成員之間的相互情感和責(zé)任感。 在布魯克霍斯特(Hauke Brunkhorst)看來,法國(guó)大革命蘊(yùn)含的團(tuán)結(jié),表達(dá)的是革命者之間的“博愛”之情。④Hauke Brunkhorst, Solidarity: From Civic Friendship to a Global Legal Community, trans. By Jeffrey Flynn, 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 2005, p.1.同樣,約翰·貝克(John Baker)也認(rèn)為團(tuán)結(jié)與“愛”“友誼”等事物相聯(lián)系。 本質(zhì)上,情感表示的是一種需求,既可以是內(nèi)在歸屬感,也可以說是外部刺激下的聯(lián)合需要。
實(shí)踐中,主觀需要與實(shí)際團(tuán)結(jié)往往存在一定差距。 原因在于,主觀需要可以表達(dá)社會(huì)成員“個(gè)體層次”的某種期望,但是這種期望很難與社會(huì)成員“個(gè)體之間”的現(xiàn)實(shí)團(tuán)結(jié)相等同。 在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團(tuán)結(jié)既表現(xiàn)為主觀狀態(tài),更表現(xiàn)為實(shí)踐狀態(tài)。 作為兩者的有機(jī)統(tǒng)一,“個(gè)體層次”主觀需要能夠解釋“因何團(tuán)結(jié)”,但是未必可以實(shí)現(xiàn)“如何團(tuán)結(jié)”。 因此羅素(Bertrand Russell)認(rèn)為,團(tuán)結(jié)重在實(shí)踐,“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是必要的,但人類迄今還不曾有過單憑說理就能加強(qiáng)團(tuán)結(jié)的事”。⑤[英]伯特蘭·羅素著,何兆武、李約瑟譯:《西方哲學(xué)史》(上卷),商務(wù)印書館,1982 年版,第 23 頁(yè)。在此當(dāng)中,最重要的是尋找共同需要,即在社會(huì)成員不同需要之間尋找共同點(diǎn),從而將主觀需要從“個(gè)體層次”上升為“個(gè)體之間”。
可見,從社會(huì)層面看,團(tuán)結(jié)遵循“從個(gè)體需要到集體共識(shí)”的邏輯。 “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既不是一廂情愿的自我滿足,也不是無奈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而是一種與隱藏在歷史深處群體生存需求聯(lián)系起來的社會(huì)財(cái)富。”⑥秦文鵬:“‘群’,非自足——‘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理論依據(jù)三種”,《理論與改革》,2012 年第 6 期,第 20 頁(yè)。一方面,團(tuán)結(jié)源于社會(huì)成員的個(gè)體需要,情感需要、風(fēng)險(xiǎn)刺激等會(huì)激發(fā)個(gè)體主觀上的聯(lián)合需要;另一方面,團(tuán)結(jié)實(shí)現(xiàn)于集體共識(shí),團(tuán)結(jié)的實(shí)現(xiàn)離不開社會(huì)成員之間共同需要這一共識(shí)的產(chǎn)生。
3.2 從理想到契約:國(guó)際社會(huì)的團(tuán)結(jié)機(jī)理
以建構(gòu)主義為代表的國(guó)際政治社會(huì)學(xué),其核心特點(diǎn)是最大程度上將社會(huì)建構(gòu)論引入國(guó)際關(guān)系領(lǐng)域,“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huì)和社會(huì)成員替換成國(guó)際社會(huì)和國(guó)家”。⑦同①,第180 頁(yè)。據(jù)此,作為團(tuán)結(jié)的一種類型,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遵循著團(tuán)結(jié)的發(fā)生邏輯。“所謂國(guó)際團(tuán)結(jié)涉及國(guó)家與國(guó)家之間的關(guān)系,意味著不同國(guó)家就它們關(guān)心的共同問題或共同利益達(dá)成某種共識(shí)而形成的聯(lián)合。”⑧左高山、段外賓:“論團(tuán)結(jié)問題”,《倫理學(xué)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90 頁(yè)。根據(jù)上述分析,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之所以發(fā)生,關(guān)鍵是共同需要的存在。 在實(shí)踐中,這種共同需要主要以幸福追求為主觀起點(diǎn),同時(shí)又以制度規(guī)范為保障。
第一,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以幸福追求為內(nèi)驅(qū)。幸福是人類的永恒追求。 英國(guó)思想家休謨(David Hume)認(rèn)為,“人類心靈的主要?jiǎng)恿屯苿?dòng)原則就是快樂和痛苦,一切人類努力的偉大目標(biāo)在于獲得幸福”。①[英]大衛(wèi)·休謨著,關(guān)文遠(yuǎn)譯:《人性論》,商務(wù)印書館,1997 年版,第 616 頁(yè)。長(zhǎng)期以來,人們對(duì)于幸福的認(rèn)知存在多種理解,但是卻始終與國(guó)家存在十分緊密的聯(lián)系。 例如,在古希臘哲學(xué)家柏拉圖(Plato)看來,幸福即善與德行,真正的幸福只能存在于城邦國(guó)家之中。 同樣,意大利思想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也指出,國(guó)家的責(zé)任在于創(chuàng)造幸福,“掌握國(guó)家的統(tǒng)治權(quán)實(shí)際上成為一種責(zé)任,由擁有統(tǒng)治權(quán)的政府來?yè)?dān)任道義上的義務(wù),就是通過政治統(tǒng)治,維護(hù)和平與秩序,使人民過上有道德的幸福生活”。②浦興祖、洪濤著:《西方政治學(xué)說史》,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25 頁(yè)。
對(duì)于現(xiàn)代國(guó)家而言,創(chuàng)造幸福生活是其重要職責(zé)。 當(dāng)前,無論是中國(guó)正在奮力構(gòu)筑的“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guó)夢(mèng)”,還是拉美國(guó)家正在努力的“實(shí)現(xiàn)團(tuán)結(jié)協(xié)作、發(fā)展振興的拉美夢(mèng)”,為民謀福祉都是其根本所在。 即便是曾經(jīng)高喊“讓美國(guó)再次偉大”的美國(guó)前任總統(tǒng)特朗普(Donald Trump),改善國(guó)民生活也是其重要追求。 為此,在國(guó)際系統(tǒng)“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guó)家的功能高度相似,都是對(duì)外保證國(guó)家安全,對(duì)內(nèi)要從經(jīng)濟(jì)、民主和法治等方面保證國(guó)民福祉。③[美]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guó)際政治的社會(huì)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202 頁(yè)。有鑒于此,在國(guó)際社會(huì)中,民生幸福感日益受到廣泛關(guān)注。④丘海雄、李敢:“國(guó)外多元視野‘幸福’觀研析”,《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225 頁(yè)。早在1972 年,不丹國(guó)在世界上便最早提出“國(guó)民幸福總值”研究。 2008 年,法國(guó)時(shí)任總統(tǒng)薩科齊(Nicolas Sarkozy)也著手組建經(jīng)濟(jì)表現(xiàn)和社會(huì)進(jìn)步委員會(huì),目的是推動(dòng)包含幸福的綜合發(fā)展指標(biāo)建設(shè)。 聯(lián)合國(guó)也極為看重“幸福”的價(jià)值,自2012 年開始,每年對(duì)外發(fā)布《世界幸福報(bào)告》。 可見,“民生幸福”已具有國(guó)際共識(shí),成為世界上廣大國(guó)家和政黨執(zhí)政的重要理念。⑤陳東冬:“倫理學(xué)視域下的民生幸福與服務(wù)型政府建設(shè)”,《中共桂林市委黨校學(xué)報(bào)》,2011 年第2 期,第44 頁(yè)。
第二,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以共同利益建構(gòu)為紐帶。 對(duì)于國(guó)家而言,幸福追求需要通過行動(dòng)來實(shí)現(xiàn)。 現(xiàn)實(shí)中,由于民族國(guó)家的邊界性,幸福實(shí)踐往往首屬內(nèi)部事務(wù),主要在本國(guó)內(nèi)部完成。然而隨著全球化的興起,商品、資本和勞動(dòng)力等跨國(guó)流動(dòng)日益增多,國(guó)境以外的因素對(duì)于國(guó)境以內(nèi)的影響越來越頻繁。⑥李雪著:《社會(huì)學(xué)視野中的全球化與現(xiàn)代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8 年版,第2 頁(yè)。19 世紀(jì)以來,隨著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完成、資本主義世界擴(kuò)張和科技革命的興起,全球化不斷推進(jìn)與發(fā)展,國(guó)與國(guó)之間的地理藩籬日漸消弭,相互聯(lián)系日益加深。“單是大工業(yè)建立了世界市場(chǎng)這一點(diǎn),就把全球各國(guó)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guó)家的人民彼此緊密聯(lián)系起來,以致每一國(guó)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國(guó)所發(fā)生事情的影響。”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 444 頁(yè)。全球化發(fā)展給世界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莫過于兩點(diǎn):其一,相互聯(lián)系加大,原本屬于一國(guó)內(nèi)部的事務(wù),卻愈發(fā)影響其他國(guó)家。 其二,相互依存加大,很多事務(wù)很難在一國(guó)內(nèi)部解決,需要共同努力方能解決的問題日益增多。⑧陳玉剛:“國(guó)際政治對(duì)國(guó)家行為的結(jié)構(gòu)影響”,《太平洋學(xué)報(bào)》,1998 年第 1 期,第 67 頁(yè)。在此情形之下,在國(guó)家幸福實(shí)踐中,探索“個(gè)體之間”的新路徑,也注定成為一種必然。
“個(gè)體之間”幸福實(shí)踐的主要路徑是合作,即不同國(guó)家通過相互合作的方式,實(shí)踐自身的幸福追求。 合作即團(tuán)結(jié),目的是在相互合作當(dāng)中實(shí)現(xiàn)彼此對(duì)于幸福生活的追求。 “團(tuán)結(jié)是利益和情感的協(xié)調(diào)一致,是我為人人和人人為我。人們?cè)趫F(tuán)結(jié)中展示個(gè)性,達(dá)成最佳發(fā)展,享受最大可能的幸福。”⑨Errico Malatesta, Anarchy, London: Free Press, 1974,p.24.毫無疑問,在此過程中,共同利益是前提,也是關(guān)鍵。 對(duì)于不同國(guó)家而言,共同利益的找尋,需要彼此在幸福實(shí)踐中建構(gòu)共同點(diǎn)。 在貝克(Ulrich Beck)看來,全球化進(jìn)程中的共同利益,主要存在兩種類型:其一,不同國(guó)家在發(fā)展中存在資本、技術(shù)和資源等方面的相互需求。 其二,金融危機(jī)、生態(tài)危機(jī)等外在風(fēng)險(xiǎn)會(huì)使得不同國(guó)家產(chǎn)生合作的需要。 在工業(yè)社會(huì)中,共同利益主要表現(xiàn)為“需求”;隨著后工業(yè)社會(huì)來臨,面對(duì)科技發(fā)展帶來的“潛在的副作用”,不同國(guó)家會(huì)因風(fēng)險(xiǎn)“焦慮”產(chǎn)生合作。 整體而言,國(guó)際社會(huì)正從“需求型團(tuán)結(jié)”邁入“焦慮促動(dòng)型團(tuán)結(jié)”。①[德]烏爾里希·貝克著,何博聞譯:《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譯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 56 頁(yè)。
第三,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以制度規(guī)范為保障。在建構(gòu)共同利益的過程中,團(tuán)結(jié)往往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原因包括:其一,在客觀上,國(guó)與國(guó)在合作中往往奉行利益至上,而國(guó)力上的差異通常使得利益的實(shí)現(xiàn)存在差異。 其二,從主觀上,這種差異會(huì)促使其在利益計(jì)算上產(chǎn)生“相對(duì)收益”與“絕對(duì)收益”的區(qū)別,從而使不同國(guó)家對(duì)于團(tuán)結(jié)的認(rèn)知形成差異。 因而在實(shí)踐當(dāng)中, 為了確保團(tuán)結(jié)的有效性,國(guó)際社會(huì)往往通過制定制度與規(guī)范來降低這一脆弱性的負(fù)面影響。 基歐漢認(rèn)為,制度與規(guī)范的作用在于降低合法交易成本、增加非法交易成本、減少行為不確定性等機(jī)制,從而促進(jìn)合作。②[美]羅伯特·基歐漢著,蘇長(zhǎng)和、信強(qiáng)、何曜譯:《霸權(quán)之后:世界政治經(jīng)濟(jì)中的合作與紛爭(zhēng)》,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07 頁(yè)。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歷史上不同國(guó)際體系和文明的國(guó)家及人民之所以能在戰(zhàn)爭(zhēng)、和平、聯(lián)盟和商業(yè)方面達(dá)成協(xié)議,是因?yàn)樗麄冋J(rèn)識(shí)到信守承諾、履行協(xié)議的好處”。③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4-5,434.
制度規(guī)范的本質(zhì)是契約。 對(duì)于國(guó)家合作而言,其根本作用是為共同利益的建構(gòu)提供保障,避免團(tuán)結(jié)陷入利益紛爭(zhēng)的失序狀態(tài)。 當(dāng)前在國(guó)際社會(huì),制度與規(guī)范的數(shù)目繁多,諸如《羅馬條約》《聯(lián)合國(guó)憲章》《世界貿(mào)易組織協(xié)定》等皆是其表現(xiàn)。 赫德利·布爾認(rèn)為,在國(guó)際社會(huì)中,制度側(cè)重協(xié)調(diào)性,規(guī)則偏向于具體性。 其中,規(guī)則主要是國(guó)際法、國(guó)際道德準(zhǔn)則和國(guó)際慣例等限制國(guó)家行動(dòng)的一般性原則,而制度旨在讓規(guī)則產(chǎn)生效力。④章前明:“布爾的國(guó)際社會(huì)思想”,《浙江學(xué)刊》,2008 年第1 期,第 111 頁(yè)。雖然存在一定區(qū)別,但兩者都是為合作提供契約保障。

圖1 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機(jī)理示意圖
根據(jù)上文所述,筆者基于團(tuán)結(jié)的發(fā)生邏輯,勾畫出了一個(gè)簡(jiǎn)要的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機(jī)理示意圖。 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是以主權(quán)國(guó)家為主體的團(tuán)結(jié),現(xiàn)實(shí)中這一主體的數(shù)量應(yīng)當(dāng)是涵蓋大多數(shù)主權(quán)國(guó)家,圖中為了便于闡釋,主要以A、B、C等國(guó)來體現(xiàn)。 總而言之,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是全球化作用之下,國(guó)家幸福追求與幸福實(shí)踐的統(tǒng)一。這具有兩層含義:其一,隨著相互依存加深,不同國(guó)家在幸福實(shí)踐中需要突破國(guó)別地理界限,通過合作來實(shí)現(xiàn)幸福追求。 其二,合作以共同利益建構(gòu)為前提,以制度規(guī)范為保障。 其中,內(nèi)在道德、客觀制度、外在風(fēng)險(xiǎn),無疑都在發(fā)揮作用。 反觀近現(xiàn)代國(guó)際關(guān)系變遷,它所經(jīng)歷的威斯特伐利亞合約、 國(guó)際聯(lián)盟和聯(lián)合國(guó)三次里程碑式的進(jìn)步,本質(zhì)上都是幸福追求內(nèi)驅(qū)下,廣大國(guó)家建構(gòu)共同利益、形成契約的過程。
四、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中逆全球化的產(chǎn)生過程
逆全球化并非以破壞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為目的,因?yàn)槟嫒蚧膰?guó)家從不否定幸福追求。無論是特朗普的“美國(guó)優(yōu)先”還是英國(guó)“脫歐”,他們無不以創(chuàng)造幸福生活為口號(hào)。 只是在幸福實(shí)踐上,這類國(guó)家存在顯著差異。 逆全球化的產(chǎn)生,不僅與諸如資本主義內(nèi)在矛盾、全球化危機(jī)等因素有關(guān),更為關(guān)鍵的是,它始終蘊(yùn)含著一定的因果過程。 事實(shí)上,引發(fā)逆全球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置身于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之內(nèi),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之所以出現(xiàn)逆全球化之舉,也是基于一系列前因后果而做出的選擇。
4.1 從“受益者”到“受損者”:空間轉(zhuǎn)換帶來的身份轉(zhuǎn)型
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以全球化為重要推力。 作為波及全球范圍的社會(huì)變遷,“全球化并非自己本身就具有明確的目的和動(dòng)力,相反,是人類行動(dòng)者和社會(huì)組織才構(gòu)成全球化動(dòng)力的本質(zhì)源泉”。①[英]羅賓·科恩、[英]保羅·肯尼迪著,文軍等譯:《全球社會(huì)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1 年版,第34 頁(yè)。在全球化的推進(jìn)過程中,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扮演著重要角色。 整體而言,全球化的影響是全球性的、具有深遠(yuǎn)意義的,“既是商品、資本、勞動(dòng)力跨國(guó)流動(dòng)的結(jié)構(gòu)性過程,也是個(gè)制度性過程”。②李雪著:《社會(huì)學(xué)視野中的全球化與現(xiàn)代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8 年版,第5 頁(yè)。與此同時(shí),這種影響是波浪式的、逐步呈現(xiàn)的,因?yàn)槿蚧耙砸环N相當(dāng)不穩(wěn)定的方式來影響不同地方、國(guó)家和個(gè)體是需要很長(zhǎng)時(shí)間的”。③同①。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化的波浪式發(fā)展即為這種不穩(wěn)定方式的集中體現(xiàn)。 原因在于,市場(chǎng)是一把雙刃劍,受其影響,全球化始終在兩種空間,即“正面效應(yīng)”和“負(fù)面效應(yīng)”交織過程中螺旋前進(jìn)。 與之相伴的是,在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當(dāng)中,這兩種空間也始終是共生共存的。
兩種空間鑄造了“受益者”“受損者”兩種身份狀態(tài)。 全球化伊始往往“正面效應(yīng)”正盛,推動(dòng)者也是“受益者”。 相反,后期則“負(fù)面效應(yīng)”凸顯,推動(dòng)者往往成為“受損者”。 毫無疑問,在幸福追求驅(qū)動(dòng)之下,不同國(guó)家的反應(yīng)往往是:身處“正面效應(yīng)”的國(guó)家,作為“受益者”,往往對(duì)全球化持支持態(tài)度;相反,因“受損者”身份的出現(xiàn),身處“負(fù)面效應(yīng)”的國(guó)家往往對(duì)全球化持反對(duì)態(tài)度。 正因如此,“發(fā)達(dá)資本主義國(guó)家需要擴(kuò)張時(shí),則主張貿(mào)易自由政策;需要調(diào)節(jié)、維護(hù)時(shí),則主張貿(mào)易保護(hù)政策”。④甘子成、王麗榮:“逆經(jīng)濟(jì)全球化現(xiàn)象研究:理論基礎(chǔ)、本質(zhì)透視及應(yīng)對(duì)策略”,《經(jīng)濟(jì)問題探索》,2019 年第2 期,第187 頁(yè)。
問題是對(duì)于“負(fù)面效應(yīng)”空間,即便作為全球化發(fā)起者與推動(dòng)者的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也很難形成天然免疫。 一方面,這是市場(chǎng)規(guī)律的必然結(jié)果,在市場(chǎng)的資源配置作用之下,沒有哪個(gè)國(guó)家能夠注定成為贏家。 另一方面,發(fā)達(dá)國(guó)家內(nèi)部治理失調(diào)也是一個(gè)重要原因。 對(duì)此,發(fā)達(dá)國(guó)家往往持有不同的認(rèn)識(shí)。 面對(duì)“負(fù)面效應(yīng)”引發(fā)的貿(mào)易赤字、內(nèi)部失業(yè)等問題,他們往往淡化內(nèi)部治理的不足,通過貿(mào)易保護(hù)主義片面地歸罪于全球化。 對(duì)于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這一做法,馬克思(Karl Marx)早已斷言,“保護(hù)關(guān)稅制度不過是某個(gè)國(guó)家建立大工業(yè)的手段……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shí)現(xiàn)國(guó)內(nèi)自由貿(mào)易的手段”。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758 頁(yè)。
4.2 推動(dòng)與阻撓:身份轉(zhuǎn)型引發(fā)的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悖論
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與否,大國(guó)起著關(guān)鍵作用。約瑟夫·奈(Joseph Nye)認(rèn)為,“一國(guó)內(nèi)部,需要政府提供諸如警察、清潔的環(huán)境等公共產(chǎn)品,每位公民都將獲益,沒有人被排除在外。 同樣,在全球?qū)用?也需要以最強(qiáng)大國(guó)家為首的聯(lián)盟提供公共產(chǎn)品,如穩(wěn)定的氣候、穩(wěn)健的金融及海洋上的自由航行”。⑥Joseph Nye, “ The Kindleberger Trap,” Project Syndicate,January 9, 2017, https:/ /www.project- 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在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當(dāng)中,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承擔(dān)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責(zé)任,這不僅為其在全球事務(wù)中把握話語權(quán)提供了便利,也為自身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然而,“受損者”身份的出現(xiàn)意味著原有利益格局受到?jīng)_擊,難免引起這些國(guó)家的反思。
西方國(guó)家傾向于從全球化的負(fù)面作用之中找尋原因。 米歇爾·于松(Michel Husson)認(rèn)為,全球化具有收入分配效應(yīng),容易引發(fā)內(nèi)部不平等問題;①[法]米歇爾·于松著,潘革平譯:《資本主義十講》,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3 年版,第56 頁(yè)。克利希那(Pravin Krishna)也指出,貿(mào)易自由化的替代效應(yīng)將增加勞動(dòng)者就業(yè)和收入風(fēng)險(xiǎn)。②Pravin Krishna and Mine Zeynep Sense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abor Income Risk in the USA,”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81, No.1, 2014, pp.186-218.如此意味著,“對(duì)于發(fā)達(dá)國(guó)家來說,國(guó)際貿(mào)易一方面會(huì)通過減少發(fā)達(dá)國(guó)家低技能勞動(dòng)力的就業(yè)機(jī)會(huì)而使其收入狀況惡化,另一方面則有可能降低低技能勞動(dòng)力的相對(duì)報(bào)酬或收入水平,從而拉大其與高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③李奇澤、黃平:“經(jīng)濟(jì)全球化與發(fā)達(dá)國(guó)家收入不平等”,《紅旗文稿》,2017 年第 22 期,第 16 頁(yè)。與之不同,在國(guó)內(nèi)一些學(xué)者看來,“從理論邏輯上看,經(jīng)濟(jì)全球化與發(fā)達(dá)國(guó)家內(nèi)部收入不平等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并不存在”,④同③,第17 頁(yè)。因?yàn)榘l(fā)達(dá)國(guó)家內(nèi)部治理中的職業(yè)培訓(xùn)、最低工資保障等機(jī)制,對(duì)于不平等可以起到有效的抵消作用。 本質(zhì)上,“受損者”轉(zhuǎn)型是內(nèi)外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不可否認(rèn)全球化帶來了負(fù)面影響,但是更多的原因應(yīng)從內(nèi)部找尋。
然而“受損者”身份的出現(xiàn),往往使得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面臨雙重壓力。 其一,持續(xù)“受損”的壓力。 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存在消費(fèi)非競(jìng)爭(zhēng)性、非排他性特點(diǎn),在承擔(dān)這類產(chǎn)品供給時(shí),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需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cái)力為后盾。 隨著全球化不斷推進(jìn),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的需求與日俱增,“以全球經(jīng)濟(jì)治理領(lǐng)域?yàn)槔?全球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與發(fā)展的壓力依然很大,對(duì)公共產(chǎn)品需求量巨大”。⑤任琳:“中國(guó)全球治理觀:時(shí)代背景與挑戰(zhàn)”,《當(dāng)代世界》,2018 年第 4 期,第 46 頁(yè)。在“受損者”轉(zhuǎn)向之下,繼續(xù)推動(dòng)全球化勢(shì)必導(dǎo)致“受損”持續(xù)化。 其二,國(guó)內(nèi)幸福追求的壓力。對(duì)于發(fā)達(dá)國(guó)家而言,“受損者”身份使得本國(guó)幸福追求受到影響,勢(shì)必招致國(guó)內(nèi)民眾、政治精英的反對(duì)。 自20 世紀(jì)90 年代以來,發(fā)達(dá)國(guó)家與發(fā)展中國(guó)家經(jīng)濟(jì)實(shí)力一直呈縮小態(tài)勢(shì)。 例如,在各國(guó)國(guó)內(nèi)生產(chǎn)總值(GDP)世界占比方面,在1991 年至 2011 年這 20 年間,七國(guó)集團(tuán)(G7)的這一指標(biāo)從66.7%下降到48.1%,而金磚五國(guó)則從7%上升到20%左右。⑥郭強(qiáng):“逆全球化:資本主義最新動(dòng)向研究”,《當(dāng)代世界與社會(huì)主義》,2013 年第 4 期,第 18 頁(yè)。與此同時(shí),發(fā)達(dá)國(guó)家內(nèi)部貧富差距卻日益加劇。 2005—2014 年期間,在全球25 個(gè)高收入經(jīng)濟(jì)體中,65%~70%的家庭(約5.4 億~5.8 億人)實(shí)際收入出現(xiàn)停滯或下降。⑦“家庭收入停滯,發(fā)達(dá)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遇瓶頸”,人民網(wǎng),2016 年 8 月 2 日,http:/ /world.people.com.cn/n1/2016/0802/c1002-28602201.html。在此雙重壓力下,推動(dòng)全球化則意味著繼續(xù)受損,阻撓則導(dǎo)致國(guó)際供給產(chǎn)品供應(yīng)不足,從而使得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陷入困境。 由此,如何選擇幸福實(shí)踐路徑,則是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面臨的考驗(yàn)。
4.3 重利、輕義、玩弄規(guī)則:悖論之下“另類”幸福實(shí)踐選擇
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倡導(dǎo)互利合作,通過對(duì)話協(xié)調(diào)化解分歧,進(jìn)而邁向共同幸福。 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經(jīng)濟(jì)全球化進(jìn)入階段性調(diào)整期,質(zhì)疑者有之,徘徊者有之。 應(yīng)該看到,經(jīng)濟(jì)全球化符合生產(chǎn)力發(fā)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勢(shì)所趨”。⑧習(xí)近平:“在亞太經(jīng)合組織第二十四次領(lǐng)導(dǎo)人非正式會(huì)議上的發(fā)言”,新華網(wǎng),2016 年 11 月 21 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1/21/c_1119953815.htm。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背景下,面對(duì)全球化帶來的“負(fù)面效應(yīng)”,合理應(yīng)對(duì)之策應(yīng)是強(qiáng)化國(guó)內(nèi)治理,加大國(guó)際協(xié)調(diào),通過對(duì)話與合作促進(jìn)發(fā)展。 然而與之不同的是,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卻傾向于選擇一種“另類”路徑,即以“狹隘利己主義”化解自身危機(jī)。 對(duì)此,有學(xué)者指出,表面上或許是應(yīng)對(duì)內(nèi)部民眾不滿,其背后的真正目的則是轉(zhuǎn)移國(guó)內(nèi)矛盾、尋求自我保護(hù)。⑨“中國(guó)引領(lǐng)打造‘新型全球化’”,《參考消息》,2017 年3月 15 日,http:/ /ihl.cankaoxiaoxi.com/2017/0315/1770327.shtml。
“狹隘利己主義”的核心特點(diǎn)是只求利己,不求利他。 結(jié)合現(xiàn)實(shí)表現(xiàn),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這一路徑主要集中為三類:追求本國(guó)利益至上、輕視責(zé)任與義務(wù),或者選擇性遵守制度與規(guī)則。
首先,唯本國(guó)利益至上的國(guó)家,一切以本國(guó)利益為主,無視其他國(guó)家的正當(dāng)權(quán)益和合理訴求。 無疑,美國(guó)是這類“重利”的典型代表。 自2008 年次貸危機(jī)以來,為了刺激出口、復(fù)蘇國(guó)內(nèi)經(jīng)濟(jì),美國(guó)以綠色貿(mào)易保護(hù)、技術(shù)壁壘等方式頻頻掀起反傾銷調(diào)查。 據(jù)英國(guó)經(jīng)濟(jì)政策研究中心發(fā)布的《全球貿(mào)易預(yù)警》,2008—2016 年美國(guó)對(duì)其他國(guó)家采取的貿(mào)易保護(hù)措施達(dá)600 多項(xiàng),僅2015 年就采取了90 項(xiàng),居各國(guó)之首。①“以開放發(fā)展引領(lǐng)經(jīng)濟(jì)全球化步入新時(shí)代”,人民網(wǎng),2017 年 3 月 9 日,http:/ /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309/c1003-29132780.html。一直高喊“讓美國(guó)再次偉大”的前任總統(tǒng)特朗普,在2017 年上臺(tái)之初,就以“美國(guó)優(yōu)先”為口號(hào)啟動(dòng)對(duì)中國(guó)的301 調(diào)查,掀起中美貿(mào)易摩擦。 與此同時(shí),出于自利考慮,美國(guó)制裁“大棒”不惜揮向傳統(tǒng)盟友。 2018 年,在對(duì)歐盟鋼鐵和鋁開征25%關(guān)稅后,美國(guó)陸續(xù)對(duì)墨西哥、加拿大、日本等國(guó)家提高關(guān)稅稅率。 之所以漠視經(jīng)濟(jì)規(guī)律、選擇與盟國(guó)為壑,美國(guó)最為看重的還是本國(guó)利益。
其次,放棄國(guó)際責(zé)任是“受損者”身份轉(zhuǎn)向下,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又一極端做法。 借此既能降低本國(guó)相應(yīng)支出,也能回應(yīng)國(guó)內(nèi)民眾關(guān)切。在全球經(jīng)濟(jì)低迷、各國(guó)經(jīng)濟(jì)復(fù)蘇乏力的背景下,勞動(dòng)力跨國(guó)流動(dòng)和大批難民、非法移民的涌入,給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guī)砹司蜆I(yè)機(jī)會(huì)減少、社會(huì)治安惡化和經(jīng)濟(jì)福利下降等問題。②廖曉明、劉曉鋒:“當(dāng)今世界逆全球化傾向的表現(xiàn)及其原因分析”,《長(zhǎng)白學(xué)刊》,2018 年第 2 期,第 31 頁(yè)。對(duì)此,美國(guó)采取移民禁令、建美墨邊境墻等措施來消極應(yīng)對(duì)。而歐盟內(nèi)部反移民的呼聲和政治力量也不斷壯大。 2018 年6 月20 日,匈牙利國(guó)會(huì)通過“史上最嚴(yán)”移民法案(即“阻止索羅斯法案”),規(guī)定幫助非法移民的援助行為將被認(rèn)定為犯罪。③“匈牙利通過‘阻止索羅斯法案’,幫助非法移民可能坐牢 1 年”,觀察者網(wǎng),2018 年 6 月 21 日,https:/ /www.guancha.cn/internation /2018_06_21_460890.shtml。而一向?qū)σ泼癯纸蛹{態(tài)度的德國(guó),面對(duì)內(nèi)部壓力也開始收緊政策。 對(duì)于這些國(guó)家而言,上述移民政策的出臺(tái),其根源在于無視國(guó)際責(zé)任。本質(zhì)上,“當(dāng)前這些帶有民粹主義非理性色彩的孤立主義事件,反映的是英美大國(guó)經(jīng)濟(jì)實(shí)力漸衰及其全球責(zé)任與擔(dān)當(dāng)意識(shí)的下降”。④張超穎:“‘逆全球化’的背后:新自由主義的危機(jī)及其批判”,《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68 頁(yè)。
最后,為了本國(guó)利益玩弄制度、漠視規(guī)則,也是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慣用做法。 對(duì)于這類國(guó)家而言,制度與規(guī)則只是其獲取利益的工具,于是“合則用,不合則棄”。⑤“國(guó)際規(guī)則不是提線木偶——看清美國(guó)某些政客‘合則用、不合則棄’ 的真面目”,人民網(wǎng),2019 年 6 月 12 日,http:/ /world.people.com.cn/n1/2019/0612/c1002-31131556.html。其中,美國(guó)頻繁“退群”無疑是這一類型的典型。 特朗普自推出“美國(guó)優(yōu)先”以來,是否符合美國(guó)利益便成為其衡量和判定國(guó)際社會(huì)制度與規(guī)則的標(biāo)尺,由此頻頻出現(xiàn)退出《巴黎協(xié)定》《中導(dǎo)條約》、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等操作。
五、逆全球化下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的走向及應(yīng)對(duì)
當(dāng)前,貿(mào)易壁壘、“脫鉤”威脅等逆全球化行徑與思潮甚囂塵上,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面臨極大考驗(yàn)。 如何化解與應(yīng)對(duì),成為亟需探索的一項(xiàng)重要工作。
5.1 未來走向:團(tuán)結(jié)將是國(guó)際社會(huì)的主要基調(diào)
對(duì)于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而言,逆全球化具有一定破壞性。 概括而言,這種破壞性可以歸結(jié)為四點(diǎn):⑥張剛生:“論美歐發(fā)達(dá)地區(qū)的逆全球化現(xiàn)象”,《國(guó)際觀察》,2020 年第 2 期,第 147-150 頁(yè)。其一,引發(fā)國(guó)家主義的復(fù)歸,使得政府對(duì)于經(jīng)濟(jì)與市場(chǎng)的干預(yù)增多。 其二,強(qiáng)化本國(guó)優(yōu)先和本國(guó)利益至上,導(dǎo)致民族主義復(fù)興。 其三,促使制裁與反制裁這類現(xiàn)象逐步增多。 其四,導(dǎo)致國(guó)與國(guó)之間沖突與對(duì)抗的可能性增加。 由此導(dǎo)致,“長(zhǎng)久以來旨在實(shí)現(xiàn)市場(chǎng)自由化的運(yùn)動(dòng)已經(jīng)中斷,全球已進(jìn)入新一輪國(guó)家干預(yù)與管制以及保護(hù)主義蔓延的時(shí)期”。⑦Roger C. Altman,“Globalization in Retreat Further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Foreign Affairs, Vol.88,No.4, 2009, pp.2-7.尤其是在當(dāng)前全球經(jīng)濟(jì)整體萎靡的背景下,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逆全球化思潮及其消極影響,在短期內(nèi)很難消解。盡管如此,這并不影響對(duì)全球化發(fā)展的樂觀判斷。①M(fèi)artin Sandbu,“Three Reasons Why Globalization Will Survive Protectionism Rebellions,” The Financial Times, March 9,2017.從長(zhǎng)遠(yuǎn)來看,團(tuán)結(jié)將是國(guó)際社會(huì)的主要基調(diào),這既能從歷史中找尋力證,也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
歷史證明,團(tuán)結(jié)實(shí)屬國(guó)際社會(huì)發(fā)展的主流。“在第一次工業(yè)革命以來的200 年間,人類經(jīng)歷了兩次全球化浪潮,但同時(shí)也見證了三次逆全球化思潮”,②盛斌、黎峰:“逆全球化:思潮、原因與反思”,《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問題》,2020 年第 2 期,第 6 頁(yè)。在兩者的此消彼長(zhǎng)之中,逆全球化從來沒有占據(jù)主導(dǎo)。 從現(xiàn)實(shí)來看,這股負(fù)能量也不具備形成氣候的條件。 其一,國(guó)際社會(huì)的幸福追求未變。 在當(dāng)今世界,幸福追求仍是發(fā)展的內(nèi)在驅(qū)動(dòng),是大多數(shù)國(guó)家的主要追求。 其二,國(guó)際社會(huì)面臨的共同問題有增無減。 “人類也正處在一個(gè)挑戰(zhàn)層出不窮、風(fēng)險(xiǎn)日益增多的時(shí)代。 世界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乏力,金融危機(jī)陰云不散,發(fā)展鴻溝日益突出,兵戎相見時(shí)有發(fā)生,冷戰(zhàn)思維和強(qiáng)權(quán)政治陰魂不散,恐怖主義、難民危機(jī)、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持續(xù)蔓延。”③習(xí)近平著:《論堅(jiān)持推動(dòng)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18 年版,第415 頁(yè)。其三,制度與規(guī)則早已深入人心。在和平與發(fā)展的時(shí)代主題之下,基于國(guó)際法、國(guó)際慣例等規(guī)則化解矛盾、達(dá)成合作,已成為各國(guó)共同的心聲。
5.2 應(yīng)對(duì)路徑:維護(hù)制度理性與探索制度超越
約瑟夫·奈認(rèn)為,“不平等會(huì)導(dǎo)致政治反應(yīng)……發(fā)生導(dǎo)致大規(guī)模失業(yè)的金融危機(jī)和經(jīng)濟(jì)蕭條,這樣的政治反應(yīng)可能會(huì)最終限制世界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步伐”。④[美]小約瑟夫·奈、[加]戴維·韋爾奇著,張小明譯:《理解全球沖突與合作:理論與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96-297 頁(yè)。據(jù)此有學(xué)者提出,逆全球化是美歐發(fā)達(dá)國(guó)家出于對(duì)全球化中遭遇的“經(jīng)濟(jì)不平等的政治反應(yīng)”。⑤桑百川、王偉:“逆全球化背景下東亞經(jīng)濟(jì)合作的機(jī)遇”,《東北亞論壇》,2018 年第 3 期,第 82 頁(yè)。當(dāng)然也有不同看法,有學(xué)者提出,“美國(guó)并未在國(guó)際體系中獲利”只是該國(guó)政府對(duì)外給出的一種冠冕借口,其真正關(guān)心、在乎的實(shí)際上是其他國(guó)家獲利過多而導(dǎo)致自身霸權(quán)利益受損。⑥陳庭翰、王浩:“美國(guó)‘逆全球化戰(zhàn)略’的緣起與中國(guó)‘一帶一路’的應(yīng)對(duì)”,《新疆社會(huì)科學(xué)》,2019 年第6 期,第74 頁(yè)。事實(shí)上,無論何者更加成立,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握有主動(dòng)皆屬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其逆全球化的背后,舊有的全球治理體系才是關(guān)鍵。 逆全球化的化解或許與美歐發(fā)達(dá)國(guó)家內(nèi)部治理改善存在關(guān)系,但是并不能寄希望于此,問題最終的有效解決仍然需要新的全球性制度安排。⑦汪毅霖:“‘逆全球化’的歷史與邏輯”,《讀書》,2020 年第 2 期,第 22 頁(yè)。而在其成型之前,在現(xiàn)有體系內(nèi)維護(hù)制度理性也同樣重要。
第一,維護(hù)并完善現(xiàn)有機(jī)制,強(qiáng)化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 制度理性是全球化以來人類幸福實(shí)踐的最大成果。 當(dāng)前,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的制度與規(guī)則是在聯(lián)合國(guó)框架下,以美國(guó)為主導(dǎo)而建立的。雖存有缺陷,但制度理性對(duì)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的價(jià)值卻是毋庸置疑的。 多伊奇(Karl Deutsch)就明確提出,“它預(yù)先做出了許多規(guī)定,減少了溝通和決策的負(fù)擔(dān),協(xié)調(diào)了不同行為者的期望”。⑧[美]卡爾·多伊奇著,周啟朋譯:《國(guó)際關(guān)系分析》,世界知識(shí)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71-272 頁(yè)。而逆全球化的出現(xiàn),無疑使制度理性遭到?jīng)_擊,從而給現(xiàn)有的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制造障礙。 一方面,這與國(guó)際社會(huì)現(xiàn)有的團(tuán)結(jié)機(jī)制缺陷有關(guān),“如聯(lián)合國(guó)安理會(huì)的目標(biāo)是保證國(guó)際社會(huì)集體安全,國(guó)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目標(biāo)是保證國(guó)際金融穩(wěn)定,世界銀行的目標(biāo)是消除貧困,但今天這個(gè)世界上,集體安全、經(jīng)濟(jì)穩(wěn)定和共同富有的合理需求在許多國(guó)家和地區(qū)仍是嚴(yán)重匱乏的”。⑨潘一禾:“多元認(rèn)同方式與國(guó)際社會(huì)認(rèn)同”,《杭州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8 年第 4 期,第 62 頁(yè)。另一方面,又與機(jī)制自身的現(xiàn)實(shí)約束力有關(guān)。國(guó)際制度與規(guī)則是主權(quán)國(guó)家通過締約賦予的,因而是有限的。 即便作為最具權(quán)威性的制度,“聯(lián)合國(guó)大會(huì)的決議只不過是反映著大多數(shù)成員政府利益的虔誠(chéng)的期望而已。 這些決議既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具有實(shí)質(zhì)上的約束力”。①[美]西奧多·A·哥倫比斯、[美]杰姆斯·H·沃爾夫著,白希譯:《權(quán)力與正義》,華夏出版社,1990 年版,第317 頁(yè)。
盡管如此,現(xiàn)有機(jī)制對(duì)于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依然起著關(guān)鍵作用。 一方面,“國(guó)際制度改革不可能在‘一張白紙’上理想地進(jìn)行,必須在原有的歷史遺產(chǎn)基礎(chǔ)上逐步改進(jìn)”。②潘一禾:“多元認(rèn)同方式與國(guó)際社會(huì)認(rèn)同”,《杭州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8 年第 4 期,第 62 頁(yè)。另一方面,目前在國(guó)際社會(huì)中,對(duì)于現(xiàn)存國(guó)際秩序與制度表示完全不認(rèn)同的國(guó)家?guī)缀醪淮嬖凇?因此,在信任基礎(chǔ)依然存在的前提下,維護(hù)并完善現(xiàn)有機(jī)制將是合理的選擇。 為此,在聯(lián)合國(guó)框架內(nèi),要強(qiáng)化對(duì)話機(jī)制,通過對(duì)話與合作紓解全球化發(fā)展帶來的問題,避免陷入制裁與反制裁、沖突與對(duì)抗的惡性循環(huán)。 同時(shí),要加強(qiáng)多邊機(jī)制建設(shè),發(fā)展中國(guó)家要尤其加大合作,建立更廣泛的團(tuán)結(jié)。
第二,堅(jiān)持共商共建共享,探索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新機(jī)制。 制度失靈是引發(fā)逆全球化的重要因素。 表面上,這種制度失靈不僅與現(xiàn)行機(jī)制的碎片化有關(guān),也與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所蘊(yùn)含的危機(jī)存在很大關(guān)系。 然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文化層面。 一直以來,西方國(guó)家在世界秩序上推崇人性惡假設(shè),習(xí)慣以“二元對(duì)立”的沖突觀審視和處理外界關(guān)系。 受其影響,“近代以來,國(guó)際制度的建立和發(fā)展基本上源于西方文化,無論從組織形式還是文本風(fēng)格,都體現(xiàn)了西方文化價(jià)值觀的要求,成為國(guó)際制度中的主流價(jià)值取向”。③同②。因此,探索建立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新機(jī)制顯得尤為重要。
團(tuán)結(jié)新機(jī)制的建立,重點(diǎn)要突破新自由主義利己、虛偽的本質(zhì)。 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國(guó)際社會(huì)現(xiàn)有團(tuán)結(jié)機(jī)制以維護(hù)美歐西方大國(guó)的利益為出發(fā)點(diǎn),“市場(chǎng)規(guī)則只對(duì)你,不對(duì)我;除非‘游戲場(chǎng)’正好向著有利于我的方向發(fā)生偏斜”。④[美]諾姆·喬姆斯基著,徐海銘、季海宏譯:《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49 頁(yè)。為此,新機(jī)制的建立要緊緊圍繞三個(gè)方面:其一,杜絕話語權(quán)單一,崇尚多方參與。 其二,避免重利輕義,推崇“義利相兼、以義為先”。 其三,規(guī)避自由風(fēng)險(xiǎn),注重公平與共贏。 在逆全球化業(yè)已引發(fā)“全球主義已經(jīng)死亡”⑤Jayshree Bajoria, “The Danger of ‘ Deglobalization’,”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16, 2009, http: / /www.cfr.org/immigration/dangers-deglobalization/p18768.等悲觀論調(diào)的背景下,探索構(gòu)建團(tuán)結(jié)新機(jī)制的主要目的在于繼續(xù)支持全球化,其核心特點(diǎn)是開放與包容,“它不同于以往以市場(chǎng)為導(dǎo)向的單一模式的全球化,而是以發(fā)展為導(dǎo)向、強(qiáng)調(diào)包容性增長(zhǎng)、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新型全球化”。⑥盛斌、黎峰:“逆全球化:思潮、原因與反思”,《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問題》,2020 年第 2 期,第 12 頁(yè)。毫無疑問,這正是習(xí)近平總書記所致力倡建的“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這一時(shí)代命題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
“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是中國(guó)站在全人類高度,對(duì)于人類發(fā)展與未來走向的系統(tǒng)思考,⑦習(xí)近平:“順應(yīng)時(shí)代前進(jìn)潮流促進(jìn)世界和平發(fā)展”,《人民日?qǐng)?bào)》,2013 年 3 月 24 日,第 2 版。和而不同、共贏發(fā)展是其內(nèi)核。 因與新自由主義存在顯著差異,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對(duì)于這一新的理念,必然有所忌憚。 為此,在實(shí)際構(gòu)建過程中,要堅(jiān)持團(tuán)結(jié)多數(shù)、爭(zhēng)取少數(shù)的原則,廣泛建立以發(fā)展中國(guó)家為主體、涵蓋不同國(guó)家及國(guó)際組織在內(nèi)的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統(tǒng)一戰(zhàn)線,加強(qiáng)對(duì)話協(xié)調(diào),凝聚共同主張。 具體而言,一是體現(xiàn)差異,堅(jiān)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底色,恪守與現(xiàn)有“贏者通吃”規(guī)則的區(qū)別。 二是強(qiáng)調(diào)包容。 要堅(jiān)持以發(fā)展為導(dǎo)向,不斷推進(jìn)涵蓋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內(nèi)的世界各國(guó)發(fā)展。 三是凸顯責(zé)任。 彰顯大國(guó)擔(dān)當(dāng)?shù)某缮?積極推動(dòng)“一帶一路”建設(shè),大力提供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基于平等互利,攜手發(fā)展中國(guó)家實(shí)現(xiàn)共同發(fā)展。
六、結(jié) 語
針對(duì)逆全球化何以產(chǎn)生,筆者基于國(guó)際政治社會(huì)學(xué)視角,重點(diǎn)從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層面嘗試展開新的解讀。 立足于現(xiàn)有研究,通過將逆全球化納入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這一時(shí)空范疇當(dāng)中,筆者重點(diǎn)從行動(dòng)者即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認(rèn)知—行動(dòng)”角度,對(duì)其發(fā)生過程進(jìn)行了動(dòng)態(tài)分析。 其一,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是全球化作用下,國(guó)家幸福追求與幸福實(shí)踐的統(tǒng)一,存在互利與自利兩種路徑。其二,受市場(chǎng)規(guī)律支配,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存在“正向效應(yīng)”“負(fù)向效應(yīng)”兩種空間。 即便是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也無法對(duì)后者產(chǎn)生天然免疫。 其三,鑒于本國(guó)治理不善與全球化沖擊,在“受損者”身份轉(zhuǎn)型下,承擔(dān)國(guó)際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存在“受損”持續(xù)化和國(guó)內(nèi)幸福追求的壓力。 受人性惡的西方價(jià)值觀影響,為了轉(zhuǎn)移本國(guó)矛盾、獲取選民支持,他們傾向于選擇自利路徑,由此產(chǎn)生逆全球化。 其四,逆全球化集中表現(xiàn)為重利、輕義、玩弄規(guī)則。 面對(duì)其給國(guó)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帶來的破壞,根本的應(yīng)對(duì)之策是建立新的制度安排,推動(dòng)全球化轉(zhuǎn)型升級(jí)。 其中,既要在現(xiàn)有體系內(nèi)重塑制度理性,又要堅(jiān)持共商共建,探索制度超越,中國(guó)無疑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關(guān)于如何發(fā)揮“中國(guó)力量”、貢獻(xiàn)“中國(guó)智慧”,將是后續(xù)研究的一個(gè)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