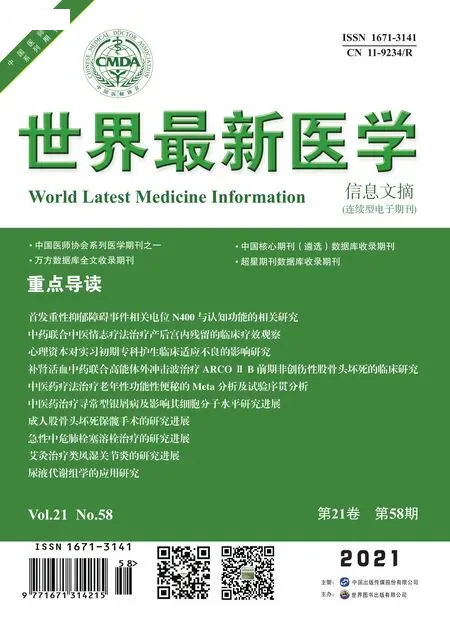中醫(yī)診治兒童及青少年抑郁癥的研究進展
趙森瑩,楊其芬,楊祥正
(深圳市龍崗區(qū)中醫(yī)院,廣東 深圳 518172)
0 引言
兒童和青少年抑郁癥與基因遺傳、性格、家庭經歷等有關,是指發(fā)生在未成年時期,以顯著、持續(xù)的情緒失落、興趣缺失為主要表現(xiàn)的一種精神疾病。由于特殊的時代因素,現(xiàn)發(fā)病率較高,且逐年上升,并有低齡化趨勢,嚴重危害兒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近年來,臨床醫(yī)生對其關注程度不斷提高。目前西醫(yī)治療方法主要有心理治療、藥物治療、物理治療[1]。藥物治療方案服用時間長,費用較高,且存在不良反應,部分藥物有增加未成年人自殺風險的可能[1],而中醫(yī)治療本病具有明顯優(yōu)勢。近年來關于中醫(yī)治療本病的報道逐漸增多,主要通過辨證論治及與西醫(yī)結合達到標本兼治的目的。本文通過綜述近年來中醫(yī)對兒童及青少年抑郁癥的臨床研究最新情況,為該疾病的中醫(yī)治療提供依據。
1 兒童及青少年抑郁癥中醫(yī)病名的認識
中醫(yī)沒有抑郁癥病名,兒童及青少年抑郁癥屬于中醫(yī)郁證、郁病的范疇。中醫(yī)認為其是以悲憂善哭、心神不寧、煩躁不寐、食欲減退、精神恍惚為主癥的一種病證。《黃帝內經》部分章節(jié)對抑郁癥做了描述,雖未提及抑郁癥的病名,但“鬼神”的表現(xiàn)當歸屬現(xiàn)代抑郁癥的范疇。張仲景在描述郁證臟躁及百合病特點時也用了“象如神靈所作”“如有神靈”之類的詞匯,其來源均為《黃帝內經》[2]。國醫(yī)大師路志正則認為抑郁癥可以參考中醫(yī)文獻記載中的意傷、郁證、百合病論治[3]。亦有辨為“狐惑病”“臟躁”“卑惵”者。
2 兒童及青少年抑郁癥中醫(yī)病因病機的認識
中醫(yī)對郁證、郁病的中醫(yī)病因病機有深入認識。《黃帝內經》提出了情志致病,而且將情志致病看作與外感邪氣致病處于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對于郁證的因機證治,進行了深入而全面的介紹:在病因方面,指出情志不遂可對人體造成傷害;在病機證候方面,指出郁證的病機特點為氣機郁滯或紊亂[2]。《素問·舉痛論》指出“余知百病生于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4]。《素問·六微旨大論》指出:“氣機調暢人即安合,一有怫郁,百病尤生。”[4]
古代醫(yī)家認為,郁證不僅發(fā)生于成年人,也發(fā)生于小兒,如《溫病條辨·解兒難》認為:“小兒但無色欲耳,喜怒悲恐,較之成人,更專且篤”[5]。《續(xù)名醫(yī)類案》記載了2則小兒郁證醫(yī)案。病因皆為情境改變,導致小兒情志不遂,思慮不已,發(fā)為郁證。醫(yī)者通過詢問病史,發(fā)現(xiàn)了小兒情志不遂發(fā)生的原因。滿足小兒情志所需后,小兒氣機調暢,郁結得開,病證即獲自愈[6]。
但總體來講,既往醫(yī)家認為小兒較少存在七情致病的狀況,對小兒郁證關注較少,然而,隨著時代、社會的變遷,由于現(xiàn)代育兒方式、理念的影響,小兒氣機郁滯或紊亂者已不在少數,并可延續(xù)至其青少年、成年人階段,表現(xiàn)在統(tǒng)計數據上即為抑郁癥患者的逐年上升。
2.1 稟賦對小兒發(fā)生郁證的影響
現(xiàn)代醫(yī)學認為,遺傳因素是抑郁癥發(fā)病的重要因素。如一級親屬患有抑郁癥,患病的可能性就越高,遠高于其他親屬。研究發(fā)現(xiàn)父母患有抑郁障礙的,其子女發(fā)生抑郁障礙的概率約為健康父母子女的3-4倍,并且這些子女抑郁的預后也可能特別差[7]。
《黃帝內經·靈樞》指出了部分人群存在“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于病”的現(xiàn)象,并認為原因與個體心有大小、志有堅脆有關。心小志脆,即多思多慮、疑神疑鬼、心結難解、無故悲傷者,即使外在并無負性生活事件發(fā)生,仍可自內生出煩惱與恐懼;情志不遂而得郁證,心大志堅者,志意堅強,雖有深憂大恐怵惕的遭遇,仍能在思想上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影響身體健康[2]。說明郁證的發(fā)生與稟賦有關。
2.2 現(xiàn)代育兒方式對小兒發(fā)生郁證的影響
由于當代社會生活節(jié)奏緊張,新生兒期母嬰分離導致母愛缺失較以往顯著增多,在兒童成長過程中,身為職場女性的母親也往往難以給予兒童較多的陪同和關愛。
另外,現(xiàn)代生活方式對小兒脾臟有較大不良影響。脾之功能本為運化水谷精微及水液,維持機體正常功能。小兒生機旺盛,發(fā)育迅速,但其脾胃功能尚不完善,飲食亦不知自節(jié),冰箱等家電和飲用冰凍飲料習慣的普及,更讓兒童多食寒涼之品,損傷脾陽,加之現(xiàn)代家庭多溺愛小兒,縱其多食、暴食,擇食亦不辨優(yōu)劣,多食高熱量、高糖高蛋白食物,使得痰濕內生,肝氣正常疏泄受到阻滯,肝氣郁結最終也影響脾臟功能,因此當代小兒較古代小兒更易出現(xiàn)“脾常不足”。
2.3 不良環(huán)境對小兒發(fā)生郁證的影響
在小兒步入學齡期,進入學校接受教育后,又面臨新的學業(yè)壓力。孫思邈在《千金翼方》中闡述了古代育兒理念:“十歲以下,依禮小學,而不得苦精功程,必令兒失心驚懼;及不得苦行杖罰,亦令兒得癲癇,此事大可傷怛;但不得大散大漫,令其志蕩;亦不得稱贊聰明;尤不得誹毀小兒。十一以上,得漸加嚴教。此養(yǎng)子之大經也。不依此法,令兒損傷,父母之殺兒也,不得怨天尤人。”[8]然而,由于望子成龍的心理和學歷內卷帶來的焦慮,現(xiàn)代家庭中的父母往往對兒童及青少年的學業(yè)采取“苦精功程”的做法,使其“失心驚懼”,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
另外,部分小兒生長于存在家庭冷暴力、父母離異、父母打罵小兒或父母存在專制的家庭教養(yǎng)方式,根據自身的意向和喜好干預小兒的興趣愛好和個人行為的家庭,還有部分小兒遭遇人際關系緊張等負性生活事件、又采取消極的歸因方式。
這些因素都會導致兒童氣機郁滯,尤易影響肝、脾二臟。《丹溪心法》及《醫(yī)門法律》分別指出:“氣血沖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于郁。”[9]、“諸病多生于肝”[10]。且小兒還有“肝常有余、脾常不足”的生理特點。肝主疏泄,乃人體氣血調控之樞紐,一旦其失于疏泄,不僅本臟易發(fā)生病變,還可波及它臟,最常見的便是肝有余則克脾,使得小兒的“脾常不足”進一步加重,導致郁證易感性增加。
2.4 諸家對小兒郁證病因病機的認識
對于郁證的病機,現(xiàn)代許多專家學者提出不同的見解,例如,國醫(yī)大師路志正指出,“志意”具有“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等功能,抑郁癥的發(fā)生與“志意”傷損有關[3]。閻兆君也認為,志不足、意不舒,可致魂弱魄抑、精神不專、情志失常,故抑郁癥基本病機為神魂不足、意郁魄抑[11]。劉盼等從心常有余、脾常不足出發(fā),認為兒童思慮過度亦可致心脾兩虛之證。心脾氣血兩虛日久,脾失健運,氣機不暢致痰濕內生、痰蒙清竅,血不養(yǎng)肝、土不達木可致肝失疏泄、肝氣郁結而出現(xiàn)抑郁癥,故兒童抑郁癥的病位主要在“心、脾”兩臟,其病機之本為心脾兩虛,標為肝郁痰阻[12]。馬丙祥提出,抑郁癥最主要的病因是肝失疏泄,肝郁不疏是郁病的核心病機,肝郁氣滯則貫穿了郁病的始末,認為本病的病因病機主要為肝失疏泄兼脾失健運、腎陽不足[13]。陳鴻雁鑒于“脾常不足”“治脾可以安五臟”,提出郁病雖然與五臟皆相關,但在治療上應以調理脾胃為主[14]。余云進認為,青少年時期為陽氣生發(fā)之初,對應少陽,其抑郁癥的形成與少陽樞機不利密切相關。青少年在學業(yè)競爭壓力、父母和成長環(huán)境等外在因素影響下,情緒極易受到影響,導致陽氣不升,氣機郁滯,且現(xiàn)今青少年因使用網絡與手機,普遍晚睡,而子時(23時至1時)是少陽時令,長期的晚睡及低質量睡眠勢必會阻礙陽氣的開闔樞,導致少陽之樞運轉不利,經氣流動不暢、氣機郁結,形成抑郁癥[15]。韋卿等認為該病發(fā)生與以下方面有關:個人體質;或是受到外界環(huán)境刺激致自身情感壓抑而不得宣泄,引起氣機郁滯,造成體內臟腑氣機紊亂、功能失調,影響臟腑功能,從而誘發(fā)陰虛火旺、氣血不和、肝氣郁滯、心神失養(yǎng),導致抑郁癥發(fā)生[16]。何淑琴等認為郁癥病機為陰陽失調,形神失合[17]。
3 中醫(yī)分型治療及相關研究
3.1 中藥分型治療
3.1.1 中藥
路老嘗以養(yǎng)血柔肝、和胃降濁之法治血虛神躁、肝胃不和青少年抑郁癥患者1例,緩解后繼以疏肝解郁,運脾調中收功[3]。馬丙祥指出郁證的病因病機為肝失疏泄兼脾失健運、腎陽不足,認為應用小柴胡湯隨證加減,以疏肝解郁、運脾溫陽之法治療本病[13]。陳鴻雁提出,郁證可分為不同證型: (1)脾胃虧虛型。本型應以歸脾湯為主健脾養(yǎng)心安神。(2)邪阻中焦型。治療以祛邪為主,方選越鞠丸加減,重在行氣解郁、通調氣機[14]。劉盼等認為兒童抑郁癥病機之本為心脾兩虛,標為肝郁痰阻,治療上以補益心脾為主,解郁化痰及心理疏導為輔,方選“養(yǎng)心解郁湯”,處方:西洋參、龍眼肉、合歡花、郁金、遠志、石菖蒲、白芍、柴胡、大棗[12]。呂秀玲治療青少年抑郁癥患者1例,辨為肝郁脾虛且心脾兩虛夾濕,治以疏肝解郁、養(yǎng)心安神、健脾化痰而收效[18]。
3.1.2 中成藥
史盼等觀察舒肝解郁膠囊聯(lián)合鹽酸舍曲林治療青少年首發(fā)抑郁癥,發(fā)現(xiàn)其總有效率高于單用鹽酸舍曲林的對照組,可緩解抑郁癥狀,且不良反應較少[19]。平晶等觀察消郁安神湯聯(lián)合疏肝解郁膠囊對青少年抑郁癥的療效,發(fā)現(xiàn)給予消郁安神湯聯(lián)合疏肝解郁膠囊治療的聯(lián)合組患者較僅給予疏肝解郁膠囊治療的對照組療效更好[20]。
3.1.3 中藥藥對
閻兆君在治療青少年抑郁癥方面,主張志意辨證結合臟腑、氣血、津液辨證,常以巴戟天與蒼術配伍,從志(巴戟天)意(蒼術)角度治療[11]。初倩等研究認為巴戟天-蒼術藥對發(fā)揮治療青少年抑郁癥的作用途徑可能是通過神經活性配體-受體相互作用、多巴胺能突觸、5-羥色胺能突觸、MAPK等多種信號通路參與神經可塑性、信號傳導、激素調節(jié)、炎癥反應等生物過程[11]。
3.2 針灸
王志堅等對青少年癲癇伴發(fā)抑郁狀態(tài)的患者采取電針治療,取穴百會、三陰交、印堂、水溝以及豐隆等。經治療,患者思維遲滯、情緒低落等癥狀得到顯著改善,且癲癇的發(fā)作次數減少[21]。余云進認為治療青少年抑郁當從少陽入手,運用調暢少陽經氣使樞機通利的思路取穴。從頸項部選穴以調肝且行少陽經氣,再結合少陽經循行過頸項的經絡分布特點,主選風池、風府、天柱、完骨、翳風、天牖,以通利少陽之樞,疏導少陽經氣之法而助陽氣生長升發(fā),舒暢氣機,調節(jié)情志[15]。董艷等觀察調督通腦針法針刺配合心理療法對青少年抑郁癥的治療效果。主穴:百會、神庭、啞門、肝俞、心俞、脾俞、腎俞、太沖、神門、內關、膻中,并配合心理療法。發(fā)現(xiàn)調督通腦針法針刺結合心理療法治療較西藥結合心理療法起效更快且療效穩(wěn)定,而不良反應更少[22]。口鎖堂觀察針刺輔助抗抑郁藥物對青少年抑郁癥的療效,在口服抗抑郁藥物的基礎上,給予針刺治療。主穴:四神聰、風池、鳩尾、內關、合谷、豐隆、太沖。發(fā)現(xiàn)針刺可有效減輕抗抑郁藥副反應,減少抗抑郁藥的應用劑量,減少青少年抑郁癥的復發(fā)[23]。楊超等以電針刺激迷走神經,觀察其對青少年抑郁癥患者的臨床療效及炎性因子表達水平的影響,發(fā)現(xiàn)電針刺激迷走神經+舍曲林的治療組較單用舍曲林的對照組抗抑郁作用更佳,且與降低炎性因子表達水平有關[24]。韋卿等觀察帕羅西汀配合針灸治療青少年抑郁癥效果。其選穴以豐隆、百會、陽陵泉為一組,內關、印堂、太溪為一組,兩組隔日交替使用,針刺后在上述穴位進行艾灸,同時結合夾脊穴針刺。發(fā)現(xiàn)與鹽酸帕羅西汀單藥治療比較,鹽酸帕羅西汀配合針灸治療青少年抑郁癥效果更好,且可減輕藥物毒副作用,推測其原因可能與以下方面有關:針灸既能興奮神經—內分泌—免疫調節(jié)網絡衰退的功能,又能抑制其過度亢奮狀態(tài),使生理激素水平恢復正常,達到“陰陽調和、扶正祛邪”效果;夾脊穴是調理臟腑氣血陰陽的樞紐,針刺夾脊穴能調和陰陽,利于平衡神經遞質;情感低落、食欲減退等抑郁癥表現(xiàn)與中醫(yī)陽氣不足相符,而艾灸可扶陽,調動一身氣機[16]。
3.3 針灸、中藥并用
何淑琴等等觀察電針配合解郁安神湯、鹽酸舍曲林治療青少年抑郁癥效果。電針取穴:百會、印堂,同時配以小劑量鹽酸舍曲林及解郁安神湯。發(fā)現(xiàn)電針配合解郁安神湯、鹽酸舍曲林治療青少年抑郁癥比單用鹽酸舍曲林療效好[17]。青少年抑郁癥患者中多數血清尿酸增高,劉靜等由此觀察柴胡加龍骨牡蠣湯配合針刺對青少年抑郁癥患者的療效,發(fā)現(xiàn)柴胡加龍骨牡蠣湯配合辨證針刺的治療組療效明顯優(yōu)于僅使用鹽酸氟西汀的對照組,并且能有效降低血清尿酸水平[25]。齊建華等觀察針刺聯(lián)合柴胡桂枝干姜湯對青少年抑郁癥的療效,發(fā)現(xiàn)給予針刺聯(lián)合柴胡桂枝干姜湯的治療組較給予鹽酸氟西汀的對照組療效更好,且治療后的肝膽經循行于脅肋部的溫度及兩經的原穴穴位溫度減低更明顯[26]。
3.4 動物實驗
郭麗麗等對青少期大鼠進行母子分離,以此誘導其抑郁樣行為學改變,觀察其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軸)的變化以及調肝方藥加味四逆散對其的干預作用,發(fā)現(xiàn)母子分離后慢性不可預計性應激可誘導青少期大鼠出現(xiàn)抑郁樣行為,而加味四逆散可改善此狀況,并在一定程度上調節(jié)HPA軸功能,具有一定抗青少期抑郁癥的作用[27]。斷奶前母本隔離可顯著增加小鼠的焦慮樣行為及下丘腦室旁核(PVN)腦區(qū)C-Fos陽性神經元表達,降低小鼠血清催產素(OT)表達。袁偉等觀察針灸干預對斷奶前母本隔離模型小鼠情緒、PVN神經元C-Fos及血清OT表達的影響,發(fā)現(xiàn)針灸耳穴干預可顯著緩解因早期生活壓力所致的情緒異常,逆轉PVN腦區(qū)C-Fos陽性神經元、血清OT的表達,為針灸治療兒童抑郁癥提供了理論及實驗依據[28]。
3.5 其他相關研究
譚詩亮等指出,利用中醫(yī)心理理論結合中醫(yī)治病思想制定的符合我國青少年心理狀態(tài)的中醫(yī)心理治療對青少年閾下抑郁的預防和治療效果較好,并認為中西醫(yī)心理治療方法相結合、中醫(yī)心理治療方法與現(xiàn)代科技手段相結合的青少年閾下抑郁干預模式具有較大臨床潛力[29]。
趙澤琳等指出音樂對兒童、青少年抑郁癥患者具有良好治療作用,且針對患者病癥發(fā)生的臟腑、經絡結合陰陽五行之間相生相克的關系開展的五行音樂療法對改善患者的抑郁狀態(tài)有顯著作用[30]。
總之,在兒童、青少年抑郁癥的臨床觀察中,最常見的證型是肝氣郁結證,諸家多從肝、脾、心入手,認為肝、脾、心失調是關鍵。中醫(yī)治療上,總的治療原則是通過調肝、脾、心來糾正兒童及青少年抑郁癥的病機和改善癥狀,調肝是本病治療大法,應貫穿治療的始終。
4 討論
兒童及青少年抑郁癥屬于典型的身心疾病。中醫(yī)的醫(yī)學模式是自然-生物-心理-社會模式,故在調治身心疾病方面有著突出的優(yōu)勢和理念,并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通過辨證論治和辨病辨證相結合,可根據兒童及青少年抑郁癥患者的具體的病因、病機、證型制定個體化的治療方案,配合西醫(yī)方法治療,改善患者臨床癥狀、生活質量。但目前這方面研究大多仍屬于單中心、小規(guī)模研究報道,對證型的劃分也欠統(tǒng)一,亟需進一步規(guī)范化,并開展多中心、大樣本的研究,以期為應用中醫(yī)藥治療兒童及青少年抑郁癥提供更多理論基礎和新的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