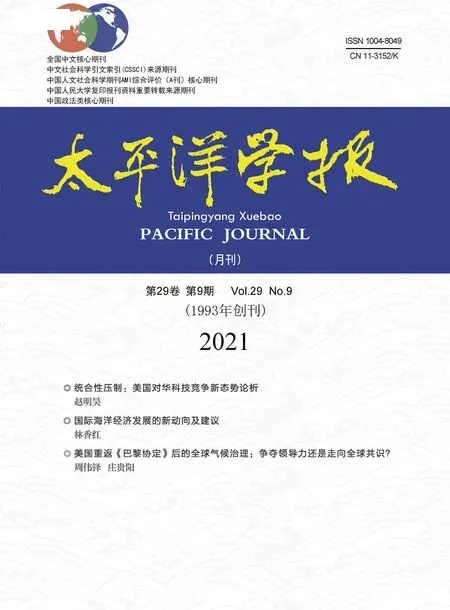美國(guó)重返《巴黎協(xié)定》后的全球氣候治理:爭(zhēng)奪領(lǐng)導(dǎo)力還是走向全球共識(shí)?
周偉鐸 莊貴陽(yáng)
(1.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上海 200020;2.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北京 100710)
當(dāng)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guó)際秩序進(jìn)入動(dòng)蕩調(diào)整期。①陳須隆:“在世界大變局中推動(dòng)國(guó)際秩序演變的方略和新視角”,《太平洋學(xué)報(bào)》,2021年第1期,第35-42頁(y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國(guó)際大變局的進(jìn)程,當(dāng)前世界格局或?qū)⒊尸F(xiàn)出中美歐三個(gè)超大經(jīng)濟(jì)體、多個(gè)中等強(qiáng)國(guó)并存的“三超多強(qiáng)”架構(gòu)。②張宇燕:“后疫情時(shí)代的世界格局:‘三超多強(qiáng)’?”《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2021年第1期,第1頁(yè)。疫情防控常態(tài)化背景下,應(yīng)對(duì)全球氣候變化成了世界主要經(jīng)濟(jì)體重點(diǎn)關(guān)注的議題。歐盟正在加緊落實(shí)《歐洲綠色協(xié)議》(European Green Deal)的相關(guān)政策,中國(guó)以內(nèi)外一致的邏輯推進(jìn)2030年前碳達(dá)峰、2060年前實(shí)現(xiàn)碳中和目標(biāo)愿景,美國(guó)也在拜登政府上臺(tái)之后正式重返《巴黎協(xié)定》,全球氣候治理再次呈現(xiàn)中美歐三方鼎立的格局。
當(dāng)前在全球氣候治理領(lǐng)域,大國(guó)博弈的特征凸顯,而中國(guó)、美國(guó)和歐盟再次成為主導(dǎo)全球氣候治理走向的“三駕馬車”。美國(guó)重返《巴黎協(xié)定》,意味著中美歐三大經(jīng)濟(jì)體在致力于實(shí)現(xiàn)長(zhǎng)期目標(biāo)方面達(dá)成共識(shí)——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內(nèi),并努力控制在1.5℃以內(nèi)。本文在國(guó)內(nèi)外學(xué)界對(duì)全球氣候治理已有研究的基礎(chǔ)上,以“美國(guó)重返《巴黎協(xié)定》”為切入點(diǎn),試圖回答以下問(wèn)題:當(dāng)前階段,美國(guó)拜登政府爭(zhēng)做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者的動(dòng)因是什么?中美歐三大經(jīng)濟(jì)體如何體現(xiàn)氣候領(lǐng)導(dǎo)力?中美歐三大經(jīng)濟(jì)體圍繞全球氣候治理可能進(jìn)行合作的領(lǐng)域是哪些?
一、全球氣候治理格局的深刻調(diào)整:機(jī)理及進(jìn)程
《巴黎協(xié)定》的簽署和生效意味著世界各國(guó)應(yīng)致力于實(shí)現(xiàn)達(dá)成共識(shí)的長(zhǎng)期目標(biāo),這需要全球碳排放快速達(dá)到峰值,且203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與2010年相比要降低45%,并在21世紀(jì)中葉達(dá)到凈零碳排放量。①“Global Warming of 1.5℃,”IPCC,https://www.ipcc.ch/sr15/,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4月27日。中國(guó)、美國(guó)和歐盟作為推動(dòng)《巴黎協(xié)定》達(dá)成的重要力量,在國(guó)際氣候治理領(lǐng)域的利益訴求各有差異,因而在推動(dòng)《巴黎協(xié)定》目標(biāo)及實(shí)施細(xì)則落實(shí)方面存在博弈。
1.1 全球氣候治理需要領(lǐng)導(dǎo)者推動(dòng)形成集體理性的共識(shí)
全球治理更多體現(xiàn)為國(guó)際政治和世界經(jīng)濟(jì)中為了應(yīng)對(duì)各種全球性問(wèn)題而設(shè)立的各種規(guī)范、規(guī)則、程序和機(jī)制。②謝來(lái)輝:“‘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的關(guān)系——一個(gè)類型學(xué)分析”,《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2019年第1期,第34-58頁(yè)。全球氣候治理是針對(duì)全球氣候變化問(wèn)題而開展的國(guó)際集體行動(dòng),最終目的是穩(wěn)定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而這是一種典型的加總型公共物品,因?yàn)楦鲊?guó)全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努力的結(jié)果才能導(dǎo)致全球大氣溫室氣體濃度在特定水平維持穩(wěn)定的結(jié)果。③謝來(lái)輝:“領(lǐng)導(dǎo)者作用與全球氣候治理的發(fā)展”,《太平洋學(xué)報(bào)》,2012第1期,第83-92頁(yè)。而對(duì)于加總型公共物品來(lái)說(shuō),大國(guó)領(lǐng)導(dǎo)是達(dá)成集體行動(dòng)推動(dòng)全球公共物品供給的關(guān)鍵。④Daniel Arce,“Leadership and the Aggreg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Actions,”O(jiān)xford Economic Papers,Vol 53,No.1,2001,pp.114-137.
第一,基于集體理性的多邊主義本應(yīng)是氣候領(lǐng)導(dǎo)者達(dá)成氣候共識(shí)的根本倫理原則。冷戰(zhàn)結(jié)束以來(lái),新興市場(chǎng)國(guó)家群體性崛起和發(fā)展中國(guó)家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中的份額不斷提升,使得發(fā)展中國(guó)家成為全球氣候治理進(jìn)程中問(wèn)題“引爆者”“發(fā)源地”“重災(zāi)區(qū)”的疊加效應(yīng)明顯,提高多邊機(jī)制代表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迅速增強(qiáng)。⑤吳志成、劉培東:“促進(jìn)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的中國(guó)視角”,《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2020年第9期,第23-44頁(yè)。而隨著全球氣候風(fēng)險(xiǎn)的逐漸凸顯,氣候風(fēng)險(xiǎn)對(duì)于人類來(lái)說(shuō),已經(jīng)超越了國(guó)家界限。應(yīng)對(duì)全球氣候變化,一國(guó)利益難以同人類共同利益進(jìn)行徹底分割。對(duì)全球氣候治理領(lǐng)導(dǎo)者來(lái)說(shuō),“人類”身份的“共同性”和氣候責(zé)任的“共同性”是相伴相生的,基于這一身份產(chǎn)生的共同理性和生存理性是達(dá)成氣候基本共識(shí)的理論基礎(chǔ)。⑥張肖陽(yáng):“后《巴黎協(xié)定》時(shí)代氣候正義基本共識(shí)的達(dá)成”,《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8年第6期,第90-100頁(yè);華啟和:“氣候政治博弈對(duì)倫理共識(shí)的訴求”,《中國(guó)地質(zh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年第3期,第15-19頁(yè)。多邊機(jī)制要求國(guó)際合作以互利為目標(biāo)取向,以共贏推動(dòng)多邊合作的持續(xù)發(fā)展。多邊主義的互惠性實(shí)現(xiàn)了個(gè)體利益的相容性蛻變,使國(guó)家間互動(dòng)由競(jìng)爭(zhēng)性零和博弈轉(zhuǎn)向合作性正和競(jìng)爭(zhēng)。
第二,基于個(gè)體理性的單邊主義和保護(hù)主義帶來(lái)的氣候領(lǐng)導(dǎo)者博弈,使得全球氣候治理進(jìn)程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個(gè)體理性是當(dāng)今世界西方民族國(guó)家世界秩序觀的理性基礎(chǔ),個(gè)體理性強(qiáng)調(diào)行為體的行為動(dòng)機(jī)是追求個(gè)體利益最大化。⑦郭樹勇、于陽(yáng):“全球秩序觀的理性轉(zhuǎn)向與‘新理性’——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理性基礎(chǔ)”,《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2021年第4期,第4-32頁(yè);高奇琦:“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觀的差異及其調(diào)和”,《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2015年第4期,第68-70頁(yè)。個(gè)體理性觀導(dǎo)致戰(zhàn)后冷戰(zhàn)思維與零和博弈主導(dǎo)世界秩序,而冷戰(zhàn)結(jié)束后,基于個(gè)體理性的全球氣候治理觀依然在全球氣候治理進(jìn)程中發(fā)揮重要影響。基于個(gè)體理性導(dǎo)致世界各國(guó)的談判立場(chǎng)存在的差異難以協(xié)調(diào),全球氣候治理出現(xiàn)“囚徒困境”的情況。基于個(gè)體理性的單邊主義、保護(hù)主義愈演愈烈,領(lǐng)導(dǎo)者“退群”、設(shè)置“碳關(guān)稅”等霸權(quán)主義行為對(duì)全球氣候治理多邊談判體制帶來(lái)嚴(yán)重沖擊,造成全球氣候治理進(jìn)程的混亂和失序。
第三,發(fā)展階段的“南北分割”導(dǎo)致氣候治理領(lǐng)導(dǎo)者的談判立場(chǎng)沖突。全球氣候危機(jī)產(chǎn)生的本質(zhì)是人類不合理的發(fā)展方式造成的“公地悲劇”。盡管在《聯(lián)合國(guó)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文簡(jiǎn)稱《公約》)談判階段就已經(jīng)形成了發(fā)達(dá)國(guó)家陣營(yíng)和發(fā)展中國(guó)家陣營(yíng),而全球氣候治理興起之時(shí)正值冷戰(zhàn)結(jié)束,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處于壓倒一切的支配性地位,全球氣候治理初始階段的進(jìn)程由西方國(guó)家的目標(biāo)、優(yōu)先考慮和利益所主導(dǎo)。氣候政治博弈的核心是國(guó)家、集團(tuán)之間的利益紛爭(zhēng),以及“權(quán)力話語(yǔ)”的爭(zhēng)奪,而如何分配未來(lái)溫室氣體排放空間成了兩大陣營(yíng)氣候分歧的焦點(diǎn)。發(fā)達(dá)國(guó)家自工業(yè)革命以來(lái)排放的溫室氣體累積構(gòu)成了當(dāng)前大氣層中溫室氣體的絕大部分,一些國(guó)家在《公約》談判階段已實(shí)現(xiàn)碳達(dá)峰;而發(fā)展中國(guó)家由于發(fā)展權(quán)的需要,碳排放至今仍在增加。在國(guó)際氣候談判中,“南北分割”現(xiàn)象日益明顯。美國(guó)、歐盟等發(fā)達(dá)經(jīng)濟(jì)體利用其政治、經(jīng)濟(jì)、科技、傳播等方面的雄厚實(shí)力與話語(yǔ)權(quán)優(yōu)勢(shì),根據(jù)自身利益、標(biāo)準(zhǔn)及知識(shí)制定規(guī)則,從大國(guó)競(jìng)爭(zhēng)的角度出發(fā)“積極”推動(dòng)發(fā)展中國(guó)家落實(shí)減排責(zé)任。①李昕蕾:“全球氣候治理中的知識(shí)供給與話語(yǔ)權(quán)競(jìng)爭(zhēng)——以中國(guó)氣候研究影響IPCC知識(shí)塑造為例”,《外交評(píng)論(外交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9年第4期,第32-70頁(yè)。而發(fā)展中國(guó)家強(qiáng)調(diào)發(fā)達(dá)國(guó)家應(yīng)該為當(dāng)前的氣候變化問(wèn)題承擔(dān)主要責(zé)任,但來(lái)自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科學(xué)理性聲音和公正性訴求往往被邊緣化、被削弱,領(lǐng)導(dǎo)力供給過(guò)程缺乏有效的互動(dòng)及多元話語(yǔ)的爭(zhēng)鳴。
第四,全球氣候治理中領(lǐng)導(dǎo)力的“赤字”使得該治理進(jìn)程陷入僵局。當(dāng)前全球氣候治理沿著兩條路徑進(jìn)行:第一條路徑是以《公約》為核心的聯(lián)合國(guó)框架下的全球治理,第二條路徑是聯(lián)合國(guó)框架之外的全球治理。然而,這兩條路徑都呈現(xiàn)出“碎片化”特征。②李慧明:“全球氣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時(shí)代的國(guó)際領(lǐng)導(dǎo)及中國(guó)的戰(zhàn)略選擇”,《當(dāng)代亞太》,2015年第4期,第128-156頁(yè)。鑒于全球氣候治理的全球公地和全球公共產(chǎn)品特性,其更多需要一種基于多邊主義的國(guó)際氣候制度,進(jìn)而形成綠色國(guó)際合作領(lǐng)導(dǎo)。由于國(guó)家之間實(shí)力的差異以及國(guó)際制度的分配性和非中性,國(guó)際制度設(shè)計(jì)的過(guò)程充滿斗爭(zhēng)與妥協(xié);同時(shí),制度設(shè)計(jì)的實(shí)現(xiàn)需要特定成員發(fā)揮領(lǐng)導(dǎo)力,并承擔(dān)相應(yīng)成本,進(jìn)而引領(lǐng)和協(xié)調(diào)諸多國(guó)家間的合作,③陳琪、管傳靖:“國(guó)際制度設(shè)計(jì)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分析”,《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2015年第8期,第4-28頁(yè)。但是,存在領(lǐng)導(dǎo)力供給不足問(wèn)題是常態(tài)。這種領(lǐng)導(dǎo)力赤字既包含對(duì)某些國(guó)家或國(guó)家集團(tuán)發(fā)揮帶頭減排作用的要求和主張,也包含對(duì)某些國(guó)家或國(guó)家集團(tuán)擔(dān)當(dāng)協(xié)調(diào)國(guó)際合作和引領(lǐng)作用的期待與希望。
綜上所述,大國(guó)領(lǐng)導(dǎo)是推動(dòng)全球氣候治理形成共識(shí)的必要條件。而面對(duì)全球氣候變化這個(gè)人類共同危機(jī),要突破氣候政治博弈的“囚徒困境”,必須增強(qiáng)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意識(shí),實(shí)現(xiàn)從個(gè)體理性到集體理性的超越。④郭樹勇、于陽(yáng):“全球秩序觀的理性轉(zhuǎn)向與‘新理性’——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理性基礎(chǔ)”,《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2021年第4期,第4-32頁(yè);華啟和:“氣候政治博弈對(duì)倫理共識(shí)的訴求”,《中國(guó)地質(zh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年第3期,第15-19頁(yè)。全球氣候治理的領(lǐng)導(dǎo)者只有通過(guò)樹立共同的人類命運(yùn)觀和共同的人類合作觀,發(fā)揮自身的領(lǐng)導(dǎo)力,堅(jiān)持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和合作共贏的原則,尋找合作的最大公約數(shù)但又不推卸共同的減排責(zé)任,才能達(dá)成向全球零碳目標(biāo)轉(zhuǎn)型的共識(shí)。
1.2 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的變遷
全球治理的領(lǐng)導(dǎo)力是多層面和多維度的。國(guó)際環(huán)境政治領(lǐng)域?qū)︻I(lǐng)導(dǎo)力的劃分存在分歧,常用的是“四分法”:結(jié)構(gòu)型、方向型、理念型、工具型,⑤李慧明:“全球氣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時(shí)代的國(guó)際領(lǐng)導(dǎo)及中國(guó)的戰(zhàn)略選擇”,《當(dāng)代亞太》,2015年第4期,第128-156頁(yè);董亮:“歐盟在巴黎氣候進(jìn)程中的領(lǐng)導(dǎo)力:局限性與不確定性”,《歐洲研究》,2017第3期,第74-92頁(yè)。或者是結(jié)構(gòu)型、榜樣型、認(rèn)知型和企業(yè)家型四類。①肖蘭蘭:“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領(lǐng)導(dǎo)—跟隨邏輯:歐盟的實(shí)踐與中國(guó)的選擇”,《中國(guó)地質(zh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年第2期,第91-102頁(yè)。除此之外,還有“三分法”:結(jié)構(gòu)型、企業(yè)家型和智力型,②Oran Young,“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3,1991,pp.281-308.或者結(jié)構(gòu)型、方向型和工具型。③Gupta Joyeeta and Grubb Michael,Climate Changeand Euro?pean Leadership:A Sustainable Role for Europe?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0.在已有研究的基礎(chǔ)上,④董亮:“歐盟在巴黎氣候進(jìn)程中的領(lǐng)導(dǎo)力:局限性與不確定性”,《歐洲研究》,2017第3期,第74-92頁(yè);寇靜娜、張銳:“疫情后誰(shuí)將繼續(xù)領(lǐng)導(dǎo)全球氣候治理——?dú)W盟的衰退與反擊”,《中國(guó)地質(zh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年第1期,第87-104頁(yè)。本文將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定義為一種影響全球氣候治理集體行動(dòng)方向,并將自身偏好擴(kuò)散上升為國(guó)際共識(shí)的能力,以氣候領(lǐng)導(dǎo)者所依賴的資源和領(lǐng)導(dǎo)的方式為標(biāo)準(zhǔn),把全球氣候治理領(lǐng)導(dǎo)力劃分為結(jié)構(gòu)型、方向型、理念型和工具型四種類型。其中,結(jié)構(gòu)型氣候領(lǐng)導(dǎo)力是指按照自身的意圖改變其他行為體的運(yùn)行環(huán)境及設(shè)定必須遵循的機(jī)構(gòu)規(guī)則的權(quán)力;方向型氣候領(lǐng)導(dǎo)力是指通過(guò)榜樣和示范進(jìn)行領(lǐng)導(dǎo),為其他行為體提供示范和前進(jìn)方向的能力;理念型氣候領(lǐng)導(dǎo)力是指通過(guò)提供特定的知識(shí)和理論,界定特定問(wèn)題的概念和解決方案,影響其他行為體認(rèn)知和偏好的能力;工具型氣候領(lǐng)導(dǎo)力是指運(yùn)用高超的談判技巧和外交協(xié)調(diào)手段來(lái)達(dá)到政策目標(biāo)的能力。而全球氣候治理的領(lǐng)導(dǎo)者是指為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而運(yùn)用各種資源引導(dǎo)并推動(dòng)其他行為體明確治理目標(biāo)、創(chuàng)設(shè)治理制度,最終為實(shí)現(xiàn)治理目標(biāo)而努力的特定行為體(一般是大國(guó))。⑤同①。
分析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的變遷,可以將這一時(shí)期劃分為五個(gè)階段。第一階段(1990—1996年),《公約》談判及生效時(shí)期。自1990年起,國(guó)際社會(huì)在聯(lián)合國(guó)框架下啟動(dòng)了關(guān)于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國(guó)際制度安排的談判,1992年《公約》達(dá)成,1994年生效。《公約》取得的最重要的三項(xiàng)成果分別是全球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的目標(biāo)、全球氣候治理的原則和各締約方義務(wù)。這一時(shí)期,歐盟和美國(guó)共同發(fā)揮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第二階段(1997—2005年),《京都議定書》談判及生效準(zhǔn)備時(shí)期。《京都議定書》于1997年達(dá)成,2005年正式生效。最終達(dá)成的《京都議定書》事實(shí)上是一個(gè)糅合了歐盟堅(jiān)持的量化減排目標(biāo)和美國(guó)堅(jiān)持的靈活機(jī)制(三個(gè)靈活合作機(jī)制)的綜合體。由于小布什政府2001年退出了《京都議定書》,這一時(shí)期美國(guó)(1997—2000年)和歐盟(2001—2005年)各在一段時(shí)間內(nèi)發(fā)揮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第三階段(2006—2011年),《京都議定書》生效時(shí)期。這一階段,歐盟提出將國(guó)際航空納入排放交易體系(EU-ETS),但因受到美國(guó)、中國(guó)等大國(guó)的強(qiáng)烈反對(duì)而被迫放棄。而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huì)上,歐盟也未能實(shí)現(xiàn)“全球達(dá)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協(xié)定”的目標(biāo)。這一時(shí)期盡管歐盟的領(lǐng)導(dǎo)力有所弱化,但歐盟仍是主要的領(lǐng)導(dǎo)者。第四階段(2012—2015年),“德班平臺(tái)”進(jìn)程和《巴黎協(xié)定》達(dá)成。在2015年召開的巴黎氣候大會(huì)上,歐盟與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區(qū)國(guó)家集團(tuán)積極協(xié)調(diào),并與中國(guó)、美國(guó)等共同推動(dòng)《巴黎協(xié)定》達(dá)成,這成為各國(guó)攜手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的政治和法律基礎(chǔ)。這一時(shí)期,中國(guó)、美國(guó)和歐盟作為三大經(jīng)濟(jì)體共同發(fā)揮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第五階段(2016—2020年),《巴黎協(xié)定》生效及完善時(shí)代。在這一階段,美國(guó)宣布退出《巴黎協(xié)定》,全球氣候治理圍繞《巴黎協(xié)定》實(shí)施細(xì)則進(jìn)行談判,基本達(dá)成了《巴黎協(xié)定》實(shí)施細(xì)則。盡管美國(guó)主動(dòng)放棄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但歐盟和中國(guó)堅(jiān)定維護(hù)多邊主義原則,共同發(fā)揮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
其中,歐盟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主導(dǎo)者,體現(xiàn)在多個(gè)階段的氣候治理進(jìn)程中。在第一階段,歐盟(歐洲共同體)是氣候治理的領(lǐng)導(dǎo)者,《公約》基本采用了歐盟提出的“穩(wěn)定排放”的目標(biāo)要求。歐盟(歐洲共同體)是全球氣候變化議題的提出者,為《公約》的成功簽署提供了結(jié)構(gòu)型領(lǐng)導(dǎo)力。在第二階段,歐盟是碳市場(chǎng)機(jī)制的最早實(shí)踐者,于2005年1月1日開始實(shí)施溫室氣體排放配額交易制度。歐盟通過(guò)落實(shí)《京都議定書》為歐盟各成員國(guó)規(guī)定減排目標(biāo),率先在全球探索市場(chǎng)化減排機(jī)制,為全球提供參照模板和經(jīng)驗(yàn),展現(xiàn)了強(qiáng)大的方向型領(lǐng)導(dǎo)力。在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歐盟展現(xiàn)了強(qiáng)大的理念型領(lǐng)導(dǎo)力。歐盟將“全球平均氣溫不應(yīng)高于工業(yè)革命前水平2℃”目標(biāo)從一個(gè)科學(xué)標(biāo)準(zhǔn)轉(zhuǎn)化成為《哥本哈根協(xié)議》《坎昆協(xié)議》和《巴黎協(xié)定》等全球限制和減排努力的指導(dǎo)標(biāo)準(zhǔn)。在2015年《巴黎協(xié)定》談判期間,歐盟聯(lián)合79個(gè)非洲國(guó)家、加勒比與太平洋地區(qū)國(guó)家,組成“雄心壯志聯(lián)盟”(High Ambition Coalition),成功將“全球升溫控制在1.5℃”目標(biāo)納入《巴黎協(xié)定》。在第五階段,歐盟在2019年馬德里氣候大會(huì)期間公布了實(shí)施《歐洲綠色協(xié)議》的全文,明確提出2050年“氣候中立”目標(biāo),展現(xiàn)了歐盟強(qiáng)大的方向型領(lǐng)導(dǎo)力。
美國(guó)的全球氣候治理領(lǐng)導(dǎo)力隨著執(zhí)政黨的輪動(dòng)而呈現(xiàn)明顯的波動(dòng)性變化。作為民主黨前總統(tǒng),克林頓政府1998年簽署了《京都議定書》,極大地推動(dòng)了全球氣候治理的進(jìn)程。而在第二階段,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議定書》的同時(shí),開始嘗試《公約》外氣候治理機(jī)制,從《公約》制度之外挑戰(zhàn)歐盟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如建立亞太清潔發(fā)展與氣候伙伴關(guān)系(APP),參與主要經(jīng)濟(jì)體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會(huì)議(MEM)等。而在奧巴馬任期內(nèi)美國(guó)氣候領(lǐng)導(dǎo)力得到快速提升,逐漸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引領(lǐng)者。美國(guó)通過(guò)建立主要經(jīng)濟(jì)體能源與氣候論壇(MEF),弱化了歐盟在《公約》中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在第四階段,奧巴馬第二任期美國(guó)氣候變化政策實(shí)現(xiàn)了重要的調(diào)整和升級(jí)。2013年《總統(tǒng)氣候行動(dòng)計(jì)劃》的頒布為全球碳減排市場(chǎng)的建立提供了方向,提升了美國(guó)在碳市場(chǎng)方面的方向型領(lǐng)導(dǎo)力。美國(guó)在這一階段倡導(dǎo)“自下而上”的溫室氣體減排模式,這與中國(guó)提倡的基于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zé)任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共同為《巴黎協(xié)定》的達(dá)成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撐,展示了美國(guó)的結(jié)構(gòu)型領(lǐng)導(dǎo)力。①莊貴陽(yáng)、薄凡、張靖:“中國(guó)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與戰(zhàn)略選擇”,《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2018年第4期,第4-27頁(yè)。在第五階段,特朗普政府2017年6月1日宣布退出《巴黎協(xié)定》,導(dǎo)致美國(guó)的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迅速衰減。其后果不僅僅是美國(guó)國(guó)內(nèi)溫室氣體減排進(jìn)程的減緩,還撕裂了傳統(tǒng)的跨大西洋伙伴關(guān)系,導(dǎo)致美國(guó)的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進(jìn)一步下降。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xié)定》,還導(dǎo)致其他國(guó)家的氣候雄心也發(fā)生了動(dòng)搖。博索納羅(Bolsonaro)在2018年當(dāng)選總統(tǒng)后,巴西放棄了第25屆聯(lián)合國(guó)氣候大會(huì)的承辦國(guó)資格,氣候大會(huì)的主辦權(quán)由智利接手,但由于智利國(guó)內(nèi)的騷亂問(wèn)題,最終將主辦地轉(zhuǎn)移到西班牙的馬德里。②寇靜娜、張銳:“疫情后誰(shuí)將繼續(xù)領(lǐng)導(dǎo)全球氣候治理——?dú)W盟的衰退與反擊”,《中國(guó)地質(zh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年第1期,第87-104頁(yè)。
綜上所述,大國(guó)的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在不同時(shí)期的表現(xiàn)形式不同,大國(guó)的領(lǐng)導(dǎo)力變遷對(duì)全球氣候治理進(jìn)程產(chǎn)生了顯著影響。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jí)大國(guó),美國(guó)政府對(duì)待全球氣候變化問(wèn)題的政治態(tài)度是影響全球氣候治理進(jìn)程的重要變量。美國(guó)政府既可以發(fā)揮自身強(qiáng)大的結(jié)構(gòu)性領(lǐng)導(dǎo)力,推動(dòng)全球氣候治理機(jī)制變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拖累全球氣候治理進(jìn)程,這背后的原因是美國(guó)的氣候政策是執(zhí)政政黨基于個(gè)體理性而作出的有利于自身競(jìng)選成功的戰(zhàn)略選擇。美國(guó)拜登政府重新以領(lǐng)導(dǎo)者的身份出現(xiàn)在全球氣候治理舞臺(tái),必然會(huì)對(duì)全球氣候治理格局帶來(lái)新的調(diào)整。
二、美歐氣候博弈的新焦點(diǎn):領(lǐng)導(dǎo)力
隨著美國(guó)重返《巴黎協(xié)定》,美歐兩大經(jīng)濟(jì)體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領(lǐng)導(dǎo)者,都將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問(wèn)題與自身發(fā)展戰(zhàn)略深度融合,凸顯自身的全球氣候治理領(lǐng)導(dǎo)力。而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美歐雙方存在明顯的氣候博弈。美國(guó)學(xué)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Keohane)認(rèn)為,大國(guó)博弈并不遵循類似經(jīng)濟(jì)中的自由主義原則,而是傾向于現(xiàn)實(shí)主義邏輯,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是在大國(guó)博弈中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的最有效路徑。①楊成玉:“反制美國(guó)‘長(zhǎng)臂管轄’之道——基于法國(guó)重塑經(jīng)濟(jì)主權(quán)的視角”,《歐洲研究》,2020年第3期,第1-31頁(yè);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Relations,Old and New,”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462。盡管美歐兩大經(jīng)濟(jì)體氣候戰(zhàn)略的主要目的是落實(shí)《巴黎協(xié)定》既定承諾,最終實(shí)現(xiàn)全球凈零碳排放,但美歐兩大經(jīng)濟(jì)體依據(jù)自身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和利益訴求,制定了不同的氣候轉(zhuǎn)型戰(zhàn)略,這背后體現(xiàn)的是在不同價(jià)值觀導(dǎo)向下對(duì)全球領(lǐng)導(dǎo)力的追求。從大國(guó)戰(zhàn)略博弈角度來(lái)看,拜登政府通過(guò)將氣候變化作為外交政策規(guī)劃和國(guó)家安全考量的中心,極力恢復(fù)和鞏固二戰(zhàn)后美國(guó)主導(dǎo)的“自由主義秩序”;歐盟以《歐洲綠色協(xié)議》為框架打造零碳?xì)W洲,展示了歐盟氣候戰(zhàn)略的全球領(lǐng)導(dǎo)力。
2.1 美國(guó)的氣候領(lǐng)導(dǎo)力:以拜登氣候新政重建“自由主義秩序”
美國(guó)總統(tǒng)拜登執(zhí)政的精神內(nèi)核是帶領(lǐng)所有美國(guó)人“重拾美國(guó)的靈魂”(Restore American Soul),重建美國(guó)世界燈塔的地位(America is a beacon for the globe),恢復(fù)并鞏固二戰(zhàn)后美國(guó)主導(dǎo)的“自由主義秩序”②The White House,“Inaugural Address by President Joseph R.Biden,Jr.,”January 20,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1/20/inaugural-address-by-president-joseph-r-biden-jr/,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2月27日。。拜登競(jìng)選總統(tǒng)提出“更好地重建美國(guó)(Build Back Better)”計(jì)劃以及其執(zhí)政以來(lái)實(shí)施的《美國(guó)就業(yè)計(jì)劃》都體現(xiàn)了這個(gè)內(nèi)核。
(1)拜登氣候新政的戰(zhàn)略考量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導(dǎo)致美國(guó)經(jīng)濟(jì)迅速陷入衰退,如何解決制造業(yè)萎縮的問(wèn)題,為百萬(wàn)失業(yè)人口創(chuàng)造就業(yè)成了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務(wù)。《美國(guó)就業(yè)計(jì)劃》是涵蓋基礎(chǔ)科學(xué)研究、供應(yīng)鏈支撐、基礎(chǔ)設(shè)施鞏固等領(lǐng)域的投資計(jì)劃,在8年內(nèi)每年投資1%的國(guó)內(nèi)生產(chǎn)總值(GDP)來(lái)更新國(guó)家基礎(chǔ)設(shè)施,激活制造業(yè),總額近2萬(wàn)億美元。③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The American Jobs Plan,”March 31,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31/fact-sheet-the-american-jobs-plan/,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4月27日。拜登在白宮演講中提到,“在基礎(chǔ)設(shè)施方面,我們?cè)谑澜缗琶?8位——從運(yùn)河到高速公路到機(jī)場(chǎng)等等,我們需要做而且能夠做讓我們?cè)?1世紀(jì)有競(jìng)爭(zhēng)力的一切事情”④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before Meet?ing with Labor Leaders to Discuss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and Infra?structure,”February 17,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17/remarks-by-president-biden-before-meeting-with-labor-leaders-to-discuss-the-americanrescue-plan-and-infrastructure/,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2月27日。。為了應(yīng)對(duì)氣候風(fēng)險(xiǎn),當(dāng)前基礎(chǔ)設(shè)施的智能化、低碳韌性轉(zhuǎn)型是世界的主流趨勢(shì),拜登政府在2021年1月27日公布的《應(yīng)對(duì)國(guó)內(nèi)外氣候危機(jī)的總統(tǒng)行政令》⑤The White House,“Executive Order on Tackling the Climate Crisis at Home and Abroad,”January 27,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7/executive-order-on-tackling-the-climate-crisis-at-h(huán)ome-and-abroad/>,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2月27日。和同年3月31日公布的《美國(guó)就業(yè)計(jì)劃》中,對(duì)智能電網(wǎng)、新能源車和可再生能源發(fā)電等領(lǐng)域進(jìn)行了重點(diǎn)規(guī)劃。
第二,美國(guó)的高科技產(chǎn)業(yè)優(yōu)勢(shì)明顯,需要通過(guò)“新工業(yè)革命”維持產(chǎn)業(yè)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技術(shù)霸權(quán)是美國(guó)的全政府策略,具體手段主要包括貿(mào)易保護(hù)和技術(shù)壁壘策略、經(jīng)濟(jì)制裁和司法干預(yù)策略、限制交流與技術(shù)封鎖策略、政策脅迫與技術(shù)聯(lián)盟策略,根本目的是維護(hù)美國(guó)的全球領(lǐng)導(dǎo)力。⑥蔡翠紅:“大變局時(shí)代的技術(shù)霸權(quán)與‘超級(jí)權(quán)力’悖論”,《人民論壇·學(xué)術(shù)前沿》,2019年第14期,第17-31頁(yè)。21世紀(jì)以來(lái),以美國(guó)為核心的全球地緣科技格局并未改變,而且美國(guó)的核心地位不斷鞏固和加強(qiáng)。⑦段德忠、杜德斌、諶穎:“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貿(mào)易下的全球地緣科技格局及其演化”,《地理研究》,2019年第9期,第2115-2128頁(yè)。當(dāng)前,全球大部分的清潔技術(shù)投資仍然集中在美國(guó)。⑧蔣佳妮、王文濤、王燦、劉燕華:“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需要以生態(tài)文明理念構(gòu)建全球技術(shù)合作體系”,《中國(guó)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2017年第1期,第57-64頁(yè)。美國(guó)通過(guò)為相關(guān)技術(shù)發(fā)展提供財(cái)政支持、與盟友在相關(guān)產(chǎn)業(yè)建立聯(lián)盟或國(guó)際組織,從而制定行業(yè)規(guī)則并掌握話語(yǔ)權(quán),與傳統(tǒng)能源大國(guó)形成聯(lián)盟、共謀改革,尋求以提供資金和技術(shù)援助的方式向發(fā)展中國(guó)家提供幫助等,維護(hù)自身在清潔能源技術(shù)等領(lǐng)域的領(lǐng)導(dǎo)地位。
第三,積極應(yīng)對(duì)氣候風(fēng)險(xiǎn)、促進(jìn)公正轉(zhuǎn)型,是美國(guó)民主黨的價(jià)值觀追求。重視價(jià)值觀和民主人權(quán)問(wèn)題,是美國(guó)民主黨政府外交政策的傳統(tǒng),如克林頓執(zhí)政時(shí)期采取的“民主擴(kuò)展”(Democratic Enlargement)戰(zhàn)略。①Douglas Brinkley,“Democratic Enlargement:The Clinton Doctrine,”Foreign Policy,No.106,1997,pp.116-120.全球氣候變化問(wèn)題是民主黨長(zhǎng)期關(guān)注和支持的領(lǐng)域之一,拜登政府將價(jià)值觀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深化“自由世界”成員之間的合作,而建立更加緊密的“民主國(guó)家聯(lián)合體”也符合民主黨的價(jià)值追求。美國(guó)的拜登政府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wèn)題,認(rèn)為這一問(wèn)題給美國(guó)帶來(lái)“日益加劇的威脅”,稱將大力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等問(wèn)題所體現(xiàn)的“環(huán)境不公正”(environmental injustice)挑戰(zhàn)。②Umair Irfan,“We Asked Joe Bidens Campaign 6 Key Ques?tions about His Climate Change Plans,”Vox,October 22,2020,ht?tps://www.vox.com/21516594/joe-biden-climate-change-covid-19-president,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2月27日。在2020年,美國(guó)遭受了22個(gè)損失超過(guò)10億美元的氣候?yàn)?zāi)害,對(duì)家庭、商業(yè)和公共設(shè)施造成的損失高達(dá)950億美元,《美國(guó)就業(yè)計(jì)劃》明確提出要將40%的氣候和清潔基礎(chǔ)設(shè)施投資收益給弱勢(shì)群體。
(2)拜登政府發(fā)揮氣候領(lǐng)導(dǎo)力的具體行動(dòng)
第一,拜登政府將氣候變化作為外交政策規(guī)劃、外交和國(guó)家安全考量的中心,通過(guò)構(gòu)建雙邊、小多邊和多邊機(jī)制,積極修復(fù)特朗普政府時(shí)期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對(duì)美國(guó)全球領(lǐng)導(dǎo)力帶來(lái)的破壞,重振美國(guó)工具型領(lǐng)導(dǎo)力。在美國(guó)主辦的“領(lǐng)導(dǎo)人氣候峰會(huì)”上,拜登提出了美國(guó)溫室氣體排放到2030年比2005年減少50%~52%水平的新目標(biāo),并推動(dòng)日本、加拿大、英國(guó)提出了新的減排目標(biāo)。③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President Biden Sets 2030 Greenhouse Gas Pollution Reduction Target Aimed at Creating Good-Paying Union Jobs and Securing U.S.Leadership on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April 22,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22/fact-sheet-president-biden-sets-2030-greenhouse-gas-pollution-reduction-targetaimed-at-creating-good-paying-union-jobs-and-securing-u-sleadership-on-clean-energy-technologies/,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4月27日。美國(guó)還推出旨在支持發(fā)展中國(guó)家實(shí)現(xiàn)凈零目標(biāo)的“全球氣候雄心倡議”(Global Climate Ambition Initiative),推出由美國(guó)和加拿大主導(dǎo)的國(guó)際組織“綠色政府倡議”(Greening Government Initiative),與重要的油氣生產(chǎn)國(guó)形成“凈零生產(chǎn)論壇”(Net-Zero Producers Forum),與印度建立2030年美印氣候和清潔能源議程伙伴關(guān)系(U.S.-India Climate and Clean Energy Agenda 2030 Partnership),支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qū)國(guó)家的清潔能源發(fā)展,發(fā)起包括澳大利亞、博茨瓦納、加拿大和秘魯在內(nèi)的能源資源治理倡議(Energy Resource Governance Initiative),加入或創(chuàng)建新能源汽車、小型模塊化反應(yīng)堆等具體行業(yè)或技術(shù)的相關(guān)國(guó)際聯(lián)盟等。
第二,重視凈零碳技術(shù)的研發(fā)及應(yīng)用,確保美國(guó)在關(guān)鍵脫碳技術(shù)創(chuàng)新方面的方向型領(lǐng)導(dǎo)力和理念型領(lǐng)導(dǎo)力。《美國(guó)就業(yè)計(jì)劃》中,涉及新能源的直接投資約為3 270億美元,包括電動(dòng)汽車(1 740億美元)、聯(lián)邦采購(gòu)清潔能源(460億美元),以及重點(diǎn)支持農(nóng)村制造業(yè)和清潔能源(520億美元)、解決氣候危機(jī)的相關(guān)技術(shù)④其包括碳捕集與封存、氫、先進(jìn)核能、稀土元素分離、海上風(fēng)電、生物燃料/生物產(chǎn)品、量子計(jì)算和電動(dòng)汽車等。突破(550億美元)。美國(guó)在領(lǐng)導(dǎo)人氣候峰會(huì)提出,通過(guò)與瑞典、英國(guó)和阿聯(lián)酋等國(guó)分別達(dá)成雙邊合作伙伴,努力在工業(yè)、電力和農(nóng)業(yè)等關(guān)鍵部門開展全面脫碳,加快清潔技術(shù)在美國(guó)經(jīng)濟(jì)部門中的投資和應(yīng)用,到2035年將美國(guó)建筑庫(kù)存的碳足跡減少50%,在2030年底前部署超過(guò)50萬(wàn)個(gè)新的公共充電站,到2035年實(shí)現(xiàn)100%零碳電力。
第三,美國(guó)通過(guò)擴(kuò)大國(guó)際氣候融資規(guī)模,增強(qiáng)方向型領(lǐng)導(dǎo)力和工具型領(lǐng)導(dǎo)力。美國(guó)制定的“美國(guó)國(guó)際氣候融資計(jì)劃”(U.S.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Plan)提出,美國(guó)打算到2024年,與奧巴馬—拜登政府下半財(cái)年(2013—2016財(cái)年)的平均水平相比,每年向發(fā)展中國(guó)家提供的公共氣候財(cái)政翻一番。⑤The White House,“U.S.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Plan,”April 22,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4/U.S.-International-Climate-Finance-Plan-4.22.21-Updated-Spacing.pdf#:~:text=Meeting%20U.S.%20international%20climate%20finance%20pledges%20and%20commitments,mobilize%20and%20align%20capital%20at%20the%20scale%20required,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4月27日。2021年6月召開的七國(guó)集團(tuán)峰會(huì)啟動(dòng)了美國(guó)主導(dǎo)的、名為“重建更好世界”(B3W)的新全球基礎(chǔ)設(shè)施倡議,幫助發(fā)展中國(guó)家縮小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領(lǐng)域所需的高達(dá)40萬(wàn)億美元的資金缺口。拜登政府認(rèn)為B3W是由“主要民主國(guó)家領(lǐng)導(dǎo)的、以共同價(jià)值觀為導(dǎo)向、高標(biāo)準(zhǔn)和透明的”基礎(chǔ)設(shè)施伙伴關(guān)系。①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Partnership,”June 12,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6月27日。
第四,實(shí)施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增強(qiáng)方向型和理念型領(lǐng)導(dǎo)力。在領(lǐng)導(dǎo)人氣候峰會(huì)上,美國(guó)提出實(shí)施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的倡議,主要包括三個(gè)方面:(1)投資熱帶森林,推動(dòng)實(shí)現(xiàn)凈零的世界;(2)資助以自然為基礎(chǔ)的沿海社區(qū)和生態(tài)系統(tǒng)復(fù)原力方法;(3)促進(jìn)南大洋(Southern Ocean)的復(fù)原力。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倡議得到最不發(fā)達(dá)國(guó)家和廣大小島嶼國(guó)家的支持與追隨,塞舌爾、加拿大、哥斯達(dá)黎加、秘魯、印度尼西亞和加蓬等國(guó)還提出了本國(guó)在保護(hù)陸地和海洋方面的新目標(biāo)。
2.2 歐盟的氣候領(lǐng)導(dǎo)力:以《歐洲綠色協(xié)議》為框架打造零碳?xì)W洲
氣候中和(Climate Neutrality)作為展示歐盟普世價(jià)值體系的重要抓手,在歐盟多個(gè)成員國(guó)具有強(qiáng)大的民意基礎(chǔ)。2019年12月發(fā)布的《歐洲綠色協(xié)議》提出,歐盟力爭(zhēng)到2050年成為世界第一個(gè)氣候中和的大洲,打造氣候中和的經(jīng)濟(jì)體,這也為《巴黎協(xié)定》實(shí)施細(xì)則的談判提供氣候雄心,向全球展示了方向型領(lǐng)導(dǎo)力。
(1)零碳?xì)W洲目標(biāo)下歐盟的戰(zhàn)略考量
歐盟在各個(gè)領(lǐng)域推行綠色化、去碳化政策,需要投入巨額資金,客觀上將增加歐盟及其成員國(guó)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成本。歐盟推出綠色新政的戰(zhàn)略考量主要有以下三點(diǎn)。
第一,發(fā)源于歐洲的所謂普世價(jià)值體系陷入困境,2050年零碳?xì)W洲倡議是歐盟重振普世價(jià)值觀的抓手。在歐洲,以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為代表的綠色議題是公眾表達(dá)民主訴求的重要空間。20世紀(jì)70年代開始,公眾在反核、環(huán)境保護(hù)等問(wèn)題上的抗議活動(dòng)對(duì)全球有引領(lǐng)作用,并催生了綠黨的崛起。西方國(guó)家倡導(dǎo)并極力推廣一系列所謂普世價(jià)值觀,包括民主、人權(quán)、法治、自由貿(mào)易,以及自由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等,這被視為西方主導(dǎo)的全球秩序的基石,但是這套普世價(jià)值觀正在遭受來(lái)自歐盟內(nèi)部及其他國(guó)家的質(zhì)疑。②張健:“大變局下歐洲戰(zhàn)略取向及其影響”,《現(xiàn)代國(guó)際關(guān)系》,2021年第1期,第10-20頁(yè)。當(dāng)前,綠黨在歐洲議會(huì)、德國(guó)、法國(guó)、英國(guó)、芬蘭和愛(ài)爾蘭等都是重要的黨團(tuán),積極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作為“政治正確”的價(jià)值觀,具有強(qiáng)大的民意基礎(chǔ)。歐盟推出《歐洲綠色協(xié)議》,體現(xiàn)了歐盟希望再次領(lǐng)導(dǎo)全球氣候治理的訴求。
第二,《歐洲綠色協(xié)議》將加大減排力度,有助于歐盟達(dá)到《巴黎協(xié)定》履約目標(biāo),保持或提升歐盟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中的領(lǐng)導(dǎo)力。歐盟是《巴黎協(xié)定》的主要推動(dòng)方之一,然而,按照現(xiàn)行的歐盟《2030年氣候與能源政策框架》,2050年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相當(dāng)于1990年的60%,無(wú)法完成對(duì)《巴黎協(xié)定》的履約。③張敏:“歐洲綠色新政推動(dòng)歐盟政策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2020年5月25日,第1932期。歐盟實(shí)施《歐洲綠色協(xié)議》,通過(guò)調(diào)整減排目標(biāo),加大減排力度,力爭(zhēng)在落實(shí)《巴黎協(xié)定》上發(fā)揮積極表率作用,有助于歐盟進(jìn)一步鞏固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主導(dǎo)權(quán)。
第三,《歐洲綠色協(xié)議》將成為歐盟增強(qiáng)內(nèi)部凝聚力的共同行動(dòng)綱領(lǐng)。歐盟內(nèi)部問(wèn)題逐漸累積,南北經(jīng)濟(jì)分化形成的鴻溝難以彌合,價(jià)值觀矛盾沖突加劇,民粹主義、國(guó)家主義思想泛濫,歐盟層面的民主赤字與成員國(guó)民主的被限制、被剝奪更是形成難以克服的巨大沖突,這些都嚴(yán)重削弱了歐盟的凝聚力和行動(dòng)能力。《歐洲綠色協(xié)議》作為歐盟一項(xiàng)長(zhǎng)期發(fā)展戰(zhàn)略,為歐盟及其成員國(guó)不斷凝聚共識(shí)、增進(jìn)互信,提高內(nèi)部凝聚力和團(tuán)結(jié)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歐盟發(fā)揮氣候領(lǐng)導(dǎo)力的具體行動(dòng)
《歐洲綠色協(xié)議》是歐盟于2019年12月首次推出的新增長(zhǎng)戰(zhàn)略,為歐洲氣候戰(zhàn)略提供了總體框架。圍繞《歐洲綠色協(xié)議》,歐盟近期在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方面的主要政策有以下五點(diǎn)。
第一,率先提出地區(qū)“碳中和”目標(biāo),展示方向型領(lǐng)導(dǎo)力。氣候中和作為展示歐盟普世價(jià)值體系的重要抓手,在歐盟多個(gè)成員國(guó)具有強(qiáng)大的民意基礎(chǔ)。歐盟在2019年12月發(fā)布的《歐洲綠色協(xié)議》中提出,到2050年成為世界第一個(gè)氣候中和的大洲,打造氣候中和的經(jīng)濟(jì)體,為《巴黎協(xié)定》實(shí)施細(xì)則的談判提供氣候雄心。它的總體目標(biāo)是于2050年過(guò)渡到氣候中和、環(huán)境可持續(xù)、資源高效及具有韌性的經(jīng)濟(jì),以及到2030年至少減少55%溫室氣體排放量,并且保護(hù)、維持并增強(qiáng)歐盟的自然資本。
第二,打造全球綠色價(jià)值鏈,展現(xiàn)工具型領(lǐng)導(dǎo)力。為了支持綠色轉(zhuǎn)型,促進(jìn)負(fù)責(zé)任和可持續(xù)的價(jià)值鏈,歐盟委員會(huì)利用自身的國(guó)際貿(mào)易主導(dǎo)地位,在多個(gè)領(lǐng)域開展首要行動(dòng):與非洲國(guó)家合作,將氣候和環(huán)境問(wèn)題納入雙邊關(guān)系的核心;與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80%的二十國(guó)集團(tuán)(G20)國(guó)家進(jìn)行接觸,推動(dòng)共同應(yīng)對(duì)全球能源和氣候挑戰(zhàn);在波茲南峰會(huì)之后,為西巴爾干地區(qū)制定了綠色議程;與拉美、加勒比、亞太等伙伴國(guó)家和地區(qū)建立綠色聯(lián)盟。與此同時(shí),歐盟議會(huì)通過(guò)碳邊境調(diào)節(jié)機(jī)制(CBAM)議案,成為全球第一個(gè)以碳邊境稅作為貿(mào)易工具的國(guó)家集團(tuán),對(duì)全球貿(mào)易的脫碳進(jìn)程將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
第三,推動(dòng)氣候變化立法,展示方向型領(lǐng)導(dǎo)力。歐洲議會(huì)于2020年3月4日出臺(tái)了《歐洲氣候法》(European Climate Law)草案,2020年3月10日公布了《歐洲新工業(yè)戰(zhàn)略》(A New In?dustrial Strategy for Europe),翌日歐盟又頒布了《新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行動(dòng)計(jì)劃》。這些政策和行動(dòng)計(jì)劃旨在幫助歐洲經(jīng)濟(jì)向氣候中和與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提高其全球競(jìng)爭(zhēng)力。2021年4月21日,歐洲理事會(huì)發(fā)表公告稱,歐洲理事會(huì)、歐洲議會(huì)及各成員國(guó)議會(huì)已就《歐洲氣候法》達(dá)成了臨時(shí)協(xié)議。2021年6月28日,歐盟正式通過(guò)了《歐洲氣候法》,這意味著歐洲在2050年實(shí)現(xiàn)“碳中和”的承諾已寫入法律,為其他國(guó)家提供立法參考。①European Commission,“European Climate Law,”March 4,2020,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88581905912&uri=CELEX:52020PC0080,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4月27日。
第四,歐盟提出可持續(xù)金融的歐盟分類體系,展示了方向型領(lǐng)導(dǎo)力和理念型領(lǐng)導(dǎo)力。《歐盟分類條例》(EUs Taxonomy Regulation)于2020年7月12日生效,《分類條例》確立了六項(xiàng)環(huán)境目標(biāo):減緩氣候變化、氣候變化適應(yīng)、水和海洋資源的可持續(xù)利用和保護(hù)、向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的過(guò)渡、污染防治、保護(hù)和恢復(fù)生物多樣性和生態(tài)系統(tǒng)。②European Commission,“Sustainable Finance Package,”April 21,2021,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210421-sus?tainable-finance-communication_en#taxonomy,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4月27日。歐盟在2021年4月21日原則上通過(guò)了《歐盟氣候授權(quán)分類法》(EU Taxonomy Climate Delegated Act),為確定對(duì)減緩和適應(yīng)氣候變化有重大貢獻(xiàn)的活動(dòng)提供了第一套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將會(huì)成為歐洲金融領(lǐng)域新監(jiān)管框架的制定基準(zhǔn),為歐盟2050年實(shí)現(xiàn)氣候中和提供了工具。《歐盟分類條例》及相關(guān)法律為參與者及公司進(jìn)行氣候風(fēng)險(xiǎn)披露提供了分類標(biāo)準(zhǔn),為全球氣候投融資提供了參考標(biāo)準(zhǔn)。
第五,歐盟發(fā)布能源系統(tǒng)一體化戰(zhàn)略和氫能戰(zhàn)略,展示了方向型領(lǐng)導(dǎo)力和理念型領(lǐng)導(dǎo)力。③European Commission,“EU Energy System Integration Strate?gy,”July 8,2020,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fs_20_1295,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4月27日。2020年7月發(fā)布的《歐盟能源系統(tǒng)一體化戰(zhàn)略》(EU Energy System Integration Strategy)包括三個(gè)支柱:(1)一個(gè)以能源效率為核心的更“循環(huán)”的能源系統(tǒng);(2)加強(qiáng)最終用途部門的直接電氣化;(3)對(duì)于那些電氣化困難的部門,該戰(zhàn)略提倡清潔燃料,包括可再生氫氣(綠氫)、可持續(xù)生物燃料和沼氣。同期發(fā)布的《氫能戰(zhàn)略》(EU Hydrogen Strategy)則提出了綠氫的分階段發(fā)展路徑。④European Commission,“EU Hydrogen Strategy,”July 8,2020,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fs_20_1296,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4月27日。歐盟建立一個(gè)更加高效和一體化的能源系統(tǒng),為能源脫碳和2050年實(shí)現(xiàn)碳中和提供了戰(zhàn)略支撐。
2.3 歐盟和美國(guó)的氣候博弈
對(duì)比美國(guó)和歐盟對(duì)氣候領(lǐng)導(dǎo)力的博弈,可以發(fā)現(xiàn),美國(guó)重返《巴黎協(xié)定》之后,美歐兩大經(jīng)濟(jì)體在全球氣候風(fēng)險(xiǎn)認(rèn)知方面實(shí)現(xiàn)了“局部”的統(tǒng)一。美國(guó)和歐盟都通過(guò)發(fā)揮自身在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領(lǐng)域的科技和投融資優(yōu)勢(shì),增強(qiáng)自身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方向型領(lǐng)導(dǎo)力和理念型領(lǐng)導(dǎo)力。美國(guó)還將歐盟作為“自由世界”的重要成員,通過(guò)主辦多邊氣候領(lǐng)導(dǎo)者論壇、提出新的氣候倡議來(lái)增強(qiáng)自身的工具型領(lǐng)導(dǎo)力,強(qiáng)化自身作為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者的重要地位。然而應(yīng)該看到,美歐兩大經(jīng)濟(jì)體追求氣候領(lǐng)導(dǎo)力的背后,將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問(wèn)題與國(guó)內(nèi)發(fā)展戰(zhàn)略深度融合,搶占低碳技術(shù)制高點(diǎn)與實(shí)現(xiàn)國(guó)內(nèi)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零碳轉(zhuǎn)型是兩大經(jīng)濟(jì)體的內(nèi)在訴求。在全球氣候承諾目標(biāo)日益趨緊的剛性約束下,美歐對(duì)爭(zhēng)奪氣候領(lǐng)導(dǎo)力的追求面臨著集體理性與個(gè)體理性的沖突,對(duì)低碳技術(shù)和低碳經(jīng)濟(jì)規(guī)則制定權(quán)的爭(zhēng)奪成為新一輪國(guó)際權(quán)力政治的核心內(nèi)容。①李彥文、李慧明:“全球氣候治理的權(quán)力政治邏輯及其超越”,《山東社會(huì)科學(xué)》,2020年第12期,第168-176頁(yè)。
一方面,美國(guó)和歐盟在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方面存在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美國(guó)在特朗普政府時(shí)期,一度放棄了全球氣候治理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歐盟與中國(guó)密切合作,共同發(fā)揮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而中美博弈對(duì)世界政治發(fā)展的“牽引力”②袁鵬:“新冠疫情與百年變局”,《現(xiàn)代國(guó)際關(guān)系》,2020年第5期,第3頁(yè)。上升,導(dǎo)致歐洲在世界政治中趨于邊緣化。歐洲人發(fā)現(xiàn),自己正在成為地緣政治的角逐場(chǎng)而非角逐者,③Jacopo Barigazzi,“Borrell Urges EU to Be Foreign Policy‘Player,Not the Playground’”Politico,December 9,2019,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on-foreign-policy-josepborrell-urges-eu-tobe-a-player-not-the-playground-balkans/,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2月27日。面臨選邊站隊(duì)的強(qiáng)大壓力。而隨著美國(guó)重返《巴黎協(xié)定》,并提出重新發(fā)揮氣候領(lǐng)導(dǎo)力,歐盟需要在戰(zhàn)略上適應(yīng)美國(guó)的氣候戰(zhàn)略,而歐盟傳統(tǒng)的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有可能被削弱。
另一方面,美國(guó)和歐盟在對(duì)中國(guó)清潔技術(shù)投資方面存在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盡管在出口清潔能源產(chǎn)品和技術(shù)領(lǐng)域,歐洲與美國(guó)類似,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市場(chǎng)開放、所謂不公平競(jìng)爭(zhēng)及價(jià)值觀等方面對(duì)中國(guó)則有相似的訴求。④張健:“大變局下歐洲戰(zhàn)略取向及其影響”,《現(xiàn)代國(guó)際關(guān)系》,2021年第1期,第10-20頁(yè)。但美國(guó)和歐盟對(duì)于爭(zhēng)取中國(guó)市場(chǎng)存在明顯的利益沖突。歐盟認(rèn)為,“美國(guó)在2020年初與中國(guó)達(dá)成第一階段經(jīng)貿(mào)協(xié)議的做法,損害并嚴(yán)重?cái)_亂了市場(chǎng)秩序,是典型的單邊主義和利己主義”⑤Paul Taylor,“In Defense of the EU-China Investment Deal,”January 8,2021,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atlarge-eu-china-investment-deal/,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2月27日。。而美方認(rèn)為,“歐洲率先與中國(guó)達(dá)成《中歐全面投資協(xié)定》,就意味著美國(guó)將在中國(guó)市場(chǎng)面臨損失,美歐就面臨在利益面前被中國(guó)‘分而治之’的風(fēng)險(xiǎn),并且可能由于缺乏團(tuán)結(jié)喪失更多對(duì)華要價(jià)權(quán)”⑥Hans Binnendijk,Sarah Kirchberger,and Christopher Skalu?ba,“Capitalizing on Transatlantic Concerns about China,”August 24,2020,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capitalizing-on-transatlantic-concerns-about-china/,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2月27日。。
三、全球氣候治理走勢(shì)展望
盡管中國(guó)、美國(guó)和歐盟三大經(jīng)濟(jì)體都把全球氣候治理作為施展自身領(lǐng)導(dǎo)力的“舞臺(tái)”,然而當(dāng)前中國(guó)、美國(guó)和歐盟在兌現(xiàn)《巴黎協(xié)定》承諾時(shí),任何一個(gè)領(lǐng)導(dǎo)者都無(wú)法主導(dǎo)全球氣候治理的方向。當(dāng)今世界各國(guó)已經(jīng)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隨著全球氣候風(fēng)險(xiǎn)日益凸顯,客觀上為中美歐合作應(yīng)對(duì)全球氣候變化提供了抓手。盡管中國(guó)、歐盟和美國(guó)三大行為體依據(jù)自身的不同發(fā)展階段和利益訴求,制定了不同的氣候轉(zhuǎn)型戰(zhàn)略,在全球氣候治理領(lǐng)域存在諸多博弈,但他們氣候戰(zhàn)略的主要目的是落實(shí)《巴黎協(xié)定》的現(xiàn)有承諾,最終實(shí)現(xiàn)全球凈零碳排放。中國(guó)在提出推動(dòng)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理念時(shí)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一國(guó)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別國(guó)的動(dòng)蕩之上,他國(guó)的威脅也可能成為本國(guó)的挑戰(zhàn)”⑦陳明琨:“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思想的多重超越”,《經(jīng)濟(jì)社會(huì)體制比較》,2018年第6期,第9-17頁(yè)。。因此,如果各國(guó)能從集體理性的角度出發(fā),堅(jiān)持多邊主義合作方向,中美歐三方存在合作的客觀條件。全球氣候治理領(lǐng)導(dǎo)者需要通過(guò)加強(qiáng)領(lǐng)導(dǎo)者合作,深化全球氣候共識(shí),克服自身在全球氣候治理中面臨的困難。
3.1 美歐可能達(dá)成的氣候合作
2020年12月2日,歐盟委員會(huì)發(fā)布了《全球變局下的歐美新議程》,為美歐在跨大西洋與世界范圍內(nèi)開展全球合作提供了方向。2021年3月9日,美歐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指出,“美國(guó)堅(jiān)持不遲于2050年實(shí)現(xiàn)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的目標(biāo),歐盟堅(jiān)持在2050年實(shí)現(xiàn)‘碳中和’”①“Joint Statem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ommit to Greater Cooperation to Counter the Climate Crisis,”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9,2021,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the-united-states-and-the-european-union-commit-to-greater-cooperation-to-counter-the-climate-crisis/,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4月27日。。這將使氣候中和成為格拉斯哥氣候峰會(huì)(COP26)籌備階段的新全球基準(zhǔn)。具體來(lái)說(shuō),美歐未來(lái)的合作可能從以下四個(gè)方面開展。
第一,提出新的跨大西洋綠色貿(mào)易議程,其中應(yīng)包括世界貿(mào)易組織(WTO)內(nèi)的貿(mào)易與氣候倡議以及避免碳泄漏的措施。在氣候變化問(wèn)題上,中美兩國(guó)因地緣政治的因素難有深度的合作。2021年3月10日,歐洲議會(huì)投票通過(guò)設(shè)立“碳邊界調(diào)節(jié)機(jī)制”的決議,提出構(gòu)建與世界貿(mào)易組織(WTO)兼容的歐盟碳邊界調(diào)整機(jī)制,以避免碳泄漏。未來(lái)以跨大西洋碳定價(jià)和關(guān)稅為基礎(chǔ)的美歐“氣候俱樂(lè)部”,是美國(guó)與歐盟為此類措施設(shè)定全球標(biāo)準(zhǔn)的合作機(jī)會(huì)。
第二,借鑒歐盟分類法的經(jīng)驗(yàn),共同擬定可持續(xù)金融全球監(jiān)管框架。歐盟和美國(guó)是主要的金融中心和監(jiān)管者,在可持續(xù)金融監(jiān)管框架中開展跨大西洋合作,讓私營(yíng)部門了解什么是綠色投資。這種私人融資對(duì)投資合適的技術(shù)、給予創(chuàng)新者與公司先發(fā)優(yōu)勢(shì)方面至關(guān)重要。歐盟和美國(guó)兌現(xiàn)氣候融資承諾對(duì)廣大發(fā)展中國(guó)家十分重要。美歐的共同支持,可以幫助發(fā)展中國(guó)家在最新的科學(xué)發(fā)現(xiàn)和最優(yōu)技術(shù)上取得進(jìn)步。
第三,建立跨大西洋的綠色技術(shù)聯(lián)盟,以確保在開發(fā)清潔和循環(huán)技術(shù)以及領(lǐng)導(dǎo)市場(chǎng)方面加強(qiáng)合作。歐盟和美國(guó)應(yīng)利用其經(jīng)驗(yàn)和專業(yè)知識(shí),通過(guò)新的綠色技術(shù)聯(lián)盟領(lǐng)導(dǎo)市場(chǎng),并在清潔和循環(huán)技術(shù)方面進(jìn)行合作,例如可再生能源、電網(wǎng)儲(chǔ)能、電池、清潔氫,以及碳捕獲、封存和利用。這將補(bǔ)充歐盟—美國(guó)能源理事會(huì)(EU-US Energy Council)的工作,為跨大西洋投資提供肥沃土壤,并支持伙伴國(guó)履行各自的氣候承諾。
第四,更廣泛地保護(hù)自然和環(huán)境。歐盟鼓勵(lì)美國(guó)加入《生物多樣性公約》,共同致力于領(lǐng)導(dǎo)反對(duì)森林砍伐運(yùn)動(dòng)并加強(qiáng)海洋保護(hù)——從共同致力于達(dá)成一項(xiàng)全球塑料條約并規(guī)劃南冰洋海洋保護(hù)區(qū)開始。美國(guó)也在氣候領(lǐng)導(dǎo)人峰會(huì)上提出要開展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歐盟和美國(guó)努力確保達(dá)成一項(xiàng)雄心勃勃的協(xié)議,以保護(hù)世界30%的土地和30%的海洋。
3.2 中美可能達(dá)成的氣候合作
2021年4月15日至16日,中美兩國(guó)氣候特使在上海舉行會(huì)談并發(fā)表《中美氣候危機(jī)聯(lián)合聲明》,提出中美兩國(guó)堅(jiān)持?jǐn)y手并與其他各方一道加強(qiáng)《巴黎協(xié)定》的實(shí)施。未來(lái),中美兩國(guó)可能的合作領(lǐng)域有以下三個(gè)方面。
第一,重建中美氣候變化合作關(guān)系,提振全球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的信心。以美國(guó)領(lǐng)導(dǎo)人氣候峰會(huì)為契機(jī),成立“中美零碳工作組”,推動(dòng)溝通并建立互信。中美零碳工作組可以設(shè)置由行業(yè)和技術(shù)合作、定期高層政策對(duì)話和國(guó)內(nèi)政策對(duì)話組成的三方聯(lián)動(dòng)架構(gòu),共同推進(jìn)《巴黎協(xié)定》相關(guān)機(jī)制的落地,加強(qiáng)中美在氣候變化領(lǐng)域的公開透明和對(duì)話溝通。中美零碳工作組應(yīng)將所取得的進(jìn)展直接融入二十國(guó)集團(tuán)(G20)、主要經(jīng)濟(jì)體論壇(Major Economies Forum),以及一年一度的聯(lián)合國(guó)氣候大會(huì)等國(guó)際進(jìn)程中。中美可以發(fā)揮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倡導(dǎo)建立“凈零排放聯(lián)盟(Net-zero coalition)”,圍繞實(shí)現(xiàn)凈零碳排放所需要的貿(mào)易政策、投融資政策、科技創(chuàng)新政策等內(nèi)容,開展制度互認(rèn)和對(duì)接,積極踐行綠色發(fā)展承諾,提振全球綠色發(fā)展信心。
第二,重新凝聚氣候共識(shí),推動(dòng)《巴黎協(xié)定》實(shí)施細(xì)則落地。《中美氣候危機(jī)聯(lián)合聲明》中也提出要啟動(dòng)制定美國(guó)在《巴黎協(xié)定》下的“國(guó)家自主貢獻(xiàn)”,提高全球氣候雄心。因此,中方可以推動(dòng)工業(yè)和電力領(lǐng)域脫碳、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綠色和氣候韌性農(nóng)業(yè)、節(jié)能建筑、綠色低碳交通、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合作、國(guó)際航空航海活動(dòng)排放合作等相關(guān)議題的交流,爭(zhēng)取在COP26上,推動(dòng)制定圍繞《巴黎協(xié)定》第六條、第十三條國(guó)家自主貢獻(xiàn)(NDC)和透明度框架相關(guān)的具體實(shí)施細(xì)則。
第三,圍繞清潔技術(shù)和產(chǎn)業(yè)升級(jí)的政策開展合作,深化中美利益共同點(diǎn)。拜登上臺(tái)后,在《美國(guó)就業(yè)計(jì)劃》中更加主張政府扶持基金資助新能源汽車企業(yè)、鋪設(shè)充電基礎(chǔ)設(shè)施和其他燃料電池、固態(tài)電池、無(wú)人駕駛、第四代核反應(yīng)堆技術(shù)等重大前瞻性技術(shù),推動(dòng)美國(guó)企業(yè)向全球出口清潔能源技術(shù)。總體看,在基礎(chǔ)材料、關(guān)鍵零部件、系統(tǒng)集成等方面,我國(guó)新能源電池汽車產(chǎn)業(yè)與國(guó)際先進(jìn)水平還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中美清潔能源科技合作與技術(shù)交流具有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
3.3 中歐可能達(dá)成的氣候合作
2021年4月16日下午,中法德領(lǐng)導(dǎo)人視頻峰會(huì)在北京舉行,國(guó)家主席習(xí)近平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yè),不應(yīng)該成為地緣政治的籌碼、攻擊他國(guó)的靶子、貿(mào)易壁壘的借口。中法德領(lǐng)導(dǎo)人峰會(huì)在美國(guó)領(lǐng)導(dǎo)人氣候峰會(huì)之前召開,為中歐凝聚共識(shí)提供了交流平臺(tái),重新明確了中國(guó)和歐盟的氣候領(lǐng)導(dǎo)者地位。中歐氣候合作未來(lái)的可能思路有以下三個(gè)方面。
第一,從戰(zhàn)略層面來(lái)看,中歐應(yīng)從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角度對(duì)氣候合作進(jìn)行整體規(guī)劃。氣候變化是全球性問(wèn)題,在改善、加強(qiáng)全球氣候治理的共同利益方面,中歐雙方要用好中歐環(huán)境與氣候高層對(duì)話機(jī)制,借助中國(guó)—?dú)W盟領(lǐng)導(dǎo)人會(huì)晤、“27+1”中歐峰會(huì)、中國(guó)—中東歐國(guó)家領(lǐng)導(dǎo)人會(huì)議,相互支持中歐舉辦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自然保護(hù)國(guó)際會(huì)議,增強(qiáng)應(yīng)對(duì)全球氣候變化的共識(shí)。尤其是在對(duì)非洲不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氣候援助方面,歐盟的利益在于推動(dòng)非洲提高氣候適應(yīng)能力,從而阻止新的移民潮,遏制極右翼政黨的復(fù)興。這與中國(guó)提倡的“南南合作”在利益上有共同之處。
第二,從機(jī)制層面來(lái)看,中歐應(yīng)打造具有更廣泛內(nèi)涵的“綠色伙伴關(guān)系”機(jī)制。而如期完成的中歐投資協(xié)定談判,消除了歐盟某些行業(yè)在中國(guó)的投資壁壘,包括新能源汽車、云計(jì)算服務(wù)、金融服務(wù)等,這將為歐洲和世界應(yīng)對(duì)氣候風(fēng)險(xiǎn)提供更多市場(chǎng)機(jī)遇、創(chuàng)造更大合作空間。中國(guó)已經(jīng)加入國(guó)際可持續(xù)金融平臺(tái)(IPSF),并對(duì)綠色基金和債務(wù)減免表現(xiàn)出了一定的興趣,中歐可以攜手完善“一帶一路”綠色融資機(jī)制。①M(fèi)ichael I.Westphal and Shuang Liu,“In the Time of COVID-19,China Could Be Pivotal in Swapping Debt for Climate and Health Action,”November 4,2020,https://www.wri.org/blog/2020/11/time-covid-19-china-could-be-pivotal-swapping-debt-climateandhealth-action,訪問(wèn)時(shí)間:2021年4月27日。中歐可在碳邊境調(diào)節(jié)機(jī)制政策領(lǐng)域加強(qiáng)溝通,將《中歐全面投資協(xié)定》中關(guān)于市場(chǎng)準(zhǔn)入、公平競(jìng)爭(zhēng)環(huán)境和可持續(xù)發(fā)展三個(gè)方面做出的必要的實(shí)質(zhì)性承諾予以落實(shí)。
第三,從行動(dòng)層面來(lái)看,中歐在氣候合作領(lǐng)域存在多個(gè)抓手。中歐可以利用好COP26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會(huì)議,加強(qiáng)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在城市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中的應(yīng)用合作,支持中歐可持續(xù)金融標(biāo)準(zhǔn)對(duì)接,推動(dòng)“一帶一路”投資的綠色化,共同為非洲國(guó)家提供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領(lǐng)域的資金支持,支持發(fā)展中國(guó)家能源供給向高效、清潔、多元化方向發(fā)展,共同發(fā)起并參與雙邊、區(qū)域和多邊碳市場(chǎng)等。
四、結(jié) 論
美國(guó)重返《巴黎協(xié)定》后的全球氣候治理格局發(fā)生了新的變化,中美歐圍繞全球氣候領(lǐng)導(dǎo)力開展的氣候博弈日益凸顯。美國(guó)重返《巴黎協(xié)定》后,美國(guó)和歐盟在爭(zhēng)奪氣候領(lǐng)導(dǎo)力方面的戰(zhàn)略考量和具體行動(dòng)各有不同。美歐對(duì)爭(zhēng)奪氣候領(lǐng)導(dǎo)力的追求面臨著集體理性與個(gè)體理性的沖突,對(duì)低碳技術(shù)和低碳經(jīng)濟(jì)規(guī)則制定權(quán)的爭(zhēng)奪成為新一輪國(guó)際權(quán)力政治的核心內(nèi)容。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領(lǐng)導(dǎo)者,中國(guó)、美國(guó)和歐盟只有以集體理性為原則,才能推動(dòng)形成國(guó)際社會(huì)的氣候雄心和行動(dòng),共同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
一方面,要完善全球綠色金融的政策體系,更好地支持發(fā)展中國(guó)家“綠色復(fù)蘇”。推動(dòng)中美歐綠色金融標(biāo)準(zhǔn)合作和趨同,逐步實(shí)現(xiàn)全球主要綠色金融標(biāo)準(zhǔn)接軌。另一方面,針對(duì)重點(diǎn)行業(yè)開展零碳技術(shù)轉(zhuǎn)型示范,提升零碳技術(shù)行動(dòng)引領(lǐng)的全球領(lǐng)導(dǎo)力。聚焦能源轉(zhuǎn)型戰(zhàn)略下能源、建筑、交通三大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綠色化解決方案,為實(shí)現(xiàn)全球零碳能源轉(zhuǎn)型探索可行路徑。此外,還要完善全球碳交易市場(chǎng)機(jī)制的構(gòu)建,形成搭橋方案,確保格拉斯哥大會(huì)達(dá)成《巴黎協(xié)定》下全球碳市場(chǎng)機(jī)制實(shí)施細(xì)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