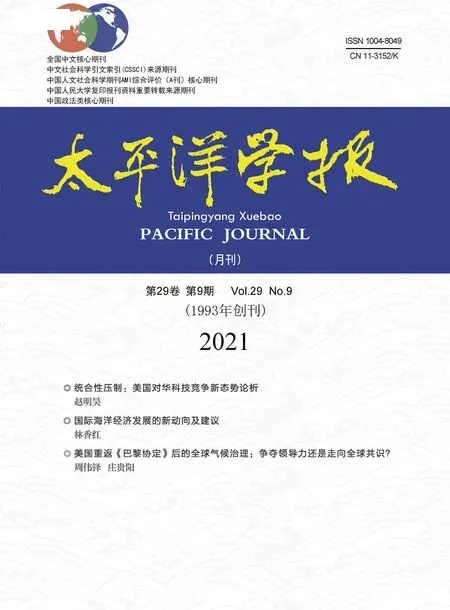正確義利觀與“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治理
張中元
(1.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北京 100007)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現(xiàn)代化需求旺盛、城鎮(zhèn)化建設(shè)步伐加快,這給國際產(chǎn)能合作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國際產(chǎn)能合作鼓勵中國企業(yè)走出國門,推動沿線國家的工業(yè)化進程、技術(shù)進步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增強沿線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的自生能力。在“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中,中國企業(yè)更深入地參與到全球價值鏈和區(qū)域價值鏈中,構(gòu)建“一帶一路”價值鏈成為加強沿線各國企業(yè)之間經(jīng)濟技術(shù)聯(lián)系和利益的紐帶,產(chǎn)能合作通過滿足各參與方的利益訴求,提高人民生活質(zhì)量,更好地應(yīng)對技術(shù)與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支持“一帶一路”建設(sh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使部分沿線國家的跨越式發(fā)展成為可能。
但長期內(nèi),在全球價值鏈中占主導(dǎo)地位的發(fā)達國家企業(yè)壟斷了企業(yè)社會責(zé)任標(biāo)準(zhǔn)的制定,給發(fā)展中國家企業(yè)經(jīng)營活動帶來了較強的限制。在西方模式主導(dǎo)下的傳統(tǒng)產(chǎn)能合作中,以競爭效率為核心的倫理價值觀長期占據(jù)主流地位,導(dǎo)致經(jīng)濟權(quán)力過度掌控在主導(dǎo)企業(yè)手中。而且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試圖以相互競爭的方式為自己獲取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主導(dǎo)地位,各社會行為體有意或無意地利用自己掌握的話語權(quán),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界定自己與其他社會行動者的差異,將其作為獲得權(quán)力的載體和創(chuàng)造話語霸權(quán)的機會。因此,在產(chǎn)能合作參與方多極化的情形下,當(dāng)前傳統(tǒng)的國際產(chǎn)能合作治理遠(yuǎn)遠(yuǎn)不能解決產(chǎn)能合作實踐中出現(xiàn)的許多問題。
為了破解產(chǎn)能合作治理實踐和發(fā)展的困境,中國對企業(yè)行為選擇背后的倫理價值觀進行了深度思考,在堅持義利關(guān)系辯證統(tǒng)一的價值內(nèi)核基礎(chǔ)上,從建設(sh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biāo)出發(fā),提出了正確義利觀。正確義利觀強調(diào)取之有義、以義統(tǒng)利、見利思義、義利統(tǒng)一等價值理念,對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倫理價值觀與現(xiàn)代產(chǎn)能合作治理的重塑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正確義利觀超越了傳統(tǒng)西方產(chǎn)能合作治理中“非義即利”的簡單對立,強調(diào)平等基礎(chǔ)上的利益交匯和共同參與中的利益分享,引導(dǎo)企業(yè)在實現(xiàn)自身利益、促進自身發(fā)展的同時,要兼顧東道國本地利益,既保持了對民族國家核心利益的真實關(guān)切,又強調(diào)人類整體利益和互利共贏的重要性。正確義利觀為“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提供了價值引領(lǐng),有助于中國企業(yè)打破西方國家主導(dǎo)的產(chǎn)能合作治理給中國和沿線國家?guī)淼牟焕绊憽?/p>
一、“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進展與面臨的挑戰(zhàn)
隨著越來越多的發(fā)展中國家以可持續(xù)性發(fā)展理念來指導(dǎo)自己的發(fā)展政策,“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聚焦于沿線國家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高度重視實現(xiàn)各國獲得平等的增長機會,注重沿線國家實現(xiàn)能力建設(shè)導(dǎo)向的可持續(xù)性產(chǎn)業(yè)合作。
1.1 “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的進展
“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優(yōu)先支持能夠有效拉動當(dāng)?shù)鼐蜆I(yè)、增加當(dāng)?shù)鼐用袷杖氲拿裆a(chǎn)能合作項目。參與“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的中國企業(yè)立足主業(yè)優(yōu)勢,加速融入當(dāng)?shù)禺a(chǎn)業(yè)鏈中,為東道國經(jīng)濟發(fā)展與社會進步提供助力。企業(yè)不只局限于自身盈利上,還注重當(dāng)?shù)孛癖姷睦嫘枨螅谘鼐€發(fā)展自身業(yè)務(wù)的同時,對當(dāng)?shù)貑T工開展技術(shù)培訓(xùn),培養(yǎng)當(dāng)?shù)毓芾砣藛T,給當(dāng)?shù)乩习傩諑硖嵘寄堋?chuàng)造就業(yè)等發(fā)展機會,讓當(dāng)?shù)厝饲袑嵉玫綄嵒菖c尊重。企業(yè)通過設(shè)立公益基金、捐資當(dāng)?shù)鼗饡确绞剑e極參與海外公益事業(yè)。例如,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口城是由中國港灣投資建設(shè)運營的大型城市綜合體開發(fā)項目,項目公司與斯里蘭卡政府協(xié)商,推出“漁民生計改善計劃”,分期總計提供5.5億盧比(約330萬美元)費用用于幫助當(dāng)?shù)貪O民改善醫(yī)療、教育、衛(wèi)生等方面的生活條件。為了配合計劃實施,斯里蘭卡政府也專門成立了“漁民生計改善協(xié)會”并提供專門款項。這一計劃得到了尼甘布當(dāng)?shù)貪O民的強烈擁護,他們對項目的態(tài)度也從最初的抵觸轉(zhuǎn)變?yōu)槔斫夂椭С帧"佟爸袊煌ńㄔO(shè)集團有限公司:在斯里蘭卡講好‘一帶一路’履責(zé)故事”,國務(wù)院資產(chǎn)管理委員會網(wǎng)站,2021年1月12日,http://www.sasac.gov.cn/n4470048/n13461446/n14398052/n1646 0319/n16460417/c16495887/content.html,訪問時間:2021年2月17日。
“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在促進中國企業(yè)成長的同時,也促進了沿線國家進行自生能力建設(shè),使經(jīng)濟增長惠及更多的國家、更多的民眾,使沿線國家分享經(jīng)濟發(fā)展成果。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是“一帶一路”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重點所在,推動基礎(chǔ)設(shè)施重大項目順利完工能夠更好惠及沿線國家和人民。基礎(chǔ)設(shè)施互聯(lián)互通作為“一帶一路”建設(shè)的優(yōu)先領(lǐng)域,對沿線國家的能力建設(shè)與經(jīng)濟起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一帶一路”基礎(chǔ)設(shè)施重大項目建設(shè)過程中,中國政府引導(dǎo)企業(yè)算好“政治賬”和“經(jīng)濟賬”,在合作中盡可能考慮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實際困難,對那些既有戰(zhàn)略意義、又有經(jīng)濟價值的項目建設(shè)給予優(yōu)先支持。一些企業(yè)主動提供基礎(chǔ)設(shè)施,參與社區(qū)發(fā)展計劃,改善所在社區(qū)的生活條件,化解當(dāng)?shù)孛軟_突,減少經(jīng)營活動的負(fù)面影響。
在“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中,中國企業(yè)注重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堅持可持續(xù)發(fā)展、遵循共贏理念。中國走出去的企業(yè)在追求經(jīng)濟利益的同時,注重環(huán)境保護,主動構(gòu)建資源節(jié)約型、環(huán)境友好型綠色企業(yè)。①“央企‘一帶一路’履責(zé)情況分析”,國務(wù)院資產(chǎn)管理委員會網(wǎng)站,2019年3月25日,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4423279/n4517386/n10745109/c10803539/content.html,訪 問 時間:2021年2月17日。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依靠企業(yè)重大工程和優(yōu)勢產(chǎn)業(yè)追求環(huán)境可持續(xù)發(fā)展。②“中交集團發(fā)布中國企業(yè)首份‘一帶一路’專題社會責(zé)任報告”,國務(wù)院資產(chǎn)管理委員會網(wǎng)站,2018年5月28日,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24/c9056819/content.html,訪問時間:2021年2月17日。在穩(wěn)步推進工程建設(shè)的同時,采取相應(yīng)措施為當(dāng)?shù)丨h(huán)境保護貢獻力量,獲得了當(dāng)?shù)厣鐣兔襟w的認(rèn)可。③“土耳其‘一帶一路’建設(shè)項目積極履行海外社會責(zé)任”,“一帶一路”網(wǎng),2020年9月30日,http://ydyl.china.com.cn/2020-09/30/content_76766780.htm,訪問時間:2021年2月17日。中國政府鼓勵企業(yè)在項目建設(shè)中積極回應(yīng)當(dāng)?shù)厣鐣V求,注重保護環(huán)境等社會責(zé)任,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chǎn)能合作的各方實現(xiàn)共贏和共同發(fā)展。2017年5月,環(huán)保部發(fā)布了《“一帶一路”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合作規(guī)劃》,規(guī)劃推動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環(huán)境目標(biāo),并對落實一系列生態(tài)環(huán)保合作支持政策進行了系統(tǒng)規(guī)劃,全面提升了“一帶一路”建設(shè)中生態(tài)環(huán)保合作水平。
1.2 “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中存在的問題與挑戰(zhàn)
新冠疫情的暴發(fā)和全球保護主義的進一步升溫,成為推動“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持續(xù)健康發(fā)展面臨的主要挑戰(zhàn)。中國企業(yè)能否成功應(yīng)對產(chǎn)能合作過程中面臨的社會、制度壓力,關(guān)系到跨國企業(yè)經(jīng)營能否融入當(dāng)?shù)厣鐣踔翛Q定著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產(chǎn)能合作的成敗。
國家對企業(yè)的非監(jiān)管(如資源控制、行政要求或規(guī)范、意識形態(tài)影響)影響至關(guān)重要,如何應(yīng)對和管理這些非監(jiān)管權(quán)力關(guān)系到參與產(chǎn)能合作企業(yè)的生存和發(fā)展。企業(yè)利用各種途徑尋求與國家的合作,履行企業(yè)社會責(zé)任以滿足東道國的期望,以用來加強與東道國的關(guān)系。目前,中國企業(yè)與沿線國家產(chǎn)能合作主要集中于礦產(chǎn)、能源、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等極易對當(dāng)?shù)丨h(huán)境造成影響的領(lǐng)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正處于工業(yè)化發(fā)展的初級階段,法律尚不健全,造成生態(tài)破壞和環(huán)境污染的事件時有發(fā)生,從而造成沿線國家愿意降低標(biāo)準(zhǔn)、犧牲環(huán)境吸引中國企業(yè)投資的表象。沿線部分國家的政策、立法也存在很大不確定性,有時東道國政府為了應(yīng)對社會、民眾的壓力,不愿與或無法兌現(xiàn)政府的政策承諾,從原先支持項目投資發(fā)展,到削弱支持力度甚至限制項目投資,隨意采取的規(guī)制措施使得政策性支持投資項目極易橫生變故。“一帶一路”沿線較多國家處于政治地緣分裂地帶,一些產(chǎn)業(yè)(如采礦業(yè))的經(jīng)營活動可能會強化一個國家現(xiàn)有的權(quán)力不對稱,加劇沖突。中資企業(yè)面臨著地區(qū)復(fù)雜政治經(jīng)濟環(huán)境誘發(fā)的治理政治不穩(wěn)定、政治審查等風(fēng)險,導(dǎo)致中國企業(yè)的潛在投資風(fēng)險也隨之增加。
在社會層面,一些西方主導(dǎo)的社會組織利用話語權(quán)優(yōu)勢抹黑“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隨著國家通過公共政策,以明示或默示的授權(quán)方式,將各種治理職能和權(quán)力下放給非國家行為體,加強了非國家行為體權(quán)力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和全球非國家機構(gòu)在制定全球商品可持續(xù)生產(chǎn)、貿(mào)易跨國規(guī)則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除了大型主導(dǎo)企業(yè)、全球貿(mào)易商、分銷商等參與者群體,其他諸如關(guān)注環(huán)境和社會問題的非政府組織、行業(yè)標(biāo)準(zhǔn)制定者、媒體和社團的影響也與日俱增,多元行為體對全球產(chǎn)能合作治理規(guī)則和互動方式的塑造能力也大為增強。④Stefano Ponte and Timothy Sturgeon,“Explaining Governa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A Modular Theory-Building Effor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1,No.1,2014,pp.195-223.在“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過程中,中國走出去企業(yè)除了面對來自東道國的制度約束外,還要面對來自第三方(如發(fā)達國家主導(dǎo)的國際組織)的規(guī)則、標(biāo)準(zhǔn)等方面的壓力。這些非政府組織、工會、媒體對企業(yè)施加壓力,要求企業(yè)制定企業(yè)行為準(zhǔn)則或遵守預(yù)先確定的道德準(zhǔn)則。但一些西方社會組織憑借自身的專業(yè)性以及相對獨立的身份,在塑造和引領(lǐng)產(chǎn)能合作規(guī)則、規(guī)范方面具有較大的優(yōu)勢,他們更多的是將產(chǎn)能合作治理作為一種技術(shù)手段,把推進產(chǎn)能合作治理作為自己獲得表達權(quán)和話語權(quán)的過程,試圖壟斷產(chǎn)能合作治理的界定和內(nèi)涵解釋以謀取私利。例如,中國以國企為主的投資主體結(jié)構(gòu),企業(yè)的正常投資行為就常常被一些國際社會組織惡意誤導(dǎo)為背后有國家力量支持,是反應(yīng)中國政府意志和意圖的戰(zhàn)略行為。少數(shù)西方大國為維護、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利益,利用其控制的社會組織肆意挑撥中國與沿線國家的關(guān)系,給“一帶一路”投資項目貼各種標(biāo)簽,煽動沿線國家部分民眾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當(dāng)?shù)孛癖娫诿襟w的宣傳攻勢之下,往往會很容易接受媒體宣傳中所攜帶的誘導(dǎo)性觀點,并把媒體的觀點不自覺地轉(zhuǎn)化為自己的觀點。
在傳統(tǒng)的價值鏈治理中,國家、社會和全球機構(gòu)在制定適用于全球市場規(guī)則方面能力有限,①William S.Laufer,“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Corporate Greenwashing,”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43,No.3,2003,pp.253-261.,②Marina Prieto-Carrón,Peter Lund-Thomsen,Anita Chan,Ana Muro and Chandra Bhushan,“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SR and Development:What We Know,What We Dont Know,and What We Need To Know,”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2,No.5,2006,pp.977-987.來自發(fā)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治理責(zé)任轉(zhuǎn)移到了跨國公司身上。跨國公司使用多種工具來管理其全球供應(yīng)鏈和價值鏈,包括但不限于行為準(zhǔn)則、合同和旨在監(jiān)督其內(nèi)部社會和環(huán)境狀況的監(jiān)督審查等。跨國公司受利益驅(qū)動,利用其在價值鏈中的支配地位,在其供應(yīng)鏈內(nèi)執(zhí)行產(chǎn)能合作行為準(zhǔn)則,往往強調(diào)保護財產(chǎn)收益,以加強發(fā)達國家主導(dǎo)企業(yè)的地位,并限制發(fā)展中國家供應(yīng)商轉(zhuǎn)向高附加值生產(chǎn)的能力,從而剝奪了發(fā)展中國家獲取價值的機會,導(dǎo)致中國與沿線國家企業(yè)在產(chǎn)能合作中受到極大的擠壓。
二、“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中的正確義利觀實踐
2.1 正確義利觀的提出
“一帶一路”建設(shè)不僅需要利益共享,而且還需要價值共識。2013年10月,習(xí)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處理對外關(guān)系要“找到利益的共同點和交匯點,堅持正確義利觀”。③習(xí)近平:“堅持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習(xí)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299頁。在2014年年底,習(xí)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diào):“要堅持正確義利觀,做到義利兼顧,要講信義、重情義、揚正義、樹道義。”④習(xí)近平:“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習(xí)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443頁。2016年4月29日,習(xí)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體學(xué)習(xí)時強調(diào):“要堅持正確義利觀,以義為先、義利并舉,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為。要統(tǒng)籌我國同沿線國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異性的利益關(guān)切,尋找更多利益交匯點,調(diào)動沿線國家積極性。我國企業(yè)走出去既要重視投資利益,更要贏得好名聲、好口碑,遵守駐在國法律,承擔(dān)更多社會責(zé)任。”⑤習(xí)近平:“推進‘一帶一路’建設(shè),努力拓展改革發(fā)展新空間”,《習(xí)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501頁。正確義利觀將功利和道義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主張正確認(rèn)識和處理義利關(guān)系,超越了狹隘功利主義和抽象道義論的局限。“以義為先,弘義融利”突出了“義”的重要性,在國際合作中講求道義和公平正義,堅持道義為先;“義利兼顧,義利共贏”強調(diào)了義利統(tǒng)一,將功利和道義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義重于利,公道正義”,強調(diào)在義與利發(fā)生矛盾的情況下,堅持道義當(dāng)先,不以利害義,必要時舍利取義。總之,正確的義利觀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出發(fā),為建構(gòu)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產(chǎn)能合作提供價值基礎(chǔ)和道德基石,從而有利于加快構(gòu)建中國特色商業(yè)義利觀,克服產(chǎn)能合作中的治理赤字。
2.2 正確義利觀對“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治理的指導(dǎo)意義
正確義利觀倡導(dǎo)的共同價值超越了單純的自利或效用最大化,而是激勵企業(yè)在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建立各種合作方式,在公平規(guī)范的范圍內(nèi)運作,從參與中獲得利益。能力建設(shè)導(dǎo)向?qū)ρ鼐€國家來說非常重要,通過培養(yǎng)能力,避免發(fā)展中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對經(jīng)濟增長產(chǎn)生持久的推動作用。①李曉華:“能力建設(shè)導(dǎo)向的包容性國際產(chǎn)能合作”,《經(jīng)濟與管理研究》,2019年第5期,第20頁。“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聚焦發(fā)展問題,提倡“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重視推動沿線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自生能力的提升,旨在同沿線各國分享中國發(fā)展機遇,實現(xiàn)共同繁榮,切合各國迫切需要。在“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中,正確義利觀強調(diào)企業(yè)追求“利”的行為必須受“義”的約束,做到先義后利,提高了產(chǎn)能合作中參與者的合作傾向和能力,有利于在利益相關(guān)者之間建立責(zé)任結(jié)構(gòu)。
首先,正確義利觀有利于塑造合理化的政府、企業(yè)、社會關(guān)系,克服了產(chǎn)能合作治理中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領(lǐng)域的嚴(yán)格分離。在全球化時代嚴(yán)格分離社會的私人和公共領(lǐng)域,可能是不成立的。②Frederick W.Mayer and Nicola Phillips,“Outsourcing Gov?ernance:States and the Politics of a‘Global Value Chain World’,”New Political Economy,Vol.22,No.2,2017,pp.134-152.在當(dāng)前企業(yè)和非企業(yè)參與者爭相界定產(chǎn)能合作治理的含義和范圍背景下,對于公共和私人治理是否或如何能夠形成一個互補的體系,關(guān)鍵在于企業(yè)、社會、國家是否實現(xiàn)協(xié)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正確義利觀關(guān)注國家在產(chǎn)能合作治理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國家并不局限于正式規(guī)則和硬性法律,也不僅僅是傳統(tǒng)的、層級意義上的政府監(jiān)管。國家通過規(guī)范企業(yè)在法律規(guī)范之內(nèi)追求自己的“私利”,企業(yè)作為社會成員,有責(zé)任為改善社會條件作出積極貢獻,有利于在企業(yè)與公共利益之間形成共贏的伙伴關(guān)系,實現(xiàn)促進國家、社會“公利”的目標(biāo),在企業(yè)—社會—國家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實現(xiàn)企業(yè)的“私利”與社會的“公利”的統(tǒng)一,從而有助于獲得政治認(rèn)可和國家支持。
其次,在“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中,正確義利觀還要求企業(yè)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其他相關(guān)者的合理關(guān)切,不斷擴大共同利益匯合點,把自身利益和國家、社會利益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在發(fā)達國家跨國企業(yè)主導(dǎo)的全球產(chǎn)能合作治理中,企業(yè)把產(chǎn)能合作治理看作是促進企業(yè)經(jīng)濟利益的有效的工具和手段,產(chǎn)能合作中的主導(dǎo)企業(yè)出于維護自身競爭力和主導(dǎo)權(quán)的目的,過度強調(diào)履行高水平的產(chǎn)能合作治理標(biāo)準(zhǔn),借以削弱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貿(mào)易中依賴低勞動成本帶來的競爭力,限制發(fā)展中國家供應(yīng)商轉(zhuǎn)向高附加值生產(chǎn)的能力,從而剝奪了發(fā)展中國家獲取價值的機會。傳統(tǒng)的產(chǎn)能合作治理工具往往無法產(chǎn)生預(yù)期的結(jié)果,也無法在產(chǎn)能合作參與者中獲得合法性。③Patrick M.Erwin,“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The Effects of Code Content and Quality on Ethical Performance,”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99,No.4,2011,pp.535-548.而在正確的義利觀中,“義”和“利”本質(zhì)上是合一的,正確義利觀承認(rèn)商業(yè)企業(yè)的經(jīng)濟價值偏好,尊重企業(yè)運行的商業(yè)邏輯和市場邏輯,不以道德倫理要求代替企業(yè)的經(jīng)濟價值偏好,但也不用社會邏輯替代商業(yè)邏輯和市場邏輯;而是承認(rèn)企業(yè)與社會之間存在“雙贏”的潛能,從根本上激勵企業(yè)內(nèi)生出參與解決社會問題的動力。
再次,正確義利觀承認(rèn)義與利是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社會中企業(yè)不可回避的問題,它將企業(yè)層面的目標(biāo)(重視投資收益)與國家層面的目標(biāo)(贏得好名聲、好口碑)有機結(jié)合起來。這一理念將“義”的思想從道德領(lǐng)域引入經(jīng)濟領(lǐng)域,通過企業(yè)與政府、社會部門合作參與解決面臨的合作問題。正確義利觀既強調(diào)企業(yè)正當(dāng)利益的實現(xiàn),又突出企業(yè)的政治責(zé)任維度、國家戰(zhàn)略導(dǎo)向;既倡導(dǎo)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廣泛合作、互利共贏,又保持對民族國家核心利益的真實關(guān)切,在“經(jīng)濟責(zé)任”“政治責(zé)任”與“社會責(zé)任”之間尋求動態(tài)平衡,并以此來引領(lǐng)國際社會的合作發(fā)展。在正確義利觀導(dǎo)向下,既不是見利忘義,也不是單純地強調(diào)以義制利,而是倡導(dǎo)企業(yè)要見利思義、義利兼顧,更是強調(diào)在不損害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前提下,要弘義融利、義以生利。在“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實踐中,中國企業(yè)在“走出去”和“引進來”的過程中不斷合理化企業(yè)的價值訴求,按照正確義利觀的指引,搭建“共享、共商、共建”的價值分配結(jié)構(gòu),能夠改善東道國社會對企業(yè)的認(rèn)知和評價,提高了社會對企業(yè)的形象、聲譽、影響力的認(rèn)知水平,從而利于其國際化行動,也減少了供應(yīng)商的機會主義行為。
總之,傳統(tǒng)產(chǎn)能合作治理中重利輕義的狹隘功利論,以自我利益為本的利己主義,割裂企業(yè)、國家、社會的思維,無法正確認(rèn)識當(dāng)今世界格局中的義利關(guān)系,也無法為建構(gòu)健康有序的當(dāng)代國際產(chǎn)能合作治理做出進一步的貢獻。正確義利觀提倡政府、企業(yè)與社會尊重與優(yōu)化各自運作規(guī)律,通過平等互動釋放各自積極價值創(chuàng)造潛能,既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豐富和踐行,也是推動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追求,對矯正傳統(tǒng)國際產(chǎn)能合作治理中由市場自發(fā)治理、政府主導(dǎo)性治理和社會監(jiān)督調(diào)節(jié)性治理的碎片化所帶來的問題和缺陷具有重要意義。
三、正確義利觀理念引導(dǎo)下的“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治理
以正確義利觀理念指引“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治理,不僅決定了“一帶一路”建設(shè)的合法性,而且還決定了它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成為中國跨國企業(yè)健康發(fā)展的關(guān)鍵支撐。把正確義利觀這一理念落實到“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實踐中,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既需要全面把握正確義利觀在產(chǎn)能合作下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又需要探索符合正確義利觀理念的“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治理結(jié)構(gòu)與運行機制,讓更多的國家認(rèn)同中國的和平發(fā)展道路,提高中國的“軟實力”。①李向陽:“‘一帶一路’建設(shè)中的義利觀”,《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17年第9期,第12頁。在“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治理中,企業(yè)實踐正確義利觀的模式可分為主動實踐和被動(或強制)實踐;在考慮政府發(fā)揮引導(dǎo)、監(jiān)管、協(xié)調(diào)作用的基礎(chǔ)上,本文提出在“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治理中三種互補的治理形式:便利型、監(jiān)管型和分配型治理。
3.1 便利型治理
在“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中,企業(yè)是主要參與者,因此基于市場原則(平等交換)的經(jīng)濟合作仍是國際產(chǎn)能合作的主要原則。在產(chǎn)能合作中,帶動力強的中國企業(yè)經(jīng)過技術(shù)改造升級,在“一帶一路”沿線進行產(chǎn)業(yè)布局、轉(zhuǎn)移先進產(chǎn)能,積極尋找與沿線國家產(chǎn)業(yè)合作切合點,通過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形成自生能力,幫助沿線經(jīng)濟體實現(xiàn)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中國跨國企業(yè)在沿線市場經(jīng)營管理活動中,企業(yè)以自愿的方式參與合作,尋求利用商業(yè)資源來補充服務(wù)自身業(yè)務(wù)的發(fā)展。據(jù)《中央企業(yè)海外社會責(zé)任藍(lán)皮書(2019)》顯示,65%的中央企業(yè)把培訓(xùn)作為促進當(dāng)?shù)禺a(chǎn)業(yè)發(fā)展的助推劑,82%的央企投身當(dāng)?shù)厣鐓^(qū)的文化建設(shè),與當(dāng)?shù)厣鐓^(qū)進行共建的意識進一步增強。企業(yè)不僅多維度構(gòu)建企業(yè)海外品牌形象,獲得了提升自身生產(chǎn)力并擴大市場的機會,而且為東道國企業(yè)和當(dāng)?shù)厣鐣?chuàng)造共享價值,樹立優(yōu)秀國家形象和企業(yè)形象,提高了自身的合法性。
在企業(yè)能夠主動實踐正確義利觀的情形下,政府對“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可采用便利型治理,在國家層面則可對企業(yè)提供一些便利條件和激勵措施,促進企業(yè)、國家與社會形成良性互動,通過便利性治理所帶來的包容性、凝聚力和多樣性,進一步提升企業(yè)獲得競爭優(yōu)勢,良好社會評價、品牌價值和凝聚力的能力,以實現(xiàn)企業(yè)、社會和國家多贏的局面。近年來,不斷擴展的產(chǎn)能合作治理使國際社會的關(guān)注度已經(jīng)從單個生產(chǎn)商延伸到整個供應(yīng)鏈、產(chǎn)業(yè)鏈,一些議題也擴展到廣泛的社會領(lǐng)域,讓參與沿線產(chǎn)能合作的中國企業(yè)很難跟上節(jié)奏。由于部分中國企業(yè)在進入沿線市場時,對于當(dāng)?shù)匚幕⒗嫒后w以及社區(qū)訴求缺乏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產(chǎn)能合作治理的績效。便利性治理的目標(biāo)不是參與或推動更廣泛的產(chǎn)能合作治理議程,也不是強迫企業(yè)承擔(dān)更多社會責(zé)任,而是通過經(jīng)濟激勵幫助企業(yè)解決面臨的具體和緊迫的社會問題。
對于可能缺乏必要的資源、專業(yè)知識和社會合法性或權(quán)力的企業(yè),單靠企業(yè)可能沒有能力解決“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中的系統(tǒng)性問題或發(fā)展需要,因此需要政府的幫助或介入。國家利用補助政策這一互惠措施適當(dāng)干預(yù)企業(yè)履行正確義利觀的行為,能夠提升企業(yè)履行正確義利觀的水平。國家利用積極的激勵手段,針對“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中的國有企業(yè)、具有較大影響力的主導(dǎo)企業(yè),通過金融手段(開發(fā)性金融)、財政手段(稅收優(yōu)惠、轉(zhuǎn)移支付)引導(dǎo)企業(yè)的投資方向并承擔(dān)一部分政府職能(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甚至通過行政手段(組織項目、會談交流)影響企業(yè)的預(yù)期和行為。通過構(gòu)建相對穩(wěn)定的制度安排,引導(dǎo)企業(yè)在參與“一帶一路”過程中把企業(yè)的目標(biāo)與國家的目標(biāo)有機結(jié)合起來,通過外交手段(政府間的合作協(xié)定)規(guī)范企業(yè)的跨國行為。
激勵措施不僅關(guān)注企業(yè)履行在產(chǎn)能合作中的義務(wù),而且也重視企業(yè)自身利益。國家可根據(jù)企業(yè)披露履行正確義利觀的政策、行動方案、正確義利觀實踐成果以及企業(yè)面臨的政治風(fēng)險,作為是否給予企業(yè)政府補貼以及補貼力度的重要依據(jù)。對承擔(dān)戰(zhàn)略任務(wù)和促進公共利益項目的企業(yè),政府需要引導(dǎo)企業(yè)服務(wù)于國家戰(zhàn)略目標(biāo)和提升公共福祉。對產(chǎn)生良好社會效果,但承擔(dān)高水平正確義利觀標(biāo)準(zhǔn)的企業(yè),政府可以出臺相關(guān)政策降低企業(yè)的經(jīng)營成本,給予一定的財政、稅收、優(yōu)惠政策等扶持。便利性治理的政策重點還要為激勵企業(yè)進一步實踐正確義利觀創(chuàng)造有利環(huán)境,在市場環(huán)境下協(xié)調(diào)促進正確義利觀實踐,例如,國家可以利用主導(dǎo)企業(yè)的權(quán)力來規(guī)范供應(yīng)商的行為,①Sandra Polaski,“Combining Global and Local Forces:The Case of Labor Rights in Cambodia,”World Development,Vol.34,No.5,2006,pp.919-932.建立信息門戶、提供技術(shù)援助和組織專業(yè)網(wǎng)絡(luò),提供針對中小企業(yè)的信息和培訓(xùn)方案,幫助資源有限的中小企業(yè)管理供應(yīng)鏈中的社會和環(huán)境挑戰(zhàn);建立獨立的論壇,將政府、企業(yè)和社會聚集在一起解決涉及產(chǎn)能合作治理的問題,滿足市場的需求和期望等。
3.2 監(jiān)管型治理
在“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中實踐正確義利觀,對部分還處于起步階段的“走出去”中國企業(y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問題。參與產(chǎn)能合作的中國企業(yè)面臨經(jīng)濟制度的變化,導(dǎo)致企業(yè)實踐正確義利觀成本加大;加上部分企業(yè)缺乏正確義利觀意識等因素,導(dǎo)致其在實踐正確義利觀上仍缺乏積極性和可行性。特別是一些企業(yè)基于市場邏輯導(dǎo)向,在產(chǎn)能合作中沒有踐行包容性和可持續(xù)的發(fā)展模式,為節(jié)約成本采取的排污不達標(biāo)、勞動合同履約不健全等失責(zé)行為,給其他利益相關(guān)者造成傷害。在“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中,企業(yè)會面臨當(dāng)?shù)厣鐣M織或國際組織施加給企業(yè)履行企業(yè)社會責(zé)任的壓力,但對于可能缺乏必要的資源、專業(yè)知識和社會合法性或權(quán)力的企業(yè),單靠企業(yè)可能沒有能力解決“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中的系統(tǒng)性問題或發(fā)展需要,因此需要政府的幫助或介入;另一方面,單獨的企業(yè)自律或私人治理可能不足以確保企業(yè)履責(zé)的改善,這需要政府采取行動來促進和塑造企業(yè)行為,采取產(chǎn)能合作的監(jiān)管型治理模式。
在產(chǎn)能合作的監(jiān)管型治理模式中,國家可以在較多的領(lǐng)域?qū)ζ髽I(yè)進行指導(dǎo)或監(jiān)管,幫助企業(yè)克服產(chǎn)能合作中的社會和環(huán)境挑戰(zhàn),引導(dǎo)企業(yè)踐行正確義利觀,滿足政府、行業(yè)和非政府組織的需求和期望。首先,建立中國企業(yè)在沿線國家實踐正確義利觀的監(jiān)控體系,構(gòu)筑和完善保障安全生產(chǎn)、消費者權(quán)益、環(huán)境保護等方面的監(jiān)督框架體系,把實踐正確義利觀問題納入法制化、規(guī)范化的管理體系之中。其次,對企業(yè)實踐正確義利觀的效果進行監(jiān)督和評估,將中央企業(yè)實踐正確義利觀績效納入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形成實踐正確義利觀的制度環(huán)境。再次,提高中央企業(yè)在沿線國家投資的“基準(zhǔn)”和“門檻”,通過國內(nèi)母公司對沿線子公司施加影響,提高中國企業(yè)在沿線國家實踐正確義利觀的意識,將當(dāng)前的實踐正確義利觀活動轉(zhuǎn)化為未來市場機遇、創(chuàng)新和競爭優(yōu)勢。
國家還可以參與各種規(guī)則制定以影響和引導(dǎo)產(chǎn)能合作治理的觀點和實踐,國家參與是一種“行為的行為”,其作用不在于決定產(chǎn)能合作中的企業(yè)應(yīng)該如何行動,而在于構(gòu)建企業(yè)可能的行動領(lǐng)域,以塑造企業(yè)的經(jīng)濟和社會行為。相關(guān)政府部門為企業(yè)制定或提供參與正確義利觀實踐的指南或指導(dǎo)方針,加強對企業(yè)正確義利觀的培訓(xùn),使企業(yè)更便利地了解自己應(yīng)遵守的規(guī)則、條例和國際慣例。例如,2014年9月,中國新修訂的《境外投資管理辦法》中,敦促境外企業(yè)重視在東道國的環(huán)境保護,樹立環(huán)境保護意識,履行環(huán)境保護責(zé)任,這反映了中國監(jiān)管部門希望引導(dǎo)企業(yè)積極主動實踐正確義利觀的價值取向。此外,還可依托行業(yè)協(xié)會、媒體和其他社會組織,加強對企業(yè)家正確義利觀思想的培訓(xùn)和學(xué)習(xí),相關(guān)政府部門可以牽頭組建專家學(xué)者組成的團隊為企業(yè)提供專業(yè)咨詢,開展沿線實踐正確義利觀專項培訓(xùn)和調(diào)研活動,診斷沿線實踐正確義利觀履責(zé)問題并提供建議。
加強宣傳,使積極實踐正確義利觀成為沿線企業(yè)產(chǎn)能合作的內(nèi)生價值取向。鼓勵沿線產(chǎn)能合作企業(yè)制定實踐正確義利觀的計劃,對秉持正確義利觀理念的企業(yè)和企業(yè)家加強宣傳和獎勵,通過示范效應(yīng)使更多的企業(yè)意識到積極實踐正確義利觀的必要性。通過政府間的合作,提高中國企業(yè)與沿線國家企業(yè)的合作傾向和能力,提高中國企業(yè)的本地化經(jīng)營水平。鼓勵企業(yè)積極與媒體進行交往,以樹立更好的實踐正確義利觀的形象。由政府指導(dǎo)的方式建立統(tǒng)一的實踐正確義利觀認(rèn)證和信息披露平臺,真實、動態(tài)、及時地披露企業(yè)實踐正確義利觀的典型事件和失責(zé)行為,加大對企業(yè)見利忘義行為的監(jiān)管力度和處罰的力度,實現(xiàn)企業(yè)實踐正確義利觀的方式由借助道德壓力約束逐漸轉(zhuǎn)化為基于理性的自覺行為,在規(guī)則制度的約束下獲取自身經(jīng)濟利益。
3.3 分配型治理
隨著中國海外利益的拓展以及“一帶一路”建設(shè)步伐加快,國際上出現(xiàn)了一些批評中國跨國企業(yè)只注重追求經(jīng)濟利益、忽視社會責(zé)任的聲音。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批評與中國部分企業(yè)海外經(jīng)營經(jīng)驗不足、管理體制相對落后有關(guān),①馬骦:“企業(yè)社會責(zé)任與跨國公司政治風(fēng)險管控”,《外交評論》,2019年第4期,第88頁。也與某些西方國家對于中國的迅速發(fā)展及其世界影響力的擴大懷有敵意有關(guān)。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主要依靠品牌、服務(wù)和技術(shù)創(chuàng)新在全球運作不同,目前“一帶一路”走出去企業(yè)有一部分是從事生產(chǎn)制造、粗加工和資源開發(fā)業(yè)務(wù)的企業(yè)。特別是在一些國家和地區(qū),中國企業(yè)對不同產(chǎn)業(yè)部門的投資存在嚴(yán)重失衡問題,較多的中國企業(yè)投資聚集于當(dāng)?shù)氐牡V產(chǎn)資源挖掘與開采,招致了其他國家及當(dāng)?shù)孛癖姷馁|(zhì)疑,有時甚至被誤解為“新殖民主義”、“自然資源掠奪者”等。加上勞工待遇與權(quán)利、環(huán)境保護等問題是當(dāng)前全球社會責(zé)任運動最關(guān)注的主題,一些中國企業(yè)在高風(fēng)險、高污染、高事故頻發(fā)行業(yè),容易成為媒體關(guān)注的焦點;特別是在某些競爭對手的惡意宣傳與抹黑下,將企業(yè)的社會責(zé)任泛政治化并與國家意識相聯(lián)系,影響了正確義利觀實踐的社會效應(yīng)。
一些沿線國家由于長期受到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影響以及國際組織的長期援助和政治影響,往往(被動)選擇某些較高標(biāo)準(zhǔn)的產(chǎn)能合作規(guī)范和指南作為其落實企業(yè)社會責(zé)任的依據(jù),而這些標(biāo)準(zhǔn)并沒有考慮到當(dāng)?shù)氐膶嶋H發(fā)展條件、背景和現(xiàn)實需求,加上宗教、傳統(tǒng)等要素直接影響了各國對產(chǎn)能合作治理的理解與認(rèn)知,沿線國家對于產(chǎn)能合作治理的方式及最終目標(biāo)往往與我國企業(yè)存在一定的差異,給中國企業(yè)在沿線國家實踐正確義利觀增加了額外的困難與障礙。部分發(fā)達國家及非政府組織制定所謂的高標(biāo)準(zhǔn)產(chǎn)能合作治理,在市場邏輯主導(dǎo)下演變?yōu)楸Wo自己競爭優(yōu)勢的工具,內(nèi)嵌了一系列身份歧視、偏見等(如對國有企業(yè)),其目的就是為了削弱競爭對手的市場競爭力。②仰海銳、皮建才:“企業(yè)社會責(zé)任標(biāo)準(zhǔn)差異下我國企業(yè)‘走出去’策略分析”,《西安交通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0年第1期,第75頁。在東道國承擔(dān)某些社會職能的能力較弱的情況下,跨國企業(yè)有時會被認(rèn)為是類似于國家或“準(zhǔn)政府”行為者,③Andreas Scherer and Guido Palazzo,“Toward a Political Concep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Business and Society Seen from a Habermasian Perspectiv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32,No.4,2007,pp.96-120.導(dǎo)致東道國賦予企業(yè)過度的社會元素,盲目追求企業(yè)的社會價值,一般的企業(yè)社會責(zé)任實踐往往給社會公眾帶來了極大的心理落差,并加劇了公眾對企業(yè)社會責(zé)任的質(zhì)疑,導(dǎo)致企業(yè)社會壓力不斷加大。
正確義利觀實踐基于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理念,這其中也包括了企業(yè)自身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盡管社會對企業(yè)的期望是多層次的、變動的、不斷擴展的,在產(chǎn)能合作中實踐正確義利觀的分配型治理中,實踐正確義利觀不是強迫企業(yè)承擔(dān)過度的“企業(yè)辦社會”職能或企業(yè)為“政府買單”,而是通過適當(dāng)調(diào)整政府、企業(yè)、社會分工,解決企業(yè)行為脫嵌于政府、社會監(jiān)管之外,糾正企業(yè)的原子化傾向,在追求企業(yè)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共同增加的同時,最終形成企業(yè)、政府與社會螺旋上升式的共同演化。如果企業(yè)不顧自身經(jīng)濟利益和生存發(fā)展,企業(yè)“過度”承擔(dān)社會責(zé)任,這將會影響企業(yè)的市場競爭力,最終會被太多的責(zé)任拖累,被市場競爭淘汰①靳小翠、鄭寶紅:“國有企業(yè)董事長的自戀性與企業(yè)社會責(zé)任研究”,《管理評論》,2020年第10期,第229頁。。中國政府和企業(yè)需要因地制宜,在緊密結(jié)合沿線國家社會需求、經(jīng)濟特點及發(fā)展階段的國別特征基礎(chǔ)上,參考國際慣例、指南與規(guī)范,指導(dǎo)企業(yè)根據(jù)自己的發(fā)展能力分別踐行不同義務(wù)水平的正確義利觀。對于一些盈利能力弱,但已合規(guī)經(jīng)營的企業(yè),在面對部分國家、國際組織制定的過分苛刻或明顯不合理的企業(yè)社會責(zé)任標(biāo)準(zhǔn),則不能一味地迎合,企業(yè)需要按照自身的能力,履行力所能及的責(zé)任,保障企業(yè)的合法利益。
總之,在產(chǎn)能合作治理中,便利性、監(jiān)管性和分配性治理的背景大不相同。國家政策對培育企業(yè)正確義利觀產(chǎn)生重大影響,分配性政策涉及分配結(jié)果,其重點限制和減輕市場、社會不平影響,便利性和監(jiān)管性治理主要通過制定和實施國家政策來實現(xiàn)的。在國家有能力通過監(jiān)管約束企業(yè),并通過便利措施提供政策優(yōu)惠的情況下,這類政策能夠發(fā)揮積極的作用。在“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治理中,通過這些政策促進或限制企業(yè)的活動,達到履行正確義利觀的目的。
四、結(jié) 語
“一帶一路”建設(shè)聚焦發(fā)展問題,通過開展產(chǎn)能合作讓沿線各國分享中國的發(fā)展機遇。②王飛:“‘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拉產(chǎn)能合作:理論基礎(chǔ)與潛力分析”,《太平洋學(xué)報》,2020年第2期,第66頁。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政治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異,以及大國戰(zhàn)略博弈、地緣政治競爭和意識形態(tài)等因素影響,一些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存在認(rèn)知赤字、誤讀誤判,阻礙了一些“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項目的推進。當(dāng)前“一帶一路”下的國際產(chǎn)能合作較多依靠政府間合作機制來推動,尤其是基于國家間良好的政治及經(jīng)貿(mào)關(guān)系為前提。正確義利觀實踐意味著政府、企業(yè)、社會組織和公眾等主體針對產(chǎn)能合作過程中出現(xiàn)的公共問題進行互動協(xié)商,其實踐效果有賴于政府、企業(yè)和社會的合力與協(xié)同。“一帶一路”高質(zhì)量發(fā)展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國家與企業(yè)的獨特融合,③白云真:“‘一帶一路’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政治經(jīng)濟邏輯”,《太平洋學(xué)報》,2020年第3期,第12頁。隨著中方企業(yè)的大規(guī)模走出去,這些企業(yè)文化或“軟實力”層面上的考量越來越具有經(jīng)營管理或“硬實力”層面上的重要性。以正確義利觀為原則開展“一帶一路”產(chǎn)能合作及其治理,強調(diào)義利統(tǒng)一、義利并重和先義后利、以義制利等特點,既順應(yīng)時代發(fā)展潮流,規(guī)范企業(yè)在產(chǎn)能合作中的行為和價值取向,也為建構(gòu)新型國際產(chǎn)能合作提供了價值基礎(chǔ)和倫理指南。
正確義利觀作為一項獨具中國特色、中國智慧的新倡議,在國際社會的擴散必然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在科學(xué)認(rèn)識和把握義利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實踐正確義利觀,能夠在道義上為世界樹立標(biāo)準(zhǔn)和典范,為國家聚攏軟實力,對中國在新時期推進高質(zhì)量“一帶一路”建設(shè)具有重要意義。讓正確義利觀成為世界共識,成為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抓手和價值追求,這要求中國企業(yè)、政府在參與產(chǎn)能合作及其治理過程中必須切實做到義利兼顧、實現(xiàn)義利統(tǒng)一;“走出去”企業(yè)要身體力行,減少失責(zé)事件的發(fā)生,充分發(fā)揮示范作用。要在“一帶一路”建設(shè)中圍繞正確義利觀凝聚價值共識,既要把正確義利觀的精神要義融于各大工程、大項目的產(chǎn)能合作執(zhí)行過程中,讓沿線各國人民能夠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也要將其融入貫徹到“民心相通”工作中,增進沿線各國人民對正確義利觀的認(rèn)同與共識,從而為“一帶一路”建設(shè)夯實民意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