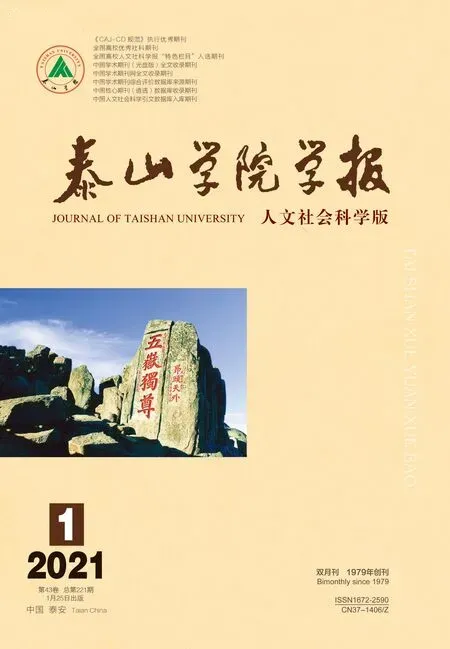僧安道壹入隋后書刊風格分析
——以《曹植廟碑》為起點
張 強
(四川美術學院 世界實驗書法高等研究中心,重慶 401331)
引言
以《曹植廟碑》為起點,揭示僧安道壹偶然之作背后所關聯的邏輯系統,從最基本的“筆性”與特定文字“結體”特征入手,感知其書刊美學趣味與魅力,有助于驅散歷史迷霧,解決其書刊風格困惑問題。
一、曹植廟碑的基本情況
據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的《山東省志》載:
“曹植墓位于東阿魚山西麓。座東朝西,依山營穴,磚土壘就。1951年夏,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清理。后墓殘破,1981、1985先后整葺修復。
墓室為前堂后室磚室墓,前堂4.35米見方,后室長2.20米,寬1.78米。墓室以青磚錯縫平砌。前堂后室之間辟門,以磚封護。清理出石圭、石璧、青玉璜、瑪瑙泡和云母片以及罐、盆、杯、盤、灶、案、車、禽畜俑等各式陶器132件。
……
墓前左側有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重修碑樓一座,單層硬山式建筑,內置開皇十三年(593年)立曹植墓碑。碑圓首方趺,趺坐半入土中,高度不詳。碑冠與碑身為整石雕出。通首高2.47米,寬1.03米,厚0.21米,碑首雕而不起礱,起龕有三身像。碑身高1.80米,鐫文22行,行42-44字不等,共935字。書雜篆隸楷三體,結體險峻,氣韻高邁,筆力雄奇。此碑早年湮沒在大清河中,清代撈出,還置墓前。此外尚有題詠、記事碑碣4方。[1]
值得重視的是,在《曹植廟碑》之中出現了以“凊”代“清”的情況。從碑文內部的上下文來看,“清雅自得”顯然是與“濁”“俗”以及“隨波逐流”相反的意思。《曹植廟碑》使用了篆書的“清”,可見其深沉的用心。筆者在《“清”何以變“凊”——僧安道壹后期書刊研究系列之一》(1)參見《書法研究》2020年第1期。一文中,通過對僧安道壹在其書刊的遺跡之中,幾乎將所有的“清”改寫為“凊”的論證,認為這種改寫不是平時所謂的“俗字”書寫(可以增刪筆畫而不改變其涵義),據此可以猜測《曹植廟碑》乃僧安道壹的丹書。山東汶上中都博物館所藏的開皇九年(589)《章仇氏造像殘碑》,山東東平白佛山的《王子華題記》(587)、《曇獻題字》(590)與《曹植廟碑》具有共同的古意書體美學特征,因此可以納入僧安道壹的書法體系之中來加以考察,在“隋朝的書法史語境”之中,進行重新、全面認知。
以往人們只是孤立地從文人趣味上來貶斥《曹植碑》,認定一個時代的風格,總是從集體無意識的角度來加以粗暴地對待。[2]但如果從僧安道壹的角度來看,顛覆文人趣味一直是他書法觀之中一個重要的意趣與旨意。作為曾經的“大沙門”或者佛門耆老的僧安道壹,為一個不得志的、前朝于數代的皇親文人書刊碑文,且受托者的家族已經敗落,或許連支出購買書刊碑素石的費用都難以支付。碑刻使用的也不是一塊素石,而是一塊佛教造像碑的再利用。顯然,從書刊碑文獲得報酬并不是僧安為之書刊的目的。其意或在藉此將“古體趣味與書刊”美學全面地釋放出來,或者進行預言式的書刊,這些都有待于進一步證實。
二、新近認定的僧安道壹遺跡地理分布
以《曹植廟碑》和《白佛山石窟題記》相繼以“凊”代“清”為標志,被我們確定為僧安道壹所書刊之后,還有相關聯的《章仇氏造像殘碑》,三者在時間與地理上的關系如下。
《白佛山石窟題記》(山東東平白佛山)開皇七年至開皇十年(587—590)
《章仇氏造像殘碑》(山東汶上中都博物館)開皇九年(589)
《曹植廟碑》(山東東阿魚山)開皇十三年(593)
據此,我們可以做出推測:北周大象二年(580),僧安道壹在葛山書刊“維摩詰經”之后,回到了長久掛單之處(或者同時是他的家鄉),即今山東省東平縣舊縣鄉洪頂山寺院,或者是在其附近的平陰洪范鎮,二者相距15公里。同時,洪范鎮附近分布著三處“大空王佛”,其中就包括目前發現最早署有河凊元年的“大空王佛”。
在這里還分布著被隋代皇帝勅頒“舍利塔”的崇梵寺。雖然勅頒行為發生在僧安身后的“仁壽”年間(601—604),但卻可以看出其早已具備顯赫的地位。“山東省平陰縣洪范池,位于平陰縣城西南約32.5公里的洪范公社管委會院內,北距原東阿縣老城約7.5公里。在洪范池以南 80米是一高出地表約3米的臺地,其斷崖上東西 80余米范圍內,暴露出大量隋唐時期的蓮花瓦當、筒瓦、板瓦、獸飾等建筑構件。在其以東約 500米,有天池山隋代摩崖造像。此處當是一處隋唐時期的寺院遺址。1982年11月,公社在修建社際間公路正好沿臺地北邊緣穿過,社員在取土平整道路時,在離臺地表面1.6米深處發現一個石函……蓋頂分兩行鐫刻‘大隋皇帝舍利寶塔’八個字。”[3]
在這里,經過北周到隋改朝換代的動亂之后,過了7年(這個期間的僧安道壹在做什么,由于沒有書刊遺跡支持,我們無法貿然揣測),他受邀為距離洪頂山27公里外的危山(白佛山)書刊造像記,2年后,又應邀赴約53.9公里汶上三官廟村,書刊《章仇氏造像碑》。一年后,僧安道壹再為落成的危山(白佛山)石窟寺院書刊“寺主王子華”題記,同時,書刊里面299人的象主題名榜。
首先討論被筆者認定為僧安道壹遺跡的地點與洪頂山的距離。洪頂山作為僧安道壹的精神與書刊家園,分布了其19處書刊遺跡。尤其重要的是,這里有9.6米的“大空王佛”與“僧安道壹”小傳以及“安公之碑”。從這里隔湖向北瞭望,隱約可見模糊的小山影便是山東聊城市東阿縣魚山的曹植墓。
從東平舊縣鄉洪頂山僧安道壹刻經遺跡處到曹植墓約17.7公里,洪頂山到白佛山約27.6公里,從洪頂山到汶上三官廟村約53.9公里。從地理分布來看,以古代最基本的交通方式步行,出行都在24小時范圍之內。由此可推知,僧安就是本地人氏。他很有可能出道于青州,然后回到家鄉洪頂山附近,創作出驚世駭俗的“大空王佛”以及19處佛名與佛經篇章,從此名揚北齊境內,之后被皇家工程所邀,西行涉縣、鄴城,后來南抵滕州、鄒城。隋代立國之后,回歸洪頂山居住,應周圍慕名者的邀請,時常外出書刊。晚年的僧安已經不可能跨越更遠的路途,入隋之后,其書刊也就限定于方圓50公里左右了。
三、歷史上對于《曹植廟碑》與僧安道壹的關系論述
最早記載與評價《曹植廟碑》的是明代的王士禎(1634—1711),他對于這塊碑整體書風的描述便是因為集合了不同字體:“東阿魚山陳思王墓道有隋碑,書法雜用篆、隸、八分,甚古。此碑文不極工,考歐《集古錄》,趙《金石錄》及近代《金薤琳瑯》《石墨鐫華》《金石志》俱不及載。”[4]
楊守敬(1839-1915)認為《曹植廟碑》這種跨越字體的方式,雖然采納的是北魏的傳統,但是,本身卻也是在篆隸意味的筆法上,有著精妙的發揮:“王阮亭居易錄始著此碑,用筆本之齊人,體兼篆隸,則沿北魏舊習。然其筆法實精,真有篆隸遺意,不第如《李仲璇》等之貌似也。褚河南《倪寬傳》胎息于此。”[5]
最明確地將《曹植碑》與僧安道壹書刊遺跡聯系在一起的是康有為(1858-1927),他在其碑學著作《廣藝舟雙楫》之中如此評論:“今按此經完好,在薤山映佛巖,經主為梁父縣令王子椿,武平元年造,是齊碑也。是碑雖簡穆,然較《龍顏》《暉福》尚遜一籌,今所見岡山、尖山、鐵山摩崖,皆此類。實開隋碑洞達爽闓之體,故《曹子建碑》亦有《般若經》筆意。[6]
不過,在洪頂山僧安道壹的作品發現之前,沒有人能夠想象到存在著僧安道壹的一個龐大的書法系統,況且,時代的隔離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心理障礙——當一個歷史人物被劃定在某個朝代之后,人們已經很難再超越審視。所以,康有為才會認為存在著這樣截然不同的“齊碑”與“隋碑”概念。
孫葆田(1840-1911)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曹植廟碑》相關聯的其他書刊作品。他認定汶上的《章仇氏造像碑》與東平白佛山《王子華題記》,出自一人之手,其標志是“雜用篆隸,博異趣耳”,這里雖然是一種“異端”的觀念,但畢竟從另一個角度把僧安道壹的書法系統關聯起來了:“碑字與章仇禹碑,白佛山王子華題名,當出一手,其雜用篆隸,博異趣耳。若別體字以意會之,皆可識也。”[7]
李佐賢(1807-1876)則認定東平白佛山的“曇獻題名”是《曹植廟碑》的作者所為,“《曇獻題名》作篆隸真三體書,與東阿之開皇十三年曹子建碑相類,余則罕有此式,或即一人所書歟”。[8]
其實,按照我們從題記上所隱藏的以“凊”代“清”的現象而言,白佛山造像題記及供養人題記,皆是僧安道壹所為。按照白佛山《王子華題記》,所署年款為大隋開皇7年,公元587年,而白佛山石窟外壁的左面摩崖上《曇獻題記》為開皇十年,公元590年。“根據石壁上供養人的題記,象主姚清娘的‘清’字,被書刊為‘凊’字。作為人名的謬誤,很容易被認真而虔誠的出資者發現。因此,僧安道壹被要求補上一‘點’,所以有了現在的‘清’字中間一點,脫離了文字。而在另外兩個名字嚴清與呂清女的書刊上,僧安道壹則沒有任何理由書刊減筆之‘凊’了。這個修補性的改正,恰恰證明了他在書刊之中試圖改寫‘清’的動意。”[9]
至于《章仇氏造像碑》又稱《章仇禹生等造經像碑》。隋開皇九年(589)十二月七日立石于今汶上縣劉樓鄉辛海村三官廟。孫葆田在記載《章仇氏造像碑》的時候,又一次談到它與《曹植廟碑》之間的關系:“書體略兼篆隸,雅與曹子建碑為近。”[10]
香港《書譜》雜志社出版的《中國書法大辭典》對于《章仇氏造像碑》有比較高的評價,也認為與同時期汶上的《文殊般若碑》有密切關系,甚至認為與《曹植廟碑》是一人之作:“此碑為歷代金石家所重視,清王昶《金石萃編》、錢大昕《潛研堂金石》和楊守敬《環宇貞石圖》等均有著錄和評價,是中國書法史和佛教藝術史上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刻石。明代碑斷為兩截,上半又失一角。所存下截又斷為二。碑文為佛經,字體正書,兼作篆、隸。十七行,行四十八字。石邊有題名一行。今存碑文約七百字。書法用筆渾圓,行筆暢中有澀,飄中有沉,筆畫粗細勻停,提按頓挫痕跡不顯,轉折處多用篆法,筋骨內含,結構疏朗自然,風格安祥、靜穆、簡約,開宕峻爽,尖利瘦硬,體勢寬博,為北齊《文殊般若》碑遺風之漸變者,與《曹植碑》如出一人之手,禇遂良、顏真卿書風隱然欲出。其在書法史上承前啟后,貢獻顯赫,功不可沒。”[11]從與《文殊般若碑》的關系,以及與《曹植廟碑》如出一人之手的判斷,可以看出僧安這個譜系內在邏輯的一致性。
四、悖論的書法史邏輯:關于《曹植碑廟》與“隋代書法”概念
按照時代風格來劃分,是一種歸納法,這種風格的歸納,可以用在那些集體意志書寫的作品上,對于跨越時代的書法家僧安道壹及作品而言,這種生硬的劃分,便自然遭遇了尷尬。
如果從時代特征的角度,把《曹植廟碑》放置到隋代書法的語境之中來加以探討,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悖論,如康有為而言:“隋碑內承周、齊峻整之緒,外收梁、陳綿麗之風,故簡要清通,匯成一局,淳樸未除,精能不露……隋碑風神俊朗,體格峻整,大開唐風。唐世歐、虞及王行滿、李懷琳諸家,皆是隋人。……快刀斫陣、雄快俊勁者,莫若《曹子建碑》矣”。[12]在康有為眼中,“隋碑”已經是一個獨立的概念,唐初的書法大家本身就是“隋人”,所以,隋碑開啟唐代的書風也就自然成為可能。同時,隋碑來源于北朝周齊,又接受南朝梁、陳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曹植廟碑》自然具有“快刀斫陣、雄快俊勁”的獨特之處。康有為將《曹子建碑》列為“能品上”。[13]
《曹植廟碑》的古體趣味與書刊美學,被康有為解讀為一種瘦硬與尖利,認為其具有“承魏開唐,獨標俊異”:“《曹子建碑》如大刀闊斧,斫陣無前。”[14]“曰齊碑之《雋修羅》《朱君山》,隋碑之《龍藏寺》《曹子建》,四者皆有古質奇趣,新體異態,乘時獨出,變化生新,承魏開唐,獨標俊異。四碑真可出魏碑之外,見標千古者也”。[15]
從這個層面上來看,康有為進入了一個解讀的誤區,這是因為僧安道壹的《曹植廟碑》,其書刊美學早在北齊河清年間已經完備,而絕非到隋代才出現的。
在這里,康有為提示了這樣幾個關鍵的詞語與范疇:“古”“奇”“新”“異”,所謂的“古”,就是一種時間的距離感,以及由時間所帶來的“心理包漿”。針對書法史的潮流而言,它同時具有耳目一新的奇異感。
沙孟海對于隋代的書法,歸納出四種類型:“隋代真書,主要有四種面貌:第一,平正和美一路。從二王出來,以智永、丁道護為代表,下開虞世南、殷令名。第二,峻嚴方飭一路。從北魏出來,以《董美人》《蘇慈》為代表,下開歐陽詢父子。第三,渾厚圓勁一路。從北齊《泰山金剛經》《文殊經碑》《雋敬碑陰》出來,以《曹植廟碑》《章仇禹生造像》為代表,下開顏真卿。第四,秀朗細挺一路。結法也從北齊出來,由于運筆細挺,另成一種境界,以《龍藏寺》為代表,下開遂良、二薛。
以上四種,第一、二種屬于“斜畫緊結”的類型,第三、四種屬于“平畫寬結”的類型,承前啟后,跡象顯明。在第三種“渾厚圓勁”里面囊括了僧安道壹在北齊時書刊的《泰山金剛經》《文殊經碑》并認為是《曹植廟碑》《章仇禹生造像》的來源。這里,沙孟海敏感意識到了所謂“隋代風格”與北齊間的混合關系。[16]
五、穩定的筆性:以二十八年的時間長度做比較
一位書法家接近30年之間的書體風格,呈現出大幅度的變化,是極其可能的。有時候甚至出現對于早期的否定。但是,這只是其中一種類型的藝術家,可以稱之為“晚成型”藝術家。而對于另外的藝術家而言,其藝術似乎一開始便是成熟的,具有突出的風格特征,后來的歲月只是豐富其風格表達。而僧安道壹似乎是“兼二者之長”。一方面具有內在穩定的書法“筆性”特征,帶有漸進“加強”的意味;另一方面卻又極盡變化之能事。我們從《沙丘尼寺題贊》(564)與《曹植廟碑》(593)相同字型的比較中,可以看出二者在其書體與筆法美學上的一致性。
筆者在《“清”何以變“凊”——北朝僧安道壹后續研究系列之一》中將這塊碑確定為是僧安道壹所為:“但是,在同年內《沙丘尼寺題贊碑》之中,僧安道壹則似乎徹底放松了,不僅是在年號上用了‘凊’字,而且在內文之中所提到的‘三空明澈,六度凝凊’這樣的句式之中,也把‘清澈’‘清明’‘清白’這樣明確的語義表達,轉換為‘冬暖夏涼’,包含了人倫孝道的涵義。”[17]其實,盡管此刻石之中有與洪頂山完全一致的“大齊河清三年歲月實沉”落款,人們幾乎可以據此斷定是僧安道壹所為,但是,只有河“凊”的改寫,才真正把時間落到實處。
《沙丘尼寺題贊》《曹植廟碑》中“奉”字結體舒朗,撇捺間開張的弧度與收筆姿態,之間形成的空間與勢度如出一轍,“為”字在結體上幾乎是完全一致。同樣是上面的兩點顧盼回應,長撇如大刀般地斜開,甚至底下的四個點分散的位置都均等。不同的是《沙丘尼寺》肥腴內斂,《曹植碑》則是瘦硬開張。“魏”之間的比較,可以看出文字結體幾乎完全一致,《沙丘尼寺》肥瘦相間,《曹植碑》則瘦硬通達。“皇帝”二字,《沙丘尼寺題贊》中“皇帝”一氣呵成,文人氣質的書寫感;《曹植碑》卻稍見布置呼應之意。“靈”字,二者字體的勢度一致,不同的是一氣貫通的書寫感,與筆畫粗細呼應的布置感。“正”字,其字形結構完全一致,不同之處在于用筆的收縮感有區別。“歲次”二字,是最常見的用字,二者在筆畫動勢處理上有所差異,而在用筆上卻依舊呈現出章法上的差異。“無”的變化,前兩個出自《沙丘尼寺》,后兩個出自《曹植碑》,可以看出前面的行草書意味較強,而后者則是以筆法布置與書寫性為兼顧。“美”字上下形成兩個獨立的部分,上為不露底的“羊”字,下為開展度不同的“火”字,前者圓筆內斂,而后者形成“展開”方圓并用。“焉”字,其結體一致,前一個出自《沙丘尼寺》,書性較強,后一個出自《曹植碑》,刀法感突出。
通過以上隨機選取的十個漢字作基本的比較,可以看出,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跨度里,僧安道壹的書刊風格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相對于他的其它書刊作品,這些更接近楷書的直接書寫,更能夠挖掘其內在的氣質。這個特征也許是時間的演變所無能為力的。也就是說,《曹植碑》之所以看起來顯得異常地突兀,并不是其內在的氣質差異,而是對于“古意書體”的全面實踐而已。
六、以“一”“弌”“壹”為案例:圓形篆、方形篆、隸書、楷書集合一體
在僧安道壹的書刊生涯之中,對于“壹”字的書寫,曾經有過各種形態,在具有代表性的《曹植廟碑》里面,有六個“壹”字,其中一個寫成了“弌”,兩個寫成了“一”,另外三個寫成了大寫的“壹”。
“一”字的處理多樣化,這符合僧安的一貫作風。“一”的涵義是:“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從一。”[18]而“弌”在《說文解字》里是被列入“古文”的。在這三個繁體的“壹”中,有兩個是“圓形篆”,一個是“方形直筆篆”。而在《說文解字》里面,卻是“專壹也,從壺,吉聲,凡壹之屬皆從壹。”[19]
而有趣的是,在此之前的書刊之中,“方形直筆篆”的“壹”,曾經出現在河北邯鄲峰峰礦區南響堂的《文殊般若經》篇章,也出現在山東東平縣司里山的《大般涅槃經·憍陳如品》,以及山東泰安徂徠山《文殊般若經》篇章,還有隋開皇九年(589)的山東汶上《章仇氏造像碑》中。
在《曹植廟碑》里面,有兩個“圓形篆”的“壹”則比較少見,除此之外,唯有在山東東平白佛山開皇十年造像題記之中,可以看到這種處理方式。
在“壹”字篆書結構的“壺”型體里面,是一個“吉”字。這個吉字并沒有隨著外在的筆畫而改變。從《曹植廟碑》對于“壹”字多向處理,可以看出,它伴隨著僧安的“簽名”,而成為一個具有符號性質的文字。這正是其對于這個“壹”字的用心之處。
以象形的篆書與楷隸結體在一起,并不是僧安道壹的發明,其實,在漢代的一些碑刻之中早已有所體現,但是,卻沒有人像僧安那樣,可以產生出如此多的變化。這個豎心字在《曹植碑》里面,得到了更為極致的發揮。《曹植廟碑》的“豎心”,第一個類型是大篆形態的“心”字部首,以“心”上封口為標志。封口式的豎“心”,可以向前追溯到北響堂、南響堂,以及鐵山、葛山等。第二個類型的豎心部首,則是如“樹形”的“心”,是一種小篆形態。公元173年的《漢巴郡朐忍令景云碑》里面,有9個帶豎心的字,全部被保留了小篆的“樹形”部首。第三種類型是在下部首的“心”,這個心的中間一點,基本采取短豎,它帶有篆書的痕跡。它們分別是《曹植廟碑》、隋開皇九年山東汶上的《章仇氏造像殘碑上碑》、隋代開皇十年(579)的山東東平白佛山《曇獻題記》(577)。
結 語
本文在新確認的僧安道壹的書刊遺跡基礎上,進一步從《曹植廟碑》的具體情況、其它兩處僧安書刊遺跡與《曹植廟碑》三者之間的地理關系、歷史上對于三處僧安書刊遺跡的趨同性論述等方面,進一步分辨了“隋代書法”這個概念的局限性,同時,從僧安最早的“刻經體”為起點,到《曹植廟碑》29年間為終點,考察了其書刊風格的穩定性及變化維度。祈望能為今后進一步研究入隋后僧安道壹的書刊風格,提供一個可靠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