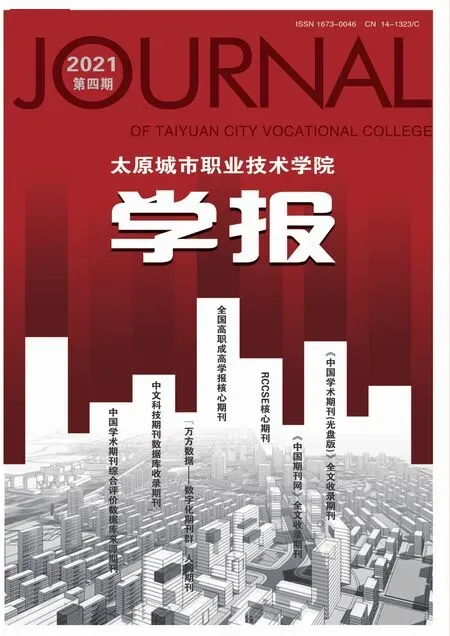解析西方文學理論與英語語言學的關系
■王 晶
(宿遷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蘇 宿遷 223800)
文學理論和語言學具有相互影響、相互伴生的密切關系。一方面,可將文學理論視為語言學的直觀體現或具象延伸,語言學的發展深度支持著文學理論的發展;另一方面,文學理論又會向英語語言學發揮一定的反作用,為語言學提供新的研究視角、評述經驗或變革思路。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西方文學理論與英語語言學的內在關系展開解讀探討。
一、西方文學理論與英語語言學的相關概述
(一)西方文學理論的內涵與發展
所謂“西方文學理論”,即以西方文學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內涵、形式、本質、特點、規律、價值等一系列理論研究的學科領域。由于文學自誕生以來就與人類社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西方文學理論也始終與西方社會、西方文化的變遷發展相伴而行,形成了悠久的發展歷程與豐富的歷史積淀。從本質上講,西方文學理論的研究過程,就是研究者處在不同時代背景、不同角色視角下品讀西方文學作品、評價西方文學作品的實踐活動。因此,西方文學理論具備與西方社會文明相伴生的必然特點,其研究與發展從未停止,也不會停止。從這一角度來看,西方文學理論產生于西方社會與西方文學,又通過深層次、多元化的理論研究與思想碰撞,極大程度地影響和推動著西方文學、西方語言乃至西方社會的進步發展[1]。
從歷史層面來看,西方文學理論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時期。在此時期,柏拉圖開創了“唯心主義文學思想”,指出文學藝術、世界與理念三者是線性的模仿關系,即文學藝術模仿現實世界,現實世界模仿人的意識理念,所以文學藝術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具有本質上的不真實性。在此基礎上,柏拉圖進一步提出了文學創作的“靈感說”,表示文學創作并不完全是人為的,而是靈感與“神力”對創作者實施支配的產物,一首偉大詩歌的出現勢必伴隨著詩人某一創作階段的“狂迷”。隨后,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的文學理論觀點進行了辯證的繼承與完善。一方面,亞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圖對文學藝術的唯心化、虛無化認知,強調文學作品是可以反映客觀現實的,即文學具有真實性;另一方面,亞里士多德在文學理論研究上雖然重視客觀與實踐,但并未否認“神之手”在文學創作中的存在價值,認為優秀文學作品是與“天才”有關的。在此基礎上,亞里士多德將“天才”解釋為理性與智慧達到某種高度的表現。其后,隨著西方社會的持續發展以及西方文學的不斷豐富,西方文學理論在古羅馬時期、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等歷史階段漸趨完善,人們對西方文學中語言文字細節的研究也越發深入,西方文學理論與語言學的密切關聯也隨之愈加明顯。
后至20世紀中期,文學理論研究在大量文學批評家、語言學家的推崇下逐漸獨立成學科,并受到了許多高校文學系的青睞,人們嘗試將西方文學理論正式作為一門研究學科與教學課程,促使西方文學理論新的現代意義與學術價值產生。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當時的西方文學理論大多佶屈聱牙、晦澀抽象,故而引發了西方學術界的很大爭議。20世紀90年代以后,西方文學理論的“熱度”逐漸減退,相關爭議也日趨淡化,但西方文學理論在文學、語言學研究中已占據了相對重要的地位。從目前看來,雖然文學創作、語言學研究等活動中作者、學者很少提及理論性內容,但西方文學理論始終潛移默化、深度滲透地影響著西方文學和英語語言。
(二)英語語言學的內涵與發展
顧名思義,“英語語言學”即研究英語語言的學科,其在英語語言文學研究中具有基礎性的重要地位,研究活動涉及的范疇也相對寬泛。發展至今,英語語言學除了要研究詞匯、語法、語音、語用、形態等英語本身的理論性或實踐性內容以外,還需對英語語言與社會、生理、心理、文化、習得、文學等領域的相互關系展開探究分析。與西方文學理論相同,英語語言學的誕生也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且仍以柏拉圖為語言學研究的代表人物。在唯心主義思想的影響下,柏拉圖認為知識是越過客觀現實對理念的命名,在認知客觀世界中萬事萬物的過程當中,人們對著理念說出語言,便與事物締結了某種“自然關系”。隨著哲學與語言學的逐漸交融,一些學者已不滿足于對語言現象的研究,進而展開了對語言產生內因及深層理論的探索。在此階段,過度理性的“思辨語法”逐步形成,思辨語法學家們傾向于用相對固定的程式進行語句建構,并未對語言的適用情境、交際價值提起重視。后至文藝復興時期,相對理性的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在英語語言學領域嶄露頭角,學者們試圖建立一種世界通用的“哲學語言”,對語言的普遍性進行闡釋與強化。從現代視角來看,這種想法顯然有些“天真”[2]。
19世紀后,比較語言學與結構主義語言學在經驗主義、理性主義的理論基礎上逐漸建立發展,學者在研究語言的同時也開始注重社會背景、文化語境、文學情境、情感色彩等語料的采集、對比、分析與解構。基于此,英語語言學逐漸步入現代化、豐富化的新研究階段,其與西方哲學思想、文學理論的相互影響也實現了進一步強化。
二、語用分析視角下西方文學理論與英語語言學的關系
在西方文學研究與英語語言研究中,語用分析都是基礎性、核心性的內容與方法。細化來看,語用主要包含“發話者”“受話者”“語言內容”以及“語境”四個要素。其中,“發話者”即語言信息的發出方,“受話者”即語言信息的接受方,“語言內容”即發話者發出、傳遞語言符號時所表達的內容,“語境”即語用活動所處的特定環境。進一步講,語境還可細化分為“上下文語境”“社會文化語境”“交際場景語境”“角色關系語境”“背景知識語境”等多種類型,這些語境類型單一或混合作用于語用活動,對語言符號的表達效果有著極大影響。以“I am a descendant of the dragon”一句為例,若拋開詞匯“dragon”與“loong”的具體差異,將“dragon”解釋為廣義上的“龍”,那么不同語境下該例句所表達出的意思將存在很大差異:若受話者為中國人或深諳中華文化的西方人,其會將此句視為褒義話語,即“你是龍的傳人”。而當發話者與受話者皆為西方人時,此句將很可能被理解為“你是惡魔的后裔”,即一種批判或詛咒。造成這種差異的最根本原因,是角色關系、社會文化、交際場景等語境因素的不同,也就是中西方文化語境的不同。
可想而知,當“I am a descendant of the dragon”這個句子出現在文學作品當中時,其所表達出的情境與效果具有很大不確定性。意味著英語語言學對西方文學研究在語用分析方面具有極大影響。所以,學者普拉特在談及日常語言與文學語言時指出“在西方文學理論的研究過程中,要將文學作品中的語言符號、語言行為引向社交語用的層面,而不是武斷地將生活語言和文學語言視為對立區分的雙方”。在日常生活的語用場景當中,文學作品中常見的隱喻、虛構等修辭方式也具有應用意義。相反,文學作品的內容創作、閱讀感悟也會以現實生活中語用規則作為基礎,并表現出明顯的交流特性。因此,西方文學理論與英語語言學并不是涇渭分明的兩個體系,而是以特定語用規則、文化管理、語境背景為紐帶的交融關系[3]。
此外,在20世紀50年代,學者奧斯汀還創立了“言語行為理論”,即把文學作品或現實生活中的語言分成兩個種類:一是“施行話語”,二是“記述話語”。其中,施行話語在描述某一動作現象時,不僅要通過語言進行闡述,還要用語言進一步表現相關動作的執行,如一個新娘在婚禮上捧著鮮花對身邊的丈夫說“我愿意”,一個老人揮舞著拳頭對另一個人說“我還充滿力氣”,一個男人在撞倒另一個人時說“對不起”等。而記述話語則只是陳述或解釋某一事件或現象,如“他在跳舞”“貓在睡覺”等。在此基礎上,奧斯汀認為記述話語在某種角度上可被看作是施行話語的內涵符號,且可通過有無真假、有無適當等標準來判定施行話語、記述話語的真實性。所以,在奧斯汀的語言學觀點和文學批評理論下,文學作品中的語言既不具備真實性,也不具備施行性,因此其語用屬性相對生活語言來說是不嚴肅、不認真的。從這一觀點來看,在英語語言學的影響下,文學創作是一種特殊的的語言行為,其本文的虛構程度、語用效果是由創作者主觀意圖來決定的。
三、結構評價視角下西方文學理論與英語語言學的關系
現代語言學之父、結構主義創始人索緒爾在其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提出,語言學的研究行為應保證“共時性”,即把語言的存在狀態作為研究對象,而不是脫離特定的時間條件,研究語言的歷史狀態。同時,索緒爾還將語言符號分成兩個部分:一是“能指”,二是“所指”。其中,能指即語言文字的聲音、形象,所指則為語言的本身意義。通俗地講,人們在語用活動中,其想要表達的信息可成為“能指”,語言實際表達出來的信息叫做“所指”。在同一語言符號的結構系統中,能指與所指的相互關系具有很強自由性與波動性,但有時也會遵循一定的社會規則或約定邏輯。以此為基礎,索緒爾還對結構語言學體系下的“語言”與“言語”進行了明確區分,指出語言具有傳承性,是多代傳遞下的語法、句法、語素、詞匯等語言系統,而言語則是語用雙方可能說出、可能理解的信息內容。將這種語言學觀點代入到西方文學理論研究當中,可基本將語言與言語的關系視為詩歌文本與詩歌體驗的關系。一方面,詩歌文本作為既定產生的文學作品,其詞匯內容、語法結構都是相對固定的,且存在相應的“能指”本意。另一方面,在創作者與閱讀者的信息傳遞過程中,詩歌本意會因為種種因素影響而得不到直接表達,此時詩歌對于某個閱讀者的“所指”體驗便會特化形成。
此外,對于文學作品來說,索緒爾認為語言、能指是高于言語、所指的。所以,無論是在文學理論的研究中,還是在文學作品的創作中,學者或作者都應將語言符號的基本結構、組合邏輯、本質意義等系統要素放在首位,將一般敘事放在具體敘事以上,以確保某一故事情節、語用場景中人物、時間、背景、狀態、事件等關鍵信息的傳遞明確、組合準確。這樣一來,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能指與所指、語言與言語的傳遞或評價發生偏離,實現語言發出者與接受者的意愿對等[4]。
四、話語解構視角下西方文學理論與英語語言學的關系
有結構就必然有解構,所以話語解構也是西方文學理論與英語語言學研究的一大重點。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從結構向解構展開研究探索的過程,就是由純文學分析向文學觀分析探索、由作品封閉性向文本開放性探索的發展過程。20世紀80年代,英語社會評論家、文學評論家喬納森提出了“社會文本”這一概念,并將小說、詩歌、新聞故事、影視劇等一系列文學藝術產物納入到了該范疇當中。喬納森表示,社會文本不僅能預先性地反映或構建客觀世界的事物面貌,還具有很強的社會寓言和政治意涵屬性。所以,通過有效的研究手段,對社會文本進行解構處理,能達到“透過現象看本質”的目的,對文本語言中包含的深層內涵進行感知,從而更客觀、更全面地促成語言和言語、能指和所指的對等。
在談及語言的建構與解構時,學者約翰·塞爾指出:“當我們體驗世界時,我們是通過語言的范疇來體驗世界的,而語言又幫助我們形成了經驗本身”。所以,在語言建構、解構的過程中,是具有一定轉向動作與“反叛色彩”的。其既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世界、描述世界,同時又會形成一定的經驗積累和邏輯規則,對人的語言運用、文學創作等行為產生反作用。結合主題來看,西方文學理論和英語語言學的關系,與約翰·塞爾的觀點是相類似的。一方面,西方文學理論以英語語言學為基礎和依托,若缺乏語境、語法、語構等語言學要素作為支持條件,西方文學理論的形成土壤將不復存在,其研究活動也大概率會停滯在淺層階段;另一方面,西方文學理論是英語語言學的具象表達,若西方文學理論停滯不前,英語語言學也較難有所突破。所以,西方文學理論與英語語言學是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
五、文學批評視角下西方文學理論與英語語言學的關系
在進行西方文學理論的研究時,很多學者會將英語語言學的價值觀念代入到文本分析當中,以此“阻隔”外部環境對文學作品特征的影響,實現文學內在規律的客觀探尋。這種理論研究、文本分析的方式,通常被稱為“文學的語言學批評”。在此視域下,語言學家卡勒以喬姆斯基的文學觀點為基礎,從語言學批評角度提出了文學作品的“深層結構”“表層結構”“文學能力”等概念,并嘗試建立一個“理想讀者”對文學作品的語言規約進行明晰解讀,從而探究獲得可產生文學效果的主要元素或潛在體系,而不是對文學作品的情節、內涵、背景進行闡釋。從這一方面來看,以卡勒為代表的語言學批評家們更傾向于視文學作品為一個客觀、嚴謹的精密系統。同時,又一語言學家詹姆遜提出,語言文字對文學作品的影響,是以符號學、邏輯學為基礎的。只有按照特定邏輯對語言文字進行建構處理,才能以文學作品為載體生成與現實世界相并列的符號系統,從而賦予語言文字代表客觀世界或反映客觀世界的能力。若拋開了這種符號系統的邏輯關系,單一詞匯、句子是無法表示客觀世界中的事物或事件的。也即條理化的語言系統才具備與客觀世界的可比性,文學作品與客觀世界的對應關系是整體與整體的關系,而不是細節上的“一對一”關系[5]。
從很大程度上講,以語言學為背景的文學批評為西方文學理論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催生了西方文學理論研究的兩個維度,即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其中,確定性研究就是分析和發現文學作品的共性特點,如某一章節、某一語句通過相同的符號構成邏輯,表達出了相似甚至一致的事物或事件含義。而不確定性則是在語言批評學的基礎上,融入文化、場景、主觀情感等背景因素,從而對相同語言符號在不同邏輯關系、不同系統結構中的含義產生差異性。在這兩個維度的支持下,文學作品中語言和元語言、現象和元現象、批評和元批評、思考和元思考等的關系都能被更加清楚、細化地解讀,遮擋在西方文學理論前的迷霧都可被語言學、符號學的風吹散澄清[6]。
六、結束語
總而言之,無論是在語言研究領域中還是在文學研究領域中,英語語言學和西方文學理論都是密不可分的兩大研究重點,兩者既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又相互輔助、相互促進,共同為人們提供出了探索語用關系、文學作品的優質工具。所以,做好英語語言學和西方文學理論的探索分析,能幫助人們更加高效、順利、辯證地學習西方文化、強化英語水平、充實人文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