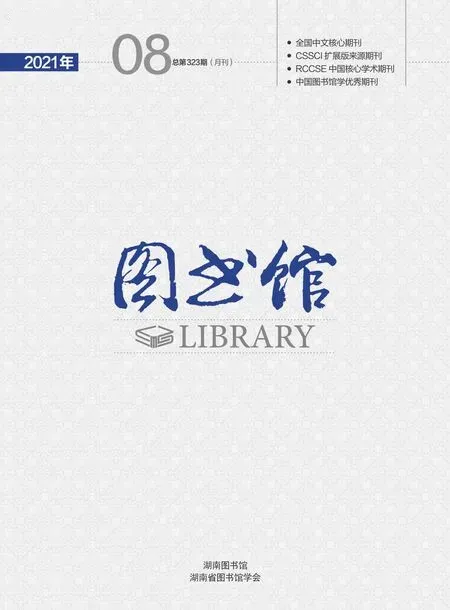唐代官方藏書場域中的機構博弈研究*
郭偉玲
(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 杭州 310018)
中國古代官方藏書呈現出多機構相輔相成合作競爭的建設態勢,但歷朝歷代“皇家藏書在更替、繼承中續有發展,形成各自特色”[1],西漢“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2]614,曹魏有“秘書中外三閣”,南朝文館與秘書監(省)、內府均有藏書,隋唐兩地宮城內外多機構按照藏書職責進行分割與合作,兩宋館閣并存,“三館秘閣一省”數足鼎立。從歷史維度來看,公元7世紀到10世紀之間,古代官藏機制呈現多元并進的局面,其中又以唐朝三百年最為多變,一元制、二元制、多元制的布局變化,成為官方藏書格局的“試驗田”,機構廢立興衰、權力此消彼長,機構間博弈形態暗流洶涌,卻還是造就了唐代“藏書之盛”,其中緣由值得探索。
唐代統治者修文重書,積極建設官藏,將分散于各地方、各私家的圖書聚集京城,建成龐大的政府轄制下的知識集合,通過復制抄寫、藏書分割等資源再分配的手段,促進知識載體在不同的政治空間里流動。筆者借用“流量”這一概念,假設唐朝某一時刻,生產力一定,其所能支撐的圖書流通總量一定,政府所能控制的知識流量一定,選取秘書省、內府、弘文館、史館、集賢院五個機構作為參數變量,以他們的建立為時間節點,采用混沌理論(一種兼具質性思考與量化分析的方法,用以探討動態系統中無法用單一的數據關系,而必須用整體、連續的數據關系才能加以解釋及預測之行為)分析方法勾勒唐政府藏書流量在各中央文化機構中的流向與分布,通過形象化的敘述建立唐代中央官方藏書建設的動態圖,并以此為基礎構建唐代官藏場域,并結合政治制度史展示機構間的合作與競爭。
1 唐代官方藏書資源流向與分配
唐代君臣奉行重書政策,廣開獻書之路,增設藏書機構,官方藏書格局幾經改易,藏書事業一直處于開放與探索中,表現形式就是藏書話語權在機構間的挪騰轉移,在這場博弈中,職掌圖籍的秘書省無先天優勢,反而成為“被剝奪者”,各文化機構對有限的藏書資源所進行的占據性競爭,成為推動唐朝圖書事業發展的潛在動力。
1.1 一元制初期:秘書省單一機構時期(武德年間)
唐初,秘書省占據了所有的藏書資源,承擔官方藏書建設任務,如接收并安置隋代舊藏、武德五年開始的圖書購募活動,藏書機制處于絕對的“一元”狀態,這一局面源自隋末秘書省地位的驟升,“大業年間,隋煬帝增加秘書省人數共有91人”[3],唐初官制“皆依隋舊”[4]1217,但“一枝獨秀”的建設機制并未體現力量集中的優勢,武德年間,朝政重點并非文化,唐高祖輕視秘書省職官,認為其“清而不要”[5]1053,官員任免遵從“為人擇官”,秘書省前“門可張羅”,官藏建設推進遲緩。
1.2 多元制肇始:弘文館、史館、內府等多頭分流時期(貞觀年間—開元初)
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李世民令于弘(宏)文殿側置弘文館,目標藏書二十萬卷,秘書監魏征、虞世南、顏師古相繼負責抄寫圖書,以增弘文館藏。內府入藏熱點緊隨其后,太宗雅好二王法書,重賞收集,書畫作品持續入內,同時還有書籍,開元三年唐玄宗言及內庫所藏:“內庫書,皆是太宗、高宗前代舊書。”[5]644貞觀三年閏十二月,唐太宗于門下省北設置史館,由于史職原屬秘書省著作局,史館另立時,應從秘書省中分割了部分藏書。
自貞觀年至開元初,唐朝官藏圖書流向主要是:第一,圖書社會征集和社會呈獻、官方修書,大部分入藏秘書省,少數內府入藏,秘書省和內府成為唐代官藏的源頭,以供他處;第二,貞觀至顯慶間四十余年,秘書省抄寫之復本多充實弘文館,造就“二十萬卷”的數字神話;第三,史館除卻建館分割秘書省部分藏書,之后藏書與歷史相關或者制度入藏,可實現自給;第四,內府主要接收“特定”圖書,開元十四年(726年)元行沖撰成《類禮義疏》五十卷,遭丞相張說反對,唐玄宗“留其書貯于內府,竟不得立于學官。”[4]2153
1.3 二元制:匯集一處的集賢院(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
開元七年,唐玄宗對內府和秘書省進行的圖書整理活動告一段落,負責人員在麗正殿繼續進行官藏書目的編撰;十三年麗正修書院改名集賢殿御書院,簡稱集賢院 “其職具秘書省”[6]279,之后開元天寶年間,秘書省的圖書職責被集賢院接管,《唐會要》“秘書省”條對秘書省的記載就是秘書郎減員、校書郎省員、正字減少、著作郎減少,而同書“經籍”條的主角幾乎全是集賢殿。無論是基于史實還是合理推測,我們都可以認為這一時期,唐代官方藏書的流向主要是集賢殿,秘書省、弘文館等機構的入藏可忽略不計,尤其是秘書省獲得的關注度驟然下降,藏書管理松懈,“不存勾當。或詮次失序,或鉤校涉疏,或擅取借人,或潛將入己,”[7]157天寶十二載十二月二十二日,玄宗“令左相兼武部尚書陳希烈充監秘書,令省圖書。”[7]157
1.4 一元“主導”多元并存(中唐至晚唐)
安史之亂后,唐朝官方藏書數次歸零重啟,天然屬性為圖籍管理機構的秘書省優勢明顯,中央財政無力支撐數個圖書中心的建設,只能專心經營秘書省,成效顯著,開成元年(836年)七月“秘書省四庫見在雜舊書籍,共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5]1125,唐文宗更令地方府道分擔機構抄寫任務,秘書省藏書從四庫擴充為十二庫,真正成為唐代官藏中心。于此同時集賢院、弘文館、史館等機構內應有藏書,但規模卻比不上盛唐,唐德宗建中年間,集賢殿“于散亂中,厘集二萬余卷”[8],唐宣宗大中四年二月,集賢院對上年的工作量進行統計,一年內圖書抄寫并填缺書籍共三百六十五卷;弘文館穆宗長慶三年曾奏請“添修屋宇,及造書樓”[5]1116,之后弘文館藏書的記載逐漸消失,只能通過機構內職官變動和借調來推測藏書的存在了。
“太和五年正月,集賢殿奏:‘應校勘宣素書籍等,伏請準前年三月十九日敕,權抽秘書省及春坊、宏文館、崇文館見任校正,作番次就院同校,其廚料請準元敕處分,事畢日停。’從之。”[5]1121
“大中四年七月,弘文館奏:‘當館楷書典書等,與集賢史館楷書等,承流前例,并勒校成五考赴選。……今集賢史館奏,勞役年深,補召不得,已蒙敕下,免三年授散訖,今當館請準例處分。’敕旨,依奏。”[5]1116
2 唐代官方藏書機構分工與合作
唐代中央各藏書機構的職責不僅限于藏書,時人認為官方圖書收藏是途徑,而資治、儲才等功能才是目的,這就使得秘書省、弘文館、集賢院、史館、內府等機構藏書各自依托于設置愿景形成了分工合作關系。
2.1 機構藏書分工
秘書省“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領著作、太史二局,各職修撰、天文歷法,但秘書省并非單純的藏書機構,尚兼具儲才職能。中唐白居易曾在策《大官乏人》中提到:“秘著之宦,不獨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丞郎之椎輪,公卿之濫觴也”[7]3026,秘書省的圖籍職責并不孤立職官的專業化,而是通過基礎的圖書繕寫刊校的職責為國家儲育高級行政人才,藏書工作兼顧文化與政治目的,具有職責與職官的雙重性。圖書管理機構與藏書建設機構的雙重屬性影響了秘書省在中央藏書中的分工,當政治功能突出的時候,秘書省的圖書受到重視,圖書趨向封閉保藏,如中唐以后;當政治性退卻或者由其他機構接管時,藏書會回歸本源,成為一個單純的藏書中心,甚至可以為其他機構、職官提供藏書資源,如貞觀年間、開元天寶年間。
內府的屬性明確,藏書更為封閉,也因內府的“秘藏”屬性,收入了部分其他機構沒有的圖書,在某種情況下,內府藏書可以向其他機構提供特定藏書,如開元六年,內府出張王古跡書法,交予集賢院拓印,分賜諸王;天寶十四載四月,內出御撰韻英五卷付集賢院行用。
史館的藏書是為了修史,它在藏書體系中的分工相當于專業的歷史檔案資料館,史館所編撰的《實錄》《起居注》等“既終藏之于府”[6]281,這些資料記錄“只有那些被授權的人,才可以查閱這些材料”[9],如皇族、史官等。
弘文館職責有三:圖籍、教授、參議朝廷典制,其藏書建設是為了后兩項職責而存在的。“開元二年正月,宏文館學士直學士學生,情愿夜讀書,……愿在內宿者,亦聽之。”[5]1115弘文館書架是開放性的,放置在文館之內,藏書對文館學士學生吏員開放,其藏書的利用已形成一定的體系和規模。
《唐六典》記載:“集賢院學士,掌刊緝古今之經籍,以辯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6]279秘書省的圖籍職能、弘文館的侍從咨詢職能、內府的御覽職能等一并歸入,集賢殿書院成為唐代諸多文館之集大成者,雖然開元二十五年刊定的格令再次強調“秘書省以監錄圖書”[10],強調了秘書省的圖籍職能,但集賢殿在玄宗時期仍代替了秘書省成為國家保藏中心,代替了內府成為御覽之所。“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7]2492安史之亂之后中央文館重新洗牌,大中六年(852年)六月“宏文館奏:伏以三館制置既同,事例宜等”[5]1116,一個“等”字說明了中唐以后集賢院與史館、宏文館地位相等,待遇同級,分工各有側重,原來的咨詢、承旨、推薦等職能被翰林學士院等新設機構接過。
秘書省、內府、史館、弘文館、集賢殿等五個藏書機構,因機構性質和職責交替、朝局變幻等原因,在圖籍職能上各有分工,各有特色。秘書省側重于人與書,內府則傾向于帝王私用,史館職在修史,弘文館意在資政,集賢院則總而有之。各個文化機構在政治的指揮棒下,命運各異,但均為唐代官府藏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了應有的歷史作用。
2.2 機構藏書合作
或因資源的調配和共享,或是機構間有意識的合作建設,或因參與人員官職官位,唐代中央藏書機構在圖書編撰與收藏等建設環節合作緊密,各機構之間的合作,時間集中,應時匹配,應事而生,共同推進唐代國家藏書事業的發展。
2.2.1 圖書編撰
武德初修前代史,參與者以秘書省官員和其他朝官充任,數年無功;貞觀初唐太宗重啟修史工作,秘書省設置秘書內省,秘書省官員與弘文館學士參與其中,貞觀三年后,史館史官亦參與其中,再加上兼職的朝官,多方人員合作編撰了唐初官修五史。這種合作模式并非個案,太宗朝《群書理要》《五經正義》《文思博要》《武德實錄》《貞觀實錄》《氏族志》等書,高宗朝《文館詞林》、武后時期《三教珠英》等書,均產生于這種合作模式下。秘書省職掌圖書校勘,弘文館雖無常員,但職責涉及圖籍勘正、授教生徒并參議典制,史館修國史,這些職責綜合在一起,很容易在圖書編撰領域進行合作。武后時麟臺監張昌宗領銜編撰《三教珠英》,參與者來自各部,地點卻是在秘書省內,沈佺期曾寫《黃口贊》序曰:“圣歷中,余時任通事舍人,有敕于東觀修書。”[11]玄宗朝圖書修撰均以集賢院學士為主導,秘書省以及其他官員參與,開元十三年四月,“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與禮官于集賢書院刊撰儀注。”[4]602-603
2.2.2 藏書建設
唐代藏書機構因設立時間有先后,因此機構之間存在資源計較補遺的互惠。
秘書省與史館:貞觀三年末史館獨立,史館分割秘書省藏書,獲得起初的館藏積累;之后,史館所撰史書多收入秘書省書庫,如“貞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元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太宗……遣編之秘閣,……京官三品以上,欲寫者亦聽。”[5]1093《舊唐書·經籍志》根據盛唐藏書目錄編撰而成,史部錄唐朝實錄八種,收得玄宗前所有史館編撰的實錄,由此可知,唐朝史館所修實錄并非單存于史館書庫內。
弘文館與秘書省:武德九年,太宗即位伊始設弘文館,史載館內二十萬卷藏書,但巨大的藏書體量無法憑空產生,是貞觀年間秘書監魏征、虞世南、顏師古相繼帶領數百名秘書省書手抄寫,抄寫工作持續至高宗乾封年間,秘書省成為弘文館館藏的來源地和建設者。
集賢院與秘書省、史館、弘文館等:唐代藏書機構之間最大規模的一次合作始于開元七年,時秘書省內庫圖書已經整理上架完畢,唐玄宗并未止步于此,下詔秘書省、史館、弘文館等機構與麗正院之間異本借抄,征集抄寫民間士庶異本。雖然這次活動以集賢院(麗正院)為核心,但還是極大豐富了唐代官藏。開元天寶年間,機構之間的藏書建設合作一直在持續,見于史料的有從史館借抄至集賢史庫者:“韋述知史館,敕令述寫燕公所撰《今上實錄》廿卷,藏集賢史庫。”[12]天寶十一載六月秘書省非比省內四庫書,將結果奏上,十月,“敕秘書省檢覆四庫書,與集賢院計會填寫”[5]1125,秘書省藏書與集賢院藏書再次進行計算對比,互相補充。
3 唐代官方藏書機構的競爭與博弈
唐代藏書機構分布在長安、洛陽兩地的多個宮城內,機構之間雖有合作,但更多的是以競爭的狀態存在,這種競爭不存在于文字上,而是體現在結果上。以不同機構的輪番登場作為主要表現形式,因此藏書機構之間表面競爭的是圖書資源,背后博弈的則是政治權力。
3.1 機構間競爭
唐初秘書省作為藏書專職機構,在繼承前朝藏書的基礎上多次進行民間的圖書購募,完成了初步的藏書積累,之后出現的其他機構如內府、史館、弘文館、集賢院,其藏書的原始積累都是來自對秘書省圖書的分割與復制。如弘文館的巨量藏書來源于秘書省內持續四十余年的抄寫補充,明人胡應麟質疑:“文皇初年,亦似留意經籍。……然迄貞觀中,未聞增益……何也?”[13]按《隋志》言,唐初見存圖書“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2]614,《唐會要》載兩京集賢殿書院于天寶十四載圖書單本為71 417卷,百余年的藏書建設,在唐太宗、唐高宗、武后、唐玄宗數位君王的努力下,唐代官方藏書單本量不升反降,除了政治動蕩、管理不善、建設方向等原因之外,多機構并存的藏書局面,秘書省藏書多次被“割榮”,藏書建設生產力被分流也是影響統計數字的因素。
在前印刷時代,圖書生產的主要形式是人工抄寫,生產能力有限,這就造成了唐代多個藏書機構交替出現,雖在制度上延續了秦漢以來多機構藏書布局,但在整個國家藏書事業的前進維度上,反而因為國家圖籍職能的數次遷移造成了中唐之前藏書建設的顧此失彼,藏書單本量的增長出現停滯,藏書復制抄寫的副本分布各處,增長明顯,數量超越質量。中唐以后,秘書省成為官方藏書建設的核心,雖自安史之亂后從零開始,但百余年的時間內,經肅宗、德宗、憲宗、文宗銳意經營,開成元年七月“秘書省四庫見在雜舊書籍,共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5]1125,分藏于十二庫,更有四萬余卷的抄寫任務分配給地方政府,增長速度遠超唐初。
但從統計數字上來說,集中所有力量建設一個藏書機構,遠遠比多元并存的藏書機構格局,更能促進藏書事業的發展,但一元式的藏書建設并不是歷史選擇,無論漢魏六朝與隋唐,還是宋明清,多個機構并存的格局是歷史事實,如西方亞歷山大圖書館這樣的超級圖書館并未出現在中國古代,是歷史元素和個人因素造就的結果。官方藏書機構的建立,有制度的因襲,如秘書省承襲自東漢末年的秘書監一職,內府作為君王的私庫其歷史淵源也頗為久遠;也有君主的意志,如新館建立,起初因為帝王的需求,新機構在權力傾斜下發展壯大,接替了舊機構的職能,接受或分割了原機構的資源。但文館制度有其歷史必然性,如文化整合、官制改革、權力集中等因素,值得指出的是,在權力與制度的博弈中,圖籍往往最先成為突破口,從秦漢時期的御史大夫、到漢武帝時期職掌秘籍書奏的尚書,還有曹魏時期的秘書令與中書令,圖書作為天子公私交融的邊界點,被用作試金石,擴張君王的權力影響領域,藏書機構的政治性由此得以體現。
3.2 職官地位
中國古代官制常有新舊交替,但“新官與新機構設立之后,舊的仍然存而不廢”[14]18,新舊機構之間存續著職責重疊,如唐代秘書省、弘文館、集賢院,原來皇帝御覽的圖書可能出自內府或秘書省,后集賢殿成為“御書院”,原來圖書編撰多在秘書省,開元天寶年間轉移至人力物力更為充沛的集賢院內。在多機構并存、職掌交叉的狀態下,資源與話語權出現爭奪,往往會出現“舊不如新”的局面。
古代職官的地位取決于兩個因素,職責與任官,在職責一定的情況下,天子私人身側的機構更容易獲得權力,如弘文館之于唐太宗,集賢院之于唐玄宗;另外情感因素影響職責與權力的轉化,如天子為了自己的統治力,往往會支持自己的近臣獲取更大的權力,因此產生了“官隨人轉”的情況,即皇帝認可某人的時候,即使他所擔任的職官沒有此項職責,往往也會被賦予更多的權力,“彼居甲官則甲官之職重要,居乙官則乙官之職重要。”[14]23
唐太宗弘文館內, “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量政事”[5]1114,任職弘文館學士者多來自太宗潛邸,景龍之前,弘文館學士多出自君意,任命條件、員額、品級不定;景龍之后,學士任命要求“攻文之士以充之”[5]1114,定員額、品級,文館學士成為官員認可標識,地位清顯,重視德才。
唐玄宗時期集賢院雖源自圖書,但不止于圖書,學士職責不僅僅限于圖籍典校,更逐漸摻雜較濃的政治色彩,“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藉其刊削。”[4]2067集賢學士任職具有文化與政治的雙重性,時人異常推崇。賀知章同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在回答侍郎與學士何者為美:“侍郎……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最矣。”[15]唐一代,文館學士的清顯地位得到整個朝野的認可,大學士常由宰相兼領,中唐時期又明令禁中行走,弘文館、集賢院、史館“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謂三院連鑣也”[16]。
秘書省職官并不受時人青睞,“唐初,秘書省唯主寫書貯掌勘校而已,自是門可張羅,迥無統攝官署,望雖清雅,而實非要劇。權貴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職,流俗以監為宰相病坊,少監為給事中中書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為尚書郎病坊,秘書郎及著作佐郎為監察御史病坊,言從職不任繁劇者,當改入此省。”[17]相對于文館學士的爭相競取,秘書省成為病退者、避世者的任官選擇,顏師古兩任秘書少監,因“仕益不進,罔然喪沮,乃闔門謝賓客”[18]。安史之亂后,文館學士名存職非,原有的尊崇地位、待遇遭到削減,貞元末,秘書少監陳京降低集賢學士待遇,將其與校理官同酬,“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為膳;有余,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19]而同時秘書省內高級文官學術性質變淡,“秘書監開始與六部尚書、侍郎等政務部門的官員相互遷轉”[20],成為三品官序中內外遷轉的關鍵點;而基層官員如校正郎官,成為登第士子起家之良選,中晚唐時期詩人符載在《送袁校書歸秘書省序》中寫道:“國朝以進士擢第為入官者千仞之梯,以蘭臺校書為黃綬者九品之英。”[7]3132秘書省校正較之于弘文館、集賢院、崇文館、左春坊、司經局等地的校正,名望更優,任職要求更高,不僅要求進士出身,且“等第稍高,文學兼優者”[5]1397才能注擬秘書省校正。從職官地位上來說,中唐以后秘書省職官地位有所提高,但這種提升并非因為本職,相反是因為秘書省職官逐漸褪去學術性質,成為官職遷轉中的一環,秘書省職官得到了政治儲才功能的加持,地位才得以提升。
4 結語
從藏書體制上來說,中國在秦漢時期就已經確定了內外多機構的官方藏書布局,之后魏晉南北朝時期,因政權更替頻繁,官方藏書體制日漸復雜。從魏晉時期內外臺閣多元制到南朝秘書監(閣、省)一元制,以及北朝從秘書一元制到“文館+秘書”的二元制,各類體制因政治文化等因素而短暫出現。隋統一后,也經歷了從宮城內外到京城兩地的內外雙機構發展模式,唐代藏書制度“是混合和承襲了南北朝的制度”[21],一元制、多元制藏書機構布局均有出現,變化原因雖可歸結為君主、經濟等因素,但根源還是在于政治,新機構的出現代表著新的藏書空間的建立,而藏書空間跟隨著政治中心的轉移,從一到多,再從多匯集一處,然后回歸,與唐代的政治緊密關聯。藏書不僅僅是彰顯“文治”的工具,更是政治局面穩定的表象,唐朝多位君王在喪亂之后,重啟官方藏書建設。太宗、玄宗、德宗、文宗、僖宗、昭宗在動亂之后,明發詔書,重視藏書的管理與聚集,不只是因為藏書事業的文化意義,更多的是想通過最直接明了的方式重立政治權威,因此初唐與盛唐時期,權力的重塑通過新舊的交替,新舊藏書機構之間因權力出現競爭合作的博弈局面;而中唐以后,局勢更加動蕩,中央權力受限,新的空間難以拓展,恢復性建設成為官方藏書事業的首選,因此秘書省成為名副其實的官府藏書中心,也是統治秩序恢復穩定的最佳代表,藏書機構之間更多的是合作而不是競爭。
唐代多機構并存的藏書格局以安史之亂為界,之前,風起云涌,內府、弘文館、史館、集賢院加入秘書省所在的官藏場域中;之后,風平浪靜,秘書省重新成為藏書資源匯集地,藏書建設從多元轉向一元。唐代官藏格局的變化改變的只是受到政府支配的藏書資源的流向,而知識自下而上的流動過程與流通總量并未削減,唐代官方藏書場域的構建一直在持續。唐朝三百年所秉持的“經籍之道”的治國理念,圖籍資治的認知深深影響了李唐王室與統治階層,官方藏書場域是由政治場域與文化場域的分化交匯而成,其成因雖受到政治與文化因素的影響,但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在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一定的特質,如建設目的圍繞著統治者的需求和國家文化制度,藏書事業的建設方、圖書資源的提供方、圖籍文本的生產方同處于場域之中,可以說唐代官藏場域的形成是自主的,是一種治國理念的貫徹,也是一種精神文明的傳承。
(來稿時間: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