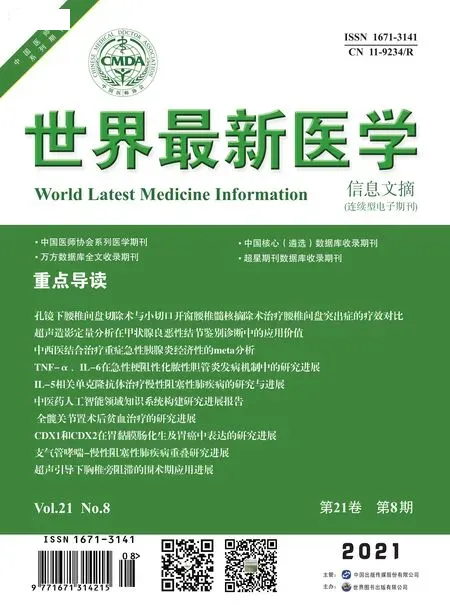引火湯臨床應用新知
楊鑫杰,陰倩雅,陰澤政,張軍鋒*
(1.山西中醫藥大學,山西 太原 030024;2.河南科技大學,河南 洛陽 471000)
0 引言
引火湯是傅山用于治療陰蛾證所創立的一首方劑,最早見于陳士鐸《辨證錄·咽喉痛門七則》。該方由熟地三兩、巴戟天一兩、茯苓五錢、麥冬一兩、五味子一錢組成。引火湯顧名思義,為引非其本位之火復歸其位,是引火歸原治法的代表方劑之一。
引火歸原法是中醫治法之一。“火”即“相火”、“虛火”、“龍雷之火”,丹溪在《格致余論·相火論》寫到:“見于天者,出于龍雷,則木之氣;出于海,則水之氣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于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他認為相火是寄存于下焦肝腎,以肝腎之陰為物質基礎的陽氣。人體應與天,生理狀態下“雷不鳴”、“龍不飛”陽氣潛藏于下焦,而“龍”出于水,雷鳴于天系為相火妄動,人體會隨之出現相應的病理變化。而引起“火不歸原”的原因,又有陰不斂陽、陰盛格陽、虛陽浮越之別。治宜“引火歸原,導龍入海”[1]。
1 方義分析
引火湯由熟地三兩、巴戟天一兩、茯苓五錢、麥冬一兩、五味子一錢組成。此方就藥物組成來看,為陰陽雙補劑。方中以熟地大補陰精為君;加麥冬、五味子,取金水相生之意,虛則補其母,水源得以充足,水足則火自平;又以巴戟天溫而不熱,既益元陽,復填陰水三者共為佐藥;《本草新編》云“夫命門火衰……用附子、肉桂以溫命門,未免過于太熱,何如用巴戟天之甘溫,補其火而又不爍其水之為妙耶?”故此處選用巴戟天而不用桂附之屬。水火既濟,又以茯苓甘、淡,趨下之性為先導,引諸藥下行,火隨水降,水濟龍潛而諸癥得消。
2 臨床應用現狀
引火湯在《辨證錄》中系為陰蛾之癥所設,其癥狀表現為:咽喉腫痛而稍干,日輕夜重,飲水咽之稍覺舒適,咽下又覺脘腹不適,吐涎水甚多。后世醫家多以此方治療陰虛火旺之病癥,同時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發揮運用,拓寬了其臨床應用范圍。劉要武[2]等醫家認為此方對于鼻衄、倒經、三叉神經痛、復發性口瘡、咽痛、牙齦出血等以頭面癥狀為主的均有很好的療效。高飛[3]總結李可老中醫經驗,認為下元不足,龍火失藏所致口舌牙齦糜爛、生瘡、腫毒用此方治療臨床可有顯效。雷之火寄存于肝,龍火寄存于腎。肝腎同源,腎水虧涸,肝血既虧,雷火隨腎中龍火上燔,而成燎原之勢,而見種種上熱見證[4]。咽痛之癥為虛火上炎之外候,其病機在于下焦水虧,虛火不藏,燔灼于上,而腎經上行又循咽喉,故此癥多見。此外,此方不止運用于頭面上焦部癥狀,林煒濠等[5]用此方加減治療皮膚病癥,如脂溢性皮炎、痤瘡、單純皰疹等,每有奇效。亦有研究表明此方治療女性更年期不寐臨床療效顯著[6]。
然中醫治病在于辨證論治,李榮光[7]枚舉了運用此方治療陰蛾、鼻衄、口腔糜爛、癇衄并發的臨床驗案,提出此方加減化裁不止于治療頭面上焦病癥,也可以治療內科雜病,需要契合元陽虛衰,虛火上浮這一病機。王興臣教授[8]認為對于腎陰或腎陽虧虛導致的心腎不交證候,不論何種疾病,皆可臨證試用,不必拘泥于“陰蛾”。筆者亦認為在臨床上使用此方時,當把握病機,不拘泥于病名、病位,辨證使用即可。筆者對此方使用略有體會,現陳述于下。
3 驗案新知
患者,男,25 歲。平素畏寒,一次發熱后,熱退出現舌咽生瘡,痛劇,不可進食,進溫熱食尤甚,心悸而脈來數疾,一息七八至。舌質淡苔水滑,舌瘡瘡面略紅。診為陰陽不交之證,此為下焦陰火不得歸其本位而致虛火上燔。方選引火湯:熟地15g、巴戟天10g、茯苓15g、麥冬10g、五味子6g,2 劑水煎服。1 服之后,脈勢已緩,心悸大除,只覺睡前醒后心悸不能自主,每由朦朧持續至完全沉睡或清醒方得消失。2 劑服盡,心悸已除,舌瘡面始收,繼服3 劑,舌瘡已痊。幾日后又因熬夜、起居失常而心悸復作,每于睡前及睡醒時分出現,清醒方止。又以此方2 劑治之,后不復作。
按語:此案患者素為陽虛之體,外感之后更傷其陽。舌咽生瘡,疼痛劇烈,心悸而脈疾,似為陽證,然舌質淡苔潤,為陽虛不能化津之象。舌為心之苗,相火上越,擾動君火,故使舌生瘡而心悸。火當溫下,而今上浮,不得暖土,陽不化津,故舌淡而苔水滑。此本為陽虛,而“火實”為標,火不歸原而燔灼上焦。以引火湯引火歸原、導龍入海則火自熄。此方于此案中本以治陽虛陰火證舌瘡,然此方對于特定時間段(睡眠前后)發生的心悸確有明顯療效。中醫學的睡眠理論早在《內經》中便有論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9],這一理論經過后世醫家的發展豐富,逐漸分化演變成為各種睡眠學說,如:營衛、陰陽、心神、魂魄等睡眠學說[10]。而后世醫家均以“陽不入陰”理論為不寐病癥的總病機。“陽不入陰”源于《內經》,是“衛氣不得入于陰”概括,根本上天人相應的具體體現之一,人體內陰陽二氣的運動變化與自然界陰陽二氣的運動變化相應,自然界的晝夜節律體現在人體即為人的寤寐周期。故在正常的生理狀態下,入睡之時當為陽始入陰,睡醒之時當為陽始出陰。清代汪文綺論述了陽虛不寐的病機為人體陽虛,虛陽浮越。他在《雜癥會心錄》中言:“陽浮于上,營衛不交,神明之地,擾亂不寧,萬慮紛紜,卻之不去。”“緣陽升而陰降……奈營弱衛強,出入之時,契合淺而脫離快”[11]正契合此時發生心悸的病機。這就不難理解這一時段心悸發生的病理特點為虛陽外浮,因此以引火湯治此種心悸當有特效。
4 小結
引火湯作為世傳良方,初為治療陰虛火旺“陰蛾”病所設,然后世醫家多有傳承發揮,用此方治療頭面五官的虛火諸證,常得良效。而此方所治病機當為陽虛陰火,且絕非僅限于頭面五官病癥。此方對于睡眠前后發生的心悸具有桴鼓之效。筆者認為在使用此方時,不必拘泥癥狀,應把握其陽虛陰火的病機,可更好的將此方運用于治療臨床雜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