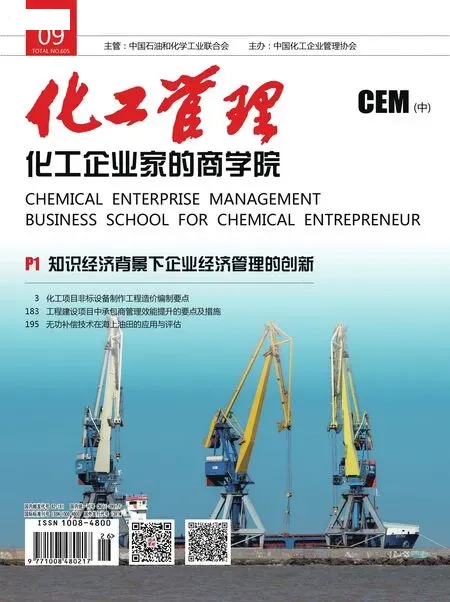世界農藥市場發展趨勢與中國農藥研發生產現狀
董志鵬(河北蘭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北 晉州 052260)
1 世界農藥市場的發展趨勢
綜合分析農藥發展趨勢可以發現,農藥曾經歷了以無機農藥為導向的發展期,以有機混合農藥為主的增長期及以安全、高活性,擁有特異性與選擇性的新型農藥時期。傳統的化學農藥對牲畜和人類的健康危害較大,如果使用不合理、不恰當,將導致農藥成分留存在食品當中,進而危害到人體的身體健康。而使用不科學,還會導致病害對農藥產生抗藥性,弱化農藥防治病害的功能和作用。此外由于農作物栽培方法、制度、品種及所在地區的氣候環境有所不同,導致農業的生產發展對農藥的研制與發展也提出了全新的標準與要求。現階段全球農藥市場逐漸走向穩定和成熟,市場增長幅度日益平緩,趨于飽和,年均增長率約為2%~3%。就銷售地區或區域而言,市場經濟較為發達的區域,農藥使用與銷售的規模較大,譬如東亞地區與北美地區的農藥市場銷售總額得到了明顯提升。但由于農藥市場的日漸飽和,世界各國的農藥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協同合作與強強聯合開始成為世界農藥市場現代化發展的基本趨勢。而根據太平洋證券研究院所整理的資料可以發現,2015年—2018年,世界農藥市場的增長率呈直線上升趨勢,增長速度較快。其中2018年的農藥市場規模達到575.61億美元,非農作物農藥的市場規模則達到73.1億美元。在農藥消費市場層面,全球農藥消費市場主要以巴西、美國、中國、日本、印度為主,約占消費市場的55%。而在未來五年,農藥消費增速較為快速的國家有阿根廷、巴西、西班牙、加拿大、墨西哥、中國等國家。在品種上,傳統的氟、砷等危害較大、毒性較高的殺蟲劑及滴滴涕等農藥已經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環境友好、低毒、高效的農藥。這類農藥能夠在降低施用量的基礎上,提高畝產產量,使農藥投用效率與產出成本得到有效地提升。而在新藥投用的過程中,新煙堿類、麥草畏、草甘磷等農藥逐漸被歐盟、美國、法國等國家禁用。總體來講,全球農藥市場對有毒、低效的農藥進行了持續的淘汰,并通過提高農藥研發與銷售標準,制定相關法案的方式,規范農藥市場的發展方向。譬如2019年歐盟通過正式禁止320多種含有化學物質的農藥在歐盟等地區銷售。而在農藥市場健康、快速的發展背景下,龍頭企業逐漸呈現出強強聯合、優勢互補的發展趨勢。世界各農藥企業和集團,通過重組與融合的方式,逐漸形成科迪化、巴斯夫、沙隆達及拜耳孟山都等農藥集團。再譬如2018年拜耳以630億美元成功收購孟山都公司,2019年陶氏杜邦宣布通過拆分成三家子公司的方式,從事特種產品、化學材料及農業研發等業務。中國化工集團(2021年重組,進入新組建的中國中化控股有限責任公司)收購安道麥和先正達后,全球原有競爭格局有望逐漸發生改變。
2 中國農藥的生產與研發現狀
我國農藥行業起步較晚,但已成為全球第一大農藥生產國,對外出口比例達到70%以上。2018年我國農藥原藥總產量約為209萬噸,同比下降16.7%,2019年農藥總產量為225萬噸,同比增長8.2%。其中農藥產量最高的地區主要有四川、江蘇等地。2019年我國江蘇的農藥總產量高達74.3萬噸。而根據植保部門及農業部門的數據調查,發現我國農業對農藥的需求總量為92萬噸,但殺螨劑、殺蟲劑的需求量卻持續下降,約占總農藥需求量的45%。究其原因在于:(1)我國對高殘留、高毒及菊酯類農藥的管理強度有所提升;(2)市場不景氣與農業市場的整體發展水平相對降低。(3)棉花種植業的萎縮與抗蟲棉范圍的擴大。而在殺菌劑和生物農藥的需求上,卻有所提升,其中生物農藥的需求量持續增加。其原因在于我國雜草群落的改變、耕作制度的變革及生態理念的發展,使無毒、高效的殺菌劑獲得更顯著的發展。而在我國農藥市場發展的層面上,我國法律法規日漸完善,法律所覆蓋的范圍也更加全面,對環保和安全的要求日漸嚴苛,從化肥零增長、農藥溯源系統、廢料安全處理及新藥管理條例上都得到了長遠的發展。并通過技術優勢、生產優勢、資本優勢、區域優勢、市場優勢等產業整合優勢,實現了行業洗牌與產業重組,使我國上市企業、中小型企業,國有企業與跨國企業形成緊密的內在聯系。而在國家產業重組的過程中,我國相關政府部門也提出資金支持及政策支持等,并通過優勢互補的方式,加大中印兩國在農藥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中國的殺蟲劑品種主要以氨基甲酸酯、有機磷及除蟲菊酯等類型為主,其中有機磷占市場總量的68%左右,含有六個品種,如:“氧化樂果”“久效磷”“甲胺磷” “對硫磷”等,產量約為24萬噸。而我國其他產量較高的農藥品種,還有氰戊菊酯、克百威、滅多威、殺蟲雙等、殺菌劑則以抗菌素、有機硫、雜環類為主,譬如井岡霉素、甲霜靈、百菌清、三唑酮、多菌靈等。除草劑則包括乙氧氟草醚、麥草畏、滅草喹、二氯喹啉酸。至于生長調節劑,具體有助壯素、多效唑、乙烯利等類型。2014年以來,我國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健康成長,極大推動了除草劑的發展。2015年除草劑產量則為145萬噸,2018年產量則高達170.2萬噸。其中應用于水田的除草劑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旱田除草劑的研發與應用速度卻相對緩慢。伴隨我國農藥產品質量與生產技術的不斷提升,應用于旱田的除草劑也得到了顯著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我國北方地區的農業生產水平。但整體來講,我國農藥產品的質量與技術得到了顯著的發展,譬如三唑酮的質量已經達到國際水平,進出口規模也得到了明顯的提升。譬如:2018年進口規模就達到127.09萬噸;2019年我國農藥出口規模已經達到203.33萬噸,總金額高達102.25億美元。在農藥研發技術引進與發展的層面上,我國農藥產業“引進海外技術”與“對外技術合作”的程度日益加深,譬如與拜耳、先正達、科迪化、安道麥等公司,都有合資或合作項目,且世界前十名的農藥研發企業,都與我國有所合作,如:上海中西與拜耳公司已建成克百威合作項目,預計年產1 000噸農藥;上海農資與日本三菱公司在精禾草克項目中的合作也取得了顯著的進展。雖然我國農藥產業獲得了全新的發展,卻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譬如品種老化、技術落后,科研助力薄弱等。首先是品種老化,我國農藥品種存在結構不合理,新品種不足及品種老化等嚴重問題。截至2018年底我國處于有效登記狀態的農藥產品41 514個,其中大田用農藥38 920個,衛生用農藥2 594個。大部分農藥主要以“殺蟲劑”為主,且占農藥市場的67%,而“殺菌劑”、“除草劑”的市場占比相對不足。因此可以說,我國在農藥品種上依舊存在明顯的不合理問題。其次是技術落后。西方國家的農藥生產逐漸向生物技術、自動化、精細化、高科技等方向發展,而我國當前的農藥生產技術依舊停留在間歇、單杠等層面,高度純化、高效催化及生物技術等技術,依舊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導致農藥生產與研發的成本高、物耗多。最后是科研助力問題。我國農藥產業雖然得到了較快的發展,然而卻沒有形成自主研發的體系,相關農研機構也沒有獲得“GLP”的認證。此外,我國在農藥項目的投資與科研經費的投入力度上相對薄弱,難以提高農研機構的研發效率和創制質量。而為應對我國農藥產業發展與產品研發中所面臨的問題,部分學者和專家提出了相對科學合理的建議。首先針對產品老化問題。楊潔等[1]文獻指出,我國相關政府部門制定出了相應的規章制度,調控農藥產品的結構,使農藥產品的結構日漸合理,如:降低殺菌劑、除草劑及殺蟲劑的比例,提高新品種產品的生產與研發比例等。而在新品種農藥研發的過程中,提高環境友好型農藥的研發比例,控制高毒及環境有害農藥產品的比重,能夠更好地優化我國農藥產品的結構。其次在研發技術上,李金金[2]則認為我國應在加大資金投入的前提下,將精力集中在定向立體、高度純化、高效催化及生物技術等層面上,注重綠色農藥技術的研發。與此同時,他也指出,我國的龍頭企業應肩負起技術研發的使命,努力將技術指標提高到國際水平。最后是科研。在科研層面上,相關政府部門應提高財政投入的力度,構建出符合國標標準的“安評”與“生測”中心,并以科研成果轉化為抓手,促進農研機構與農藥工業的市場化銜接。
3 結語
綜合當前世界農藥市場發展趨勢與我國研發生產等文獻資料,我們發現世界農藥產業正朝著綠色化、環境友好型的綠色農藥研發方向快速發展。我國雖在農藥市場的經濟浪潮中取得了突出成績。但在生產研發與市場化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諸多問題,嚴重影響到我國農藥產業的健康發展。對此,我們應結合農藥的市場發展趨勢,提高財政投入力度、制定相關法律法規,破解農藥研發生產問題,推動我國農藥市場健康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