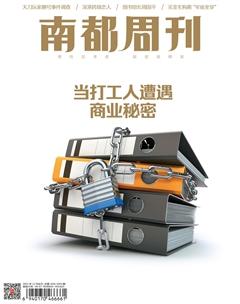被競業協議“逼瘋”的打工人
敖瑾
年底了,跳槽旺季來臨。但一紙競業限制協議,讓現單位成為了很多打工人無法說走就走的圍城。
因競業限制,張悅然對是否從某互聯網大廠辭職猶豫了很長一段時間,最終,她在10月份從運營崗位正式離職。HR對她啟動了競業限制,半年內,她每月可以領到原公司發放的競業補償金,數額是前一年總工資平攤到月之后的30%,但同時,她無法到協議所列的8家競品公司工作,若違反,她需要賠償24個月的薪酬作為違約金。
競業限制是勞動法中的重要內容,是對離職員工去向的一種限制,是企業保護商業秘密的重要手段之一。按照勞動法規定,競業限制只適用于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其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三類員工。然而現如今,很多企業為了管理方便,要求所有新入職員工簽署競業限制協議,已成為常規流程。這導致競業協議“濫簽”現象普遍,糾紛頻繁發生。
王珂就因競業限制協議和前公司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她不滿公司讓她簽署了競業限制協議卻不發放補償金,因而發起勞動仲裁。公司后來卻反訴王珂違反競業限制,要求賠償違約金50萬元。
非必要的競業限制,讓“打工人”陷入困惑。競業限制到底限什么?簽還是不簽?會給未來換工作帶來什么影響?可以要求原公司發放競業補償嗎?在社交平臺上,隨處可見職場人對競業協議的討論。
在通過勞動仲裁拿到前公司發的競業補償金后,王珂被前公司反告了,理由是她違反了競業限制。
王珂的前東家是北京一家主營網絡安全的公司,她此前擔任美工一職。入職時,她簽訂了競業限制協議。今年3月,她從該公司離職,在家待業近3個月,其間未收到公司發放的競業限制補償金。
向法律援助咨詢過相關事宜后,5月,王珂對原公司提起勞動仲裁,希望公司能遵守競業限制規則,補發她這段時間的競業限制補償金。
對此,原公司辯稱,在王珂離職時,公司已向她明確,公司不會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視同競業限制協議自動解除。8月時,公司還向王珂發去了一份關于競業限制的補充說明通知,稱“在離職時已告知對你沒有競業限制,公司不會支付補償款,則視同自動解除競業限制。且你的崗位僅為低端美工類職位,根本沒有競業限制必要。對此你都是明知的。”
讓非核心人員也簽競業限制協議,是目前大多數公司的普遍做法。因為人員流動性增加,為了避免有漏網之魚,全簽署是更方便,且看起來更加萬無一失的做法,但現實情況并非如此。
星漢云法務創始人曹立森律師發現,越來越多的公司前來咨詢與競業協議相關的問題,但很多公司并不太了解競業限制協議,“問的問題比較粗淺,普遍問的都是怎么簽、簽了怎么履行,一旦因為競業的問題對簿公堂,這其中涉及的問題就復雜、專業得多。”
僅競業是否啟動這個問題,就讓很多企業以及員工疑惑。這也是王珂和前東家之間的競業限制糾紛的起因——王珂覺得自己簽了協議,加上履行了限制義務,就應該拿到競業補償;公司卻認為雖然簽過了協議,但在離職時已經口頭告知解除,沒有發動限制也就不需要補償。
曹立森根據自己接觸過的公司估算,真正啟動競業限制的比例并不高,“按公司算的話,我接觸過的公司里,有5%曾經向簽署過競業限制協議的員工啟動過限制;但如果按單個公司對簽署過協議的員工啟動的數量算,還到不了5%,也就是說,公司讓100個員工都簽了競業限制協議,可能最后一個都沒啟動。”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企業沒有在協議中約定好啟動競業限制的細節,就容易產生糾紛。
11月,北京市海淀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做出了仲裁決定,對王珂的主張予以支持。根據王珂提供的裁決書,仲裁委認為,王珂的前公司雖主張已向王珂告知無需履行競業限制義務,但并未提交任何證據。在王珂不予認可的情況下,仲裁委對該公司的主張不予采信,而選擇采信王珂。此外,原公司未提交反證,反駁王珂履行了競業限制義務的主張,因此仲裁委采信王珂。
仲裁委最終裁決,前公司應支付王珂從今年3月19日到4月30日的競業限制補償金,共計2827.59元。
關于補償金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第三十六條就經濟補償標準作出了原則性規定,“當事人在勞動合同或者保密協議中約定了競業限制,但未約定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后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勞動者履行了競業限制義務,要求用人單位按照勞動者在勞動合同解除或者終止前十二個月平均工資的30%按月支付經濟補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前款規定的月平均工資的30%低于勞動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資標準的,按照勞動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資標準支付。”
曹立森介紹,競業限制是否啟動,主動權在企業手上,因為競業限制本身,就是為了保護公司利益而誕生,“但關鍵是你要做好約定”。
“如果你沒有相應的有效約定,就會發生這種情況:公司不發動競業限制,但沒有跟離職員工做好有效約定,離職員工轉行了,根據自己曾經簽訂競業限制協議,向原公司要求發放競業限制補償金,這種情況,法院或是仲裁部門會支持離職員工的訴求。”

公司享有啟動主動權,另一方面,員工也享有法定解除權。曹立森告訴記者,在司法實踐中,存在一個3個月的期限,即在競業限制啟動的情況下,公司應按時向離職員工發放競業補償金,最遲不超過3個月,一旦超過此期限,則員工有權向原公司提出解除競業限制。
但這個時間點中的交叉地帶,讓事情變得復雜。“公司超過3個月沒給補償,但如果員工在這3個月內到競品公司工作了,那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公司不付競業限制補償金了,直接起訴員工承擔違反競業限制的責任。”曹立森說。
這跟王珂在仲裁成功后的遭遇有相似之處。
在仲裁結果出來后,王珂接到了仲裁庭的電話,“公司向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要求我支付公司競業限制違約金50萬,理由是我違反了競業限制協議。”
待業幾個月后,王珂先后入職過兩家公司,“一家是普通業務公司,還有一家是物聯網公司。”王珂也無法準確判斷,它們和最早離職的那家公司,是不是競爭對手。“經營范圍有重合,都是技術開發、技術服務之類的,但它們屬于不同行業。”
王珂沒想到,自己通過仲裁主張發放競業補償金的做法,竟然為原公司反過來主張自己違反競業限制提供了便利。她拿不定主意,想放棄那筆不足3000元的補償金,甚至希望原公司的競業限制協議如其早前主張一樣,不曾啟動。
11月30日,王珂到北京市海淀區的勞動仲裁庭領取了原公司申請仲裁的材料。她對案件接下來的走向不甚了解,也不知道應該做哪些方面的準備。她把材料的部分內容拍了照,關鍵信息打了碼,發到了小紅書,并配文“太難了”。
在經歷這件事之前,王珂對競業限制不甚了解,她不知道存在相關的制度,對協議里的條款也不大關注,“只記得入職的時候,老板拿了一堆文件讓我簽字。”直到她從原公司離職后,在一次法律援助中聽說了競業限制補償金,她才想起自己曾簽過一個叫競業限制協議的東西。
王珂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前公司發起的仲裁。更重要的是,對她來說,無論最后結果如何,競業限制引起的一系列糾紛所花費的金錢和時間成本,都已經遠遠超過了前公司補發給她的競業限制補償金。王珂甚至后悔自己此前對公司提起了勞動仲裁。
曹立森這些年接觸了很多對競業限制有疑問的公司和個人,他發現,職場人最關心的點,并不在于補償金。“非常少人會問到賠償金相關的問題,他們大多更關心怎樣才能規避掉競業限制,順利找到新工作去上班。”
而到了真正對簿公堂,大多數跟競業限制有關的訴訟,都由企業發起,“10個案子中企業作為原告的有8個。”而這些企業的訴求,也并非重點關注違反賠償本身。
天元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郭世棧律師,代理了深圳一些由公司發起的競業限制相關訴訟。他告訴記者,競業限制相關的案件原告要勝訴的難度不小,因為存在取證難的問題,但企業仍然會選擇提告一些違反競業限制的員工,主要是出于警示的目的。
“如果沒有相應的法律后果,員工可能不會太把競業限制當一回事。”郭世棧觀察,一般來說,企業在做完一兩起競業限制案件后,員工至少會在兩三年內比較“消停”,不會有明顯的違反競業限制的行為出現。
曹立森認為,在競業限制這件事上,員工處于相對被動的狀態。
“大部分競業協議的簽訂都是按照企業要求去簽的,員工很少有議價的權利。我給很多企業做法律顧問,企業會對保密協議、競業協議提出各種需求,但我從沒聽說過哪個公司提到,員工要求針對各類協議哪些要調整。”
曹立森建議,一旦因為競業限制協議的問題員工和企業對簿公堂,在法庭對抗的過程中,員工可以審查規章制度的程序合法性。
“因為競業限制這塊,有的是單獨簽競業協議,有的則是公司通過規章制度里的條款來規范的。如果是單獨簽了競業限制協議,因為是員工本人簽的,這種很難再有議價的余地,但如果公司只是在員工手冊里有一章,要求員工有競業限制義務,這種情況建議員工去審查規章制度,看它的程序是不是合法。因為這類制度跟員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按照法律規定,這種制度應當履行相應的民主程序。”
民主程序,即公司擬定的規章制度草案,要先發征求意見稿征求員工的意見,接著,公司要聽取意見,可能需要與工會或員工代表溝通,之后再把定稿下發。“北京這邊的法院,目前,10個案子里可能有兩個法官會考慮,公司有沒有履行民主程序,如果沒有,就可能直接導致制度無效。如果說這個制度無效,那對于員工的競業要求也就自然無效了。”曹立森說。
離職至今已有兩個多月,張悅然仍在待業,還沒開始找工作,“限制和補償金的影響都有,但主要還是想先緩一緩。”
王珂則在最近告訴記者,她已和原公司達成和解,她刪掉了小紅書上一些關于她和原公司糾紛過程的帖子。“我放棄要補償金,對方放棄要違約金。”
(文中張悅然、王珂為化名)